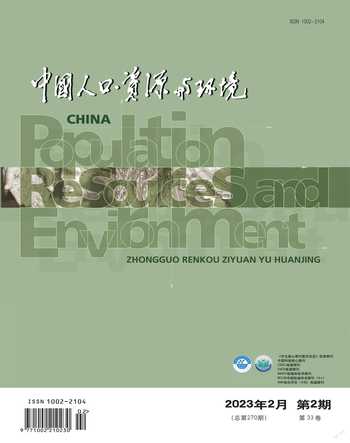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优势、机制与进路

摘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推动脱贫户从外力帮扶框架中提升自生发展能力,实现生计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从决胜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脱贫户”面临的生计资本和政策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脱贫户生计逐渐从以务农为主的“单一型”生计向以拥有抗风险冲击能力的“多元型”生计转型,从以解决温饱为核心的“生存型”生计向以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的“发展型”生计转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的,通过“财产联合”或“劳动联合”实现“再合作”的经济形态,能够把包含脱贫户在内的广大农户组织起来对接“大国家”和“大市场”。通过构建“赋权-增能-包容”的分析框架,识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理论机制,即通过赋予脱贫户更充分的农地产权、自由择业权和市场参与权,将国家资源和政策内化为可量化、可折算的经济利益,走出“集体产权模糊论”的困局,让脱贫户能够公平分享集体经济收益;通过在赋权中增能,有效拓展了脱贫户的发展机会和生计空间,提升了脱贫户生计转型能力;加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包容性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赋予脱贫户机会更加公平、参与权更加保障的制度环境,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为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扶贫时代,只有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领导、宣传示范、制度供给、要素投入、生产经营、动力培育、联合管理等“七大”体系,才能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好地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把脱贫户完整纳入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脱贫户;生计转型
中图分类号 F321;F3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3)02-0143-10 DOI:10. 12062/cpre. 20221008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中国在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在于推动脱贫户从外力帮扶框架中提升自生发展能力[1],实现脱贫户生计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从“单一型”向“多元型”的双重转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政府组织产业扶贫、产业振兴的重要载体,也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生性力量[2]。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制定实施贫困地区集体经济薄弱村发展提升计划,通过盘活集体资产、入股或参股、量化资产收益等渠道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同样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也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产权权能,将经营性资产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实践维度看,贵州塘约村“再集体化”[3]、山东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4]等集体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虽然已被部分村域的发展所证实,然而在全国来看尚未形成良好的发展格局。因此,在学理上理清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内在机理,在实践上阐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具体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文献综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的具体实践形态,其发展遵循了马克思主义集体所有制下“合作生产”的理论思想,是消除绝对贫困和推动脱__贫户生计转型的强大动力,也是脱贫户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5]。因此,关于脱贫户生计转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及其功能的相关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1. 1 关于脱贫户生计及其转型研究
生计作为“一种生活的手段或方式”,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贫困治理领域[6],“解决贫困人口生计”被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时开始关注生计问题[7]。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能力贫困理论把贫困定义为社会生存、适应及发展能力的低下,因而实现贫困户的可持续稳固脱贫,就应该提高贫困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能力亦被称为可行能力,构成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核心范畴[8]。根据这一框架,农户会根据自然环境与社会政策、家庭生计资本的变化对生计进行调整,表现为重新组合生计资本或者重新选择生计活动[9-10]。因此,贫困户生计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而且总是根据生计资本、生态环境、社会政策的变化处于不断的调适过程之中,这种调适和转变的过程就是贫困户生计转型的过程[11]。在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脱贫户面临的生计五边形(物质、人力、自然、社会、金融)空间向外扩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脱贫户自生发展能力稳步提高[12]。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以促进包括脱贫户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的生计转型为根本导向,即推动脱贫户从外力帮扶框架中提升自生发展能力,实现生计向“发展型”和“多元型”转型[13-14]。
1. 2 關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及其功能研究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15],是无产阶级彻底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16]。遵循这一理论思想,农村集体经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的立基之石[17],早在1931年就提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18],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历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发展探索,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框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逐步形成“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探索出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走向新型集体经济的道路,但这并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再合作”,不仅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实现了“党的领导、共同富裕、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机融合,破解了农户“动力”与“能力”的矛盾和农村经营“统”“分”困局,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契合性。加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内生于乡村社会“公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具有合作传统、组织基础和治理优势[21],能够把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广大农户组织起来,让脱贫户有能力参与市场活动和对接国家资源,并将其内化为自我发展能力,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22]。
综上所述,在全面摆脱绝对贫困之后,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应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框架,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23]。有别于已有文献,该研究回归后脱贫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一现实问题,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把脱贫户组织起来对接“大国家”和“大市场”的优势出发,构建“赋权-增能-包容”的分析框架识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内在机制,并在实践上阐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具体进路,以期为更好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提供镜鉴参考。
2 后脱贫时代脱贫户生计转型的特征事实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贫困户的生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扶贫政策框架的变化而变化,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标志着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推动减贫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新阶段,导致“精准脱贫户”的面临的生计资本和政策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脱贫户生计逐渐向“多元型”生计和“发展型”生计转型。
2. 1 从“单一型”生计向“多元型”生计转型
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第一就业空间,1949年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围绕农户的贫困问题,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全国无地或少地的3亿农民共分得约7亿亩(1亩≈666. 7 m2,以下同)土地[24],1958年1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广大农户被限制在土地上,绝大多数贫困户生计是以务农为主的“单一型”生计。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规模庞大的民工潮的逐渐兴起,非农产业逐渐成为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广大农户的第二就业和增收空间,贫困户生计也逐渐从传统纯农业生产型向农业生产为主型、非农活动为主型转变[25]。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脱贫户面临的生计资本和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村产业振兴和三产融合步伐不断加快,依托农业景观、乡村文化和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乡村__旅游、休闲农业等已成为主流趋势,脱贫户生计从以务农为主的“单一型”生计向以拥有抗风险冲击能力的“多元型”生计转型也成为必然趋势。
2. 2 从“生存型”生计向“发展型”生计转型
贫困户在不同阶段面对的现实需求是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吃不饱饭、经济低效、发展缓慢的实际,贫困户生计以解决温饱、维持基本生存为主要目标,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贫困户生计也开始摆脱以解决温饱为核心的“生存型”生计,持续三十年的“1978年贫困线标准”是按1978年价格每人100元为贫困线确定低水平的温饱型贫困标准,直到2008年以2000年价格每人865元为贫困线确定基本满足温饱的贫困标准[26]。党的十八大以来,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有脱贫户完整达到了“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极大拓展了生计资本边界,其中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脱贫户住房安全拓展了物质资本的边界条件,教育扶贫提升了脱贫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并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两山论”的实践和生态扶贫拓展了脱贫户的财富边界,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改变了脱贫户面临的社会环境,普惠金融的发展拓展了脱贫户的信贷可及性。因此,后脱贫时代脱贫户面临的是容易返贫的脆弱性问题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问题,生计也由以解决温饱的“生存型”生计向以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的“发展型”生计转型。
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新优势
脱贫户是通过打赢脱贫攻坚战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超过了当地农民的贫困线识别标准,实现“精准退出”的原贫困户,但如何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必须完整地解决好“扶上马送一程”中“送一程”的问题,推动脱贫户提升自生发展能力,实现生计转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的,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导向,集体成员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27],能够通过“再合作”的发展包容性把脱贫户组织起来对接“大国家”和“大市场”,对接“大国家”能够实现国家资源和政策的精准对接,并将其内化为自生发展能力;对接“大市场”能够提升脱贫户市场参与能力和水平,形成可持续生计。因此,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的重要经验,而且在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具有独到优势。
3. 1 组织脱贫户对接“大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依托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等把广大农户组织起来,不仅巩固了党和国家在农村工作的基础,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国家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改善了农户的生产经营条件。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农业生产重新回到小农户的组织形式,但没能很好地解决农业生产“统”的问题,农村经营陷入“统”“分”困局[28]。在贫困地区,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民自治组织有名无实,所谓的集体经济组织早已名存实亡。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推动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并未实现与小农户的有机融合,大量分散的脱贫户不仅无法表达自己的实际需求,也无力融入政府组织的大项目,難以对接“大国家”[29]。加之绝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被大户和精英控制,成为套取国家补贴的假合作组织,导致分散的脱贫户难以对接国家巨大的扶贫资源,而且扶贫资源配置的“精英俘获”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分化[30]。
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依托自身的组织基础和治理优势,把分散的脱贫户和一般农户组织起来,把分裂的农村社会重新整合起来,以合作与联合再造村社共同体对接国家资源和政策,实现组织再造基础上的赋权增能,可以有效解决“大国家”与“小脱贫户”之间交易成本过高和资源供需不匹配的问题,提高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的利用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从2013年的381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 465亿元,累计达6 600亿元,而且同期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高达15 980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提供了基础性支撑,但也导致农村形成巨大的扶贫资金资产存量,加之“脱贫不脱钩、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的政策要求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推进,国家将继续向农村转移大量资源。以陕西临潼区为例,2021年全区投入各级财政衔接资金5 715万元,采取“龙头企业+集体经济+产业+脱贫户”的模式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19个脱贫村年经济收入全部超过5万9_↘9_魗元,带动脱贫户5 395户。可见,在后脱贫时代用好这些资源的关键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强有力的组织带动作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把广大脱贫户组织起来对接国家资源和政策,并将其内化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实现脱贫户生计转型,更好地“送一程”。
3. 2 组织脱贫户对接“大市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农户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31],在生产方式选择上,“小农生产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32],这就决定了小农生产与先进的生产力无法相融,也直接导致农户陷入贫困。因此,传统小农生产的未来出路在于合作化,即在尊重小农意志的前提下,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方式改造传统小农。然而在脱贫攻坚之初,中国大多数贫困村的集体经济陷入空壳化,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经过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署和努力,2020年全国贫困村的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2万元,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极大地增强了村级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在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后,实现脱贫户生计转型应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框架,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和“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包容性和组织动员能力,通过“劳动联合”或“财产联合”把脱贫户完整纳入集体经济的发展轨道,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和机械化水平,这不仅符合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实现了组织脱贫户对接“大市场”的要求,使得脱贫户在市场中的生存力和竞争力有效提升。另外,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为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和激活乡村沉睡资源提供物质保障,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居委会)能够为脱贫户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好的服务,进一步激发了脱贫户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为提高村集体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创造了优势条件。在曾深度贫困的新疆沙雅县,通过土地整理增厚集体经济“家底”,2020年19个村、6 253户拿到分红收入200. 51万元,其中奥图拉库勒达西村通过土地平整新增3 500亩耕地,集体经济“家底”在230万元以上,除改善居住生活环境等,还用到支持发展果树、蔬菜、花卉等高附加值农业经营中,带动脱贫户增收。可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能够组织脱贫户进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对接“大市场”,提升脱贫户参与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并将其内化为自我发展能力,赋能生计转型。
4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内在机制
新型農村集体经济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财产联合或者劳动联合,实现“再合作”的经济形态,能够把脱贫户组织起来对接“大国家”和“大市场”,并嵌入科学适宜的自生发展能力培育机制,形成“赋权-增能-包容”的治贫框架,这不仅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经验,也是后脱贫时代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选择[33]。因此,从“赋权-增能-包容”的分析框架(图1)出发,识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内在机制,对于更好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意义重大。
4. 1 赋权:分享收益扶持脱贫户
传统的贫困理论谱系把贫困问题单纯地理解为经济问题,强调收入平等对贫困治理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__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4]。无产阶级作为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却被剥夺了物质产品的占有支配权,所有的产品都归资本家占有和支配,这样“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34],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衍生权利的缺失。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一书中明确指出贫困、饥饿及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权力的丧失和剥夺”,即经济衰退和物质匮乏并不构成贫困产生的全部原因,在“食物生产富足”的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存在因权利分配不均而引发的严重“饥荒”问题。因此,贫困治理必须赋予并保护贫困群体的权利,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权利的合理分配。比如,湖北省京山市城畈村作为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村,2016年开始推动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造,综合评估发现集体经营性资产达到1. 57亿元,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 815 名,通过以户籍人口设置基本股、以家庭劳动耕种年限时长设置劳龄股,进一步考虑到集体经济发展、脱贫户等特殊人群的利益诉求,增设集体股、特殊股和贡献股,配置股份49 116. 5股,保障脱贫户能够从集体经营性资产收入中分得红利[35]。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全面小康时代,脱贫户对以土地为载体的集体资产的功能诉求已不再局限于保障生存,而是希望获得更多的发展权益,实现了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历史性转变,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必须保障脱贫户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赋予脱贫户更多的财产权利,构建“多元赋权”的改革方案。首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集体”属性的核心在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科学确定集体成员身份,明晰农村集体资产归属,赋予脱贫户等集体成员更加充分的农地产权。其次,脱贫户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下通过“共同生产、统一经营”实现“劳动联合”,通过土地、资产、技术等入股实现“财产联合”,不仅赋予脱贫户更加自由的择业权和更加充分的市场参与权,而且理顺了集体和个体的物质利益关系,形成了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第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把分散的脱贫户组织起来对接国家向农村巨大的资源投入,并通过集体成员权将其分解和量化,确认产权身份,为脱贫户分享收益和参与市场创造条件。因此,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赋予脱贫户更充分的农地产权、自由择业权和市场参与权,而且这些权利已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化为可量化、可折算的经济利益,走出了“集体产权模糊论”的发展困局,建立了脱贫户和集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脱贫户有了稳定可持续的增收渠道,生计也向“发展型”转化。
4. 2 增能:提升能力发展脱贫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无产阶级消除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剥夺剥夺者”,对于农业工人而言,“只有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的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转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業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种,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36],表明作为无产阶级之一的农户要彻底摆脱贫困,不仅需要“社会财产”的赋权,也需要“劳动联合”,其中蕴含着“提升能力”的减贫思想。同样,阿玛蒂亚·森赋权反贫困思想的实质就是“赋予权力、使有能力”,舒尔茨进一步提出“能力贫困”假说,即农村贫困主要源于农户人力资本匮乏、健康状况低下、自由流动受阻等可行能力的剥夺,因此,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不仅要引入农业机械、优良种子、化肥等“物”的要素,还需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培养具有接受能力、能够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而且“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37]。可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必须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脱贫户自生发展能力。比如,陕西汉中南郑区福成镇坚持党建引领,围绕“村村有集体积累,户户有产业覆盖,家家有增收渠道”目标确定村集体优势主导产业,推行“党支部+合作社+脱贫户+农户”等合作模式,实现所有脱贫户利益联结全覆盖,脱贫群众累计分红收益300万元以上,脱贫户稳定增收成果得到不断巩固拓展。
在赋权中增能,向贫困户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减贫实践的核心线索[38]。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资金、物质、人力等资源要素向农村大量集聚和叠加,短时间内支撑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发展目标,但是重外力帮扶、轻内力提升的治理偏向导致脱贫户自生发展能力缺失,这就需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阶段强化内生发展激励,提升脱贫户的生产技术能力、经营能力、合作能力[39]。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多元赋权盘活了农村集体资产,通过优化配置内部生产性资源,不仅强化了脱贫户对各类产权的实施能力和市场参与能力,而且有效改善了脱贫户生计资本质量和生计转型能力。另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集体组织”支持的脱贫户技能培训、教育普及大大提升了脱贫户的人力资本水平,拓展了脱贫户的生计转型能力和生计空间。根据2021年4月25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自2016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__开展试点以来,核清农村集体资产65 000亿元,集体土地等资源65. 5亿亩,确认集体成员9亿人,全国共有53万个村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导致脱贫户不再依附于土地以农为生,从事“单一型”农业生产经营的脱贫户占比逐年下降,来自非农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可见,农村集体经济通过给脱贫户赋权,有效拓展了脱贫户的发展机会和生计空间,提升了脱贫户生计转型能力。
4. 3 包容:机会均等富裕脱贫户
传统减贫的“涓滴理论”认为贫困人口的收入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政府不需要针对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只需实现经济增长就能缓解贫困[40]。但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及资本与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异质性,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不仅难以解决贫困问题,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经济财富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向贫困人口“涓滴”,而且导致贫困状况更加恶化。为了更好地解决贫困问题,学术理论界开始寻找新的减贫理论,Chenery等[41]提出的增长再分配模型,强调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目标一体化,成为“亲贫式增长”或“益贫式增长” 的理论溯源,2000年世界银行提出“益贫式增长”,强调社会利益均等化。考虑到“益贫式增长”只侧重度量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的局限,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包容性增长”,旨在通过消除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均等,这是治理包括收入、健康、教育、社保等多维度贫困问题的前提和基础[42]。“包容性发展”作为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贫困治理理念,把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边界进一步拓展,更加强调公平、全面和共享,在贫困治理中突出机会平等和参与公平,从而实现成果共享,这一理念也始终贯穿于中国贫困治理的伟大实践之中[43]。例如安徽长丰县吴山镇立足本地特色实施集体资产收益项目,发展各类设施大棚种植产业,探索出集生产、销售和技术“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解决了脱贫户、监测户的就近就业问题,而且以“老弱病残”无劳动能力为参考依据,开发公益性岗位,实行不同档次的分红,带动脱贫户稳定增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包容性不仅实现了“物的联合”,而且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人的联合”,在解决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的衔接过渡期,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实现脱贫户生计转型存在内在一致性。首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包容性在党的领导下能够牢牢掌握利益分配的主动权,不仅能够对接国家和社会注入的巨大资源,而且能够把土地和产业增值收益留在集体和脱贫户手中,脱贫户可以根据集体成员资格享受股金和返利。其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包容性在组织方式上可通过土地置换、集体赠股、设置公益岗等方式,把脱贫户完整纳入集体经济的发展轨道,让脱贫户能够公平分享集体经济发展红利,拓宽增收渠道,实现生计转型。再次,脱贫户“组织起来”能够大大降低社会治理、养老、养小的成本,而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包容性能够改善农村医疗救助、生活救济、互助养老、教育补助等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和服务水平。最后,后脱贫时代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需更加关注体面生活和精神富足,将“包容”的维度进一步拓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包容性能够赋予脱贫户机会更加公平、参与权更加保障的制度环境,保障脱贫户更多选择机会和获得幸福的权利,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
5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实践进路
后脱贫时代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把脱贫户组织起来对接“大国家”和“大市场”,通过“赋予权力、提升能力、包容性参与”赋能脱贫户生计向“多元型”生计和“发展型”生计转型。然而现阶段全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尚未形成良好的发展格局,只有约40%的行政村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超过70%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5万元[4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归大堆”的方式强制推广,正如马克思强调的那样“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31]。因此,只有顺应脱贫户对美好生活的新企盼,理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逻辑关系,打通“堵点”,补齐“断点”,才能更好地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把脱贫户完整纳入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5. 1 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领导体系,保障“组织”赋能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成就充分证明“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组织在农村领导核心地位的弱化和集体经济的空壳化,是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和农户陷入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时代新征程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堅成果、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领导体系,把脱贫户组织起来更好地对接国家资源投入和参与市场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首先,党能够统领一切、协调各方,发挥好村党组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党组织(村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实现党的领导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确保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姓公不姓私”,__最大限度地维护脱贫户的利益。其次,选准配强党组织(村党支部)领导班子,通过“稳”“培”“引”选择头脑活、懂经营、会管理、责任心强的优秀人才进入村“两委”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班子,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综合能力和领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能力,走“能人”带动脱贫户转型发展的路子。最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任务,赋予脱贫户更加充分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脱贫户走向共同富裕的坚强战斗堡垒。
5. 2 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宣传示范体系,强化“认知”赋能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旨在通过互助合作,把不同农户组织起来集体发展经济,不是发展集体经济[45]。新时代新征程中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是“一大二公”,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入社自由、权责清晰、利益共享的原则,在“确权”基础上通过合作与联合将脱贫户和一般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组织,这与人们理解的传统集体经济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后脱贫时代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必须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宣传示范体系,推动思想观念上的“赋能”。首先,从理论上讲清楚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党的领导下建立在“确权”基础上的集体经济组织,能够真正赋予脱贫户权利、提升脱贫户能力,让老弱病残也都能有保障,是引领脱贫户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其次,通过对相关领导干部和村“两委”领导班子组织集体培训、网络培训强化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宣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数字网络及新媒体宣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意义、优惠政策、组织方式、先进典型,提高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知晓度。最后,用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发展成功案例,强化“示范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涌现出一批“典型案例”,如贵州塘约村的“再集体化”、山东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要进一步放大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效应,让脱贫户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激发脱贫户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5. 3 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供给体系,实现“政策”赋权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从实践上来看全国已有约40%的行政村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而且在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方面有很多成功探索;从政策支持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中均明确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特的法人地位和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但也应该看到当前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不足和政策资源碎片化问题,因此,为更好地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必须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供给体系,凝聚政策支持合力。首先,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章制度,明确政府、村“两委”及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边界和成员权利,强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在政策上讲清楚脱贫户分享集体经济红利的权属条件。其次,发挥财政金融的政策引领作用,撬动整合各类涉农资金,设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探索建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化资金投入体系。最后,把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纳入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特色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政策有机衔接起来,探索建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支持体系。
5. 4 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要素投入体系,实现“资源”赋权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立基之石,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将脱贫户和一般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不断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要素投入体系,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资源使用的内外结合、共同赋权。首先,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和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把明晰产权作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起点,持续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赋予脱贫户更加充分的财产权,明确的权属关系将激发脱贫户推动生计转型的内生动力。其次,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动员优势,能够在更大范围激活乡村沉睡资源,整合脱贫户小而散的资源,优化村域内资源配置,改善土地、水利、交通等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延长农业产业链,为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注入更多动力。再次,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接“大国家”的优势,国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向农村投入的资源存量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进一步注入的资源增量,只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对接和用好这些资源,并将其内化为脱贫户生计转型的内生动力。最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既要用好资本,也要约束资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以规范有序和互利共赢方式引入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才能既容纳资本进入农村,给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同时利用党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领导优势维护脱贫户的利益。
5. 5 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体系,实现“模式”增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许多贫困村新型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2022年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丰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有效实现形式”,为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体系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条件。因此,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效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应该充分用好政策机遇,秉持“因地制宜、因村制宜”的发展原则,依托村域产业特色和禀赋优势把脱贫户组织起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体来看,在集体经济初始禀赋好、有产业优势的村域应围绕农业现代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组织化联结、专业化生产、市场化运营的产业主导型集体经济,把脱贫户纳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没有集体资产、发展产业难度大的村域应鼓励多种运作方式,通过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投资入股龙头企业,吸引外出务工经商能人带资金、带项目回乡创业,引导脱贫户利用土地、劳动等入股,发展入股分红型集体经济;有文化资源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的村域应该在党组织(村支部)的领导下围绕乡村全域旅游、农业生产经营把脱贫户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服务型集体经济。另外,必须用好政府资源进村、乡村全面振兴等政策机遇,进一步完善农村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体系,更好地提升脱贫户自生发展能力创造良好的“硬”环境。
5. 6 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动力培育体系,实现“市场”增能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把脱贫户和一般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对接“大市场”,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承认脱贫户等个体与集体权属关系基础上面向市场的“合作生产”,提升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脱贫户个体的市场参与能力,对形成推动脱贫户生计转型的市场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体系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赋予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完整的市场交易权,明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权属关系和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法人资格的规定要求,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办法,在“政经分开”“折股量化”的制度框架下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治理模式,建立村“两委”领导班子和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班子“双向进入”机制,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参与能力和水平。最后,把脱贫户组织起来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改善了单个脱贫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提升了脱贫户在农业生产资料獲取、农产品销售及务工工资等方面的议价能力,为实现脱贫户生计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5. 7 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联合管理体系,实现“利益”包容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劳动联合”和“财产联合”把脱贫户组织起来,以差异化的“确权”实现了脱贫户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联结,赋予脱贫户等集体成员以收益权为核心的各种财产权利,走出了集体经济产权虚化和集体收益“精英俘获”的困局,增强了脱贫户与一般农户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利益关联。首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确权”,将集体成员权以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具体化,明确了集体成员的资格身份,形成了一套集体和个体产权互认、共融的联合管理体系,使之真正实现可流动、可增值,以此维护脱贫户的利益,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其次,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尽可能把脱贫户完整纳入集体经济发展轨道,通过优化股权比例设置、集体收益分红等方式确定集体成员的持股份额,开发公益性岗位,建立起一套倾向于保障脱贫户利益的产权执行体系,防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被大户控制或者垄断,警惕“精英俘获”现象的出现。最后,优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在普通个体、管理干部及村集体的分配机制,脱贫户等普通个体获得“工资+分红”、管理干部获得“工资+绩效奖金”、村集体获得“企业上缴经营收益+土地等集体股权收益”,另外,村集体的集体收益将用于改善村域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以此支撑脱贫户生计转型,不断满足脱贫户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1] 王建洪,李伶俐,夏诗涵,等. 制度性合作机制下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与脱贫政策效应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5):68-76,192.
[2] 丁忠兵.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同扶贫模式创新:重庆例证[J]. 改革,2020(5):150-159.
[3] 张慧鹏. 集体经济与精准扶贫:兼论塘约道路的启示[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6):63-71.
[4] 陈义媛.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以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J]. 求实,2020(6):68-81,109.
[5]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193.
[6] CHAMBERS R,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R].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2.
[7]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livelihoodsguidance sheets[R]. 1999: 68-125.
[8] 李明月,陈凯. 精准扶贫对提升农户生计的效果评价[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1):10-20.
[9] TSVEGEMED M,SHABIER A,SCHLECHT E,et al. Evolution ofrur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a remote Sino?Mongolian border area:across?country analysis[J]. Sustainability,2018,10(4):1011.
[10] 孙晗霖,刘新智,张鹏瑶. 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及其动态风险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2):145-155.
[11] 王娟,吴海涛,丁士军.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滇西南为例[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5):133-140.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N]. 人民日报,2021-04-07(9).
[13] 汪三贵,胡骏. 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J]. 农业经济问题,2020(2):4-14.
[14] 陆远权,刘姜. 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扶贫政策效应研究[J]. 软科学,2020,34(2):50-58.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3.
[1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2.
[17] 耿羽. 壮大集体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习近平关于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研究[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2):14-19,107.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64.
[19] 高鸣,芦千文.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70年发展历程与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19(10):19-39.
[20] 张弛. 中国特色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基础、新特征及发展策略[J]. 经济纵横,2020(12):44-53.
[21] 孔祥智. 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形态转换与发展方向[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12(4):83-108.
[22] 徐凤增,袭威,徐月华. 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21,37(12):134-151,196,152.
[23] 崔超.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2):89-98.
[24] 王小林. 新中国成立70年减贫经验及其对2020年后缓解相对贫困的价值[J]. 劳动经济研究,2019,7(6):3-10.
[25] 杨伦,刘某承,闵庆文,等.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J]. 生态学报,2019,39(21):8172-8182.
[26] 鲜祖德,王萍萍,吴伟.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J]. 统计研究,2016,33(9):3-12.
[2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6-12-30(1).
[28] 李天姿,王宏波.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现实旨趣、核心特征与实践模式[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2):166-171.
[29] 贺雪峰. 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72(4):185-192.
[30] 邢成举,李小云. 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13(9):109-113.
[3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8,70.
[3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8.
[33] 罗必良,洪炜杰,耿鹏鹏,等. 赋权、强能、包容: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2021,37(10):166-181,182.
[3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1,49.
[35] 杨磊,王俞霏. 多元赋权: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划分的逻辑与制度功能[J]. 北京社会科学,2020(4):105-116.
[3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1.
[37]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35.
[38] 邓金钱. 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的历史方位与理论贡献[J]. 上海经济研究,2022,34(7):50-59.
[39] 郭晓鸣,王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相对贫困:特征、优势与作用机制[J]. 社会科学战线,2020(12):67-73.
[40] DOLLAR D, KRAAY A .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 Journalof economic growth, 2001, 7(3):195-225.
[41] CHENERY H B , AHLUWALIA M S , BELL C , et al. Redistributionwith growth[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42] 黎藺娴,边恕.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包容性增长的识别与分解[J]. 经济研究,2021,56(2):54-70.
[43] 黄承伟,徐丽萍. 中国包容性增长与减贫:进程与主要政策[J]. 学习与实践,2012(7):67-75,2.
[44] 解学智. 加大金融对村集体经济的支持力度[J]. 中国银行业,2020(6):34.
[45] 黄延信.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亟需更新观念[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21(4):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