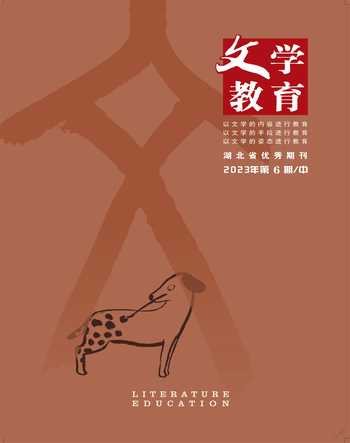日本能乐与“幽玄”观演变
赵昕
内容摘要:能和狂言是日本传统的古典戏剧代表,二者合并起来称为能乐。在其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经过反复凝练、升华为极具“幽玄”性质的独特曲艺。“幽玄”作为日本文艺理论和传统美学的范畴之一,往往被阐释为“微暗、朦胧、神秘、难以知晓的微妙境界”等,是富含日本民族特色的美学代表。能乐与“幽玄”观的演变相互糅合,交错发展,将演出和理论结合,不仅形成了辉煌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于现代音乐、文学等领域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能乐 幽玄 日本美学
日本的能与狂言、文乐、歌舞伎并称为日本四大古典戏剧。能作为一种传统的日本艺术表演,和狂言一同发源于日本南北朝时代,合起来统称为能乐,经历多次变迁和革新延续到现在,可谓世界上拥有最长的戏剧生命和历史传统的舞台艺术,在2001年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乐有独特样式的能舞台,像世阿弥所言“舞歌二道”一样,是融合了用精妙的演技抽象化的舞蹈要素和歌谣、伴奏等音乐要素的戏剧。而自世阿弥即能乐大家世阿弥元清著《风姿花传》以来,能乐作为一种特殊的舞台演剧其艺术性首次被详细整理论述,世阿弥指出能乐的本质即模仿、花和幽玄,能乐即是与之修行的过程。中世,能乐在足利氏将军的幕府庇护下逐渐发展壮大,盛极一时。但无论是中世祭祀春日神社的大和四座流派还是后来江户的新兴喜多派,伴随着他们的“幽玄”能乐美学理论却一同演变至今。
早在奈良时代,我国唐朝的唐乐随着大量汉文化的输入也登入了日本贵族的雅堂。唐乐中,与雅乐相对应的俗乐称为“散乐”,主要是以曲艺、杂技、魔术、歌舞等为主的各式各样的表演艺术。到了平安时代,散乐中滑稽而令人捧腹的模仿艺术渐渐成为主流并在庶民之间流行起来,被称为“猿乐”。与之相对,在农村农民们在田地耕作时,有表演农耕祭祀和礼法的“田乐”。这两者不久间也在贵族阶级之间流行起来,特别在室町时代受到了幕府将军和武士的喜爱。后来,“猿乐”和“田乐”被加入了歌舞伴奏和角色对话,成为一种对话剧并被称为“猿乐能”和“田乐能”,也就是今天所谓能乐的起源。中世,因佛教广泛传播,经常伴随着大寺院法会和神社祭礼的艺术表演逐渐兴盛,尤其在镰仓时代末期,这些宗教艺术表演者自发结成“座”这样的集团,从属于有权势的大寺院,比如当时最有名的“大和猿乐”和“近江猿乐”两座。
“猿乐”的表演者担当的表演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寺院的法会上上演念咒,一是扮作老翁的样子演示神的祝福,也是现在被视为神圣的属其他系列演剧《翁》的原型。到了南北朝时期,“大和猿乐”和“近江猿乐”已发展至多种支流派系。其中“大和猿乐”包括隶属于奈良兴福寺的圆满座、阪户座、外山座、结崎座这四座,侍奉于春日神社,也就是今天的金春、金刚、宝生、观世流派的起源。再到了江户时代,能作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成为了幕府官署正式的式乐,表演更加凝练考究,曲目数量达到二百四十曲之多。能每日正式的表演从形式和内容上一般分为叫“五番立て”的五种类型,也就是神事物、修罗物、蔓物、现在物、鬼畜物这五种依次表演的顺序[1]。此外,除了大和四座之外,还形成了新的喜多流,这“四座一流”统归江户幕府管辖,一直延续至今。
创立了能乐这一完全崭新类别的戏剧的是曾组织过结崎座的观阿弥清次和世阿弥元清父子二人。观阿弥对能的功绩在于对以模仿为本位、主张猛烈风格的大和猿乐中,改编加入田乐和近江猿乐等歌舞的要素和把幽玄之美放到中心位置,另外还要把节奏本位的曲舞的技法导入到以旋律为主的大和猿乐当中,写出吸引大众的活泼生动的能本。世阿弥吸收了近江猿乐的名人犬王道阿弥的唯美主义,在大和猿乐戏剧性本位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幽玄的情趣为中心的诗剧类能及其理论。在世阿弥的能乐论中,主张与强硬猛烈的表现相反,变现优雅、柔和、典丽的美。不仅有存在于美女、美少女等具备自然的幽玄,甚至有具备卑贱的人物、鬼等演出来的高深的幽玄[2]。要理解世阿弥的幽玄美,则必须了解幽玄这一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幽玄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后汉时期,记载在《后汉书·何后妃》中汉少帝的《悲歌》中:“逝将去汝兮适幽玄。”[3]而在隋朝汉译佛典《金刚般若经疏》中,智顗将这个词解说为“微妙难测”,唐朝的法藏在《华严经》中解说为“甚深”[4]。无论哪种解释都意为佛法深远,不易理解。幽玄一词传入日本后有所改变,在平安末期已经不只限于佛典使用,但也几乎不离原意。此后幽玄大都醒目地出现在歌论的场合,被赋予了新的不同的含义。纪贯之在《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把幽玄用在日本的诗歌评论中,“或事关神异,或兴入幽玄”,由此把“幽玄”引入文艺批评,随着日本和歌的创作渐趋成熟,和歌也明显表现出轻言辞而重意境的“幽玄”诗趣。
日本的和歌名人藤原俊成认为日本当代歌人应该把自己置于歌学的传统之中,而和歌的这种传统犹如佛门《天台摩珂止观》的金口相承,万古不易。今人应该了解和歌的历史,尤其应该了解和歌的“姿、词”的变迁,了解在其变迁中保持永恒不易的普遍意义上的美的诸相。歌人只有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牢固地确立发现这种普遍美的主体性才能创作出“风体幽玄”的上乘之作。我国学者高文汉认为:“俊成倡导的‘幽玄已与壬生忠岑等中古歌人之说有所不同,他努力使和歌的传统美进一步内潜、深化,旨在寻求一种深邃、静寂的氛围和意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韵味清幽、余味绵长的复合性情调美。同时他强调和歌的声调视其为和歌的生命。”[5]在《古来风体抄》中,他说:“凡歌者,颂于口咏于言也,故应有艳丽而幽古之声。”其子定家不僅继承了他的这些观点,而且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歌学理论。
藤原基俊在《作文十体》中赋予“幽玄”深邃和悠远的余情,幽玄开始接近余情。后来藤原正彻以“幽玄”作为咏歌的最高理想,他的歌论以禅的精神深化了藤原俊成、定家的幽玄理论。他在《正彻物语》中写道:“幽玄者,人人内心应有,进而用词表达出来,心里应有鲜明的理解,只把漂泊之体称作幽玄体。”他用“心中万般有”的禅的精神强调了幽玄的“有心”,使幽玄带有一种异端的飘渺感,一种无边无际的心灵宇宙。所以,“幽玄”不仅仅局限于感觉上,而是发展成一种精神性、内在性,达到了“有即是无,无即是有”的超越意识的幽玄世界[6]。他又在《正彻日记》中解说:“所谓幽玄,就是心中去来表露于言词的东西。薄云笼罩着月亮,秋露洒落在山上的红叶上,别具一番风情,而这种风情,便是幽玄之姿。”因此,幽玄是由朦胧和余情两大因素构成,形成难以用言辞表达的超越现实具象的神妙意境。这样,定家和正彻等人就把幽玄理解为朦胧、隐约、含蓄、悠远、空寂和余情之美。
大西克礼在《幽玄·物哀·寂》中进一步阐释了“幽玄”的含义,他认为“幽玄”有七重。第一,“幽玄”意味着审美对象某种程度上被隐藏、遮蔽、不显露、不明确;第二,“幽玄”是“微暗、朦胧、薄明”,这是与“露骨”“直接”“尖锐”等含义相对立的一种优柔、委婉、和缓;第三,是寂静和寂寥;第四,是“深远”感,它往往意味着对象所含有的某些深刻、难解的思想(如“佛法幽玄”之类的说法);第五,是“充实相”,是以上所说的“幽玄”所有构成因素的最终合成与本质;第六,是具有一种神秘性或超自然性,指的是与“自然感情”融合在一起的、深深的“宇宙感情”;第七,“幽玄”具有一种非合理的、不可言说的性质,是飘忽不定、不可言喻、不可思议的美的情趣。[7]“‘幽者,深也、暗也、隐蔽也、不明也;‘玄者,空也、黑也、暗也、模糊不清也。”[8]对日本传统美学研究大家王向远也对此重新作出解释。“幽”“玄”二字并置,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义的重复加强,也各有独特内涵的阐释,更强化了该词深邃、神秘、暧昧、模糊、不可名状的气氛与境界。而在日本,随着日本文学中“最纯粹的民族形式”——和歌体系的建立,日本人渐渐构建了蕴含着强烈独立意识、有意与汉民族文学创作相区别的审美批评体系,他们在中国主流的诗歌体系之外,摘取了“幽玄”这一抽象概念,赋予它最高的统率地位,指导着和歌、能乐等等诸多文学样式的创作。通过文人及其作品的不断阐释、演绎、丰富,给予了“幽玄”一词更为广阔的解读空间和更为哀切动人的感染力,“幽玄”最终成为了日本民族美学显著的特征。
在日本歌道创作、实践、批评体系基本成熟之后,“幽玄”的理想已然融入到了各种文学样式的创作理想之中——世阿弥在其一系列能乐理论著作中,都反复强调着“幽玄”的追求,这一取向体现在他创作的方方面面,都要力求“幽玄”化。能乐的前身猿乐,滑稽可笑,难登大雅之堂,在世阿弥看来,如果不将其脱去低级趣味,进行高雅化、贵族化的处理,能乐难以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在论及艺术的主体时,世阿弥在《至花道》中指出:“观赏艺能之事,内行者用心来观赏,外行者则用眼来观赏。用心来观赏就是体。”[9]此处“体”可以理解为本体、主体。可以说“幽玄美”,作为世阿弥理论的中心,不仅仅局限于感官上美的刺激,更要生发出一种内心的审美体验,是精神上、向内散发的美。
就能的艺术性而言,美即幽玄,幽玄即美。这种美是集“柔、丽、雅、顺”为一体的美,是演员余生俱来的一种气质。世阿弥在《风姿花传》写道:“少年之举皆美”、“人中女官、宫女、娼妓、好色、美男子,草木中花类,如此种种,其形皆幽玄之物。”[10]在舞台艺术方面,扮相逼真,形同神似即谓幽玄,世阿弥一改观阿弥时代“模仿表演为主”的传统形式为置能的舞蹈和音乐因素于表演之上的艺术形式,使能成为极富戏剧性、象征性的独特的舞台艺术。
能的剧本即谣曲。谣曲大多在《源氏物语》、《平家无语》等古典文学或民间传说中取材,尤其是在古代和歌和文章的基础上,使用缘语挂词等技巧修饰点缀,形成韵、散文相互交织的华丽七五调文章。谣曲充满幻想象征性的幽玄之美的同时又能达成剧本演出的效果。谣曲作者大多是能乐演员自己本身,创作沿袭观阿弥和世阿弥的能本或其改编。世阿弥称能的美丽和趣味为“能之‘花”,“花”意为能的趣味、新奇。与幽玄之美相对应,能应具备从“时节之花”到“妙花风”也就是从感官上的美到无心无位的美的丰富性和深奥性。而“年年来去之花”就是两者的和谐统一。[11]四川大学何春兰认为此处的“花”是能乐的生命,它的形象象征着一种艺术魅力,是能乐的精髓所在。要想在表演艺术上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有“花”,从而达到“阑位”的最高境界。对于什么是“花”,世阿弥在《风姿花传》中写到:“感动、有趣、新奇此三者同为心也”。在他看来,“花”就是要不断地磨练自己精湛的演技,懂得怎样给观众带来新奇感和视觉上的冲击,即强调它的感染力。因此他大力批判粗糙露骨的下品味的表演,提倡幽远清寂、典雅含蓄的上品味的幽玄美意识[12]。
能乐对后世文学文化的影响之巨不言而喻。在能的开创期,上演了很多与歌舞伎的世界相近的戏剧性曲目,不久梦幻能占据了能乐首位,但随之而来也迅速从能的世界淘汰,其戏剧性的性质就这样转移到了净琉璃和歌舞伎。将能原封不动地转化为歌舞伎的《劝进帐》《红叶狩》等“松羽目物”,虽有从幕末一直发展到昭和的轨迹,但能的《翁·三番叟》、《道成寺》等还产生了在近世以后的舞蹈、邦乐等很多流派。在文学与艺术方面,《闲吟集》中记载了很多能的词章、狂言歌谣,而江户时代谣曲的流行,起到了为古典文化总括简编的作用,为俳谐、川柳、假名草子、读本等提供了题材。松尾芭蕉说,谣曲是俳谐的《源氏物语》,也就是原著。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的文学也大量利用了谣书中的句子。泉镜花、郡虎彦、野上弥生子等人也有从能乐中取材而写成的作品,三岛由纪夫的《近代能乐集》也在西欧上演。爱尔兰的耶茨受到能乐启发写了一部的《鹰之井》,后来被反进口成为了新作能乐。此外,能乐对现代音乐、电子音乐也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也是不容置否的,“幽玄”在现代其意义上的丰富也有待当代人的进一步挖掘和升华。
参考文献
[1]肖霞.日本文学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2]周建萍.“幽玄”范畴的审美阐释[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4):52-54.
[3]高文漢.日本中世文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93-96.
[4]陈雯蓓.试论世阿弥能乐中的美学特色[J].长江文艺评论,2020(6):122-123.
[5]王向远.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1(6):90-96.
[6]王向远.论日本美学基础概念的提炼与阐发——以大西克礼的《幽玄》、《物哀》、《寂》三部作为中心[J].东疆学刊,2012(3):1-7.
[7]宿九高.集能艺术之大成 开能理论之先河——世阿弥及其《风姿花传》[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7(9):54.
[8]邱紫华.日本美学范畴的文化阐释[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1):58-76.
[9]何春兰.论日本能乐中的幽玄美意识[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7):91-92.
注 释
[1]肖霞.日本文学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2]肖霞.日本文学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3]周建萍.“幽玄”范畴的审美阐释[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4):52.
[4]日本大百科全书[Z].小学馆,2001.
[5]高文汉.日本中世文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94.
[6]周建萍.“幽玄”范畴的审美阐释[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4):52-54.
[7]陈雯蓓.试论世阿弥能乐中的美学特色[J].长江文艺评论,2020(6):122-123.
[8]王向远.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1(6):90-96.
[9]陈雯蓓.试论世阿弥能乐中的美学特色[J].长江文艺评论,2020(6):123.
[10]宿九高.集能艺术之大成 开能理论之先河——世阿弥及其《风姿花传》[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7(9):54.
[11]肖霞.日本文学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12]何春兰.论日本能乐中的幽玄美意识[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7):91-92.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