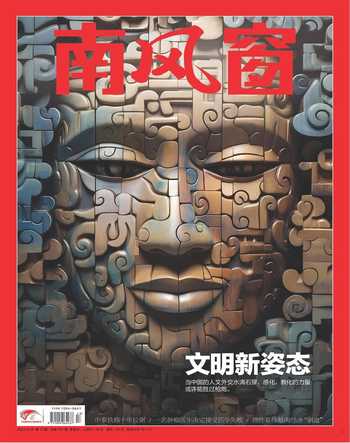一名肿瘤医生决定接受医学失败
赵佳佳

今年3月,在一场关于儿童舒缓治疗的专家课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蒋轩竹,他是这场专家课的组织筹备者,同时他也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一名医生。
我之所以对蒋轩竹产生兴趣,是由于他的医生身份很特别,其中容纳了两条看似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方面,他为儿童治疗血液肿瘤,竭尽全力让孩子的生命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他为他们进行舒缓治疗,只为了让小孩体面地离开人间。
舒缓治疗即安宁疗护,是医学延伸向死亡而非延伸向生还的路途。
在很长时间里,像蒋轩竹一样的肿瘤医生,更多地被患者及家属寄予着妙手回春治愈疾病的厚望。哪怕病人最终生命垂危,也常常难以阻挡家属同病魔抗争的执着意念,直到最后时刻,也要切开气管维持呼吸,要按压胸膛挽留心跳。
但变化在暗自发生。与蒋轩竹类似的医生正在逐步成长起来,他们决定接受医学的有限性,当他们确定疾病已然很难再有治愈可能时,会采取主动的干预,引导患者和家属共同迎接患者生命的完结。
这并不是一场轻易的转变。存在于他们工作中的,是一种生与死不断拉扯的张力,人对生的渴望仍旧旺盛,对死的恐惧永远幽微。更何况,蒋轩竹面对的还是小孩,是最被期待的新生命。
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方法都未知而陌生。但他们正为此不断努力。
以下是蒋轩竹的讲述:
“就好像蛇杖一挥,世上就没有肺癌”
我出生并成长在台中市,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每当生病时,妈妈总是带我去我家对街的儿科诊所,找一位名叫林焰的医师看诊。
林医师是个慈祥的老伯伯。他出门诊是不穿白大褂的,他会戴一个工牌,穿西装,戴领带,当时他也挺大年纪了,头发花白。每次看诊,他都会很和善地摸摸我的头,跟我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完成查体,最后送我很可爱的贴纸,再交代我回家好好吃药。
有一次我妈妈对他说,其实你们可以准备一点巧克力糖或是饼干这些东西,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很清楚地记得林医师说,我们尽量不给小朋友这些东西,是因为怕会呛到他们。因此我才发觉他已经体贴细致到这样的程度。
“你为什么要当医生?”
在小时候的某次看诊过程中,我曾问过林医师这个问题,他跟我说:“因为我很喜欢修理东西,你们的身体坏了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你们修理好。”
其实我原本不是当医生的。曾经在高雄市读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生物科技,那时候很不成熟,花光了爸爸给的零用钱,就只好自己去做兼职。
当时我还是没有放弃小时候很想要当医生的梦想,所以尽管我不是医学生,也还是去我们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科找了一份兼职,当护工,就是去推病床、送病历,干这种体力活儿,一小时赚80块台币。
有次我去上大夜班的时候,就出车祸,我听到两辆120开车进来,送来了两团血肉模糊的生物体。
当时冲击很大,觉得很恐惧。因为你不懂,你只看到血肉模糊的画面。
那是一对小情侣,半夜两点多吃完宵夜之后去约会,在回程的路上被货柜车碾过去,男孩子当场就没了,女孩子进了抢救室,凌晨两点多钟来的,到大概七点半也不行了,也送进了地下室。
我对这个事情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如果我当时有足够的技能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只推病床,还可以去帮忙他们多做一点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回去找我爸说,我还是很想当医生,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爸说,你试试看能不能考大陆的医学院。然后我就过来了。
当了医生之后,我总是还会回想起那天晚上的场景,我会一直思考,如果某天我再遇上那样子的事情,我该做些什么。
后来当了医生之后,我总是还会回想起那天晚上的场景,我会一直思考,如果某天我再遇上那样子的事情,我该做些什么。我会把那天晚上的画面放出来,重新审视每一个细节。我终于开始搞懂他们在做什么,我还会想,这个地方说不定还可以这样子做,那个地方如果当时那样处理的话就好了。
但是,在我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之后,我发现,有些人你根本就救不活,有些病你根本就治不好。
我在大学读内科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插曲。
当时我们的教授在讲肺癌,他挺老的,已经五六十岁了,感觉学识很渊博。他在PPT上面放了很多肺癌的X光、CT,还有切出来一些大体的组织,整个黑黑的。他最后说,患者可能会呼吸衰竭,肺要大切。
重要的是,他一面给我们讲课一面抽烟。他说,你们知不知道抽烟的人罹患肺癌的概率比不抽烟的人高百分之多少?
紧接着,他把烟往天花板上一喷,然后把烟头丢在地上踩熄,对我们微笑了一下。
突然之间,我们全班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他传达给你的那种感觉,在当下理解起来好像就是说,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有天你就可以跳脱于这些规则之外,你可以用你的专业知识去解决它,哪怕你抽烟,你也再不用恐惧这些东西。
就好像我们手握阿斯克勒庇俄斯蛇杖(神医用以起死回生的灵物),蛇杖只要一揮,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肺癌。
但现在,我感觉我应该是曲解教授的笑容了。
在我自己工作几年后,我再回想起那一幕,我突然对我们教授那个笑容有种新的认识,我觉得他好像是在说:“跟你们讲这么多也没有用,反正也治不好,该抽烟还是抽。”
以前在课堂上,我们觉得他的笑容是一种很自信、很有力量、很有士气的微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笑好像是很无奈的看清现实的那种苦笑。
“原来蛇杖挥动受限于诸多枷锁镣铐”
梦想被现实打碎的那天,我正在参加新生儿科的规培轮转,这件事大概发生在我规培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当时我还是个很菜的新手。
那天的情况是这样,有位妈妈本来一直没有怀上小朋友,后来好不容易怀上了,还是去做的试管,而试管本来就不太稳定。孕期26周的时候,这位妈妈就宫缩了,只能把小朋友生出来。生出来之后一看,是个女孩子。
可能他们本来就来自农村,没有太多的钱。我猜如果这个孩子是男生,他们也许还会到处去筹钱,但是后来夫妻俩看到是女孩子,我感觉他们也不是很想承担,说是不想继续治疗。
在我现在工作的港大深圳医院,救治一个早产儿大概需要花费十来万。如果你有深圳医保的话,甚至十万元都不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可能十几二十万都是有可能的。
我的带教老师其实人挺好的,但她是国内很典型的那种医生思维,就是“你想治,我一定尽力帮忙,但是你自己提出要放弃的话,我也不用再多跟你啰嗦什么”。
所以当家长提出不想治疗以后,我的带教老师就说,这个手续很简单,就是在这边签下要放弃治疗、后果自己承担的一个文书。但是签完之后,小朋友是不能留在医院里面的,只要留在医院里面,不管你同不同意,国家法律规定是有义务要抢救的。
所以家长不能带着小孩在医院的环境里等她去世,你得在医院外面的小凉亭或者其他地方等着。
我觉得每个医生应该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让家属领着病人到医院外面去等死。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但我读书的时候是有的,我規培是八九年前的事情。那时候这就是SOP(标准操作流程)。
我的带教老师等家属签完字就走了。
家长其实是有准备衣服来,但因为小朋友真的太小了,26周,真的就跟手臂一样大而已,而家长带的那种足月儿的衣服,小女孩的小裙子跟袜子,套在早产儿身上肯定是很不合身的。
其实那对父母也很痛苦,他们也不会帮这么小的孩子穿衣服,所以我要帮他们穿。后面小朋友的四肢开始有花斑,我一摸,手脚是冷的。我问他们,有没有带被子过来?可能要给她包一下,早产的小朋友体温本来就不好,这样下去会失温。
他们没带,所以我跑到库房里面,拿了我们本院的包被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抱着孩子离开了。
我在他们边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原来蛇杖挥动受限于诸多枷锁镣铐,非但如此,它的法力也远不如我心目中那样强大。
现在回想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很残忍的过程,很不人道,让父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孩在自己的怀里去世。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可以让家人抱着他们的小孩待在病房里面,吸着氧气。留下一个很漂亮的东西,证明小朋友来过这个世界。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面对临终的患儿,我们其实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但是当时我自己没有这个意识,科里面的人也没有这个意识,大家就按照放弃治疗的SOP在走—第一步,签字;第二步,驱离医院;第三步,等小孩离世之后回医院开死亡证明。
后来我去了港大深圳医院工作,这里会有临终关怀同意书。
就是说,你仍然可以在医院里继续处理这件事情,只是医生会放弃有创抢救,以保持小朋友的舒适和他的人生尊严作为我们最后的努力目标。
如果现在让我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我就不会让家长签放弃治疗同意书,我会让他们签临终关怀同意书,然后我们会让小朋友继续待在病房里面,不给予高强度的呼吸支持,可能会给予普通的面罩吸着氧气,就这样。因为这种小孩没有办法喝奶,所以我们可能会帮他简单打个针,给一点点基础的葡萄糖水。
像这样的小孩,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支持,他本来也没有办法坚持太久。
所以,我们就可以让家人抱着他们的小孩待在病房里面,吸着氧气。我可能会在病房里面帮他们拍照合影,然后我可能会帮他们留脚印,或者是脚模,留下一个很漂亮的东西,证明小朋友来过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医者的渺小”
来到现单位后,我加入了血液肿瘤团队,接触了更多患有生命受限疾病的孩子。但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越长,我越是明白医者的渺小。我们掌握的知识在病魔及命运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跟医学技术本身的有限性相关的故事,数不胜数。
在这些事情里面,小凝的经历是给我冲击最大的。她是神经母细胞瘤患儿,三岁的时候就发病了,从她发病开始,一直都是被妈妈带着来看病,从没见过她爸爸。
她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我们给她吃了一些很简单的口服化疗药,其实控制得也挺好的,当时她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小孩那样生活。
她妈妈是个很自律的人,一直要求自己不能把小凝当作生病的小朋友,会要求小凝每天六点半就要起床,洗漱并吃完早餐以后,七点就要开始学习。因为这位妈妈相信,小凝的病总有一天可以治好。就是这样子的一对母女。
刚开始的几个疗程都还不错,小凝也不用待在医院太多时间,每半个月回来一次就可以了,控制得挺好。但是疗程进行了半年左右,我们就发现不行,她可能有点复发的迹象,所以就过来开始上一些大化疗。
小凝最惨的一点是,因为她的食道做过放疗,所以她的细胞就特别薄弱。有天晚上,她突然之间咳嗽咳得非常厉害。
当时的夜班医生不明就里,就给她开了一点止咳药,可是小朋友一点都没有好过,她一整晚都咳得很辛苦。隔天早上我来之后,我说这个不对,我们必须很紧急地扫一个CT,看看她肺上到底有什么问题。最后一看,已经出现很严重的肺炎了。
为什么会肺炎?因为她的食管穿了一个很大的洞,而且这个大洞是跟气管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小凝吞进去的每一口口水都没有办法下到胃里头去,而是直接下到气管里头去。其实口腔是有很多细菌的,所以人的口水本来就很脏,口水到肺里头去,那肺就会发炎。
这种情况,内科医生肯定搞不定的。所以,我赶快联系外科医生,说这个是食管气管瘘,看我们要做什么检查,问他们能不能帮忙安排,我们看能不能做修补或者打个补丁,什么办法都好。
外科医生就说先做胃镜,把小朋友麻晕,伸个镜子下去看。
我们于是把镜子从嘴巴伸进去,想要进到她的胃里头去,没想到胃镜一往下走,它竟然直接到肺里头去了。这意味着她的食管跟她的气管已经整个烂开来,中间的分隔都没了,这两个已经变成同一条管。外科医生看了之后说,没法搞。
当时我们想,好吧,那不管怎么样,你也得先让这小孩有东西可以吃。我就想让外科医生准备一条胃管,我们在胃镜的辅助之下,把胃管从鼻子插进去,从缝里用力往下送,这样是不是可以把管子打到她的胃里头去?这样的话,她不吃东西也可以,我们可以从管子里面打一些食物给她吃,胃可以消化东西。
外科医生说,这个点子可以。我们就把管子放进去,然后当我们从缝里往下一送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喷血出来了。外科医生马上在镜下把血给止住,然后我说不行,这真不能搞了,否则出血太多,漫出来全流到肺里头去,马上呼吸就不行,就要抢救了。
当时,我们本院的医生肯定是没辙了,那我想听听其他医院的医生有没有什么意见,所以我就请院际会诊,邀请深圳儿童医院的主任来会诊。儿童医院的主任看了她的片子,直接告诉我说,真没得搞,没救了。
他说不行,我到死都要抢救的,我不能让这个小孩离开我。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抢救是个什么概念?你们有没有见过真正的抢救是什么样子?
但我还是不死心,不愿意放弃,我说你可不可以去做一个模具或是补丁之类的,现在不是有人工的气道或者人工的食管吗?我们把两端缝在上面,帮她把管重新塑造出来,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小伙子你太天真了,这是多浩大的工程。那个地方是肿瘤,肿瘤周围的组织是很薄弱的,如果你去动它,风险会很高,因为那不是正常的组织,而是肿瘤组织,可能已经烂得跟豆腐渣一样了,一弄可能就会整个就碎掉。对于一个烂掉碎掉的东西,你怎么缝啊?
然后这位主任就跟我一起去跟小凝的媽妈说,真的没有手术机会,手术的价值也不大。
后来她妈妈从房间里追出来了,一直跟主任哭着说,再危险我们都还是想试试看,还想做手术,怎样都好。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你会绞尽脑汁在想,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没想到。因为大家的知识面都太窄了,我可能只会这些东西,他可能只会那些东西,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会找更多的人,看看有没有其他处理方法。
但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无能为力,没有办法。
“但彻头彻尾我们都很积极”
我在刚进血液肿瘤科的时候,就面临着专业方向的选择。
我们科的主任说,你既然想留在这个科,也要定一个你的专长。而我的个性就很适合做安宁疗护,当时我们医院需要这样子的人,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做,这就是我开始做这方面工作的契机。
说真的,不仅仅是医生不愿意做安宁疗护,其实老百姓们也不太买账。我遇到很多家长,他们都说,你做安宁疗护不就是叫我们等死的意思?
不是等死,是治疗方针发生了变化,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帮你治疗了,放弃的东西就叫作安宁疗护,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搞不明白。
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想要把肿瘤治疗跟安宁疗护的工作结合起来,这是如何定治疗方针跟治疗目标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些肿瘤是可以治好的,能治好这些肿瘤,我们当然要很积极地治疗。有些瘤子切干净了,手术做好了,小朋友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对于这种情况,你就要用最积极的态度,最激进的干预方法,很快速地做检查,进行手术,雷厉风行地把这个活给干完。
第二阶段,就是对症治疗的部分。好比有一些慢性的病,可能它确实已经治不好了,我会给病人一种关怀,就是告诉他,此时此刻你好好地吃药,定期来打一两针,疾病还是勉强可以控制住的。我们尽力地用不影响你生活的方式,去想办法让这个疾病不要进展得太夸张。
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对症支持治疗,这时候我们也预期这个小朋友大概已经寿命有限,但是又没到最临终的那一刻,就会进入这个治疗阶段。
我就会跟家属说,你时不时地要带孩子回来输个血,或者说肿瘤控制不住了,要回来上个化疗,如果在家里面疼得厉害,我就开一点口服的吗啡给你,让小朋友在家里面至少舒服。
有一些化疗是舒缓性质的化疗。当小朋友疼痛很厉害,化疗药其实本身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止痛药,因为你只要把这个肿瘤压制住,它本身也不会这么痛。此时,我已经不是奔着把这个肿瘤给治好的方针去上化疗,而是主要奔着减轻小朋友的身体负荷,让他舒服一点点。
到最后阶段,就是临终关怀的阶段,就是你预期这个小朋友快要没有了,但是家属又不想让他在家里去世,那他可能需要一个基础的支持。
他可能需要医院里面可以让他减轻痛苦、不要那么难受的一些设备,比如说镇痛泵、呼吸支持、营养支持、补液支持,还有一些症状的控制,比如有些患者到临终的时候会流口水,会大小便失禁,其实我现在都有办法可以处理。
但是想要让患者顺利地接受这些方针和目标的变化,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想要引导家属不断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首先要让家属信任你,否则你跟他谈这些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比如我曾经遇到一个高级别胶质瘤的小朋友,两夫妻还挺年轻,把孩子养到三四岁,发现他脑子里长了肿瘤,而且肿瘤恶性度很高,长在脑干上面,基本上一经诊断活不过七个月,一年都活不到。
诊断这个病之后,家属的态度非常积极,说倾家荡产跑遍全地球的每个角落,也一定要治好,就是这个态度。
这个孩子的家长很喜欢跟我讲话,我就一直跟他灌输这个观念,但他说不行,我到死都要抢救的,我不能让这个小孩离开我。
当你遇到一个安宁疗护的小朋友,你仍然是很积极地给他进行舒缓治疗,让他可以很舒适,最后很安详、没有痛苦地离开,这是很积极的安宁疗护。
所以等到有天我值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抢救是个什么概念?你们有没有见过真正的抢救是什么样子?他们说没有,抢救不就是医生很努力让小朋友们能活下来吗?
于是,我就把自己当医生的时候经历过的一些抢救的场面告诉他。
第一,我们要压胸,压胸可能会让小朋友肋骨断掉。第二,我们可能要插管,要弄个管子到小朋友的肺里头去。这一切操作都会增加小朋友的痛苦,如果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小朋友是有望活过来的,可以治好的,我当然要很努力地抢救,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们让小朋友经历了这么多痛苦之后,就只是把他呼吸给维持住了,把他的心跳又压回来了,最后又怎么样?你控制得住他脑子里的情况吗?你也搞不定,对不对?后来家属好像就了解了我想跟他说什么。
原本是铁了心打断腿都一定要治好,但最后他说,那就按蒋医生的意思走,我们就不要按压,不要再强求了,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可以在天亮的时候,在有太阳的地方离开。我说我们尽最大程度努力。
所以,最后小朋友是在早上9点多的时候离开的。在此之前,当我们看到他血压不太好,我们就走肾上腺素,泵一些药让他心脏跳得好一点点,维持到天亮的时候再把药停掉,等到他心脏不行,自然就走了。
安宁疗护并不是表示医生的态度是从积极治疗转变为放弃治疗。
当你遇到一个安宁疗护的小朋友,你仍然是很积极地给他进行舒缓治疗,让他可以很舒适,最后很安详、没有痛苦地离开,这是很积极的安宁疗护。我们彻头彻尾都很积极,只是我们的治疗方针在根据小朋友的情况慢慢地转变,我们都很努力,爸爸妈妈也都很努力,我们没有一刻是要放弃小朋友的。
我认为安宁疗护观念的形成不应该只发生在肿瘤科内部,而是整个医学界都要认同这个东西才行。重点是观念的转变,只要观念转变了,哪怕只有一张床位,你都可以做安宁疗护。
但是,我知道这需要时间。这个国家要走到这一步,还有非常远的路。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小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