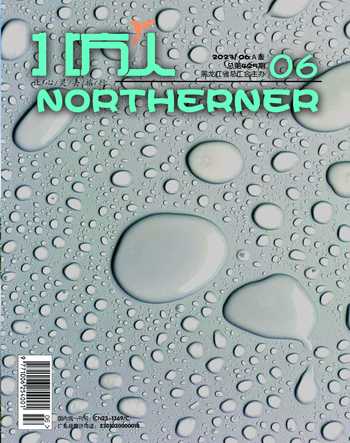我们拥有的,只是如此微小的时间份额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
我和爸爸慢慢地走在长长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上。灯火通明的小店外头,银树牌冰激凌的广告牌矗立在人行道上。
这儿是图柏镇,是休伦湖畔的一个老镇。枫树阴遮住了一部分街道。树根挤裂了人行道,把路面高高地抬起来,裂纹像鳄鱼,在光秃秃的空地上爬伸开来。穿衬衫、穿汗衫的男人,戴围裙的女人,都坐在门外。我们不认识他们,但只要有人点头打招呼,比如说“今天晚上真暖和”,我爸爸就也点点头,说句类似的话。
孩子们在玩。我也不认识他们,因为妈妈把我和弟弟都关在自家的院子里。她说他太小了,不能离开院子,所以我得看着他。看见他们傍晚时分玩的游戏,我也不至于难过,因为他们的游戏乱七八糟,各自为政。
孩子们随心所欲,一个或者两个,分散在阴沉的树阴底下,孤立成岛,各居一隅。他们孤独的游戏和我每天忙的事也没什么区别,在地上堆鹅卵石,用树枝在地上写字,而己。
我们把这些院落和屋子都甩到了身后,经过一座窗户己经被尘土封住的工厂、一家高大的木门到了晚上就上锁的木料场。小镇消失在一堆废弃的棚屋和一个小型垃圾站的后头。
人行道也不见了。我们走在一条沙路上,身边全是牛蒡草、车前草,还有各种各样的无名野草。我們到了一块空荡荡的场地里。其实这儿是一块景观地,垃圾都清除干净了,还有一把后背缺了一块板条的长椅,可以坐下来看看湖水。
夜晚阴暗的天色下,湖水通常是灰色的,地平线黯淡无光,并没有落日的景象。湖水冲刷着沙滩上的石头,声音静谧。
他告诉我北美五大湖的历史。如今休伦湖所在的位置,他说,曾经是一块平坦的陆地——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然后,从北方来的冰雪缓缓地推进,深入低地。就像这样——他给我看他的手。他伸开的手指按在我们坐着的地上,地面坚硬得像岩石一样,一点儿痕迹也没留下来。
他说:“藏在古老的冰冠身后的力量可远远超过我这只手。”后来,冰又回去了,缩回了它的北极,冰的手指留在了自己挖出的深洞里,于是冰变成了湖,成就了今天的样貌。对于流逝的时间来说,湖还年轻。
我试着让自己看见面前的大草原,看见正在漫步的恐龙。不过,我甚至没法想象在有图柏镇以前、印第安人居住时期的湖岸。
我们拥有的,只是如此微小的时间份额,这个事实让我惊骇,但爸爸对此却很平静。有时候我觉得,世界存在了多久,爸爸就在我家里生活了多久。其实,相比这个地方有人居住的历史,他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仅仅比我长一点点而己。
他对时代的了解,对那个汽车和电灯还不曾存在的年代的了解,也不比我多多少。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在世界上。等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己经垂垂老矣,老得不知道还活不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喜欢想这些。我希望湖永远都是这样的湖,永远有浮标标记的安全游泳区,还有防浪堤和图柏镇的灯火。
(摘自译林出版社《快乐影子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