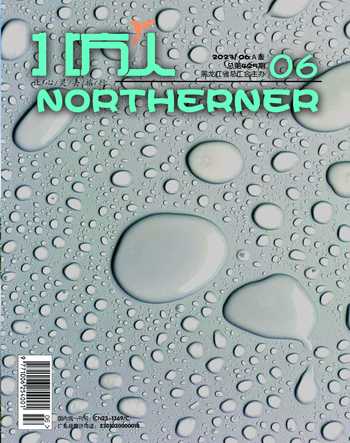遇到了解
陈百忧
心理学上有一个解释:抑郁症的人是活在过去的。在大爷的心里,他一直是那个养尊处优的少爷,只是历史的变迁让他经历了从被捧在手心里,到被踩在脚底下,再到现在他能在一个人的守护下,有尊严、体面地活着。
每天查房,老太太照旧会拿出她的小本子,很认真地跟我们汇报大爷吃完药多久以后说心慌,又过了多长时间有点头晕,躺了多久之后头晕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查房,主任对老太太说:“姨啊,人不能活得那么仔细。你越是观察你有没有心慌,你就越会觉得自己心慌,你越是想看看自己有没有头晕,你就越觉得晕,越是想为什么睡不着,就越睡不着……还不如就顺其自然,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吗干吗!”听完主任的话,老太太看着自己的本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每天认真坚持的东西可能真的强化了大爷的症状,就好像他们女儿说的,我爸的病就是我妈惯的。但我看着老太太,突然有点于心不忍。我在想,如果有人说你做了一辈子的事情其实没什么意义,你会怎么办?你这一辈子还有意义吗?
我没有问过老太太,你就这样照顾大爷一辈子不委屈吗?但其实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太太说过,“那么多人他一下就选了我,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我这种条件的人怎么可能跟他说上一句话?”
在旁人眼中,大爷和老太太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家世、背景、性格,甚至连外貌都相差很多,如果不是因为抑郁症和由此而来的种种原因,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走在一起。但正是这份连女儿都无法理解的感情一次又一次救了“两个人的命”:大爷所有的举动和情绪,老太太一个眼神就能懂;大爷不跟别人说话,要说什么都只告诉老太太,老太太再转达……60年,她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唯一出口。
大爷其实当了一辈子的少爷,他这一辈子都是老太太的少爷。
三周之后,我给大爷换了一种副作用小一些的药物,大爷失眠的症状稍微缓解了一些,就出院了。
抗抑郁的藥不可能治好大爷的抑郁症,但我突然想明白了,大爷的症状,对他和老太太而言都“意义重大”。我听过很多抑郁症患者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说,陈大夫,好多时候我都不愿意好,我不知道我不抑郁了该怎么活。抑郁会上瘾,会很容易让人沉溺其中,但症状的存在一定有存在的环境、存在的道理和存在的意义——无论是对抑郁症患者,还是抑郁症患者的家人们。有了老太太这个守护神,大爷的死亡计划从未“得逞”,而老太太也从大爷“专属”的信任和依赖中得到了满足和抚慰。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很难判断抑郁症降临在这个家庭是好还是坏——他们借由抑郁症找到了互相了解、支撑的方式。如果有一天大爷突然好了,不抑郁了,能睡一整晚不醒了,也不会总让老太太“临危救命”了,老太太会不会开始觉得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了?
我一直记得,第一次听大爷讲完自己身世的那个下午,往停车场走的时候,西边的天空被染得通红,明明只是在楼与楼的缝隙间看到了快要落下的红日,我的内心却感觉非常宽广,以前读过的诗句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好像杜甫晚年饱含苦愁与寂寞的感慨都借由大爷的故事说尽了。
对整个时代而言,大爷确实如沙鸥一般渺小,确切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爷是幸运的。他的身旁有另一只沙鸥依偎着、陪伴着,这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本身已足够温暖了。而依偎着他的那只沙鸥大概也觉得如此。
我们这一生,遇到爱并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摘自台海出版社《寻找百忧解: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观察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