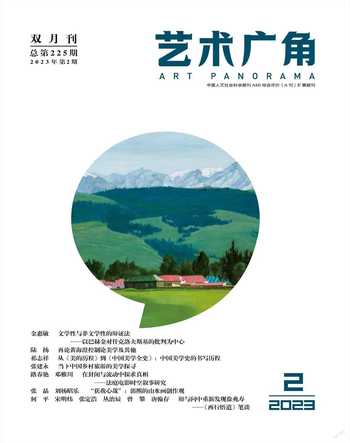一本为己的著作
张定浩
这应该是一本受众更广的书,它不应只是学术圈或文学圈的读物,而是一本可以让去西部旅行的人随身携带的、可以很好了解西部的普及性和导引性著作,它是面对普通读者的,这很重要。并且这本书并不是停留在表面或是百度百科上能搜索到的东西,它真正走到了西部的深处。我看到这本书还提到了西王母文明,从西王母文明时期逐渐过渡到当下,这样纵横捭阖是很难得的。
兆寿老师写任何事情都带着自我的热情,在书中,他提到了“古之学者为己”,我们的写作不光是为了向别人传达某种知识,同时也是一个“为己”的事情。其实也可以将这本书看作是一部西部史,这里面谈到了很多的历史,中国的学问都是从历史开始的,老子也曾经是史官,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是从重新讲述历史开始的,每一次文化的更新也都是一次通史心得,是对过去整体的认识,每一个转折点都有一些学者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部作品也可以当做关于西部的通史来看。
当下的历史学变成了特别琐碎的学科,当我们看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或是流行的学者的著作时,我们会发现都是些非常琐碎的文章,每篇文章考证的都是很微小的细节,这些文章作为历史研究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它涉及各种学术性的问题,我们无法将视野从这些琐碎的东西中脱离出来,故而不能以宏大的视野、不能以整体性看待历史,而这种整体性正是史学的基础和最终的抵达。正如兆寿老师反复提到的钱穆,钱穆先生早年也是按照乾嘉学派的样子抠一些很细的文献,但到了晚年,在他的一些讲座中就会发现,他谈的都是整体性的判断,这些判断直到今天依旧是有益的,并且他也是在中西对比的情况下谈中国,但他主要谈的是中国的儒家文明,因为当时他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不能阅读太多的文献,所以他对西方的认识有一点局限,但钱穆先生对于儒家的认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相信兆寿老师也从钱穆先生那里获益匪浅,关于西部的整体认识,我认为是更加艰难的,因为它涉及多种文明的交融,所以在这本书中,能够充分显示出兆寿老师的功力。
我认为兆寿老师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写作去认识事情,当他想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去写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比如他对鸠摩罗什这个人感兴趣,他就去写一本关于鸠摩罗什的小说,这是一个很现代的做法,也是我比较欣赏的。他的写作始终洋溢着一种活力,一种能够感染人的东西,他并不只是简单地传达某种知识,而是带着你一起探索,通过写作去认识一些未知的事物。前段时间看过一本陈福民老师的《北纬四十度》,我觉得跟《西行悟道》这本书之间有很多历史线索上重合的描述,比如汉朝和匈奴的战争,以及一些对于西部的征伐,还有对杨贵妃的讨论,两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走到了一起,且都是站在中华文明而并不是简单的汉文明的视角下去重新观察历史,依赖的材料也都是二十四史系统内的,虽然汉文明好像有点自高自大,但它依旧把异族的材料都放到了它的历史里,这也证明了在历史上,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常态化的,也是开放的。当然了,陈福民老师这本书相对偏学术一点,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史料的、文献的案头工作。兆寿老师这本我觉得相对偏散文一点,风格各有不同,所以对照读起来也很有意思。
这本书以地点为经,以时间为纬,比如天水的麦积山,再到敦煌、凉州,以这几个点为支撑,向外放射性地写作,开出了很多线索和话题。甚至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小说笔法,一些虚拟的对话,非常有意思。这本书里说到凉州是儒家文明在西部的一个重镇,说到藏传佛教在西部如何获得一种权威的认定,都挺新奇。我觉得可以将这本书当做一个全新的开始,重新认识中华文明。所谓中华文明是一个理性的精神,它不仅仅是信仰一种宗教或学说,就像在西部,不仅有儒家文明,还有各种各样的信仰,比如书中提到的萨满教、基督教等,信仰和理性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丰富的话题。我们可以以西方为参照,西方也有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也有层出不穷的战争,可以将中西方做一个平行对比,而不仅仅是将西方放在我们的对立面去审视,倘若我们将西方几千年里富有张力的矛盾与中国西部文明对比,会很有意思。
我之前在访谈中看到兆寿老师之后还有好几本关于西部的書,我期待能够有一些细节上的比较。如果说《西行悟道》这本书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宏观的框架,那么在接下来的书中,可以做一些具体的阐释。另外这本书可能因为阐述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比如会反复提到家族史等,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们要通过写作去认识问题,这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但是我相信,通过漫长的写作,兆寿老师对西部一定有他更加独到和深邃的见解,期待他接下来的著作。
——谈谈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