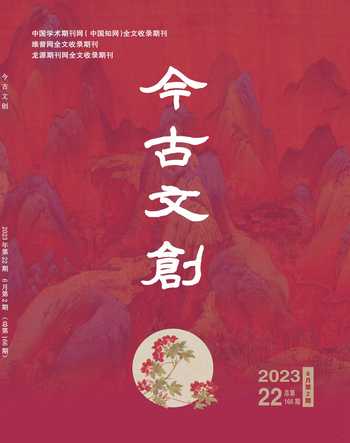“郑恒为何要死?”
邹汶睿 周志强


【摘要】《西厢记》中的配角郑恒,长期以来被定性为反派人物,其缺席与在场共同演绎了文本深层次的结构冲突。本文通过格雷马斯矩阵分析、发现隐含在文本后张生与郑恒的镜像指涉关系。由荣格镜像理论并结合《西厢记》的流变史,得出郑恒为张生人格阴影,论述郑恒死亡的充分必要条件。回归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挖掘郑恒之死下被遮蔽的男性焦虑。
【关键词】结构主义;镜像理论;阴影人格;集体无意识;男性焦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2-0007-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2.002
基金项目:广东金融学院2021年“冲补强-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学科教学(语文)硕士专业学位点培育项目。
一、成张败郑:张生与郑恒的镜像指涉
《西厢记》中登场的主要男性角色,均以娶得崔莺莺为妻为目的出发进行了一系列行动:张生初遇崔莺莺,心生爱慕而开始追求;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请杜确退敌;郑恒以张生另娶谣言抢亲,张生请来杜确证伪。
以格雷马斯矩阵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以张生为基准X,则孙飞虎是张生的绝对对立项非X,与张生形成矛盾且不对立的关系为郑母、郑恒,分别为非反X、反X。如果说孙飞虎是张生忠臣良婿形象的彻底否定,那么郑恒事实上是与张生所共处的封建文人形象的补充。
孙飞虎因凭借武力试图攫取作为权力象征符号的崔莺莺,与包括张生,崔母与郑恒在内的整个文明体系相抵牾。这一行动结果反映了原始抢婚制风俗在社会进入封建文明后逐渐衰落之事实①,张生请来杜确退敌的情节,也就蕴含着华夷冲突的时代叙事。而郑恒、崔母同样也因抢亲事件与孙飞虎形成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不可化解,只能通过彻底否定以消除威胁。显然,在文明秩序下的郑恒与张生对孙飞虎“掠夺者”身份的绝对摒斥,也说明了他们同为汉族文人的一致诉求,这也为他们的同体性质奠定了基础。
张生和郑恒的同体性质亦表现于二人相似比极高的人物设定。两人对情之追求极烈,失败的一方必然倒向死亡结局;均为前礼部尚书之子;郑恒父母双亡,在孙飞虎抢亲事件中因“家中无人”而“来得迟了”落魄失势,以及抢婚失败时孑然一身、无人声援的状况,与张生此前同是父母双亡,孤身一人“书剑飘零”之情节设定重合甚多。张生在《莺莺传》原著中与崔母的姑侄关系也位移到了《西厢记》中的郑恒。张生与郑恒的重合度之高,亦印证了其同体性质。
雅克·拉康认为,主体的认知和成长既离不开主体自身,也离不开主体的对应物——他者。同时,他将“他者”区分为想象界“小他者”和象征界“大他者”。主体只有在与他者的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具有社会功能的人,同时主体是他者的他者。在《西厢记》的故事背景中,“大他者”即为“修齐治平”的儒家文明话语体系,张生或郑恒若想获得认知与成长,就不得不被这个话语体系规训。这种规训表现在具体的情感角逐场上,就必然涉及占有崔莺莺这个主体的对应物的要求。张生对于郑恒、孙飞虎潜意识梦境或是显意识现实中的仇恨敌对情绪,正是将郑恒、孙飞虎等人视为“小他者”,通过不断贬斥对方,强化被剥夺恐惧的心理来完成自我建构。
郑恒与张生的同一性,还在于他们同处于“想象界的幻觉”中。拉康在分析爱伦坡《失窃的信》中发现了一个重复的三角结构,同样的结构也能在《西厢记》中窥见端倪。在与崔莺莺私会事发之后,崔母拷红娘,红娘驳斥崔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因此张生被迫上京取应。另一个三角结构的再现出现于郑恒抢亲时,在这两个三角结构中,崔母左右摇摆的举动表现了代掌父权的女性封建大家长在现实界的无能,而张生在驿站产生的梦境和郑恒的谣言表现了他们想象界的幻觉,两次解围推动叙事主线的角色都是居于象征界的红娘。张生和郑恒在情感面临危机时处于同一位置层面,亦证明了其同体性质。
而代表了二人异面的特征是张生的才学、相貌、品德、能力与郑恒亲缘、身世等因素。红娘与郑恒争辩中,突出张生之“君子清贤”“俏”,郑恒之“小人浊民”“颓嘴脸”“村”;以及郑恒自况“仁者能仁”“身里出身”“亲上做亲”,实质上是张生与郑恒相互诘问、质疑以确定自身合法合理性地位的过程。此时的张生通过对皇权(大他者)的依附,借红娘之口辱骂郑恒为“村驴屌”,彻底完成了对郑恒的“他者化”,亦确认了自身的主体地位之正当性。
张生与郑恒的前镜像阶段,即他们不知道对方存在之前。没有镜像进行“一次同化”,张生与郑恒均处于主体的“空白”阶段,他们在现实界中庸庸碌碌忙于取应。正因为张生/郑恒的显现,与另一个“自体”同台竞争,谁是崔莺莺的合法夫婿的问题涉及了他们的自我同一性。张生与郑恒争取崔莺莺这一过程,也就意味着他们正经历着将自己从彼此“镜像”中区分开来,将己身支离破碎的、重合的概念整合成“完整的影像”。然而任何一种“认同”,本质上都是一种“误认”。对郑恒而言,身为“白衣饿夫穷士”的张生自然比不得“先前阔”的自己,对张生加以排斥、贬低也就是确立自我身份的必然。张生同为前尚书之子,身份地位上未必与郑恒相去甚远,郑恒单方面的指控也因此落入无意义的自我貶斥。
因而在崔张故事流变中,张生与郑恒各自形成自我镜像的过程对他者有明确的排他性,结局必然导向“生存还是毁灭”的存在问题。郑恒于这场自我之战中败北,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以及由“自我理想”向“理想自我”过渡的能力被剥夺。郑恒在董西厢和王实甫《西厢记》中失败,最终表现为对自我存在的否定,“倘见亲知,有何面目?”触阶而死;反之,同样在董西厢里,假如张生未能迎娶崔莺莺,则不难得出其“把一条皂条梁间系,大丈夫死又何悲”结局的推论。同体异面的 “成张败郑”也就由此而来。
二、无理之合理:郑恒为什么要死?
(一)郑恒之死的二重逻辑悖论
在王实甫《西厢记》中,郑恒因与张生争夺莺莺失败而触树身死,死亡和婚礼的交织,使整部作品在大团圆的结局中笼罩着一层非理性的隐患。为抢婚失败而死,不但在现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看来是无理且愚蠢的行为,在传统社会中更是大不孝之举。惯常做法是郑恒退婚另娶别家高门贵女,一如崔母赠予张生金帛,令其与莺莺认兄妹一般。那么,既然郑恒毫无死亡之必要,王实甫为何要在《西厢记》的结尾设计郑恒自杀情节?
《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
[将军云]那厮若不去呵,祗候拿下。[净云]不必拿,小人自退亲事与张生罢。[夫人云]相公息怒,赶出去便罢。[净云]罢罢!要这性命怎么,不如触树身死。妻子空争不到头,风流自古恋风流;“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净倒科][夫人云]俺不曾逼死他,我是他亲姑娘,他又无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唤莺莺出来,今日做个庆喜的茶饭,着他两口儿成合者。②
后世对于这段的解读多趋向于郑恒强娶不成,无颜面见亲故,羞惭而死,但如前文所说,郑恒自杀是不孝且无理之举,在逻辑学上也不符合排中律的定则,因此郑恒的死亡必另有缘故。根据唐律,崔莺莺和张生是先奸后娶,私订终身,不受当时的法律保护。如果郑恒利用法律强制与崔莺莺完婚,则将故事的男主人公张生置于尴尬地位,这一法律与人情上的漏洞王实甫必然得顾及周全,否则也无法契合观众的期待视野,留有制度性的漏洞。因此,郑恒只有死去或退婚,崔张二人的结合才是名正言顺的。这一思想在《西厢记》中也有体现:
[净云]那个张生?敢便是状元。我在京师看榜来,年纪有二十四五岁,洛阳张珙,夸官游街三日。第二日头答正来到卫尚书家门首,尚书的小姐十八岁,结着彩楼,在那御街上,则一球正打着他。我也骑着马看,险些打着我。他家粗使梅香十余人,把那张生横拖倒拽入去。他口叫道:“我自有妻,我是崔相国女婿。”那尚书有权势气象,那里听,则管拖将入去了。这个却才便是他本分,出于无奈,尚书说道:“我女奉圣旨结彩楼,你着崔小姐做次妻。他是先奸后娶的,不应娶她。” ③
这一段谣言由郑恒编造并叙述,在戏剧中起到了突转的效果,于郑恒强娶崔莺莺的目的而言,这段谣言与郑恒之存在是符合逻辑学同一律的。但很显然,既然郑恒能为了强娶崔莺莺散播谣言,其人品既已经卑鄙无耻到如此地步,又怎会在谣言揭穿后,礼义廉耻突然占据上风,促使他自戕呢?而崔母与郑恒是亲姑侄关系,先前热情积极地主张崔莺莺与郑恒亲上加亲,又怎会在侄子自杀后全无一丝悲哀情绪的流动?这也不符合逻辑学的矛盾律定则。因此可以认定,这段不利于张生的谣言于郑恒强娶崔莺莺的目的是存在同一性的,但谣言揭发的结果却与郑恒卑劣无耻的存在本质是矛盾的。所以,郑恒之死必另有原因。
(二)缺席的在场:被杀死的张生阴影
“缺席乃是在场的最高形式。”在《西厢记》这个阴盛阳衰的文本中,男性角色的缺席与在场,共同构成了民族集体无意识景观的呈现。
首先从接续上一节郑恒的谣言说起。在郑恒的谣言合目的性叙述的背后,也隐藏着郑恒与张生的镜像关系:“我也骑着马看,险些打着我。”这句对情节推动毫无意义的话,除了表明郑恒虚构的在场身份,从而增强谣言的可信度,还透露了郑恒深层次的渴望:他也想像张生那般金榜题名,被相府小姐抛绣球择婿。在权势的淫威面前,崔张二人的结合便轻易地给否定了:“他是先奸后娶的,不应娶她。”
可以说,郑恒在叙述的暗箱中构建了一幅权力景观,这景观指涉着张生、莺莺、郑恒等存在主体的牵制关系。在这些关系的动态变化中,张生与郑恒对崔莺莺的占有与支配地位也在不断交替转换,在文本中具体体现为在场与缺席。郑恒是崔相国指定的女婿,而普救寺是崔相国主持修建的则天娘娘香火院,崔相国死后的尸体停灵于此。崔相国的死亡无疑是全剧中最大的缺席,也是最深层次的在场。死去的崔相国停留在崔氏一族的记忆中,代表着崔氏一族过去的荣耀与辉煌,也代表着封建等级制的上层统治者。在崔母的哀悼与追忆的叙述中,不断提及的“无犯法之男,无再嫁之女”的相府门风和“三代不招白衣女婿”的相府门第,正是崔相国“故鬼重来”不断对生者施加影响,从而操控生者的行动的体现。同样的“缺席者”形象也出现在曹禺的《日出》中,金八玩弄着所有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而全程都只在其他人物的叙述中体现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这正是最高形式的在场。幸而对于张生而言,这个能够在幕后操控所有人意志的无形力量已然走进了坟墓,因此传统民间故事原型中岳丈与女婿的矛盾也变异为张生考取功名,获得和崔相国一样的社会地位,从而取代崔相国成为一家之主的故事。
在崔氏一族为崔相国停灵普救寺之行中,崔家呈现出一副阴盛阳衰的景观:父性的死去、母亲代掌父权、躁动的青春期少女、不安分的侍女。在这个男性家长缺席的场域中,作为崔母内侄、崔莺莺未婚夫的郑恒也是缺席的。因此郑恒作为《西厢记》中第二个缺席的形象,在情节的设置上起到了伏线的作用。作为来自崔相国生前遗留的阻碍,郑恒不仅是崔相国死去的父权意志的复活,还是作为与崔相国同样的“缺席的在场”的形象,为崔张二人的结合笼罩上一层阴霾。而在他最不该缺席的时刻,即为崔相国奔丧时,在义理上郑恒应当去吊唁,但正是因为他关键的缺席才给了远游客张生可乘之机。而郑恒在大结局时由缺席转为在场,正是拨云见日,阴霾驱散之时。所以通过对人物缺席与在场的分析,我們发现崔相国、郑恒、张生三人的出现与隐没是交替进行的,这是人物在文本中权力牵制的拉锯战。
作为故相国门第的崔家是一个等待被占有的权力象征,张生要想彻底地占有崔莺莺,只能通过“成为崔相国”的方式,也即考取功名,以夫权行父权,成为崔家的男主人。崔母则作为张生能力的注脚,她认可父权社会的丛林法则而不是母系氏族的情感联结,这也是她为何能在郑恒自杀的现场无动于衷的根本原因。在最后一轮对崔莺莺乃至崔家的占有与支配地位的博弈中,一转开局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张生获胜,郑恒惨败。
但这一身份地位的转换,只能用层递的方式显现张生与郑恒之争的充分性,而不能完整阐释郑恒之死的必要性。因此,如果我们要深究这一转换背后的文本逻辑,就不得不回溯到《西厢记》的前身《莺莺传》中去。
《莺莺传》中的张生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薄情浪子的形象,而真实故事中的元稹与崔双文更是负心汉与痴情女的悲剧形象。道德上的瑕疵是《莺莺传》为人诟病之处,也是后世改编剧作公演的障碍。在戏剧表演上,这样的人物形象和悲剧结局是不会为当时的市民阶层所接受的。而由于戏剧的特殊性,在传播力度和影响程度上远大于文人士大夫阶层把玩的传奇小说。在古代中国重视道德伦理的文化语境中,如果改编不慎,剧作家极有可能遭到卫道士的攻击甚至是当局的迫害。因此,如何利用《莺莺传》这一家喻户晓的原始母本的话题性,又能洗脱传奇小说艳情浮浪的先天不足,成为剧作改编的关键问题。
早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就定型了故事的基本框架,也修改了张生的人物形象,并增加了郑恒这一人物。董解元在处理《莺莺传》道德瑕疵的过程中采取的办法是把原著的元稹与张生割裂开来,将元稹美好的特质,如痴情、英俊、才高八斗赋予了张生,而新增郑恒承载元稹丑恶阴暗的一面,如始乱终弃、散布谣言、背后中伤崔莺莺等。然而在分割张生阴暗人格的过程中董西厢有所保留,张生依然存在轻浮浪荡的行为举止,这也体现了董西厢在《莺莺传》和王西厢之间的过渡性。
分割人物一技术策略被王实甫《西厢记》所继承,而其背后的心理学依据是荣格的阴影理论。荣格认为:阴影即人格中的“恶”,包含个人精神因素和集体精神元素,“是那个被压抑、被隐匿的部分,它隶属于卑劣同负罪人格的范畴,其绝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动物祖先的时代去” ④。因为这些因素与已被选择的意识共存,因此它们拒绝出现在生活中,往往成为“分裂人格”的始作俑者。阴影将患者不愿意承认、却又能与他有关的各种事情人格化了,尽管它们仍然直接地刺激着他。它们也许是性格中的某些恶劣品质和其他不协调的倾向。文学作品中的阴影可阐释为“隐含读者不希望作品中人物成为的对象”。郑恒作为张生的否定性存在,他的举止行为的猥琐,是不被观众所期待的。以及他为崔母郑氏的侄子的出身,是《鶯莺传》中张生的残留,也是元稹的现实身份。只有杀死了郑恒,张生的阴暗面或说是《莺莺传》带来的原罪才能消除,才能作为高大全的戏剧形象进行公演。
“阴影是一个道德问题,挑战着自人格。如果没有相当多的道德努力,就没有人能意识到阴影。”《莺莺传》到《西厢记》中的不断删改是剧作家主动积极自发的创作活动,是金元时期文人对历史上男性角色的反思与批判。荣格认为,如能具备面对阴影的勇气,通过对阴影的挑战,在与阴影交战的过程中获得积极力量,那么患者即可康复。正是董解元、王实甫等剧作家从《莺莺传》中的张生形象分离出了郑恒这一阴影,才使《西厢记》具备了青春昂扬的积极色彩,摆脱了《莺莺传》先天带来的道德瑕疵。
三、集体无意识探微:张生潜意识的被剥夺焦虑与
替代性满足
除了戏剧表演受众的审美期待之外,结合王实甫的时代背景,很难忽视靖康之难少数民族南迁的影响。在战乱中,女性被当成是战利品和性资源被不断掠取侮辱,哪怕是北宋的贵族女子也难逃一劫。在当时不可言说的民族心理创伤之下,郑恒与孙飞虎的形象不仅是张生的情敌,更是中下层男性的假想敌。我们可从张生的梦中瞥见一角:
[外净一行扮卒子上叫云]恰才见一女子渡河,不知哪里去了?打起火把者。分明见他走在这店中去也,将出来!将出来![末云]却怎了?[旦云]你近后,我自开门对他说。
[水仙子]硬围着普救寺下锹镬,强挡住咽喉仗剑钺。贼心肠馋眼恼天生得劣。[卒子云]你是谁家女子,夤夜渡河?[旦唱]休言语,靠后些!杜将军你知道他是英杰,觑不觑着你为了醯酱,指一指教你化作膋血。骑着匹白马来也。
[卒子抢旦下][末惊觉云]呀,原来却是梦里。且将门儿推开看。只见一天露气,满地霜华,晓星初上,残月犹明。无端燕鹊高枝上,一枕鸳鸯梦不成!⑤
这个梦境传递出的是张生潜意识的被剥夺焦虑:男性的战争思维支配着张生进入普救寺这一阴性场域与崔莺莺结合,也支配着张生利用杜确这一武力外援作为自身的弥补。权力匮乏和武力无能所造成的被动性失职,也是张生被剥夺焦虑的主要来源。在以杀戮、臣服和统治为逻辑基础的战争思维指引下,郑恒在张生与崔莺莺的结合前也不得不死,因为只有郑恒的死亡,才能缓解张生也即受众男性潜意识的被剥夺焦虑。
这一集体无意识的男性被剥夺焦虑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语境后,变异成文与武两条不同的对抗模式:面对孙飞虎,张生的策略是书信一封(文),寻求好友杜确将军的援助(武);面对郑恒,张生的策略是考取功名(文),当面对质拆穿谎言,占据道德高地,营造舆论优势(文)。张生与郑恒同为文人,不再选择动物界求偶战争野蛮的肉搏,而是笔枪舌战,穿梭于成文法与习惯法之间的文人较量。
周玮璞学者认为,张生是王实甫的理想投射,郑恒是王实甫在现实中厌恶的官僚子弟的形象的凝缩。⑥《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流变,不单是文体和艺术技巧的转变与完善,还有创作主体的下移。元稹所代表的是一心跻身于高门贵胄的唐代文人士大夫,科考应举,迎娶五姓女是那一个群体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在董解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剧作家从为《莺莺传》弥补遗憾和为张生“补过”的创作动机出发,借红娘之口,为中下层汉族文人发出对门阀权贵的嘲讽。
[红唱]君端是个“肖”字这壁着个“立人”,你是个“木寸”“马户”“尸巾”。
[净云]木寸、马户、尸巾——你道我是个“村驴屌”。我祖代是相国之门,倒不如你个白衣、饿夫、穷士!做官的则是做官。⑦
经过了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宋代大量扩张科举取士,寒门庶族进一步兴起。到了王实甫的时代,汉族文人成为第四等民,多民族的交融使古典时代的士族阶层的道德观念逐渐瓦解。可以说,郑恒的自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下层汉族文人长期受门阀权贵压制而产生的不平之气的替代性满足。
综上所述,《西厢记》中体现了我们民族深层次的男性焦虑,这或许是自元稹创作《莺莺传》发端这一故事到王实甫最终定型的传唱过程中都没有意识到的民族创伤情结。对经典文本的现代阐释,有助于发掘我们民族性格中真正恐惧、焦虑以及渴求的对象,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研究价值。正是因为郑恒的死亡在想象界里消解了男性的深层焦虑,也作为文学替代性满足的对象曲折地实现了求偶战争中战胜者一方的优越感,郑恒的死亡也从非理性的为情而死,变为集体无意识作用下毫无选择余地的触树自戕。
注释:
①杨波:《略论元明戏剧中的抢婚与收继婚风俗》,《文化遗产》2015第2期,第51页-56页。
②王春晓、张燕瑾评注:《西厢记·窦娥冤》,中华书局2016版,第226页。
③王春晓、张燕瑾评注:《西厢记·窦娥冤》,中华书局 2016年版,第215页。
④荣格:《阳向离子》,《荣格全集》第9卷第二部分,第266页。
⑤王春晓、张燕瑾评注:《西厢记·窦娥冤》,中华书局 2016年版,第180-182页
⑥周玮璞:《“类张者”与“类孙者”:镜像角度下郑恒形象发微》,《戏剧之家》2021年第31期。
⑦王春晓、张燕瑾评注:《西厢记·窦娥冤》,中华书局 2016年版,第210页。
参考文献:
[1]周玮璞.“类张者”与“类孙者”:镜像角度下郑恒形象发微[J].戏剧之家,2021,(31).
[2]詹庆.《西厢记》的结构主义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3,(02):91-104.
[3]杨波.略论元明戏剧中的抢婚与收继婚风俗[J].文化遗产,2015,(02):51-56.
[4]申敏.对荣格理论中阴影涵义的理解[J].学园,2014,(10).
[5]王珍.追忆·等待·寻找:“缺席的在场”人物模式与功能[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31).
作者简介:
邹汶睿,女,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在读。
周志强,男,文学博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