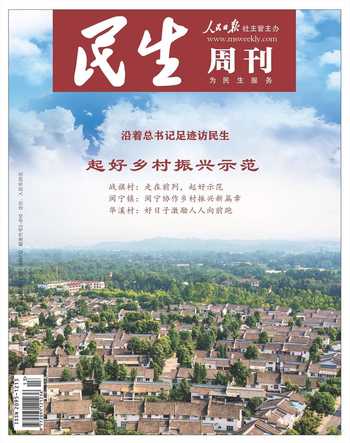走在天地间:左边历史,右边现实
贺有德
我与知名作家张雄文在微信江湖偶遇,一见如故,遂成好友。在现实生活中,同在湘中腹地,却至今未曾谋面。不过,在网络与现实中,我始终关注着张雄文的最新动态:作品刊发、参赛获奖、新书出版……在我最初的印象里,身为湖南大学客座教授的张雄文是学者型作家,博闻强识,满腹诗书;后来才知道,张雄文是通才型的,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路路通”,且硕果颇丰。张雄文的散文,常见诸大报大刊,忙里偷闲,读过不少,但比较零散。直到遇见最新行走散文集《白帝,赤帝》,才开始系统阅读,并引发我对行走散文写作新模式的探索。
多年以来,我有点偏执地认为:散文写作与阅读,当从标题开始——标题是文章的眼睛,题好一半文,好标题见才情,若能一见惊艳,必然心生欢喜。传统游记散文,标题是写实的,直至当代,写实标题依然流行。游览白帝城,标题写实,无外乎《游白帝城》或《白帝城纪行》或《走进白帝城》之类;张雄文则不然,以《白帝,赤帝》为题,仿佛异军突起,横空出世,才情与高度尽显。我读行走散文集《白帝,赤帝》,就从标题开始。书中收录张雄文行走散文共44篇,长篇短章,不少标题颇见匠心:《烟雨深处的紫鹊界》《一个书生的万水千山》《聆听书院的回响》《沧桑在浪尖上的老龙头》《清韵满勾蓝》《白帝,赤帝》《浮在波光上的书声》《紫云下的书香》《平原上群座突起的高峰》《凝固在穿岩山的时光》等,亦虚亦实,虚实相生,诗情画意,尽显精妙,一见之下只想一睹为快。
在文学作品四大体裁中,散文最灵活自由,也最难驾驭,正如学贯中西的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言:“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确实,写散文貌似容易,写好却难。有幸数次与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谭谈面谈,谭主席反复告诫,好散文不易写,必须静下心,沉下去,多写作,多打磨……张雄文的行走散文,极其讲究谋篇布局,行文如行兵布阵,颇见匠心。
古人极重文章开头,有“凤头”之说。清代文学家李渔云:“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妙语夺目,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张雄文深谙此中堂奥,其行走散文深得其法。开头出其不意,要言不烦,却有深意,甚至有穿透力,显然精心打造。看《芋头寨的静》开头:“我是被山间的一条小溪引入芋头寨的。”小巧,别致,简洁,引人遐想;看《清韵满勾蓝》开头:“勾蓝是一首唐人笔下的山水诗。”惜墨如金,尺水兴波,诗情画意扑面而来;再看《濂溪记》的开头:“心头恒久淌着一条小溪。”寥寥十字,韵味悠长,耐人寻味;洋洋洒洒的《白帝,赤帝》,开头也是如此:“我是被李白引到白帝城的。”瞬间穿越大唐,李太白与白帝城有何关联?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而《聆听书院的回响》和《雪峰山之晨》等篇,开头不求简洁明快,然而以诗性的语言打造,开头有着唐诗宋词般的诗意美,或者说像一节玲珑剔透的散文诗或诗散文,愉悦如水漫溢,很有吸引力。
张雄文的行走散文,最大的亮点是打破或跳出传统游记笔法,独辟蹊径,别开生面。
传统游记常以游踪为行文线索,偶有双线结构,明线或者说主线仍然是游踪,暗线或者说副线是作者的情感变化,比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大多如此……张雄文行走散文则不然,有意无意淡化游踪,而重历史、地理、文化、人文,纵向或横向深化,凸显每一处山水、每一篇游记的深厚底蕴,在天地间行走,同时又在文化殿堂徜徉。行走之时,恍若两个身影分分合合,一个在山水高处,一个在历史深处,時分时合,蒙太奇般风云变幻。行文之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下笔如有神助,历史、地理、文化、人文无缝对接,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在历史与现实中无障碍穿行,彰显历史文化底蕴,彰显深度与厚度。代表作《白帝,赤帝》,彻底打破传统游记模式,也与诸多白帝城游记迥异,游踪几乎忽略,按时间顺序,以纵线贯穿始终:自少昊、太昊始,至周王室,至汉高祖,至王莽,至公孙述,直至刘备,紧紧围绕白帝、赤帝,亦正史亦野史,收放自如,在王朝更迭中,在历史长河中漫游。诸多行走散文,往往沉迷于此,到此止步。张雄文更上层楼,翻出新境:于王朝更迭之外,引出由李白领衔的大群文人墨客:陈子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王士祯……因为“他们早已超越了白帝、赤帝,是这座城真正的王者……”卒章显志,另辟蹊径,翻出新意蕴与高意境,让人称奇。《浮在波光上的书声》也是如此:置身禹碑亭、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敬业堂和合江亭,在石鼓书院“草树拥覆的曲折石径间”行走,在历史天空“搜寻古贤与今人的足迹”,从“与书院齐为不朽”的李宽,至宋太宗亲书御制匾额,自宋至元、明、清乃至民国,书声穿越时空,弦歌不绝,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乃至同样名垂青史的门徒,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直至近代的曾国藩、杨度、齐白石……与《白帝,赤帝》相比,游踪更为隐秘,历史文化底蕴则同样丰厚,也彰显了张雄文读万卷书,博闻强识,令人叹服!苏轼诗云“读书万卷始通神”,其实行走万里亦通神乃至更通神,张雄文为此作出了精彩的注脚。
行走散文重历史文化底蕴,淡化游踪,并非游踪忽略不计。张雄文的行走散文,每一处山水胜迹,游踪或浓或淡,以淡居多,但其中一定有“我”,“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以“我”观史,打通历史与现实,现实的高度与历史的深度水乳交融。《白帝,赤帝》中,“我是被李白引到白帝城的”“我到来也是一个清晨”“我听着脚下拍岸的惊悚涛声”“我默然立在白帝城的红墙绿树间”“我徘徊于白帝城的青石板古道上”“当我步入苍翠掩映里的托孤堂”“我肃然默立在沉郁的托孤堂”“我踏着杜甫的足迹”“当我立在白帝城头”……足之所至,目之所及,心之所思,依然清晰,且不拘一格,打破了平铺直叙式的“流水账”写法。一反常态,历史文化成了明线或者说主线,而游踪则成了暗线或者说副线,明暗错位,别具匠心。长篇如此,短章亦然。游滕王阁,“我的炫目只是一瞬”“我惴惴然步入阁中”“我仿佛置身于万千粉黛的后宫”“我像登上泰山极顶”(《披风滕王阁》);游耒水,“我从湘东的闹市跋涉而来”“我的目光穿过浓密的竹林”“我饶有兴致地走进去”“我告辞主人往山下而行”(《漫溢耒水的绿》);游大围山,“我的目光被山顶的峰峦热辣辣地牵引”“我悚然惊呼起来”“我沉吟间”“我肃然点头”(《燃烧的大围山》)……依然是明暗错位,张雄文就像出色的导游,读者随之漫游山水,因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引领,移步换景,虚实交错,耐人寻味。
张雄文的行走散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时代性强,现实感足,紧跟时代,紧扣现实。早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便主张并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里也如此说:“文运同国运相连,文脉同国脉相牵。”毋庸置疑,作家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当时代的歌手;作品应该反映时代主题,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可以说,这也是行走散文集《白帝,赤帝》的主旋律,长篇短章,大多如此。从“烟雨深处的紫鹊界”出发,登山临水,行走天地间,登临滕王阁,北戴河看海日,耒水的绿,西岭的静,阳雀坡流连忘返,芋头寨诗兴大发……直到不老的濂溪,一路行走,一路歌吟,所到之处,名山大川乃至名不见经传的所在,满眼的青山绿水,丰厚的历史人文,感慨系之,今非昔比,新时代,新气象,新姿态,新征程,崭新的山水画卷在天地间、在你眼前次第铺开,美不胜收,沉醉不知归路……
“一切景语皆情语”,行走散文大多抓住景物特征,从不同角度写景抒情,古来如此。张雄文的行走散文,叙事、描写、议论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不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摇曳多姿。比如《白帝,赤帝》以叙事取胜,自少昊至刘备,漫长的历史风云变幻,众多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叙述极易因繁琐而纷乱,在张雄文笔下,不疾不徐,从容大度,縱线贯穿,铺叙、插叙、议论、想象,笔法多变,有条不紊,生动而不苍白。比如《三峡记》以描写见长,瞿塘峡“在陡山重障间曲折延展”,水道、江水、崖壁、水线,突出“绝险”;“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重峦叠嶂,“悄怆而幽邃”,重点写神女峰;西陵峡“原本最为宽阔”,大坝,江面,峰峦,波光,船只,鸥鸟,屈原和昭君故里……语言精准,形象生动,却不大肆铺叙,简明扼要,点到为止。而议论和抒情则如孪生兄弟,在张雄文的行走散文里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有时借助心理描写和想象夸张,画龙点睛,平添风采。叙事和描写,也因之笔法摇曳,生动起来,丰富起来。
品读张雄文的行走散文,随之登山临水,大为受益,对行走散文新摸式的探索,豁然开朗。文无定法而有大法,从标题到语言,从行文到笔法,从现实到历史,从所见到所思,从底蕴到格局,“看似平实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张雄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前者为后者打基础,后者因前者而精彩,两者交融,相得益彰。走在天地间,左边历史,右边现实,无缝对接,巧妙穿插,为行走散文写作提供了新模式,如一面多棱镜,在山水之间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