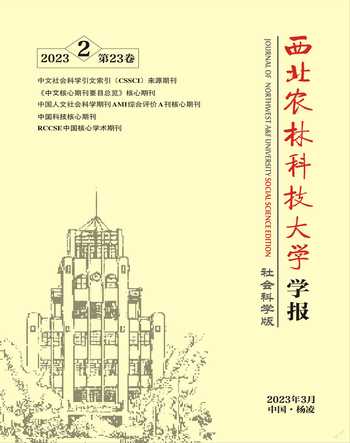农民的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
胡荣 段晓雪



摘 要:如何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以解决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政府信任在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第一,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是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变量,二者均能对公共精神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信任是民生保障获得感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机制,在二者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政府要进一步把握民生关切,增强民生保障的精准性、公平性与普及性,同时通过制度建构确保在社会保障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以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升农民的政府信任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抓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价值规范与价值引领,强化农民的集体归属感,涵育农民公共精神,加强乡村社会凝聚力。
关键词: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农民公共精神
中图分类号:F328;F3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3)02-0103-10
收稿日期:2022-05-16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2.12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81)
作者简介:胡荣,男,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建设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层细胞,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我国新时代治理现代化的绩效。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成为衡量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农民民主意识得以增强,然而市场元素的渗入也激发了农民的个体意识与个体理性[1]14。乡村中原有熟人社会形成的密切社会联结网络发生改变,农民从传统的乡村集体纽带中抽离出来,社会联结的弱化意味着农民社会角色意识的缺失[2]110。农民更多地将生产生活转嫁到个人身上,对自身的主体性和利益得失更为关注,独自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由于缺乏公共理性的引导,村庄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被忽视。村庄内部交往变得世俗化、物欲化,农民社会公德意识缺失、公共性价值意涵减弱[3]。乡村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价值冲突与碰撞直接导致了村庄治理危机与价值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潜在威胁。
就此,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在原子化社会背景下个体工具主义的扩张与各种人为风险的累积对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发起了挑战,然而即使潜藏的多种社会风险影响着社会的融洽关系,在面临重大公共事件时乡村社会生活何以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有序?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过程中,村民在面临恐慌时并未出现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侵占公共利益的现象。与之相反,在应对外来公共危机时村庄内部为维护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所达成的“团结一致,共同抗疫”的风险规避举措,如各村寨“自救式封村”的现象[4],不禁让我们重新审视乡土社会中私利与公益、集体与个人间的关系。
在托克维尔看来公共精神是社会团结与凝聚力的所在,表现为公民具有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能够让看似独立的个体摆脱“一己之私”的囹圄[5-6],有效地协调个人与集体、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公共精神是以公共生活为载体,公民在正确认识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对基本道德与公共利益的认肯,且以利他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态度与行为[7],[8]9。如果将面对外来风险时乡土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部分归因于公共精神的整合作用,此时的研究问题就变成了“中国农民的公共精神从何而来?”。对公共精神生成逻辑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研究向度,分别为:“国家-社会”的结构演进、“政府-市场”的偏好转变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规则[9]。相较之下前两者属于更为宏观的视角,而“公权力-私权利”间的博弈规则或许能为我们的研究带来启示。简单来说,“公权力-私权利”的博弈规则强调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良性互动。公权力理性回应私权利的合理诉求,为私权利提供了切实的保障。而私权利理性监督公权力,赋予公权力合法性和权威性。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均衡支出为“公共性”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政治空间,成为公共精神的集萃与自觉所在。
目前我国风险分配呈金字塔型,处于底层的个体承担了较大风险,究其原因是缺乏显性或者隐性的社会保护[10]。在乡土社会中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与乡村内部的阶层分化不仅推动了作为底层群体的农民生产生活原子化,也使得在面临风险时个人会以自身或者小团体的利益为落脚点来选择风险规避的路径[11],助长了农民工具理性的发展。个体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亦呈现减弱态势,直接导致公共精神的失落。邹英认为现下中国的社会福利正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而这样的转变适用于目前风险分配系统下的中国社会,能够提升原子化社会个体风险承担的能力,维护个体利益[12]。其潜在的逻辑是,由政府承担起散落在社会底层的风险,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力度让民生福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农民,对个体民生保障获得感产生积极影响,以此调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减缓工具理性对公共精神的消解。由此可见,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互相关联,但“其间路径为何?”这一问题依旧值得追问。一个践行服务理念的政府能够推动和引导民众的公共意识,带动社会公共精神的发展[2]37,政府在公共精神培育过程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于政府而言建构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权益关联和价值关联是公共精神形成的核心[8]22,这就涉及到对民众政治认同的强化与集体归属感的引导,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正是其政治认同的体现。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可以通过合理分配资源、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民生福利获得感进而提升民众的政府信任。在此基础上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引导群众的公共意识,涵育公共精神。由此可见,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之间相互关联。就现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多从理论层面梳理三者间的联系,鲜有实证探讨三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和影响力。
本研究试图阐释政府通过民生福利增进农民民生保障获得感,提升农民的政府信任,进而促进公共精神的培育,以此抵御原子化社会乡村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与碰撞对公共精神的消解所带来的潜在威胁这一逻辑关系。本研究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年数据构建模型来回答两个具体的问题: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是否会对农民的公共精神产生影响?若会,影响机制如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
探讨农民的公共精神,首先要回到对公共精神的概念及其维度的理解。公共精神源于对“公共性”“公共”的深刻表达,当将公共精神置于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这一语境下时,其重要性便受到学者们的进一步关注。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和研究视角赋予公共精神丰富的内涵,使得公共精神成长为一个具有多层概念和多个维度的概念群[7]。
国外将公共精神作为专题的学术著作较少,散见于将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作为关键词的学术研究中。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公共参与、公共服务、公共理性等与公共精神相关的问题[1]17,对公共精神的内涵形成了不同的阐释。保罗·霍普认为公共精神是个体不考虑个人得失,谋求个体与他者间共同利益的思想观念与行为[13]。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从公共行政角度出发,认为公共精神是公共理念与公共能力的统一,前者是公民的公共性理念,而后者强调公共行政人员承担起公共责任,为公共利益的实现积极获取信息、提供服務的公共能力[14]。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普特南将公共精神概括为是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最深层次的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普特南还给出了公共精神应当包含的价值命题,分别为公民参与、政治平等、团结和信任以及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15],从普特南的表述中我们能归纳出公共精神的两个核心要素:伦理道德精神与政治价值理念。在国内,学者们也围绕着道德伦理精神与政治价值理念形成了关于公共精神概念范畴的三种研究路径。一是伦理学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将公共精神看成是一种伦理精神,是公民个体与社群应该拥有的理性风范和行为规范,体现为公民社会交往中的道德自律和遵守社会秩序[16-17]。秉持该观点的学者将利他、社会公德意识、互惠互信、民主和平等视为公共精神的构成要素[18]。二是政治学的研究路径,该路径将公共精神看成是一种政治品质,认为公共精神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理念、事务的遵守和执行[7]。三是综合型的研究路径,认为公共精神应该介于二者之间,是道德伦理精神与政治价值理念的统一[19-20]。周庆智、刘鑫淼等均认为公共精神是孕育在人类公共生活中,以公共性为价值皈依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观念[8]9,[21]。围绕着该定义,学者们将公共精神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公共理性、公共关怀以及公共参与[5]。其中公共理性被视作是公共精神的思想内核,公共关怀是公共精神的情感呈现,公共参与是其行为体现。已有研究中虽未对农民公共精神的概念与维度进行较为明确的界定,但是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内涵特征的概述,本研究中将农民公共精神视为是农民以公共性为依归的基本道德与政治秩序观念,且包含三个维度,分别为农民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公共关怀以及对村庄公共利益的维护[22]。
那么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在“原子化”的社会背景下,因维护个体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不断,究其原因是风险分配不均。当农民生产生活面临较大的风险时,处于理性选择的个体必然就会侵占公共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进而消解公共精神,如此循环往复。民生保障获得感是民众基本生存需要和基本发展机会得以满足而形成的主观感知[23-24],涉及到个人生存和发展会面临的最现实、最有切身感受的利益问题,如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障等。民生保障获得感的提升意味着个体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都已经得到切实回应,能从源头上遏制个体过分的风险规避行为[25]。作为最大的公共性组织,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回应公民的切实需要,诉求公共利益和公共幸福[26]56。所以民生保障制度本质上是政府对农民个人正当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引导。这正是在公共精神语境下有效解决乡村社会矛盾、协调乡村社会关系的发轫点。具体地说,民生保障获得感的提升隐含着农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满意度,说明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发展机会等都得到了公平的保障。这也意味着农民在公共生活中需要自觉地承担起社会公共责任,避免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陷入价值误区。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1:民生保障获得感对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指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或信念[27]。政治信任是解释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核心维度[24],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良性关系的纽带,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坚实基础。解释政府信任的理论视角有二,分别为社会文化视角与制度绩效视角。社会文化视角认为个人的政府信任源于社会的历史文化体系中,与个人长期内化的价值体系、文化体系以及和他人的交往方式相关[28]。制度绩效视角则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源于对政府绩效的理性评估,政府绩效主要体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能力[23]。已有研究均论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间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29],且越来越多研究指出政府在公共产品、民生福利领域的政绩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甚于经济绩效[24]。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民生福利是农民政治认同的重要制度性资源,在构建农民的政府信任与维护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中起着重要作用[22]。而民生保障获得感正是个体民生问题得以保障从而产生的主观感知,也是对政府均等化、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评价[30],可以视作是衡量政府民生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
政府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与公共服务需求,使农民对政府合理的预期产出得到满足,进而衍生出个体对政府的信任,反之则导致信任危机。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2:民生保障获得感会正向影响农民的政府信任。
(三)政府信任与农民公共精神
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乡村社会价值走向了裂变和多元的进程,农民开始构筑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以集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念逐渐被淡化[2]116。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不仅引起了不同程度的价值冲突,更进一步导致了个体对国家、政党与社会认同的匮乏,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农民公共价值观念的萎缩与公共精神的缺失,也带来村庄的治理危机与价值危机。在孙杰看来执政党需要通过对国家-政党-社会三个维度的认同进行价值整合,建立三位一体的价值体系,以缓解公民认同匮乏与公共精神短缺的问题,其中,强化政党认同是核心目标[31]。执政党作为价值整合的责任主体,增进政党信任是其组织公众构建公共价值规则、协同个体价值目标、强化以公共精神为内核的社会认同之本。周庆智认为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政治联系与文化认同对公共精神的涵育有着重要作用,且只有在政府与个人间建立实际权益联系,产生政治纽带后才具备建构公共精神的社会基础,这一纽带形成的根基是政府公信力的建构[8]49。这样才有利于培养社会公众对公共生活中的制度规范与价值规则的认同感。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当个体对政府产生信任感与归属感时,二者间便建立起基于实际权益联结的合作关系,相互授予权利与责任,个体利益、集体利益以及国家利益得以协调。个体也会接受公共价值规范和价值引领,建立起文化认同,以滋养多元价值冲突下农民价值观念与信仰的缺失,带动农民公共精神的发展。就此,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间具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3:政府信任会正向影响农民公共精神水平。
(四)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
鉴于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政府信任对公共精神的影响,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可以体现在一句话中:民生决定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民生保障获得感将个体生存和发展需求与国家基本制度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促进了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增进了政府信任。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一方面能够在政府与个体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赋予农民公民权利、义务和相应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有益于传递社会的价值共识,建立文化认同,整个过程即是涵育公共精神的过程。基于此,本文设立如下假设。
假设4:政府信任是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的中介变量。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CSS 2019年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数据不仅包含了客观特征的描述,也包含了主观感知的反馈。调查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市,样本量较大且分布广泛。2019年调查共收集10 283份样本数据,经过数据清洗后,获得符合条件的农村样本7 176个。本文旨在讨论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对农民公共精神的影响路径,因而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对相关变量进行界定和测量。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公共精神。公共精神在数据库中没有直接的题目来体现,本文结合已有公共精神的研究成果与调查问卷的研究设计,采用间接方法对被解释變量进行测量。研究借鉴何齐宗、戚万学等学者的观点[5,7],从公共理性、公共关怀与公共参与3个维度测量公共精神。其中,公共理性是公共精神的思想内核,是个体超越自身利益,以公共利益的原则规范自身行为与选择的道德意志能力,同时也体现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32-33]。公共关怀是指个体与社会成员、共同体之间的情感关系与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既反映为社会成员间相互尊重与相互信任的关系[26]41,也是个人对自身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认知[32],是公共精神的情感呈现。公共参与主要关乎个人在参与公共事务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能够通过个体参与各类社会生活事务的意愿与需求反映出来,是公共精神的实践形式[26]39。CSS 2019问卷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与上述3个方面相对应(见表1)。
我们采用主成分法对表1中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数据显示KMO值为0.680,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632且通过Bartlett 球形检验,说明该数据具有内在一致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法对5个指标进行分析后,提取出2个因子。以各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作为权重,我们把2个因子的得分加在一起,求得本项研究的因变量公共精神(见表2)。具体算法为:公共精神=(因子1×0.396)+(因子2×0.202)。
2.解释变量:民生保障获得感。民生保障获得感的实质是民众基于政府公共服务对其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而产生的主观评价[30],参考相关研究选取民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民生保障获得感进行测量[23]。CSS 2019问卷的相关问题是“你对政府所提供的下列公共服务满意度如何?”。问卷中共列举了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5个问题,其关系标尺为1~10分,由不满意至非常满意依次递增。我们采用主成分法对上述这5道题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773,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763且通过Bartlett 球形检验。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抽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命名为“民生保障获得感因子”(见表3)。
3.中介变量:政府信任。选取CSS 2019问卷中的问题“您对以下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问卷中将政府机构具体划分为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以及乡镇政府三级。对政府机构的满意程度由低至高,分别赋值为1~5分。为简化数据,对政府信任的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数据显示KMO值为0.570,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22,且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共提取出一个因子,研究中将其命名为“政府信任”因子(见表4)。
4.控制变量。基于已有研究,公共精神可能还会受到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等8个因素影响[34],为排除非核心变量对公共精神的影响,将以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
(三)模型介绍
本研究旨在探讨政府信任介入后,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故构建中介模型检验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在连续变量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中,X为自变量民生保障获得感,Y为因变量公共精神,M为中介变量政府信任,且三者关系如图1所示。其含义是自变量X通过影响中介变量M,进而影响到因变量Y。c是X对Y的总效应,c'是控制了M后X对Y产生的影响。
根据温忠麒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35]分别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Y=cX+e1(1)
M=aX+e2(2)
Y=c′X+bM+e3(3)
首先,分别验证系数c、a、c'、b是否显著,且abc'是否同号,再确认c'是否小于c,判断是否按中介效应立论。其次,在控制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等变量的条件下,通过Bootstrap 5 000次样本抽样、在95%置信区间内估计政府信任在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公共精神之间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四、实证结果分析
参照温忠麟等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35],研究采用依次检验法进行回归分析,选择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计算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以考察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以及公共精神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和中介效应。依据前文的3个回归方程,表6中的3个模型分别呈现了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对农民公共精神影响的3个回归分析结果。下列3个模型均已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数据结果显示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值皆小于1,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36]。
模型1是将公共精神作为因变量Y,民生保障获得感为自变量X,只加入控制变量所构建的线性回归,模型显示总效应c显著,按照中介效应立论。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民生保障获得感越高,越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培育,假设1成立。另外,年龄、年龄平方、政治面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对公共精神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在模型3中依旧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性别与公共精神水平呈显著正面效应,说明相较于农村女性,农村男性拥有更高的公共精神水平。这可能是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规范和农村“公私领域的性别区隔”的固化[37],使得农村女性倾向于遵循传统的性别认定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其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易受到忽视。年龄与公共精神呈“U”型相关,即农民的公共精神先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当到达了一定极值点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政治面貌在1%的水平上对公共精神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党员、团员的公共精神水平更高。这是因为多数党员和团员具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较无党派人士亦具有更好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因而更有利于公共精神水平的提升[34]。结果亦显示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共精神水平的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基于较高的道德素养、自我效能感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对公共事务、公益事业保持着较高的积极性[38],公共精神水平更高。
根据步骤检验,本研究构建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回归模型2。自变量民生保障获得感X能够显著影响中介变量政府信任M,系数a显著,民生保障获得感有益于农民政府信任的提升,假设2成立。政府通过对农民基本生活需要与公共服务需要的满足,提高个体生活质量的同时亦提升了个体的民生保障获得感,从而增加个体的政治认同感。另外,政治面貌对政府信任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39]。为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中介变量政府信任M。模型3显示中介变量政府信任M对公共精神的影响显著,系数b显著,假设3得到验证。系数a、b均显著,间接效应存在。民生保障获得感对公共精神的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系数c′显著,存在直接效应。经Bootstrap法检验,间接效应乘积结果显示95%BCI[0.052,0.063]不包含0,结果显著。直接效应乘积结果显示95%BCI[0.139,0.159]不包含0,结果显著(见表7)。
系数c、c'、a、b均显著,按中介效应立论。经Bootstrap法检验间接效应乘积结果与直接效应乘积结果在95%置信区间内均不包含0,结果显著直接效应c'与政府信任的间接效应ab的符合一致,且c'小于c。中介效应模型的作用机制验证了政府信任在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公共精神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经计算效应量(|ab/c|=|(0.337×0.173)/0.208|)为28%,假设4得到證实,整体模型如图2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公共精神作为乡村振兴中的铸魂工程极具重要性[40]。然而,原有村庄集体意识与伦理观念的解体、乡土社会内部分层加剧,加之功利主义对农民趋利化价值观念的催生,使得农民“社会人”意识趋于淡薄,乡村社会矛盾凸显,在村庄内部出现认同真空的现象。因此,我们亟需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以摆脱农村“集体行为的困境”。通过构建中介模型论证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农民公共精神三者间的关系和作用路径,根据分析结果,结论如下。
首先,民生保障获得感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公共精神水平。在“原子化”社会的背景下,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农民可能因为个体所承担的风险增加,出现过于关注本身的利益得失、忽视公共利益或对公共资源占用无度的行为。在此条件下,对农民个体利益的制度性保障和对公共利益的引导成为涵育公共精神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体系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其实践准则在于增进民生福祉和改善社会福利,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政府通过对农民基本生活和基本发展机会的保障,满足个体利益需求,能有效避免其过分的风险规避行为。在此过程中,个人切实需要与国家基本政策一致,二者建立起了实际联系并依赖这种合作关系共生。农民个体之间及其与政府之间划分了权责,个人权益得到保障的同时也要肩负起维护乡村集体利益与秩序的责任与义务,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利益满足与权责行为间的关联性得以建构。
其次,政府信任是民生保障获得感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中介变量。政府应通过对个体民生福祉的保障和改善,切实有效回应农民的实际诉求,有效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在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增进个体民生保障获得感。当政府与个体之间存在共享利益时,农民才会真切的感受到政府的“在场”和个体的价值所在,能够强化农民的政治情感与角色认同,个人与政府建立密切相关的政治权益关联。个体参与公共事务时不再是局外人、旁观者、单体人的视角。另外,政府信任有利于推动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认知、认同和接受,让农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共空间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准则,形塑乡村生活共同体意识。在此良性的互动关系中,农民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以及规则意识得到填补,权力与权利得以理性的沟通与互信。政府与个体间基于利益共享、社会价值共享建立的联结,能够有助于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的统一,从客观上促进乡村社会凝聚,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总的来说,在“原子化”社会的背景下,以自我为中心、排他的个人主义造成了公共精神的阙如,所以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不仅仅是国家提供物质资源,还肩负涵育公共精神的使命。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启示有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应进一步把握民生关切,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主动回应农民最现实、最关心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民生问题。切实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维护农民的个人利益,共同追求公共利益和公共幸福,让农民的生活更具幸福感。第二,通过制度规范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保障治理。个体作为利益相关者有权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社会保障治理[41],这就关乎到如何有效规制权力与权利的问题。一方面,于政府而言制定政策的过程需要具有一定的约束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经过合法化程序。另一方面,健全农民利益诉求与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民参与社会保障治理的法律法规,让农民参与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既要激发农民群体的责任意识与主人翁精神,又要用制度对其权利给予规制,以避免社会保障治理过程中零和博弈、负和博弈的出现。第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把握乡村优秀文化的纵向传承,抓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价值规范与价值引领。乡村文化的特殊性源于传统乡村文化不仅会对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也会对凝聚地方力量、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同时传承乡村文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的优秀文化,让农民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在公共生活领域中要协调好农民个体的合理需求,引导农民自觉遵守公共规范与公共价值观念,加深农民的共同体意识、提升村庄凝聚力,形成农民集体行动的认同基础,弥补当前乡村社会存在的认同裂痕。
参考文献:
[1] 甘永宗.农民公共精神培育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D].北京:中国矿业大学,2017.
[2] 祝丽生.重塑公共精神: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治理探索[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3] 辛宁.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公共精神的建构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17:32.
[4] 张国磊,马丽.重大疫情下的农村封闭式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中H村的调研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3):32-41.
[5] 戚万学.论公共精神的培育[J].教育研究,2017,38(11):28-32.
[6] 王晓楠.托克维尔的公共精神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20:13.
[7] 何齐宗,苏兰.我国公共精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江西社会科学,2018(01):199-207.
[8] 周庆智,蔡礼强.现代公共精神的重塑——来自监利的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9] 陈富国.国家治理视域下公共精神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99.
[10] 郑永年,黄彦杰.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J].文化纵横,2012(05):50-56.
[11] 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J].探索与争鸣,2012(04):46-51.
[12] 邹英,向德平.风险理论视域下原子化社会的个体危机及其化解途径[J].新视野,2016(06):32-37.
[13] 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建构[M].沈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7.
[14]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5.
[15] 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0.
[16] 李萍.论公共精神的培养[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02):83-86.
[17] 肖飞飞,戴烽.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精神[J].求实,2012(11):65-67.
[18] 李曼.我国公民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8.
[19] 黄勇辉.转型期公共行政精神的重建[J].江西社会科学,2009(10):186-189.
[20] 褚松燕.论公共精神[J].探索与争鸣,2012(01):44-49.
[21] 刘鑫淼.公共精神:现代公民的核心品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6):36-40.
[22] 王丽.公共治理视域下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构[J].行政论坛,2012(04):17-21.
[23] 王亚茹.民生保障获得感、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20(04):18-27.
[24] 李鹏,柏维春.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J].行政论坛,2019,26(04):75-81.
[25] 谭旭运.获得感概念内涵、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2020(05):195-217.
[26] 王雅丽.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16.
[27]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79.
[28] 李艳霞.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4(02):16-26.
[29] 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25(01):96-117.
[30] 文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J].社会科学,2018(03):3-20.
[31] 孙杰.国家、政党、社会:基于认同匮乏与公共精神短缺的价值整合[J].河海大学学报,2016,18(03):78-83.
[32] 刘鑫淼.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4-35.
[33] 吴春梅,席莹.村庄治理转型中农民公共精神的核心向度[J].青海社会学科学,2014(04):27-33.
[34] 孙俊阳,莫明帅.东北地区公民公共精神研究——基于黑龙江省H市的调查[J].理论观察,2018(02):8-12.
[35]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5):731-745.
[36]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3-124.
[37] 金一虹.嵌入村庄政治的性别——农村社会转型中妇女公共参与个案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9(04):10-27.
[38] 崔岩.当前我国不同阶层公众的政治社会参与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6):9-17.
[39] 张仁鹏.社会阶层、获得感与居民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基于CSS 2017数据考察[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20:32-34.
[40] 陈洪连,孙百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塑[J].长白学刊,2022(03):148-156.
[41] 高荣.公众参与社会保障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有效路径[J].学习论坛,2020(12):76-83.
Study on Sense of Gain in 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s,Government Trust and Public Spirit of Farmers
HU Rong,DUAN Xiaoxue
(School of Society and Humanit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farmers public spirit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current rural governance is a key conten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SS 2019,this paper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influence of a sense of gain in 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s on farmers public spirit.In the first place,the findings show that a sense of gain in 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s and government trust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fluencing farmers public spirit,and both of them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public spirit.In the next place,government trust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sense of gain in 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s to farmers public spirit,in which it plays a partly mediating role.Accordingly,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focus on peoples livelihood,enhance the accuracy,fairness and universality in 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and in the meanwhile,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security governa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reconciling individual interests with public interests effectively,and enhancing farmers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sense of citizen identification.In this foundation,correctly grasping the value norms and value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pace of rural society and strengthening farmers collective sense of belonging,thus cultivate farmers public spirit and promote rural social cohesion.
Key words:sense of gain in 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s;government trust;farmers public spirit
(責任编辑: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