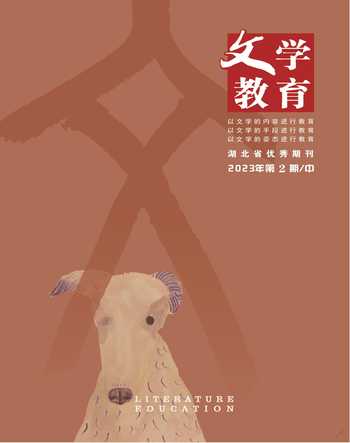《玻璃动物园》中的异化和自我身份建构
徐胜男
内容摘要: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中下层阶级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田纳西·威廉斯将戏剧《玻璃动物园》置于北方工业社会和旧南方文化冲突的语境中,刻画了阿曼达、劳拉和汤姆这三个被异化的人物形象,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压抑和扭曲。阿曼达未能直面残酷的现实,无力改变生活的困境,因而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惨遭失败。而劳拉在经历了身份的失败和重建后成功塑造了自我身份认同。汤姆则挣脱了命运的束缚,在异化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出路,最终完成了自我身份建构,获得精神的解放。本文试图从工业社会下人性的物化和异化角度出发,探讨戏剧中人物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
关键词:《玻璃动物园》 田纳西·威廉斯 异化 自我身份建构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 1911-1983)的《玻璃动物园》于1944年首次上演,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方中下阶层一个普通家庭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母亲阿曼达是一个典型的南方淑女,她沉迷于过去南方美好生活的回忆之中,却又被家庭中的琐事及经济负担所困扰。姐姐劳拉年少时因意外而变成一个“瘸子”(25)①,极度自卑使她无法在鲁比卡姆商学院学习打字,只能整日在家中摆弄玻璃动物。汤姆心怀诗人和冒险的梦想,却只能在一家鞋厂打工,他受母亲嘱托带回同事吉姆介绍给劳拉。劳拉在吉姆的引导下终于找到自我,走出了自卑的阴影。詹姆斯·雷诺兹指出,技术的发展使得温菲尔德一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成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牺牲品(Reynolds 523)。吴洁则借助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揭示该剧中的人物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如何寻求自身价值(吴洁 44)。据此,本文通过分析阿曼达、劳拉和汤姆三个人物的生活境遇,解析他们在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下被异化的表征,以及他们做出反抗与挣扎后试图重建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
一.工业社会中的物化和异化
故事开场时,威廉斯就介绍了其动荡的社会背景,西班牙已经发生过战争,欧洲战争即将爆发,美国城市劳工骚乱此起彼伏。美国南北战争及紧接而来的经济大萧条给南方造成了重大创伤,他们固守旧南方文化,生活贫困惨淡,在工业社会中成为了边缘人物。阿曼达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南方文化特征的南方女性,面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她失去了安全感与归属感,沉浸在昔日南方的种植园文化中。在种植园文化中,人们一起播种,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幸福的,并且他们十分注重礼仪。可是在工业文化中,人们不断重复着乏味的工作,也不再追求文雅,生活中充满“热烈的摇摆音乐和甜酒啦、舞厅、酒吧间和电影院啦,还有象支形灯架那样挂在黑暗中、用短促而虚幻的虹彩充斥全世界的性欲啦”(50)。剧中反复提及的“玻璃”“打字机”(9)等,都暗含了工业社会的影子。此外,劳拉和汤姆的爸爸曾经是一个“电话接线员”(11),电话、留声机、电影、电灯等的出现,暗示温菲尔德一家面临从旧的农业生活向现代城市生活的转变。而其中电影和留声机是汤姆和劳拉逃离现实的象征,汤姆因为不想在鞋厂上班,且不想面对家庭的琐事,只能借助电影、小说这些艺术形式宣泄心中的苦闷,在其中感受冒险的乐趣。而劳拉则因对自己身上的缺陷感到自卑和脆弱,只能依赖留声机和旧唱片打发时光。正如雷诺兹所说:“电影和留声机对于那些生活被仓库里的非个人商业所控制的男人和那些希望通过机械文书工作为商业服务或与成功的无线电工程师结婚而生活的女人来说,仅仅是一种逃避”(Reynolds 523)。
工业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使得亲情被物化,成为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阿曼达不仅将自己物化为婚姻市场上的商品,也将劳拉和汤姆作为赚钱的工具。每当阿曼达回忆起美好的过去,都会提到上门来的“男客人”,且都是些“最显赫的年轻的种植园主”(15)。她提到种种如何招待男客人的方式,意图替自己在婚姻市场上寻得一个好价钱:“一个姑娘光有漂亮的脸蛋和苗条的身段是不够的……她还需要有机灵的头脑和高明的口才来应付各种场面才行”(15)。除此之外,阿曼达也将女儿物化为可以带来金钱回报的商品,她希望女儿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或是嫁个好男人以维持家庭。在阿曼达看来,“那些没有本领找一个职位的”且“不结婚的女人”都不能落得一个好下场(23)。她让劳拉去商学院学习打字,却发现劳拉并没有去上课,而只是去四处溜达:“五十块学费,咱们的全部计划——我寄托在你身上的希望和理想——都一下子完了,就这样一下子完了”(22)。阿曼达将替女儿劳拉付的学费作为一种“投资”,希望劳拉将来能通过工作给她带来更多的“回报”,她并不关注女儿劳拉的真实感受,而只在乎她能不能给这个家庭带来金钱支持,亲情已经完全被物化,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疏远了。
对于儿子汤姆,阿曼达也将其物化,只是希望他能通过工作赚更多钱来养家,却从没在意汤姆内心的感受。她不停责怪汤姆抽烟:“你抽烟抽得太多了。一天一盒,一盒一毛五。一个月加起来得花多少钱?三十乘十五是多少,汤姆?算一算,你就会大吃一惊,你能节省多少钱啊。够你到华盛顿大学夜校部去念一门会计啦!”(49)阿曼达看到汤姆抽烟,首先关心的就是这样会浪费多少钱,可见工业社会下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之重。同时阿曼达希望汤姆能把抽烟的钱省下来去念会计,也可见她将汤姆物质化为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商品,将他作为生产利益和维持家庭的工具。在阿曼达知道吉姆已经订婚了之后,又责怪汤姆让他们上了当,“种种工作”“一切费用”“新的落地灯啊、地毯啊、劳拉的衣服啊”都白费了(111)。在阿曼达的眼中,金钱和利益永远是最重要的。
正如家庭成员被物化,家庭关系在此背景下逐渐被异化。“异化是指人的实践活动及产物(包括物质财富,精神产物,社会体制等),成了主宰人,约束人的异己力量,人成了自己行动和行动产物的奴隶”(吴洁 45)。阿曼达对劳拉和汤姆的关心都是基于能否给这个家庭带来经济上的支持,但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劳拉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异化的代表,她被阿曼达包装起来,以取悦男性来获取婚姻。阿曼达教她如何与男客人打交道,并在男客人到来之前将她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女性作为性客体的异化。而汤姆每天日復一日在鞋厂工作,流水线式的枯燥工作将他与外界孤立,这种生活像一个囚笼一样束缚着他(曾紫琪 49)。因此他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异化的代表。资产阶级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使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而被异化。
吉姆是戏剧中唯一没有被工业社会异化的人物,他跟上了工业社会前进的步伐。吉姆“在夜校里念无线电工程课”,“还学演讲”,他“相信电视的未来”,“只等这种工业兴旺起来”(96)。吉姆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所谓的民主。戏剧开始时,汤姆把他视为“现实世界里来的使者”(11),他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和憧憬,对未来有明确的打算,他是资本主义文明和美国梦的代言人。该剧正是通过将吉姆的与时俱进与温菲尔德一家的守旧形成对比,凸显工业社会下人性的物化和异化特征。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自我身份建构
在被物化和异化的工业社会,阿曼达试图重建自我身份,但却惨遭失败,而劳拉和汤姆则经过一系列抗争挣脱了命运的束缚,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阿曼达丈夫的出走宣告了她婚姻的失败及家庭生活的惨淡。她一方面通过回忆过去的南方生活来慰藉自己;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扮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来重建自我身份,然而这两者她都失败了(胡娅娟 70)。阿曼达沉浸在旧南方文化中无法自拔,面对汤姆“冷冰冰的”态度,责怪他“不是南方作风”(75)。她反复回忆自己曾经的那些“男客人”:“有一个礼拜天下午在蓝山——你们的妈接待了——十七个!——上门来的男客人!”(14)阿曼达在美好的回忆中得到慰藉,在回忆中抽离现实,可南方文化没落的悲惨现实使她丧失了自我意义和价值。阿曼达也曾进行抗争,试图找回自我身份,她首先将希望寄托在儿子汤姆身上,希望可以依赖儿子在制鞋厂的工作获得家庭收入,害怕他像他父亲一样抛弃家庭。但阿曼达对汤姆的说教越发让汤姆想要脱离家庭,寻找自由。另外,阿曼达还想通过劳拉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嫁给一个条件不错的人来维持生活。可劳拉与吉姆爱情的幻灭再次使阿曼达遭到现实的抛弃,最终导致她自我身份构建的失败。
而劳拉在构建自我身份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破裂到建构成功的过程。利维指出,一些角色将其他角色用作镜子,以反映他们自己希望认同的自我形象(Levy 529)。他者在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阿曼达就是劳拉在构建自我身份时的他者。阿曼达总是希望把劳拉装扮成像自己一样的南方淑女形象,以赢得男客人的喜爱。可是阿曼达又忽视劳拉自身的感受,无意间放大了劳拉跛脚的问题。“别说瘸子!你知道我绝不容许人提到这个词儿!”(58)阿曼达看似在保护劳拉,但她并没有让劳拉接受这个现实且变得自信,而是让他人闭口不提,让劳拉内心的自卑越来越深,相信自己是与别人不同的特殊的存在,从而始终沉浸在自己的“自卑情结”中(95)。实际上,劳拉的残疾不在于腿的长短导致的跛行,而是母亲灌输给她的消极自我意识(Levy 530)。
直到吉姆的出现,劳拉的自我身份建构面临了从破裂到建构成功的转机。与阿曼达不同,吉姆则告诉劳拉,“你身上是有一点小小的缺陷。几乎看也看不出!”(95-96)吉姆让劳拉直面现实,面对自己的缺陷,并让她明白即使她是个瘸子,她也与任何人一样,并没有低人一等。吉姆还邀请劳拉一起跳舞,让劳拉突破心理防线,迈出了追求自我的步伐。在吉姆的开导下,劳拉终于重拾自信,接纳自我,试图重建自我身份。可在她知道吉姆已经订婚了以后,“劳拉的脸上象圣坛上的烛光那样的亮光已经熄灭了。她的神情简直无限凄凉”(105)。此刻劳拉对爱情的幻想幻灭了,但这并没有击垮她,她微笑着把摔坏的独角兽送给吉姆当作“纪念品”(106),她已经重新找回了自我,并下定决心要面对现实,最终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
与劳拉不同的是,汤姆不接受家庭给他的定位,主动拒绝母亲给他树立的形象,希望找到自我的价值,因为他一旦认同这一点,他将永远无法自由。剧中汤姆把父亲当作构建自我身份过程中的他者,那张“挂在壁炉架上”“比真人大的相片”(11),就像一枚镜子反映了汤姆的自我身份。汤姆的父亲曾经是一个电话接线员,但他却爱上了长途旅行,逃到墨西哥寻找自由和冒险。与父亲一样,汤姆想成为一个“航海家”,“去南海岛——去远征——去遥远的异国”(72-73)。汤姆还喜欢写诗,想成为“诗人”(11),他“在仓库里工作清闲的时候,躲在厕所一个小间里偷偷地学写诗”,吉姆管他叫“莎士比亚”(62)。汤姆对艺术和冒险的追求体现了他的反异化和反拜物教特征。汤姆在艺术和冒险中体验着真实生活的乐趣,找到了自我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汤姆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
20世纪30年代,美国正处于内战后和经济大萧条之际,生活的困境和家庭的负担使得温菲尔德一家遭遇现实和理想的割裂,家庭成员和家庭关系在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被物化和异化。母亲阿曼达不仅将自己物质化,还将劳拉和汤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他们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被异化,成为了现实和金钱的奴隶。在此语境中,阿曼达、劳拉和汤姆试图找到自我价值和自我身份,重建自我身份认同。然而,阿曼达在旧南方文化的没落和女儿爱情的失利中丧失了自我身份。劳拉则在经历失败后重新构建自我价值,找到出路。汤姆在理想的引领下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走向了艺术和冒险,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也有的学者认为,劳拉并没有走出自卑的阴影,而是在得知吉姆已经订婚之后仍然重回“玻璃动物园”之中,或许正是多种解读的存在,才使得该戏剧更加引人深思和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
[1]Eric P. Levy, “Through Soundproof Glass”: “The Prison of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Glass Menagerie”, Modern Drama, 36, 1993, pp. 529-537.
[2]James Reynolds, “The Failure of Technology in The Glass Menagerie”, Modern Drama, 34(4), 1991, pp. 522-527.
[3]胡娅娟.旧南方文化桎梏下的认同危机——田纳西·威廉斯《玻璃动物园》中阿曼达的人物形象分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第35卷第6期,2014年6月,69-72.
[4]田纳西·威廉斯.玻璃动物园[M].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5]吴洁.异化的世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玻璃动物园》[J].飞天,第14期,2010年,44-46.
[6]张闪.《玻璃动物园》中的自我身份构建[J].青年文学家,第9期,2022年,140-142.
[7]曾紫琪.从异化理论出发探寻《玻璃动物园》中的真相[J].喜剧世界,第一期,2022年,49-51.
注 釋
①详见田纳西·威廉斯:《玻璃动物园》,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文中对《玻璃动物园》文本的引用将只标注页码,不再另注.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