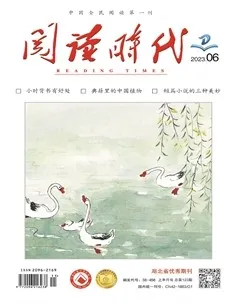清汤本应是鸡汤
五柳七
古代没味精、鸡精,在传统烹饪中,鸡汤是调味汤,不是味精加水所能替代的。
中国有俗语“将靠枪,厨靠汤”,《法国烹饪》主编威沙尼也有句名言:“鸡对于厨师来说,就像油画家的画布。”这两句都不如清代袁枚《随园食单》的比喻来得精髓:“鸡功最巨,诸菜赖之。如善人积阴德而人不知。”画布和枪毕竟都摆在明面上,而鸡汤是升华美味的隐形翅膀。
“清明如水”是标准
古人以汤调味,叫法很多。北方人常说“老汤”,南方人常说“鲜汁”,再如高汤、哨汤、对汤、毛汤、鲜汤,都是一个意思。
有句俗语“有鸡无蹄不肥,有蹄无鸡不鲜”。“吊汤”其实是“八鲜”过海,鸡汤并非白水炖鸡,工序复杂。如清初朱彝尊《食宪鸿秘》载“提清汁法”:
好猪肉、鲜鱼、鹅、鸭、鸡汁。用生虾捣烂和厚酱(酱油提汁不清),入汁内。一边烧火,令锅内一边滚泛末,掠去。下虾酱三四次,无一点浮油,方笊出虾渣,澄定为度。如无鲜虾,打入鸡蛋一二个,再滚,捞去沫,亦可清。
重点说“清汤”一词。“清汤寡水”是成语,不过古人说“清汤”,说的不是白水,而是鸡汤。《调鼎集》载有“提清老汁”“诸物鲜汁”等法,其中有“清汤”一条,强调鸡汤一定要做到“清明如水”:老鸡两只,瘦猪肉二斤,好火腿半斤,净鸡肉半斤(或拿瘦猪肉半斤代用亦可)。先将鸡宰洗干净,同肉、火腿一并煎熬,直至成浓汁一钵。汤熬好,将三物取出,另将所备鸡肉(或所备瘦猪肉)切成细丁,趁汤滚开放进去,再等半顿饭的时间,用漏勺捞起碎肉,将汤倾在细夏布袋内,细滤一过。再倾入钵内,蒸一炷香的时间,等澄清汤底,将上面清汤滗下,就成了水一样的清汤。
关于清汤,美食家各有所述。学者崔岱远在《京味儿》一书中说,当年老北京大饭庄和家里做菜的区别全在汤上。因为大饭庄用的汤是“清汤”:“用整只的老母鸡、填鸭,大块的五花肉经过熬汤,过箩,把鸡肉、牛肉分别剁成肉茸,在汤里煮了以后压成饼,再把两种饼下到汤里用小火煨,打净浮沫儿做出来的。这种方法叫双吊法,看上去清澈,喝起来鲜美。”
南北朝时,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爱吃水引饼,“挼如箸大,一尺一断,盘中盛水浸,宜以手临铛上,挼令薄如韭叶,逐沸煮”“细如委莚,白如秋练”。由此想来,水引饼很可能就是清汤面。
厨行吊汤各有窍门
汪曾祺先生回忆过,写《红岩》的作家罗广斌总说女孩子是“清汤挂面”。但他和罗广斌一起吃过清汤挂面,四川人做清汤挂面,用的是撇净油花的纯鸡汤,“清可注砚”。再有开水白菜,汪曾祺头一次吃的时候,很纳闷白开水为什么能做出好菜。“喝了一口,鲜美无比,这不是开水,也是鸡汤。”
唐鲁孙说,煮白汤面的原汤,是把鸡鸭的骨头架子、鲫鱼、鳝鱼、猪骨头、火腿爪放汤大煮,所有骨髓都渐渐融入汤里,煮到色白似乳,自然味正汤浓。他听富春茶社老板陈步云说,厨行吊汤,各有窍门秘不传人。有的另放羊肠,有的把上等虾子缝在布袋内下锅同煮,等汤煮好,再把虾子包拿掉。手法门道名堂甚多,每一家面馆的白汤面都有它自己的独特风味,一般家庭是没法子仿效做的。“要吃上等白汤面,一定要到茶馆去吃。”

《神州轶闻录》一书中有篇《萃华楼的鸡汤菜》,认定当年老字号萃华楼的鸡汤为佳。他们做出的鸡汤,清汤如水,奶汤乳白。清汤要用鸡脯肉、鸡腿肉剁成鸡肉泥,再用凉水调稀往锅里倒。文火煮沸后,清去汤面上的漂浮物,使汤汁干净变清。奶汤用同样的鸡肉泥为料,用火则须猛烈,烧滚数时始见乳白,“所以清汤,是清如水的鸡汤”。萃华楼名菜“清汤燕菜”就是用清如水的鸡汤和上等燕窝做成的,做好后透明清亮,“细看还可见到燕窝的丝纹,吃时清鲜醇香”。
鲜味未必来自大鱼大肉
“南唐北陆”指民国时两位名媛,北陆是陆小曼,南唐是唐瑛。让唐鲁孙念念不忘的是,一次在上海,唐瑛请他吃的热汤面。汤既非鸡汤,又无味精,只在碗底发现比米粒长一点的小鱼一撮。唐瑛跟他说:“这种小鱼是鄱阳湖特产,渔户把它晒干,論斤来卖,拿来下面,比苏北的白汤面还来得鲜美适口。”这种小鱼,应该是鄱阳湖的野生白鱼。
鱼羊为鲜,鲜味却未必全得来自鸡鸭鱼肉,蔬食同样能让清水变鸡汤。
宋代士人,最重在大鱼大肉之外,寻找果蔬之鲜。苏东坡煮菜羹,名为东坡羹,“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陆游也仿效苏轼,手烹甜羹,“年来传得甜羹法,更为吴酸作解嘲”。
蔬菜做鲜汤,首推蘑菇汤。唐鲁孙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天津认识一家元兴旅馆的掌柜,祖父是摆摊卖嘎巴菜的。一位从石家庄过来卖皮货的老客有次突然晕倒在摊子前,被老掌柜救醒,一问才知是赌钱输光,气急攻心。老掌柜给他凑了几个钱当盘川。过了两年,有人给他捎来四大麻袋上好的口蘑丁,口蘑熬汤比鸡汤都鲜,口蘑之中又以口蘑丁最鲜,所以价钱最贵。原来皮货老客是张家口一家大口蘑店的少东家。从此张家的嘎巴菜,每天就改用口蘑丁熬汤。
“人人吃了他家的嘎巴菜,都觉得除了鲜美味厚外,还带点卤煮鸡的湛香。”不几年老张家成了附近一带的大富户。
寻常小菜变名肴
《红楼梦》有一道给宝玉解酒的酸笋鸡皮汤。《调鼎集》中记“酸笋”做法:“大笋滚水泡去苦味,井水再浸二三日取出,切细丝,醋煮……”又记:“冬月宜汤,鸡蹼、鸡皮、火腿、笋四物配之,全要用鸡汤,方有味。”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中,绍兴福兴楼有道用鸡汤做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是不可不吃的。很疑惑,那确定是鱼翅,不是粉丝?一直奇怪,像鱼翅、海参这类昂贵食材,本身却都无味,只能借着鸡汤来提鲜,图什么,豆腐、锅巴不香吗?
鸡汤之美,贵在贫富皆宜,同样能化寻常食物为珍馐,使得诸多小菜同样成了名肴。
国民党大佬陈果夫口气很大,曾经独创一菜,号称“天下第一菜”,不过就是什锦锅巴。这道菜的做法是:先把鸡汤煮成浓汁,待虾仁番茄爆炒后,加入雞汁轻芡;锅巴油炸盛盘,再趁热浇上勾过芡的鸡汁番茄虾仁。
近代金融家岳乾斋,创办过中国第一个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他的最爱是畏公豆腐。豆腐要先用吊好的黄豆芽汤煮,等豆腐生满了蜂窝眼,再用清鸡汤炖。鸡汤灌注蜂窝眼,炒菜的油不能渗入,豆腐入口腴润,柔而不腻。
可以商榷的是袁世凯的口味。他喜欢吃的一道菜叫清炖肥鸭,要在鸭肚子中塞入糯米、火腿、酒、姜汁、香菌、大头菜、笋丁等,然后再用鸡汤来蒸,蒸三天,让鲜味慢慢渗入鸭肉里。这道菜还不如叫“鸡同鸭讲”,鸭子已经够肥美,想不出再用鸡汤入味的道理,反倒平添油腻。
论鸡汤的“独立品格”
车辐《川菜杂谈》一书是谈川菜名作,论鸡汤,他是观点最“纯粹”的一位。他记四川鸡汤的做法,大有不同。四川农村里杀鸡炖于沙罐内,放在燃过的草灰堆子中,将沙罐口用青叶子包好,然后泥封,埋入草灰中,两三个小时后取出,首先闻到的是鸡汤香味。鸡香的本味,不加任何作料(包括常用的姜、葱),全用白汤出之。
车辐说:“这种本味白汤(又称“原汤”),不失其纯真,那是汤中之上乘,回味厚而浓,它是一种独立的品格。什么是原味?以鸡汤为例,不放盐是原汤味,放了盐仍然是鸡汤,可不是原汤味了。”
正如美食家蔡澜在书里说:“用鸡汤调味的都是火候菜,需要慢功夫。”
《川菜杂谈》有道鸡汤菜,叫“莲蓬豌豆”。用鸡脯肉去脂皮、白筋后砸成泥,加鲜菠菜汁、绍酒、猪油、盐,调成稠糊。另取小碗倒入鸡蛋清,再加入面粉和干淀粉搅匀,分三次掺入鸡泥中。接着将鸡泥分别倒入十四个内抹猪油的小酒盅内,每个酒盅内又再嵌上七粒豌豆,中间一粒,周围六粒。然后撒火腿末,点缀少许用油菜叶切成的细丝。上笼蒸后,逐个取出,它就成了一个个小巧嫩绿的小莲蓬。面朝上放在大汤碗里,倒上烧开调好味的鸡汤,随即上桌。这样的口福,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杀时间”。
今人总对过去的老味道念念不忘,显得厚古薄今。现在的人,难得的不在鸡汤,而是慢功夫。当代生活加速,进了饭馆上菜都是一眨眼就满了桌,预制菜都成了年夜饭,鸡汤越来越近似于清水,而那份“独立的品格”,倒都油腻成了“鸡汤学”。
(源自《北京晚报》,王世全荐稿,有删节)
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