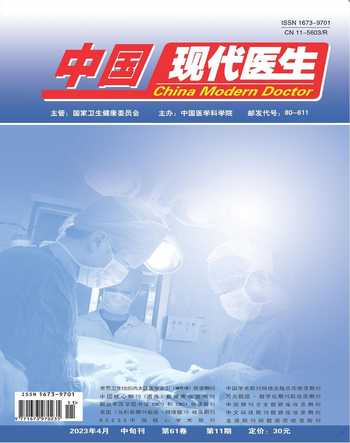抗生素骨水泥治疗慢性创面的研究进展
庞哲栋 肖连根 樊光亚 苏文硕 陈晨 董黎强
[摘要] 慢性创面的治疗一直是再生医学领域的难题之一,传统治疗主要以清创、全身应用抗生素、定期换药等方法为主,临床疗效总体欠佳。近年来,随着抗生素骨水泥在骨髓炎、骨缺损等骨科疾病中取得卓越的临床疗效,其抗菌能力优秀、机械稳定性良好、可促进诱导膜形成等优点给慢性创面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基于此,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临床中抗生素骨水泥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应用现状和特点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抗生素骨水泥;创面;感染
[中图分类号] R65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9701.2023.11.028
慢性创面是指在机体皮肤及皮下组织因不同原因的损伤形成创面,并接受超过1个月的系统治疗后,仍无法通过正常的修复过程达到解剖及功能完整,也无明显愈合倾向的创面[1],是一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病程长,治疗难度大、治疗费用高且易反复发作,致残率较高。近年来随着糖尿病、卒中、慢性骨髓炎等发病率的上升,致使糖尿病足、压力性创面、感染性创面等的发病率也随之升高,基础疾病多、细胞代谢合成能力下降的老年人往往更容易形成慢性创面[2]。慢性创面病因病情复杂,无法在短时间内愈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3]。
慢性创面主要包括压力性溃疡、糖尿病性溃疡、静脉性溃疡、动脉功能不全溃疡、创伤性溃疡和感染性溃疡,其中最常见的是糖尿病性溃疡[4]。目前治疗慢性创面的治疗原则包括清除坏死组织、控制炎症及感染、保持创面正常湿度、去除创缘受损表皮,其中控制炎症及感染是治疗慢性创面的关键。感染是慢性创面发生的重要诱因,随着细菌在创面中不断定植,局部感染导致创面发生的过度炎症反应将会促进组织细胞坏死,增大创面面积,最终导致创面愈合延迟。因此针对慢性创面的治疗,关键在于控制感染[5-6]。抗感染可以分为全身治疗和局部治疗,全身治疗具有不良反应大、局部抗生素浓度低、作用持续时间短等缺点,而创面局部使用抗生素能够长期维持抗生素有效浓度、降低不良反应、减少局部给药次数,临床疗效优于全身治疗[4],因此对于能够负载抗生素的载体研究逐渐成为临床热点。
1 概述
1.1 历史沿革
![]()
 骨水泥的主要成分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athyl methacrylate,PMMA),骨水泥具有良好的填充及支架效果,能够提供稳定的机械力学状态,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被大量应用于固定内植物、椎体骨折、填充骨缺损或组织空洞。1958年,PMMA率先在髋关节置换术中使用并逐渐成为人工关节固定的金标准[7];1970年,PMMA被用于局部抗菌[8];1979年,PMMA被制成念珠,临时性地填入骨髓炎清创后的死腔,而后抗生素骨水泥(antibiotic-loaded bone cements,ALBC)珠鏈逐渐发展成为治疗创伤后慢性骨髓炎的主要措施,同时ALBC还被广泛应用于骨不连、骨缺损、髓内感染的治疗中,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9]。近些年,基于慢性创面由于局部感染而迁延不愈的特点,研究者们开始论证ALBC治疗慢性创面的可行性。
骨水泥的主要成分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athyl methacrylate,PMMA),骨水泥具有良好的填充及支架效果,能够提供稳定的机械力学状态,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被大量应用于固定内植物、椎体骨折、填充骨缺损或组织空洞。1958年,PMMA率先在髋关节置换术中使用并逐渐成为人工关节固定的金标准[7];1970年,PMMA被用于局部抗菌[8];1979年,PMMA被制成念珠,临时性地填入骨髓炎清创后的死腔,而后抗生素骨水泥(antibiotic-loaded bone cements,ALBC)珠鏈逐渐发展成为治疗创伤后慢性骨髓炎的主要措施,同时ALBC还被广泛应用于骨不连、骨缺损、髓内感染的治疗中,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9]。近些年,基于慢性创面由于局部感染而迁延不愈的特点,研究者们开始论证ALBC治疗慢性创面的可行性。
1.2 ALBC的作用机制
1.2.1 抗菌 各种细菌引发的感染性炎症是创面难以愈合的关键因素,有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糖尿病足患者存在创面感染情况,其中两成患者面临截肢[10]。因此慢性创面在清创及去除坏死组织后,要通过局部或全身使用抗生素以对抗炎症反应。ALBC在慢性创面中的应用可实现抗生素的局部用药,能够形成高达几百倍于全身用药的局部药物浓度,此时ALBC局部释放的药物浓度远高于最低抑菌浓度,局部抗生素血药浓度的大幅提升避免了因抗生素用量不足而导致的耐药菌株出现和创面的迁延难愈[11]。ALBC治疗慢性创面时,由于是局部用药,进入血液循环的抗生素较少,极大降低了抗生素对全身器官造成的不良反应,同时ALBC可不受创面血供的影响而持续释放高浓度抗生素。
1.2.2 促进诱导生物膜的形成 1986年,诱导膜技术被提出,起初主要应用于骨缺损的修复治疗,具有成骨较快、愈合率较高的优点[12]。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组织学及细胞功能学的发展,临床逐渐认识到创面微环境对创面修复的影响,Masquelet技术诱导形成的自体膜(induced membrane,IM)能够产生一个相对独立且稳定的封闭环境,阻隔细菌的侵入,为创面的生长提供稳定安全的微环境。黄红军[13]研究发现,PMMA覆盖创面能够促进IM的形成,IM能够分泌转化生长因子-β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并使其富集保留,这些生长因子能够促进局部组织的血管化,由此形成的垂直骨长轴方向的血供系统有利于创面的愈合。控制感染不仅是创面重建的前提,也是诱导膜成功形成的关键,ALBC的抗菌性能够为诱导膜的形成提供相对无菌的微环境。
1.2.3 缺损覆盖及促进肉芽组织的生成 除了抗菌和促进诱导膜形成,ALBC还对组织缺损有填补和覆盖作用。彻底清创时除了要切除感染及坏死的组织,还要切除2~5mm的健康皮缘,要求切除后的皮缘血供良好,切除的深度达到骨面,但由此形成的较大组织空腔会大幅增加感染风险。ALBC能够提供稳定坚固的机械力学状态和良好的支架作用,塑形后可充分填充覆盖缺损组织,避免了死腔的形成,其覆盖创面还能对显露的肌腱、筋膜、骨骼起到保护作用。同时ALBC形成的诱导膜分泌的生长因子可诱导生产性细胞向慢性创面移动,能够刺激成纤维细胞增殖,促进肉芽组织的生长,从而使创面逐渐缩小。
1.3 传统敷料的不足
纱块、棉垫及绷带等是目前临床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的主要敷料,具有使用简便、性价比高等优点,但需定期频繁更换,易对创面造成机械性损伤[14]。传统敷料本身不具备抗菌功能,换药时使用的消毒剂会对创面产生刺激,不利于慢性创面的愈合。近些年出现了工程皮肤、泡沫辅料、水凝胶敷料、银离子敷料为代表的新型敷料,这些新型敷料不仅可以保护创面,还具有一定的抗感染、保湿、促进创面愈合等作用[15],但慢性难愈性创面常伴有严重的感染且患者的自主修复能力不足,新型敷料往往难以奏效。ALBC作为一种新型负载抗生素敷料,抗菌能力优秀且无需频繁换药,能促进诱导膜的形成,创造稳定的隔绝环境,较常规敷料优势明显,为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治疗选择。
2 ALBC在慢性创面中的应用
2.1 糖尿病足溃疡(diabetic foot ulcers,DFU)的治疗
DFU继发于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因创面愈合能力受损,在感染、重复应力等多重损伤性因素影响下形成表皮溃疡及深层组织破坏,最终形成慢性难愈创面。糖尿病足感染(diabetic foot infection,DFI)病情进展迅速,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负担[16-17]。传统的DFI慢性创面主要以清创植皮甚至截肢等手术治疗方案为主,辅以全身抗生素治疗,存在手术创伤大、感染无法有效控制等缺点,往往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而ALBC不仅能够在DFU创面局部持续释放高浓度抗生素控制感染,还能覆盖填充清创术后形成的死腔,对DFU创面的良性进展具有积极意义。一项回顾性研究将50例DFU合并外周动脉疾病(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PAD)的患者分为植入ALBC的试验组和常规清创治疗的对照组,通过长期随访发现PMMA组清创频率更低,截肢率更低,愈合时间更短,而且PMMA组患者生存率远高于常规组[17]。PAD作为DFU常合并的血管病变,其带来的局部动脉功能不全加重了DFU患者感染和截肢的风险,PMMA植入后形成的诱导膜能够一定程度地缓解PAD导致的血供不足,对局部血管生成和伤口愈合具有积极影响[18]。陈清华等[19]对84例DFU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常规清创联合ALBC相较于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技术临床疗效更佳,可进一步缓解患者疼痛,能更有效地改善下肢功能与纠正足背动脉血流动力学异常,促进创面快速愈合。钟云雪等[20]证实ALBC可纠正血流动力学异常、加速创口愈合,缩短DFU患者的住院时长。DFU患者常伴有下肢缺血、感染、神经病变及多种基础疾病,往往病情复杂难以愈合,上述研究表明ALBC有机会成为治疗DFU的高效治疗方案,为全身情况较差的高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但仍需通过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数据来验证该方案的可行性。
2.2 压力性创面的治疗
压力性创面常见于瘫痪等长期卧床患者,软组织在持续的压力及剪切力作用下出现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皮肤及深部软组织发生缺血、缺氧,最终导致组织坏死,最常发生在骨隆突处。患者往往伴随大量基础疾病,全身营养状况差,创面愈合较慢,常合并细菌反复感染,且彻底清创后出现的较大空腔容易形成死腔。针对这些问题,陈华等[21]将坐骨结节Ⅳ期压疮患者经骨水泥负压封闭引流处理后行股后带蒂肌皮瓣修复,疗效显著。骶尾部骨隆突明显且皮肤薄,长期患着此处长期受力,因此最易发生压力性溃疡。而且骶尾部筋膜下有较大的潜行空间,容易形成死腔,发生感染后预后较差。孙勇等[22]采用ALBC串珠填充空腔后联合皮瓣覆盖治疗骶尾部压疮患者,获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ALBC填充创面空腔能够有效防止死腔形成,结合自身的抗菌功能可有效抑制细菌滋生,同时还能刺激创面内组织细胞增生活跃,促进肉芽组织的形成。
2.3 感染性创面的治疗
感染性创面常继發于坏死性筋膜炎、开放性损伤、糖尿病足等疾病,治疗时间长且棘手,单纯的清创术无法彻底控制感染灶,创面感染易反复发作,极易导致骨髓炎及截肢,预后欠佳。ALBC覆盖治疗感染性创面能有效控制感染且简便效廉[23]。尤加省等[24]在28例下肢感染性创面清创后覆盖ALBC,术后创面细菌培养阳性率较术前大幅降低,而且C反应蛋白等全身炎症指标也较前明显好转,创面感染得到有效控制。ALBC不仅可以在感染性创面愈合初始的炎症反应阶段起到关键作用,还能够促进血小板的活化及诱导膜的形成,两者富集的生长因子能够促进血管的成熟,为创面愈合后期阶段肉芽和组织的生成奠定基础。
2.4 创伤性创面的治疗
皮肤撕脱伤在临床中多见于车祸、机器等暴力损伤,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在皮肤撕脱伤中的应用较早期疗法优势明显,但也存在因感染造成的创面愈合不佳的问题。有研究中将去甲万古霉素混入PMMA,制备成鳞片状覆盖于患者创面,并根据病情选择性使用VSD,长期随访结果显示该方法能有效抗菌,促进损伤创面的愈合[25]。王栋栋等[26]在下肢大面积皮肤撕脱伤创面的治疗中使用ALBC,结果显示感染率大幅降低,值得推广。
2.5 ALBC的联合治疗
2.5.1 ALBC联合改良胫骨横向骨搬移术(tibial transverse transport,TTT) TTT通过将截骨部位上移至血供良好且软组织丰厚的胫骨结节下方,能够较好地保护骨膜,改善DFU患者下肢血供[27]。而DFU患者往往伴有严重的感染,常规的清创手术结合抗生素治疗控制感染疗效欠佳,在清创后以ALBC覆盖创面,能够及时降低炎症因子浓度,有效控制感染,对空腔的填充也能防止死腔的形成,为TTT争取治疗时间。熊风等[28]通过对22例Wagner分级3~4级的重症DFU患者的临床研究表明,TTT通过持续牵拉刺激神经、血管等组织,能够明显改善患者下肢神经营养及血液循环,同时联合ALBC能有效控制感染,从而促进创面的愈合,对DFU患者的保肢具有积极意义。
2.5.2 ALBC联合VSD VSD目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于创面的治疗中,创面在负压下可将引流区域的细菌、脓液及坏死组织彻底排出,持续保持创面的清洁。Wynn等[29]通过系统回顾发现VSD可改变创面局部血流并减少局部水肿,负压吸引后创缘出现的高灌注有利于改善血供,促进创面愈合。然而VSD负压气密稳定性不佳时重复感染风险骤增,且其自身抗菌效果的不足易导致创面迁延难愈。ALBC具有良好的抗菌功能,可用于严重感染、脓性分泌物较多的创面,为VSD的临床治疗手段提供了新选择。陈哲等[30]对90例DFU患者的观察结果显示,VSD联合ALBC相较单独使用VSD治疗,具有感染创面细菌转阴时间短、创面愈合进展快和住院时间短的优点,骨水泥的填充能够避免死腔的形成,有利于构建无菌环境,其抗菌特性也能有效控制感染。张苏岭等[31]对90例DFU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VSD联合ALBC治疗DFU临床疗效突出,不仅能有效控制炎症反应,而且VSD能刺激创面释放多种生长因子,同诱导膜富集的生长因子一起促进肉芽组织的生长,改善足部血流,减轻肿胀程度,为后续植皮或皮瓣修复创造良好环境。
2.5.3 ALBC联合皮瓣 对于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治疗,皮瓣联合ALBC往往能取得良好的临床获益。该联合治疗方法分为两期,清创术后一期使用ALBC填充覆盖创面以控制感染,同时诱导膜的形成也为创面愈合的奠定基础;二期则在取出PMMA后仍保留诱导膜,再使用皮瓣封闭创面。方勇等[32]使用承载ALBC联合皮瓣修复慢性难愈性创面,其中DFU 27例,创伤性创面19例,骨感染创面11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皮瓣联合ALBC试验组,研究发现清创术后不同时间点的试验组创面愈合进展均好于对照组。虽然目前ALBC联合皮瓣成功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在临床上屡见报导,但其学习曲线较长,尤其是皮瓣的穿支定位严重依赖于主刀医生的主观经验,目前在临床的推广难度较大。而且该联合疗法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缺乏足够的临床研究来论证其疗效可靠性。
2.5.4 ALBC联合自体富血小板血浆(autologous platelet rich plasma,APRP) APRP是患者自身的外周静脉血通过离心分离得到的血小板浓缩物,内含有大量生长因子,在组织愈合的每个阶段均能有效促进创面自我修复,其中的抗菌肽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可用于治疗难愈性创面[33]。一项回顾性研究将60例慢性创面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清创后予以APRP外敷,观察组清创术后先植入ALBC形成诱导膜后再联合APRP治疗,结果表明联合疗法的细菌清除率、创面缩小率、肉芽组织覆盖率等指标均优于单独使用APRP治疗[34]。控制感染是APRP治疗慢性创面的前提,清创术后先植入的ALBC先释放高浓度抗生素控制感染,再通过Masquelet技术生成诱导膜,联合APRP可诱导真皮细胞DNA复制,加速细胞增殖。APRP中的高浓度白细胞和抗菌肽能够协同ALBC起到消毒抗菌的作用,而ALBC形成的诱导膜富集的生长因子也能与APRP中的生长因子一同促进创面的再血管化,从而加速创面的向愈。
3 小结与展望
目前慢性创面的传统治疗手段效果欠佳,ALBC治疗慢性创面的有效性被越来越多的论床研究论证,但其释放抗生素的稳定性及不良反应的研究尚不全面,仍需要更多循证医学证据。但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超级耐药菌在临床中日趋多见,导致ALBC的治疗效果大打折扣,给PMMA中抗生素的选择及用量带来了考验。万古霉素与PMMA搅拌后热稳定性及缓释性優秀,并且对绝大多数创面感染致病菌敏感,临床常以其作为PMMA的搭载抗生素,而对于慢性创面中定植的革兰氏阳性菌,混合庆大霉素的PMMA往往成为首选[35]。临床医生在使用PMMA时要密切关注骨水泥植入综合征及过敏反应,避免导致严重的并发症。总而言之,ALBC治疗慢性创面具有光明的前景,但其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论证该治疗手段的有效性,而且推动其临床应用标准化规范化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1] JARBRINK K, NI G, SONNERGREN H, et al. The humanistic and economic burden of chronic wounds: a protocol for a systematic review[J]. Syst Rev, 2017, 6(1): 15.
[2] GOULD L, ABADIR P, BREM H, et al. Chronic wound repair and healing in older adult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research [J]. J Am Geriatr Soc, 2015, 63(3): 427–438.
[11] GOURON R, PETIT L, BOUDOT C, et al. Osteoclasts and their precursors are present in the induced-membrane during bone reconstruction using the Masquelet technique[J]. J Tissue Eng Regen Med, 2017, 11(2): 382–389.
[20] 钟云雪, 李莉, 王达利, 等. 扩创联合抗生素骨水泥在严重感染糖尿病足溃疡治疗中的应用研究[J]. 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电子版), 2022, 17(1): 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