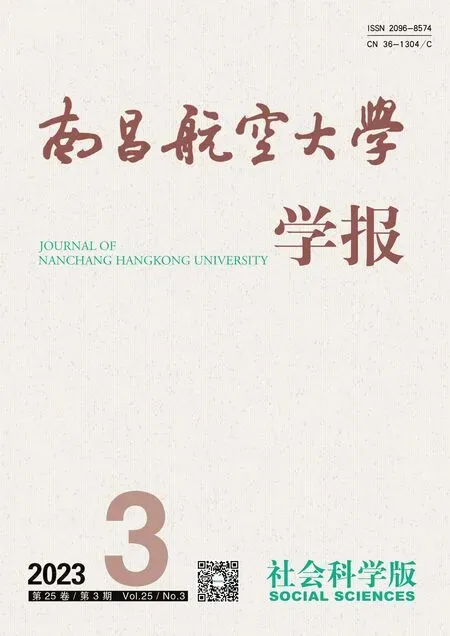新时代脱贫攻坚书写的新探索:论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
陈晨力,杨超高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南昌 330013)
当前乡村现实主义书写呈现爆发的态势,乡土文学与现实乡村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打破了以往创作类型单一、远离现实的局面,出现了一个日渐宽阔的新文学视野-脱贫攻坚主题文学。脱贫攻坚主题文学是围绕“扶贫”“脱贫”主流话语而展开的文学叙事,代表作品有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赵德发的《经山海》、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滕贞甫的《战国红》等。
四川籍作家贺享雍在这一方面有突出贡献。他是一位创作力和时代感都很强的作家,他的乡土书写承继了茅盾的写实风格与赵树理的农民立场。比如他的十卷本“乡村志”系列小说,就表现出“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1]的创作宗旨,反映出时代变革中真实的乡村面貌,包括土地流转、乡村伦理、政治生态、民主选举、乡村医疗以及养老、创业、脱贫等方面的问题。作家以志书式的实录方式,将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乡土儿女的心灵嬗变以及当下乡村的现实问题,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出来。而新近出版的“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则是在“乡村志”收官之作《天大地大》基础上续写而来的,以一个村庄(贺家湾)的命运来表现乡土中国脱贫的历程与命运。在这里,贺享雍聚焦在扶贫、脱贫领域,关注乡村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并直面扶贫中的种种问题,将中国扶贫的温暖故事和艰难历程全景式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从“贺家湾”看中国:脱贫攻坚的真实写照
和十卷本的“乡村志”一样,“时代三部曲”试图通过对一个位于川东地区的小乡村-贺家湾的细致描写与冷静观察,来反映、剖析中国乡村的历史与现实。和现实中的乡村一样,贺家湾饱经历史沧桑,记录着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映照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乡村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村庄人口的大量流失和空巢化现状,显示了当下乡村的凋敝。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外乡打工者回乡创业,标示着城乡关系的重构。现代化的村庄进入了“无医时代”,揭露了乡村医疗存在的许多不良现象。贺家湾虽然是地域的,但具有典型性,作为乡土中国的一个“窗口”,它是中国乡村历史变化的缩影,又是当下中国乡村生活的现实写照。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书写贺家湾,既是一种个体行为方式,也具有某种方法学的意义。
和十卷本“乡村志”又有些不同,“时代三部曲”属于扶贫题材的作品,聚焦于近年来的“脱贫攻坚”战役,并对其进行全面而真实的表现。作家采访、整理的《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 位第一书记访谈录》是作品素材的主要来源,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创作方式,表现出非常可贵的“现实主义”品格。小说讲述了贺家湾“第一书记”乔燕带领村民易地搬迁、控辍保学、发展产业等一系列的故事,生动展现了中国乡村脱贫的心路历程。其中,在扶贫政策的感召下,刚参加工作的乔燕主动请缨前往贺家湾担任“第一书记”是小说叙事的开始。到贺家湾后,她深入田间地头,倾听他们的真实想法,不断探索着脱贫致富的方法。最终,在村庄基层干部们的共同努力下,贺家湾顺利通过了全国脱贫攻坚第三方检查验收组的验收,贺家湾的父老乡亲实现了脱贫致富。
“时代三部曲”不仅表现出脱贫攻坚的宏大叙事,而且做到了“细节真实”,它具体地写出了乡村社会中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一方面,它真实描绘了乡村物质层面的贫困场景,展现了脱贫前底层百姓恶劣的生存环境,如贺大卯因残疾没有稳定的收入,还要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妻子,一家三口的生活非常艰难。“土坯房一共有三间,每间屋上都开有窗户,但窗子上既没有玻璃,也没有木板,只有几块破烂的塑料布在窗洞口旗帜一般随风摇曳。”[2](36)另一方面,小说还表现了部分农民的精神贫困。如贺勤不去劳动而向乔燕讨要政府物资,寡妇吴芙蓉为谋求低保资格到村委会闹事,贺世东因私人恩怨阻挠土地流转,这类“等、靠、要”的散漫懒惰思想,“红眼病”心理以及群众不配合的状况,正是脱贫攻坚的“坚”之所在。作者笔下的脱贫,并不只是政府单方面的物质援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扶志。譬如,乔燕主动提出资助贺勤的儿子读书,给予他最大的鼓励和尊重,一步步把他拉回正轨。此外,还组织贺家湾的贫苦户到模范村学习脱贫致富的经验,激发村民们的脱贫斗志,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贺享雍对这场举全国之力的脱贫攻坚战役作了理性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他没有一味地歌颂和迎合国家政策,而是客观地反映脱贫攻坚进程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例如,在贫困户精准认定阶段,贺家湾出现了信息漏报、瞒报,确认标准与实际情况冲突等复杂情况;在易地搬迁阶段,一些非贫困户不患寡而患不均,心理失衡,阻挠易地搬迁工程的进展;在产业扶贫阶段,贺小川兄妹的生态蔬菜面临着滞销。针对扶贫政策本身,作家也敏锐地发现了其弊端:由于扶贫任务安排不科学,形式主义严重,第一书记们“几乎每天都在长时间地连续加班工作,‘5+2、白+黑’成为工作常态,不是在村里走访、调查、登记,就是填表、建档等”[3](98),以致黄龙村的第一书记张文岚,因为长期劳累而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政策之间的抵牾也是一大问题,如环保评估工作的“一刀切”使已经脱贫的杨英姿和余文化被迫关掉了“养鸡场”和“养猪场”而可能返贫。最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官员不顾村庄实际情况和农民切身利益,与企业家勾结,从中获利,比如,罗书记强硬地要求全镇两万亩土地一次性流转,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体现。诸如此类的书写,更增加了小说的写实精神与真实品格。
作家还试图让小说中的人物说话,揭示出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乔燕时常思索贺家湾面临的发展困境和未来的规划,思考乡村凋敝、人才流失的现实原因,并分析打工者返乡的可能性,提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的构想,并努力培养贺波成为下一代村支书。作家将脱贫攻坚的单一主题,扩展到了乡村建设和人才培养层面,这是对一般扶贫文学的超越,如此一来作品就具有了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显示出面向未来的深远眼光。作家这样的处理方式,提升了这部扶贫史诗的思想质地,也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思想深度。
二、乡土“新人”:人物形象的有力塑造
“时代三部曲”的另一贡献,是为当代文学画廊添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性格的时代新人形象。“新人”形象的建构并不是新世纪独有的产物,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早已有之,有其自身的嬗变轨迹和历史渊源。“农村新人”形象较早可以追溯到40 年代赵树理小说中的小二黑(《小二黑结婚》)。此后,梁生宝(《创业史》)、孙少平与孙少安(《平凡的世界》)、关仁山(《九月还乡》)、曹双羊(《麦河》)也属于这一谱系。可以发现,乡土小说中的“新人”形象不断发生着裂变与新生。这些人物的出现与时代的变迁、政策的调整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贺享雍又创造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质的“新人”形象。他们与时代共同成长,体现了时代精神,承担着国家社会历史转型与乡村发展、振兴的重任。
首先是下乡扶贫的“第一书记”(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新出现的一种形象)。他们不仅有能力与魄力,而且心系乡村、无私奉献,展现出崇高的道德精神。例如,作品中以乔燕为代表的扶贫女书记群像,就呈现出这一特质。她们是时代造就的平凡英雄,她们在扶贫工作中扎根基层、融入真心,带领村委会成员开展扶贫工作,为贫困农民谋求各种生存之道。作品中,乔燕组织大家学习脱贫经验,号召实行垃圾分类和清运,建设美丽贺家湾。她还积极带领返乡农民创业,创造新的乡村致富经验。在丰产的蔬果面临着滞销时,多次进县城找销路,最终让贺家湾的无公害蔬菜注册成为了驰名商标。这些来自城市的扶贫干部身上所具有的现代性经验,成为了乡村振兴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扶贫、脱贫的过程中,乔燕也有了明显的转变与成长:从不被村民信任而遭遇尴尬到得到村民拥护,从面对问题时手足无措到能够从容应对,从与村干部时有分歧和矛盾到与志同道合的乡村干部创造“村暖花开”的美丽景象。
作为女性,她们也完成了性别角色的突围。西娜•德•波伏娃指出:“妇女是他者,她作为对象的意义是被决定的。如果妇女要成为自我,她必须像男人一样逾越所有那些限制她存在的界定和标签,她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她所希望成为的任何人。”[4]作品中的她们早已跳出传统旧女性在家相夫教子的模式,她们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事业。正如,红花村第一女书记金蓉在面对丈夫指责她不照顾家庭时,她大声地喊出:“我的事不要你管!你有你的事业,难道我就不能有我的事业?我又不是你的随身物品,要被你拴在裤腰带上?”[5](165)不仅如此,她们还试图唤醒农村妇女的主体意识。比如,乔燕积极帮助吴芙蓉争取婚姻自由,帮助其获得正当权益,开办妇女夜校,提升乡村妇女的知识素养,鼓励女性化妆美容,增强她们的自信。
在塑造这些“扶贫女书记”形象时,一方面,作家坚持人物形象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原则。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大多有现实出处,比如,乔燕的爷爷是原南江县扶贫办老主任蓝有荣,包括“七仙女”姐妹群像也是四川巴中市多位“第一书记”的混合体。然而,不同于李准笔下的李双双-一个“超我”的集体主义的无私女性,也不同于赵树理笔下的翻身农妇孟祥英-一个具有超强劳动力的“女英雄”,亦不同于丁玲晚期作品中的杜晚香-一个无私无欲、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时代三部曲”还描写了她们性格上的软弱性。她们的形象相比于前期作家塑造的丧失性别意识的女性干部,显得更为真实贴切。另一方面,作家也坚持人物个体形象与群体形象相统一的原则。作品反映的不单单是人物个人的命运、群体的命运,更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她们的个人命运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家这种“反脸谱化”的写作方式,让她们的形象更加真实立体,开辟了一条新的时代新人塑造路径。
其次是返乡农民形象,他们代表着农村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返乡农民曾经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家乡,最终又怀揣着梦想回到故土,积极投身于乡村家园的建设。例如,贺波就是一个不断成长起来的返乡型的农村“新人”形象。因当兵的缘故,在城市中,他接触到了“新农村”的概念,立志回乡改造旧农村,却一直缺乏施展拳脚的机会。后来,在乔燕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次次的锻炼,从录入贫困户信息,撰写贺家湾的灾情报告,负责修桥事宜,到组织贺家湾全村年宴。最终,贺波的乡村情怀与政治能力得到提升,成为新的贺家湾村主任。他勇于尝试新事物,接受新理念,因而成为脱贫之后、乡村振兴新的领导力量。此外,那些在城市漂泊的打工农民有着深厚的乡恋情结,在脱贫攻坚政策的开展后,毅然选择返乡创业,放弃在大城市努力打拼的事业,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外,“时代三部曲”中心系故土、回报社会的外乡农民亦是如此。他们靠着个人奋斗发家致富,却总是忘不了那片养育自己的故乡。比如,建筑公司老板蒲毅,帮助贫困家庭的学生重返校园,将上千名农民工安置在自己的建筑工地,耗费了15 年的时间把家乡的路修通。他用现代化思维管理乡村企业,开办“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农业”“新型养老院”,懂得跨界发展与融合之道,为乡村发展谋求了新的路径。这些无私伟大的企业家一同搭建起中国农村经济文化的庙宇,用实际行动演绎着故乡情感与乡土精神。这类新人形象展现了乡村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为乡土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力量。
最后,一些在乡农民也展现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有着一股向上、勤劳、坚韧和不畏艰难的精气神。相比于以往的闰土、祥林嫂以及陈奂生等农民形象,他们有巨大的超越。面对苦难的命运,他们没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是努力改变命运,成为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正如余文化小时候因一场意外落下终身残疾,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养蚕、种植果树,经营打米机和榨油机,遭遇失败却从不放弃。后来,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之下,办起了两百多亩的畜禽养殖场。不仅自己脱贫,还带动周边的贫苦户一起脱贫。他们的存在,寄托着作家对中国农民品质的颂扬。农民是扶贫的对象,只有他们发自内心的觉醒,才能真正完成脱贫攻坚这个时代任务。这些时代农村新人是社会前进的基础,作家应该为他们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写“旧人”,“时代三部曲”也有一点新意。爱•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提出了“圆形人物”的概念。小说中塑造的基层干部贺端阳就是这样的立体形象。如他说:“我算不上好人,但绝对不是坏人,这年头好人不好做,坏人最好做,不好不坏的人最难做,我只希望自己是个不好不坏的人!”[3](76)事实上,他在竞选之初确有建设家乡、为村民们办实事的梦想,也作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后来他利用关系在外面承包工程、赚取外块,给这一形象增加了“公私兼顾”乃至“以权谋私”的新特征。从他与乔燕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某些方面。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的不同常引起利益冲突,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在乔燕上任之际,贺端阳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后来又因承包造桥工程计划泡汤,二人心生芥蒂。然而,当他得知乔燕发展了他的儿子作为支部委员,渐觉自己的自私狭隘,理解了乔燕的用心,两人的误会得以消除。作为基层干部,贺端阳身上既有农民的淳朴和狡黠,又有乡村干部的智慧与能力,同样是不支持全乡土地流转,贺端阳不会像年轻的乔燕一般公然反对领导,而是懂得周旋和调解,采取灵活的方式来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时代三部曲”在讲述中国扶贫故事上的经验范式
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为当前乡土小说如何讲述中国扶贫故事提供了启发。近年来,用“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李云雷在《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中指出:“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6]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理念,而是一种具体的真实的存在,指向广阔的社会现实。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38 年就提出了文艺作品应该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此后,许多作家从不同方面书写了各具特色的中国故事。“中国扶贫故事”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属于“中国故事”的一种,那么,作家有责任去讲述那些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乃至将来可能发生的扶贫故事,参与“中国形象”的建构。这需要作家用心观察乡村社会,关注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人文精神。贺享雍一直坚持书写“当下”中国故事,对“中国扶贫故事”有着自己的思考,他的“时代三部曲”为脱贫攻坚主题文学提供了重要经验和范式。
首先,讲述中国扶贫故事要有写实性,传达出中国大地最真实的声音。正如加达默尔说:“文学其实是一种精神性保持和流传的功能,并且因此把它的隐匿的历史带进每一个现时之中。”[8]古往今来,无数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建立在反观和沉思现实的基础之上。新时代中国扶贫故事需要有一种当下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基于历史和现实进行整体性观照,这也是脱贫攻坚文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所在。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也希望在作品中找到现实社会的影子,感受到乡土中国的变化,在生动感人的扶贫故事中获得心灵的触动,建立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时代三部曲”在这些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一方面,“时代三部曲”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乡村脱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贺家湾“脏乱差”的生活环境、贫困户的识别与认定、农村土地的流转、易地扶贫搬迁中的钉子户、自然灾害后的基础设施重建、非贫困户的抱怨、返乡农民创业艰难、扶贫政策本身的缺陷等问题,几乎是脱贫路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作家将纵深的历史视野与开阔的现实意识相结合,完成“扶贫脱贫”这一重要主题的表达。另一方面,“时代三部曲”还展现了农民在扶贫过程中的性格心理和文化心态。如小说中的贺勤从一开始对政府的帮扶心安理得,到主动出门找活干;非贫困户贺世富从带领众多村民阻挠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到心平气和与乔燕畅谈贺家湾的困境和未来的发展;杨英姿和余文化在脱贫后,主动申请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还帮助同村的贫困户致富。作家在叙写扶贫故事的同时,也记录了当代乡村农民的精神蜕变。
其次,讲述中国扶贫故事还要保持必要的反思。有学者指出,“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伟大的作家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永远带有一种批判和审视”[9]。这要求作家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去发掘那些潜藏于时代深处的罅隙。作为一个长期立足乡村现实,观察乡村变化的乡土作家,贺享雍始终思考着当下中国所面临且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从《土地之痒》中的农村土地问题,《民意是天》中的政治选举问题,到“时代三部曲”所反映的扶贫、脱贫与乡村振兴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需要作家有敏锐的意识和思想深度。当然,仅仅提出问题是不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能显示作家的功力。例如,作品中对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作出了反思。乔燕发现产业扶贫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无非就是养鸡、养羊、种果树、种蔬菜。“这种雷同性扶贫产业出现的原因,还有来自上级领导的施压。简单说来,产业扶贫资金下达多少,是检验脱贫成果的一项硬指标。如果贫困户没有得到产业扶贫,帮扶就不算完成。”[10]作品中还反思了非贫困户心态失衡的真实原因,他们认为因懒致贫的贫困户得到帮扶是一种不公的体现,此外,乡村干部在执行帮扶政策时的简单粗暴,也让他们产生了逆反心理。作家站在乡土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交汇点上,思考当下扶贫、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与乡村未来,这样的中国扶贫叙事才更有深度。
最后,讲述中国扶贫故事还应当具有文学自身的审美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乡土感情让作家参与到“政治话语”的叙事中,这是令人敬畏的。但文学始终是艺术作品,有其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这并不是说文学无需“载道”的社会功能,而只是说,它首先需要建构文学自身的审美性。正如苏联文学理论家阿•布洛夫曾说过:“艺术引起人的一种称之为审美的状态,而根据艺术家本人证实,艺术创作本身的特征首先是具有这种状态,没有它,艺术作品无论如何不可能被创造出来。”[11]比如,“时代三部曲”就蕴含着浓浓的诗意乡愁,这种饱含深情又催人断肠的乡愁,构成了乡土文化的魂,并成为脱贫攻坚战略所要唤起的深层力量。作家巧妙地将贺家湾的脱贫攻坚事业与诗意风景、浓郁乡情结合在一起,将乡村振兴与农民命运相交织的一个个“小故事”如清明上河图般一一呈现,弱化了脱贫攻坚的“政策性话语”,使得贺家湾的扶贫工作得以审美化地呈现。如《土地之子》中所写:“田野上,大片大片的庄稼和蔬菜茁壮成长,到处一片葱绿。家家房前的鲜花绽放,红的红如胭脂,黄的黄似金箔。溪水沟畔、堰塘边,杨柳青青,柳枝鹅黄,一派春色。”[3](225)作家的描述展现了贺家湾旧貌换新颜的美好画面。同样,在千人团年宴中,村民们对家乡的爱和血脉相连的情是乡土最好的黏合剂,他们分享着从外地打工带来的礼物,相拥而泣,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回家的路》。
地域性书写也是审美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从乡土文学创作实践来看,鲁迅的鲁镇、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都有着显著的地域性特征。贺享雍的“贺家湾”亦是如此。地域性色彩与地方性经验是他作品中鲜明的风格印记,他的“时代三部曲”渗透着一种独特的巴中人气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运用的方言俗语,以及传达的生命哲学、文化立场,都展示着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审美个性。比如,新时代扶贫干部和农民群像,反映了巴中人在脱贫道路上的追求和精神气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排难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脱贫的信心。作家还巧妙地将一些方言俗语贯穿到小说中,这些带有不同地域性的方言俗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拓宽了文学的视野。如乔燕去看望贺世富时所说的“只带了两挂生姜”,意思是“空着两只手”[5](45),形象地表现了巴中人幽默风趣的地域文化性格。一些日常口语化的语言,如“真是贫困户,大家都帮助。想当贫困户,肯定没出路。争当贫困户,永远难致富。抢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怕当贫困户,小康迈大步。拒当贫困户,荣宗展傲骨”[2](81),也被用来宣传国家政策。这些恰到好处的日常口语取得了书面语言难以企及的传神效果。作家既从宏阔的视野去把握整个时代脉搏,又对“地方”进行艺术性的再现,从而让中国扶贫故事更具有可读性和感染力。
结语
总而言之,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表现了中国乡村底层民众的生存处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讲述了普通人在波澜壮阔的扶贫事业中的成长故事,总结了扶贫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彰显了中国农民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和力量。作家“经世致用”的问题意识、日常生活化的叙事以及地域化的风格,为讲述中国扶贫故事提供了新方法与新范式。而这些中国扶贫故事,也必将承载起一代国人的历史记忆。“时代三部曲”是历史的、当下的,又是未来的,它在乡村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描绘着乡村未来的发展;它是冷色调的,又是暖色调的,在展现乡村衰落、农民贫苦的“昨日之景”的同时,又给予了我们对乡村美好未来的愉悦畅想,因而在众多的脱贫题材作品中散发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成为“脱贫攻坚文学”中的代表。或许,“脱贫攻坚文学”能否成为一个文学潮流还有待观察,但脱贫题材的文艺答卷已经成为事实。可以相信,伴随着人类反贫困事业的进展,脱贫攻坚文学创作一定会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