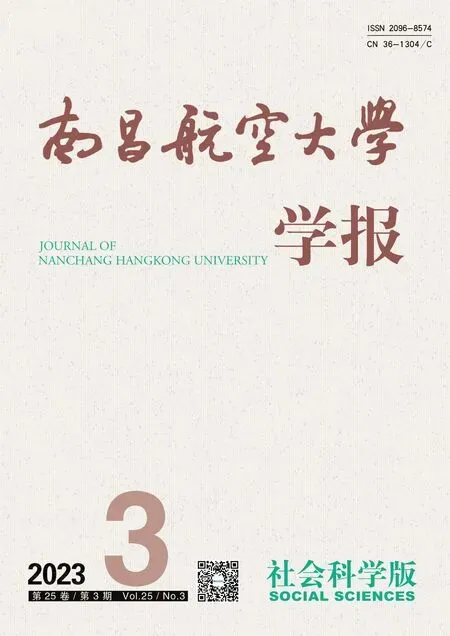主体与文本:塔奇曼和萨义德的新闻建构思想比较
张晓娴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以社会建构理论探究新闻是新闻传播研究的经典路径,从“拟态环境”“把关人”概念的提出到“框架”“场域”等理论的形成,新闻的建构性质日渐“完善”。描摹新闻建构研究的脉络,绕不开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闻室观察研究浪潮,彼时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社会学著作。其中,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1978)被视为典范,她用社会建构理论解析新闻生产过程,具有较明确的建构观①虽然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闻生产研究著作都有建构论取向,但只有塔奇曼的《做新闻》直接引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并对建构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舒德森的《发掘新闻》探究客观性观念的缘起与发展,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以个案佐证建构的方式开展论述,此二者均是间接表达新闻的历史建构特征;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虽以包罗万象的方式看问题,但未整合起一个内部结构完整的理论,建构观最不明确。参见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 [M].石林,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张斌.新闻生产与社会建构——论美国媒介社会学研究中的建构论取向 [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25-26;STONBELY S.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of the U.S.“Newsroom Studies” and the media sociology of today [J].Journalism studies,2015,16(2):266-267.。同一时期,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揭露了西方用新闻生产“东方学”话语以制造殖民合理性的行径,同样表明了新闻的建构特征。
如果只是以建构视野来理解二者的理论思想,便容易自然而然地认为研究者只是将同一理论视角移植到不同实践中,于新闻建构理论而言并无新意,于研究者个体的理论贡献而言也并无可圈可点之处。塔奇曼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与新闻建构理论的揭示被学界业界加以推崇,然而,因提出“东方学”而闻名的萨义德,其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备受关注,关于新闻媒体的讨论则被忽视。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注重实践性,主张从新闻实践活动中把握新闻与政治、国家、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方媒体生产“东方学”,现当下,国际舆论出现“中国威胁论”,新闻的建构作用在政治的运作中不仅从未退场,反而“历久弥新”。就这一意义而言,萨义德以“东方学”的新闻生产实践理解新闻建构,能为研究者在审视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问题、讨论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问题时提供新思考。探究萨义德在阐释和运用新闻建构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话题。
迈克尔•舒德森曾将有关新闻生产的研究概括为三条路径:一是政治/经济学视野,即把新闻与政治、经济结构相联系;二是社会组织路径,即研究职业意识形态,以记者决策权为中心,理解其如何受到职业惯例的限制;三是文化取向,即强调文化符号系统对新闻的约束力[2]。如果说以塔奇曼为代表的新闻室观察研究,是基于“社会组织”的论述路径的话,那么萨义德对新闻的思考,则可以归纳到“政治/文化”的研究视阈中。鉴于比较研究有助于提出问题,检视已有的解释,进而引出新的思考。因此通过比较塔奇曼和萨义德关于新闻建构的观念,可以探索不同的新闻认识论以及建构论视野下新闻具有的普遍规律,并以“对话”的方式发掘研究者关于新闻思考的独特之处。研究将在细读塔奇曼与萨义德文本作品的基础上,考察以下问题:塔奇曼和萨义德分别形成何种新闻建构观?二者如何认识新闻,有何异同?相较于塔奇曼,萨义德关于新闻建构的论述有何突破与创新?
一、主体还是文本:两种建构观
塔奇曼把新闻制作过程视为研究对象,凸显出记者的主体性,形成以主体为中心的新闻建构观;着眼于新闻生产结果的萨义德,围绕“东方学”文本讨论新闻建构性质,主张以文本为中心的新闻建构思想。
(一)塔奇曼的主体建构观
20 世纪60 年代,受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于能否客观认识社会现实这一哲学命题产生了怀疑。在此背景下,媒体行业标榜的客观性成为质疑的对象。同一时期,伯格和卢克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提出,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应纳入常识性的“知识”,强调应关注现实的社会建构[3]。基于此,塔奇曼将新闻视为日常生活中的知识,论述新闻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建构性,以“现实的建构研究”(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作为《做新闻》一书的副标题,将新闻生产视为社会建构论的一个注脚。
在《做新闻》中,塔奇曼运用解释社会学、现象学等多种理论阐释新闻的建构特征,这些理论均突显出新闻工作者的主体身份,具体如下。第一,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关注社会行动者及其主观意义的建构,因而作为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能发挥个体主动性、赋予事件以意义。第二,在现象学影响下,舒茨认为社会行动者把自然现象当作已知事实予以接受,并用“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对已有认知加以概括,于是新闻工作者在为社会实在创造寓意时,会不加质疑地运用既有经验。第三,民族方法学中的自反性(indexicality)、索引性(reflexivity)概念指出了人为因素得以嵌入新闻生产的条件,即叙述主体会对生活事件加入自身的理解使其转换为新闻,这一叙事行为会使事件产生与其原始语境无关的意义;第四,戈夫曼论述了框架可以约束主体对事件的认知,据此,记者会寻找框架以提供界定事件的方式。这些理论有共同的思维规律,即记者的能动性、主体性是创造社会意义的基础。塔奇曼依据以上理论解读新闻的生产:作为主体/社会行动者的新闻记者有个体能动性,能够理解现实、嵌入语境、运用框架、生成意义,进而对现实进行建构,“是人们的积极活动建构了社会意义”[4](175)。
塔奇曼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5],是可以“做”出新闻的主体,借此证实创造日常知识的新闻具备人为的建构成分,佐证了“对客观现实加以怀疑”的哲学命题。拥有主体性的记者是新闻得以生产的前提。因此,可以将塔奇曼的新闻建构思想提炼为以主体为中心的新闻建构观。
(二)萨义德的文本建构观
萨义德,出生于巴勒斯坦,曾接受西式教育,后赴美留学并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边缘化作为写作的主要命题。他曾言: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西方、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即使获得政治上存在的权力,也是以“东方人”身份而存在[6](35)。具有中东和英美背景的萨义德,把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身份感知融于研究,以提出“东方学”思想而闻名。实际上,萨义德对新闻媒体也有诸多讨论,有研究总结了萨义德的“媒介批评思想”[7]。不过,虽然用“媒介”一词可以概括萨义德对新闻文本、新闻记者、媒体机构等方面的认知,但是,萨义德关于新闻媒体的论述,都是围绕“东方学”的新闻文本而展开,其著作《报道伊斯兰》即为例证。故而,在此讨论的是萨义德的新闻文本思想以文本为中心的新闻建构观。
首先,需论证,在萨义德的思想中,为什么新闻是被建构的?《东方学》指出了西方生产“东方学”话语以进行文化霸权的行为。“东方学”涉及多个理论渊源,其中,福柯的“话语”观念是主要基点。萨义德说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6](4)《知识考古学》对话语的实践展开说明,揭示了语言能够建构知识[8];《规训与惩罚》论述了社会惩罚机制从公开酷刑到个体自觉接受“规训”的演变过程,说明了社会权力运作方式的隐蔽性[9],话语与权力相联系,人们用话语进行斗争[10]。在福柯的理解中,话语和权力成为复合体,权力通过话语机制的运作生产知识,知识在话语实践中维系着权力。基于福柯“话语即权力”的思想,萨义德从帝国、政治、权力的视域开展研究,揭露文化与政治的共谋关系,他将有关媒体的研究内容视为论据,论证了西方通过生产“东方”话语实行文化霸权的论点。具体来说,媒体在生成并传播有偏见的“东方”方面具有影响力,作为话语实践机构的媒体是生产“东方”文化的重要一环,因而媒体只是服务于权力的知识生产机构,所制造的新闻自有一套合乎政治目的的媒体框架,如“东方学”话语框架。既然“东方学”话语由权力所建构,那么生产“东方学”话语的新闻媒体也会受到权力建构的影响,新闻的建构作用得以澄清。
此外,萨义德曾言,自己感兴趣的是“为了宰制的帝国文化所产生的再现”[11](56)。再现(representation)是让某一客观现实在另一情境中以另一方式再次出现的行为,再现需要工具,如语言。以柏拉图的摹仿说为参照,语言对现实的描绘是镜子式的复制,再现是对现实的反映。但20 世纪以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反映论”形成了冲击,索绪尔指出,能指到所指的意指行为具有任意性。所谓意指,是主体把客体的多元含义建构为单一含义的意义锚定过程。于是再现的客观性面纱被掀开,人们认识到:语言对现实的再现通过人为的意指而实现,再现含有建构因素。在萨义德看来,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均包含了诠释成分[12](60)。新闻文本是对现实的再现,这一再现行为包含了记者的诠释,而诠释正是一种意义构建。这说明萨义德受到了社会建构思潮的影响,持有建构性的再现观,当新闻文本对现实进行再现时,其“建构性”不言自明。
进一步要回答的是,萨义德的新闻建构思想为何是以文本为中心?关于文本的思考,萨义德以“开端”(beginnings)和“现世性”(wordlyness)概念展开说明。“开端”是世俗的、人造的,是在一定意图下制造差异的行为/思维结构[13](10),对前人来说代表着断裂,对后继者而言可以缔造权威、构成认可,即文本始终恒定着创作的意图。“现世性”概念表明,文本自身并不是一个自洽性的系统,而是与其生产的语境相关,是指涉现实世界的,“文本拥有存在的方式,即使以最精致化的形式出现,也总是羁绊于境况、时间、空间和社会之中-简言之,它们是在世的,因而是现世性的”[14](56)。此外,萨义德否定德里达所持有的关于文本意义无限“延宕”的观点,认为文本通过重复性的生产可固定意义,文本会限制读者的释义方式[14](63)。根据以上内容思考新闻文本。第一,文本自诞生(“开端”)起即有一定的意图,能形成权威,具有被认可的功能。这可视为新闻文本的“互文”条件,文本的再生产将始终围绕原初意涵进行同义反复。在有意图的生产行为和可重复的操作过程中,新闻文本的建构功能得以发挥。第二,文本在生产时会“含纳”现实世界的话语,从经验现实转为语言表达的过程始终沾染着权力。也就是说,新闻生产嵌入了附和现实语境的观念,新闻文本的建构具有必然性。第三,文本对释义者而言可发挥意义框定作用,即新闻文本会形成认知框架,制约受众的读解方式。当创作者赋予新闻文本的含义成功被受众理解后,新闻文本便实现了建构的目的。
二、对新闻真实与媒体角色的认知差异
以建构论解读新闻,新闻被视为人为建构的成果,新闻文本的真实性被消融。由于塔奇曼和萨义德持有不同的“建构观”,二者对文本真实的理解、对媒体角色的定位具有一定区别。
(一)新闻真实的存在与消解
休谟探讨了关于“是”能否推出“应该”的问题[15],涉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论述。塔奇曼在主体维度下讨论新闻建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真实、客观的现实,且它是可以被主体直接认识的。这说明新闻在事实层面上含有真的成分,且主体可以对真实世界进行认识和理解,主体通过对现实的选择、裁剪和拼贴,将事件转变成新闻。此过程是主体对新闻的建构,运用了价值判断。因此,塔奇曼解构的只是新闻价值意义上的真实。
萨义德则消解了新闻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的真,在他看来,没有人能直接触及真理或真实,“我们对真实的感知,不仅依赖于我们为自身塑造的诠释与意义,还依赖于我们接收的诠释和意义”[12](60)。换言之,诠释始终横亘在主体与世界之间,是诠释决定了社会以何种方式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中,萨义德否认了人能够认识真实的可能。新闻文本是记者主体对现实世界的诠释,自诞生时即烙印了诠释/建构成分,在事实层面的真需要打一个问号。此外,文本的“现世性”特征说明诠释具有语境性。在“东方学”话语思维下,新闻的本质是为权力发声,诠释的情境特征即是为当权者(作为殖民者的西方)服务,权力会参与并谋划新闻文本诠释的方向与范围,新闻文本在价值层面也没有“真”可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新闻的真实性,认为“报刊的本质是真实和纯洁的”[16],真实性不应取决于为谁服务[17],否则新闻将成为当权者的特权,无法反映人民意志。萨义德以“东方学”话语的存在证实了西方媒体所言说的“真实”的空洞性与虚无性,西方媒体压制新闻自由、维护资本与权力的一面昭然若揭。
由此,塔奇曼认可新闻存在着事实层面的“真”,否定的是新闻价值层面的“真”,而萨义德对新闻的事实真实和价值真实都予以否认。彼得•诺维克曾言:“‘怀疑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名称与‘相对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否定存在真正的知识而后者强调知识标准的多元性。”[18]如果说塔奇曼不否认真实的存在,偏向于相对主义,萨义德则否定存在真正的知识,能够被认识的只是权力/主体装饰后的社会,倾向于怀疑主义。
(二)对媒体角色的不同界定
虽然从新闻建构论出发审视新闻,会质疑新闻的真实性,但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新闻业的价值。塔奇曼辩证地看待媒体的角色。一方面,她分析了媒体的意识形态性,认为新闻是受众认识的手段,会建构出某一知识,这种建构是权力通过压制其他观念而实现的。也就是说,新闻在排斥多元的认识维度时,会限制受众的分析性理解,新闻成为回避认识的工具,被视为使现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4](199)。但另一方面,她认识到媒体所具有的公共性价值。因记者是社会政治运动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能运用报道对事件进行选择性披露,这使新闻具有了公共性特征,譬如,关于美军对美莱村子进行大屠杀一事,屠杀报道的出现可以让受害者的死为人所知[4](179)。因此,在塔奇曼看来,媒体既服务于意识形态,也为公众发声。
相较而言,萨义德无意宣扬媒体的积极意义,而是把新闻媒体界定为权力的工具,认为媒体是政治的合谋者。依据萨义德的新闻文本建构观,意识形态锚定于文本中,文本生产时所具有的权威性、强制性特征将“涵化”(格伯纳语)记者和受众,媒体可以通过文本实现为权贵服务的目的。关于记者的论述,萨义德对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可提供思考,他指出,专业态度/职业态度(professionalism)是对不为利益所动的知识分子的威胁,所有教育体系均存在专门化(specialization)的工具性压力,这种压力会戕害人的发现感和兴奋感,使人变得怠惰、温顺[19]。媒体职业准则对记者而言是一种工具性压力。媒体的职业准则不仅包含自上而下的组织条例,也包括自下而上的新闻生产实践中的文本规则。由于新闻文本的生产自有一套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特征的操作规范,当规范形成行业规则后,将会以政治/权力/组织观念(即工具性压力)的形式存在,并作用于记者的日常实践。因此,文本规则对记者行为而言可产生约束力。就文本作用于受众方面而言,“新闻媒体在如乔姆斯基所说的制造共识中起了特殊的作用,使一般美国人觉得,应当由我们来纠正世界上的错误,管它什么矛盾与不一致”[20]。换言之,西方媒体在生产“野蛮”的东方、“文明”的西方这一文本框架时,是在塑造西方受众的共识,使其认可媒体提供的观点,并在差异性和优越感中形成阶级区隔,进而使西方宰制东方的行为在受众的“同意”甚至“拥护”下获得了“合法性”。此时,塔奇曼所言的“新闻具有让事件公之于众的公共性特征”,在萨义德这里则是新闻让意识形态“为人所知(known)”、让政治力量可见。
根据萨义德的看法,文本的生产受控于政治操纵,并始终戴着权力的镣铐作用于记者和受众。从权力到新闻业再到“东方学”文本,是“道成肉身”的过程。媒体是国家政治运作的机构,是政治授予媒体表达权甚或指定表达方式,这种“授予”凌驾于媒体职业的专业性,进而剥夺媒体所再现的对象得以阐明自身的权力,使得真实的东方被掩盖,媒体与政治的一体化特征得以阐明。
三、理解新闻建构的逻辑共识
若把社会建构理论视作理论图示,它便具有“框架”效果,这使得塔奇曼和萨义德虽然从不同的切入点认识新闻,但二人对新闻记者、文本、权力的理解具有共通性,这一共通性可视为建构场域下新闻具有的普遍特征。
(一)记者:被“位置”限定的主体
如果说对现实的建构是作为主体的人来运作,那么社会建构理论所体现的“反身性”便是:人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做新闻》论述了新闻通过哪些环节实现社会建构,呈现出新闻记者的工作日常,如记者为了实现新闻业要求的客观性目标,会按照新闻发布时间筛选新闻,或引用专家用语等策略撰写新闻。这意味着记者主体行为已被组织成功驯化,因而能生产出符合组织目的的内容;记者在建构的同时被建构,成为被安置于组织/权力系统中的某个“位置”并受其规约的主体。若以书中运用的现象学知识进行解读,记者是生活世界中的社会行动者,在用“自然态度”(对世界已有经验的默认)思考现实时,理解与阐释范围也被“自然态度”锁定。此外,在舒茨的理解中,主体的身体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是“此在”,主体将以此为中心点来组织“在场”的环境(前后左右)和时空(过去将来)[21]。记者的意识、身体都被组织所构建,主体性的发挥始终受限于“位置”。
塔奇曼认为记者的角色被限定在组织的“位置”中,萨义德也持有相似的看法。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一文中论述到:是话语让作者在言说,谁在说话不重要[22]。作者只是话语实践位置中的主体,在话语给定的位置中发挥作用。当媒体被视作“东方学”话语生产机构时,媒体成为话语实践的工具,新闻文本是为权力“说话”。记者作为书写新闻文本的作者,是权力运作的手段,是话语扩散工具的工具,其主体性让位于工具性。不过,萨义德并非直接否定记者的主体性,而是先肯定其拥有诠释能力后,再通过论述诠释的“信仰”特性,质疑记者的主体性。由于美国媒体的“信仰”具有“亲美”属性,使得美国的媒体有为美国服务的共识,此共识“塑造出新闻,决定什么是新闻以及它如何让它成为新闻”[12](68),因此记者的诠释思维也被框定,主体性的发挥受到限制。从福柯主张的话语决定论来看,话语/权力决定了包括记者在内的一切,记者的诠释限制在话语给定的有限视域之内,生产为权力所用的知识,使得新闻媒体成为扩散、确证、固化“东方学”知识的有效武器。
(二)文本:语境化的产品
塔奇曼运用民族方法学中的“自反性”“指称性”概念讨论新闻[4](178),即主体在生成文本内容时,会对现实中的悬置结构与自身已有经历进行调和,并加入自身的理解,赋予事件以意义,且文本因语境的变化会生成新含义。也即,从文本生成语境迁移到媒介语境时,新闻文本会受到生产者、媒介、技术等中介因素的影响,衍生出新的涵义。也就是说,新闻文本始终渗透着生产者所属的社会情境以及自身所依附的媒介“语境”,经语境作用后,以“结果”的方式呈现,成为一种语境化的产品。
文本的语境包含生产、传播、接纳等多个方面,塔奇曼聚焦在文本的生产语境,而萨义德的新闻文本思想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话语得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有一脉相承的关联,强调话语何以生成的情境,对语境的理解则涵盖了文本的生产行为和传播过程。首先,萨义德以“开端”与“现实性”文本观质疑了文本生产时的纯粹性。“开端”思想表明文本在出场时便含有意图,意图能框定主体的建构行为,如创造负面的“东方”形象;“现世性”特征强调文本存在的社会情境,“东方学”文本的“现世”是殖民主义语境,因而文本生产者会把殖民者的图谋赋予文本,如使用“恐怖主义”话语界定伊斯兰。其次,“理论的旅行”思想说明任一理论/观念从一处旅行至另一处时会发生“在地化”变动,因为“它势必要涉及不同于源点(point of origin)的表征和体制化进程”[14](400)。“东方学”话语的变迁即为例证:在拿破仑实施东方研究计划之前,对东方的研究是对经验的阐释-依据现实抽象出理论,而拿破仑则是在预先设定的征服目的下讲述东方-基于已有理论框架组织现实[6](103-104)。“东方学”成为权力意志的产物,有关“东方”的观念因语境的差异而被重构。
由于塔奇曼和萨义德对语境的界定有所不同,二人对文本的认识程度也有所区别。塔奇曼论述了新闻文本的被生产过程,语境是此时此地的瞬时性观念,这一语境下的新闻文本是现在进行时的取向,并未关联结构。而萨义德所论述的语境包含历史脉络与现实社会,涉及权力结构沉潜至新闻文本的过程,他认识到了新闻文本的历史性与结构性特征。
(三)建构:遮蔽权力的体现
塔奇曼曾引用史密斯的话语:“考察没说什么和没做什么要比考察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更能分析出知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她建议要检查人们如何掩盖真相的方式而不是揭示真相的方式。”[4](171)关于建构的论证,对显在的建构结果进行分析可当作直接路径,揭露被隐没的现实则可视为间接路径。
塔奇曼认为,新闻的权力体现在记者的过滤行为上。记者对于维持国家合法性的认知会反映在新闻实践中,会剔除事实的多面性,这种“能决定让一个事件不予见报的权力,体现的就是新闻的权力”[4](159)。权力会作用于记者,记者仅凸显符合政治目的的内容,通过框定事件的命名方式,控制对有关问题的争论,阻塞受众的多元认知,阻碍分析性的理解,也就阻塞了人们的质询精神以及接近真理的道路[4](172)。故而,记者对现实的筛选过程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认识事件全貌的可能,使得受众仅接受到记者所呈现的事件的部分面貌,进一步,新闻在遮蔽的权力中实现了建构。
萨义德同样关注到新闻媒体以遮蔽实现建构的权力运作方式。《报道伊斯兰》原名为Covering Islam,Covering 一词表明新闻在报道的同时也在遮蔽。萨义德以文本的化约(reduce)行为展开说明。媒体对伊斯兰的再现会为了国家的需要而化约,造成掩饰的多于揭露的,如影片《美国圣战路》呈现了穆斯林策划恐怖活动攻击美国的内容,隐瞒了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曾攻击黎巴嫩等地的历史背景,使得美国观众对伊斯兰教的憎恨导向穆斯林[12](99-101)。化约行为通过把无序、多元的现实抽象为有序、单一的主题/结论,限定了文本符号的意义。福柯认为,文本的书写行为是对言说的阻碍,萨义德借用这一论点对文本的遮蔽性加以阐述:批评家在书写时会受到现实和其他作家现成资料的干预,从而屏蔽某些写作观念,最终以对某些信息进行选择性隔离而完成书写,所留下的只是对未言说之物的缅怀[13](52-53)。这可理解为,文本会受到现实的决定性影响,仅展示出允许被呈现的一面,它始终是部分的,更多未被言说、无法言说的现实则被尘封。文本在生产时渗透进权力,甚或说,文本成为了权力本身。于是,建构本身即是遮蔽,遮蔽与建构互相实现、彼此“成就”。
四、萨义德对新闻建构论的创新
通过以上内容可发现,萨义德确证了塔奇曼的新闻建构思想。首先,萨义德曾论及塔奇曼、舒德森等人的媒体研究著作,认可已有研究中关于新闻是经过选择的观点[12](65)。从这一证据来看,萨义德承继了塔奇曼的媒体建构论,当塔奇曼以新闻生产的过程视角指出新闻存在建构行为后,萨义德用媒体生成“东方学”框架作为结果,确证了新闻的 “建构性”。其次,塔奇曼阐明,在新闻记者将现实内容转换为媒体语言的过程中,记者会对现实进行过滤,只突出“合目的性”的内容。这只能说明媒体文本内容与现实有所不同,尚无法证实媒体框架的存在,而萨义德则以“东方学”媒体框架确认这一点。再次,塔奇曼认为新闻的建构会使现状合法化,萨义德则证明新闻所生产的“东方学”框架使西方殖民行为合法化,用经验材料验证了新闻的意识形态性。
综合上述分析,通过萨义德对塔奇曼的新闻建构思想的推进,可以窥视出萨义德对新闻建构理论的创新之处。其一,萨义德将话语分析与新闻建构思想相结合,创新了新闻生产的研究方式。塔奇曼的新闻编辑室研究聚焦于主体的理解与主体间的互动,忽视了主体背后的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如,他把记者视为组织中的职业身份,未说明记者把意识形态转变为个体行为的主观化过程,附属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地位、利益关联、制度嵌入等属性均未在记者角色中得到阐明。仅以观点/理论(如“自然态度”)说明新闻融入了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是:新闻文本虽然被塔奇曼视为日常生活中的“知识”,但社会意识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并不明晰;只关注文本生产的操作流程,新闻文本被“制度化、合法化”的内在肌理均被模糊。这也使得塔奇曼对新闻的认知是“避开了历史分析,而是采取具体的逻辑分析,强调的是事件的偶然性而不是结构的必然性”[4](169),最终,得出新闻是社会现状的再生产这一结论[4](194)。无论从理论框架、论述过程,还是从研究结果来看,塔奇曼并未体现出知识生产与社会现实、文化条件之间的关联,而此“关联”才是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来源)的核心要义。萨义德则为新闻圈定了一个具体的社会语境-西方殖民文化。在此设定下,记者的身份属性表征了西方的霸权角色。记者虽然作为话语“陈述者”而出场,实则存在于话语之外,并以平台的方式搭建起意识形态与新闻机构的互动,在制度惯性下,围绕权力结构设定的殖民情境,开展“东方学话语”实践。如,以标签化命名、重复性生产、权威性确证等方式,凝聚并强化“东方学”话语的体制特征,使“东方学”成为一种专门知识甚或社会“真实”。此时,新闻文本已然跃迁为话语,新闻媒体的权力效应、政治色彩在记者与文本的互动中得到证实。
萨义德将话语与知识社会学相结合,对围绕主体建构的新闻生产研究加以推进。这可视为一种对知识社会学的话语式研究,即SKAD(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pproach to Discourse),该理论通过对知识的社会生产、流通和转化过程,论说知识以及话语的权力效应[23]。就此层面而言,将话语理论与社会建构理论相耦合,描摹符号秩序的制度化及其转化过程[24],是萨义德的创新与突破所在,也是其开辟文本式的新闻建构观的路径所在。
其二,塔奇曼和萨义德对新闻的建构态度有鲜明的区分:前者以默认的态度接受,后者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呼吁-采取抵抗行动,从实践层面发挥了建构理论的功效。在塔奇曼的理解中,新闻是可以提供认知框架的知识,也是会阻碍探询精神的意识形态,在承认了知识与权力的一体化后,得出“新闻活动的结果是使现状合法化”的结论[4](199)。这证实了新闻“是什么”,但并未回答“怎么样”,塔奇曼的批判性目标止步于“新闻是对现实的建构”这一论点。而萨义德在看待权力问题时,呼吁采取行动、积极抵抗、改变现状,不仅揭露了新闻的建构性质,而且指明了“新闻应该由谁来建构”。在倡导“批评”的人文主义思想之下,萨义德呼吁知识分子应向权势说真话,重构一种“参与式的、合作式的、非强制的再现系统”[11](57),以防止霸权再现。这体现了新闻建构理论本身能够发挥的作用。萨义德本人亦践行其所倡议的行为,他虽然身处西方,但勇于披露西方的霸权行径,并书写《最后的天空:巴勒斯坦众生相》等论著,呈现被媒体遮蔽的现实。然而,从文本的“现世性”思想出发,悖论之处显而易见。因为批评家也有“现世性”特征,并不能摆脱其身处的文化与社会,在论述所谓的“真相”时,无法确保由知识分子运作的再现行为不会产生“扭曲”。但总体而言,作为生存于西方的东方人萨义德,敢于把生存体验融于研究,并对权势加以挞伐,这是他具有现实关怀的体现。
结语
在现象学、解释社会学、民族方法学的理论影响下,塔奇曼生成了具有主体性特征的新闻建构观。在她看来,新闻价值层面的真实性在记者对客观现实的解释中被分解,具备政治性色彩的记者也赋有人文关怀,新闻媒体既为政治服务也为民众发声。萨义德借用福柯关于话语—权力的论述思考新闻,批判媒体生产“东方学”的行径,持有以文本为中心的新闻建构思想。对他而言,新闻在权力的操控下没有真实可言;媒体机构周旋于政治、资本的权力中,是权力的共谋者。不同的建构视点延展出的新闻认识论具有差异,当建构论成为一种叙事范式时,无论主体的还是文本的新闻建构,都处于思维定式中:组织牵制着记者,语境包裹着文本,压制权力发挥着建构功能。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萨义德对塔奇曼点到为止的观点加以推进:把“东方学”作为新闻框架存在的证据,说明西方的新闻的确发挥着建构作用-为西方帝国主义而效劳;将话语研究加入新闻的建构视野,勾勒出权力作用于新闻建构的痕迹,增强了新闻建构论的解释力;借助新闻能够定义现实的建构功能,呼吁知识分子重构现实,反击权力的建构。
塔奇曼的主体新闻建构观指出了记者发挥建构作用的逻辑,萨义德的文本建构观意图呼告:文本之外,绝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充斥着权力。萨义德掀开了权力借以文本的建构特征作用于新闻记者、媒体机构的层层面纱,呼吁并实践着“以建构反建构”的目标。相比于以塔奇曼为代表的新闻组织视野下的建构研究,萨义德让新闻建构论走得更远,使其接轨国际政治、世界文学。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