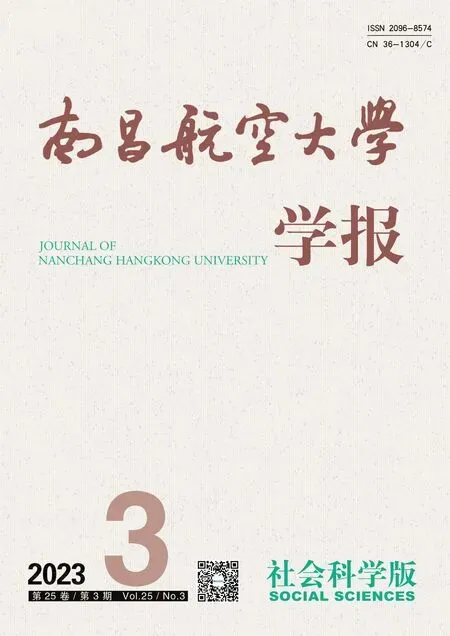接受与召唤:接受美学视野下合唱指挥的双重角色探析
王晓勇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福州 350003)
学界对一部优秀的合唱艺术进行品评,主要是针对其舞台呈现的音响文本而言。指挥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指挥主体作用进行深入探究,是推动合唱艺术向前发展的重要路径。
接受美学兴起于20 世纪60 年代的德国,正值西方后现代理论走向成熟发展阶段,其中孕育出的多个新理论,不断地碰撞出火花,对西方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接受美学理论强调文本与主体关系,重视读者的审美生产价值。就此而言,指挥在合唱艺术生产时,处于重要的“读者”位置。然而,合唱生产与文学生产相比更为复杂,指挥在参与合唱文本转换,处理合唱文本与合唱队员、合唱观众关系时,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因此,鉴于以往学界对于合唱指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指挥动作、指挥素质培养等方面,本文从接受美学视角入手,对指挥的角色进行细致地“解构”。
一、合唱文本类型及与指挥角色生成的关系
2009 年10 月17 日,上海音乐学院赵晓声教授在“多元文化中的音乐审美”专题笔会上提出了音乐的“5 个文本”说,在此基础上,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提出了“10 个文本”说,分别对应5 类主体-即作曲家、表演家、录音师、审美者、言说者。但是,人们日常研究多集中在乐谱文本、音响文本和听赏文本上[1](12)。
参照宋瑾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合唱乐谱文本的音响化主要包括前阙、中阙、后阙3 个阶段。3 个阶段中的合唱文本可以解构为“未定性文本”“感悟文本”“表演文本”“听赏文本”几大类型。合唱文本最终的动态呈现,正是各阶段不同类型合唱文本之间有效融合、转换的结果,从而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完整艺术作品。指挥一直作为重要角色参与其中并起到核心作用。从音乐的活动方式来看,通常认为,指挥(Conductor)是指“在合奏(唱)作品中的表演和诠释中指挥乐队、合唱队、歌剧团、芭蕾舞团或其他音乐组合的人”[2]。
田晓宝教授认为:“指挥的职责是与演奏、演唱者,在音乐表演实践中共同完成音乐的二度创作。其所完成的,不仅有审美意识的对象化,而且还有对象化的产品-乐曲(文本)的音响实现;不仅有音响形态的听觉呈现,而且还有通过听觉而引起的情绪、情感体验,以及与人的精神、理想和文化观念等相关的音乐审美意识的产生。”[3](71)
或许还可以认为,指挥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对音乐音响形态的调控,以手势等“体态语言”(包括眼神,甚至表情),依据音乐作品文本的“受动性”物化形态,以乐队、合唱队为对象,体现实践的超越受动的主动性-“音乐的二度创造”[3](72)。通过这样的音乐实践过程,各合唱音乐文本得以顺利地生产与转换。由此,探究指挥角色离不开对合唱文本类型、转换形式以及指挥与合唱队员、合唱观众及各文本关系等方面的解析。
(一)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合唱文本
“文本”是西方后现代理论思潮中的重要研究对象。索绪尔、福柯、巴赫金、克里斯蒂娃等思想家都从各自角度对“文本”进行分类、阐释。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推动“文本”意义从结构主义的“一元”性走向解构主义的“多元”性,不再被单一地固化为“作者”创造的孤立物。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从7 个方面列举了文本的特征[4],使文本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文本与读者间的关系开始得到关注。
接受美学兴起后,德国学者对“文本”的“解构”更为深入、细化,尤其是在与之相关的主体结合进行阐释方面更胜一筹。“读者”不仅摆脱了“消费者”的被动身份,还逾越“作者”地位,成为“文本”审美生成与再造的真正“主体”,这为“文本”分类以及意义阐释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从作者与读者视角入手,将文本分为“未定性文本”和“感悟文本”。
合唱文本生产过程中,指挥、合唱队员、观众是参与主体。其中,指挥一直参与合唱文本转换、以及处理转换过程中文本与合唱队员、观众的各种关系。促成合唱文本由“未定性文本”转换为被指挥所接受的“感悟文本”,并在指挥“感悟文本”基础上推动合唱队员“表演文本”(第二感悟文本)、观众的“听赏文本”(第三感悟文本)生产。“表演文本”和“听赏文本”是在指挥“感悟文本”基础上建构的,不是与合唱队员、观众与“未定性”文本直接发生联系。但因“表演文本”与“听赏文本”融入了主体自身的创造性,也是对作品“接受”的结果,因此,具有“感悟文本”与“表演文本”属性以及“感悟文本”与“听赏文本”属性的双文本属性。
(二)合唱文本及其特征解析
1.未定性文本
如姚斯所说:“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5]英加登称其为“未定性”。也正是说,一部合唱作品在被“他者”阐释的前后,其文本意义是不同的。因此,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下,那些未被指挥者演绎的合唱艺术作品应隶属于“未定性文本”范畴。“未定性文本”主要表现为静止的“乐谱形态”,表现为只是作为作曲家创作灵感的产物,是没有被指挥者所创造、规范的文本。然而,一部优秀的合唱作品犹如一部畅销的文学作品一样,在历时与共时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先后得到不同读者的“解读”“品评”。但这不影响其作为“未定性文本”的属性,每当它首次出现在一位新的读者(指挥者)面前时,就可以视为又一次新生命的开始。而经过指挥解读、阐释后的合唱文本,便快速进入“感悟文本”阶段。
2.感悟文本
“未定性文本”在经历了被生产过程后,便由半成品文本转化为带有主体思维、创造性的新文本形式,即“感悟文本”。其中,作为第一读者的“指挥者”,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打破了人们约定俗成地将指挥视为“尊重原作”的“督导者”或者是再现经典作品的“搬运工”的观念,融入了主体审美经验,赋予了作品新的审美意义。“感悟文本”的特征是“接受”,不同主体对作品进行接受都可以产生“感悟文本”。然而,合唱队员和观众所感悟的都是“指挥”二度创造后的合唱“文本”。从这个角度而言,合唱队员的“表演文本”是融合了自我与指挥审美经验的第二“感悟文本”。观众所生产的是“欣赏文本”,是最终的表演文本与其审美期待、欣赏经验碰撞后的文本,可称为第三“感悟文本”。借用宋瑾教授的观点:“听众在现场聆听或在非现场通过数字媒体聆听表演者表演的经典音乐作品,总是会跟他在心里所把握的该作品进行比照,从而判断表演的质量。他心里的那个作品就是第三感悟文本。”[1](16)
(三)合唱文本转换与指挥角色生成
从上面阐述不难发现,作为“未定性文本”及“感悟文本”,都与各合唱主体密切相连。指挥者在处理文本与各主体关系、主体与非主体关系的链条中,其角色经常发生改变、游移。首先,一部合唱作品转化为音响过程中,最先对“未定性文本”进行解读的是“指挥”。他成为首次融入个体创造、审美经验的“接受者”。
然而,在对文本接受的过程中,指挥的角色并没有完全固定化,接受的方向也不是单向、顺势的。指挥并非将最终的接受结果竭尽全力地“表演”出来,而是将其转化为无形的“感悟文本”,并将这些内在意识转化为肢体语言,传递给合唱队员,“召唤”“引导”他们,生产出“表演文本”。“表演文本”生成的同时,其与观众之间的“听赏文本”也同时产生。指挥作为合唱队员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以召唤队员表演激情、满足观众审美期待为己任。处于主体与文本、主体与非主体交界点的指挥,其角色也与不同文本缠绕一起,不断地变换、游移,呈现出多重性特征。表演文本对聆听者而言是客观物,是现代感知心理学S-O-R 模式中的前项S 即刺激,而听赏文本则是经过大脑储存的相关经验O 的作用(过滤、筛选或交互作用)之后形成的反应R 的感知表象。从哲学释义学观点看,听赏文本是聆听者的经验与音响文本“视域融合”的结果[6]。
二、合唱指挥的“接受者”角色
(一)指挥的“接受”职能
“接受”是接受美学的重要观点,主要是指读者审美经验参与作品创造、意蕴挖掘的过程。合唱指挥与合唱队员相比,处于宏观掌控、解读作品的位置,承担合唱乐谱文本到合唱音声文本转换的职责。指挥者作为合唱第一“感悟性”文本的生产者、策划者,扮演着最重要的“接受者”角色。他的积极介入是主体审美经验与文本结合后的初次“发酵”,通过自身的情感思想、心理结构以及自化能力对文本进行解构与重构,使得合唱作品成为被“指挥者”感知、规定、创造的文本。
(二)接受者的二度创造性
1.个性化
接受是个性迸发的过程,指挥应“是带有指挥个性色彩去诊释作品深刻内涵,具有二度创作的特性,他已不是过去音乐活动中起辅助作用的产物,而是在乐队或唱队中将静止的乐谱还原为生动音响中起关键作用的核心人物,是作品的解释者,是乐队、唱队的灵魂”[1](14)。因此,指挥与指挥之间因创造性不同,使得作品呈现出差异性。同一首合唱作品虽被无数次演绎,但最终产生的版本不尽相同。例如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指挥大师卡拉扬与阿巴多的指挥版本完全不同。相比之下,卡拉扬指挥棒下的乐团霸气十足,他对合唱的处理却较为粗枝大叶。而阿巴多的指挥虽是中规中矩,但合唱音响处理则颇为饱满、细腻。可见,在指挥者“接受”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正是主体个性的融入,赋予合唱艺术新的审美性。
2.非模仿
如上文所述,合唱指挥作为接受者,其接受过程是极具个性、创造性的。我们对于个性的强调,也是对僵化的模仿行为的一种干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指挥在向“经典”“大师”学习之时,陷入极力模仿而不能有所创新的漩涡,从而失去其作为“接受者”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将指挥的作用简单地等同于“提示者”,抹杀其阐释美、创造美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学习“经典”的全盘否定,巧妙、适当地吸收大师们的精华,有助于在指挥者心中建立一种“理想模式”,从而引导其建构具有“主体”意向的“感悟文本”。
(三)接受过程的层次性及要求
接受过程的基本层即指挥作为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解读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要按照文本中隐藏的规则、暗示进行。正如“文学本文把某些暗示性的限制强加在空白上,所以读者的想象不是漫无边际的”[7],要尊重原作轨迹、遵循作曲家创作之章法。一部合唱作品好坏与否,“主要决定于指挥把音符转换成视觉动作是否准确、以及合唱队(乐队)接受的是否准确”[8](57)。
这就需要指挥对合唱相关文本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为此,排练前期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案头工作上,对作品的创作背景、音乐本体、内涵情感、作曲家生平等都进行细致分析、准确定位。尽量“把握好这些参数,按照作曲家谱写的乐谱去正确完成谱面的技术要求”[9]。这是合唱文本还原为音声文本的基础工作,也是指挥接受过程的基本层面。此外,还要对其中的重难点做到心中有数,提前做好预案,以防止合唱排练时出现错误。这需要合唱指挥平日里通过学习、实践过程不断地积累知识,增强分析能力。
接受过程的高级层次是对作品情感内涵、审美特征、表现力进行再现和提升。这不仅需要指挥对作品进行细致的研究、掌握,在此基础上还要融入自己的主体创造性、审美经验,从而填补作品中的“空白”,赋予作品新的艺术性、审美力。可以说,基本层面与高级层面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
三、作为“召唤者”的合唱指挥
作曲家是赋予合唱艺术第一生命的建构者,而指挥家在对作品进行“接受”的过程中,为作品缔造了新的审美意义,深化了作品情感内涵,填补了原著中的种种“空白”,被视为合唱艺术第二生命的建构者。因此,从接受美学视角而言,作为第一“读者”的指挥才是合唱作品真正审美意义的生成者。没有指挥主体参与的合唱作品只能算作“半成品”。
(一)由接受角色延伸的召唤角色
接受者也好,重构者也罢,似乎都只是在强调、肯定指挥的主体“创造”作用,对其采用何种方式、何种姿态参与合唱文本转换,并没有确切的标识。因此,针对指挥者作为“读者”的特殊身份,在接受角色基础上延伸出“召唤角色”,主要是强调指挥者在解构、重构合唱作品过程中,不是单纯地通过指挥动作去“诠释”“再现”文本,而是通过一系列内在、外在的“召唤”性行为,将展示自我的舞台变为引导合唱演员情感的舞台。从而促成合唱指挥与合唱队员,合唱队员与合唱观众,合唱文本与合唱队员、观众之间视界融合,重构一部优秀的合唱音声作品,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
(二)指挥动作:召唤行为的外在显现
如前所述,指挥者在前期需要进行大量扎实的案头工作,在此基础上方可进入由自我想象和情感体验营造的艺术世界中。指挥者填满作品中预留的空白,正是作品中“召唤结构”在发挥作用。“感悟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指挥者也同时进入了“召唤者”角色,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指挥动作予以完成,完成新的“召唤结构”。其中,指挥动作、技巧成为“召唤”有效性的关键。
第一,指挥动作恰如其分。指挥动作是指挥召唤行为的外在显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著名指挥家马革顺先生曾就此问题作了深入阐释,他认为指挥的活动是以音乐中的拍子为骨骼,并在这骨架上充实以血肉和灵魂。“一个高明的指挥,能将自己的意图以恰如其分的动作告诉对方。”[10]这里,“恰如其分”4 个字道出了其中精髓。可见,指挥动作并不是越多越好,精简适度方为上策。因此,20 世纪80 年代末期,马革顺先生就针对当时指挥动作过于繁复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由繁到简、由机械到弹性的动作改革,从而达到了更好地带动合唱队员的情感、促发他们激情的目的。
第二,指挥动作空无与忘技。马革顺先生对指挥动作改革的更高层次是达到了将内在气质、动作神韵提升至“空无”“混沌”的至高境界。对此,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指挥家杨鸿年先生与马革顺先生的做法可谓是如出一辙,他将“忘记”动作视为指挥最高境界。杨鸿年先生在一次指挥《蝴蝶夫人》中的合唱《盼》时,从头到尾都没有加入一个指挥动作,合唱声音全部在他的眼神、表情中流转。旅法学者赵越胜曾回忆他观摩杨鸿年先生给合唱团排练的情形:“他左手轻轻托起,右手放在胸前几乎完全不动。只用手指开合来控制合唱队的呼吸,让歌声飘飘渺渺,绵绵不绝。突然手指并拢,乐句戛然而止,收得极干净。他并没有挥动双臂去打拍子,而是把右手放在腰间,仅用手腕的动作控制速度,带动乐队。”[11]人们常说“此处无声胜有声”,而这一时刻正是“此处无技胜有技”的最高指挥境界的体现。
(三)空白填充:召唤行为的内在表现
1.伊塞尔与“空白”理论
英加登认为艺术作品“只是一个具有各种未定点以及尚需对无数未定点予以确定的图式化结构……但在这些作品的阅读过程中,新的未定性则可能被不断地填充,并被读者的阅读投射赋予新的特征,实现未定点的完成”[12](220)。伊塞尔在此基础上,提出“召唤结构”概念,认为每个文本都有着“召唤结构”,其中“空白”与“未定点”不同,它“暗含着文本各不同部分的相互联接”[12](221)。此联接又不只单纯作为“接头”“空隙”,而需要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去填补,促进创作者与读者意识的交融。
2.表现一:赋予作品深层内涵
指挥的召唤行为之一便是填补文本中的种种“空白”。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召唤行为,虽然其终止于指挥外在语言、动作,却始于内在感悟及长期积累。例如杨鸿年先生在一次指挥学生演唱《黄水谣》的排练过程中,学生认为这个歌曲十分简单,只要把谱子唱准确并将其背下来就可以,然而杨鸿年先生却根据作品的历史背景、伴奏织体与和声等元素,指导学生将两句旋律完全相同的乐句“黄水奔流向东方”与“黄水奔流日夜忙”唱出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如图1 所示。

图1 《黄水谣》呈示部
他把两句旋律中的每个字都进行了不一样的处理。“第一段的伴奏织体用了十六分音符的分解和弦音型,音乐显得流畅轻快,展现了日寇入侵前黄河岸边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状况。‘黄’字是在日寇侵略之前,要唱得稍微靠前明亮一些;‘a’母音则明亮,与后面的‘男女老少喜洋洋’相吻合。第2 段的‘黄’字出现在‘鬼子来’之后,要唱得黯一些;‘U’母音发声位置稍微靠后一点,音色稍暗,可以联想黄河的呜咽,与‘妻离子散,天各一方’相吻合。伴奏织体则使用了柱式和弦琶音奏法,音乐情绪显得痛苦而沉重。这样唱,又更深一层地揭示了作品的内涵。”[8](61)具体如图2 所示。

图2 《黄水谣》再现部
3.表现二:满足观众期待视野
空白的填补作为指挥者召唤行为的内在表现,决定了合唱作品艺术性的高低,也决定了合唱队员的“表演文本”能否满足合唱观众的审美期待。当作品演绎得细腻、到位,情感挖掘深入,形成的“听赏文本”审美意义也就越高,标志着合唱文本从音到声的转换过程越成功。正如“音乐的圣殿在哪?不是外在的音乐厅,也不是纸上的音符,音乐的圣殿在每一个欣赏者的心里。杨鸿年从来都奉欣赏者为上帝。如果说琴弦是合唱队(乐队),拨动琴弦的是杨鸿年,那么欣赏者则是共鸣箱”[8](63)。空白的填补,虽然是指挥与合唱队员的交互行为,但是,一位优秀的指挥者不得不先考虑观众的审美期待问题。对于群体表演者,感悟文本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时候往往需要以一位表演者的意向性存在作为标准,例如指挥[12](227)。这样,最后集体共同努力形成的表演文本才具有一致性和完备性。因此,指挥者在对合唱队员进行召唤时,也是在召唤合唱观众的审美意识,观众们的审美期待在这时就能够更好地融入其中。
合唱指挥在合唱表演中既扮演着“接受者”,又扮演着“召唤者”,这两种角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地游移和转换。作为召唤者,指挥负责音乐的解释、指导、节奏、情感表达和整体音乐方向。他们使用手势、目光、指挥棒以及表情等来传达对音乐的愿景和要求。他们决定演出的速度、力度、音调以及合唱团各个声部的平衡。指挥作为“召唤者”的任务是将音乐的精髓传达给合唱团员及观众。作为“接受者”来说,合唱指挥同时也是合唱团的一部分,他们在表演中通常会与合唱团成员一起演唱,哪怕是用嘴型来示意歌词等。在这个角色中,指挥也可以认为是音乐的“接受者”,他们与合唱团员一起负责执行合唱表演的指示。
因此,在演出的过程中,合唱指挥始终不断地在“召唤者”和“接受者”两种角色之间转换。当指挥需要向合唱团传达特定的音乐要求时,他们充当召唤者,通过手势动作、指挥棒和表情、指示语言来引导合唱团演唱。而当指挥自己参与演唱时,他们又成为接受者,与合唱团员一起表现音乐。这种双重角色的转换使合唱指挥成为音乐表演的中心,他们既领导着合唱团的演出,又积极参与其中,确保音乐的表现力和质量达到最佳水平。这需要指挥具备丰富的音乐知识、演出经验以及与合唱团员长期磨合形成的默契和协作。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接受美学视角入手,将指挥角色定位于“接受者”与“召唤者”。然而,这两个角色之间并不是前后割裂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不断地游移变换。作为接受者的指挥,在融入自身审美经验,制造“感悟文本”时,其作为“召唤者”的角色也正浮出水面。指挥在制造“召唤结构”、引导激发合唱队员填补空白时,正是再次融入“创造”的最佳契机。与此同时,指挥起到了间接召唤“观众”的作用。指挥作为个体与合唱作品文本、群体合唱队之间特殊关系的连接者,在指挥实践过程中,将指挥主体对音乐文本赋予的审美认知外化实践于客体的合唱队之上,力求达到三者间的统一,以控制、平衡音乐中各种存在的关系[3](73)。
因此,指挥在合唱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完成由音符到声音的转换,这个过程对其所提出的要求也更高。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像是“悟道”。正如杨鸿年先生所提到的“忘我”境界。“忘我”不仅仅是忘掉技术,也是将自我融入音乐、融入合唱队员、融入观众审美视域中。
恰如席勒所论述的美学教育原则-“美学教育的内在驱动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建造着一个愉快的第三王国,即游戏和表现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美学教育的内在驱动力解除了人的一切关系的束缚,把人从物质上、精神上,所有强迫性的东西中解放出来……”[13],这或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之“道”在合唱指挥这种角色中的精彩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