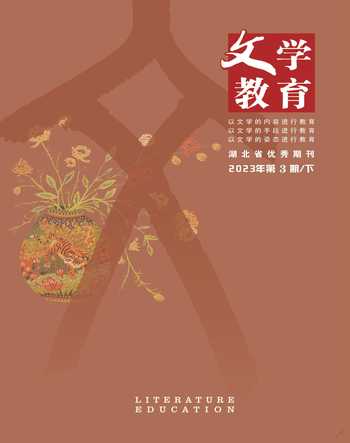试析长诗《安娜·斯涅金娜》中的叙述者“我”
张芳丽
内容摘要:具有史诗性质的长诗《安娜·斯涅金娜》是俄罗斯经典诗人叶赛宁叙事长诗创作成就的一份重要证明。诗中的主人公,即外显叙述者“我”,借助作者的自我虚构,在制造强烈在场感的同时,始终保持客观叙述者的立场,参与但不干预所述事件的进程,实现宏观历史层面与微观情感层面之间的平衡与融合,展现出叶赛宁对长诗创作技艺的稳定把握。
关键词:《安娜·斯涅金娜》 叶赛宁 叙述者
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璀璨群星之一、极具民族性的经典诗人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不仅以初入文坛即已开始创作的抒情诗见长,且在成熟于生命历程晚期的叙事题材长诗创作中亦彰显其卓越才华。具有史诗性质的长诗《安娜·斯涅金娜》即可视作对叶赛宁叙事题材诗歌创作成就的一份重要证明。该诗完成于1925年初,以发生于俄国1917年革命前后的爱情故事以及一系列真实经历为蓝本而创作。作者本人将此诗确定为抒情性叙事长诗的同时,认为它与自己写于该诗之前的作品相比,是最好的一部。
在广义叙述学视域中,“找到叙述者,是讨论任何叙述问题的出发点”。(赵毅衡2013:91)在叙事性诗歌作品中,对叙述者的判别与分析同样是解读诗歌叙事艺术的必要准备。具体而言,作者与叙述者分别作为创作主体和叙述主体,是明确分开、不可等同的两个概念。在此基础上,“叙事主体应为创作主体和叙述主体二者的有机结合,而叙事主体意识则必须要由创作主体、叙述主体和读者的参与才能真正实现。”(王莎烈2014:18)对叙事性长诗来说同样如此。然而,当作者赋予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讲述身份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始变得微妙,尤其在当“我”与作者本人在诸多方面的经历与体验有所重合,体现出鲜明的自传性特征的情况下,这时既实现了创作主体与叙述主体的有机结合,同时也成为建构叙事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这种建构难免对理解文本带来不同程度的“迷惑性”,这类叙事主体也因此对作品中的故事生成发挥独到的艺术效果,需要我们首先探清作者与叙述者的重合及分离、作者对作品的渗入程度,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均围绕叙述主体,即作者的自我虚构而展开。
《安娜·斯涅金娜》就是主人公模拟作者本人的身份展开叙述的长诗,一定程度上含有作者自传的特点,作者的自我虚构正是通过诗中的主人公,亦即叙述者“我”得以实现。
一
首先,叙述者的身份即与作者身份相近,同是一位出自农村的诗人,且作者为了向读者强调这个讲述故事的人就是作者本人,还将自己的真实名字“谢尔盖”用在叙述者身上,此外,诗中其他人物分别对应各自身份特征及言语习惯,对“谢尔盖”使用“谢尔古哈”、“谢尔贡”、“谢尔古沙”这些带有不同语气色彩的称呼,仿佛一致在证明叙述者就是作者本人。
不仅身份一致,叙述者“我”的人生经历与作者也有诸多重合之处。在长诗首章,叙述者提到曾在临时政府时期逃脱过一次兵役,当时正值克伦斯基上台执政后继续发动民众参与一战之时:在隆隆炮声中/我表现出另一种勇敢——/我成了国内第一个逃兵。(译文来源见文末注释)作者曾在写于1923年的自传中提到此事:“我自愿抛弃了克伦斯基的军队,当了逃兵,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工作,不过不是作为党员,而是作为诗人。”(谢·叶赛宁2000:111)诗中的这段叙述与作者本人的经历相符。
接下來,作者也和主人公一样在1917年春天曾回到家乡村庄,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诗中的拉多沃村,而是作者真实的出生地康斯坦丁诺沃村。从细节处可以发现,诗中对拉多沃村美丽风景的描写也与康斯坦丁诺沃村的真实面貌相符:这里林木茂盛,水草丰美,/大片的田地,足够的牧场,/整个田庄到处/都生长着挺拔的白杨。据托尔斯塔娅-叶赛宁娜讲述,拉多沃和克里乌沙其实也是当时坐落于康斯坦丁诺沃村周围的两个村庄,只是两村之间的距离比在诗中呈现的要远。在拉多沃村,主人公住进磨坊主家的第一晚,见到了那道勾起他的初恋回忆的篱笆:从前就在篱笆旁边/在我十六岁那年光景,/一位披着白色披肩的少女/对我柔声说:“不行”!这道篱笆墙与披着白色披肩的少女都真实存在于康斯坦丁诺沃村,存在于作者曾经历的真实生活中。这位少女,即出现在该诗下文的女主人公安娜,原型正是作者年少时爱慕过的康斯坦丁诺沃村地主家的女儿卡申娜。卡申娜一家所住的庄园也正是如诗中所言,有花园和一道篱笆墙,丁香也不是毫无缘故地在诗中出现,叶赛宁的妹妹回忆道:“他曾与卡申娜交好。曾从地主家花园把茉莉和丁香花带回家来。”(Есенина А.А.1986:59)当安娜·斯涅金娜在诗中正式出现后,便开始了一系列与她密切相关的情节,在第三诗章中,叙述者“我”与普隆同去斯涅金娜家,描写阁楼的这些语句对应的也正是当时卡申娜家的庄园:房子上有个阁楼。/略微前倾。/篱笆墙/散发着醉人的茉莉花香。
在第二诗章中,主人公与普隆的相识,是在从拉多沃村去到克里乌沙村时遇见的农民集会上,主人公提到,当时庄稼汉们都聚在普隆家的门廊里,主人公本人也参与其中,还收到农民们的一系列提问,正如诗中所述:只见普隆家的门廊上/一群农夫在大声叫喊。/他们正在讨论新法律,/核计牲畜和蔬菜的价钱。与此相关的是,叶赛宁的妹妹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叶赛宁于1917年和1918年都曾回到过康斯坦丁诺沃村,返乡期间不仅亲眼见证了革命事件在农村引起的一系列风波,而且频繁参加村会,常与庄稼汉们长谈。(Есенина А.А.1986:58~59) 这又成为主人公与作者经历重合的实证之一。在长诗的结尾章,六年没回乡的主人公收到磨坊主从村里寄来的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长诗的情节走向与情感选择。作者本人经过长期游历后,也是1924年夏天再次返乡,期间也曾与亲人通信,对家乡的状况保持关切。
除了事实经历外,从诗中主人公的情感体验来看,作者其实早在1912~1913年就有过与诗中主人公同在十六七岁时经历的类似愁绪与悲伤,这从作者在少年时给潘菲洛夫和巴尔扎莫娃的通信,以及早期的一系列抒情诗歌中都可以看出。诗中反映出的主人公对乡村生活的天然喜爱与依恋,也与作者本人相符。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作者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通过主人公在诗中的自我呈现,可以说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自己的真实经历以及情感体验,不断加深主人公在诗中所见所闻的可信性,这种情况下最容易使读者将叙述者与作者本人相等同。
二
诚然如此,我们仍须意识到作者的这种写法并不是以成就一篇诗体传记为最终目的。“我们只能将直接采用作者自己的名字作为作者自我虚构的一种特殊修辞方式来看待。”(谭君强2008:243)正如巴赫金所说,“作者是我们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能发现的(都能感知、理解、意识、感觉)”(巴赫金1988:308)。在叙事作品中,作者在尊重事件客观时间的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布局谋篇、情节取向的构思而成为叙事的参与者。无论作者的自我虚构与作者本人有多大程度的重合,都不能将作者等同于叙述者。
具体在这部长诗中,正如研究者马尔琴科指出的那样,作者“只是在制造最完整的、有根有据的真实性错觉”。(Марчен
коА.1972:286)她提醒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作者在一些细节处理上已经有意识地将作为诗中主人公的谢尔盖与作者本人区分开来。
首先在主人公经历的事实层面,出现在第一诗章中的磨坊主和老太婆家,并非作者返乡时真正居住的地方,而是作者為诗中主人公特意做出的选择,为的是与这两位重要的辅助人物共同拉回往事思绪,铺开情节背景。接下来,在第三诗章,在主人公返乡生病后,安娜前来探望,这也是他们在诗中的第一次见面,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我给您/读点诗吧,/关于酒馆的罗斯……/写得很清晰很严谨。/情调有点吉卜赛人的忧郁。/谢尔盖/您可真够坏的。/我感到可惜,/我感到遗憾,/您的酗酒滋事/已经远近闻名。在诗中主人公返乡的1917年,作者正专注于革命浪漫主义小长诗创作,相信革命马上就要实现庄稼汉的天堂,将俄罗斯带上另一条轨道。这段对话与作者的真实生活状态、创作经历显然不符,当时作者不仅尚未写作《小酒馆的莫斯科》系列组诗,也并未因酗酒滋事而影响声名。
继而在第四诗章,出现了在革命年代颇具典型性的查抄地主庄园的场景。在现实事件中,据亲友回忆录提供的情况,作者起初制止了同乡人自发查抄地主庄园的行动,后来查收卡申娜家族庄园是由一位布尔什维克工人在村会上带头提起并实施的。卡申娜并没有被赶出村庄,也没有远赴伦敦,而是去了莫斯科的住处,作者曾去为她送行,并对这一切情况了然于心。而在诗中,查抄事件却在一开始就由颇具讽刺效果的人物——“臭虫”拉布佳,在查抄地主庄园时带头冲在最前,并得以强制执行。“我”后来才得知并赶去看望安娜,接下来就是最后收到她已随全家远走,不知所踪的结果:抄家他倒是兵贵神速:/——交出来!以后我们再搞清楚!/他们把全庄园的人全抓到乡里。/都不放过那些牲口和主妇。
主人公在诗中目睹农村风波所积累的一些感受,实则作者将自己经过长期思想挣扎与多地游历后思考而来的状态投射到诗中尚处于1917年事件当下的主人公身上。也就是说,选取同在诗中截取的年代来对比,主人公已然比真实的作者本人更具洞察力、更有先见之明。诗中的“我”早在1917年就已感受到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将在一系列的革命与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破坏,也有料想到领导农民暴动的野蛮头子普隆最终被杀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与其下场相反的是普隆的兄弟拉布佳。诗中的拉布佳具有很多与普隆完全相反的特点:平时无事,牛皮很大,/危险一到便吓个半死。/<...>/但他依然趾高气扬,/俨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兵。就是这样一个喜好吹嘘、看风使舵的拉布佳在当时的混乱形势中仍旧得以苟活,并继续无所事事。作者使自己的人生思考以及后来对所发生事件的洞察,在主人公身上于更早的年代、于事件发生当时就得到展现,“这样的人物叙述者,一如隐含作者可以在智力和道德标准上常常高于真实作者本人一样,人们显然更无法将它与真实作者相等同。”(谭君强2008:242)主人公与叶赛宁在诸多事实层面的重合,以及在思想观念上的超前成熟度,“似乎在使读者相信诗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可靠性,同时防止读者本人简单地把长诗当成所收到的一封由叶赛宁寄来的信。”(Марченко А.1972:286)
由此我们可以验证之前的错觉,证明诗中的主人公与作者本人并完全不等同。作者在主人公身上使用了自己的某些特征性信息,而又更多地从内在层面赋予主人公以不同于自己在当时年代的成熟思想,从而得以将主人公与作者本人分离开来。
作者的自我虚构难得地在作为外显叙述者的同时,并没有干预事件发展,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与评论,而是保持着客观叙述者的身份。诗中主人公完全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述诗中事件,并保持着异常清醒与冷静的自我立场,没有将如此鲜明的自传性特征纯粹变成表达自我思想情感的工具,这也符合叶赛宁创作大长诗所表现出的整体特点。
叶赛宁在《安娜·斯涅金娜》中进行自我虚构而来的诗人谢尔盖,作为诗中的叙述者“我”,做到了尽最大可能使读者相信这是作者本人在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感,同时又始终保持客观叙述者的立场,参与但不干预所述事件的进程。宏观历史层面与微观情感层面之间的平衡与融合,展现出叶赛宁对长诗写作技艺的稳定把握,反映出对“顺应时代美学要求”的呼应,以及“一位感受到‘严峻的成熟已经到来的艺术家的强烈愿望。”(Марченко А.1972:302)
参考文献
[1][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王莎烈.叙述主体、叙事主体意识[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4(1):18~21.
[4][俄]谢·叶赛宁.玛利亚的钥匙[M].吴泽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5]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6]Есенина А.А.Родное и близкое//С.А.Есенин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G].В2т.Т.1.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6.
[7]Марченко А.Поэтический мирЕсенина[M]. M.: Советскийписатель,1972.
注:本文所引诗歌译文出自:[俄]谢尔盖·叶赛宁.叶赛宁诗选[M].郑体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259~289.
基金资助:本文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博达科研提升专项计划项目《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叶赛宁诗歌叙事研究》(课题编号:2021QNYB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