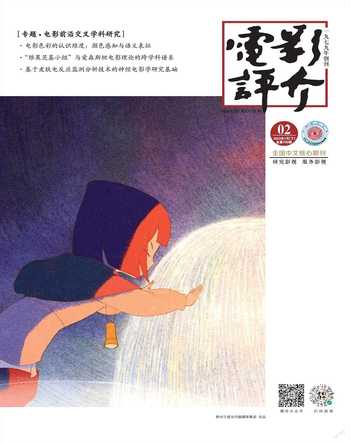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传奇”叙事下的明星“神话”转置
赵晓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中国电影明星的生产与消费提出了新要求。与之前演员匮乏和明星初起的时代不同的是,该时期明星之于电影的市场价值更加凸显。正如有学者指出:“明星的身体,包括身体的局部,不管化妆与否,都成为视觉快感和形象展示的特享区域,从而提供了一系列欲望的中转,是人与现代(西方诸国或上海国际都会)的时尚和消费文化认同。”[1]在以软性电影为代表的商业风潮之下,明星成为视觉快感的制造提供者和被凝视的对象,电影在满足观众视觉欲望的同时,亦加深与固化了明星的消费属性,并使得明星制度对演员的控制进一步加深。在这之中,以陈波儿为代表的新明星在左翼电影的传奇叙事话语模式之下,直观表现出对明星制度的反抗以至决裂,由此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生产与消費的重要方向。
一、银幕表演:作为明星的类型转置
电影明星的生产与消费和其所处的社会情感紧密相连。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在历经一定探索发展之后,本土的明星生产与消费机制逐步确立,迎合市民欲望的电影明星群体不断出现。在这一机制运转之下,类型化的银幕表现与承接现代都市欲望的幕下表演不断出现,借助媒介与资本等的合力推动,明星被构建成现代意义的市民欲望的指涉符码。对于陈波儿而言,其初期的电影实践亦指向了此种明星形象生产。1930年前后,陈波儿于上海地区从事戏剧表演活动,随后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出演电影《青春线》(1934)。在片中,陈波儿饰演为追求浮华生活而步入歧途的大学生“沈兰”,这一电影实践对其银幕类型表演影响深远。在上映之前,电影《青春线》的广告语如此写道:“舞台上曾被誉为‘小天使的陈波儿,在银幕上更显出她的美丽与天才”[2],由此不难窥见明星影片公司对陈波儿明星形象的类型生产指向,而这正是明星制度运转的重要法则。虽然该电影上映后市场反应冷淡,导演姚苏凤更是向明星影片公司负荆请罪,但却未使陈波儿的银幕实践陷入困境。根据《青青电影》的说法,电影《青春线》的市场失败反而映衬出陈波儿银幕尝试的成绩(“终以导演技术的拙劣,与配角的不配称,《青春线》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虽然陈波儿尽了她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它。”[3])可以说,陈波儿在电影《青春线》中的类型表演尝试,为之后明星影片公司“神话”的构建勾勒出了大致轮廓。
正如上文所提及,陈波儿初入银幕的类型表演成为其明星影片公司“神话”建立的重要前奏。从消费维度来看,青年学生是这一时期接受明星的重要群体,“青年学生,是很广泛的影迷群,由他们构成明星崇拜的基础。”[4]在电影《青春线》之后,陈波儿转入电通影片公司,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再次饰演青年学生“梨丽琳”。该片上映后反响热烈,陈波儿的银幕类型表演得到进一步确立。可以说,电影《桃李劫》对陈波儿的银幕形象构建有着重要意义。在《世界电影明星评传》,时人如此写道:《桃李劫》“为陈波儿在电影界奠定地位之作。”[5]《电声》杂志也对陈波儿在《桃李劫》中的银幕实践极为肯定:“故事是以失业问题为主题的,对现代社会生活颇有深刻暴露。演员方面以新星陈波儿为最佳……”[6]如果从电影文本来讲,电影《桃李劫》与《青春线》存在一定相似性——以青年的命运困境展露社会现实问题。但与《青春线》不同的是,陈波儿在《桃李劫》中并非如沈兰般走向堕落,而是积极进步但却屡遭伤害。片中人物“梨丽琳”(陈波儿饰)与丈夫“陶建平”(袁牧之饰)的跌宕命运直指时代青年的现实困境。较之《青春线》对青年人群的迷茫与沉沦的表达,电影《桃李劫》更加凸显了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对青年一代所造成的影响,陈波儿的银幕表演由此也成为青年苦难的影像言说。
从电影《青春线》到《桃李劫》,陈波儿的明星身份及内涵已发生重要折转。从文本层面来讲,电影《桃李劫》有着明显的传奇叙事特征。所谓传奇叙事,其多注重新奇的故事情节及曲折跌宕的人物命运的影像呈现。有学者认为传奇叙事有“情节的结构原则”,这一原则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奇、‘异内容的叙事选择,而且与叙事(情节)推进的动力学模式有深入关联。”[7]在电影《桃李劫》中,梨丽琳与陶建平在毕业之时意气风发,满怀希望地投身于社会建设之中,但在黑暗的现实背景之下,两人屡屡受挫,灾难不断。在历经一系列艰难苦困之后,梨丽琳患病而死,陶建平锒铛入狱,人物的悲剧结局与开篇时的壮志凌云形成鲜明对比,让整个电影的历时叙事展现出了十足的传奇性。同时,在左翼电影运动这一背景下,形成于中国早期电影的传奇叙事范式在《桃李劫》中亦发生了重要的时代嬗变,即片中人物所遭遇的曲折经历并不是《孤儿救祖记》(1923)中余蔚如式的个体苦难,而是阶层苦难的激烈控诉,这些苦难所指向的是以资本为代表的都市新权力对底层群体的集体压制。考察该时期有关此片的评价,可发现“力”这一字眼被时人多次提及,如《电声》曾刊文称《桃李劫》具有“剧的力量”[8];《青青电影》亦指出“《桃李劫》的题材接触到社会当前的问题,而使这一题材更进一步接触到大众,其效果至少可以引起更多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注意。这注意使失业者果然感动,使有工作的一般劳动者也受到感动。”[9]这些都折射出了左翼电影借助传奇叙事所形成的现实批评力度,这也让陈波儿的银幕类型表演获得广泛关注。
要讨论陈波儿这一明星文本,则需要对电通影片公司进行考察。作为由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制片公司,其在内容创作方面展现出明确的左翼指向。电通影片公司原为经营电影录音、放音的设备公司,1934年改建成为制片公司,左翼艺术家同盟力量进入其管理层,田汉、夏衍等主持工作,袁牧之、应云卫等担任导演,同时发行厂刊《电通》画报进行左翼电影宣传。虽然电通从事电影制作的时间很短(1935年5月-11月),但是生产了一批具有明确左翼指向的电影、明星,并成为1930年代反明星制度的重要阵地。正如中国电影史学家程季华所指出:“‘电通没有明星制度,有的是对整体事业的责任感,因此演员也常常做各种事务工作。”[10]对于陈波儿而言,其在《桃李劫》中饰演的梨丽琳的苦难遭遇并不局限于个体,而是象征着青年一代的集体受难,其以充满“力”的银幕表演姿态实现了左翼电影对劳工阶层的命运呈露的目的,陈波儿饰演的角色所遭受的苦难及其对苦难的承接方式,更进一步深化了电影的社会批判力度。这些角色所承载的苦难越深重,电影文本所展现出的力量也越强烈。在左翼电影的传奇叙事之下,陈波儿的银幕表演无疑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当然,电影《桃李劫》对“力”的诉诸与强调亦引发了一定争论,凸显出意识形态在电影创作领域的交锋,一些评论质疑其左翼创作思路,如《<桃李劫>毒害青年》的文章如此写道:“《桃李劫》描写青年在学校毕业以后‘无出路的问题,作者未免太显露悲观色彩,给正在奋斗的青年们在社会上得不到出路造成恶劣影响,将使有志青年灰心于前进,反而醉生梦死。其遗毒青年实非浅鲜!”[11]该文作者不仅没能直视当时中国国内的严重社会问题,还反而觉得《桃李劫》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过于深刻揭露会打击青年人的奋斗意志,其中心思想在于抨击左翼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指向。该作者在文中如此写道:“近来一般剧作家似乎多倾向于此种悲观主义,吴永刚的《神女》中有‘我不识字也过此半生的流氓;史东山的《女人》中有结局自尽的女主角,都是此种作品的榜样,今得此《桃李劫》可谓无独有偶。此种毒害青年的影片电检会似宜有所指正也”。[12]与之相似的观点亦见于其他报刊,如有文章认为《桃李劫》“只使观众看到了‘颓废‘苟取腐化的社会观念。”[13]“所以我除敢赞美《桃李劫》演出上的成功外,是不敢再赞美它意识上的成熟的。”[14]对于这些言论,时人亦针锋相对地进行回击。如一篇名为《我们的话:<桃李劫>给我们的指示》的文章便如此写到:“因此我们可以觉悟,平时叫青年忍耐吃苦的‘社会导师们不是欺骗青年去做牺牲品,就是将有用的青年送到牛角尖里去碰壁!”[15]该文指出电影《桃李劫》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桃李劫》揭穿了不少现实社会的阴险和黑暗——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然现象。”[16]同时,文章号召劳工、女性应该觉醒和奋斗:“我们痛念着所处的地位,我们更加热烈地要获得真正自由,被抛弃到职业门外的女同胞们,此刻是加紧向前步伐的时候,我们要获得光明,我们是不能退缩的……”[17]
电影《桃李劫》所遭受的双重评价,既折射出了左翼电影创作所遭遇的复杂语境,也为陈波儿明星形象的转型提供了可能。正如程季华所言:“陈波儿在《桃李劫》和《生死同心》(1936)这两部影片中的巨大成功,使她很快成为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这就给她从事公开的、合法的革命进步活动,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18]在这些电影中,陈波儿的银幕实践不再成为传统的关乎性的欲望符码,而是走向无性别化的意识形态表达。在左翼电影的传奇叙事中,陈波儿用个体的银幕身体完成了对劳工的集体话语表述,脱离了电影明星(特别是女明星)的市民欲望“神话”构建的传统方式,由此成为这一时期电影明星生产与消费新的方向。
二、幕下表述:作为劳工的话语合集
“明星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超越了演员的职业范畴,一个明星身上能够体现一种观念信息”。[19]在银幕之上,陈波儿以表演身份完成了对集体命运的表述;在银幕之下,陈波儿通过各类文化表演实现了对电影明星传统身份的进一步转置。作为20世纪30年代新兴的电影明星,陈波儿对所处时代的电影表演及其背后的明星制度有着较深刻的认识,正如其所言:“我们在银幕上所表现的都是伪想、不真切,更没有方法表现出‘力来!”[20]银幕之下的陈波儿可谓是走向了明星制的对立面,除了披露电影界黑暗与明星制的弊端外,更是对电影演员的本体地位、发展前路提出了诸多思考。
1935年,陈波儿公开发表《上了银幕以后的感想》一文,直指中国电影的现状弊端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在文中,陈波儿提到:“……我不管现在中国的电影圈子是黑到像矿山那样可怕,我还是要鼓着勇气努力地冲进去,去把那深藏着的煤精从险的黑暗圈子里带到光明的所在来。我个人固然决定了要努力向前的志趣,同时也希望我国演员们共同奋进,使中国电影艺术得以猛速发展,负起它对于社会的重要任务来,这样才不丧失了我们做演员的价值。”[21]对将明星视为视觉商品的“软性”电影,陈波儿亦发起了猛烈的批判,直指电影明星不应只依靠华丽的容貌、服装在观众间造成“虚荣的传染”[22],更不应将自身的定位局限于电影表演之中:“我们希望成就的不是单独的表演方面,不单单在求做有名的明星。”[23]陈波儿指出:“电影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工具文艺的大众化是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和左翼电影运动的方向。”[24]明星在进行银幕表演时不仅需要指向“市民”娱乐,更需要指向“大众”情感,由此才能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
1937年,陈波儿再次发表《对于新年的希望》一文,在文中就国内电影演员的处境进行了深入探讨。陈波儿指出在明星制度下,演员与电影生产被紧密捆绑在一起而无学习的时间与机会,以至沦为电影产业的工具。“我却深深地领略了电影演员的痛苦和考慮着他们的前途黯淡。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该受教育,但是每个人只有一次青年时代!”[25]在《电影艺人与读书》一文中,陈波儿再次提到电影演员的文化素养问题,指出“电影艺人最大的痛是读书问题”[26]。陈波儿认为在明星制度之下,电影演员成为电影生产的劳工。电影演员要改变自身的处境,就要拒绝成为视觉商品,并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由此可见,陈波儿不仅在银幕上将表演对准工农群体,在银幕之下更是转向演员劳工群体,其将明星视为在明星制度的运转之下被压迫的劳工阶层,是“大众”重要的构成部分。由此,陈波儿十分关注在明星制度之下作为劳工的演员的教育机会被剥夺的问题。正如其所指出:“……我认识到电影演员的痛苦生活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压迫,疲劳于无谓交际,或时刻背诵应付人事的经文,勉强摆出一副圆滑的笑脸,埋藏自己的天真纯洁。”[27]在陈波儿看来,经济原因是电影演员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很多“大众”之所以选择电影演员这一职业,最重要原因便是经济压力。即使在成为广受关注的电影明星之后,演员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依然存在。即按照陈波儿的说法:“……过去加入电影圈的,他们的动机除了少数好奇的成分之外,毫无疑问的都是背负着重要的经济责任而来的。由此我们更可推想到艺人的家庭状况,而决定了他们缺乏教育的供养。正因为教育供养不够,出身清苦,更使电影成为一些‘正人君子所鄙夷的角落。”[28]
可以说,陈波儿指出因“出身清苦”而加入电影表演行业的人并不占少数,因此,电影演员这一职业很多时候是被动选择的结果。部分演员因“负着重要的经济责任”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沦为明星制度下的生产要素以及被消费商品。陈波儿将明星职业化,即将其视作都市场域下的劳工群体,认为明星与工农阶层一样遭遇着严重的压迫问题。可以说,陈波儿反明星制的观点指出了中国早期明星文化的诸多症结,这在阮玲玉、夏佩珍以及周璇等多位电影明星的身上都有所体现。以演员夏佩珍(1908—1975年)为例,其因幼时家贫而辗转进入电影界,凭借《火烧红莲寺》(1928)等电影成为广受关注的武侠类型明星。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夏佩珍先后在《狂流》(程步高,1933)、《香草美人》(陈铿然,1933)与《女儿经》(张石川等,1934)等电影中担任主要角色。从银幕表演来看,夏佩珍可谓是该时期中国电影界重要的女明星之一。但在银幕之下,夏佩珍却无法脱离家庭的经济控制,所面临的正是陈波儿说的“经济压迫,疲劳于无谓交际”等诸多问题,并因此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而最终被明星制度淘汰出局。夏佩珍这一明星文本契合了陈波儿对中国早期电影明星文化所做出的论断。在陈波儿的表述之中,作为劳工的电影演员因经济问题而成为电影生产的工具,并在资本的剥削下失去了成长机会。而这种资本对劳工群体空间的抢夺与挤占的剥夺方式,违背了都市空间的公平逻辑。关于这一点,陈波儿在文中有着明确表述:“直至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抬头的今日,反封建的新势力认为这一行业是一种时髦的发财把戏。极力鼓吹电影之后,在这个短促的空间变幻中,虽然可以把前一时期的近视者的眼光转移或是变换,但这些本为着争取饱暖的电影工具——演员是断不能因为这短促的变幻而开发了他们在电影路上光明的前程的!原因是艺人那原来恶劣的社会背景已经决定了他们的现实生活待遇,现在要克服这个缺陷,实现艺人远大的前途,努力读书才是先决条件。”[29]
英国导演理查德·戴尔认为:“明星参与将他们生产成商品的过程,他们同时是劳动力和劳动力创造的物品。”[30]在陈波儿看来,电影明星要突破来自阶级的剥削,就必须自我奋斗,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需要指出的是,陈波儿所主张的演员“读书”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界对于演员表演的培育与道德规训有着本质区别。换言之,陈波儿认为演员进行自我提升的目的在于改变社会地位,而非迎合观众口味或者是成为道德楷模,而是需要以抗争的思想与行动去冲破明星制度的压迫。由此可见,陈波儿的幕下实践印证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对明星身份的转置,即对明星进行去个体、去性别以及去欲望化的构建后,转成劳工集体的符码。在此之下,明星生产与消费不再局限于制造视觉欲望符号,明星身份亦从视觉商品维度延展到政治层面,明星“神话”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置。
结语
较之于同时期的其他明星,陈波儿虽然从影时间较短且拍片数量较少,但是其大部分银幕实践都与青年劳工密切相关,可谓是这一阶层的银幕言说者。同时,陈波儿以新的类型表演及反明星制的幕下表述与传统明星生产进行决裂,在左翼电影实践中完成了对明星“神话”的时代重建,印证出该时期明星生产由市民“神话”想象向大众话语表述的深刻转变,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的生产与消费注入新的活力。以陈波儿的电影实践活动为研究个案亦可窥见左翼电影传奇叙事对明星去性别化、合集化的生产尝试,而这或许应该成为中国早期电影明星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作者简介】 赵 晓,男,四川巴中人,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影视文化传播与电影史论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资料发掘、整理与资源库建设”(编号:18ZDA26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美]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包卫红.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 J ]. 当代电影,2004(01):44-51.
[2]佚名.《青春线》广告[N].申报·本埠增刊,1934-12-13(008).
[3]佚名.影人小史:陈波儿[ J ].青青电影,1939(12):21.
[4]丁亚平.影像心灵: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电影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378.
[5]佚名.世界电影明星评传(中国之部)[ J ].中华(上海),1837(52):17.
[6][8]佚名.电影批评:评《桃李劫》[ J ].电声(上海),1934(50):994.
[7]虞吉.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事”的原初性建构[ J ].文艺研究,2010(11):80-86.
[9]华光.从《桃李劫》的题材说起[ J ].青青电影,1934(10):1.
[10][24]程季華等 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402,406.
[11][12]赵简明.《<桃李劫>毒害青年》[ J ].电声(上海),1935(02):42.
[13][14]克真.电影与戏剧:《桃李劫》评:银坛新人的处女作[ J ].新人周刊,1935(19):396,397.
[15][16][17]慕珍.我们的话:《桃李劫》给我们的指示[ J ].小职员,1935(03):65,64,63.
[18]程季华.巾帼英豪四十春——追寻陈波儿银幕外的历史足迹[ J ].当代电影,1991(04):22-36+2.
[19]陈刚.早期上海电影明星文化消费的形成[ J ].当代电影,2012(08):88-93.
[20][26][27][28][29]陈波儿.读书生活面面观:电影艺人与读书[ J ].读书,1937,(03):179,178,178,178,178.
[21][22][23]陈波儿.上了银幕以后的感想[ J ]. 趣味,1935(01):7-8.
[25]陈波儿.对于新年的希望[ J ].电声(上海),1937(01):45.
[30][英]理查德·戴尔.神圣的肉体:电影明星和社会[ J ].电影艺术,2009(06):9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