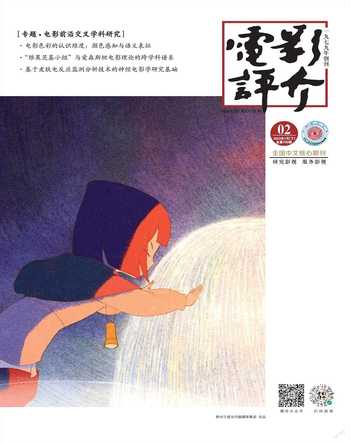新美学叙事:野兽派和点彩叙事
孟中

一、程耳电影的新美学
2016年,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虽然是之前只有《第三个人》(2007)、《边境风云》(2012)两部作品的年轻导演,但现已一跃成长为把现代叙事美学执行得较为完整、自觉的中国电影导演之一。《罗曼蒂克消亡史》用精致的镜头语言和实力派的角色演绎,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精致世俗,同时用暴力将那个时代的情欲(羅曼蒂克)撕得粉碎,令人窒息。影片整体塑造的时代感非常到位,将旧上海滩的声色犬马和波云诡谲展现得淋漓尽致。由此,程耳电影成为中国学派精致主义新美学的代名词。在导演精雕细琢的光影与画面里,程耳向美国导演昆汀致敬,将暴力美学发挥得淋漓尽致。《罗曼蒂克消亡史》所呈现的空间城市上海,是中国近代史无法绕过的城市。在这部电影中,程耳重现了上世纪60年代香港导演张彻的阳刚美学。所不同的是张彻将暴力与情义相结合,而程耳注重表现暴力,将男性与女性的缠绵情欲彻底瓦解。
“暴力美学”属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范畴,是指后现代主义文艺基本审美特征中的主体消失和深度消失,即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覆。暴力美学在电影中主要呈现在视听等感官上,即将暴力以美学的方式呈现,比如富有诗意的构图画面、艳丽的色彩,被舞蹈化、表演化的动作倾向,被装饰的血腥、凶残的暴力场面,反倒呈现出一种视觉的眩晕美感,人们惊叹于艺术化的表现形式,进而消解了暴力的残酷性,使观众来不及对内容产生不舒适感。
程耳电影的摄影与构图精致而讲究,充满中国古典的对称之美。《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场面调度非常工整细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乱世背景下,众多群像很显然没有情欲缠绵的浪漫,取而代之的是让人窒息的“杀戮”主题。暴力美学在不同文化地域中还呈现出不同的民族化风格和精神内涵。暴力美学起源于美国,本意是对死亡(悲剧)的一种态度,却在中国香港电影中成为东方电影美学。以吴宇森的“英雄系列”为代表的中国香港电影暴力美学,在美国后现代主义审美中以其神秘东方为后殖民语境,将电影中的暴力画面仪式化,将死亡的瞬间升格,使电影中的中枪、暴力场面赋予诗化,死亡成为表现英雄和解构英雄的符号。中国香港电影将暴力的形式美感发扬到诗意的极致,使中国香港电影成为暴力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吴宇森的“英雄系列”使以暴力为题材的影片不再被当成是“暴力影片”来看,这种东方电影美学的视角,第一次使暴力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1]。
纵观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三地所呈现的暴力美学,又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以好莱坞电影为向导的美国暴力美学,崇尚霸权主义,一方面臆想美国受到攻击,另一方面又在孤胆拯救地球;将美国的价值观充分表达在暴力—表现死亡过程之中。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大卫·林奇、昆汀·塔伦蒂诺等人对暴力美学进行好莱坞风格化、类型化的探索,日本导演北野武还是三池崇史的暴力美学,毫无例外地呈现出狭小民族空间所导致的生存焦虑,崇尚先发制人的暴力原则。在美日电影中,暴力被无限制放大,成为后现代电影艺术的视听奇观,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暴力美学的热潮。
程耳电影的暴力美学与中国香港电影的暴力美学完全不同,中国香港电影的东方电影美学强化的是死亡的诗意美学,特征是将死亡之花升格成诗意的慢动作来展现给人看。在价值观上对美国电影的个人英雄主义有着认同感。程耳电影的暴力美学则是以国仇家恨为核心。
在程耳电影的新美学世界中,男人和女人的情欲交织分明就是泾渭鲜明但无法融合的罗曼蒂克世界。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男人们对女人有各种情欲,既有陆先生的深爱放手,又有渡部的禁室培欲,还有贪恋风尘的女子。但相对于女人,男人们则更爱乱世,这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消亡。
程耳新美学的价值与意义在其存在本身,虽然电影的画面造型让人觉得刻意、做作,但暴力的仪式感让人们打破了美与丑的限定,看到了美的另一种可能。现实世界一直遵循的观念被消解,变得毫无意义。
程耳电影里每一个角色的死亡,都将被赋予独特的暴力美学,既有铁锹拍落时令人嗔目的暴力以及一只断掌带来的触目惊心,又有子弹乱射、血雾飞舞的枪战,这种极致的影像冲击了中国电影的新美学。
二、新美学的叙事快感
《无名》(2023)是把黑色电影视觉风格实行得较为完整、自觉的中国电影。程耳喜欢营造叙事迷局,复杂叙事是一种电影唯美主义者的执意追求,跳跃式片段叙述是作者引领观众参与的叙事游戏。《无名》的叙事与《罗曼蒂克消亡史》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重视觉的精致与艳丽,前者在继承后者视觉精致的同时,更注重叙事的方式。
“暴力美学”作为现代艺术中的反向性艺术,以反叛的游戏姿态打破泛滥而虚伪的情感。程耳电影《无名》很显然将《罗曼蒂克消亡史》所达到的暴力美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影片始终围绕在叙事方法上,冲击了中国电影的新美学。
当暴力被放置到一个情节叙事中,那就被赋予了意义,如果这个叙事中加入了过于浓厚的道德立场,那么暴力场景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受道德干扰的审美对象了。在《无名》中,程耳将暴力美学建立在主旋律的宏大叙事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名英雄们前赴后继,以生命与热血保家卫国,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在某种程度上警醒了消费文化中娱乐至死的现代人,使他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灵与肉,从而走上摆脱陈旧世界桎梏的救赎之旅。在这种主旋律意味浓厚的叙事中,暴力承载了意义。暴力情节要想成为一个审美对象,它首先必须要在叙事策略上有所特殊。而主旋律的宏大叙事确定了影片的主人公为传统悲剧的核心——英雄。一旦国家英雄被贴上暴力美学的标签,英雄之死就成为新暴力美学的核心。在《无名》中,新美学一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本质,成为一首无名英雄赞歌。
三、凌乱:电影剧作的野兽派叙事主题
电影是关于美学、情感和精神的、真相的揭示。这种真相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情感,如同程耳在电影中呈现出来对日军的厌恶与仇恨一般,是浓烈的、超乎情感的愤怒表达。这种浓墨重彩的叙事,极像野兽派绘画。野兽派是1898年至1908年在法国盛行一时的现代画流派,画家热衷于运用鲜艳、浓重的色彩,以直率、粗放的笔法创造强烈的画面效果来表现作者情感的表现主义创作方法。
程耳的电影《无名》延续了《罗曼蒂克消亡史》所创造的中国学派精致主义新美学,对视觉有着极致美感的追求。对此,导演黄建新评价说:“电影的前七八分钟就用了七八个机位,从那开始,我一直被程耳控制着在看电影,非常强烈地跟随着他。”[2]《无名》采用了程耳一贯偏好的固定镜头,很少使用移动镜头,并且景别多、画面考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视觉上的平稳与优雅。其考究的画面细节,均衡、端庄的构图、长时间的凝视感,无时无刻不传递着一种客观克制的视觉美感。固定镜头一方面削弱了导演的主观性,增强了观众的沉浸感,另一方面使镜头有了思考的空间。这种对画面美感极致追求的背后,流动着复杂人性的洪水,尽情呈现着导演对社会与人性的思考。
影片用考究的镜头语言、唯美的造型、艳丽的色彩营造出静谧又时刻会爆发的叙事张力,程耳电影成为当代中国学派精致主义新美学的典范。
如果说《罗曼蒂克消亡史》通过极具形式感的板块式结构,采用故事的时间线索与人物线索的多线索交叉叙事方式,在剧作上延续了《边境风云》的叙事风格,那么《无名》在叙事策略上则更加“疯魔”,将多线索叙事“乱剪”,用倒叙、闪回、顺叙、重复、强调、省略、放大等叙事技巧,营造出令人眼花缭乱、剑法凌厉、进而夺人心魄的叙事张力,可以说《无名》没有依靠华丽的色彩造型,而是用叙事的笔法创造出了中国电影新暴力美学的高峰。
程耳在电影《无名》中叙事手法的凌厉和混乱,如同野兽派的色彩令人嗔目,作品以直率、粗放的笔法,表现出作者对上海的浓烈情感和对1937年混乱时代的记忆。
四、细节:记忆的放大
1937年,在程耳电影《无名》中是被屡次提到的一个时间分界点。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成为中国抗日的一个缩影。《无名》对上海的书写既熟悉又陌生。“大家一想到旧上海,脑海里可能就会浮现一些元素。我一直在回避这些元素,尽量通过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环境、真实的语境去还原那个年代,营造一个更加质朴的故事。”[3]
在影片中,作者通过巨大的字幕,按照时间顺序标出了8个重要的时间点。营造了一个误读的叙事顺序,但故事讲述时却将时间和空间、人物和事件都打碎,杂糅在一起。撕碎、重组、拼贴、重复,貌似粗暴地营造了一个扑朔迷离、波谲云诡的动荡时代,在剧作策略上形成沉浸式叙事。以至于影片细节在不同破碎的片段式叙述中反复横跳,用破碎、拼贴、重复来强化唤醒观众的各自记忆,进而形成各自的影片读解。
一段沉重而混杂的历史,延续了程耳《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冷峻、精致的色调所形成的唯美视觉。影片在空间上较少表现大景别和上海全景的画面,只有日寇飞行员与名叫罗斯福的秋田犬的俯瞰视点:1938年,广州被轰炸期间,躲在防空洞的何先生看着国破山河满目疮痍,一条狗在军人的戏耍下死在了废墟间。负责这次轰炸的飞机在返航途中坠海,两名飞行员与柴犬罗斯福死亡。
在上海人眼中,上海只是被浓烟席卷的阴霾天空。程耳以防空洞外的流浪狗和日寇飞机上的军犬做对比。与之相反,大量的情节在狭小的街道和室内展开,中景的镜头给人造成心理上的压迫感。这些画面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悲怆印记。
电影《无名》的故事情节极为简单,导演将整部影片的故事都推到了背景,用冲突与人物形成叙事的无数个线头,每个观众都试图找到故事的开头,每个观众都试图分辨出人物的归属。
如同《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群像人物塑造一样,《无名》中打入汪伪76号内部高层的何主任、缱绻柔情的中统江小姐、懦弱变节的中国共产党机要张先生、笃定信念的交通员陈小姐、衣冠楚楚的汪伪特务叶秘书、多疑戾痞的冷血杀手王队长、近乎幼稚的理想主义方小姐、骑墙投机的汉奸唐部长和高深难测的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渡部等群像人物,每个人物都各有背景,都以不同的立场与方式游走在危险与混乱的城市,同时又相互紧密缠绕,使何主任与叶秘书的故事线扭结在一起。
程耳在影片中将隐喻与视听语言融为一体,尤其是对食物的细节处理,使道具、动作成为被放大的细节:被分食的排骨、替罪的羔羊、“吃不惯”的日料、血色中挣扎的呛虾等,在弱肉强食的规则下,传递出创作者的思考。
五、线头:影片叙事的开端
叙事的开端,如同故事的线头。叙事的翻转,是故事的另一个线头。在程耳的电影《无名》中,叙事的翻转并非情节的翻转,而是故事出现了第二种叙事的可能。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渡部的红人、汪伪特工叶秘书出场的第一场戏,是和冷血杀手王队长在早餐店讨论吃排骨的情节,与何主任的情节线貌似毫无关系,但是叶秘书的跳跃式动作延续,出现了故事的另一个线头。在观众的视觉暂留里,叶秘书的出场显然并非是整个故事的开端,但是两条人物线却被“公爵”所扭结。随着重复补白,作者慢慢解答前半部分为观众留下的叶秘书线头,让观众在情节流转中将剧情进行不断可能性的拼接,最终出场的“公爵”是推动全片叙事的外部驱动力。
整部影片不仅在叙事线索上扑朔迷离,而且在剧作结构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高潮之处。按照全片叙事的内部驅动力,盗取《伪满洲关东军战略地图》是全片的核心线索,即何主任与叶秘书要倾注全力完成的战略使命。导演用刺杀“公爵”这一行为作为外部驱动力,推动全片叙事的发展,使影片结尾图穷匕首见,方才出现《伪满洲关东军战略地图》,令观众惊呼这才是影片的核心叙事。
结语
《罗曼蒂克消亡史》着重于展现上海黄昏前夕的精致世俗,它的叙事是清晰的;而《无名》则侧重于展现上海沦陷后的乱世模糊、破碎的记忆,充满了危险、杀戮和血迹斑斑。程耳一方面要提醒人们1937年之前没有记忆(或者记忆没有被忘记),另一方面强调1937年之后的记忆是忘却的(不能忘却的)、混乱的、扑朔迷离的。
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和平生活是无数无名英雄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换来的,这是中国电影新美学的根基。活在当下的现代人,该如何去直面那黑暗的历史和现在呢?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的回答也许就是答案: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
【作者简介】 孟 中,男,黑龙江宁安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博士,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电影剧作理论教学研究工作研究。
参考文献:
[1][英]克莱夫·贝尔.艺术(1914)[M].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2005.
[2][3]人民日报文艺.电影《无名》导演程耳:凝视大时代下人的选择[EB/OL].(2023-01-25)[2023-01-28]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M4OTIzOQ==&mid=2650832933&idx=1&sn=01c624619f5d25f6f7a30b280c1d2299&chksm=bcc8117d8bbf986bccba5a98cdc618114844cb2a64fe963efd6a1b1ddc9275f899a01fa8dd1a&scene=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