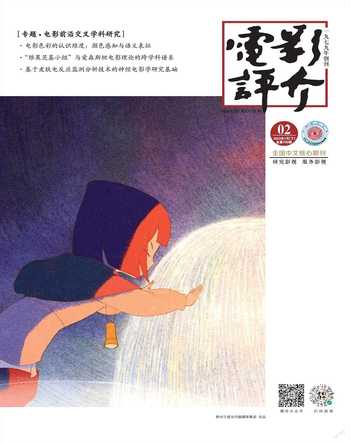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维果茨基小组”与爱森斯坦电影理论的跨学科谱系
1935年1月,前苏联电影导演、理论家谢尔盖·爱森斯坦在苏联电影工作者大會上发表了一场演讲。演讲中,他公布了彼时正在进行的、被命名为《方法》(Method)的综合性艺术理论项目。《方法》的构想是充满雄心的,爱森斯坦试图借此厘清艺术的中心问题,建立适用于所有艺术形式的分析模型,根本性地服务于艺术批评与创作实践。作为爱森斯坦引以为傲却未能于生前发表的心血,《方法》是一部宏大、多元且复杂的巨作,仅手稿就超过2500页,在不同模块下分别使用了德语、俄语、英语和法语进行写作。[1]2002年,俄罗斯电影史学家纳姆·克莱曼(Naum Kleiman)以俄文整理并出版了两卷本的《方法》;2017年,德国电影史学家奥莎娜·布加科娃(Oksana Bulgakowa)以英文对部分章节进行了翻译出版,主标题译为《原始的现象:艺术》(The Primal Phenomenon:Art)。
随着对《方法》的逐步发掘与译介,围绕爱森斯坦及其理论遗产,欧美学界展开了又一轮学术讨论。除克莱曼和布加科娃以外,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皮娅·媞卡(Pia Tikka)、朱莉娅·瓦西里耶娃(Julia Vassiljeva)、安娜·奥莲娜(Ana Olenina)、安东·雅斯尼斯基(Anton Yasnitsky)等学者均贡献出重要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讨论中,一个先前从未被注意到的跨学科视角清晰地浮现:在《方法》序言部分,爱森斯坦声明,自己是作为一支杰出团队的一员开始这项工作的,团队成员还包括前苏联文化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Luria)和历史及语言学家尼古拉·马尔(Nikolai Marr)。[2]综合各类史料与文献,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彼时被称作“维果茨基小组”(Vygotsky Circle)的知识分子联盟,在爱森斯坦理论的演进中曾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爱森斯坦,则更可能从始至终都是一名未被电影史充分认识的跨学科先驱。[3]
一、吸引力、智性情感与影像思维
爱森斯坦以电影导演、理论家身份加入“维果茨基小组”,与20世纪初期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发挥艺术的革命功能去生产和锻造“新人”。一段时间内,科学实验室、研究机构、教学机构与剧院,艺术工作室和电影摄制机构间的交流非常频繁,受国家资助的艺术实验项目也大量出现。除爱森斯坦外,库里肖夫、维尔托夫、普多夫金等电影人,以及梅耶荷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戏剧界大师,均在不同程度上主导或参与过实验性的艺术科研及创作项目。艺术与社会变革理想的交织,为科学和艺术的融合开辟了广阔的试炼场。[4]
在正式进入电影界之前,爱森斯坦曾在其导师、戏剧理论家梅耶荷德“生物力学”(Biomechanics)的舞台动作系统启发下,深度思考过演员与观众间的情感共鸣问题。在《我是怎样成为导演的》一文中,爱森斯坦回忆起一名在剧院后台观看排演的儿童,并将其称为启发自身创作与探索的“牛顿的小苹果”:
在一次排演中,我偶然瞧了瞧这小鬼的面孔(这小家伙平素总喜欢钻到我们排演休息室里来惹麻烦),不禁大吃一惊:在他的脸上,就像在镜子里似的,能够通过表情反映出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且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在台上活动的登场人物,同时还是全体登场人物的面部表情与动作。[5]
与此同时,爱森斯坦在大量阅读心理学著作时偶然发现了由英国心理学家威廉·卡朋特(William Carpenter)于1874年提出的“卡朋特效应”(Carpenter Effect)。这一心理现象指的是当观察者观察或想象一个特定动作时,通常也会引起他自己的同一块肌肉的相似性收缩。[6]结合对小男孩的观察,爱森斯坦意识到,在戏剧和电影呈现中,真正在体验和生产情感的应该是观众,而不是演员——这与俄国戏剧理论家梅耶荷德的立场是分立的。爱森斯坦坚信,演员的动作或表情会触发观众的模拟(simulation)机制,引起身体、感官上的原始反应,最终才导向情绪和情感。对此,他特别强调身体模仿是情感参与的必要条件,也是衡量其强度的标准:观众不是因为感到悲伤才流下眼泪,而是模拟演员流下眼泪后才感到了悲伤。[7]因此,艺术发挥效用的关键就在于给出可供观众模拟的强刺激,创作者则只需要对刺激类型及其组合方式进行设计,就可以经由身体中介来操控观众的反应。这一顿悟便是“吸引力蒙太奇”(montage of attractions)理论的前身与基础准备。
吸引力蒙太奇理论带有较清晰的行为主义色彩,主张在“刺激—反应”结构下理解电影的本质。这即是说,电影艺术最主要的特性是引起观众条件反射式的感官反应。这种受众关系的本质是单线、单向、单层的。对此,爱森斯坦直言不讳地宣称:“如果当时我对于巴甫洛夫学说有更多了解的话,就会把吸引力蒙太奇称作‘艺术刺激理论了”。[8]在理论和创作的互鉴之下,吸引力蒙太奇也成为爱森斯坦电影中主要的视觉手段,并被他强势譬喻为砸向观众的“电影拳头”(Cine-Fist),导演最主要的任务便是“通过组织材料来组织观众”,将艺术转化为一种可供社会革命使用的群众反应练习。[9]
不过,这一理论很快就在爱森斯坦几次对观众的观察中出现动摇。在电影放映现场,他惊讶地发现生活在城市之外的农民观众对《罢工》(1925)中屠宰场与镇压场面的并置几乎没有反馈,而以征服无产阶级观众为目标的《战舰波将金号》却意外受到德国资产阶级群体的推崇。上述现象促使他重新思考并调整关于吸引力的理论,其自我修正的突破点在于吸引力似乎不只是一种感官和心理刺激,更涉及到某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刺激。[10]在此背景下,1925年前后,爱森斯坦的好友、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介绍他结识了文化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爱森斯坦得以系统全面地阅读了后者的博士论文《艺术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Art)。在如今位于莫斯科的爱森斯坦博物馆中,陈列着一本《艺术心理学》的打印本,这是由维果茨基送交给爱森斯坦的。现有史料及研究普遍认为,这本写满爱森斯坦本人批注和笔记的书稿,标志着他与“维果茨基小组”互动的开始。
维果茨基小组也称维果茨基学派,是以维果茨基和卢里亚为主导的、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末的前苏联非官方知识分子网络。该小组以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范式(Cultural-Historical Paradigm)为中心,集结了一批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医学专家、生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维果茨基感兴趣的是人类心智在文化背景下的发展问题,他将广义上的文化视为伴随人类生产生活而产生的庞大符号系统,在对这一系统的适应、习得、使用与改造中,人类初级的心理功能得以转化为高级的心理功能。人类心理和认知的发展不全然是一个“自然—生物”的演进过程,更是一个“文化—历史”的调节过程。卢里亚则着眼于神经心理学的临床和实地考察,致力于论证大脑结构及功能如何受到文化发展的影响制约。两位科学家试图创建一种综合、全面的人类思维与大脑的科学,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艺术所引发的审美反应是其中最典型也最复杂的心智课题。对艺术本质和审美问题的共同关注,促成了维果茨基—卢里亚—爱森斯坦学术合作的前提。
通過对大量艺术作品及其引起的心理效应的分析,维果茨基在《艺术心理学》中提出,应当把艺术理解为一种中介,它处在感性系统和理性系统之间,同时影响并在这两种系统之间建立联系:
基本的审美反应包括由艺术引起的情感,我们在艺术作品中体验到的情感仿佛是真实的,但是,它却不是直接由作品本身产生,而是由被作品激发的人类想象活动所释放的……艺术的基础是感觉(feeling)和想象(imagination)的结合,它所引发的情感是一种智性的情感(intelligent emotions)。[11]
对维果茨基的详细阅读使爱森斯坦将“理性”作为必要的元素引入了审美分析之中,更使其电影美学的重心从“吸引力蒙太奇”开始向“理性蒙太奇”和“影像思维”过渡。爱森斯坦在维果茨基智性情感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了电影情感及其心理功能,认为电影情感的有效性只有在包含理性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而电影之所以能发挥它作为艺术的效用,也正是因为它允许观众通过情感模拟(emotional affective analogue)来体验和表达逻辑命题(logical thesis)。在电影中,导演把每一个逻辑命题翻译成感官语言、感官思想,最终就在观众处得到了增强的感官效果和被接收到的逻辑认知。[12]
在维果茨基和卢里亚“文化—历史”理论的整体视角下,爱森斯坦借用维果茨基提出的“内心话语”(inner speech)的概念,用这种介于思想(thought)和话语(speech)之间的中间态来类比观众观影的心理过程。较之成型的、可与他人交流的言谈,内心话语显然很难向外部敞开,也很难被他人理解,这是因为它发生在个体内部的想象与联想活动之中,既依赖于感觉和思想,又尚未彻底连贯化和逻辑化。维果茨基强调,内心话语与话语的关系不是一种静态事物,而是一个过程,是从思想到话语、从话语到思想的不断地来回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与话语的关系经历了变化,而这些变化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发展。[13]从维果茨基的论述中,爱森斯坦延伸出影像系统(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符号系统)作为象征和中介的可能性。通过《镜头以外》《电影的第四维》《电影形式的戏剧学》等一系列文章,爱森斯坦发展出建立在双重结构下的理性蒙太奇理论,吸引力蒙太奇阶段对纯粹感官和直接情感刺激的关注,并演变为一种打通了初级认知与高级认知的影像思维过程。电影在形状、色彩、声音、运动上的表现和观众对情感、叙事、意义的联想与想象,同时散落在多层次、多维度的电影结构之中,构成一种“图像—感觉—知觉”(image-sensual-conscious)的动态思维过程。在此背景下,看电影就是涉及到感官、情感和认知的有机过程。这就意味着除了初级的身体感官外,蒙太奇的组织设计还可以调控观众思维、调动观众思想,通过图像并置形成抽象的意义,进而从私人性的经验领域向着公众性的社会意识与集体思潮拓展。
作为早期电影史上极具先锋性、实验性与多元性的天才,爱森斯坦的理论体系必然是无法用线性的思路进行概括的。正如他本人在日记中所写,他更希望理论可以“创造一种空间形式,可以直接从一篇文章到另一篇,并将它们之间的关系予以赋形……循环的共时风格与文章之间的相互渗透,只能以一种球体的形式,而读者也应该根据球体的观念去转动式地阅读它们。”[14]因此,尽管理性蒙太奇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为其理论和创作的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吸引力蒙太奇及早期相关理论主张的彻底退场。在这方面,爱森斯坦高度赞同维果茨基和卢里亚对人脑发育的主张,并显然将此种模式应用到了自身的学理探索之中。卢里亚认为,大脑发育遵循一种分层的规律,“新故事、新结构建立在旧故事和旧结构之上”;同时,新旧之间保留其关联性,维持相同的工作风格和共同的因素。[15]在爱森斯坦的理论谱系中,早期的身体模拟、条件反射和审美情感等要素,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他后期对艺术中心问题的讨论中,并持续锚定着某种心理学和认知视角下的理论倾向。
二、“格兰德问题”:脑与神经的美学视角
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爱森斯坦开始大量参与到卢里亚实验室的系列实验项目中,这些实验虽然并未直接就艺术问题展开,但却为爱森斯坦理解人类意识活动提供了脑与神经的视角。1922年,卢里亚曾在《真实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a Real Psychology)一书中阐述了一个综合的心理学模型,其关键点在于强调将单一的思维现象放在整体的认知结构中进行研究。同时,个体的思维活动被认为既受生理属性决定,也受社会条件演进的影响。卢里亚的研究范式与格式塔心理学有相通之处,但其更为直接地呼应了以文化中介为导向的维果茨基理论。伴随后续对创伤、失语症及儿童脑发育等问题的临床实证研究,这种范式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神经心理学视域下的“文化—历史”方法。[16]爱森斯坦深深为卢里亚的神经探索着迷,并将其导入他后期对艺术本体的理论思考之中。具体而言,这是在卢里亚的两个研究案例中完成的。
1929年前后,卢里亚曾带队远赴中亚进行田野调查,这次调查聚焦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偏僻的农村地区,以不识字、未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少数民族妇女为对象。卢里亚通过访谈和测试,考查她们在心理分类系统和视觉空间感知上的发展程度,前者代表相对高层的逻辑推演能力,后者则代表视知觉、色觉、空间几何感等低层心理结构。考察结果显示,在没有主流世俗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字介入的地区,妇女们呈现出与儿童高度相似的认知特征。作为例证,卢里亚将一名乌兹别克斯坦成年女性和一名5岁儿童的绘画进行比较后发现,两幅画都没有按照常识性的物品关系和空间秩序进行绘制,画面的各元素间呈现出高度离散、不等比例的状态,绘画者似乎尚未受到已成型的“模式”和“系统”规范。这说明在文化介入之前,人类的感知结构是处在一种前逻辑状态之中的,包括视觉加工、空间感知、归类意识等在内的一系列基础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卢里亚将这些画分享给了爱森斯坦,后者随即在其中发现了艺术表达的一般原则。在《镜头以外》中,爱森斯坦写道:
不按比例地描绘事物是我们自来就有的天性。亚历山大·卢里亚给我看过一幅以“生炉子”为题材的儿童画…画得很认真。木柴、炉子、煙囱。但在房间中央却有一个很大的画满曲曲弯弯线条的长方形东西…这是一盒火柴。
根据火柴对于生炉子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小孩理所当然地加大了它的尺寸。
按实际(绝对)固有的比例表现事物,只是遵守正统的形式逻辑,服从不可违拗的事理…实证主义的现实主义绝不是正确的感知形式。而只不过是一定形式的社会机制…灌输的一种职能。[17]
对爱森斯坦而言,卢里亚的这些示例证实了他围绕艺术原理进行的假设,即恰恰是一种儿童式的、前逻辑的原始思维在艺术的形式、方法并尤其是功能中起到关键作用。这或许需要结合他关于“狂喜状态”(ecstatic state)的思考来理解。狂喜这一出现在宗教仪式中的词汇被爱森斯坦用于描述艺术欣赏过程中忘我的、人与自然世界完全统一的类似催眠的感受。在对一件艺术作品的狂喜感知中,艺术激活了观众大脑向前逻辑的感官思维转变,使旧有的理性规约暂时被抑制。也就是说,艺术会使人“退行”到卢里亚所观察到的儿童心理状态。不过这种退行在爱森斯坦看来似乎是以进化为目的的,因为它事实上为艺术建立新的逻辑秩序和新的意识观念预留出了空间。
在与维果茨基和卢里亚的深度互动中,爱森斯坦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艺术作品中存在两重对立统一的力量:一个是“向上”通往理性、逻辑、认知、意识的力量;另一个是“向下”诉诸感官、情感、非理性与无意识的力量。这两种力量虽然看似对立,但却以互逆互通的方式构成接受者整体性、有机性的心理认知过程。爱森斯坦从卢里亚的研究中了解到,在人类不同进化阶段下调节心理运作的规律,其实是依靠大脑的结构和机制实现的。在更高级的认知发展过程中,这些结构和机制依然存在。因此,人类的思维在不同的进化阶段下都会同时运作。延伸到艺术领域,爱森斯坦认为,这是艺术可以作用于全人类的科学前提:艺术作品的结构恰好落入人类意识结构之中——艺术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符合人类心智在逻辑思维和感官思维的脑与神经构造。
爱森斯坦将这种能够决定艺术效用的根本规则称之为艺术的中心问题,并使用德语词“格兰德问题”对其进行定义。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的《方法》写作中,曾经在爱森斯坦论述中呈现出的二元对立性逐渐演化为一种整合性、统一性的大意识结构,而在具体行文中,他常使用的措辞也由“蒙太奇”“影像”等转向了更有宏观意味的“方法”。对此,德国学者奥莎娜·布加科娃相当直率地指出,在《方法》的探究中,爱森斯坦真正分析的已经是人的意识而不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事实上充当了人类意识的痕迹与烙印。[18]
如果说卢里亚的田野考察为爱森斯坦开辟出以人类意识为核心目标的理论路径,那么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爱森斯坦与卢里亚的另一位研究对象所罗门·舍列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y)的互动,则直接启发了他关于电影创造性、表现性的方法论。舍列舍夫斯基是前苏联一位著名的记忆能力者,也是卢里亚享誉全球的著作《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中的主人公。除了“从不忘事”的超强记忆力之外,舍列舍夫斯基还被证明具有强大的图像化记忆,而这种图像化记忆背后联系着的其实是一种贯穿始终的联觉(Synesthesia)能力。1933年起,爱森斯坦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舍列舍夫斯基,并与他展开了一系列谈话和讨论,在《蒙太奇》《论色彩》和《垂直蒙太奇》等一系列文章中,爱森斯坦都充满激情地提到了舍列舍夫斯基的例子,并将其称为“S同志”。
联觉源自古希腊语synaisthêsis,前缀syn指“整合到一起”,aisthêsis则指“知觉”。[19]在当代以认知神经科学为代表的认知与心理研究中,联觉的本质是一种多模态的感官整合能力,即特定的刺激在引起固定模态系统的响应外,还触发了其他感觉模态的感知反应。在爱森斯坦对“S同志”的观察中,他发现后者听到的声音全部是有形状、颜色和亮度的,舍列舍夫斯基也在《记忆大师的心灵》中汇报过与爱森斯坦的交谈,并称爱森斯坦的声音听上去“好像一束纤维突出的火焰正朝我扑来”。[20]
对于一个全心思考电影艺术本质及其前景的青年理论家而言,“S同志”是极其难得的复合体。因为这种通感式的认知能力,一般只会出现在人类的幼年,随着逻辑、理性和日常社会经验的逐步加入,这种能力就会受到抑制,而被约定俗成的感知模式所取代。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在文化中介作用下由理性遮蔽掉原始感性的进化过程。不过,对于艺术尤其是电影而言,这种进化的结果似乎缩减了影像与观众的互动空间,并以一种规范性的对等关系约束了情感和意义的表达域,使电影走向直观记录的现实主义,而这正是爱森斯坦一贯主张突破的。
在《论色彩》中,爱森斯坦通过诗人兰波《十四行诗》中的第一行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A,黑色;E,白色;I,红色;U,绿色;O,蓝色”。爱森斯坦强调,普通读者之所以无法理解这句诗中元音字母与颜色间的对应关系,正是因为在普通人的内在认知系统中已形成规范化的模态制约,而一个正常人只有超越了常规的界限,才能将这种通感和联觉能力发挥出来。爱森斯坦也承认,除了少数艺术家和医学病理学中退行型的患者之外,常人的联觉在强度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难以被辨认的,但“S同志”的特殊性似乎说明这种来自于人类童年时代的原始能力是有可能与发育后的成人认知能力共存的。因此,在大脑与日常功能隔绝或在一些抽象的问题上极度专注时,人的认知和行为就会暂时脱离由中介经验所施加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爱森斯坦认为人就会很容易回到联觉的状态之中。[21]对于电影艺术而言,如果通过联觉体验使观众暂时进入到未被理性彻底占据的早期感官思想阶段,也就意味着艺术的“幻术”成功俘虏了它的受众,并能够将更多先锋、多元、进步的形式和理念注入其中。对此,爱森斯坦在《方法》的手稿中写道:
当艺术“抓住”观众时,观众注定要进入感官思想的现实,在那里他将失去主观和客观的区分,在那里他通过部分感知整体的能力将得到加强,在那里颜色将会唱歌,在那里声音将获得形状,在那里这个词将迫使他做出反应,就好像艺术所描述的事件确实发生了一样。[22]
爱森斯坦后期的理论整体走向一种系统化的整合,这种整合事实上配合了电影史上色彩与声音等新元素的进入,并将影像接受放置在人类心智(mind)的背景之下进行考查。在此,爱森斯坦的理论视角与当代神经电影学的基本观念产生了微妙的呼应,即二者都将电影视为落入人类意识结构内的综合性多模态系统。在回顾《总路线》的拍摄时,爱森斯坦就曾提出视听感官之间的联觉对等原则,认为镜头对视听元素的组织不应沿分立的通道进行。视听之间的配合逻辑,既不能依赖于纯粹感官的生理规律,也不应依赖于高度象征的表征逻辑,而是应该建立在电影所需的特定功能和情绪之上。爱森斯坦坚持认为,电影镜头组织应该由一个新的统一公式——“我感觉”来控制,而不是两个公式——“我看到”和“我听到”来控制。[23]作为需要不断更新的图像、声音、语言、色彩的综合系统,电影元素间固定的、一劳永逸的、绝对的对应,或者说一种相互联系、制约的法则,都将有可能损害电影艺术的本质。从这一点上看,尽管爱森斯坦的理论驳杂庞大,但始终有一条恒定的主线贯穿,即对电影艺术的生命力、创造力及其走向社会场域内生产力的重视。这种重视与对人的了解和开发结合在一起,使电影研究跃出了单一的理论场域,在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发挥作用。
结语
本文结合已有史料及研究,讨论了爱森斯坦与“维果茨基小组”在近百年前的跨学科互动,并尝试从爱森斯坦理论的检视中发现文化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学术驱动力。当下,伴随着对宏大理论及其方法的反思,电影理论正在经历着所谓情动研究、认知主义、数字人文等多重转向。在此过程中,理论的跨域对话性以及对具体情境的降落和贴近性,正在重新回到主流视野。而当人们以前沿和交叉的视角去重读爱森斯坦时,无疑会寻获到一种跨越百年的微妙对应。在对于当下正在发展的神经电影学、神经美学、媒介认知研究等前沿交叉领域而言,爱森斯坦的跨学科实践与理论路径无疑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范式,有助于持续探索电影、艺术、世界与人类自身。
【作者简介】 王娅姝,女,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师资博士后,博士,主要从事电影史论、影像认知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神经电影学视角下的影像接受研究”(编号:2021NTSS7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Oksana Bulgakowa.Eisenstein,the Glass House and the Spherical Book:From the Comedy of the Eye to a Drama of Enlightenment[EB/OL].http://www.rouge.com.au/7/eisenstein.html.
[2]Oksana Bulgakowa.From Expressive Movement to the Basic Problem:The Vygotsky-Luria-Eisenstein Theory of Art[A].in Anton Yasnitsky,René van der Veer,Michel Ferrari(eds).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ultural-Historical Psycholog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426.
[3]Pia Tikka.Enactive Cinema: Simulatorium Eisensteinense[D].the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Helsinki,2008:17.
[4][22]Julia Vassilieva.The Eisenstein-Vygotsky-Luria Collaboration:Triangulation and Third Culture Debates[ J ]. Projections,2019:24,39.
[5][8][俄]谢尔盖·爱森斯坦.爱森斯坦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494.
[6]William Carpenter.Principles of mental physiology[M].New York:Appleton,1874:316.
[7]William James.Psychology[M].New York:Henry Holt,1904:34.
[9]Maria Belodubrovkaya.The Cine-Fist:Eisensteins Attractions, Mirror Neurons,and Contemporary Action Cinema[ J ].Projections,2018(01):2.
[10]Sergei Eisenstein.Selected works:Vol.1:Writings 1922-1934[M].London:BFI,1994:67-70.
[11]Lev Vygotsky.The psychology of art[M].Cambridge:MIT Press,1971:66.
[12]Sergei Eisenstein.Psychology of Art//Psycholgia Processov Chudojestvennogo Tvorchestva,Moscow:Iskusstvo, 1980:195//Julia Vassilieva.Eisenstein/ Vygotsky /Lurias project:Cinematic Thinking and the Integrative Science of Mind and Brain[EB/OL].(2014-09-26)[2022-12-28]https://marxismocritico.com/2014/09/26/eisenstein-vygotsky-lurias-project/.
[13]Lev Vygotsky,trans by Alex Kozulin.Thought and language[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6:218.
[14][18][德]奥莎娜·布加科娃,王苑媛.爱森斯坦理论建構的三次演进[ J ].电影艺术,2020(04):83-90.
[15]Alexander Luria.Traumatic aphasia:its syndromes,psychology,and treatment[M].Mouton de Gruyter,1970:370.
[16]Janna Glozman.A.R.Luria and the History of Russian Neuropsychology[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2007(16):176.
[17][俄]谢尔盖·爱森斯坦.蒙太奇论[M].富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482.
[19]Ossian Ward.The Man Who Heard His Paint Box Hiss[N].The Telegraph,2006-06-10.
[20]Alexander Luria.The mind of a mnemonist[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24.
[21][23]Sergei Eisenstein.Selected Works:Volume 2[M].London:BFI Publishing,1991:258,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