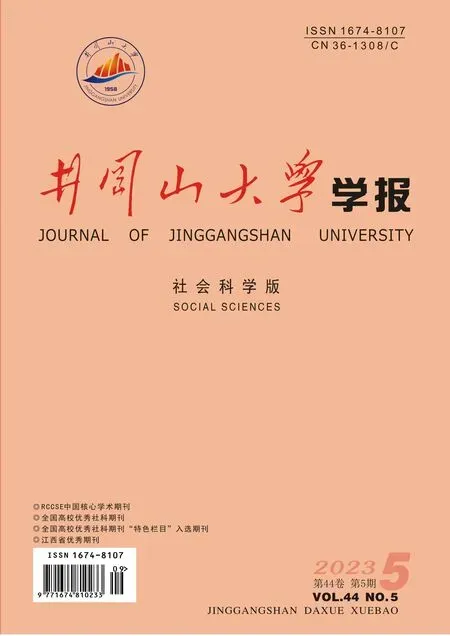以“自我经验”为介质透视女性存在之境遇
——论萧红女性苦难书写
吴 敏,魏靓文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0)
萧红,其短短三十余年的生命却一直处在“逃离”与“探寻”的路上。作为女性,她渴望安全感,因此,她逃离那冰冷的旧式家庭,追求火热的爱情与温暖的家庭;而作为现代作家,她以其独有的女性细腻敏感的心理,探寻人生的内质,摩挲人性,试图抵达人类灵魂的深处。 其创作生涯虽仅有短暂的九年,却留下了丰富且厚重的作品。但也正是这样身心饱受痛苦煎熬的女性作家, 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底,透视中国农村底层女性存在困境本质。与同时期左翼作家创作不同的是, 萧红创作中对女性苦难的书写跳脱出了左翼作家的文学视野与民族国家的情感角度,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作家并没有因为民族国家的飘摇零落而过分渲染女性苦难命运, 而是在历史滚滚洪流之中深入女性之肌理,探索女性苦难命运之根源。
萧红站在女性与底层视角观察、 处理生活素材,将尖锐的笔触直指黑暗的社会本质。因此探讨萧红创作中的女性苦难书写, 对丰富萧红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有助于大众认识上世纪黑暗社会中广大下层女性的生活,更加关注女性苦难问题、更深入地了解现实女性的真实境遇,丰富其文本社会价值。
一、“自我经验”为介质
弗洛伊德的“童年决定论”认为童年经历会对个体的现在与未来产生深刻影响, 亲历的童年生活总会桎梏着个体的生活与精神。 折射于作家群体,最直观地体现在作家创作中,作家的作品往往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生经验等息息相关。二十世纪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时期, 革命热情持续高涨,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社会大变革影响着这个时期的每一个人,萧红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另外,坎坷的人生与情感经历也化为无尽的创作素材和生活哲思,她以“自我经验”为质,在纸上镌刻下女性苦难的血泪史。
(一)社会之体验
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统治着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准则不断迫害女性,成为桎梏女性的枷锁。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枷锁成为一条条锁住女性肉体与精神的锁链,“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影响,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的境况,“教化之尤悖于道德者, 莫若幽闭妇女之一端,使全国之妇女,不读书,不识字,窒塞其聪明,束缚其能力,钳制其身体,上焉使为花为鸟,以供人之玩弄,下焉使为牛为马,以听人之鞭策”[1]26。女性视角与话语的缺失让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奴役很少被提及,女性大多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而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生活在历史交替背景之下的萧红, 不仅感受到了封建大家庭生活无形的压迫与窒息, 同样也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潮带来的精神洗涤。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自父系秩序建立以来第一个绝无仅有的弑父时代,第一个不含子承父位意味的弑父时代”[2]24,父权的崩溃以及欧美女权运动的影响, 一部分知识女性挣脱出思想禁锢,参与到写作之中来。以冰心、凌淑华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登上文学舞台,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女作家群体,她们将自身对平等、自由、独立的渴望诉诸于笔墨,以犀利或婉约的笔调批判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 以女性视角探寻女性话语,提高女性地位,这批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对幼年萧红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学接受新潮教育的萧红在思想上得到进一步解放, 新观念的习得和新运动的参与, 以及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往来,都使萧红的视野得以拓宽,“人”的理念在她心中愈发坚定,为人发声、为女性发声在萧红思想中生根发芽,成为她创作的朦胧追求。动荡的抗战时期, 作为左翼作家的萧红将目光投向了底层劳动女性,她同情战火流离中的生命,关切在现实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女性, 在与其他左翼作家, 如茅盾、胡风等人的交往中,萧红模糊的女性意识逐渐清晰,文学创作风格也趋于成熟。
在社会思潮和进步青年的潜移默化之下,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萧红得悉底层人民的贫窭生活,并于1933 年自费出版《跋涉》,其中收录了《王阿嫂的死》《小黑狗》等五部作品,作为初出茅庐的作家,萧红凭借这部合集获得文坛极大的关注。这本合集以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女性为主, 作品中体现了萧红锐利的反抗意识,如《广告副手》中芹将涂抹在广告牌上的大红色油漆比喻成自己的鲜血, 《王阿嫂的死》《夜风》里用犀利的文字揭露地主丑恶虚伪的嘴脸……萧红并没有因为自己封建地主家庭的小姐身份而“当局者迷”,反而对女性在战乱年代生活的不易更能感同身受, 她在创作之始就将自己的思想投射于女性形象, 在鲁迅帮助下出版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相继成为更成熟的作品。
社会思潮的冲击和良师益友的帮助促进了萧红女性意识的形成, 她的热血心灵不断接受着时代洗涤, 作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细腻的描写为底层女性正在遭受的苦难呼告。
(二)情感之殇
萧红短暂的三十一年生命中, 经历了世间苦痛。 亲情、爱情这些情感需求她从未真正拥有过,除了几缕偶尔从缝隙中透出来的温暖外, 她一直被黑暗阴冷所包围。
1911 年农历五月初五,民间认为在这天出生的女婴“命中带煞”,会“克父克母”。家人因这一点迷信的恐惧对她少疼爱, 旧式家庭重男轻女的传统, 在这个富裕地主家庭里的萧红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家庭的重视。自私冷漠的父亲对她态度恶劣,即使是同为女性的祖母、 生母、 继母对她也是冷漠,未能给予她一丝丝温情,整个家族里只有祖父给了她温暖, 当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祖父去世后,萧红便没有了生命里那抹最重要的色彩。童年的创伤促使她在作品中或直或曲地展现亲情的淡漠。 《生死场》中金枝因为怀孕,身子不爽利,不小心把未成熟的西红柿摘下, 母亲毫不犹豫地用脚踢金枝,萧红写到:“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 ”[3]74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叙述与祖母之间的相处:“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 我就叫起来了。 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欢她。 ”[3]760本该慈祥的祖母给萧红留下的却是可怖的记忆。 父亲更是淡漠的代名词,“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谁都没有好面孔,他仿佛是块石头。 除了祖父带来的温暖和爱之外,其余人在萧红童年记忆中留下的只有“冰冷和憎恶”。
爱情的坎坷也让萧红尝尽了苦涩。 她一生主要关键词——“逃离”就是始于她的逃婚,其人生中,萧红在不断地逃离父亲、家庭为她安排好的命运轨迹。其爱情经历了三起三落,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这三位占据她一生的男人,给予她短暂的欢愉后,留下的却是长久的痛苦。汪恩甲的悄声离去让当时怀有身孕的萧红不得不抵身旅馆, 每日做苦工还债; 萧军的大男子主义拯救了处于危难之间的萧红,却也让萧红日日受其贬低;端木蕻良细腻的心思给了萧红最大的温柔, 但端木也因家庭的宠溺而在生活中略显怯弱,保护不了萧红。萧红对爱情的希冀其实很大一部分和她的童年经历也有关,她在散文《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写到:“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3]1044一次次渴望被爱情拯救,又一次次被爱情抛弃,萧红以她瘦弱的身躯,独自承受着生存、婚恋、生育的苦难,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如芹、翠姨、金枝、月英等都同她一样几乎没有品尝过爱情与婚姻的美好,大多在婚姻悲剧中香消玉殒。
二、女性存在之困境
“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 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 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而陷于孤立。 ”[4]233萧红的苦难经历是其文学创作的养料,作家以己为自画像,以文学作品为媒展现了中国底层女性在“生死”场域中所遭受的贫困、疾病、生育之苦痛以及女性之价值竟不如牲畜的悲惨境地。
(一)肉体之苦
1.生存之难
萧红小说大都凸显“生的坚强” 与“死的挣扎”,生活在北方农村底层的女性无一不在生死之间挣扎。贫穷、疾病、饥饿摧垮了她们的生活意志,艰难的生存让她们如同荒野中的野兽般愚蒙无知地碌碌终日,苟延残喘于农村黑暗土壤之中,无法挣脱苦难命运在她们身上套下的枷锁。
贫穷是底层女性生存所要面对的基本挑战。落后的农村在时代巨变之中更显飘零,农村破产,除了人命不值钱外,什么都值钱,男人尚且需要不断谋事以忍受贫穷的日子, 更遑论处于附庸地位的女人,无论男女,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求得有一口气活下去罢了。 《王阿嫂的死》中的主人公王阿嫂是女性贫困的代表。王阿嫂是一个给“地主们流着汗”的苦工,她的丈夫因被拖欠工钱,愤怒之余喝醉睡在草堆上,被张地主趁机用火活活烧死,王阿嫂成为了一名怀着身孕、带着养女的寡妇。为了生存,王阿嫂什么活儿都做,一年到头的艰苦工作却让“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3]1,食不果腹的贫苦生活使王阿嫂身体消瘦,“若不是肚子突出,她简直瘦得象一条龙”[3]3,在她身上看不到一名健康的劳动女性本该有的力量美。 《生死场》麻面婆被贫穷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除了跟前能够满足生存温饱的事情外, 麻面婆想不到自己还能做什么,也根本没心思去想别的,每日的活计就是伺候男人和孩子,“做事是一件跟紧一件,有必要时,她放下一件又去做别的”[3]57,无尽的劳作生活正是贫穷的体现。
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5]24,“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5]56。 萧红也曾经遭遇病痛的折磨, 作家内心深处所恐惧的东西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 在萧红看来,疾病固然是农村女性生存面临的现实困境,事实上,疾病给女性所带来不仅仅是身体的病痛, 更是在男性社会遭受歧视、漠视的原因之一。旧式女性因为疾病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 无法创造生产价值或生育价值, 甚至有可能因为医治疾病而耗费家中钱财,在这样处境下,女性势必被男人所厌弃。月英拥有打鱼村里所有女人都羡慕的美丽外貌,却长期遭受疾病折磨, 每日每夜都在为身体的病痛哭嚎。因为疾病,丈夫对这个美丽的女人感到晦气,请神烧香还是不管用之后就对月英大声责骂,甚至于认为她快死了便只用几块砖依着月英那具“全身一点肉都瘦空”的病躯。 萧红直白如实地叙述了一个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女性身体,“她的前齿和眼珠变成了绿色, 紧贴在头皮上的是仿佛烧焦了的头发”。疾病带给这个美人儿的不是林黛玉般惹人怜惜的“病态美”,而是令人感到可怕的枯瘦,她清瘦得只剩下骨架的宽度,头在身子上都显得突兀万分。患病的月英已经失去自理能力,下体的失禁物沾染了炕头被子,淹没了她的骨盆,她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这个全村最美的女人最终在病魔缠身、丈夫抛弃、毫无尊严的境况中死去。翠姨(《小城三月》)得了结核病郁郁而终,马伯乐家车夫的妻子女儿(《马伯乐》)死于伤寒,王阿嫂(《王阿嫂的死》)丧命于难产……萧红笔下的底层女性大都经历着疾病带来的苦痛, 遭受生活的折磨。 萧红通过书写女性遭受的疾病困苦揭示了女性在男性世界被漠视的社会地位。
2.生育之险
萧红短暂的一生经历过两次生育, 这两段生育经历并未带给她为人母的喜悦, 窘迫的物质生活,低下的医疗水平,苦闷的内心世界无一不在困扰着萧红。 在鬼门关前生死徘徊的萧红对女性生育所要承受的痛苦有着刻骨的人生体验, 作家在作品中用浓墨重彩的笔调刻画女性面对生育时遭受的苦难。
萧红眼中的生育是什么样子? 是“刑罚”。 《生死场》中作家以“刑罚的日子”为标题来描述五姑姑的姐姐、 金枝以及二里半家的傻婆娘的生产场景。与大狗、母猪在温暖的季节里安详地生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子里女人们极度痛苦的生育过程, 女人们怀孕期间如同奴隶一般为男人洗衣做饭、纾解欲望,生产时遭受的痛苦却比猪狗多。 五姑姑的姐姐痛得在柴草上爬行,婆婆则因“压柴”之说将柴草卷收起来, 她只能赤裸着身子如同一尾鱼似的趴在土炕上等待刑罚降临, 生产期间承受的疼痛让这个受罪的女人几近崩溃,“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 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 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 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3]57除了疼痛外,酒疯子一样的男人也是她的刑罚, 面对男人的暴戾,“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3]97。 血光之中,这个可怜的孕妇终于将“罪恶”诞下,随着阵痛一起消失的是孩子的呼吸——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可怜的女人九死一生之后除了疲惫与苦痛之外什么都没得到。 同样的折磨笼罩着金枝和二里半家的傻婆娘,还有那个只用一句“快死了”就概括过程和结局的李二婶子。
萧红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弃儿》,描述了在寒冷的医院、 饥饿的困境里芹挣扎了三天才把孩子生下来的场景,芹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萧红的经历,这场难以忘怀的肉体刑罚奠定了萧红对女性生育苦难书写的基础。 萧红将自己的生育经历代入底层女性的生育之中,男权的压制、生活的贫寒、情爱的缺失, 导致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无法获得肉体与精神上的满足, 这种将身体劈成两半的痛苦是女性的牺牲, 但这种牺牲几千年来却被认为理所应当, 女性的生育就像猪狗牛羊繁衍一样天经地义。 作家在《生死场》曾描述,到了暖和的季节,全村都忙着生产: 全村的狗在生产、 全村的猪在生产、鸟雀儿在生产、人也在忙着生产。 貌似生命盎然、 生机勃勃的场景, 却深层隐喻着女性的生产(生育)等同于动物性再生产(繁殖),女性的价值等同于动物性价值, 从而消解了女性在男性社会的地位。
(二)精神之痛
1.婚恋之难
亲情的缺失让萧红对爱情有着极大的渴望,女性的身份让她对感情有更细腻的需求, 其短暂生命中对爱无尽的追求,如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的松子,渴望着爱、追寻着爱。童年时期渴望父母家人的亲情,成年后则渴望来自异性的爱情。“三起三落” 的爱情悲剧给萧红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当这份痛苦投射于作品之中时,其笔下的女性都经受了爱情的缺失和婚姻的不幸。
《小城三月》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翠姨的爱情悲歌。 故事开篇就提到翠姨大概是和“我”的堂哥恋爱了,但翠姨的爱情就像她的性子,沉静内敛,她喜欢“我”的堂哥,但是她从未说出口, 甚至于在堂哥邀请她一起吹箫时她也只是匆忙起身跑到屋里去,与堂哥保持距离。翠姨这般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单相思的秘密一直到家人给她介绍对象之时,家里介绍的对象又丑又小,和在哈尔滨读大学的堂哥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翠姨自然是不想嫁给这么一个男人。 但翠姨反抗和她的爱情一样沉默无声,最后郁郁而终。这曲爱情悲歌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悲哀,生存本就艰难,被封建礼教和父母之命夹攻的女性更是失去了追求爱情的自由和勇气,无可奈何之下的身体孱弱、肉体受损乃至郁郁而终是她们挣脱不掉的宿命。
有人困于爱情,也有人死在婚姻里,《生死场》里的金枝将自己的少女情怀倾注给成业, 在菜圃里听到了口笛声便魂不守舍地跟上去, 满腔喜悦迎来的却是男人的兽欲, 在野兽眼里金枝只是一块可以吞食的肉体, 少女美好的胴体在他眼中是“一条白的死尸”。 金枝很快就未婚先孕了, 婚后的生活正如婶婶之前对成业说过的那样——“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在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男人们心上放着女人,也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吧! ”金枝被婚姻囚禁住,完完全全成为了成业的奴隶,即使是大着肚子, 天还不明就需要起来给男人煮饭,繁杂的家务让她疲顿,想休息片刻也不能,在成业回来后还要成为他的泄欲工具。 婚后的生活让金枝疲惫不堪,她的少女心绪被繁重的家务、男人的兽欲占有, 最终只能和村里的其他女人一样麻木地承受来自男人的欺凌辱骂。 无望的婚姻只给金枝带来了无尽的劳动、肆意的辱骂、孩子的惨死,还有内心的荒芜。
不论是翠姨还是金枝,亦或月英、小团圆媳妇等, 这些女性都因为在两性中的不平等地位而遭遇不幸。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生活在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中,礼教、三从让她们的情感需求得不到重视与释放, 无法获得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存在所需要的尊严。婚姻于她们而言就是一座坟墓,她们青春逝去,年华不再,无法生育,生命价值在情爱之中逐渐褪色。
2.觉醒之艰
肉体的折磨成为底层女性的生活基色, 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意志在长年累月的暴力折磨之中被消磨殆尽。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能够过下去,她们选择了承受,在男权的压制之下消解自我,驯服于男性的价值标准。 无力抗争的后果催发了她们身上的“阿Q 精神”,默默地承受并忍耐着肉体与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变得麻木不懂反抗。
麻面婆、福发婶、月英、金枝、王阿嫂、王大姐、小团圆媳妇的婆婆等人面对男性的残忍暴力选择麻木顺从。麻面婆的丈夫二里半是村里的失败者,他不敢和红脸长人的强邻动打, 只能将火气发泄在身边的小树和辱骂妻子上, 面对丈夫的打骂斥责, 麻面婆永远都是逆来顺受,“她都是像一摊蜡烛消融下来。 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 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呼兰河传》中指腹为亲的母亲也是如此, 女儿在夫家受了欺负只能回娘家以求得母亲的一丝帮助,母亲却只会说这是女儿的命,要女儿好好忍耐。同样还有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她在夫家兢兢业业,能干且温顺,被丈夫打了,不仅不进行反抗, 反而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 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 ”
女性不仅承受来自男权的压迫, 同时她们也成为男权社会的帮凶,由受虐者成为施虐者。小团圆媳妇是老胡家买来的童养媳, 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少女, 左邻右舍却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没有丝毫怜悯,反而不断地议论她“不害羞”“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婆婆为把小团圆媳妇打造成符合道德规范的完美媳妇, 开始了对她的长久虐待。 在她看来,哪家的媳妇不受气? 不打狠点,团圆媳妇是不够中用的。团圆婆婆本身并不是暴力的人,但在彼时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观照下, 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属于暴力,在其看来作为“不合规矩”的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她有这个责任与义务“为公序良俗做出贡献”。
麻面婆的受虐经历、 小团圆媳妇的婆婆的施虐行为, 并不是只存在于萧红创造的文学世界之中,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封建糟粕和精神桎梏,污泥浊水绊住了女性上岸求生的脚步, 吞噬掉了她们的精力,迫使女性看不到活的希望,只能麻木迟钝地一步步沦陷在泥沼之中。当然,在探讨封建社会压迫的时候, 也不能规避女性自身存在的精神缺陷,肉体痛苦之下她们一再退让忍耐,忍耐到最后她们的自我意识被吞噬, 成为依附在男性身上的菟丝花,很难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无法再进行抗争。
三、苦难书写之价值
萧红短暂苦难的一生中, 鲁迅先生作为良师益友给予了萧红极大的帮助。 虽然萧红和鲁迅先生年龄相差三十岁,并且各自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鲁迅创作对萧红产生很大的影响, 她以笔为刃批判社会现实,用以唤醒国民性。在接受鲁迅文学主张的同时, 萧红又能够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女性视角来为女性书写苦难, 揭露底层女性生活的艰难和精神上的麻木, 观照与审视现实社会及批判国民精神。
(一)对女性生存困境的观照
萧红在流亡过程中亲眼见证了日寇对祖国的侵略行为, 偌大的国家处在风雨飘零的生死存亡时刻,在此期间她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陶冶,顺应时代潮流参与到文学写作之中, 用文字呐喊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萧红参与到左翼作家之中,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之一, 与左翼作家不同的是, 左翼作家们大都把目光投在人民性和世界性两个层面, 萧红却独辟蹊径,“尽管民族灾难和社会革命不断冲淡女性意识,冲刷女性话语,也尽管时代主流一再要求她着力表现社会政治意识, 但她始终未曾放弃对女性生命的终极关怀和自己的女性立场。”[6]97与同时期的女性作家相比,萧红并没有展示思想碰撞下都市女性的彷徨与抉择, 而是以悲悯的视角观照着农村底层女性的生活遭遇, 彰显对底层女性苦难命运的人道主义式的同情。
在宗族势力根深蒂固的农村, 礼教陋习的烙印导致农村底层女性如同奴隶生存着。 《生死场》形象地表现了在农村中人如动物一般靠着本能求生的模样,人命比菜圃里的菜还下贱,底层女性的存在价值甚至与动物都无法等同。底层女性的生命被他操控,成长、嫁人、生育、死亡,形成生死循环。
(二)对男权社会的审视
萧红曾在《女子装饰心理》说:“男子处处站在优越地位,社会上一切法律权利都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居于被动地位。 虽然近年来有男女平等的法律,但在父权制度之下,女子仍然是受动的。”封建社会,男性长期掌握社会话语权,从父、从夫、从子这三从将女性绑在了“依附者”的石柱之上。 萧红从父亲、三段爱情里察觉到男权对自身的束缚,她将自身感受融入到小说创作之中, 通过文字表达对男权社会的批判。
对男权社会的批判, 主要体现在对男女地位悬殊的对比。 《呼兰河传》中描写了娘娘庙和老爷庙,娘娘庙中的泥像只有一两尊,且几乎是温顺的形象;而老爷庙中的十多个泥像都是威风凛凛,叫人害怕,人们祭拜时“都以为阴间也是一样的重男轻女, 所以不敢倒反天干, 所以都是先到老爷庙去,打过钟,磕过头,好像跪到那里报个到似的,而后才上娘娘庙去。 ”仙界尚且重男轻女,人间则更不用说了。福发婶婶知道给男人做老婆是件坏事,但是在她年轻时被福发从河边拉到马房,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最后只能欢喜地给福发做老婆,男权的烙印从此印刻在了福发婶婶的言行之中,男人生气的面孔使她害怕, 不敢动也不敢笑,“她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丈夫的话她当命令一般服从。福发婶婶的经历和金枝、月英等人毫无区别,甚至可以算得上是她们的“前辈”,怕挨打挨骂使男权的压制一代又一代传下来, 男性无法平等且尊重地看待女性,“女人如衣服” 的观念让女性成为男性可有可无的物件。 其次体现在对男性形象的描写之中。二里半脸长得像马脸,地邻红着脸像是一个魔王,平儿像个猴子,小玉祖父的脸型像个马铃薯,何南生长了个人见人愁的脸,马伯乐身体消瘦且病弱……萧红用犀利的笔调刻画了一个个不同于传统认识中威风凛凛的男性形象, 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消解着男性的绝对地位。
男权社会长期的压制致使女性一直生活在男性阴影之下,成为上不得台面的“第二性”,女性价值在封建社会之中不断被压缩, 母系社会时可以是“一家之主”,和男子一样有“权力”外出打猎、制作工具、养育后代,奴隶社会之后女性地位下降,封建社会的到来更是严重打压女性,她们被限制在家庭中,价值只剩下生儿育女。 萧红在创作中对男性的讽刺描写使男权至上的这层虚假外衣被毫不留情地撕碎,引发大众对两性地位与价值的思考。
四、结语
萧红短暂的一生由苦难织就而成, 从一个泥淖掉落进另一个泥淖中,瘦小的身躯被污泥裹挟,但她从未沦陷于污浊之中, 而是从泥塘里挣扎出来, 向社会各界人士展示其她女性在泥淖中的苦难生活。
纵观萧红创作历程,“女性” 是众多学者进行萧红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主题, 女性问题更是她重要的创作母题, 从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最后一部短篇小说《小城三月》,人们看到了无数名匍匐在荒芜农田之上、 屈膝于粗野男人脚下的可怜女人。不论是死于非命的诸如王阿嫂、月英、小团圆媳妇、翠姨等人,还是浑浑噩噩活着的如麻面婆、金枝、福发婶婶等,她们无一不是赤脚行走在男权土地上,用鲜血和苦难寻觅生命终点。寻找终点的旅途中, 她们或经受贫穷, 或经历爱情,或亲历生育,但实际上,这只是对女性所遭受的苦难的一种理想化梳理方式, 她们并不单单只承受一种折磨, 更多时候是多种折磨附加于她们的灵魂和肉体上。 萧红用简单直白的笔调将农妇们所遭受的来自丈夫、 家庭、 社会的鞭笞娓娓道来,这些创作题材最后融入作品主题,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浓缩了的女性苦难一生。
漂泊奠定了萧红的创作基调, 创作中女性苦难书写是其自身经历的缩影, 作家在创作中彰显了对底层女性的怜悯之情, 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高尚的人文关怀探索女性悲剧的根源, 激发人们对旧社会底层女性的遭遇进行思考, 引领每个人重新审视男权社会存在的不合理性。
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翟永明曾言:“无论我们未来写作的主题是什么(女权或非女权的),有一点是与男性作家一致的: 即我们的写作是超越社会和政治范畴的, 我们的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以及思考方向也是建立在纯粹文学意义上的, 我们所期待的批判也应该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发展和界定。 ”[7]89纯粹文学意义上的作品应该是摒弃对物欲的过度追求,理性面对新时代的灯红酒绿。新时代的女性作家们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思想、眼界、个性都处在历史最高点,来自时代的红利则更加要求作家们关注时代命题, 歌颂新时代的同时也不要忘记那些快被时代抛弃了的可怜人。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独立人格的建立, 在独立思考之下看到日常生活的价值点, 寻找真正自然健康的女性生存意义。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