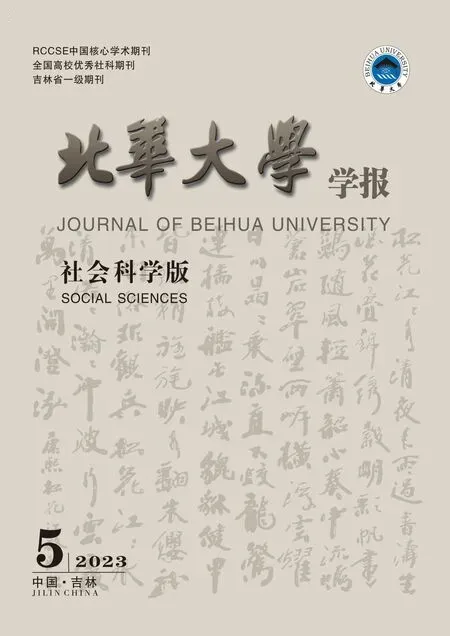变与不变的悖论
——再议津田左右吉的中国观
顾菱洁
一、问题的提出
1945年日本的战败使日本知识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既有像竹内好一样,通过积极评价中国的民族性来批判帝国日本失败的近代化模式的战后知识人,亦有如津田左右吉一般,在战后始终拒绝使用 “中国”或 “中华”(1)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津田在著作中均使用极具负面意味的 “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为反映史料原貌,本文在引用津田原话时亦使用这一用语。等称呼的旧时代遗老。
津田左右吉(1873—1961)(2)津田左右吉,1873年出生于岐阜县,是归农士族的后裔。1891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1908年受白鸟库吉邀请进入 “满鲜”调查室。1939年津田因涉嫌冒犯皇室尊严而受到右翼的控告,其著作亦被禁止销售。在战争结束以后,津田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可,于1949年接受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61年去世。是日本近代著名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家,在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本文以 “津田的中国观”为研究课题,以 “津田的日本观”为辅助性参照对象。津田自身在进行思想史研究时通常将中国和日本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而中日学者在进行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研讨时,亦习惯于将日本思想史研究视为参照物,指出津田史学具有以中国为 “他者”来塑造日本文化主体性的特征,这使得津田的中国观与日本观亦往往互为参照。
“津田的中国观”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中日学者关于津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研讨成果颇丰。日本学者岩崎信夫指出,津田从 “现代文化”角度出发批判中国文化,意在肯定以 “日本国民”为中心的公共国民论。[1]中国学者刘萍对津田的中国儒学批判、道家批判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津田对中国思想的蔑视是基于其民族主义的立场。[2-3]子安宣邦将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称为 “庞大的积累”(3)直接对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这一 “庞大的积累”提出质疑的是子安宣邦,他在《荻生徂徕和津田左右吉之间》中指出,在津田庞大的中国研究成果中事实上只能看到 “发言者本人的意图”,其研究是基于日本近代知识人自我肯定之上的 “以否定他者为目的的他者研究”。参见子安宣邦《徂来論-5-荻生徂来と津田左右吉の間》(《現代思想》1988年第14期第210页)。,对其 “以否定他者为目的的他者研究”进行激烈批判。李建华则在《津田左右吉的中国观》中兼论津田对近代中国的认识,认为津田对中日战争的批判、对中国人民力量的重视也不容忽视。[4]然而相关研究基本都集中于战前津田的中国思想蔑视论和中国历史停滞论,很少有学者探究在日本战败、中国战胜的背景下,津田对中国思想与社会的认识是否出现变化的问题。换言之,对于 “津田的中国观”这一学术课题,中日学界很少有基于 “转向”视角的研究。在此意义上,现有研究在探讨津田的中国观时,往往将史料局限于津田在战前完成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而未充分利用津田在战后发表的大量论文或时评,这是由中日两国学者各自的核心问题所致。日本学者意在考察津田对日本文化与日本天皇制的认识问题,因而仅将其中国思想史研究作为辅助性的参照对象。中国学者则通常站在学问研究的客观性立场上,指出津田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确有不实之处。如此一来,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或将成为某种 “不变”的庞大积累,而除此之外的津田的中国文学论及战后中国观则被搁置。
战后日本学者对 “思想转向”问题的研究,为理解津田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主要参考日本学者家永三郎的研究成果。家永在《对津田左右吉的思想史性质的研究》中以 “津田的思想在战后是否发生变化”为题,指出津田的思想在战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倒退(此处主要指批判精神的衰退)。[5]6通过对照津田战前与战后著作中大量字词的变动,以及津田在战后频繁发表的时评类文章,家永认为津田其人不再是战前坚持 “政治性禁欲”的书斋式学者,走出象牙塔的津田带着狂信的热情朝着战前的反方向行进。[5]591然而,家永虽然细致且深入地考察了津田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但却并未对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解读。若是站在家永转向研究的延长线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津田的思维方式确实在战后发生变化,即从 “变化的日本观”的视角出发的话,就会发现 “津田的中国观”似乎呈现出 “不变”与 “变化”的双重构造。一方面,就 “不变的中国观”而言,战前与战后的津田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先验性标准来衡量、评判中国的思想发展,这使得津田自始至终都对中国古代文化持有极其负面的评价。另一方面,就 “变化的中国观”而言,战前的津田以构筑近代日本国民思想史为核心问题,有意塑造出 “日本有国民”而 “中国无国民”的对立性构图。战后的津田则直面中日之间地位逆转的政治现实与战后日本人对日本民族性的强烈批判,积极鼓吹所谓的 “中国非民族”论,试图通过持续贬低 “他者”来重塑日本民族的 “主体性”与 “优越性”。
探析 “津田的中国观”的双重构造,对于深究津田其人的思想构造,理解近代日本人衡量与评判 “他者”的标准与态度,可谓至关重要。在此,本文将以 “津田的中国观”为研究对象,但不局限于津田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而是在充分解析津田的中国文学论与战后中国认识的基础上,将 “津田的中国观”大致分为研究内容、认识结构、核心问题三个层次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分析从战前到战后,津田中国观的思想构造是否发生转变及其变或不变的缘由所在。
二、 “以政治为尘埃”而 “以文学为珠玉”
津田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最大特征在于 “直接指导现实的政治和道德”[6]203,故而他在中国古代政治道德思想方面的著述颇丰,中日学者对此亦多有评议。然而对于宣称 “‘支那’的文学也是了解‘支那’人思维方式的重要文本”[7]351(4)津田自称其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目的在于 “从讨厌的东西中发现好的东西,从尘埃中发现珠玉”,结合后文提及的津田对中国文化的复杂态度,可以推测 “尘埃”指代津田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而 “珠玉”则与其对中国文学的评价相关。参见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7卷(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270页)。的津田的中国文学论,中日学者却鲜有研究。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津田在著作中均使用极具负面意味的 “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为反映史料原貌,本文在引用津田原话时亦使用这一语词。与此同时,直面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中日地位逆转的现实,津田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态度是否发生变化这一问题亦值得重视。此处将采用家永三郎的研究方法,考察津田于战后再刊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著作是否存在明显的添补删减的情况。
津田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尤其是儒教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说。首先,津田认为中国的儒教道德是以帝王为本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道德,“‘支那’引以为豪的文化实际上是‘支那’权力阶级的文化”[6]212,其中儒教的政治学说乃 “教导统治阶级或权力阶级如何治理民众的学说,后来成为致力于教导统治者或权力者如何维持其地位与权力的学说”[8]451-452。在批判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与道德性时,津田刻意使用 “儒教”一词,而非 “儒家”,概因他觉得以 “教”为名的思想必然会伴随 “传统性的权威与宗派式的偏执”[9]357。其次,津田指出,在这样的儒教思想统治之下,中国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被分隔开来,相互间完全未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联系。具体来说,津田认为,与西方的政治观念意在充实和发展国民生活不同,中国政治学的根本或所谓的最终目标是统治者让被统治者顺从于自己的统治,也就是 “治国平天下”之道,其政治教化主义并不想发挥国民作为个人的能力,而是想要使被统治者顺从于统治者所制定的政治秩序,从根本上来说,“其中没有国家由国民所组成的观念,而是专制政治社会为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完全分离而制作出来的东西”[5]150。在津田的认识中,即便是作为思想传播者的中国知识阶级,他们也是以做官为目的,“自然会站在统治阶级、权力阶级一方”[8]451,故而其所传播、灌输的儒教思想亦与下层民众少有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津田说道:“在儒教的思想中,普通民众被视为禽兽,被视为是必须用道德加以规范的存在,因而与民众无关的君臣关系成为人伦的重要之物,这就不足为奇了。”[6]207最后,津田格外强调中国存在 “知识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相分离”[10]318的现象,即对普通中国民众来说,传统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龃龉,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只是来自于外部的知识,并非产生于其内在的实际生活且能够展现其实际生活的知识。因此,津田屡屡声称无法从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思想中知晓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
津田坚持采用 “原典批判”的研究方法,(5)津田坚持原典批判的研究方法,他曾提到: “如果想要更好了解江户时代的东西,就不得不追溯到之前的时代,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就不得不追溯到更早的时代,最终追溯到了上代。”参见今井修《津田左右吉历史论集》(岩波书店,2006年版第15页)。试图利用中国古典文献倒推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样貌。但事实上,早在津田正式对外发表学术文章之前,即1911年,在被其命名为《鼠日记》的日记中(之前的日记通常名为《春愁记》《溟濛录》《浪之雫》《凄风惨雨录》等),津田就已对研究对象呈现出否定性的评价:“一站进去,脑袋就像要被腐蚀掉似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书中记载的不是中国人的过去吗?权谋与术数、贪欲与暴戾、虚礼包裹下的残忍的行径、巧言矫饰着的冷酷的内心,这一切不是深藏在上千册书籍的每一个字里行间之中吗?”[11]面对这样的 “中国人的过去”,津田自觉 “被这些书籍所散发出的污浊空气压迫,厌恶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故尤以《鼠日记》之名突显其内心 “自比于鼠”的厌恶情绪(“在这样的地方筑巢而居的老鼠也是很悲惨的”)。[11]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津田对中国的政治道德学说亦进行了类似的 “权谋与贪欲”的指责。他认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说与崇尚 “自然之理法”的佛教、道教思想的结合绝非偶然,概因中国的政治道德学说意在肯定 “人的肉体性的、物质性的欲求”[6]207,认为人的名利欲与权势欲是一种自我本位和利己主义的思维方式。津田如此说道:“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支那’民族的特色,那就是基于生物意义上的不断努力维持生命及竭尽全力满足肉体性的、官能性的欲求,即便认为其生活之根本就在于此也并无大错。”[12]
津田强调中国的政治思想具有 “以自然为主而人为从”且 “重视道德但轻视个人意志”[10]352的特色,与这样的否定性评价不同,津田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情感较为复杂。津田提出 “若是真正的民族精神就必然会在文学中显现出来”[13],而艺术家就是 “在无意识中不断实现国民的要求、展现国民性的人”[14]。在此意义上,津田指出,中国的文学也是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文本,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仅是逻辑性的,同时也是文学性的,“‘支那’思想、‘支那’人的思维方式与‘支那’语特有的修辞手法息息相关”[7]351。津田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评价好坏交织。关于中国的诗词,津田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其文字上的趣味性,例如 “在李商隐以《锦瑟》为题的七律中,有‘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一联。……用温润的玉来形容蓝田简直极妙,但沧海一句的‘泪’字不太适合,用‘露’这样的文字更好”[15],但同时亦指称这样的文字 “一旦被知识阶级的诗人所使用,就会被后者用知识加以修饰,其思想就会被固定下来而逐渐失去生气”[10]358。津田同样将中国的文学作品视为中国知识阶级的造物,故而在承认中国的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存在些许 “美的、内在情感的表露”[10]352的同时,亦会评价这种 “依靠诗人之手得以保存下来”的温柔敦厚的趣致不过是一种低级、单调、贫弱的东西。[10]352
津田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态度,直到1945年以后也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日本学者家永三郎通过对照津田同一著作在战前刊行的初版与在战后再刊的修订版本,发现其中存在大量段落删减与字词更替的现象,并通过分析指出津田的思想在战前与战后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然而除了家永作为例证的几部日本思想史研究著作外,(6)指《神代史的研究》、《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我国国民思想研究》与《历史的矛盾性》。津田在战前以中国思想史为研究对象所发表的诸篇文章,在战后亦有再刊的情况,例如《儒教的实践道德》《王道政治思想》等诸篇文章,在战后被汇编并刊印成《儒教的研究》三部曲。但与家永所发现的字词变化不同,津田于战后再刊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著作很少有大幅度的添补删减。参照1934年的《王道政治思想》和1956年《儒教的研究 第三》中的同文可知,津田虽然在 “绪言”部分有所修改,但这不过是在补充说明 “思想”与 “实际生活”的内在逻辑关系。津田在1934年的著作中提道:“要正确领会‘支那’思想,首先要知道塑造并支撑其思想的‘支那’民族的实际生活。”[16]3在1956年的文章中则增补道:“要正确领会‘支那’思想,首先要知道塑造及支撑其思想,并可借由其思想所推导出的‘支那’民族的实际生活。”[17]然而,及至正文真正开始论说 “先王之道” “孟子之王道” “荀子之王道”时,可见的变动则基本只有从汉字的 “支那(支那)”到片假名的 “支那(シナ)”的程度了。
三、 “停滞的中国”与 “自由的日本”
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曾被战后日本人高度评价为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座高峰,(7)日本学者町田三郎视津田为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座高峰,称 “今日之研究始终未有超过二人者(指津田与武内义雄)。”参见町田三郎著,连清吉译《日本幕末以来之中国学家及其著述》(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这要求津田的学问应有一套能够内在自洽的逻辑结构,此即战前的津田所刻画出的 “停滞的中国”与 “自由的日本”的对立构图。这样的构图延续到战后,被津田几乎 “复制粘贴”式地继承到其战后的中国观之中。然而与此同时,战后的津田对 “自由”的解读却呈现出微妙的认识侧重,从强调 “思想的自由”转向宣扬 “历史的自由”和 “学问的自由”,试图证明战后日本人也应有 “理所当然”的民族优越感。
津田的 “中国停滞论”主要包含如下三点内容:
一则关于中国思想 “停滞”的具体表现。津田在承认中国的政治思想具有稳定中国统治秩序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对该思想的保守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津田指出 “在上代形成的政治或道德的宗教作为知识社会的思想,为保证其长时间的权威而持续存在”[6]203(8)津田所指的 “支那上代”,在时间上与如今所说的 “先秦”时期大致相当,在思想上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即 “‘支那’的民族生活,尤其是其政治侧面,很少有历史性的变化,直到后世也基本都是同样状态的持续与同样情况的反复,是以作为与之相关的思想,一旦具备其形态,则就这样固定下来且流传至后世”[16]4,津田否定中国存在有如欧洲一般的历史性变化发展。在1929年的《‘支那’思潮》中,津田以 “思潮”一词寓意 “思想的历史演变”。他虽然以 “‘支那’思潮”为标题,但事实上却在否认中国的思想在秦汉以后出现过大幅度的变化。他以自知夸张的口吻阐述中国历史的特性:“虽然历史的时间很漫长,但是历史本身却可以说是极其短暂的。或者任意将中间的二三百年删减掉的话,可以说前后是直接相连的。”[10]316在此意义上,津田虽未否认中国的历史存在细微的变化(例如王朝更替),但他坚持认为:“在‘支那’的历史中,没有上代史、中世史和近世史。若是认为其与欧洲的历史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10]316
二则在论证中国历史停滞的过程中,津田所采用的重要指标是 “思想”,即以不断变化着的 “实际生活”为基础的 “思想”。首先,津田将 “思想”定义为在国民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并随之不断变化发展之物,是在某个时代的民众实际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意味其精神生活的全部思想。其次,以 “历史是人的生活”的观点为前提,津田格外重视 “生活”这一观念,屡屡指出 “思想在生活中产生,并推动生活指导其发展”[18]、 “生活是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19]180、 “生活的本质是不断面向未来创造自我”[19]172。在津田眼中,中国和日本存在完全不同的实际生活,故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民族性。一边是 “普通民众的生活依附于帝王,帝王的行为支配其民众的全部生活”[6]210的思想停滞的中国;一边是以整个日本民族为主体、其思想不断革新不断变化的日本。最后,历史的变化集中表现为某种 “革命的精神”。在津田看来,中国的思想缺少波澜,概因中国社会组织散漫、少有压抑,“既没有压迫实际生活的思想,也没有强有力的生活颠覆其传统思想的权威”[10]317-318,所以中国自上代到近代都未产生出能够推动社会秩序变化的 “革命的精神”。除了在中国思潮中被其认为是最有趣且最值得研究的孔孟时代,津田指出其余的都不过是 “年年岁岁人不同但年年岁岁事相同”[20]449,即 “人成为制度的奴隶,民众毫无活力,空气停滞,社会的发展进步遂遥不可及”[20]449(9)在这样的认识背后,有的是津田对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理解。即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与顺应型个人,但为了推动历史的进步发展,必须存在的则是尽可能承认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与骚动不安的反抗型个人。参见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2卷(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451页)。。与之相对,津田积极评价被其视为与中国孔孟时代极其相似的日本德川时代,他认为该时期的江户知识人苦于太平盛世而 “以烈火燎原之势倡导尊王论”[20]452,由此导致了明治维新的发生。
三则津田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呈现出一套内在自洽的封闭式结构。具体来说,中国历史的停滞性源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质,后者具有服务于帝王权力之永固的保守主义性格,这一特质阻碍中国民众实际生活的发展变化,同时亦使其自身与下层民众的实际生活少有接触,故而中国的社会构造呈现出一种非常稳固的上下尊卑关系,在此意义上,中国没有产生出革命的精神并借此推动社会秩序的发展,有的只是以帝王为中心的王朝更替的历史。津田在《儒教的实践道德》中以家族道德中最重要的 “孝”为例,指出在以父为家长的家族结构中,存在的只是亲对子的权力掌控,以及子乃亲之所有物的思考,因此从儒教文献中很难知晓古代中国人家族生活的实际状况。[21]15换言之,从儒教文献出发进行推演,津田自认其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基于礼而将人与禽兽、人与夷敌相区别的上下尊卑关系,“此乃中国人自古至今最显著的癖好”[21]16。在此,因为津田坚持 “原典批判”的研究方法,所以他使用的史料文献大都只局限于孔孟的书籍,这一点不容忽视。同时在论证的过程中,津田有其预设。例如正因为津田事先认定儒教思想都是服务于帝王权力之永固的思想,并且与中国人的内在实际生活无关,是以在解读中国古典文献过程中,津田会将中国的父子关系直接等同于强者与弱者的上下尊卑关系。
津田对中国历史停滞的解读,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也基本没有变化。在1946年的《“支那”文化研究的态度》中,津田仍然坚称:“‘支那’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其停滞性,其曾在上代发展以后就原封不动地固化了,这一点毫无疑义。”[22]381在历数中国文化停滞性的由来时,津田所提到的几点原因,诸如中国的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而非民众的文化、文化的根基是该民族的农业生活与社会政治机构、中国民众的生活与思想缺乏自由的精神,大都是在照搬其战前的认识,二者无甚区别。但在另一方面,津田对 “自由”的界定却出现了细微的变化。战前的津田坚持 “思想的自由”,高度肯定反抗型个人的 “革命的精神”,同时重视思想及作为基础的实际生活面向未来不断创造自我、不断革新变化的整个历史过程,这使得其 “停滞的中国”与 “自由的日本”形成对立构图。然而1945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发展并非停滞,面对这一现实,战后的津田将 “自由”重新定义为 “不受拘束”[23],开始鼓吹所谓的 “历史的自由”和 “学问的自由”。
前者指向津田的 “战争肯定论”。在1950年的《必然·偶然·自由》中,津田以 “自由”为关键词,积极评价 “人之所为”和 “人的生活”,指出 “历史是人的生活的过程”[24]42,“其根本是人的意志及其自由”[24]18。在此基础上,津田否定从事后出发分析过去的观点,强调在历史中生活着的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就是津田所说的 “人创造自我、创造环境、创造历史”[24]18,在肯定人的自由、人的意志的同时,津田还提出需要重视生活在历史中的人的 “道德性任务”,即对自己、对国家社会、对人类、对后世的责任。凭借这一所谓的 “道德性任务”,津田坚决反对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联,且直接将前二者与后者一样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观点。对此,津田主张要站在 “当时的日本人”的立场上,将这两场战争视作 “弱小国家面对压迫时的奋不顾身的反抗”[24]40。在津田看来,即便是战后的日本 “因最近的战役而导致其国际地位下降,也不能否定这一点”[25]。在此基础上,津田甚至敢于宣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不仅维护了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更是给其他亚洲各国带来了所谓的 “明显的益处”。津田具体说道:“明治时代进行的日清战争或日俄战争,或促进‘支那’人的觉醒,或使东南亚诸民族自身意识到可依靠对象的存在,这些功绩自不必说,日本的文化在台湾(应是中国台湾地区,原文如此——笔者注),)和韩国的输出取得了巨大的效果,这一点也是明白无疑的。”[26]503这样的所谓的 “殖民功绩”在战后的日本教科书中或被隐藏或被无视,对津田来说委实是 “令人惊讶”之事。
后者指向津田的 “日本学问优越论”。战前的津田反对通过战争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做法,他认为学问研究才是提高日本的世界性地位的捷径。(10)在1939年的《日本“支那”学的使命》中,津田就明确说道: “在某个民族的活动中,能够最大程度地显示其民族优越性的活动之一就是学术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具有世界性的活动。学术上的业绩才是没有任何摩擦与利益冲突,能够被任何一个民族所接受的、为世界所公认的东西。”参见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1卷(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374页)。在指出中国的本国学问研究非常幼稚的同时,津田提出 “日本必须振兴所有的学术研究,这是提高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捷径,也是向‘支那’知识人展现日本民族优越性的最好办法”[9]374,津田意欲通过学问研究使中国人转而 “以日本为师”的想法可见一斑。战后的津田仍然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战败,这是 “冷酷的事实”,但是战败所带来的却并非尽是坏事,至少一个所谓的 “令人愉悦的事情”就是 “思想的自由和学问的自由”。[27]面对战后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国际地位下降的现实,津田尤其宣称 “学问研究不应该受到一时的风潮、政治社会事件或国际形势的支配,也不应因其变化而动摇”[22]376,换言之即日本的中国学研究 “不能为任何势力所动摇,不能屈服于任何权威”[22]376,也不应受到日本军部或部分政治家与官僚曾对中国所作出的倨傲态度、错误行动的影响[22]385-386。津田屡屡声称:“尽管‘支那’人比日本人更早接触到欧洲的学问,但是‘支那’人理解与领会欧洲的学问却比日本人要晚得多。如今‘支那’文化的现代化程度远低于日本,亦在于此。从这一点上来考虑,日本确实是比‘支那’更先进、更优越。在此意义上,日本人的优越感是理所应当的。”[22]384
四、从 “中国无国民”到 “中国非民族”论
津田从战前到战后都始终坚持 “停滞的中国”和 “自由的日本”的对立构图,这与其内在的思想观念相关。家永认为,战前津田学问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对日本前近代思想(尤其是封建思想)的批判,[5]25而以战败为契机,津田转向鼓吹日本的天皇制,这是津田 “思想倒退”的重要表现。家永从 “思想性即批判精神”的角度出发阐释津田思想的变化,然而若是直接考察津田在战前与战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变化则可以看到战前的津田积极构建 “日本国民思想史”的努力,以及战后的津田意欲重建 “日本民族主体性”的狂热。
战前的津田坚持 “中国无国民但姑且是民族”的论断。津田以西方的政治观念,即现代意义上的 “国家”与 “国民”概念为标准,使用诸如 “统治者”和 “被统治者”的称呼,将拥有至高权力的 “帝王”(包括以帝王为权力本源的知识阶层)和仅被前者视为纳税者的下层 “民众”相分离,指出中国的历史事实上只是王朝史,即个人的历史,而非作为民族性集团的国民史。(11)津田说道: “‘支那’民族有政治性统一之时,亦有分裂之时,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没有使其民众作为国民结合在一起。”参见津田左右吉《王道政治思想》(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4页)。在此基础上,津田断言中国不仅对内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曾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对外亦是如此。在《王道政治思想》中,津田说道:“当‘支那’帝王的权力蔓延到周边地区,其民族文化就会受到周边异民族的尊崇,如此则‘支那’民族的帝王就会在思想上君临全世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思想,皆因其帝王统治下的民众,事实上没有与他国国民处于对立状态且在此意义上成为统一的国民。”[16]6基于土地过于广大与社会组织过于散漫等内在原因,加之周边未形成永久性国家的外在因素,津田没有将中国的民众视为一个民族性集团,很少使用 “国民”的称呼,而至多使用 “民族”或 “民众”的说法。以至于在他的心中,即便使用 “‘支那’民族”或 “整个民族”的说法,亦不过是所谓的 “权宜之计”。[16]5
战后,津田在1946年6月发表《所谓的“支那”的历史》一文,完全否定 “作为民族的中国”。以 “历史的主体是某种意义上的集团生活,而这一集团生活作为民族或国民的意义最为深远”[28]400的认识为前提,津田在战前否认中国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的基础上,舍弃其自称的 “权宜之计”,公然断言:“对于‘支那’人来说,没有作为一个民族的集团式生活,抑或至少没有使之意识到,故而在此意义上没有民族史。”[28]420在战后津田的眼中,中国没有 “民族史”,有的只是 “王朝史”(他认为 “中华民国”的称呼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 “清朝”这一王朝名的替代物),因而无论从史书的撰述形式(纪传体)还是记述内容(史料堆砌)来看,中国所拥有的都只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记事与史料编纂。事实上,津田在战后坚称中国没有 “民族史”的原因,与其在战前所论证的中国没有塑造出 “国民”的逻辑大致相同,皆因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未与周边民族形成明确的对立关系,是以存在于他们心中的只有空虚的中华意识与民族优越感。这就是津田在战前所提及的 “‘支那’远离其他民族而生活着,抑或只靠他们自己就形成了一个世界”[16]3,亦是其在战后所主张的 “在迄今为止的‘支那’人的思想中,存在的是只有‘支那’人的世界,该世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28]422
与之相对,津田始终强调日本人具有特殊的国民性与民族性,不过其言论重点在战前与战后略有不同。战前的津田更关注国民性的问题。由明治初年启蒙思想家们所塑造出的 “日本有国民”的形象,(12)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指出: “明治维新为应对西欧的冲击而建设与万国对峙的国家,同时也是形成国民的过程。”参见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等译《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序第6页)。正是津田敢于宣称的 “‘支那’无国民”认识的前提。在积极评价所谓的 “作为民族性集团的日本国民”的同时,津田通过撰写《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我国国民思想研究》(贵族文学、武士文学、平民文学的时代)三部曲,尝试建构出日本民族 “自古至今”都存在的所谓 “国民思想史”。但到日本战败以后,面对该时期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否定日本肯定中国” “视日本民族为低劣民族”[29]的思想,津田认为必须在战后重建日本民族的主体性,因而更加重视民族问题。津田声称日本民族在战后亦是作为民族的结合,其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因而 “在文化上,日本人绝不能把自己放在应该被轻视的位置之上。”[29]与 “非民族的中国”相映照,津田在战后的文章中更加频繁地连用 “日本民族日本国民”的说法,屡屡高呼 “日本是独特的日本”[30]或 “日本是独一无二的”[26]494。在1958年的《日本历史的时代划分》中,津田更进一步地强调日本民族发展的连续性与主体性。他认为,对内 “日本国民内部没有异民族,其他国民内部也不存在与日本民族相似的民族”,对外则 “即便屡屡接触不同的国民、不同的文明,但是这些接触无论如何都以日本为本位与主体,据此则日本得以形成其独特的文化。”[31]508-509与战前肯定 “历史的变化发展”不同,战后的津田格外突出所谓的 “历史的恒久性”,他认为日本所特有的 “国民史”源于其 “民族的生命、国民的生命的无间断的发展”[31]509,万世一系的日本皇室乃其标志。在此处,津田所试图肯定的不再是战前所说的推动社会变化的 “革命的精神”,而是 “作为国家的象征、作为国民生活的连贯性发展的象征”的皇室,后者使生活于其中的国民难以察觉到时间的发展变化。[31]510战后的津田尤其重视这一时间上的连续性,他认为 “人”的生活,作为个人来说,通常是过完昨日、活在今日以及在不知何时进入到明日,作为国民来说,亦是如此,在不知不觉中,世间发生了变化。[31]510
要理解津田对 “中国是否是一个民族性集团”的认识转变,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支那”的历史》的发表时间。如前文所述,《所谓的“支那”的历史》持 “中国非民族”论,指称中国从未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其帝王乃专制权力的中心,与人民没有直接联系。该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月,而在此之前的1946年3月的《“支那”文化研究的态度》中仍然随处可见 “中国民族”的说法。但在这两篇文章之间的1946年4月,津田发表《建国之事情与万世一系之思想》一文,宣称日本始终是一个民族性集团,其永恒的象征乃 “万世一系的皇室”。对照4月与6月的这两篇文章,“非民族的中国”与 “作为民族的日本”的形象可谓对立。
五、结 语
从战前到战后,若以家永所说的津田存在 “一定程度的思想倒退”,即 “变化的日本观”为参照系,那么津田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认识可谓停滞不变,其始终秉持 “停滞的中国”与 “自由的日本”的对立构图。但在另一方面,津田对中国民族的理解却略有差异,从战前 “中国无国民但姑且是民族”的观点彻底转向战后的 “中国非民族”论。
就 “不变的中国观”而言,战前和战后的津田虽然坚称其使用所谓的 “原典批判”的实证研究方法,但事实上又始终参照 “西洋文化=现代文化=世界文化”的公式,极其片面而刻板地评价中国的思想发展。如何积极导入、摄取西洋的思想,是明治初年启蒙思想家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战前的津田将西方文化视为某种 “绝对之物”,其全部的思想认识就是以明治时期两次大战的胜利为背景,极力证明日本文化相较于中国文化所拥有的主体性和优越性。换言之,津田继承明治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封建性、因袭性的思想观念,[32]以西方文化为先验性标准来描摹 “进步的日本”和 “停滞的中国”的形象,对被其视为 “外来之物”的日本儒学及作为其 “根源”的中国儒学展开极其激烈乃至颇有自我循环论证之嫌的批判与否定。
就 “变化的中国观”而言,战前的津田以构筑近代日本国民思想史为研究课题,在否定中国存在现代意义上的 “国民”及 “国民史”的前提下,塑造出 “有国民的日本”与 “无国民的中国”的对立构图。战前的津田姑且以使用 “中国民族”一词,为其所谓的 “权宜之计”,而战后的津田则直面中日之间地位逆转的政治现实与战后日本人对日本民族性的猛烈批判,以战后日本人该如何重建其民族主体性为核心问题,积极鼓吹 “中国非民族”论,试图通过持续性地贬低 “他者”以重建日本民族所谓的 “主体性”与 “优越性”。
总的来说,在津田的全部认识中,无论是在战前以 “中国无国民”来构筑近代日本的 “国民思想史”,还是在战后试图以 “中国非民族”来重构战后日本的 “民族主体性”,中国始终是一个绝对的、落后的 “他者”。在此意义上,战后津田的中国观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呈现出家永所说的明显的 “思想的倒退”,倒不如说是更多地显示出津田作为非学院派思想史家所具有的某种 “非理性”的侧面。津田不仅对中国文化进行激烈批判,其对西方文化的利用亦呈现出浅薄的拿来主义姿态,这从他为证明日本文化的所谓 “主体性”,而在大正年间不断抹杀曾经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客观事实,[5]257且在晚年亦拒不承认其学问方法借鉴自西方学说[5]99的态度中可见一斑。换言之,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津田左右吉或许都不是所谓的 “政治性禁欲”的书斋型学者,他对中国文化的极端蔑视及对中国民族性的刻意贬低,集中显示出津田其人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