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言
张定浩
一
我自己的写作,从严格意义上,或者说,从进入公众领域的层面,大约开始于在《书城杂志》连载的“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系列,后来它们结集成《既见君子》那本小书。当然,在那之前也一直在写,写诗,写书评,写时评和影评专栏,写论文,但都散乱,那种散乱的写作大多是一种消耗,是学徒期的左冲右撞,不能构成和自我生命的互补。《既见君子》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新的开端,想想动笔的时候,尚且还是二○○八年初,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回想起来,这本小书是在一种非常寂寞也非常混乱的心境中开始的,而每写完一篇,都会增加一分安宁。我一直很怀念那样的状态。
《既见君子》中那篇同名文章就是在写《诗经》,我挑出《诗经》中提到“既见君子”这句话的一些篇章,用一些我觉得尚有意思的体会,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如果说《既见君子》的写法还是偏重比兴,天上地下,东一句西一句,是某种意义上的性情文章,那么等到后来二○一六年春天,《文汇报》笔会副刊的周毅约我开一个有关《诗经》解读的专栏时,我的想法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次我希望可以用赋的方式,老老实实地一首首把《诗经》中我喜欢的诗篇讲清楚,且讲出前人所未讲之处,不光是疏通文句,更要贯通诗意,讲明这些诗何以成为诗,并从中体味诗。所以我要做的就不是写我自己,而是写这些诗;也不是求一个正解,而是求得某种属于诗的统一,是文字、句法、音韵、气息、意思、感情等多方面的统一。我觉得最好的诗未必能解释,但都是可描述的,只要我们信任那些诗人,信任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词,每一处沉默,信任它们一同所构成的那个完美坚实的存在,而诗不单是想象和哲思,诗也在这些踏实细密处。

写《诗经》文章的时候,紧挨书桌的床头摊了十几本注疏集释,电脑上又同时打开着一堆电子版的相关文献,也在知网上看一些新的文章,关于某个字、某个句子,关于某个器物,每一句都是各家说法都看一遍,比较,参详,但并不是要做裁判员和调解员,而是看完之后再自己慢慢想,想着想着就会有一点新东西出来,仿佛离那个写诗的人又近了一些。这个过程就是把自己放弃的过程,因为自己的一点点诗意是不重要的。知道自己是不重要的,随后才有切实的工夫,去吸收、感受、思索和书写。朱东润《诗心论发凡》:“治诗三百五篇之学者,则必博搜冥考,追求百家之遗说,折衷于事理之当然,而后能惬心贵当,怡然理顺,不得以一先生之说自囿也。”
这样的写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三年,其实也不过就写了六篇。后来周毅忽然去世了,没有了她那样永远怀揣“肯定的火焰”的督促者,我也就懈怠下来。加上又有其他写作任务缠身,有关《诗经》的写作热情就消退成我笔记本电脑中一个长久不再更新的文件夹。
直到二○二二年。对每个中国人来讲,这一年都是一个难忘的年份。而对我来讲,这一年的难忘收获是终于重新拾起搁置许久的《诗经》解读,并再次在我喜爱的《书城杂志》上连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鸡鸣并不是为了对抗什么,而只是对于如晦风雨的漠视。
二
詩似乎是不可谈论的,但至少每一首好诗都经得起反复地读。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尤其是在离开学校之后,有时候会疑惑为什么还要读《诗经》,其价值何在?对我而言,单纯的审美或陶冶性灵之类的理由,是远远不够的,也没有力量,因为任何愿望,一旦仅仅出于某种理由,它就一定可以因为另外更重大的理由被抛弃。而一个人最终不可抛弃也无法抛弃的,是他还没有获得之物,也就是他所欠缺之物。某种程度上,诗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种尚未获得、始终在前方的存在。我总是带着问题和欠缺感,去读那些过去的诗。而那些过去的诗也得以在这样的阅读中转化成即将到来的诗。从而,让自己的写作本身,成为一种更为积极的阅读,成为一种对于“为什么要读诗”的回答。
唯有如此,阅读《诗经》才不至于沦为一种玩弄风雅之事,不至于成为一种逃遁,抑或一种现代生活的对立面。
倘若单纯从鉴赏审美的角度去看《诗经》中的一首首诗,就好像在博物馆里看一幅幅画,其中的典故风物人情,以及用笔着色的曲折有度,都可以作很多社会学和文化史乃至艺术史上的解释,这些本身都是知识,也很好,但最后,和我们自己没有关系。我理解的《诗经》,恰恰不是知识,不是能够用搜索引擎搜索到的答案。若是谈到古典修养,在我看来,能够背多少古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打动的。
威廉·布莱克有一首写弥尔顿的诗,里面有几句是这样的:“但是弥尔顿钻进了我的脚;我看见……/但我不知道他是弥尔顿,因为人不能知道/穿过他身体的是什么,直到空间和时间/揭示出永恒的秘密。”

一个人被什么东西打动、穿过,其实自己最初是不知道的。而类似诗歌鉴赏辞典之类的存在,抑或某些诗歌赏析文章,是预设自己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了,这种预设在我看来稍微有点问题。那些能够被感受但不能自知的东西,都和自己的生活有关;那些自以为知道的,其实只是和自己无关的知识。而把那些穿过自己身体的东西,重新在回忆中审视,并且慢慢地尝试去理解它,这就是《诗经·大雅》里反复讲到的“缉熙”,所谓“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所谓“缉熙敬止”,这些天地自然的光,如何一点点成就到人的身上,并让一个人成为值得敬重的人,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才是诗。而这种穿过身体之物,在不同年龄段是不一样的。比如二三十岁的时候,或许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到了四五十岁,也许就换作“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因此,要理解《诗经》,唯有先理解现在,理解自己和时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打通古今,融贯中西,就不仅仅是每一个有志向的学者孜孜以求的事情,而是每一个对古典世界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都应该有的想法。
三
谈论《诗经》,和谈论一切事物一样,我觉得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具体化。唯有具体,才能切身,也才谈得上所谓的为己之学。凡事一旦笼而观之,难免或卑或亢。国学家、复古主义者乃至诗文鉴赏家,想象存在一个已经死去的、完全和现在不相干甚至敌对的古典世界,然后,或招魂祭奠,或消费赏玩,这是卑;而爱思想的人习惯于轻蔑《诗经》中一切文学的成分,爱文学的人则本能地排斥《诗经》中的经学教诲,这是亢。
古典诗的具体世界,一如长河,总有上行和下行两条路线。废名引晚唐人的诗句“春雨有五色,洒来花旋成”,说,“这总不是晚唐以前的诗里所有的,以前人对于雨总是‘雨中山果落‘春帆细雨来这一类闲逸的诗兴,到了晚唐人,他却望着天空的雨想到花想到颜色上去了”,又说,“各时代的诗都可作如是观,三百篇,古诗十九首,魏晋的诗,我们今日接触起来,都感得出这些诗里情感的变化”。这是沿坡而下,体会一处处即将到来的、开疆拓土的新鲜。此外,废名区别旧诗与新诗,“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是诗的;新诗则要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这其实很接近奥登对于古今诗歌的分辨,“早期的诗歌用迂回复杂的方式讲述简单的事,现代诗歌则试图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言说复杂的事情”。这种细微的辨识,无论中西,一定都是要出入新旧古今之间方能做到。真正的新旧无关文体和时代,旧体诗依旧可以写出新感受,如陈寅恪的“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而白话新诗依旧是可以迂腐不堪的,如今日随处可见的口水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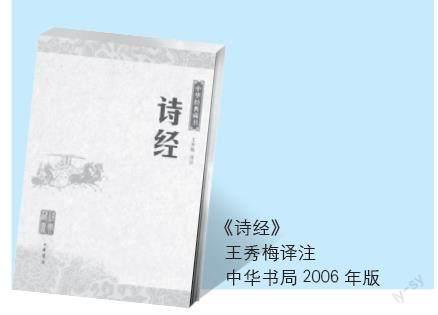
在由古至今的下行路线之外,还有自今逾古的上行之路。如曹丕《燕歌行》“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这种对于夜晚孤寂难挨的痛彻感受,在后世诗文中屡见不鲜,有时还会转向另一种极端,所谓“夜长酒多乐未央”。但若将这些诗文与它们所共同援引的原典《诗经·小雅·庭燎》相对照,会发现后者似乎更有一种刚健之气,因为在《庭燎》中,有一个从“夜未央”到“夜乡晨”的变化,它不是要用纵情欢乐来抵御没有希望的夜晚的冷意,而是有力量看到一个即将到来的清晨;它不是不要面对烦恼,而是明白生活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它要你不断往前走,向上走,向着光明走,慢慢地,你会发现那些曾经的烦恼都变得不那么重要。如此逆流而上的阅读,才能体会曾经有过的、振拔峻深的新鲜。
进而,所谓“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中国的古典诗人无一例外都受过《诗经》的滋养,所以读《诗经》就成为这么一个上下求索的过程,之后得出一个图景,一个结构,一个谱系,这个图景、结构或谱系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而是读诗人自己在阅读中被拓展的生命。
四
如果再具体一点,那么阅读《诗经》首先就要回到最基本的字词层面,要明白《诗经》中的每个字词都有其意义。我觉得有两类字词很重要却也很容易被《诗经》解读者忽视,一是虚字,二是同义词。
无论古今,实字与虚字是文法的两端。写诗文的人自然会虚实兼顾,但注解诗文的人往往顾实不顾虚。读历代《诗经》注疏,其中最语焉不详的地方就是对虚字的解释,往往一句“发语辞”,或“语辞,无义”,就打发了。而《诗经》的特别之处,正在于其中有大量的虚字,某种程度上,虚字也是铸就一个人诗歌语感的基础。
因为诗歌的交流,很多时候并非概念上的交流,而是感受性的。这种感受性,需要时间来承载。每一行诗句,不仅仅在讲述意义,也在消耗、占用和重新分配时间,这有点类似音乐给予我们的感觉,是那些声音构成时间,也构成所谓的“现在”,并铭刻成我们意识中的连续性感受。出没在《诗经》中的虚字,看似无意义,却发出实实在在的声音,这声音讲述某种不可讲述之物,它呼唤我们进入其声音的场域,和它分享一段被诗歌捕获的时间。
同时,在发出声音填充时间之外,这些虚字一方面有其原本的实在意义,另一方面有其当下的具体而微的指向,而我们要明白一首诗的确切意思,很多时候恰恰要依赖这种虚字的引导。王筠《文字蒙求》:“百官以治,万象以察,知文字为记事,世之虚字,皆借实字为之也。”历代有不少专门解释虚字的著作,我个人觉得清代学者袁仁林的《虚字说》最有启发,因为他很注重体贴和分辨不同虚字中所尝试表达的不同神情声气。当然,如果同时再参考类似《说文解字》或《故训汇纂》这样的训诂学著作,知晓每一个字的本源和去向,这对于理解诗意乃至理解古典思想,也是非常有益的。
在虚字之外,还有同义词的辨析。很多人认为《诗经》中那些复沓段落的换字都只是为了押韵,或为了节奏,而意思并没有多少改变。这种看法,多少有点小看了诗,正如方玉润提到的,“诗人用字自有浅深,次序井然”。在《诗经》中一首诗的不同章节中出现的诸多同义词,其中往往有其微妙诗意的转折递进和语气运用,而辨别这种差异本身也是对个人情感细腻程度的训练,因为读诗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加敏锐,也更准确。
五
在字词层面的具体之外,还有思想层面的具体。
我觉得今天的《诗经》解读有两个很常见的倾向。一是将《诗经》尤其是《国风》简单地视为民间歌谣,二是用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来解释《诗经》。这两个倾向都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自然有一些特别让人瞩目的启发,但他们多多少少都轻视了《诗经》中本来蕴含着的政教维度,把《诗经》变成了五四观念下的民间文学,或者是一堆做论文用的历史材料,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记述。比方说当代《诗经》解读者特别喜欢追随日本汉学家从祭祀的角度来解释《诗经》中的诸多篇章,而无视中国古典思想对于祭祀这件事的基本态度。《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又说,“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古典思想是要把所有鬼神层面的东西都落实到世间具体的人身上,强调每个人固然有天命的东西在,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在尘世间的自强不息。所以如果单純从祭祀的层面去解读《诗经》,很多篇章当然也可以解释得通,但其中的那种“古典诗教”就在无形中散失了。

我们都知道《诗经》是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那么,什么叫风?风是一种来自大地的气息,不同地方有不同地方的风,这是风的特殊性;暖风习习,能化育万物,冷风一吹,却也能让人头脑清醒,这又是风的普遍性。风又通讽。我觉得一首好诗始终都有两方面的作用,它一方面温暖你,另一方面又让你感受到一丝寒意,让你清醒和震动,从自以为是中摆脱出来,一首好诗总是通过某种方式隐隐约约地在教育它的读者。《诗大序》讲:“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上,人君通过诗来教化臣下;在下,人臣通过诗来讽谏君上。言之者无罪,因为诗讲究敦厚委婉,并不直接批评君王;闻之者足戒,是因为人君通过听取诗中的讽谏来反省自己的过错。因此,所谓风,其实是一种君臣之间沟通交流的方式。那么,风、雅、颂的区别在哪里呢?“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简而言之,风涉及的是一个诸侯国范围内的事情,所以有十五国风;雅涉及的是整个天下的事情,也就是王政之事;颂,则是涉及神人关系,也就是类似宗教祭祀之类的事情。综上,无论风雅颂,都不仅只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也不仅只是某种人类学意义上的非虚构纪实,而是通过委婉的讽谏来褒贬善恶是非,以达到教化和修身的目的。
但这种诗教,又不能仅仅追溯到大一统帝国形成时期的汉代经学为止。我们要理解《诗经》中蕴藏的古典诗教,那么至少要有一个抱负,就是有能力回到先秦古典思想世界中去,回到孔子谈论诗经的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也不是能一下子有什么捷径可以穿越回去的,因为这是一条文明的长河,你要走到源头,就要从下游逆流而上,蹚过这全部的河水,从二十世纪上半叶至清再至两宋、两汉,只有这样,那個走到源头的你,才是携带着每一个今天走到最初那个今天的探索者。
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出土文献当然会有帮助。比如《孔子诗论》的发现,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汉代经学所奠定的历史性解读和政治性解读的权威,我们由此确定,至少在战国时期的《诗经》传授者那里,尤其对于《国风》中的诸多篇章,他们就已经拥有非常自由、宽容与平等的诠释态度。在他们的解读中,重要的不是考证一首诗原本指涉的历史情境,而是体会这首诗有可能得以应用的当下和将来的情境。唯有如此,一首诗才能够在一个个不同的时空中流传,也因为如此,孔子才说:“不学诗,无以言。”
但有关《诗经》的出土文献的发现,绝不意味着对传世文献的抛弃,也不意味着我们瞬间掌握了一种新的有关《诗经》的真理。对此,柯马丁说得很好:“《孔子诗论》也许使我们更靠近《诗》起源或编纂的时代,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去除了我们或许曾经抱持过的、自以为是的确定性。”这种自以为是的确定性,不仅属于毛诗,也属于三家诗,属于朱熹的《诗集传》,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诗经》解读,而去除这过往《诗经》诠释中的种种确定性,不意味着抛弃过往的《诗经》诠释,而是要将它们汇入一条更广阔的河流中,属于诗的河流。
六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真的有可能恢复《诗经》的原貌吗?或者说,我们有能力恢复整个古典诗教传统在当时所拥有的活力吗?以古典学的名义从事种种政治学的谋划,这种类似公羊学家们的野心,我至少是没有的,甚至觉得这是行不通的。
在一篇谈论本雅明的动人文章中,汉娜·阿伦特指出:“就过去已经变成传统而言,它拥有权威;就权威历史性地展现自身而言,它变成了传统。瓦尔特·本雅明意识到,发生在他有生之年的传统的断裂和权威的丧失是无可挽救的,他总结说,他必须发现处理过去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就是“捡拾思想的碎片”,阿伦特形象地将其比喻成深海采珠,“就像深海采珠人,他不是去开掘海底,把它带进光明,而是尽力摘取奇珍异宝,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然后把它们带到水面之上。这种思考乃是沉到历史的海底—但这并不是为了恢复它曾经的样子,而是为了让逝去的时代有机会获得新生。引导这种思考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虽然生命必定受时间之衰败的支配,但是衰败的过程同样也是结晶的过程,在大海的深处,曾经存活的生命沉没了,分解了,有些东西经受了大海的变化,以新的结晶形式和模样存活下来,保持了对腐败的免疫力,仿佛它们只是等待着有一天采珠人来到这里,把它们带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种‘丰富而陌生的东西。”(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
这个说法与约翰·T.汉密尔顿在谈到十八世纪德国天才们对品达的接受史时的说法不约而同:“传统为什么必须在碎片中显示自己,这才是原因所在。这些碎片丧失了过去的真实,它们为此疼痛不已,但对未来是新的真实,它们仍有渴望,而且这些疼痛根本不能与渴望相提并论。”
诗三百,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教传统,虽然在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其中依旧有很多值得被我们铭记、能够让我们震动的诗句和篇章。我希望它们在这个时代能获得新的生命。
在这个时代,很多写作者都会有一种无力感,他们会抱怨说文字是无力的,说作家是没用的,但很多时候,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写出有力量的文字,或者说,他们自己写下的文字和他们的行为是割裂的。这些无力感缠身的写作者应该先问问自己,我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首先把文字视为一件真正有力量的东西而加以珍重呢?如果你把文字只当作一个假的东西,当作某种功利性的手段,如果你自己写下的文字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然后你再抱怨说这些文字是没有力量的,这就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在中西古典思想中所谓的“修辞立其诚”,所谓的“道成肉身”,讲的也正是言辞与生命之间彼此交融的关系。
诗可以言。一首好诗正是有力量的言辞和有力量的生命的结合,它是可以被逐字逐句讲述的,它也能帮助我们学会更准确地表达与更深刻地交流,同时,一首好诗它自己也会说话,它穿过很多个纷乱的时代,收容了很多诚恳的生命,再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要做的,唯有倾听。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八十九期所做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