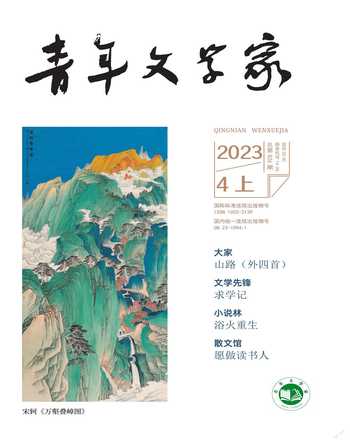追忆曾经的村小
龚银袁
故乡斯茅坪的村小,曾为目不识丁的农村放牛娃带来了融入现代社会的机会。我也有过两年在斯茅坪小学读书的时光,那条上学路和上学的日子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是艰辛的,同时又是快乐美好的。
斯茅坪小学在大堰塘下,两排白色的房子盖着黑瓦,两排房子中间就是操场。一旦下课钟敲响,安静的操场瞬间像炸开了锅一样。追逐皮球的、滚铁环的、跳绳的,无处不有其乐趣。这是我还没去读书时,在山上经常能见到的。后来某一天,我也被送到了那个地方。
我家住在山顶的垭口上,每天从家门口路过的人络绎不绝,从门口路过,去上学的娃儿也是不少。垭口走到山脚的斯茅坪小学,路程不算近。路上要经过一段丛林,到了春冬季落了雨,坡陡路滑不摔几跤是到不了学校的。道路两旁树枝上的露水也能让全身湿透,只能坐到教室打着寒战,让身体的热量慢慢把衣服烘干。大堰塘下有不少秧田,踩著稀泥路滑倒在秧田里也是常有的事。到了夏季,中午放学的路似乎又变得艰难了。从学校仰望山顶冒着炊烟的房子,衡量一下灼在头上的烈日,又摸摸早已咕咕叫的肚子,犹豫再三,还是鼓足勇气踏上了回家吃午饭的路。走到半路口渴了,遇到人家时,就嘴巴甜点儿,总会借来一瓢水。
回家吃了午饭,又赶紧返回学校。面对这条陡峭的上学路,中午偷懒不回去也是经常的。那时,母亲就会请从我家门口路过的学生,给我捎带上一瓷盅饭和一些咸菜,可长久这样也不是办法。后来,有人就带上锅碗在学校外的山包上架起灶来。学校下面不远处有一个小水凼,就从那儿打来水煮饭。再后来,越来越多的同学不愿意中午再冒着烈日走那条山路,山包上煮饭的人便逐渐多了起来。我也加入到了同村高年级同学搭伙煮饭的队伍中。我力气小,抬水抬不动,煮饭煮不来,剩下的就只有去捡柴了。可大柴捡不动,小柴不经烧,我俨然成了一个没用的人。在煮饭的队伍中是不中用的,自然也就受到个别人的排挤,我只好重新开始大中午爬那段山路。
后来,父亲和村小的喻老师商量了一下,让我背上大米去喻老师那里,让师娘帮忙煮饭。喻老师欣然同意,这才又省去了中午那趟往返上学路的麻烦。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离开村小。
后来,听说村小为了解决学生中午的吃饭问题,开始统一在学校集体蒸饭了,这为距离村小较远的学生解决了中午吃饭这一件大麻烦事,对那些住在山上的学生来说,更是一大幸福事。
那时年龄小,不懂事,我们大都没认真读书。留课是常事,打架也成了放学后的一大乐趣。回家必经之处的大堰塘处有一条岔路,一边往尖山子、欧家坪,另一边通往汤家垭口水库方向。这两条路上的学生,也分别来自两个村。两个方向的学生都想当“老大”,一般都是在分路的时候,两边的“老大”各自带着自己的小弟混战,直至打到对方认输才肯罢手。当然,也有内讧的时候,有自认为“老大”不行,想挑战“老大”权威的,被按在地上,或是骑在身上打服了才算完事。我年龄小,个头儿也小,所以打架的事完全不参与,只在一旁看热闹。
那条上学路是我童趣的天堂。我会留意能够做弹弓的树枝,每天经过时就会偷偷地看一眼,生怕被其他同学发现;我也会抓一条四脚蛇装在文具盒里把玩儿一个下午,抑或在河沟中用麻绳捉螃蟹,将绳子拴在蟹钳上,我们拉着绳子看螃蟹举着蟹钳、吐着泡沫逃跑。
那个村小是我学习文化知识的启蒙地,也是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乐土。
种种原因,曾经承载着一代人希望和山里孩子对未知世界憧憬的乡村小学,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中。
从此,斯茅坪变得静谧,教室里、操场上也已听不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村小不是没落了,只是完成了它在那一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