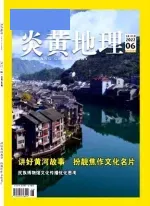简论明清时期新安县尚武景观的文化特质
朱修春 刘茗 薛晓萍
明清时期广州新安县地区存在大量海防城池、将军祠庙等尚武建筑景观。这些景观既是新安县军民保家卫国的见证,也是地方整合了中央王朝和地方社会内部互动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均体现在历史时期官方与民间对尚武传统的利用与继承过程中,深刻呈现出深港地区的社会风貌,对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文化景观是历史长河中人类与自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驱动下,相互影响并紧密结合所形成的作品,并随着人类活动的作用而不断变化,能够深刻反映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进化历程[1]。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实地留存中,不难发现众多形制与用途各异的景观建筑。这些建筑既依托山川湖海等自然景观存在,又与该地区的人文背景相辅相成,不仅能够反映自身所代表的宗教信仰和具备的功用,更能折射出当地社会的发展状况。明清时期广州新安地区大量尚武遗存蕴含的文化特质便十分值得探讨。
明清时期新安县尚武景观概况
明朝初年,今深圳隶属东莞县。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政府分别在此设立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两座城池,实行卫所制与军户世袭制。此后又经迁界、复界,于明万历元年(1573)恢复建制,更名为新安县。此地三面临海,一面临山。新安县炎热多雨,常有飓风,造成该地区土薄山深,农商不显,仅得海洋之利。因此,新安自古就是南部沿海的重要口岸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许多种族、文明杂居和交流之所。出海经营固可获利,但也存在着巨大风险。脆弱的经济基础和从大海中获利的危险使人们更易于向鬼神寻求帮助和庇佑,因而该地多崇尚鬼神,坛庙林立。而“尚武”恰恰是明清时期新安县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化传统之一。
“一定的文化形态与一定区域的地理生态条件和人文历史分不开,它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2]新安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了尚武传统景观的发展。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与战略性,使得广东新安县在明清时期沿海倭乱频发的背景下首当其冲,而残酷的战争环境又催生了尚武建筑的大量涌现。明清时期新安地区的尚武建筑景观种类多样,包括大量城池、军事工事、武官官署、官兵居所(兵房与将军第)等。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朝分别在东莞县治南和东莞县东南四百里滨海两地设立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并随之建立起东莞守御所城和大鹏所城这两座防御性城池。其他军事工事则有城垣、雉堞、吊桥、濠沟、炮台、警铺、墩台、塘房、营盘、汛房等建筑。此外,还有许多将军及其家属的墓葬群、用以祭祀的祠庙,后者的祭祀主体均为历朝于军事有所建树的将军、谋士以及普通平民,包括忠义祠、汪刘二公祠、侯王庙、谭公庙等;而祭祀方式则既有针对单个人物的祭祀,也有针对全体将士的集体祭祀仪式。
明清时期广东新安县尚武文化传统和庞大尚武建筑群落,既是新安军民保家卫国的见证,也是地方整合入中央王朝和地方社会内部互动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
明清时期新安县尚武景观与尚武传统的文化特质
著名华南研究专家刘志伟教授曾指出,对岭南山地人群的社会组织、信仰、仪式、婚姻以及亲属制度的研究能够令我们看到存在于这个地区的文化层面与更大的文化系统之间长久的整合过程及其机制[3]。特殊的地理环境、沉重的海防任务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新安地区的尚武建筑群落及其所代表的尚武传统。这一传统又为政府官吏、地方士绅所传承,通过营建祠庙、举行祭祀仪式、推广儒学教育和忠义理念等行为,对尚武文化加以弘扬,用以升华当地民众共同的信仰与情感,进而教化人心、维护统治。这一过程既展现了明清时期广州新安地区尚武景观与尚武传统的生成与发展,也折射出其中蕴藉的王朝体系下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整合机制,即借助地方信仰的影响力,将地方社会整合入中央,同时促进地方内部整合。而内部的整合,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地方融入中央统治秩序的进程。这种长久而动态的整合机制,正是新安县尚武景观与尚武传统深刻的文化特质。
对于新安县乃至广州地区来说,这一双向的整合、互动进程开始较晚,于明清两季最为活跃。新安地区历史悠久,秦朝时曾划归南海郡统辖,逐渐开始融入中原文化。“自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表,兹邑礼义之渐所由来矣。”[4]但直到唐代,岭南地区仍被中原人看作古怪野蛮之地。北宋灭亡后,南宋朝廷南移,“从此,王朝政权不再把广州当成摆满奇珍异宝的百货店,而开始希望把广州的精英整合到王朝之内。”[5]明清时期,这一“整合”在新安地区通过发挥尚武景观与尚武传统的文化特质得以展现,具体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将地方整合入王朝
明清时期,政府大力推广儒学教育,儒学教育工具化趋势日益明显。新安地区此时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学科和学制,儒学的影响与日俱增。万历二十三年(1595),知县教谕施孔训。康熙八年(1669)则“复用八股,复岁贡”[6],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又诏岁科两试,俱取一名入府学。中央通过完善学制、推崇儒学、在地方建立推崇忠义的祠庙和举行各种祭祀英雄先烈的活动来教化人心,引导百姓忠诚报国,从而实现国家维护统治的最终目的。儒学的推广使得忠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而忠义理念又激励将士们捐躯为国、誓死抗争,从而推动了新安地区尚武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地方官吏和士绅主要通过重修学宫、举行乡饮酒礼等措施推崇忠义。康熙年间,知县张明达捐俸,“倡修越岁教谕。”[7]司正举酒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8]身為国家政权的地方代表,士大夫们也在竭力向百姓灌输忠君报国的观念。“作为居间于国家和乡土社会的双重身份的‘代理人,地方士绅熟悉国家与乡土两种话语系统。”[9]因此,地方士绅不仅需要服从于国家,向百姓阐释忠义理念,也需要立足平民的立场,将“忠义”这类难以在乡民语境中被理解的抽象概念,转变成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亲族和乡里关系,由此来稳定秩序。同时,借助统治者权威与神灵的力量,地方士绅也在潜移默化中扩大自己的势力,而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又不得不依仗这些地方势力。
由此可见,在新安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大力推崇忠义和儒学教化,引导军民忠于国家、舍生忘死,促进了尚武传统的发展。这也正体现出在中央与地方互动的双轨机制之下,地方社会被整合入中央的过程。
地方社会的内部整合
“一个群体,除了要有一定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之外,更需要有精神和思想上的统一。而民间信仰则具有维护其统一的巨大凝聚力,通过群体性的祭祀活动,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升华为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10]在浓厚的军事氛围下,新安地区多样化的民间信仰与承载它们的祠庙和祭祀仪式凝聚了民心,使得拥有共同记忆和精神寄托的新安百姓团结成一个情感共通的整体,从而实现地方内部的整合。“当人们聚居某地,无论人数多少,没有建庙就只是一处生活聚落,而不被视为独立的村落共同体。惟有兴修了庙宇,建立起人鬼神俱全的天地宇宙系统,这一聚落才具有了立村资格,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建立与‘国家的直接联系,人们成为‘化内之民。”[11]通过情感和记忆的共通,新安民众逐步形成一个互相认同彼此身份的共同体。他们身处动乱多发的海疆边陲,多数人口是卫所的世袭军户,需要共同承担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有着相同的谭公信仰、侯王信仰,会在特定时间点、怀着相似的诉求,一起前往祠庙举行新安特有的祭祀仪式。这一切都为实现内部整合提供了条件。而内部整合恰恰是地方进一步与国家建立联系,整合入国家体系的前提。
“在安土重迁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民众的乡土感情很重,本地的民间信仰往往成为维系乡土渊源的纽带,是抵御外部力量的象征。”[12]被王朝整合起来的新安民众,为了保护家园免受摧残,又会奋力抗击侵略,从而再一次促进尚武传统的发展和尚武景观设施的建设。
总之,明清新安沿海地区的尚武传统,与战争背景相辅相成。前线作战的紧张局势,上阵杀敌、鼓舞士气、崇尚武力的现实诉求、全民皆兵的人口构成,使得新安长期笼罩在军事和尚武的氛围中。残酷的战争为新安地区培育出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他们骁勇善战、深受人民爱戴。同时,这些将军和纪念他们的祠庙又会激励一代又一代军民勇往直前、保家卫国。祠庙建筑群既是尚武传统下的产物,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尚武传统的发展,构成了新安百姓独有的群体历史记忆。
明清时期新安县尚武景观与尚武传统的当代启示
“纪念空间具有塑造记忆的功能。而社会记忆又是民族或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可以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13]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与渗透较弱,国家无力在地方修建大量公共设施,多数纪念空间属于社区性质。在区域社会中,中央与地方常常保持双轨互动模式,拥有广泛社会关系、财力和影响力的士绅作为中央象征性权威在地方的代表,“是民间祠庙修建最主要、也是最持久的动力。”[14]明清时期政府正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儒学文化与尚武传统相结合的手段,在新安地区修筑纪念馆、塑造忠义观念,引导人们忠于国家、保卫领土。作为当地社会风貌的深刻呈现,明清时期新安地区的尚武建筑群落及其所代表的尚武传统,对我们今天利用、保护与传承深港地区历史地理文化与民风民俗深具启示。
以清代新安地区享誉一方的“将军村”大鹏所城为例,这一军事要塞曾经涌现出无数功勋卓著的将领英豪,既有与宋朝杨家将齐名的赖氏家族“三代五将”, 为保卫清廷广东海疆立下汗马功劳,也走出了有“父子将军”之称的武显将军刘仕开与福建水师提督将军刘起龙。这些塑造了新安尚武传统的重要人物,不仅督建了众多海防设施,也留下了存世至今的将军第、祠庙、墓地等景观,使之成为今天深圳大鹏新区乃至整个深圳地区尚武传统的重要物质遗存与宝贵文化遗产。2007年,大鹏所城传承百余年的民俗仪式“大鹏清醮”入选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所谓“清醮”,本是道教祭祀仪式中的法事活动,用于生者向天地神灵祈求保佑。而大鹏所城的清醮仪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为了纪念阵亡军士和超度海上亡灵,之后战事止息,则又在原有祭祀各路神明基础上新添了拜祭历代将士英魂、开设将军宴等颇具地域特色的仪式活动,显然是受到了当地尚武传统的影响[15]。今天的“大鹏清醮”成为“大鹏追念英烈习俗”,历史古城与民俗活动相结合,使大鹏所城这一尚武景观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不仅是对英烈的纪念,更是为当今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事业、爱国主义教育事业提供鲜活而隽永的物质基础。
无论是依托大鹏所城重现“大鹏清醮”,建设古城博物馆,还是充分发挥海防历史底蕴与尚武精神,与官方、民间各类教育组织合作,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是当前时代背景下运用创新手段复兴尚武传统的有力举措。这些崭新的文化呈现形式既丰富了深圳地区的尚武景观与传统,又体现了对当地传统民俗的多元化改造。它们营造出或欢乐融洽或庄重肃穆的文化氛围,带动了更多社会群体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其中,有助于形成传承当地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记忆的个体自觉,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可见,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尚武景观这类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纪念空间和相关的仪式活动的保护,避免其原真性与完整性遭到破坏。同时,结合当代精神发展的需要,赋予传统景观、习俗以现代生命。
参考文献
[1]王向荣.景观笔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姜彬.姜彬文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3]刘志伟.天地所以隔外内——王朝体系下的南岭文化[N].东方早报,2016-01-31(A06).
[4][6][7][8]舒懋官,王崇熙.新安县志[M].新安:出版社不详.嘉庆二十五年刊本.
[5]科大卫.皇帝与祖宗[M].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0]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2011.
[11]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J].民俗研究.2016(06):14-24+157.
[12]趙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3]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J].学术月刊.2012(07):134-137.
[14]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5]王程太.深圳民间祭祀文化探析——以“下沙祭祖”等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J].文化遗产.2012(03):15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