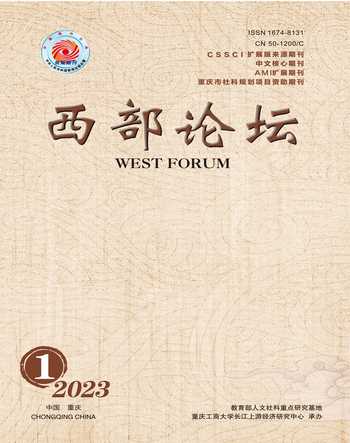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研究:多学科多视角的文献评述
刘苹 熊子悦 张一 魏怡君



摘 要:
當前,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零工经济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对零工经济研究进行文献综述:首先,在CNKI和WOS数据中以CSSCI、CSCD期刊和SSCI/SCI/JCR的Q2以上分区期刊为范围进行检索得到2009—2022年关于零工经济研究的中英文文献740篇,对其进行学术史梳理发现,国内关于零工经济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缓慢增长和快速增长3个阶段,但明显滞后于国外研究;然后,基于零工经济的核心要素(数字平台、零工劳动者、用工企业)从行为主体角度提炼出政府、企业和劳动者3个研究视角,同时通过文献编码归纳出劳动法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和劳动经济学6个研究范畴,由此构建多学科多视角的零工经济文献分析框架。最后,利用该框架对零工经济研究文献进行评述和展望。应进一步拓展零工经济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注重跨学科研究,融合多视角研究,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通过协同开展多学科、多视角、多路径的系统化研究促进零工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并为零工经济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
数字平台;零工经济;零工劳动者;新就业形态;经济新业态;系统性文献回顾法
中图分类号:F214.4;DF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0-0059-17
引用格式:
刘苹,熊子悦,张一,等.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研究:多学科多视角的文献评述[J].西部论坛,2023,33(1):59-75.
LIU Ping, XIONG Ziy-ue, ZHANG Yi, et al. Research on Gig Economy based on Digital Platforms: Literature Review from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perspectives[J]. West Forum, 2023,33(1):59-75.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因此,不仅要发展数字经济,还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特有的积极效应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产物和重要特征之一,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是一种新型的资源组织与配置方式,其以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平台为基础,汇聚信息、数据、服务等生产要素与资源,为个体、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提供多样化的平台和信息服务[1]。如何有效发挥数字平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是目前政府、企业和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因实现了数字赋能与劳动者就业需求的有效衔接而备受关注。
零工经济(Gig Economy)本质上是基于数字平台形成的一种经济新业态[2-3],以按需服务(On-demand Service)和劳务众包(Crowding Sourcing)为主要表现形式[4-6]。当前,零工经济带来的在线教育、远程办公、无接触配送、共享用工等新就业形态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7]。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的人口规模达到了2亿人次,其中以“直播带货博主”“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从业人员突破了8 400万人[4]。因此,数字平台下的零工经济不仅开辟了劳动力就业新空间,还为生产要素供给方式提供了新的载体[8]。然而在实践中,数字平台凭借海量数据和机器算法模糊了劳动从属关系[9],导致了“数字泰勒主义”的产生[10],带来了算法控制、数字全景监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11-12]。例如,国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2022年的调研报告显示,济南地区仅有13.8%的雇主为外卖骑手购买了工伤保险,而在高时效的配送要求下,本人及同事均未发生过意外事故的外卖骑手仅占39.0%。可见,数字平台和零工经济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理论界在探讨数字平台重塑个体、企业、社会活动的同时,也意识到零工经济用工模式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比如:按需服务导致了工作碎片化、时间弹性化、管理平台化等现象,这不仅使得劳动者的工作缺乏连贯性,产品和服务质量也缺乏保障[13-14],还使得劳动者难以享受企业提供的各项福利,并面临更大的劳务风险[15-16]。张成刚和张中然(2022)指出,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将劳动者置于“三重脱嵌”之中,由于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劳动者实际上长期处于“身体过劳”的状态[3]。刘苹等(2012)认为,劳务众包导致人力资本外溢,容易使企业人力资源建设陷入困境[17-18]。王蔚(2021)则认为,用工企业通过将“朋辈压力”转化成监控劳动者的工具,使得劳动者实际上处于以情绪剥削为代表的“软控制”之中[10]。
作为一种经济新业态,数字平台下的零工经济发展迅猛且前景广阔。随着实践的丰富,零工经济受到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零工经济是一种新兴且复杂的经济业态,多学科的研究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在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学者们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和侧重点出发,为零工经济的研究注入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基于学科分类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将有助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进而推动零工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有鉴于此,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SLR),在通过文献检索梳理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基于文献编码归纳相关文献的学科门类和研究范畴,同时基于零工经济的核心要素从行为主体角度提炼出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进而构建一个多学科多视角的文献分析框架,并利用该框架对零工经济研究文献进行评述和展望,以期为多学科协同开展系统化的零工经济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文獻检索与学术史梳理
1.文献分析方法
系统性文献回顾法(SLR)是一种文献研究方法(参见图1)。不同于元分析与文献计量分析,SLR具有系统性、科学性的特征。Dansese等(2018)认为,SLR能够有效降低文献检索中存在的主观偏差,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目标研究领域的知识框架[19]。因此,本文使用SLR对数字平台下的零工经济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和评价。
2.文献检索
本文基于大型学术期刊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其中,英文文献在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的检索框中键入“gig economy ”or“digital platform”or“shared employment ”or“new employment patterns”作为主题词进行组合检索,中文文献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检索框中键入“零工经济”或“数字平台”或“共享用工”或“新就业形态”等主题词进行组合检索。为提高研究文献的收敛性、科学性与可靠性,以SSCI/SCI/JCR的Q2以上分区期刊和CSSCI、CSCD期刊作为文献筛选范围。对检索结果进行逐篇阅读,剔除重复出现的文献、书评等非学术研究类文献,共得到740篇关于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研究的学术论文(英文文献575篇,中文文献165篇)。文献检索时间为2023年1月23日。
从检索到的论文发表时间来看(见图2),关于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研究的英文文献最早可追溯到2009年,自2016年以后快速增长,2022年的发文量已经达到142篇,是2015年的20.29倍。从中文文献看,检索到的最早文献出现在2016年(滞后英文文献5~6年),在2019年前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可见,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而国内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国外研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研究历程与学术史梳理
结合图2的文献发表趋势,本文对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作为伴随数字平台发展而兴起的一种经济新业态,零工经济具有将劳务的需求侧与供给侧有效匹配的灵活用工模式[20]。零工经济产生于数字经济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2009年,Uber公司率先实现了打车服务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这一新型服务模式的出现将“互联网平台+独立承包商”的灵活用工方式带入了大众视野[21],也开启了学术界关于数字平台、零工经济与新就业形态的探讨。截至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参见图3):
一是2009—2015年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增加了劳动者就业的难度,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以期促进就业。Policastro(2009)指出,零工经济是一种可能缓解社会高失业率的临时用工方式,通过签署临时的项目合同,能够保障兼职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的求职需求[22]。Friedman(2014)则认为,这种灵活用工模式以“独立承包商”或“项目顾问”为主体,劳动者与雇佣者的雇佣关系更加松散,但这种模式也可能诱发诸多社会问题[23]。在国内,国务院于2009年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9〕4号),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随后,《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支持劳动者临时性就业以及其他形式的灵活就业。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并且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的概念。“新就业形态”与传统的“灵活就业”概念首次在官方文件上出现分离,反映出国家层面对新就业形态的重视,并开启了国内学术界对“打零工”现象的分析和对灵活用工问题的探讨。
二是2016—2019年的英文文献快速增长、中文文献缓慢增长阶段。伴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灵活用工、共享用工为代表的用工模式在这一阶段快速涌现,与此相适应,英文文献出现快速增长,但中文文献增长缓慢。201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28号),提出要以5G技术为支撑,加强科技集成和创新商业模式,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用工与保障制度。在此背景下,以体验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智能经济、零工经济等为代表的经济新业态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例如:王利军(2016)探讨了如何借助互联网平台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24],王家宝和崔晓萱(2018)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分析了零工经济中个人与企业的关系[9],郑祁和杨伟国(2019)指出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需要根据自身的技能差异进行职业规划[13]。在这一阶段,国内学者对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但研究成果仍主要是基于特定视角对零工经济的概念、内涵、影响因素等开展的定性探讨,缺乏实证分析,且研究视角较为分散,尚未形成较成熟的研究体系。
三是2020年以后的中英文文献均快速增长阶段。随着5G技术的普及,以远程办公、无接触配送、在线医疗等为代表的工作模式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重要方式,对于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的研究也趋于系统化和多样化。202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国办发〔2020〕27号),提出要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优化自主创业环境、加大对灵活就业保障支持;2021年,为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的新问题,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出台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各项劳动保障权益落到实处;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的研究视角日益多元,研究范式也趋于成熟,并开始关注情绪剥削、算法控制、数字全景监狱等现实性问题[10][15-16]。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零工经济的研究不仅与数字平台和零工经济的实践发展相适应,而且受到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最初的相关研究与灵活用工、灵活就业等经济现象紧密相联[3][25],以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分水岭,学术界开始将零工经济和新就业形态作为独立的经济现象进行系统性的研究[14][26]。比如,从聚焦于零工经济的现象描述向相关宏观政策研究及企业和劳动者行为分析等拓展和延伸。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发展、新就业形态的演进以及国家政策的优化,关于零工经济研究的成果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研究视角和维度不断拓展,研究层次也持续提升。
三、多学科多视角文献分析框架构建
本文基于对零工经济核心要素的分析,从行为主体维度提炼出相关文献不同的研究视角;同时,对检索到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编码分析,梳理和总结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研究的学科门类和研究范畴;进而构建多学科多视角的零工经济文献分析框架。
1.零工经济的核心要素与研究视角
数字平台的出现推动了劳动力供求双方的高效配置[27],同时雇佣关系的短暂性和工作任务的碎片化使得企业的用工方式更加灵活[5-8]。作为一种经济新业态,零工经济是以数字平台为载体将劳动的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的用工模式。其中,是否有数字平台的参与是区分“新”“旧”零工模式的关键,对零工经济的研究必须兼顾使它得以繁荣的物质媒介(数字平台)和劳资关系的变化(新型用工模式)[3][13][14][26]。相较于传统经济,数字平台、零工劳动者、平台用工企业(指通过数字平台雇佣零工的企业,为表述方便下文简称用工企业)是零工经济最为显著的新特点,因此,可以说数字平台、零工劳动者、用工企业是零工经济的核心要素(参见图4)。
(1)数字平台。数字平台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了信息交流的物质媒介。企业可以在数字平台上发布工作任务和任职要求,劳动者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搜寻招募信息,进而结合自身精力和技能选择合适的工作[5];随后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并最终形成雇佣关系[17]。因此,数字平台在零工经济中起到了联结企业与劳动者的“桥梁”作用,通过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企业能够接触到具有多样性技能的劳动者,也使得劳动者能够在较高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下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选择适合的工作[5]。
(2)零工劳动者。数字平台重塑了传统的雇佣关系,使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一种“在线资源”[14]。零工劳动者和在职员工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工作时间与地点的灵活性。零工劳动者不受工作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不必像在职员工一样被限制在固定的工作地点,也不必遵循公司固定的上下班安排[24],可以自主决定工作地点和时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二是劳动力的技能化选择。一方面,零工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技能水平接受來自不同岗位、不同企业的工作任务[28];另一方面,用工企业更加关注劳动的结果而非过程,劳动者技能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劳务报酬水平。
(3)用工企业。在数字平台的支持下,用工企业在工作任务、用工时间、用工地点、管理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22],包括:一是工作任务的碎片化。零工经济中的工作任务被切割得更加微小和精确,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29]。二是用工时间的弹性化。零工经济中用工企业的用工时间不再固定,工作通常是以临时的“项目”形式进行派单。三是用工地点的远程化。在零工经济中,数字平台充当“平台中介”的作用[11],劳动者的服务提供和企业的管理在时空上呈现分离的特征,从而表现出用工地点的远程化与灵活化。四是管理方式的非人格化。在灵活用工模式下,工作任务的碎片化和弹性化导致管理上的困难,企业需借助大数据和算法实现与劳动者的有效对接[27];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算法的抽象性、复合性和强输出性等致使平台的劳动者处于一种“数字全景监狱”之中,表现出企业管理方式的非人格化[30]。
综上所述,零工经济具有灵活性和共享性的属性,其借助数字平台为要素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条件,但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影响到其效能的充分发挥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来看,对零工经济的研究关键在于明确用工企业与零工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并基于对其关系的改善探求促进零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策略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和路径。然而,用工企业与零工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和数字平台的发展,还受到政府的影响(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前文梳理的国内研究历程中),比如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和约束、宏观政策的激励和调控等。尤其是零工经济具有自主性、分散性、参与主体多元性等特点,多方利益的保障和协调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从行为主体的维度来看,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可大体划分为政府、用工企业和劳动者三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政府为广义的政府,包括在国家治理中行使公权力的所有机构,目的是凸显国家意志和政策对零工经济发展的影响。
2.基于文献编码的零工经济文献分析框架
首先,由三位作者通过“背靠背”的方式对文献进行独立编码,具体内容包括基础信息(文献标题、作者、发表期刊、检索数据库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主题等(参见表1)。同时,为提高编码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参考文献Liu 等(2022)的方法[7],对存在差异的编码结果进行讨论,输出一致性结果。首先,剔除编码结果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的文献。其次,对编码结果进行对比与归纳,例如,主题标签为“‘第三类劳动者立法思路与可实践性”的中文文献和主题标签为“对零工身份的法律界定和法律规范”的英文文献均探讨了零工经济对劳动法的影响,因而将其归纳为同一类文献。最后,重复上述过程,将文献整理为五种类别:第一类文献主要关注零工经济对劳动法的影响;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零工经济对宏观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的影响;第三类文献主要关注零工经济给劳动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第四类文献主要关注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发展的逻辑与特征;第五类文献主要关注零工经济对企业发展战略与行为的影响。第一类文献主要涉及零工经济对劳动法实施的挑战以及零工身份的法律界定问题,因此可以将其研究范畴聚类为“劳动法学”,并参考学位委员会14个学科门类的划分标准,将“劳动法学”归为“法学”门类下。依此类推,对各类文献研究的学科范畴进行编码,同时进行研究视角编码,编码结果见表2。
根据文献编码,目前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学科门类(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中的6个研究范畴(劳动法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和劳动经济学)。从研究视角来看,基于政府角度的零工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经济学中的劳动法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3个范畴,基于企业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管理2个范畴,基于劳动者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中的劳动经济学范畴。由此,可以构建多学科多视角的零工经济文献分析框架(参见图5)
四、零工经济研究的多学科多视角文献评述
1.基于政府视角的零工经济研究
基于政府视角的零工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法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畴,前者主要探讨零工经济用工模式对完善劳动法提出的要求,后两者则探究零工经济模式及其劳动关系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且三者呈现出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态势。
(1)劳动法学范畴的研究
零工经济的灵活用工模式对传统劳动法的冲击受到劳动法学研究者的关注,相关文献大致上遵循“零工经济的用工形态→‘第三类劳动者的法理逻辑→劳动立法思路的改进”的研究逻辑展开。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的用工形态可分为“劳务关系”“零工关系”“劳动关系”三种情况[4],而在实践中,零工劳动者通常表现出“去雇主化”和“多雇主化”的倾向,打破了传统用工系统的“雇佣”与“自雇佣”二元结构,由此引发学者们对“第三类劳动者”法理邏辑与适用性的探讨。如肖竹(2018)认为,数字平台下的劳动者可以采用“雇佣”与“非雇佣”的中间地带——“第三类劳动者”来进行界定[25]。班小辉(2019)根据经济依附属性的不同,提出应该在传统劳动法“二元模式”的基础上,将零工劳动者纳入劳动法“中间主体”的保护范围内,从而有效打击“虚假自雇”现象[35]。方长春(2022)则认为,为促进零工经济的稳定发展,应该建立起“从属劳动—第三类劳动—独立劳动”的多维劳动保障体系[8]。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制度设计上,探讨如何调整劳动法以适应零工经济的发展。Lobel(2017)认为,现行劳动法采用的“全有或全无”规则并不合理,应采取“功能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劳动法立法思路[36]。杨益晨(2020)则提出,判定劳动关系应由“构成要件式”改为“要素考察式”,综合劳动纪律、劳动自由度、劳动时间地点和劳动报酬等因素考察个人对平台和用工企业的“依附程度”,从而为规范劳动市场、保证企业和劳动者权益提供法理支持[37]。总的来看,劳动法学范畴下的零工经济研究认识到零工劳动者法律身份的界定是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与前提,并对如何调整劳动法及立法的完善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建议。
(2)宏观经济学范畴的研究
零工经济的发展必然对宏观经济发展及宏观政策产生影响。张军(2020)认为,由于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的出现弱化了就业率统计和GDP增长的基本关系,可能导致传统货币政策的失灵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颠覆[31]。数字平台的信息优势降低了就业信息的获取壁垒,导致劳动力在各产业间的转移更为频繁,例如,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2)》指出,滴滴出行、58同城等APP的广泛应用为我国煤炭、钢铁、水泥工厂工人以及转业军人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助推了不同产业之间劳动力的迁移。闻效仪(2020)认为,零工经济的过度发展会对传统制造业带来冲击,可能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引发结构性风险,应该预防零工经济带来的“去技能化陷阱”[38]。但也有学者认为“去技能化陷阱”的背后实际上是降低了零工劳动的准入门槛,是一种提高闲置劳动资源利用率的手段,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给效率。如Zwick(2018)指出,数字平台为社会闲置劳动资源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能够帮助产业工人实现再就业,是一种卓越的社会闲置资源再分配机制[21]。总体上看,宏观经济学对零工经济的研究在肯定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对有效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关注
其可能带来的“去技能化”等负面影响。
(3)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对零工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资本垄断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第一,零工经济的资本积累与垄断性。肖斌和李旭娇(2020)认为,西方的零工经济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是贯彻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经济形式[39]。王蔚(2021)、刘皓琰和李明(2017)指出,数字平台凭借数据优势实际上将劳动者置于“数字泰勒主义”的模式之下,通过“信息居间”的角色扮演和“游戏化抢单制度”的设计,模糊了劳动者的生产与工作边界,将劳动者置于以情绪劳动为代表
的
“软控制”之下;因此,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蕴含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倾向,政府需要规范灵活用工市场,采取措施有效防范“他主中的自主”问题[10][40]。谢富胜和吴越(2019)则指出,不经规制的零工经济不会带来“劳资双赢”的局面,反而可能将企业应承担的风险和成本转移给劳动者[5]。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零工经济的构建。崔学东和曹樱凡(2019)对比了中西方零工经济发展在平台租赁模式、资源共享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零工经济,需要切实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导地位、积极防范金融与经济风险并加强规范零工经济秩序[41]。政治经济学对零工经济的研究揭示了灵活用工模式产生的资本逻辑及其弊端,比如在劳动生产环节的算法控制实现了劳动者的自我控制、自我理性化、自我商品化,并带来情绪劳动,而过度的情绪劳动会导致劳动者心理失调和劳动者之间的恶性竞争,进而加剧社会矛盾,破坏经济环境,因此,探索适合国情的零工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必然选择。
2.基于企业视角的零工经济研究
企业视角下的零工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管理范畴,前者主要探讨零工经济对用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及应对,后者主要探究企业在零工经济模式下的战略转型与策略优化。
(1)人力资源管理范畴的研究
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有效的人力资本管理是企业取得长远发展的基础。零工经济的灵活用工模式对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提出了挑战,因而用工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问题受到关注。Zwick(2018)指出,零工经济实现了人力资源共享,提高了外部人力资源的匹配效率,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外部化趋势[21]。Policastro(2009)认为,工作任务的碎片化使得劳动者的就业思想发生转变,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转变为对自身专业技能的忠诚,进而导致企业需要面临更多的员工离职风险和劳务纠纷[22]。因此,如何提高人力资源政策的灵活性,优化招聘选聘流程是用工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灵活用工的劳动者素养也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王家宝和崔晓萱(2018)研究发现,零工经济模式下当劳动者的工作动机仅为消磨时间或对某一份工作的重视程度不高时,容易在中途退出劳动[9]。Meijerink和Keegan(2019)指出,由于工作的准入门槛较低、筛选聘用的程序不如传统雇佣模式严谨,常常会出现零工劳动者职业素养低下、不胜任工作的情况,从而加剧潜在劳务纠纷和法律风险,并可能给企业声誉造成损失[29]。郑祁和杨伟国(2019)认为,用工企业在聘用劳动者时更加强调劳动者的工作技能,对劳动者所具备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3]。总的来看,灵活用工模式一方面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匹配效率,另一方面导致企业人力资源结构外部化以及员工忠诚度、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及其成效。
(2)战略管理范畴的研究
零工经济给企业带来了许多机遇和优势,进而促使企业改变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Ganhdi和Sucahyo(2021)指出,零工经济模式下企业与劳动者签订的短期项目合同有利于企业快速淘汰不合格的劳动者,降低企业因招聘失误带来的损失;同时,“按需聘用”模式能够为公司带来实时回报,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转效率[30]。Lobel(2017)认为,在零工经济中“结果导向”正在取代“过程导向”,劳动者的绩效考核指标更加关注任务的完成情况,因此企业的一部分经营风险被劳动者所分担,企业在转移经营风险的同时也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36]。零工经济对数字平台的依赖性也促进了用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42],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率。由于企业对劳动者专属人力资本的培养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18],用工企业依托数字平台可以有效降低员工离职的损失。Mulcahy(2017)则认为,用工企业利用大数据算法节约了人才的搜寻成本,能够降低管理成本[6]。总之,企业应突破传统的经营思维,积极地调整自身战略,推动用工模式的转型升级,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零工经济带来的机遇和红利。
3.基于劳动者视角的零工经济研究
劳动者视角下的零工经济研究集中在劳动经济学范畴。由于劳动的碎片化、工作时间与地点的灵活性,零工劳动者可以自由地进行职业规划,但这也使得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不充分,增加了职业风险。因此,劳动经济学对零工经济的研究主要关注灵活用工模式给劳动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机遇和收益方面:董成惠(2020)认为,灵活用工模
式
使得劳动者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某一工作,并可在同样的时间内尝试更多样的工作,利用自己闲置的时间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和最大化[15]。Friedman(2014)也认为,劳动的时空限制被打破后,原本无法匹配到合适工作的失业者能够参与到灵活用工中来[23]。因此,具有高度灵活性和自由性的用工模式给予了劳动者更加丰富的职业选择,使个人价值最大化成为可能。在风险和挑战方面:Greenwood等(2017)针对零工经济中劳动者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认为在碎片化的工作项目中劳动者面临着个人权益的缺失、职业的动荡以及就业差距的扩大[43]。谢富胜和吴越(2019)指出,零工经济中就业的灵活性和自由度的对立面是职业的无保障性,适用的劳动法尚未成型,因此劳动者更容易受到企业的压榨和剥削[5]。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201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将零工经济中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称为“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即面对广大的竞争者,平台劳动者有可能被迫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预期薪酬以获取持续性的工作机会。总之,数字平台下的零工经济带来了雇佣关系的变化,增加了劳动者就业机会,也导致劳动者职业风险加剧,因此,帮助零工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自我管理能力和职业规划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五、结论与展望
在零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用工企业与劳动者是零工经济的直接参与者,政府则发挥着宏观调控作用。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给各经济主体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突出表现在其灵活用工模式改变了传统劳动力的供给与使用方式上。面对机遇和挑战,政府、企业和劳动者都应积极应对,以充分发挥零工经济的积极效应,有效规避其消极影响,进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从宏观调控主体——政府来看:零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型劳动关系,而现有劳动法律体系对这种新型劳动关系的认定和规范还不清晰,并由此产生一些现实问题[44]。因此,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劳动法律体系。一是加快制定相关劳动法规以规范各种劳动关系和行为,为数字平台下零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创新监管模式,针对零工劳动者“多身份”和“多雇主化”的特征[25],利用数字平台信息及时了解勞动者情况,提高劳动监管的针对性与精确性。
从劳动的需求侧——企业来看:零工经济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招聘和管理成本,并提高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针对用工模式带来的人力资本外溢化以及劳动者的不稳定性,企业需要调整经营战略以降低风险。同时,在逐利理性与利益导向下,数字剥削、算法控制、数字全景监狱等成为用工企业降低经营成本进而获得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因此,企业在利用零工经济获取更多收益的同时,应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尤其要树立算法伦理意识,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增加零工福利和保障,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敏捷性和亲和性。
从劳动的供给侧——劳动者来看:数字平台提高了零工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灵活性与工作内容的自主性,“去雇主化”和“多雇主化”给劳动者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遇和收入,但由于相关制度的滞后也使得零工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加大了劳动者的职业动荡与“去技能化”风险[14]。“数字泰勒主义”的工作模式不断迫使零工群体挑战生理极限,间接导致“效率之恶”[44]。因此,劳动者应不断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同时要树立权责意识,努力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合上述分析,各研究视角和各研究范畴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参见图6),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视角的劳动法学研究与劳动者视角的劳动经济学研究紧密相关,共同关注零工经济下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第二,劳动者视角的劳动经济学研究与企业视角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高度的内在联系,前者主要研究零工经济下劳动者表现出的新特征,后者在此基础上研究与之相适宜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以规避经营风险和提高生产效率;第三,企业视角的战略管理研究与政府视角的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联系紧密,企业作为零工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其经营战略和经营成本均会受到政府宏观政策的影响,反之,企业的战略选择结果也会间接影响到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总的来说,在零工经济研究中,各学科各视角的研究之间密切相关,表现出跨学科跨视角的倾向。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经济新业态,零工经济方兴未艾,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同时还有可能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基于多学科多视角的文献回顾,本文对未来的零工经济研究进行如下展望(参见图7):
一是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从更多的学科运用更多的理论对零工经济展开全方位系统化的研究。随着零工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带来的积极效应和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并具有扩大化趋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零工经济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用工企业和零工劳动者,也会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应拓展零工经济的研究视角,如劳动者家庭、其他企业、教育培训机构、社会组织等。同时还需要从更多的学科范畴来对零工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如教育学、心理学、家庭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
二是注重跨学科研究,融合多视角研究,促进零工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作为一种新业态经
济模式,零工经济具有参与主体多样化、发展模式多元化、影响效应广泛化等特征,同时复杂且动态的经济环境对零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零工经济研究的层次、维度、视角及学科范畴表现出多样性。目前,零工经济的理论体系还在形成和完善中,因而对零工经济的研究亟待理论创新。要构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单学科单视角的理论创新是不够的,需要将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理论创新整合到一起,这就要求开展跨学科研究,并通过研究视角、研究层次的深度融合对零工经济发展的机制与逻辑体系进行深度剖析,进而逐步构建和完善零工经济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三是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尤其需要加强实证研究。目前国内关于零工经济的研究大多以定性探讨为主,且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及法律制度探讨或中观层面的经济现象描述,无论是基于统计数据的经验分析还是基于经典案例及一手调研数据的深度剖析都十分欠缺。因此,一方面有关部门及学术机构要加快开展零工经济相关数据的统计工作,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应重视面向实践的调查研究,通过科学的量表设计和扎实的实地调研获取翔实的一手资料,进而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意义。同时,在分析方法上,也应综合运用有效的分析工具,如扎根理论、演化博弈与仿真、ISM解释结构模型以及计量经济模型等,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参考文献:
[1]
李海舰,李燕.对经济新形态的认识:微观经济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159-177.
[2] 郑祁,张书琬,杨伟国.零工经济中个体就业动机探析——以北京市外卖骑手为例[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0,34(5):53-66.
[3] 张成刚,张中然.新就业形态的就业留存——基于外卖骑手的定性比较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2,36(5):54-63.
[4] 于莹.共享经济用工关系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以认识当前“共享经济”的语域为起点[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21(3):49-60.
[5] 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J].经济学家,2019(6):5-14.
[6] MULCAHY D. Will the gig economy make the office obsolete?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7(3):2-4.
[7] LIU P,ZHANG Y,XIONG Z,et al. Judging the emotional states of customer service staff in the workplace:A multimodal dataset analysi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2,13:1001885.
[8] 方長春.“第三类劳动”及其权益保障:问题与挑战[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8):52-62.
[9] 王家宝,崔晓萱.零工经济模式下人力资源的特点、挑战和策略[J].管理现代化,2018,38(4):101-103.
[10]王蔚.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其情绪剥削[J].经济学家,2021(2):15-22.
[11]裴嘉良,刘善仕,崔勋,等.零工工作者感知算法控制:概念化、测量与服务绩效影响验证[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6):14-27.
[12]文军,刘雨婷.新就业形态的不确定性: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及其反思[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6):92-106.
[13]郑祁,杨伟国.零工经济前沿研究述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6(5):106-115.
[14]郑祁,杨伟国.零工经济的研究视角——基于西方经典文献的述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6(1):129-137.
[15]董成惠.零工劳动对传统劳动关系的解构以及应对措施[J].湖南社会科学,2020(5):100-111.
[16]成肖,李敬.劳动争议、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与中国经验[J].西部论坛,2021,31(1):48-58.
[17]刘苹,孙宁云,张运婷.未来性战略导向影响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12(6):62-69.
[18]刘苹,张运婷,孙宁云.前导性战略导向、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2:135-145.
[19]DANESE P,VALERIA M,ROMANO P.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recent lean research:State-of-the-art and future direc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8,20(2):579-605.
[20]张蕾.零工经济的伦理审度与校勘[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2,35(2):84-93.
[21]ZWICK A. Welcome to the gig economy:Neoliberal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case of uber[J]. GeoJournal,2018,83(5):1-13.
[22]POLICASTRO E F. Outsourcing could be way to goin short-term “gig” economy[J]. Intech,2009,56(11):29-31.
[23]FRIEDMAN G. Workers without employers:Shadow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gig economy[J].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14,6(2):171-188.
[24]王利君.我國分享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学术界,2016(12):225-232+327.
[25]肖竹.第三类劳动者的理论反思与替代路径[J].环球法律评论,2018,40(6):79-100.
[26]张成刚,辛茜莉.让政府、平台、劳动者三方共赢——以公共就业服务融合新就业形态为视角[J].行政管理改革,2022 (2):79-87.
[27]BURTCH G,CARNAHAN S,GREENWOOD B N. Can you gig it?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gig-econom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6(1):24-66.
[28]KOUTSIMPOGIORGOS N,SLAGEREN J V,HERRMANN A,et al. Conceptualizing the gig economy and its regulatory problems[J]. Policy Studies Organization,2020,12(4):525-545.
[29]MEIJERINK J,KEEGAN AE. Conceptualiz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gig economy:Toward a platform ecosystem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2019,34(4):214-232.
[30]GANDHI A,SUCAHYO G. Architecting an advanced maturity model for business processes in the gig economy:A platform-based project standardization[J]. Economies,2021,9(4):170-176.
[31]张军.零工经济对宏观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挑战[J].探索与争鸣,2020(7):13-15.
[32]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J].当代传播,2018(3):66-68.
[33]WOOD A J,LEHDONVIRTA V. Antagonism beyond employment:How the ‘subordinated agency of labour platforms generates conflict in the remote gig economy[J]. Socio-Economic Review,2021,19(4):1369-1396.
[34]刘苹,张一,汪熠杰.惩罚机制下低碳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研究——基于随机演化博弈视角[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2,38(1):16-22.
[35]班小辉. “零工经济”下任务化用工的劳动法规制[J].法学评论,2019,37(3):106-118.
[36]Lobel. The Gig Economy &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Law[J].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aw Review,2017,51(1):51-73.
[37]杨益晨.共享经济下新型用工关系认定问题研究[D].东华理工大学,2020.
[38]闻效仪.去技能化陷阱:警惕零工经济对制造业的结构性风险 [J].探索与争鸣,2020(11):150-159+180.
[39]肖斌,李旭娇.劳动形态对工资形态的影响及其对零工经济剥削研究的价值——基于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文本的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20(8):31-39.
[40]刘皓琰,李明. 网络生产力下经济模式的劳动关系变化探析[J].经济学家,2017(12):33-41.
[41]崔学东,曹樱凡. “共享经济”还是“零工经济”?——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積累与雇佣劳动关系[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1):22-36.
[42]NIKOS K,JAAP S,ANDREA M,et al. Conceptualizing the gig economy and tts regulatory problems[J]. Policy & Internet,2020,12(4).
[43]GREENWOOD B,BURTCH G,CARNAHAN S. Unknowns of the gig-economy[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17,60(7):27-29.
[44]潘旦.互联网“零工经济”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22(4):89-95+159.
Research on Gig Economy Based on Digital Platforms: Literature
Review from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perspectives
LIU Ping, XIONG Zi-yue, ZHANG Yi, WEI Yi-jun
(Business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Gig economy based on digital platforms is a new economic for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whos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have brought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enterprises and workers, and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concern for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t present,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have conducted diverse studies on the gig economy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perspective review of these studies will help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Structural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we provid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outlook for research on the gig economy. To start with, we searched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gig economy within the SSCI/SCI/JCR Q2+ divisions and CSSCI and CSCD journals in the CNKI and WOS databases, and obtained 165 domestic articles and 575 foreign articles respectively, with the finding that domestic research had significantly lagged foreign research in terms of time. Next, through collat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we found that domestic research on gig economy had not only been adapted to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gig economy, but had also been influenced by changes in national policies. The research on the gig economy had broadly gone through 3 stages: start-up stage, slow growth stage and rapid growth stage. Then, based on the core elements of gig economy (digital platforms, gig economy laborers and labor-using enterprises), we distilled thre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icipating subject, namely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labor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literature was classified into five categorie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codes. Further coding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categories showed that research based on government perspectives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categories in law and economics disciplines: labor law, macro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perspecti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two categorie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management discipline, while research based on the worker perspecti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category of labor economics in economics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e constructed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perspectiv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on gig economy. Finally, we used the framework to review and provide an outlook for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gig economy.
At present, gig economy is just unfolding. While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also brings challenges. Many issu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yet to be studied in depth, and new issues are likely to arise continuously. Besid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gig economy research is not yet mature. Therefor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scope should be further expanded to include more theories from a wider range of discipline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gig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ntegrate multi-perspective studie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gig economy.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research methods, especially to strengthen empirical research, so as to provide more target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gig economy.
Although the gig economy based on digital platforms has only been studied as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phenomenon since 2009,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its academic history and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perspective literature review that can still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atic gig economy research with multiple disciplines, perspectives and pathways.
Key words:
digital platform; gig economy; gig economy laborers;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new economic format;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CLC number:F214.4;DF47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0-0059-17
(編辑:刘仁芳)
作者简介:
刘苹(1973),女,四川资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研究。
熊子悦(1998),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组织行为学、数字经济研究。
张一(1995),通信作者,男,湖北潜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为经济学、数字经济研究;Tel:18202798522,E-mail:657518287@qq.com。
魏怡君(1999),女,四川泸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为经济学、数字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