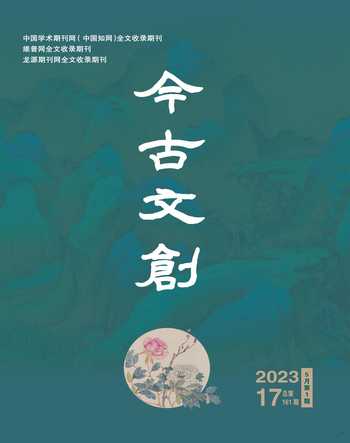试探门阀政治与贵族社会的变态
【摘要】 贵族社会自东汉末以来逐渐形成,魏晋时期得以定形,贵族社会是皇权政治的第一次变态。晋氏南迁后,东晋的门阀政治是贵族社会的一种表现,它开始于成帝,结束于淝水之战。此外,门阀政治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着贵族社会的状态,东晋结束后的南朝虽然不是门阀政治,但是依旧保持着贵族精神的一面,是贵族社会的继续。因此,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第二次变态,是贵族政治的第一次变态。这是因为南朝的君主除继承天命史观之外,依旧需要得到贵族的认可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
【关键词】 门阀政治;贵族制社会;士大夫政治;士族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6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20
田余庆在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中提出了:“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说:“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一观点也普遍的为学界所接受,成为了研究东晋政治制度的必备知识。但是,李文才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说献疑》中对田先生的观点进行批判,他认为:“君臣共治”乃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而非“变态”,且“中国自古以来只有皇权政治”,以此来否认门阀政治的存在。由此观之,尽管学界对于门阀政治讨论颇丰,但是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本文通过对贵族制社会的分析来认证门阀政治的存在,并进一步认证门阀政治是由贵族制社会发生的变态。此外,门阀政治只是贵族社会的一个特点,并不能作为支撑贵族社会存在的唯一标准,贵族制具有其特殊的自律性来支撑,并长期与皇权保持共治的状态。
一、田李二文关于门阀政治的分析
门阀政治的根本特征是“皇帝垂拱,门阀轮流执政”,也就是说,由皇帝来“统”,而门阀轮流来“治”。而绝非纯粹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
因为考虑到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一系列问题,我国古代是长期处于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的,田先生的结论上文已经提及,且为学界共知,本文不在这里详述,而是着重对比田李二文。
李先生对田先生关于门阀政治的定义提出了意见,他认为田先生的说法充满着矛盾,并指出沈约认为刘毅等人的京口起义目的只是为了兴复东晋,而并非是田著则认为的为了兴复门阀政治。
这里可以看出,李先生认为田先生将“东晋政治”等同于了“门阀政治”,并且把“东晋政治”理解成为“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治模式。因此李先生通过史料论述,提出了君臣共治并非是门阀政治的特点,且东晋不存在门阀政治,而是皇权政治的观点。
两位先生的论著十分的精彩,为中古史学的严谨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意见,但也都存在有或多或少的误差。
田先生仅从皇权政治衰弱与士族官僚兴起的角度出发,以东晋各个时期的门阀轮流执政为切入点,持有传统的史观来进行分析,自然忽视了当时整个的贵族社会意识的存在;而李文才先生关于田着的批判,也存在着部分引史料不符的误区,诸如“委以诸事,谓(诸葛)亮曰:‘政由葛氏, 祭则寡人。亮亦以(刘)禅未闲于政, 遂总内外。”以及“司空(指靳准)若执忠诚,早迎大驾(指刘曜)者,政由靳氏,祭则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等论述,无一不是短时期的战乱或王国衰弱的特例,并不具备普遍性,而东晋整一王朝自成帝至孝武帝时期都处于贵族社会下的门阀政治,时间长达百年,并非短期的“主弱臣强”,其则含有较长的时间性。
且门阀政治最基本的特征则是“门阀轮番执政”,李文似乎忽视了“皇帝垂拱”与“士大夫轮番而治”的特点,而其所举例子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单独案例,并且仅仅贯彻于一家把持朝政,而非士大夫轮番执政且皇帝“垂拱”。
此外,李先生所引的唐明宦官史料来证明“平行或超越皇权”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其中关于唐帝国的性质问题,史学界争议不断 ①,因此恐不能来以此说明唐朝时期的“主弱臣强”是常态。而明代宦官则是依附于皇权的非法定地位,并不具有超越皇权的力量 ②。
此外,李先生该文有混淆君臣共治与君与士大夫共治的嫌疑,他指出:“中國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开始进入了“皇权—吏民”时代,这一时代的政治模式就是皇权政治。”这种说法是不够严谨的。
阎步克先生所指出的秦汉时期的非士大夫政治而属于官吏政治这一观点,已成为学界普遍共识;此外,宫崎市定先生亦指出贵族社会下的士大夫是不同于秦汉以及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的,换言之,官僚政治的下的官与君主更像是主仆的关系,是一种绝对服从的法家思想的体现,倘若特指秦汉时期尚可,如果将其运用至中古时期则是不太符合事实的。
而士大夫本身则体现了其独特的“自律性” ③,这种自律性一方面来源于川胜义雄所指出的“乡论”,也就是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是由皇帝决定的,而是由乡党社会的舆论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论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道自重和抗礼帝王的意识是发展的最普遍,也是最强烈。”可知其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觉醒,而作为贵族化的中古士大夫群体来说,他的贵族化一面是绝对不能不考虑的。
综上可知,即门阀政治是贵族制社会在政治上的过激反应,是贵族制社会而不是皇权政治发生的变态,表现为士族上升为门阀轮番执政,而皇帝只能垂拱而统,贵族以皇帝的名义管理着国家。而关于贵族与贵族社会,将在下文进行论证。
二、贵族自律性的精神渊源
上文提到的“君与士大夫共治”,就不得不阐释贵族与贵族制社会。而关于贵族与贵族制社会,日本京都学派对此有着颇为详细的论述。
谷川道雄先生对于贵族的定义有个重要的补充,即大土地所有者不是贵族品质的必须,如《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宋纪十四》载:“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为乐,雅异于此。”
这里的王后是琅玡王氏王景文的妹妹,自是一品的高门士族,此曰“外舍寒乞”,实则是嘲讽其在经济上的贫穷。川胜氏则进一步区分了贵族与豪族的概念,即决定贵族的是其文化。
宫崎氏也指出了九品官人法制度下中正官职能随着贵族主义的到来而逐渐削弱,到了东晋时期的中正官已经不能成为中央意志的执行者。李济沧先生进一步从魏晋元康放达之风的角度强调了乡论主义强大的自律性与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尽管士人不等同于贵族(士族),但是士人确是贵族的载体。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文化教育根植于儒家思想之中,阎步克先生指出士大夫阶级即是社会的管理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
而其政治文化的传统便是“礼”,这种“礼”是独立于任何强权之外的一种“道”,本身就有着很强的自律性,由“礼”而分配出各种制度与形成各种社会秩序。
可见其社会活动即是礼的过程,“礼”本身又是包含修养的象征:“礼乐皆得,谓之有德。”而能承担社会活动的则是知礼的那一类群体,也就是士大夫们。
因此,在古老的封建时期无论是君主还是士大夫,都应该遵循以“礼”治国的基本方略。东晋以来的清浊观念以及士大夫“和而不同”的分职观,也是来源于古老的“礼”的规矩之中。《荀子》载:
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则体现了士大夫这种“疏导精神”,也就是让社会人物各司其职,以达到礼的效果,不得不说这是贵族精神的一种滥觞。
因此,士之自律性绝非奴隶小吏可比,他们和君王的关系不是主仆关系,而是一群合作的朋友,而儒家士大夫作为继承了“道统”的士大夫们,则更体现着这种传承自上古时期传统意识的自律性。
《礼记·儒行》载:“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④”可见士大夫拥有“不诏之臣”的性格;《后汉书》载:“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可见士大夫注重师道强于重于天子;《荀子·大略》中,更是直接说:“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人曰:何以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可知自律性早已同上古时期的士大夫融为一体;又《南史》载:“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更是士大夫高度自律性的强证。
综上,士大夫们的教化权力不是皇帝君主赋予的,而是其作为这个文化阶层天生的权力,贵族也并非是寄生官僚的产物,而是文教的天然执行者,而对于这种权力的认知亦是植根于士大夫骨子里的基因。
三、自律性与贵族制社会的形成
汉末三国的军阀割据,彻底打破了秦汉以来的君臣关系与社会秩序,而曹操军阀集团尚未完成重振皇权的使命就淹没在士族政治的浪潮之中。
宫崎氏指出,贵族所掌握的官僚机构并未随着王朝的替换而丧失,曹魏所制定的九品官人法中本身就孕育着贵族主义的因素,而其到西晋时期则完全成为贵族主义的精神象征,九品官品的设置与乡论的广泛运用,毋宁说是贵族精神发展的特点。
也就是说,汉末三国至魏晋(西晋)时期,已经是皇权政治的第一次变态了,这时期的皇帝已经不能完全凭照个人意志去剥夺士大夫阶级的自律性了。如《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引注《汉晋春秋》记载了荀顗欲拜晋王而王祥却不拜之事:
祥曰:“相国位势,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 ……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
可见此时的贵族已具备其独特的自律风骨了。与此同时,乡里地方大量豪族的兴起,逐渐对地方社会形成了最直接的影响,使得皇权对县以下的影响逐渐削弱,地方与乡论成为了士大夫立身的温床⑤。
西晋本应该在贵族制社会下发展并完结,但是由于八王之乱等因素,使得士大夫们在政治上军事上获得了特殊地位,从而产生了贵族在政治上的过激反应,发生了第二次变态,即东晋的门阀政治。
而导致第二次变态的因素即田着所论“外族的入侵”“皇权的衰弱”与“士族的兴起”。只不过本文進一步强调其变态的根基是在贵族社会的基础上发生变态的而非传统的皇权社会。又嵇康《答难养生论》载:
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
可知魏晋时期部分士大夫的心理状况是“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就向往着圣人政治而非君主专制,君主之治理天下的前提应该是君主首先是一名圣人,而圣人的传道者则是士大夫,故圣人本身也是士大夫的一员。
换句话说,圣人、君主与士大夫应该是三位一体的高度融合的人格总和,故古代又有圣王一称。魏晋时期的思想有如此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的贵族面貌。余英时先生更是指出:“魏晋之际名教中的君臣伦理已经动摇了。”
尽管最终名教与自然相互妥协,但诸如郭象所云:“无贤不可以为君”的思想,已经成为贵族社会的主流思想了,任何的君主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否则其下场一定是被贵族阶级联合推翻,而这在宋代之后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又《资治通鉴·宋纪十二》载:
废帝幼而狷暴……法兴辄抑制之,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邪!”帝稍不能平……言于帝曰:“道路皆言‘宫中有二天子:法兴眞天子,官为赝天子。……法兴与太宰、颜、柳共为一体,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法兴是孝武左右,久在宫闱;今与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复官有。”帝遂发诏免法兴……赐法兴死。
当然,戴法兴之死于其言行并不无关系,不过侧面来看,他敢帝王说:“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邪”这样的话予以警告,并且其“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可知其势力之大,渗入朝廷之内,也可从侧面反应此时贵族社会的风气。又载曰:“先是帝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宫人倮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其荒诞可知。此外,在贵族社会中轻易诛杀贵族必然会引来更为严重的灾难。又同卷载:
兴宗往见庆之,因说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伦道尽……所瞻赖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着,天下所服。今举朝遑遑,人怀危怖,指麾之日,谁不响应!”……兴宗曰:“当今怀谋思奋者,非欲邀功赏富貴,正求脱朝夕之死耳……况公统戎累朝,旧日部曲,布在宫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辈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从……公今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从之祸。”
沈庆之乃吴兴沈氏出身,虽然算不上甲等贵族,但也是次等贵族,但是其先后参与刘宋的两次北伐,多次助国讨贼,一生历仕五朝,是孝武帝的托孤大臣,其势力如史料所言:“况公统戎累朝,旧日部曲,布在宫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辈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从!且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殿中将军陆攸之,公之鄕人,今入东讨贼,大有铠仗,在靑溪未发。”
其强大可知,如果他决心行伊霍之事,必不难也,然而他坚守臣心,却遭遇废帝的杀害。
废帝的荒淫无道与诛杀贵族,最终引起了贵族的反噬。即同卷载:“彩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相同故事在南朝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论述。
综上可已知,在贵族社会之中,社会意识形态以帝王与贵族共同遵守“贤君贤臣”的伦理观而维持的,帝王能杀贵族体现了君权无上,但是帝王不能随意地诛杀贵族则体现了贵族这一阶级的自律性力量。
张兢兢博士认为的“刘宋脱离清净政治之风,故而失去了士大夫阶级的支持”这一论断。”虽在某种程度上与笔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依照本文意见,刘宋的衰亡是在贵族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
四、结语
贵族的自律性一方面来源于汉末以来的乡论主义,一方面来源于传统儒学中的士大夫精神,而后者是植根于贵族骨子里的基因。
自东汉以来,贵族主义的元素逐渐复苏,经过长期的战争、割据、党争,贵族主义终于打破了秦汉以来的纯官僚制度,中古社会走向了贵族社会,这也是皇权社会发生的第一次变态。
然而,西晋短促的灭亡给贵族主义进一步上升创造了可行性,司马氏衣冠南渡,在士族高门的扶持下建立了东晋王朝,然而贵族的势力进一步膨胀,使其在政治上产生了“君主垂拱,门阀轮番而治”的门阀政治,这是皇权社会的二元次变态,同时也是贵族社会发生的第一次变态。通过对中古时期贵族社会的分析,可以补充以门阀单一视角进行研究的缺陷,丰富学界的视野。
注释:
①历代史学家对唐朝社会的分析有所不同,其中关于唐朝社会是贵族社会的研究可参(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332页;国内有关唐代宦官的研究,可参贾志刚:《唐代宦官研究二题——〈以唐姜子荣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91-105页;裴书研:《浅析唐代宦官专权的演变及其原因》,《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第6期,第84-87页。
②可参杨向奎:《明代宦官墓志“天子家奴”形象的建构》,《学术交流》2019年第11期,第164-168页;黄小荣:《试论明代宦官权力的扩张及其原因》,《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第17-18页。
③日本京都学派对贵族的自律性问题十分的重视,相关内容可参(日)川胜义雄著,李济沧、徐谷芃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7页;李济沧:《六朝贵族的自律性问题——以九品官人法中乡品与官品、官职的对应关系为中心》,《文史哲》 2016年第4期,第66-67页。
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30页。
⑤相关内容可参(日)川胜义雄前引《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文,第42-47页;李济沧:《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第166-172页。
参考文献: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李文才.东晋“门阀政治”说献疑[J].江汉论坛, 2022,(1).
[3](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徐玉清.汉唐间周姓名门望族简述——以汝南周为例[J].天中学刊,2012,(3).
[5]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M].韩升,刘建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7](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李济沧,徐谷芃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9](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M].马彪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0]李济沧.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J].江海学刊,2014,(3).
[11](战国)荀况.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晋)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魏)嵇康.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9](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20](南朝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1]张兢兢.皇权、门阀与地方社会:刘宋政治风尚的演变[J].历史学研究,2017,(05).
作者简介:
赵健廷,男,安徽淮北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