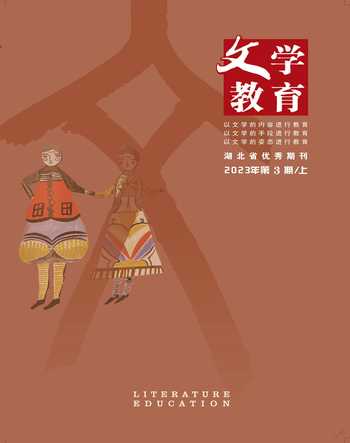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百年孤独》与《尘埃落定》的异同赏析
刘嘉雯
内容摘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照《百年孤独》与《尘埃落定》两部作品,探究马尔克斯对阿来创作的影响,发现在“面对外来者入侵”,“对宗教元素的运用”以及“作品的悲剧意蕴”等方面,两部作品具有共通之处。而在“地域选择”,“人物设置”以及“对于魔幻现象的描写”方面阿来较好地结合民族地域特色,挖掘出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且意识流手法的应用更体现出阿来在受到非本土文化影响时,很好地融合外来文学精华与本民族文化,表现出作家的强烈主体性立场以及内化能力。
关键词: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阿来 《尘埃落定》 接受者 主体性立场
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声音叙事、人物形象、艺术手法、作品主题等角度对阿来作品进行研究。本文则通过对照阅读《尘埃落定》和《百年孤独》两部作品,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找出马尔克斯对阿来的影响之处,体会两位作者关于历史的、民族的、人类的观点与思考。同时,探讨阿来在马尔克斯的影响下,在《尘埃落定》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本文将从创作背景、文本借鉴与突破、《百年孤独》对《尘埃落定》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立足作品,期待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所碰撞出的绚烂火花。
一.创作背景
“我要为我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这是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的意图[1]。19世纪到20世纪,为了反抗外来侵略者入侵、争取独立、追求公正平等,在这一百年的反抗斗争中,拉丁美洲人民显现出独特的顽强生命力,而作者则通过描写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起起落落、生死循环,以每个人都孤独至死的结局表现出对拉丁美洲人民所受苦难的深切同情,由此也展现出作者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现实责任感。
而在中国,也有一位深怀历史意识的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因为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所以他创作的《尘埃落定》洋溢着古朴动人的藏族文化[2]。在作品中,阿来以麦其土司家族为主,叙写在麦其二少爷——这个“傻子”身上所展现的智慧以及在扭曲的权力社会中难得的纯朴,谱写出一首关于中国藏族人民生活的宏大史诗,为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解读的标本。二者的创作背景表面上毫不相连,实则他们都受到本土文化的深深滋养与哺育,出于对故土的热爱以及作家的自觉性,从而承担起唤醒世人思考历史、铭记历史的责任与担当,这也是二者的作品都没缺失“人类”与“历史”这两个对象的原因。
二.文本借鉴与突破
《尘埃落定》和《百年孤独》都是关于故乡之作的小说,有共鸣也有个性。《百年孤独》是“以超现实叙述涵盖现实中的家族演变过程”[3],《尘埃落定》是批判与回归文化根源相结合,追求真善美的神秘主义叙事。其中,两位作家都有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悲悯情怀。有学者认为,影响研究“对接受者的重视不应将其看作是‘影响的补充,而应聚焦接收者对异国文学的接受和反应”[4],下文笔者将从外来者入侵、宗教以及共同的悲剧意蕴三个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比照。
(一)外来者入侵
外来者是相对于本土文化、本土文明来说的,外来者入侵可以是人、文化、经济或政治模式的入侵。《百年孤独》里经济形式的入侵比较明显。在小镇还没出现香蕉公司之前,吉普赛人就已带来磁石、灯泡,家族后代又带来火车,开拓与外界交流的途径。从自成部落的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发展过程中,马孔多是欣欣向荣的,四处萦绕着和平、幸福与安详。但是,某天来自大城市的独裁者在小镇建立起政府,打破了小镇居民自治的平衡局面,继而引发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纷争。一系列的殖民活动给马孔多带去深重的灾难,让小镇稍微一踏进资本主义社会就起义、妥协、屠杀不断。还有流水的宴席营造出小镇看似繁荣的景象,实则封建庄园经济和独裁统治已经让小镇深陷殖民主义的漩涡之中。各处充满着虚伪和膨胀,独裁者举国之力掩盖香蕉工人大罢工,三千多人惨遭屠杀的事实。动乱之后是连绵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大雨以及大雨过后十年的滴雨未降,最终,布恩迪亚家族及整个小镇,衰落于蚁患,毁于飓风,归于孤独。
《尘埃落定》则在文化与经济两方面都有体现。在文化层面,因为藏族文化的深层扎根,外来文化无法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附属的身份臣服在當地文化之下。黄特派员本来是被国民政府借机派来管辖的官员,最终甘愿在麦其土司手下挂名当一个师爷。在经济层面,外来者罂粟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战胜并取代了传统的经济形式。罂粟传入官寨后,改变了原有的种植结构,从种粮食发展到用全部的土地种罂粟,导致粮食价格飞涨,原本和平的、自给自足的各个官寨饿殍遍野。
(二)宗教
两部作品都有宗教色彩的出现,《百年孤独》中的宗教总是与殖民相联系,带有负影响,《尘埃落定》中的宗教也大多是被权力利用的工具,但是阿来保留信仰在信徒和传教者身上的个别闪光点。在《百年孤独》中,费尔南达是一个深信宗教,并受其荼毒的典型例子。她成长在一个严规戒律的落魄贵族家庭,从小被灌输长大后会成为女王的思想,甘于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修道院,成为冷漠刻板的卫道工具。她从不改变自己拐弯抹角的说话习惯,“将分娩说成排出,将血漏唤作胃热”,把她认为羞于启齿的字眼用过于隐喻的词语替代。在乌尔苏拉老去以后,她成为第二个管理家宅的人,要求所有人吃饭前必须念经,强迫大家和她一样遵守教条,把窗户用十字架木条封住,阻断与外界的联系,把家变成一个“阴森的大牢笼”。为了自己的虚荣心,逼迫女儿梅梅练习古钢琴,让儿子远赴他乡的神学院,想把他培养成教皇。结果,女儿受不了母亲对她的禁锢约束,私下与人幽会;儿子则学会撒谎,把在外的穷困潦倒伪装为学有所成。费尔南达就在这荒唐的信仰与迷信中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孩子的爱情与前程。
《尘埃落定》的宗教色彩则更加浓厚,佛教、天主教、新教派等宗教的“大杂烩”让“整部小说充满着超常、奇谲、朦胧的神秘因素,呈现迷离、虚幻之状”[5]。作品中的主流宗教是藏族佛苯结合的藏传佛教,意味着信仰与救赎。在文中,有虔诚的信徒——奶娘德钦莫措,为了朝佛,从偏僻的藏区一路跪拜到拉萨,来回用了一年零十四天,回来后,官寨里的人都快把她忘记了。书中也有出现宗教中不同派别的代表,门巴喇嘛是有真本领的僧人,济嘎活佛成了依附权势的人,传教士查尔斯则是贪图钱财、信仰不坚定的人,可见作者对于不同传教者的态度爱恨分明,对不忘初心,坚定信仰的信徒的赞扬,也深刻揭示了在麦其官寨里所谓的信仰只不过是附属于权力,为权力而服务的工具。
(三)共同的悲剧意蕴
1.归于湮灭
無论是麦其家族,还是布恩迪亚家族,两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安排了家族中“特别”的一人充当见证者,见证家族的毁灭和消失。傻子二少爷由众人以为不会有能力当上土司,到最后统领麦其家族,还娶了最美的女人做妻子,这是傻子二少爷的特别;而奥雷里亚诺作为最后一个家族毁灭的见证者,从一出生到三四岁,则是一副野人样子,家中所有人都把他当作“装在篮子里漂来”的孩子,结果只有他破译了智者留下来的羊皮卷,揭开家族的轮回命运。
《百年孤独》通过百年的历史构建出生活在小镇马孔多的布恩迪亚家族,这延续七代的族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被孤独折磨至死的命运结局。“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在旱季无边的干旱中,在漫天飞舞的蝴蝶和遍地横行的蚂蚁里,这个孤独的家族伴着人间的各种苦涩和孤寂消失。《尘埃落定》则是基于藏族文化背景下,构建一个大智若愚的二少爷形象,见证其所在家族,以及土司制度的毁灭。作者描写了一个女人之间勾心斗角,男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真实世界,有争夺领土的边境斗争,有经济方面的市场贸易,也有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最后麦其官寨就象征着古老的土司制度,毁于“红色汉人”的炮火之中,一切都尘埃落定,无声无息。两部作品共同的结局都是所写的家族整个归于湮灭,我们可以发现马尔克斯的创作模式是“开始—发展—高潮—转折—结束”的家族模式,阿来则是发展链条一样,但是是以麦其二少爷为主的个人模式。
2.象征意义
布恩迪亚家族代表拉丁美洲民族,麦其家族则代表古老的藏族土司制度。“布恩迪亚整个家族都不懂得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在这个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互相缺乏信任与了解。乌尔苏拉在漫长的雨季中渐渐缩小、腐烂;阿玛兰妲则一刻不停地缝制自己的裹尸布;奥雷里亚诺上校晚年则在金银小作坊里做小金鱼,每做到二十条就熔掉再重做。正如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轮回,马孔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如此,象征着从一开始就陷入的循环怪圈。
而《尘埃落定》它不仅是写土司制度衰亡的宿命,还写出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二少爷曾有过这样的一个疑问,在没有土司之前,这片土地上都是酋长,而当土司制度建立后,酋长永远消失了,那么在土司之后,又会是什么来取代土司呢?在这一思考的时刻,他已经明确知道土司会灭亡的结局。当然这一想法的发生也是因为作者的设计,他给我们清晰地拉了一条人类历史发展的线路,即势必有一种相对来说更加文明、更加强大的制度取代之前的权力中心。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这是阿来对马尔克斯循坏怪圈的突破。他借鉴了《百年孤独》的故事框架,但他不仅仅是局限于叙述一个家族灭亡的框架当中,更看到了在循环之外这片大地上人们的未来。在小说的尾声写出官寨毁灭后的开始,给读者对故事后续的发展留下遐想的空间,这是突破,更是一次家族历史创作小说的进步。
三.《百年孤独》与《尘埃落定》的异同赏析
20世纪8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视野,在文学创作荒芜期,各作家迫切期望打破思想禁锢,于是大量汲取外来文化和创作理论,如印象派、表现主义等,其中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因鲜明的地域文化、魔幻的风格以及国际认可度,与大多数中国作家引起共鸣。《百年孤独》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自然成为80年代在中国作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书。而阿来作为其中一位作家,也不可否认地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本章将从地域选择、人物设置、魔幻现象和创新之处四个部分探讨《百年孤独》对《尘埃落定》的影响。
(一)地域选择:马孔多与川西
马孔多是“一块放浪形骸又极富想象的土地,因孤独而耽于幻觉和种种错觉的土地”[6]。小镇马孔多的产生、兴盛、衰落再到消亡,都随同着布恩迪亚家族的兴衰胜败而起伏不断,与家族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马孔多,这个由作者创造的带有东方盘古开天地传说似的小镇,家族的第一个人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带着妻子乌尔苏拉,以及甘愿跟随的二十一个人上路,经过一年六个月的跋涉,最后来到大泽区,开辟了这个家族世代聚居且与世隔绝的小镇。它既是家族的起点,也是终点。这个世界演绎着各类人的喜怒哀乐,浓缩着世界上最深沉的孤独,也给读者带来阅读中的不可把握的神秘感。
而《尘埃落定》的故事发生在四川西北部的阿坝藏区,是作者阿来的故乡。阿来充分开发丰富的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直言二少爷这个人物的塑造就是受藏族民间故事中智者阿古顿巴的启发。二十世纪40年代,在一个被称做“嘉绒”的地方上演着土司制度的兴衰史。两位作者都把故事的开始选在一个较为偏僻、距本土的主流文化较远的原始地带,让故事的起点保留纯真性与野蛮性,更能放大外来文化给当地带来的冲击。所以在地点的选择上,阿来多少有被马尔克斯的创作所影响。在这部作品中,阿来试图在文化与政治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不仅如此,他也认清了封建的土司世袭制度必定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被淘汰的事实。面对这一事实,他知道终究敌不过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于是选择接受现实。这是作为作家难能可贵的一面,即客观地写作。不仅“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而且也不忘尊重历史事实,客观地向读者表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二)人物设置:智者代表
两部作品都有智者人物的设置,而这一相同设置绝不仅仅是巧合。比如《百年孤独》中留下羊皮卷的梅尔基亚德斯,他本来是因热病死在新加坡的沙洲上,但是马尔克斯的魔幻之笔让他死而复生。作为一个贯穿全文的线索人物,他的出场总是与他人不同,每一刻都戴着鸦翼状礼帽。而帽子的形状不禁让人联想到它的象征,即在西方文化中的乌鸦,代表着死神。这也印证着他的身份——给小镇带来死亡的第一个人,暗示小镇即将拉开衰败的序幕。再者,乌鸦的预言总是准确的,这也预示着他所留下的羊皮卷准确预测了布恩迪亚家族的未来。
再来看《尘埃落定》中虔诚正直的翁波意西。作为格鲁巴教派的追随者,智者翁波意西與济嘎活佛存在宗教内新旧派的冲突与分歧。在不可调节的矛盾下,他们发起辩论,最终翁波意西为了不做奴隶,第一次被割去舌头,忍辱负重当了麦其土司的书记官。这也让我们看到宗教之间在争夺地盘与发展资源中残酷的竞争及其生存状况的艰难。而他也是一位预言家,当他刚踏入麦其土司的领地时,就已经预测出罂粟将是加速土司制度灭亡的干柴烈火。翁波意西对他的信仰执着且坚定,因此在权力泛滥且权欲大于知识的土司官寨中,正直、有着先进思想的翁波意西因为不满大少爷当土司,第二次被割去舌头。而这一情节设定正体现阿来对历史理性的深切呼唤。
最后是大智若愚的主角,麦其二少爷。作为“智者+傻子”的矛盾统一体,作者精心设计这一人物,连出生都带有魔幻色彩,是土司父亲醉酒后与汉人母亲生下的。他是天生的领导者,在十三岁捕野画眉时,就懂得如何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慧眼识人,小小年纪就看出身边人的性格且按其个性分配任务,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捕鸟行动。在其他土司都看到种罂粟带来的利好,命令把所有的土地都拿去种罂粟时,二少爷早已洞悉其中的利弊,看到罂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不顾众人反对,坚决种粮食,这也为后来麦其家族遇到饥荒时做好了粮食储备。经过上文的比照,两位作者在人物设置中有异曲同工之妙。阿来受马尔克斯启发,在作品中加入智者成分,还在此基础上,让此特质不再强烈地聚集在一个人身上,而是让多个角色拥有,增强表现现实的真实感。
(三)奇特的魔幻现象
在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将要揭破生命所有的谜底时,却因破解“时候未到”,如同受上天惩罚似的,他说的话奇迹般地夹杂着各个国家的语言,这些语言他之前从未学过,从此以后没有人能听懂他的话。最终,因为“发疯”被捆绑在屋前的栗树干上,日晒雨淋,被马孔多的人民迅速地遗忘。只有那个冤死的鬼魂——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找他谈话,两人随着年月的增长一同老去,更是从仇人变成朋友。而这个鬼魂更是之前在布恩迪亚家中各处游荡,还长途跋涉到马孔多,时刻提醒着这对夫妇杀人的罪过,给他们带去残酷的精神惩罚。而马尔克斯似乎在用这个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表达对历史开拓者的深深同情。类似的还有家族近亲结婚生出的带有猪尾巴的孩子,智者梅尔基亚德斯的死而复生,奥雷里亚诺第二与情人的生殖崇拜,丽贝卡从小则有吃土怪病。
与美人儿蕾梅黛丝飞天的故事一样,《尘埃落定》最后一节中也有类似灵魂升天的描写,“我看见麦其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灵魂正是轮回、复活、永生的载体,肉体归于尘土。除此之外,作品中还有门巴喇嘛与汪波土司神巫斗法的魔幻现象。喇嘛设坛做法,第一回合把冰雹变成雨水,化解危机;第二回合则回赠冰雹,好像巫师们真有什么法力,把天上的云送过来又送过去。当对方的巫师要给二少爷下咒,夺他性命时,喇嘛占卜施法保住二少爷的性命,却防不胜防,没有保住央宗肚里的孩子。两本书中“灵魂”“鬼魂”意象的出现,都代表着两位作者现实中的身份意识,代表着个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关系,而灵魂视角正是他们身份意识的体现,既是代表自己并未真正融入现实,与现实文化的距离,也暗示一种观览全局的忽隐忽现的人物视角。
(四)创新之处
《百年孤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角,不是局限于一人的视角进行叙述,而是以作者的视角,讲故事似的,把最终结局一点一点地摊开。如果说《说文解字》是“始于一终于亥”,那么这部作品就是“始于零归于无”。马尔克斯通过描写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及其坎坷经历,提醒世人思考孤独悲剧的原因,寻找摆脱宿命的方法。《尘埃落定》中,阿来不是对马尔克斯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句式的简单模仿,这本书以二少爷作为第一人称讲述,以一种死去的身份,即灵魂叙述者作为全知视角,参与故事的始终。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是以意识流的方式,时不时跳脱出事件本身,好似有意提醒读者不要忘记“我”是个灵魂叙述者。以第11节《银子》为例,在将要开始叙述白银之前,作者先是暗示土司不是聪明人就是傻子两种极端身份,接着融合神话故事,写大风“哈”的几声于是世界出现,大鹏鸟产卵于是出现九个土司,最后才说到银子。这期间穿插“现在该说银子了”“是的,还没有说到银子”“但我以为我已经说了”这几句自问自答的话语,有意地创设前言不搭后语的混乱语境,看出叙述者的意识流动。再比如,寨子被轰炸后,“我”看着流血的躯体“往下陷落”,而那“干燥”的灵魂“正在升高”。这种非理性的荒诞手法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在《尘埃落定》中留下的痕迹。
有学者认为阿来是“精神上的混血儿”,这部作品折射出“当地方性风俗与统一进程存在矛盾时,少数族群知识分子对于地方性文化保护的反思”[7]。不仅如此,书中也有作者在面对历史潮流时的精神困惑和无所适从感。
对于“悲剧中之悲剧”的《百年孤独》,布恩迪亚家族的悲惨命运结局是作者建立在拉丁美洲民族革命运动的背景之下。在无法逃脱的个人命运背后,作者是想提示读者莫忘历史,同时揭示在殖民统治时期,人类会因为孤独、封闭而逐渐落后、消亡。阿来在《百年孤独》中看到马尔克斯对于人类历史的思考,对于人类敲响的警钟以及对于作家文化身份的寻求,受此影响在《尘埃落定》中选取川西的一隅之地,书写土司家族的故事,以及自己心目中的藏地文化历史。
综上所述,《尘埃落定》接受了《百年孤独》的某种影响,而阿来作为这种影响的接受者,又有着强烈的主体性立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其作品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也提示我们,民族文学想要在世界上站稳脚跟,除了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借鉴写作方法、风格之外,还与作家自我的内化、区域文化的把握、民族特色资源的挖掘息息相关。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品登上世界文坛。
参考文献
[1]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范晔,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253-276
[2]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6-10
[3]邓楠.国内《百年孤独》比较研究述评[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2):11-19
[4]宋虎堂.重审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悖论、对象与方法[J].南昌大学学报.2018(1):117-124
[5][6]徐静.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再解读[J]. 安徽大学学报.2005(2):75—79
[7]高岚.《尘埃落定》和《喧哗与骚动》的地方书写与国家进程[J].求索.2008(2):180-182
(作者单位:喀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