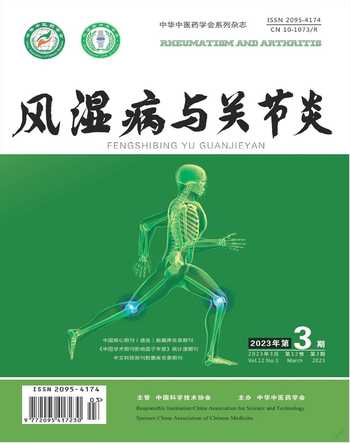从“一气周流”理论探析经方治疗风湿痹病
徐安冉 符强
【摘 要】 经方治疗风湿痹病为历代医家所重,黄元御“一气周流”理论基于经典,创新发挥,指出中气虚弱、阳气不足是风湿痹病的主要成因。从黄元御角度出发解释中气易虚的先天原因,以“一气周流”理论探析经方治疗风湿痹病的组方特点,体现为以扶阳培土为要,主以附子、干姜、白术等药;祛邪通经为辅,主以桂枝、茯苓、乌头等药。从而提出从“一气周流”理论认识经方治疗风湿痹病的组方用药特点,对风湿痹病的经方治疗起到提纲挈领,加深认识的作用。
【关键词】 风湿痹病;经方;一气周流;中气;黄元御
痹病为中医病名,痹者闭也,泛指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处发生疼痛及感觉性障碍如酸楚、重着、麻木等,甚至发生关节肿大变形或活动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病证;与西医学之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等疾病相关[1]。痹证病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中医经典理论入手可获疗效。黄元御为清代著名医家,被誉妙悟岐伯,提出了中气一元论,认为中气沉浮,不过阴阳,阴阳升降不过四象,中气者,土也,阴阳升降之枢轴是也,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癸水上温,是为坎阳,己土受之而以生发,润而不湿,乙木得土以达焉,先以三阴左升化肝木而升清阳孕阴根;辛金敛藏,戊土右转,相火得降,后以三阳下降化肺金而成真阴藏阳根,是成阴阳相交,坎离交姤,龙虎回环。形成了后世所称为“一气周流,土枢四象”的整体观。黄元御以他的角度从天、地、人整体出发,联系三阴三阳,总统五运六气,解释仲景之法,明确人体运行规律和疾病发生机制,并且指导临床的用药法则,以贵阳贱阴[2]的基本思想,勇創新方,为其理论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元御理论推陈出新,用药理论别出心裁,颇有心得。本文从黄元御的理论出发,以经方为要,治疗风湿痹病,论其组方原委,为临床组方提供理论根据,并予以临床校验,希以继往开来,开创新方。
1 基于“一气周流”理论剖析风湿痹病的病因病机
1.1 从历代医学经典中探析痹病根源 痹证根源,历来医书注解颇多,写尽繁杂。早在《素问·痹论篇》言:“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3]85
并把痹病分为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精简地指出致病原因和过程机制,以及证候愈后。《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云:“存口脉沉而弱,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肿,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故曰历节。”[4]19指出风湿痹病与肝肾亏虚、风湿侵淫皮毛筋肉而内伤坎离之位有密切关系。《中藏经·论痹》云:“五脏六腑感于邪气,乱于真气,闭而不仁,故曰痹病。”[5]强调体内元气盛衰是胜负关键。《格致余论·痛风论》云:“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6]首提痛风为病,血热血虚为其内在关键,强调祛风湿、补阴血并重,避免所谓“愈劫愈虚,愈劫愈深”之害也。《医宗必读·痹》云:“治行痹者,大抵参以补血之剂,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7]指出精血在痹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中起到关键作用。《景岳全书·风痹》云:“风痹一证……以血气为邪所闭,不得通行而病也。”又云:“然则诸痹者,皆在阴分,亦总由真阴衰弱,精血亏损,故三气得以乘之而为诸证。”[8]245划分出痹病的阴阳寒热界限且与气血关乎密切,并强调峻补真阴为要。《医林改错·痹症有瘀血说》[9]指出,痹证致病不止风寒湿,亦有瘀血凝滞经脉,并创身痛逐瘀汤以正其法。《医宗金鉴》总结历代之论有云:
“历节之病,属肝、肾虚。邪客始得乘之而为是病也。”[10]同时指出,内湿合于外风、外寒,外湿招致内寒、内热。总结出痹病的基本发病机制,外招之于风寒湿,内责之于肝肾,而关键则在于湿,不论内外。诸家对风湿痹病各有发展,不外乎受外气感召,机体素虚,邪气丛生,外伤皮毛肌肉,内负筋骨脏腑,中塞于经脉,病机随之改变,湿痰败血得以生发。总的来说,风湿痹病的病机根本是本虚标实,内外间以正虚为本,正虚则以脾虚为先[11]。黄元御切中要害,故云:“虽原于客邪之侵袭,实由于主气之感召。”[12]53前人俱言肝肾之内虚,论如何致病,却不提如何成病,虚之为何,何以环环相扣,双双俱虚。本文从黄元御的角度出发,以“一气周流,土枢四象”的整体观,探析病之为何、经方组方原委。
1.2 以“中气”为中心再辨风湿痹病 黄元御道法仲景,有言:“内因于主气,外因于客邪。”[12]53
客邪中人,必关乎六气,六气解言:“内伤者,病于人气之偏;外感者,因天地之气偏,而人气感之。”[12]9-10道明外感客气,乃因于天气地气之偏。痹证之客邪乃因于风寒湿三气为主,而热气非在其列,是痹病之热并非天之六气,而是人气有偏。《黄帝内经》早早明之,仲景法亦从之,而以酒湿内热,脉滑,谷气实,正是食饮内伤太阴。唐容川言:“湿为水火相交之气。”[13]186黄元御认为,水火之间孕育土气,寒热相逼,则湿气萌生[12]3。是其积而生内热,酒温遂与水气相搏而成湿。仲景亦言:“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4]19可见人气之中热气所偏,还需依赖客气中的风气相助而以成病,故唐荣川亦言:“此实热挟风之历节痛也。”[13]195所以痹之热气非客气所为,乃因于风寒湿三者。三气或多或少合而伤人。唐容川[13]203认为,寒伤卫气,风伤营血。黄元御亦提出,气本于胃,根于肾,统于肺;血源于脾,藏于肝,归于心。其在外是营卫,在内为气血,同气连枝,方而诱病。自此是客气所致。《灵枢·百病始生》言:“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14]黄元御认为,水寒土湿,中气不运是成病的主要因素,故言:“土湿之不升,则水木俱陷,于是癸水之寒生,乙木之风起。”[12]53
再探中气何故易湿,《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有言:“少阳太阴从本……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3]186盖太阴湿土本湿标阴,标本同气,故从本气。黄元御认为,足太阴以湿土司化,故司化者从之本气,常也。所以脾土易湿。且从其司化者化之,常得其常,则生化不息;但湿盛则燥从其化,此化之太过也。阳明戊土又何以湿?黄元御指出虽然阳明燥气,应从本气所化是其常也,但言:“己土之湿为本气,戊土之燥为子气,故胃家之燥不敌脾家之湿。”[12]13土者,中气也,故中气易伤。《杂症会心录》中更是把风寒湿之气归为内生之气,认为非投壮水益阴,则宜补气升阳。黄元御认为,水渗之以土气,则水不过润,水温土暖,则肝气调达,疏泄有常,恬静风清。相反,则是“木郁而生下热,然热在经络……其在骨髓之内,则是寒湿。”[12]54
故水流于膝踝沟壑之间,寒凝于溪谷之中,湿淫于关节之内,痰浊瘀血久久得之。此乃病成于主气,因于中气也。由此总结痹之为病,必内外相合,而以人气有偏为主。黄元御以“一气周流,土枢四象”的思想,基于经典的风寒湿三气中人,中气虚弱的观点,更加具体地解释了成病的环节,中气虚衰的原因,为临床治疗风湿痹病提供了具体的切入点,有利于经方的再发挥。
2 从阴阳升降、中气枢转探经方治痹
2.1 扶阳抑阴、培土建中为其本
2.1.1 温化之理,功在扶阳 五行之法,水不胜火,自然之理;六气之中,燥不胜湿,常也。盖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气,阳明之中,太阴湿土,燥从其湿化,以金遇土,则化湿。正如黄元御认为,足阳明在奉令之条,从其司化之气,则常得其常,却得湿而不燥;湿盛,阳明从其湿化,此化之太过。风湿痹病,寒湿之盛,或在皮毛肌肉,或在筋骨脏腑,人尽皆知。是以脾胃俱败,戊己双虚,责之于阳气也。经方用药,功于扶阳,仲景之审病用药始终将“以阳为本,时时固护阳气”的思想贯穿其中[15],痹病用药不离附子,或见乌头汤,或见桂枝附子汤,方类之多不再列举。近现代诸位医家也不乏用附子助阳,张荒生在《经方治痹》中记有,周超凡附子走窜治尪痹,朱步先膏附并用之治湿痹,赫军附夏相配治顽痹,金实乌附相合疗诸痹[16]262-265。亦有所评痹以辛温为主,佐以渗湿祛风,参以壮火[17]。更有周道凡[18]认为,顽痹需要使用辛温大热、搜剔逐邪之品才能起效。阳气者,根于肾,黄元御认为阴阳互根,坎离之中互藏阴阳,火根在坎,癸水化火,从而阴升化阳。痹者,肾阳损,故用附子,黄元御所言:“入下焦而暖肾,补垂绝之火种,续将段之阳根。”继言:“走太阴而暖脾土,入少阴而温肾水。”[19]144从而达到君相归根,神魂自安的目的。附子之药被誉除寒湿之圣药,附子所在之方乌头汤、桂枝芍药知母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风湿已取得广泛认可[20]。附子助坎阳,干姜温中阳,黄元御有言:“干姜温中以回脾胃之阳。”继言:“肝脾之阳虚,血海之寒凝也,悉宜干姜,补温气而暖血海。”[19]24所謂“附子无姜不热”莫过于此。仲景两者相合,共奏温肾暖脾、散寒止痛之功而回上下之机。至于蜀椒、吴茱萸之类,随证治之,莫有不妙。
2.1.2 回环之法,责于培土 诸温药下之,阳气已生,然欲其升腾,化肝魂,生心神,非己土所不能也。黄元御所言:“非用补土养中、燥湿降逆之味,附子不能独奏其功。”[19]144正是此意也。诸般经方用药治疗痹病,纯补土气之品,不离白术、甘草、大枣、薏苡仁、人参,参见甘草附子汤、白术附子汤、麻黄加术汤、麻杏薏甘汤等诸类经方俱可治疗风湿痹病,解关节烦痛。仲景用药与黄元御用药心心相印,志同道合。黄元御用药喜温热之品,重视中焦脾阳的健运,体现扶阳抑阴之法[21]。仲景用药归经之中以脾经居多,四气之中温性最大,五味之中甘味药频率最高[22]。可见经方用药时时固护脾胃,正如张介宾以为人之所赖以生者,惟在胃气。诸药之中当首见白术,再见薏苡仁,次见甘草、大枣、人参。李杲认为,白术“去诸经中湿而理脾胃”。黄元御认为,白术“最益脾精,大养胃气”[19]5。《神农本草经》则言:“主风寒湿痹死肌。”[23]39用术补土,不宜用苍术而用白术,《玉楸药解·草部》阐明:“白术守而不走,苍术走而不守,故白术善补,苍术善行。”[24]太阴己土得之温升而变神魂,阳明戊土得之敛降而成精魄。近现代治痹何不如此,治疗风湿不宜过汗,却须祛其邪气,但当加入白术,既可以健脾生津,亦可以燥土祛湿[25]。张荒生则认为:“脾虚湿困证常用白术,外湿困重证多用苍术。”[16]220继白术而探薏苡仁,近现代医家多用薏苡仁,《经方治痹》有记:张洪林薏苡治脉痹,韩俊生薏苡缓拘急,王纪云薏苡止疼痛,冯兴华薏苡疗诸痹[16]233-237。张荒生也认为:“薏苡仁诚为利湿之良药,疗痹之佳品。”[16]233-237
薏苡仁有如此评价,原是黄元御认为“薏苡一物而三善备焉”[19]16,上能利水,中能清气,下能燥土,继言:“补己土之精,化戊土之气。”又言:“能清能燥,兼补兼泻,具抑阴扶阳之力,擅去浊还清之长。”[19]17黄元御评价之高,可见薏苡仁作为经方选择的补土良药当之无愧。至于甘草,气色臭、味中正和平,四象齐全,五行兼备而有土德焉。黄元御认为,甘草随他药入肝入肺,合于中气,恢复阴阳升降。故盛赞其外以交互精神,内以调和气血。而人参、大枣,一言以蔽之。人参益胃气,助脾阳,补中气开经络,而生血,理中第一;大枣安中,养脾肋十二经,补精血,而化气,俱土德之全故被黄元御盛赞为天下之佳果、人间之良药。阴易盛而阳易衰,风湿痹病何止如此,俱寒湿流淫于筋骨脏腑,燥热隔绝于皮毛肌肉,是阴阳相交则成湿,水火相离则生燥,清风祛湿为其重,扶阳培土是之切也。治痹必求于本。
2.2 疏风通经、散寒祛湿乃其标
2.2.1 散寒祛湿为其主 痹之为病,邪中于人,早期一般以通为主,中晚期以补为主,然本病早期亦应着重补益肝肾[26]。继黄元御扶阳补土、温肾暖脾之功以成,中气以生,然邪气一日不除,无不为是闭门留寇。盖风寒湿痹久着于经脉、筋骨、脏腑,非药所及,难以自愈。寒湿是其关键,两邪同气,阴上加阴,非乌头不能剔除。祛除在里之寒湿,首当乌头,《神农本草经》云:“除寒湿痹。”[23]238
乌头非温脏药,而是破邪药,其入足厥阴,足少阴,祛寒湿,利关节,通经络,故黄元御评价乌头开通关节,性质峻烈,专驱寒湿[19]147-148。乌头辛温,破寒散湿,故乌头方剂主要被应用于多种疼痛疾病,且川乌成为治疗膝骨关节炎运用频率最高的单味药[20]。仲景治历节病,治疗风寒湿痹,创乌头汤,方用川乌五枚,而止痛其意正在此处。近现代名医大家亦活用乌头,张荒生记:“诸多医家常常强调重用乌附治疗顽痹,使用剂量少则数十克,多则百克以上……代云波和李可等。”[16]262-265经方祛邪次当选用细辛,《神农本草经》云:“主百节拘挛,风湿,痹痛。”[23]44其入手太阴,足少阴,味辛性温,直达少阴驱逐里水,故细辛条曰:“最清气道,兼通水源。驱水饮而逐寒湿……善降冲逆,专止咳嗽。”[19]92-93张荒生认为:“细辛散风邪,驱寒凝,无处不到;宣络脉,通百节,无微不至。”[16]247并提出其入煎剂用量可不受“不过钱”的限制,部分医家甚至超大剂量使用,而入丸散则宜“不过钱”。乌头、细辛类药乃祛里邪之灵丹,是乌头峻烈通彻肝肾,细辛温燥开通肺胃,而成肝肾寒去而生发、肺胃浊散而敛藏。仲景审病,而分内外。经方治痹,不但治寒湿深入,同治风寒初袭,是有已病防变之妙也。路志正[27]认为,解表发汗是治外湿之大法,先解表祛邪,待表证除,再治其本。参见麻黄加术汤、麻杏苡甘汤、防己黄芪汤、五苓散、猪苓汤均散在表之寒湿。邪气在表,宜以透散,俱归太阳经药,其用药首推麻黄。究其缘由,麻黄既散表寒,亦除里寒,沟通内外。黄元御认为:“麻黄浮散轻飘。”[19]103《景岳全书·本草正》言麻黄:“或兼气药以助力,或兼血药以助液,或兼温药以助阳,或兼寒药以助阴。”[8]1140可见麻黄随他药之上下或可解表寒,或可祛内湿,作为祛外湿之首,实至名归。次言防己,仲景防己黄芪汤乃是治疗风湿、风水皮水之良方。防己条云:“泻腠理之湿邪。”[19]128张荒生提出利水消肿首选汉防己,除湿祛风当用木防己[16]247。稍加分辨,擅以利用,则不失为良药。原是寒湿之气在经在脏,宜以祛之,麻黄以疗风水、溢饮,水湿兼顾,则经络开通而不为寒热;汉防己、木防己之类更祛脏腑、经络湿邪,邪气未有深入中气而在表在经在脏解之,中气不受邪则不为病。至于为何把猪苓、茯苓、泽泻归到此处作为祛湿利水之佳品,五苓散用桂枝上达太阳经气,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则用茯苓下达太阳经气,恰如唐荣川所言:“发汗即所以利水……利水即所以发汗也。”[13]401即是此类药物皆是治法不同,但本质相同,皆达太阳。黄元御认为,茯苓、猪苓、泽泻泻湿生津,是水气以去,湿气以散,三焦得通,肺气布化,津液自合。是以水湿去,则中气自运,病何以生?茯苓条言:“泻水燥土,冲和淡荡,百病皆宜,至为良药。”[19]122-123而黄元御更是盛赞其功标百病,效著千方。至于猪苓、泽泻,乃是轻重之分,黄元御在猪苓条和泽泻条指出,三者俱能利水祛湿燥土,但以泽泻最强,猪苓次之,茯苓最弱[19]122-123。自此是黄元御解经方祛内外寒湿用药之法也,擅加用之,熟知法度从而随症加减,则古方可得解,新方终可创。
2.2.2 疏风通经是其辅 王义军[26]认为,风、热皆依赖湿邪而存焉,但湿邪去二气自解,脾阳以生,胃土以燥,外风自散。然内风犹在,必内外俱清,燥热乃去。古有李中梓强调治风从血论治,而当代医家焦树德总括古今治法结合自身心得感悟出祛邪同时勿燥血、勿助火、不劫阴的治疗法则。可见疏风同时,重视精血十分重要。经方之疏风养血,不离芍药、地黄、阿胶、当归、防风诸类,而黄元御对此经方选用有特别的理解。从黄元御理论出发,内热之生发,因于肝经疏泄失令,木气郁遏,下成癃闭,上生燥热。故其用药不离其理,芍药条言:“清风燥、敛疏泄。”地黃条言:“滋风木而断疏泄。”阿胶条言:“滋乙木之风燥,而止疏泄。”当归条言:“养血滋肝,清风润木。”[19]49-57黄元御认为,诸药俱入肝血,滋肝木,顺肝之性,则肝气顺达,内风自消。防风归聚于此,黄元御认为,防风祛风是通过疏发肝性,达到木达风息的效果[19]49-57。防风为药,同时调节肝气疏泄,则张弛有度,气血自和。诸类疏风养血药黄元御多从厥阴入手,盖肝经调达,疏泄有常,则燥热不生,而能助肝脾左升之妙,但多为滋腻之品,痹病之候,皆宜寒湿为主,中气易衰,总以固护阳气为宜,故不宜多用。正如黄元御所言:“抑阴扶阳,不易之道。”[19]49-57至于通经祛瘀乃是治其标,通其气血,解其疼痛。通经之药,主用桂枝继用黄芪,参见桂枝芍药知母汤等经方。张荒生《经方治痹》记:焦树德桂枝横通肢节,张云鹏桂枝开通痹阻,邱健行则认为桂枝走表窜窍而通十二经,张荒生亦称其是内祛脏寒,外通经络的良药[16]226-228。是合黄元御所识桂枝解风邪,顺木气,疏肝郁,通经络,开痹涩,和阴阳,故言“化阴滞而为阳和”[19]75。若桂枝之不通利,黄元御加以黄芪,则通经之力倍增[12]54。黄芪擅达皮腠,专通肌表,能发能敛,能补能收,随辛甘发散,亦随酸凉敛降。于是风气去而精血和,气可通,血可流,则寒湿俱解,痛烦自消。至于患病日久,瘀血丛生,王义军[26]认为,可以根据临床症状加入活血化瘀药防止疾病传变。寒凝气滞,旧血瘀阻导致的经脉不通皆是中气虚弱外合邪气的共同结果,黄元御以桂枝、黄芪类药,佐以活血化瘀通经复脉,从而经脉邪气以去,脏腑表里可通,则内外循环周流往复,中气健运,痹证随之而解。
3 结 语
当下对风湿病的研究尚无突破性进展,同时也无根治药物;但在风湿病的治疗上,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日益明显,并蕴藏着极大的潜力[11],黄元御的“一气周流,土枢四象”观点虽是众多学说的冰山一角,但在临床工作中稍加思辨便有助于增强中医疗效。黄元御针对痹病,套用阴阳升降的观点,重视中气的盛衰,解读六气偏见、从化关系,从而重新看待经方如何选择用药,以自己的看法解释了经方的用药规律。痹之为病,中气虚弱贯穿始终,故黄元御用药以培土扶阳为中心,着重强调运用白术、甘草等纯补土气之药为主以生土津复土气,附子等温脏腑以助土阳;四象周流为旁支,多运用黄芪、乌头、桂枝等祛邪而通利经脉,从而使四维相转,而无阻碍。同时,黄元御亦明确了痹证的内外成因和各个证候出现于各个环节的缘由。黄元御扶阳抑阴一气周流理论不免有不完善甚至不正确之处,限制了发展,但不失为一次勇敢的创新,值得学习。理论的不足正给了改正和发展的机会,黄元御在六气从化言成功者退、将来者进,恐意在此。
参考文献
[1] 吴勉华.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2017:363.
[2] 汪辉东,强爱萍.从《长沙药解》探析黄元御的扶阳抑阴思想[J].青海医药杂志,1994(S2):5-6.
[3] 佚名.黄帝内经素问[M].田代华,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85,186.
[4] 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9.
[5] 李聪甫.中藏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65.
[6] 朱震亨.格致余论[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4.
[7] 李中梓.医宗必读[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314.
[8] 张介宾.景岳全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245,1140.
[9] 王清任.医林改错[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60.
[10] 吴谦.御纂医宗金鉴[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223.
[11] 黄旦,刘健,万磊,等.从脾治痹探讨[J].风湿病与关节炎,2021,10(1):46-50.
[12] 黄元御.黄元御医学名著三书[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3,9-10,13,53-54.
[13] 唐容川.唐容川医学全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86,195,203,401.
[14] 佚名.灵枢经[M].田代华,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30.
[15] 李满意.应用《伤寒论》六经理论辨治类风湿关节炎的体会及探讨[J].风湿病与关节炎,2022,11(7):42-46.
[16] 熊源胤.经方治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220,226-228,233-237,247,262-265.
[17] 何为贵.中药为主治疗类风湿关节炎102例临床效果分析[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3,12(1):18-19.
[18] 周道凡.中医治疗120例风湿病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1,9(32):390-391.
[19] 黄元御.长沙药解[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5,16-17,24,49-57,75,92-93,103,122-123,128,144,147-148.
[20] 燕美彤.含附子、乌头经方在风湿病中应用研究初探[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20.
[21]周洁,喻斌.基于数据发掘分析《四圣心源》中内伤杂病的用药组方规律[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9,31(11):2099-2102.
[22] 王楠,谢林.《伤寒论》痹证治疗用药规律探索[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4):1760-1763.
[23] 佚名.神农本草经[M].孙星衍,孙冯翼,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39,44,238.
[24] 黄元御.玉楸药解[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1.
[25] 岳峰.麻黄加术汤加味治疗风湿病患者的临床体会[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3(4):33,43.
[26] 王义军.浅谈风湿病中医用药体会[J].中医药研究,1999,15(2):51-52.
[27] 杜羽,姜泉.路志正教授运用《金匮要略》理论论治风湿病经验[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8,7(5):48-50,67.
收稿日期:2022-11-10;修回日期:2022-12-20
作者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通信作者: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