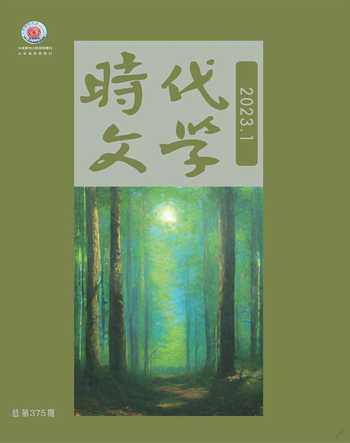隐没
赵飞燕
“枣红马,奋蹄欢腾;长嘶鸣,它也知回归故里任驰骋。”
风窜过屋子,生了铁锈的窗户片子被推搡着吱呀叫喊,拉长的阳光被捣碎一片,斜洒在灰匿的犄角旮旯。糖饧起色,加火烧开,放入泡好的油粉丝,将白细的内酯豆腐倒进油锅煎炒。巧英婶儿哼着晋剧炒着菜,气色却不减当年,麻利的劲头不输那些婆娘们。这幢教职工宿舍的同志们搬的搬走的走,一年下来,新人送旧人便成了常态。城东拆危房,城西起高楼,唯有这背靠天主教堂的两幢蜗居小楼没有被岁月淹没。巧英婶儿掀开六棱角的木制调料盘儿,撒了把葱花芝 麻,淋上香油,整个楼道便都是嫩豆腐的味道了。
晌午,学生放学,轻重不一的脚步声从头顶咣咣传来。电瓶车的鸣笛和孩子们嬉笑的叫喊,刹那间划破了小楼的死寂,也让这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有了点生气。三轮车嘎吱嘎吱地叫嚷,男人呼哧呼哧地喘息,女人泼辣豪迈地催促。“啪嗒”一声,那是新搬来的对门儿开锁的声音。日子如烟,往往总是送走那旧人迎新人。
方寸的阳光窸窸窣窣洒在刚出锅的豆腐上,也别有一番味。门厅的门没有关,风穿堂涌入,日历的扉页被掀开,在嘈杂的风里沙沙作响。
巧英婶儿老两口是前年才搬过来的,自从住进这个小楼,生活便波澜不惊,如石子坠入深水,不见半分水花。城很小,巷子也很窄,风却吹不到从前。故人在慢慢离去,往事似乎被时间遗忘。巧英婶儿看着日历,渐渐回想起几年前的旧事。
1
“云淡天高南飞雁,霜染红叶景朦胧。”
“依依远村二三里,雀鸟归巢绕树林。”
巧英婶儿爱花,是远近出了名的花大婶。野猫发困横卧在花盆里,压毁了无数新芽,倚断了刚努出的嫩枝,看见巧英婶儿出来,慌得四下逃窜。拿着笤帚的巧英婶儿四处寻猫,誓要与这“毁花大盗”斗个高下。可终究还是那野猫腿脚灵,此后,庭院便再无猫的痕迹。
别人的院子空空荡荡,或许拉根铁丝晾衣服,便已是生活的全部,巧英婶儿却拉着铁丝养牵牛花,四下里斜斜密密地扯着网,编成一堵春天的花墙。午后,暖风轻轻地吹着,总带来些花香。巧英婶儿躺在院落的藤椅上,侧脸数着还没冒芽的花骨朵, 渐渐闭住眼睛。
巧英婶儿那个年代从不轻言爱,谁也不知道爱是什么。规矩地遵守生活安排,便是最大的本分。退了休的老汉总喜欢研究《易经》,戴着厚厚的老花镜,掀着一沓信纸写着什么。似乎字里行间都是学问,但让他离了那书本说上两句,却也只会些阴阳八卦。巧英婶儿总戏谑地说他不懂装懂,除了看书啥也不会。殊不知清早院子里的花全是老汉一人浇的。浇多浇少,已经被仔细地测算过。后院的邻居每次推着大梁自行车咣咣路过,只发现花一日胜于一日,根茎粗壮,叶子肥绿, 整个巷子里洋溢着晚春的气息。
又或许这院子里的花,不只是巧英婶儿一人的。
每天人们来来往往,都会驻足欣赏一番,才会兴致盎然地各回各家。
纪瞎子是这城里出了名的风水先生,后院有鄰居赶着春天办喜事,邀他在院子里算算祭拜方位。纪老先生拄着拐杖从前院穿堂,驻足停留,只言这里有灵气,兴许是将春神请进了家。从那时起,这方院子便更有了生气。巧英婶儿的街坊经常聚在一起拉家常,扯天说地好不痛快,各家难念的经也往往在一杯茶、几支烟的消磨中渐渐淡去。或许,也正是从那时起,庭院不仅有了春气,更有了人间生活气。
傍晚,浅紫色的牵牛花簇拥着春日的阳光,在风里摇曳。老汉担着水桶去“水点”把水缸挑满,巧英婶儿哼着曲在院落的厨房里做饭。炊烟在空荡荡的天上升起,又似乎在书写着什么。缥缈的烟,缱绻地打着弯,和那被打散的斜阳将天空染成了模糊的金黄色,仿佛两面煎至焦黄的荷包蛋。
二弟从乡下骑车进了城。长姐当母,他是巧英婶儿从小背大的。姐弟俩一向感情深厚。他将一袋子窝子面放在门厅的地上,还带来了两罐子刚煮的咸菜。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了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粮菜丰足。姐弟二人坐在院中,一边喝茶一边寒暄,聊着各自儿女的近况。似乎每年都在变,又似乎每年都没变。随着人的年岁渐大,最怕的不是重逢,而是分离。时间推搡着人往前走,谁都无法幸免。巧英婶儿的母亲不喜欢城里的空气,去年索性随着她二弟住到了乡下,可她近来胃口大减,不思饮食,睡眠也不好。
二弟望着一方花墙,缝隙之间却怎么也看不到太阳。他蹙着眉,讲着老母的近况。人老了,或许花期也将近,总以为什么都看开了,又似乎什么也没看开。有的时候,只是不愿再去想,不愿再与时间纷争,以为落了一处安闲,心口却空落落地漏风。吃过晚饭,二弟又骑车赶回乡下,临走叮嘱巧英婶儿记得回乡下看望母亲。
午夜,春雨淋漓,牵牛花瓣散落一地。雨中弥漫着的草叶香萦绕在巧英婶儿的梦中,却怎么也走不出梦的桎梏。清早惊醒,她佝偻着背,撑伞在庭院中久久凝神伫立,豆大的雨珠子压弯了花枝。可她却无心看这满院的春色,暗暗焦急母亲的身体,恼恨自己被这不绝春雨困住了腿脚。有时候,岁月真叫人恼,难事事顺心,无法得偿所愿,只能慢慢等着。等什么?等待戈多吗?我们不知道,可能是等花期,又或是等待春天。
2
“渔樵互答尽乡音,农夫荷锄田间走。”
“担头春酒一瓢多,树底看山树底过。”
院井四四方方的天,蒙上了黑色的网。阻断了恶狠狠的太阳光,却逃不过酷暑的高温。老汉紧闭着窗,严磕着门,舍不得让门厅里空调吹出来的冷气四散出去。德顺,是老汉去年养的一只小土狗的名字,它窝在桌腿肚子旁,正吐着舌头长哈气。老汉边吃饭边用筷子逗弄它,巧英婶儿看了一个劲儿地说他,嫌这不卫生。老汉却总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逗弄着德顺。
电视里循环播报着新闻,这台老旧电视年久失修,画质差,声音也不好。“刺刺啦啦”的,需要细心再细心才能听得清。吃过午饭,巧英婶儿总喜欢在床上侧卧着,撑着脑袋打瞌睡。老汉将背心搂在胸前,坐在沙发上,看国际新闻。门厅里的空调早关了,风扇还在左摇右晃地转着头,风扇叶划过空气的摩擦声伴着新闻里浑厚的男声,却怎么也压不住已经熟睡的巧英婶儿的鼾声。这似乎吵到了卧在老汉鞋旁的德顺,它竟不满地翻了个身,重新找个舒服的位置继续睡。老汉看着巧英婶儿,也不满地把电视的声音再次调高。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这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不再是因为春神的传言,却是二拐子的风言风语塞满了整条巷子。二拐子守寡好多年,两个儿子都已各自成家,平时就她一个人住在小巷尽头的一个大杂院里。
事情要从后院邻居汉林平白无故要在家里养鸽子说起。酷热的天,人禽共生,且不说卫生与否,长长的臭味充斥着整个庭院。妻子险些被他这兴起的养殖业闹得离婚,带儿子大包小包搬离了院子。汉林竟也不管不顾,一根筋地喂养起了鸽子。
似乎自那时起,二拐子便天天一瘸一拐地往院子里跑。每次来,总要带些剩菜叶子,说是给汉林的鸽子吃。有时还会带一些她做的饭给汉林吃。她虽腿瘸,却从不拄拐,两脚落地总轻重不一,好像是用右腿支撑,拖拽着左腿前进。
她总穿着那件头刮出线头的西瓜红T 恤,那件T恤洗得发白。灰格裤子的屁股后面总不干净,整个人邋里邋遢,却又风风火火。
巷子的邻里喜欢在担水时聚在“水点”扯闲篇。有人说她三只手, 曾经不是本分人;又有人说她嘴很碎,总把别人的家事往别处说。现在她趁汉林妻儿离开之际,跟汉林套近乎,其目的总是让人想入非非。
看见汉林担着水桶过来,刚刚喧闹的人群霎时没了声音。水珠子咣咣砸着,溅着水花。这条巷子很窄,窄到一次只能过一辆车。车马很慢,人很喧嚣,日子却也拉长了。暮色沾染着粉色的晚霞,零零散散地闪着几处星光。小孩子们聚在巷口扣洋片,随着晚饭时间临近,大人们一声声催促,小孩们便如鸟雀般散去。
不知什么时候起,老汉开始把德顺拴在了院子里。德顺本就懒散惯了,现竟试图挣脱着寻找自由。二拐子一进院门,德顺便吠个不已,似乎在邀功,证明自己是条好狗。每当这时,老汉便习惯性地从窗前的缝纫机那儿站起,望着她一瘸一拐的背影消失在里院。老汉重重地吐着烟圈,空气里一片死寂。
巧英婶儿却不以为意,继续在院落的厨房里做着饭,没把这进进出出的大活人放在心上。庭院里每天都是各色饭香,或是西红柿炒辣椒的香辣味裹着烙饼的酥香,或是猪肉馅儿包子的清香带着倭瓜稀饭的腻歪味,似乎都成了那些闲言碎语的防弹衣。飘进老汉的屋头,压住了呛鼻的烟味。
渐渐的,德顺也懒得理二拐子了,偶尔只吠一两声,便躺在地上不再出声。再后来,德顺更是自顾自睡它的懒觉。听不到狗的叫声,老汉以为二拐子没再来。每次犬吠,老汉都习惯性地站起来在窗口张望,却发现只是进来给后院阿姨送牛奶的后生。
莫不是二拐子不来了?
直到某个傍晚,巧英婶儿与二拐子敞在庭院里,坐在马扎上聊天。德顺竟也温和地卧在她脚边,等着喂食。老汉掀开房门窗户上的厚帘子,定定地看着那吃里爬外的家伙,骂了句狗东西。
似乎谁都不知道真相,又似乎谁都知道真相。其实真相并不重要,或许巷子的邻里们根本不关心二拐子和汉林到底有没有一腿。这些也只是生活的谈资和小市民的乐趣,真正的生活从来不需要真相。风很聒噪,咋咋呼呼地吹过人们耳畔,躲在树上的知了叫嚷着夏天,彻夜的星辰却怎么也抓不住仲夏的尾巴。
3
“马儿啊,长嘶鸣。 ”
“朝倚窗台望天空,红叶纷飞满城红,唤起思念满街是。 ”
叶子渐落,秋意渐浓,厚重的霜裹着微微寒意,万物似乎又恢复了曾经的秩序。北方的秋风,没有喜怒哀乐,却如刀子般刮出干燥的口子。不如冬风凛冽,却也不似春风和煦。正像那郁达夫所描绘的《故都的秋》,来得特别清,来得特别静,来得特别悲凉。
似乎秋总是和旷古的孤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英婶儿正用手丈量着毛衣的骨架,拆了搭搭了拆,终于找到清晰的路子。老汉竟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研究起了中药材,思索着哪几种药材放在一起是袪湿的好方子。似乎环境越静,人越需要沉下心去打磨自己。冷风拍打着窗户,刮着门板,老汉亲弟竟寻上门来, 找老汉开方子。老汉扶着老花镜,顿笔思索,药方讲得头头是道。巧英婶儿总担心把人家吃坏,却不想老汉还真有两把刷子,老汉弟弟后来又找老汉开方子,据说在这秋意渐浓的季节,折磨他好多年的舌患竟然再也没犯。
日子一天天过去,巧英婶儿老两口说话越来越少,沉默却也变成了默契。可怕的并非相顾无言,而是无法相伴相守。人的孤独已然不再是情感上的共鸣,更多来自事实上的陪伴。老汉总是闷着头抽烟看书,巧英婶儿则按部就班做着每一餐饭。谁也不知道生活到底是什么,但看着窗头明晃晃的太阳,便知道这又是一天。
秋天的暖阳总是阴晴不定,太陽在云际间游离,影子也拉得越来越长。
巷子里挖出了沟渠,工人们半截身子安在地下埋着水管。“水点”的两大块青色石板被搬走了,似乎自那之后,“水点”便从这个社会空间消失了,邻里之间也少了些闲聊的机会。人们好像再也没见过二拐子,也没再听说过她的事情。
老汉也发觉那个一瘸一拐的背影似乎消失了,却又忘了何时消失。可又感觉这些已经不太重要了,或许又从未如想象中那么重要。德顺在脚边依偎着,曾经吃里爬外的叛徒,现在竟睡得更加慵懒。
整整一个秋天,巧英婶儿总是打着毛衣,坐在沙发上打,坐在院子里打,躺在床上打,似乎她在织着秋天,又似乎她在等什么人。她也不知道,只是机械地织着,或许织完就可以看到秋的意义。前天从乡下看望母亲回来,她心情又好了许多,母亲最近胃口大好,一顿要吃七八个饺子,一觉能睡到天亮。
所幸中秋月圆日留在了秋天,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儿女们携全家回到这座小城探望双亲。平日的忙碌终于有了释放的空隙,无尽的寒暄让浓浓的亲情不断升温。巧英婶儿今晚特别兴奋,她将供奉的火龙果、石榴、团圆饼摆在院落的古架上,竟也映衬了“花好月圆”四个字。
拜月开始了,孙儿孙女在寂静的夜里追赶打闹,争抢着小小的一份月饼。德顺竟也加入了这场争抢,二人一狗竟颇有些乐趣。或许这场追逐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孩子的世界,本就明净如一汪湖水,看到什么便是什么。最美好的是单纯,最让人忘不掉也是年少的单纯。
巧英婶儿在厨房笑着做中秋节的晚餐,她似乎看到了活着的意义。一阵风起,又吹落了满枝的枯叶,或许这就是深秋该有的样子吧!
4
“报个信,木兰啊,归来也。”
“万里归来一声叹,从前友人不复来。 ”
数九寒冬腊月天,冰窗花攀附其上,微微的光晕染开来,便成了万花筒的眼睛,试图窥探大自然的秘密。老汉联系年轻的后生,拉来半卡车煤,一锹一锹地装到塑料袋子里,又码放到院子的角落。刺骨的寒意钻进了厚棉袄子,直击皮肤,似乎要穿透灵魂来个赤裸的拥抱。巧英婶儿拧了把鼻涕, 将二弟拉来的脱了玉米的干棒子扔进火膛里,勾着火钳翻搅,火势愈来愈大。摊着饼子,背火烧,先刷油,后翻面,空气里充斥着一股说不上来的香。院子里干活的后生们,竟也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口卜子,火卜子。”老百姓冬天有吃的,有烧的,才会安心过冬。
或许这冬天太过强势,又或是那天抬中煤拉伤了筋骨,向来不肯服老的老汉, 竟也抱着个腰天天喊疼。巧英婶儿刚开始以为老汉太娇气,又或是不想早起生火罢了,后来才发现,天一寒,老汉走路的背影都有些颠簸,深感岁月不饶人。毕竟有点岁数了,老汉年轻时在公社交公粮一人背两麻袋麦子上仓库,气都不喘一下,现在竟也被岁月压倒了身板。
冬天的阳光再暖,仍有阵阵寒意。德顺也怕冷,它向来就是条懒狗, 吃了睡睡了吃,窝在老汉的鞋旁,似乎在表忠心。老汉反倒没那么喜欢它了,他骨子里认为不会看门的狗不是好狗,见它在家卧着,竟也看着不顺眼,但寒冬腊月赶它出去又有些心疼。
这下,反倒让它和巧英婶儿走得更近了。巧英婶儿一早起来便给这狗切肺子肉,和大块大块的馍拌在一块,它竟也吃得毛色油亮,那条粗大的尾巴总像个扫把似的, 在地上磨来磨去。似乎冬天再冷,德顺也很难感受到。或许在它的眼里,世界便只有肺子肉和馍馍头。
一天大早,巧英婶儿出门去买菜,才知道二拐子走了,突發脑溢血走的。如果当晚有个人守在身边,及时发现抢救,她或许不会走吧。巷子里的人们各忙各的,冷风呼呼地刮着,人们匆匆见面也只偶尔说起,好像二拐子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也好像她从未来过世间。
后院的汉林也早就不养鸽子了,许是没有跟上市场形势,可老婆孩子却再没有回来。满腹雄心的男人,似乎一夜之间便老了,头顶冒出缕缕白发, 恰似冬天的白雪飘落,怎么也挥之不去。
人们谁都说不清夏天那些秘密,大家似乎都愿蒙在鼓里,在鼓皮上画着一个又一个问号,试图用自身的逻辑求证对方。或许真实的秘密也不那么重要,毕竟有趣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我们洗尽凡尘后的模样。
年纪大了,对很多事力不从心。年前年后,张罗准备,本是每年最兴高采烈的事,现如今也成了巧英婶儿的烦恼。老汉整日躺在床上看书养神,能不下地便不下地,家务事一件也不做。孩子们担心母亲太操累,索性在饭店订了一桌子饭。
大厅里,人来人往,大厨子的手艺自然比巧英婶儿好多了,但饭菜里却怎么也吃不出年味。噼里啪啦的鞭炮,小孩子穿着新衣,咿咿呀呀地拜年,一年重复着一年。许是时间一直推着人走,可人却怎么也走不动了。
自那个年之后,巧英婶儿两口子便搬进了这幢单元楼,火自然不用自己生了, 省了很多麻烦事,也留下了很多遗憾。规整的楼里,哪有什么地方养花,以前院子里的花,也只能自生自灭。德顺已经吃得一身肥膘,懒得不爱动。若在这楼里养狗,可能就像当年的汉林养鸽子般扰民,只能叫二弟拉到乡下去,帮 他看猪圈,省得母猪生的崽子被偷。
也不知德顺那只懒狗,现在过得怎么样。
冬雪将至,似乎春的声音也近了。可那个夏天却再也回不去了。
“过分关,越汉岭,关山飞渡;信马由缰且缓行。 ”
巧英婶儿迟暮地望着地上斑驳的阳光,被框条窗户杠子切成了四分八块。端着那碗嫩豆腐,给老汉递进去,竟又吵着自己还不饿,俨然一个老小孩儿。搬进了这单元楼,旧友们很少来串门。或是路太远,许是事太杂,没有人匀得出时间来重逢,寂静又惬意,或许才是暮年的底色。
“咚咚咚”一阵叩门声,原来是送牛奶的后生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