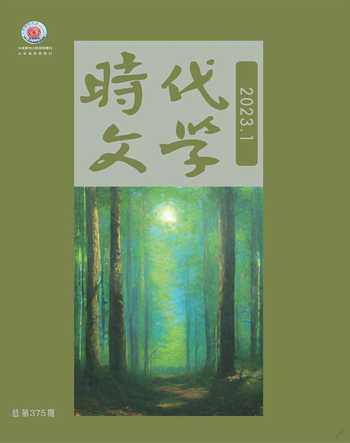南山种豆人
刘洪浩
说来也奇怪,没有喊屈原、李白“老屈”“老李”的,他们似乎总是长衣飘飘、仗剑远行的形象。当然,喊杜甫“老杜”的倒是很多,佩服他人诗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唯独喊陶渊明为“老陶”的时候,那感觉如同相邻、旧友一般亲切,甚至带点亲切玩笑的意味。比如,戴建业老师就喜欢开老陶的玩笑:“‘草盛豆苗稀’——种的是个鬼田!要是我种是这个水平,我绝不会写诗。”
当然,玩笑归玩笑,引起对老陶的误会就不大好了。首都师范大学的邓小军教授等学人只好耐心地一遍遍和大家解释:首先,从《归园田居》第一首得到证据表明老陶“种豆南山下”的那片地是人家费了老鼻子劲“开荒南野际”,刚开垦出的“生田”,而按照《齐民要术》总结的“科学种田指南”:“凡美田之法,绿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羹懿反种,七月、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这里说的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豆类植物,可以充分利用其特有的根瘤菌固氮效应,长养土壤肥力,让生田慢慢变成熟田。其次,大豆种植本就需要“均而稀”,大株距种植、粗放式管理,以利于通风结荚。江南之春,草木蔓发,赶上哪天早晨,老陶到地头上一看,“草盛豆苗稀”,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下地锄草本就是日常农活中的大宗,不能因此而批评他种地水平不行,对吧?
当然,仅仅认证“陶渊明精通农业”,恐怕远远不是“种豆南山下”的全部意蕴。“晨兴理荒秽”之“兴”,“但使愿无违”的“愿”,都远不止科学种田那么简单。
种豆南山下
读诗,不可太着相。因为诗歌从来不是关于“科学种田”的“说明文”,也不只是诗人幽默自嘲的“脱口秀”。诗歌的魅力正在于:它始终以“典故”“意象”为舟,在“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之间自如游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具体到“种豆南山下”,宋末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时即已注明,典出《汉书·杨恽传》: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南山”——“种豆”——“荒芜”,从意象到逻辑,面对这种如影随形般的高度一致,我们不可能继续止步于田园农事,而应该从历史文化精神的长河中去把握陶渊明的知识视野和思想理念。
唐人颜师古《汉书注》所汇集的张晏等汉唐学者的注解,恰好可以帮我们抵近杨恽、陶渊明在其中呼吸相通的文化语境。按照《汉书注》的分析:“南山”寄寓着古人关于光明、高远、永恒的理想追求,而“荒(芜)秽”则是混乱、腌臜、无望的现实。“南山”与“荒(芜)秽”构成一组理想和现实之间对比强烈的政治性隐喻。而“豆”则被视为“贞实之物”,“草盛豆苗稀”正是隐居放逐、“零落在野”的诗人自己的遭际。种豆是诗人在大地上、朝向永恒艰难栖居、自我实现的努力,而随时席卷而来的荒芜,是理想空间的逼仄,是信念必须面对的磨难。也许有人会说,大喊着“人生行乐耳”的杨恽和陶渊明不是一路人。岂不知颜师古注解“须富贵何时”的“须”字意为“待也”。“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的正是真正的快乐,是与“富贵”无关的完全自我的生活、行走与快乐。陶渊明正是把这种纯然无瑕的快乐描绘为“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由诗及人,我们会发现杨恽与陶渊明之间相似点奇多,堪称同病相怜,异代知己。论家世,杨恽是丞相杨敞之子,家族内“乘朱轮者十人”(公卿列侯及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重臣,即使刘宋取代了东晋政权,陶家也同王导、谢安家族一道得到继续承认,颜延之为陶渊明作诔辞时还说他“韬此洪族,蔑彼名级”——正是这种世家大族的出身,给了杨恽和陶渊明清刚狷介的骨气、底气。杨恽和陶渊明面对污秽现实时同样选择了不屑不洁、抽身而去,他们的第二点相似处便是免官躬耕、隐居务农的相似处境。因为汉宣帝宠臣的攻讦,本来在政坛上头角峥嵘、令行禁止、廉洁无私的杨恽被免为庶人,家资千万的他“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显然是有意为之,而不是生活所迫。他在“仰天拊缶”“奋袖低卬,顿足起舞”大唱“田彼南山,芜秽不治”之时,其衷肠九曲却是“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末世矣”,其间且悲且愤、痛彻骨髓,真可与司马迁《报任安书》并列。而隐居的陶渊明其实也不仅仅满足于作回归自然的“羲皇上人”。他跟儿子们说自己辞官归隐是因为“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守拙归园田”所以“种豆南山下”。这个被陶渊明反复提及的“拙”,必须通過与其相对的“巧”来理解,何为“巧”,《离骚》有言“固时俗之工巧兮,缅规矩而改错”,时俗之“巧”是为了趋时媚俗而处处妥协,为了逢迎权贵而不断拉低底线。而陶渊明所守的“拙”,绝非逃避现实,而是宁折不弯,这是以最本真的人格去直面世俗所施加的全部磨难。正如范子烨《悠然望南山》所说,“任何的隐逸,关键要自由选择,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期待与个人信念的协调问题”,陶渊明的隐居是自己对当时社会的总答复,他的“守拙”是回到自己的“本源近旁”,是对人格的捍卫、对良知的坚守。
当然,“守拙归园田”的日子并不总是快乐的,困顿清苦、寂寂无闻远不是纸面文章,而是随时随地、具体入微的磨难。比如说清贫,在隐居的陶渊明这里就可能具体为饥饿感一分一秒地轧过肌体——“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那份无助的疼痛在脉搏里跳动,在呼吸间缠绕,雄鸡报晓成了苦等未至的大赦。比如说孤独,陶渊明要面对的,常常是昔日旧友被新朝征召出山,权势地位变化带来的“压强”,噎住他想说、能说的所有话,最后以一句“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跟人家一拍两散。比如说抱负,归隐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都基本告吹,寂寂无闻的死去似乎成了陶渊明唯一可预见的结局,“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身没名亦尽”“空视时运倾”……田晓菲曾归纳说:“陶渊明是第一个反复权衡、讨论、解释和辩护他的归隐决定的诗人。”用心体会老陶的所有诗,才会明白“南山”“种豆”“荒秽”——当陶渊明与杨恽《报孙会宗书》里的这些文字在时空中应和的时候,“长为农夫以末世矣”正如一根尖刺隐隐戳入他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就算是这样,杨恽、陶渊明对自己归隐务农的抉择也九死未悔。杨恽宣称:“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公开表示自己对君主对朝廷只负有有限的责任,一旦自己抛弃“卿大夫”身份,就可以放浪形骸、随心所欲地追求自由自主的快乐。陶渊明虽然表现得比杨恽温和一些,但是如同“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一般的倔强,也不遑多让。
夕露沾我衣
顾随《驼庵诗话》有云:“陶渊明的诗不是滞水而是暗潮,表面像是平静,实质的内容是动荡的,充满了英气。”
就像他咬着牙愣是挺过一个个挨饿的白天黑夜一样,陶渊明在诗里不激烈也不绝望,只有冷静、平和、从容和坚忍。但是秉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我们应该明白归隐务农绝不只是看得到的闲适、诗意,得去深切地体谅在“长为农夫以末世矣”中潜藏着多少辛酸、不甘。老陶绝不流于愤世嫉俗,而是以抉择面对考验、用坚守挺过磨难,孤身一人跋涉在命运的荒原上,而且通过尚友古人、反身经典,在自省乃至自嘲中,蕴藉深沉的心思,生生把这片荒原,开垦为诗意的绿洲。
“种豆南山下”一诗的最后四句,便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不去理会诗歌蕴藉的历史文化精神,我们当然也能看出全诗的旨归在“但使愿无违”。可是为何“愿”只在最后时刻出现,这场“露水”反而要用三句来铺陈?好比说读《西游记》,难道说直接翻到师徒四人跪拜在灵山大殿上,取得真经、功德圆满,就可以把前边的九九八十一难一笔勾销、忽略不计吗?还是要老老实实回过头来,仔仔细细地看“夕露沾我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古直笺注陶诗时,认为这句诗与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从军诗》其三中“草露沾我衣”一句具有传承呼应关系。
“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在《归去来兮辞》小序里,陶渊明对半生宦游给自己留下的心理阴影交代得很清楚。王粲《从军诗》中那份“跋涉途中”的复杂心境,他肯定心有戚戚:征战遐远,山川迥异,归宿全然难料;暮色已至,孤鸟独飞,寂寞亘古唯新。不论是登高而望,还是独自就寝,重重心事、满怀愁绪,无处倾诉,没有援手——王粲笔下的“草露沾我衣”,写尽了征夫流离不安、迟暮无力、孤立无援、无依无助的怅惘心境。而“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等诗句,早已透露给我们陶渊明那种人生如寄、迷茫漂泊的复杂心境。归园田居意味着陶渊明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一份“道狭草木长”的全然未知的命运,做出这个抉择之后,他除了“少无适俗愿”之外,全无凭仗,他的孤立无援,较之王粲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无声无息地死去的危险倒是一直近在眼前。由荒野露浓想到王粲的《从军诗》,在四顾茫茫中咀嚼异代而相近的心事命运,当然会激起他的万千感慨。
从《昭明文选》查阅王粲之诗时,笔者注意到李善为“草露沾我衣”一句所做的注解“《说苑》曰:孺子不觉露之沾衣。”即使是只言片语,这样的线索也不应该轻易放弃。几经查找,终于在刘向《说苑·正谏》篇找到这句话的此处,竟然发现它大有來头: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原来就是这位吴国孺子站在后院里“露沾其衣”观察了三天的“发现”。他正是以这个发现为寓言,巧妙地劝阻了跋扈而好战的吴王。“露沾其衣”是劝谏前大有深意的一个“准备动作”。再想想看,无论是王粲被裹挟其中的魏蜀吴三国混战,还是陶渊明目睹的桓玄篡晋——刘裕讨伐桓玄——刘宋代晋,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又相去几何呢。作为曹操侍从的王粲,以“草露沾我衣”暗寓着对和平的渴望,而身份更卑微、处境更偏远的陶渊明,只能孤身一人,独立在暗夜中,为抵住时代的洪流,做着自己的努力。
经由古直、李善等前贤的指点,我们在“夕露沾我衣”之上发现由陶渊明上溯至王粲再追溯到《说苑》的这条“以个人之力向时代混乱劝谏”的思想线索。但是,我们却也进一步辨明这条线索不像陶渊明和杨恽之间存在“南山”“种豆”“荒秽”等多个契合点。最直接的问题在于王粲《从军诗》第三首写的是非常典型的秋景:“蟋蟀夹岸鸣”句下李善注引《毛诗》曰:七月在野。郑玄曰:谓蟋蟀也。“恻怆令吾悲”句下李善注引《礼记》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一句话,沾湿王粲衣襟的是“秋露”,而陶渊明为豆苗下地锄草时,显然是在春天。我们当然可以说陶渊明在春景中寄寓秋心,那份面对“道狭草木长”时的怅惘、无力和深深忧愁,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要想完全弄通陶渊明的“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显然在王粲这条线索上信息还不够。说来有趣,大概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日夜里,我竟然做梦时都在自己和自己辩论:“夕露沾我衣到底是什么意思?都下地干活了,还怕露珠打湿衣服吗?陶渊明真的这么矫情?”第二天一早实在忍不住,就在微信上求教国内第一位经典文化教育专业的博士选臣兄。也把王粲的《从军诗》呈给了他。熟读五经典籍的他,平实地回复我:“看到露,我首先是想到《诗经》里很多,《行露》《野有蔓草》《蒹葭》等。”
真可谓一言惊醒梦中人!我即刻找来《诗经》,在《诗经·召南·行露》一开篇就稳稳地站着这样十二个字: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对照马持盈《诗经今注今译》里的翻译可供我们了解诗句的字面意义:路上的露水很是湿潮,人们为什么不在早晚的时候走路呢,就是因为路上的露水太湿之故。
露水沾衣并不是陶渊明一个人的烦恼,而是出自《诗经》具有特定意义指向的典故。回到以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疏为主干的汉唐诗经注疏传统,尽可能地抵近陶渊明的知识视野,我们一步步确认:
照毛公的阐释,在《诗经·召南》中紧随赞美召公的名篇《甘棠》而来的《行露》一诗正是召公在甘棠树下处理的一起具体案件:“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强暴之男”试图沿用商朝末年以蛮力来粗暴抢亲逼婚,而受到周礼教化的“贞女”则机智勇敢地予以反抗,直接到召公面前以诗陈情,坚贞自持。
“厌浥行露”三句是贞女借口道上路大,委婉拒绝“强暴之男”的托词。照郑玄的笺注:“厌浥然湿,道中始有露,谓二月中嫁娶时也。言我岂不知当早夜成婚礼与?谓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强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时,礼不足而强来,不度时之可否,故云然。”因道上多露而拒婚的潜台词是“多露之时”已经是“三月、四月之中”,远不是符合礼法的结婚吉时“婚用仲春之月”,这场求婚“既失时而礼不足,故贞女不从”。
在自我贞志与外力强暴之间,横亘着微观和宏观两种“时势”的纠结,这种纠结又恰恰启动了《行露》的意义生产。贞女拒绝“强暴之男”的原因是“行露”濡己之时,野蛮粗暴的男人来迎亲“失时”“违礼”。而贞女反抗强暴、保全贞志得益于商亡周兴的宏大时代背景,旧日的衰微混乱正在逐渐隐退,全新的礼乐教化文明秩序逐渐建立,而这位不愿意行露濡己的贞女,既是礼教文明的受益者,又是它的推动者。
综上,从微观时序来看,关于陶渊明的“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用典指向在王粲一脉那里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在《诗经·行露》这里可以获得充分的对照,首先我们可以明确二者同样发生在春末夏初的早晚时分。然而,紧随而至的问题是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事选择看起来却大不相同——《召南·行露》里的“贞女”拒绝被露水沾湿衣裳,而同样的季节、同样的时段,陶渊明却在草木滋长的狭窄乡道上坚定地沾露而行,走向田野,走回居所。
这种行动表现上的不同,根源在于宏观历史境遇的天壤之别。同样是面对“易代之际”这种颠覆命运、撞击灵魂的非常事变,但陶渊明却绝难把刘宋代晋与商亡周兴等而观之,他看到的不是历史文化的进步,而是混乱血腥的加倍堕落。陶渊明的整个青壮年时期,尽管前有桓温专权、后有孝武帝“溺于酒色”,但毕竟“名贤间出,旧德斯在”:“谢安可以镇雅俗,(王)彪之足以正纪纲,桓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断军事。”(《晋书·帝纪第九》)而他后半生亲眼见到的代晋而立的刘宋王朝呢,仅用钱穆《国史大纲》中的一个统计数据就可以窥见全豹:刘宋一朝前后共八帝,国祚仅六十年,“凡四世,六十六男。骨肉相残,无一寿考令终(长寿善终)者。”陶渊明对王谢名士的遗风雅韵是赞赏倾慕的,对刘宋王朝的残暴是洞若观火的,直接的例证莫如其长诗《述酒》。汤汉、李公焕、逯钦立等古今陶诗注者公认这首诗暗写的是刘裕篡晋这段历史。在这首诗里,陶渊明一开篇就以“重黎照南陆,鸣鸟声相闻”,深深缅怀东晋开国以来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士族名臣们风流荟萃、安定社稷的动人往事。隔了几句他又用“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来写自己身处末世,人物凋零、回天无力的深痛伤心。而与他同代的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专门记录的一个细节可以做一个意味深长的旁证:自从刘裕的王业渐渐兴隆之后,陶渊明不再愿意出仕,他所写的文章都注明创作的年月,在义熙年间,他写的是晋朝年号,而在刘宋王朝建立后,他不再题写年号,直接用“甲子”来纪年。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经典作品是最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是唯一没有腐朽的神谕。”陶渊明自陈:“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詩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陶渊明对《诗经》十分熟悉、无比亲切,《诗经》直接奠基在他的思想话语和价值信仰之中。走在“道狭草木长”的田间小路上,“厌浥行露”如同那么远又这么近的一道“神谕”始终萦绕在陶渊明心头,他对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自然非常敏感。“行露”在他的心田、笔端都不是单向度地袭用着的“典故”,而是强烈的鉴照、尖锐的拷问、往复的“告解”——在陶渊明所写的“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与《诗经·召南·行露》之间构造着一种超越时空的“互文性”关系。
互文性是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莉斯蒂娃最早提出的术语。她认为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他文本,而必然卷入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她以“互文性”为全新坐标系,去发现“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的相互交汇与中和”,以此来解放文本的“生产力”。借用美国批评家费拉尔的解释:“来自文本各种网络的这种语义元素超越文本而指向构成其历史记忆的其他文本,将现时的话语刻入它自身辩证地联系着的社会和历史的连续统一体中。”
具体到陶渊明的“夕露沾我衣”,他近乎故意地把“露水沾衣”从纸上隐喻坐实为农事之余确实发生的事件,并且迎头去冲撞寓意非常明确的经典训诂,大大咧咧地直言“衣沾不足惜”。他不惜用自污自嘲的方式,突破魏晋名士“垂长衣,谈清言”的普遍形象,把人们的关注点引向更强烈的对比,更深刻的反讽。《诗经·召南·行露》折射了历史文化精神进步的理想景象,而陶渊明面对的则是越来越黯淡腌臜的堕落现实。儒家理想中的社会公义杳不可寻,而恪守儒学的陶渊明只能用反讽经典的方式表达对当下时势的无比痛心,在这反讽中,他委婉但不失庄严地呼唤着历史典则的警示和匡正作用,经典理念成为混乱现实的尖锐拷问,坚贞精神成为独立君子的不屈操守,发端于历史文化深处的悲愤,具有压抑而激越的惊人力量。
安妮·艾尔诺在《悠悠岁月》里写道:“在饥饿和恐惧的共同背景下,一切都按照‘我们’和‘人们’的方式来讲述。”理念与现实之间尖锐的巨大冲突,注定了陶渊明对待其当下历史,绝不是默然忍受,也不只旁观见证,他必得深切承受,他要把心力凝成雕刻的力量,在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间,坚持写自己的诗。诗人面向经典倾诉情感、深刻共鸣,把精神挣扎转化为向古人进行的多轮“告解”。陶渊明是在向着永恒发问:当整个世界的光热被权力的黑洞吞噬殆尽之时,横逆时代的孤勇者,以理想之舟,颠簸在天风海浪跌宕起伏的时运激流之中,到底可以希望什么,又到底能够葆有什么?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时事艰难,陶渊明在逼仄的言说和生存环境中,很难明白显豁地说出全部心事。完美的耦合“所见”与“所思”,“不谴是非”,温和自嘲,大概是他找到的既与世俗相处,又不改内心贞白的方式。终于,我们也抵近了“衣沾不足惜”最深刻的旨趣:在时势变迁面前,如何坚守人格这个根本问题。
但使愿无违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正是一个人怎样看待自己,决定了他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为了坚守人格和志愿,陶渊明决然走向那条独属于自己的路,丝毫不管什么草木蔓发,无惧什么道路狭长。是的,这条路,是陶渊明给自己选定的。“道狭草木长”的意象在《归去来兮辞》里会以更用情用力的笔调再次出现,而如果把我们的生命历程作为读懂古人经典的必要准备时,成年、老去所有的龌龊烦忧也便有了唯然如是的亲在意义。譬如,十年前读《归去来兮辞》,艳羡的是“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适意自得。今天,猛然觉得“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里边那最简单的一个“就”字,把性灵渐渐萎绝的过程写得那样惊心,而“犹”把自己的不甘和挣扎,写得那样坚决。
陶渊明秉持本愿,做了时代的孤勇逆行者。在刘宋代晋过程中,武夫出身的宋武帝刘裕为了巩固权力,争取合法性,下了一番“贯叙门次,显擢才能”的功夫,在这波统合士族、礼辟名士的政治操作中,隐居不仕的隐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减少。当时谢灵运给人写信说:
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
古人措辞中的传情达意,很容易被白话译文稀释甚至遗漏,所以要想真的理解古人,非得在原文上多下点耐心、细心的功夫不可。细读谢灵运这段信笺,许多字的落笔都可谓精警无比。第一句中的“既”描述那种既成事实的状态,紧跟着用“并”字来形容这帮名为隐居实则住着“观景别墅”的高级“隐士”们扎堆“度假”的盛况。这样一群“挂名隐士”自然架不住刘宋王朝的招引。他们本来就“慕荣”而不愿“幽栖”,他们所慕之“荣”包含着“荣誉声名”和“荣华富贵”以及名利之间勾兑变现的复杂算计,是很难被一句白话译文概括的。“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倒也把这帮排队下山的“隐士们”曲学阿世、晚节不保的丑恶嘴脸骂得酣畅淋漓。谢灵运和陶渊明一样,都称身处其中的时代是没落的“季世”,陶渊明曾心甘情愿地自陈:“我实幽居客,无复东西缘”——是的,谢灵运和陶渊明这位真正的“幽居者”缘吝一面、不曾相识。陶渊明倒是反复见识身边的熟人,和新朝之间眉来眼去,拉拉扯扯。萧统作《陶渊明传》时还专门介绍陶诗《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背后的一段公案:当时同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有一位周续之先生。这位周先生是大儒范宁的得意门生,隐居时很是卖力,为了克制身体与外物的“余累”,甚至“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就是这样“著名隐士”,一旦刘裕稳定掌权后,就欣然应邀出山,在江州城里为杀人如麻的一介武夫刺史檀韶讲授并校抄《礼记》,在无礼的时代替非礼暴徒装点门面,这难道不是对《礼记》本身的最大侮辱吗?陶渊明专门写诗《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反复规劝周续之等人不要牺牲原则逢迎权势,“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用对比强烈的事实点醒,用徒劳无功的结局预警,可谓掏心掏肺。周续之呢,却如蚁附膻、乐此不疲,并且之后一再出山入朝,先是在建康安乐寺向刘裕的世子“讲礼”,后来更是住进刘裕专门为他修建的东郭学馆宣讲儒学。刘裕在弑帝篡权之余,亲自“乘舆降幸”,来“问续之《礼记》”……大概是这样的事见多了,老陶后来干脆“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乐得跟这号名士老死不相往来。要知道,陶渊明早年曾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一般认为其与刘裕共事过不短时间,对刘裕的为人底细一清二楚。而这份洞见是周续之们所不具备的,刘裕和他的团队对着这些招揽来的名士们,摆出的是一副刻意包装过的形象。比如说刘裕写字“素拙”,丑到拉低“宣彼四远”的外宣和统战工作效果,他的首席谋士刘穆之一再提醒,他却懒于也确实难于临摹钟王小楷把字写好。刘穆之真是个人才,生生替刘裕想出来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书法小妙招,既然刘裕写不出一手标准的好字,咱索性把这个好字的“标准”给它打破,刘穆之带着刘裕“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传统意义上的书法评判标准就用不上了,刘裕在纸面上同他在政坛上一样,依仗“其势”,让人哑口无声。恰可对照的是,刘裕选定周续之来办学校、讲礼记,大大咧咧地夸奖他“心无偏吝,真高士也”——刘宋集团官方认定的“高士”首先必须不偏激、很识相。并且,跟随着刘袼这样的独裁者,就算是时时小心揣摩、处处贴心逢迎,也不会保证你得到“寿考令终”。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刘裕出兵北伐一举夺回了洛阳,积累了足够的军功,按照魏晋以来军头篡权的常规戏码,这时候晋朝的傀儡皇帝会在或明或暗的提示下,授予刘裕“九锡”大礼,让他的权力无限逼近皇权。而替刘裕在京留守、掌控朝局的刘穆之在这件事上的反应却比刘裕的勃勃野心慢了半拍,以至于刘裕都等不及了,索性从洛阳前线派人回建康,直接向朝廷要求“九锡”。史书没有记载刘裕派回来的使者和在关键时刻没有紧跟领导意图的刘穆之是怎么交代的,反正結果是刘穆之“愧惧,发病遂卒”。而这个“愧惧”的病因只能是刘裕的强横粗暴、猜忌残忍。傻傻的周续之“尽室俱下”,替刘裕在东郭学馆宣讲《礼记》的时间正在刘穆之“愧惧”病亡之后。《宋书》本传没有说周续之感没感受到政治中心的高压,只写到可怜的周续之尽管饱受“风痹”病痛折磨,却一直讲学讲到“不复堪讲”的程度,移居钟山不久病亡,殁年四十七岁。——从来不随着时尚迎风起舞的陶渊明,老老实实地在南山脚下种豆、锄草,想起杨恽和他的《报孙会宗书》,很可能会想到给杨恽带来杀身之祸的那句“县官(皇帝)不足为尽力”,也可能会把其最后一句送给周续之们:“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这样的盛世如你们所愿,你们好好干、努力干、拼命干,就不用跟我白费口舌了……
陶渊明的政治不合作,不只是针对一时、一君,而是面对整个君主专制政体不合作。首先,陶渊明勇于跳出王朝史观,在《读史述九章》等以诗歌形式完成的自主历史叙述中表彰那些对王朝历史叙事“唱反调的人”。《读史述九章》第一首写伯夷叔齐。他一起笔就是绝大的对照——“天人革命,绝景穷居。”——上句出自《周易·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商汤灭夏和周武灭商号称“上顺天命,下应人心”,陶渊明故意在这样歌颂王朝更迭的经典论述后面,紧接着来了一个神反转“绝景穷居”,伯夷叔齐从这样的“盛世”抽身而去,选择避世幽居。陶渊明所缅怀的伯夷叔齐的“采薇高歌”唱的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戳穿了王朝更迭顺天应人的谎话,揭开专制统治者“以暴易暴”的老底。诗的最后化用《孟子·万章下》的名句直言自己重述伯夷叔齐事迹的目的是“贞风凌俗,爰感懦夫”——鼓舞坚贞自守、凌越世俗的道德勇气!《读史述九章》中的《鲁二生》写道:“介介若人,特为贞夫。德不百年,污我诗书。逝然不顾,被褐幽居。”王朝历史用略带揶揄的口气,记下鲁地两位无名书生对叔孙通的拒绝,本意是反衬叔孙通的识时务善变通,通过文饰皇权而成为“大汉儒宗”,而陶渊明却把历史正义的天平拨回到“鲁二生”这边,盛赞他们以决绝不屈的个人选择,保护了历史文化精神的高贵和自我人格的清白。这些王朝历史叙事的失语者、逆行者,重新在陶渊明诗歌世界的中心发出自己的心声。田晓菲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既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也代表了历史上具体个人的心声,很多诗创作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性场合,读诗是直接聆听这些个人在具体特定的社会场合发出的声音,因此,这些诗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叙事,而且,它们不是大叙事,而是众多的个人小叙事,弥足珍贵。”陶渊明正是通过“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把这些主动选择幽居到历史聚光灯之外的高尚之士表彰出来。
在汉末魏晋六朝这段“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愿无违”究竟如何实现?陶渊明对自己一败涂地的现实生活无比清醒,他在《闲情赋》里直接说:“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历史舞台的中央终究是刘裕他们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式无君无长、自给自足的理想生活只存在于“桃花源”之中。“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在艰难时世,无权无势的诗人保全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无比奢侈,无比艰难。而“但使愿无违”的真正发力点在于既是愿望也是行动的“使”上——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做,是尽力去做了才有希望。以良知抵御时代,用希望点亮暗夜,陶渊明用诗歌替历史的失语者们发声的过程,其实也是自我求证、自我实现的过程。博尔赫斯在谈到卡夫卡时曾说,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创造着他自己的前辈。这一点在陶渊明身上同样非常明显。无论是他直接述评的伯夷叔齐、张长公,还是互文对话中的杨恽、王粲,都是陶渊明默默形成自己坚不可摧的精神信念的鼓舞者、参与者——“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民诗人陶渊明的精神抱负,在诗歌怀古与田园生活中同时展开,他的不屈尊严胜利在笔端和纸上。
回到那个草长、露浓的早晨,和陶渊明一起“晨兴理荒秽”——正如梭罗《瓦尔登湖》中所言“黎明使我们回到了英雄时代”,诗人满腹英雄豪情干着最普通的农活。他所走过的所有路,都是为了认识此刻——“什么也不能阻挡一个诗人,他的动机是纯粹的爱”,那份执着,那份坚守,那种对追求理想的信念百折不挠,指引他在南山下本着心灵经验写出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