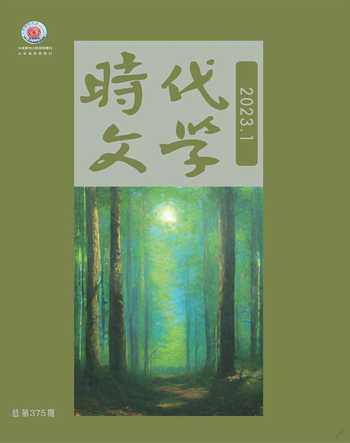私人博物馆
李达伟
1
图书馆和博物馆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有成千上万的杰作。这种巨大的财富挑动着我们的野心。
——【美】索尔·贝娄《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博物馆在图书馆附近。图书馆和博物馆适合建在相近的地方,它们里面都放了一些杰作,这些杰作会影响一些人的人生与命运,它们会让我们清醒和自卑。我在图书馆里借阅了一本关于博物馆的书,然后进入博物馆。许多人进了博物馆,却忽略了一些杰作。我在不知不觉间,也忽略了很多杰作。有时还会遇到尴尬的情形,误以为是杰作的实际却是平庸之作。在图书馆和博物馆,才发现分辨和判断能力已经滚落于幽暗的角落,自己已经无力把它们拾起来了。
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所藏之物,有很多已经被时间证明是杰作,特别是博物馆里的许多文物,而图书馆里,多少鱼龙混杂,其中有好些是在当下出版业异常发达的现实中产生的平庸之作。在图书馆里,我们会有“什么是杰作”的疑问。我出现在图书馆,没多少人。我出现在博物馆,同样人影稀少。空落无人,可能是一种常态,也可能是我出现时恰巧是这样。有几次,我看到一些孩子出现在博物馆。那几次,我是来接女儿的。最多的竟是小孩,我的心绪莫名复杂。最近一次,女儿刚走出博物馆,就跟我说等有时间再带她去博物馆里看看,其中一个展馆她还没看完。听到女儿表达出这样的渴望时,我感动不已,那同样是莫名的感动。女儿其实还什么都不懂,我让她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跟我说一下,她说基本都忘了。她不断出现在博物馆,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记住什么吗?每次我出现在博物馆接女儿时,她都异常兴奋,那是因为她刚参观完博物馆,意犹未尽。那些孩子被大人陆续接走后,博物馆里就没多少人了。
出现在博物馆中的一些人,沉浸于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中。如果一个人出现在博物馆里只是为了看那些残碑,这种可能很小,只有很少人会有那种渴求。一些很少的研究古碑的人出现。那些散落于苍山中的古名碑,多被移到了博物馆的碑林里。那个人惊诧不已,他不曾想过,他想到过的是在苍山中行走,在某处遇见一块珍贵的古碑,然后在别处又见到一块。只有不断行走,才会遇见那些古碑。在每块古碑前停下,让时间慢下来,再次进入时间缓慢的那个维度。此时,他面对的那些古碑,有好些是他在山野中到处寻找却找不到的,他顿时手足无措,竟迷失在了碑林中。我有意过来看看碑林。一些人对之熟视无睹,人们似乎并不知道什么是杰作,或者杰作对我们情感的介入正变得式微,割裂开来,与之无关,杰作消隐了光芒。图书馆的那些杰作,你有时间就可翻看触摸,博物馆的那些杰作,往往禁止触摸,禁止拍照,你只能付诸眼付之于心。
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有序的空间,按时间排序,仔细聆听,时间的声音一直回荡着,在内心产生一些回响,不同的人将遇见不同的声音,世界将会借助这些人之口,喧闹起来。只是我们所希望的喧闹,暂时并没有如愿发生,依然只是很少的人,有时就只是图书管理员或文物管理员,他们沉默着。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就在百无聊赖的孤寂中完成和重复。他们依然重要,他们会对少数人的人生产生影响,与那些杰作的作用相似。我曾被小城图书管理员影响着。那时我们更多地不是受杰作的影响,而是变杰作旁的人,受那些守着杰作的人影响。
我想起了另一个特殊的图书管理员对一个男孩的影响。男孩和老人所处时代的特殊,让那种影响的产生显得惊心动魄,那是一个喧闹甚于沉默的年代,而老人和男孩之间更多是沉默的,那样的沉默与我和图书馆员之间的沉默很相近。还是有些不同,男孩眼中的老人所受到现实的冲撞与挤压更强烈,老人本应该成为其他的人,但一切男孩希望成为的身份老人都没能拥有,或是老人到那时已经接连失去了一些身份,最终老人成了一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老人管理着那些书籍,没有读者。当一些人陷入狂热与喧闹时,男孩对图书馆的渴望,让男孩与别人不同,男孩成了最独特的那个人,成了出现在老人面前的第一个读者。像老人一样的人很多,他们本应拥有不平凡的人生,他们本应在某些领域做出别人无法替代的成绩。男孩发现了老人的特别。男孩最终成为真正不同的人,甚至拥有了老人本应该拥有的艺术家身份。
我出现在图书馆时,看了看四周,没有人,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其他,若大的图书馆里,没有多少读者。我在面对那个图书管理员时,竟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让我的借书和阅读行为,变得不那么普通。我和男孩都有着对于阅读的狂热感。老人用他的人生与命运影响着男孩。图书管理员让我直接来到图书面前,感受着一排又一排图书的压迫,由此对我产生影响。
我与图书管理员并不熟悉,对他的人生与命运的认识几近空白,我甚至连他跟我说的是普通话还是白族话都已经想不起来了。他的人生一直就是个谜。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来自他的影响一直延续着。老人对于男孩的影响也持续了将近一生。少年与老年,这是年龄差。少年与老年的友谊,在某些时刻,似乎更加牢固。不知道博物馆里有没有类似少年与老年这样的友谊。时间并不能把一些东西从精神与身体里剔除,反而会把一些东西加深,会刻入骨头,会融到血液中。如果有人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熟悉的话,他们一眼就能看到我与他相似的东西。我们的沉默,我们的安静,我们会在一些时间里沉浸于阅读与思考。
博物館管理员,同样也可以以他们的方式对一些人产生影响,他们引导人进入博物馆,对人们进行美的启蒙,让人认识过往的时间。我的女儿不断出现在博物馆,无疑也在美上受到了启蒙。女儿发现了一些美,她说在一个展馆里看到了很多民族服饰,各种各样的色彩,那些色彩会出现在女儿的梦中。文物管理员对文物产生影响,那些文物又反过来对他们产生影响。文物在那间房子里面,随意地摆放着。那时,它们还未被放到博物馆里。那些被修补一新的文物,并没有那种长时间不见天日之感。它们对于文物修复者的意义与考古学家的意义不一样。他们在有关那些文物的谈话中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文物修复者的注意力放在了文物的残损上,考古学家把注意力放在了文物背后的时间上,用文物来佐证时间,他们更看重的是时间的长度与厚度。其中一个指了指其中一个文物,这是新石器时代。又指着另外的文物,又是其他的时代。他们不断在强调时间。我想打断他们,我看重的是艺术感。我没有任何要打断他们的理由。他们同样看重它们的艺术感,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别的艺术风格,他们用风格来反证文物出现的时代。除非是一些赝品,首先要证明它们不是赝品。赝品有时会迷惑人,但迷惑不了考古学家,他们无法忍受赝品的存在。当然这也是悖论,一些考古学者同样会把一些真品忽略,他们将面对众多的迷雾森林。博物馆中的那些仿品,可以被定义为赝品吗?仿制品存在的意义与赝品是不同的。当然,真实同样是文物艺术价值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博物馆中工作的人,很快就发现我的外行。我们的理解可能最终无法交汇,一直都将在各自的空间平行着,貌似已经很近,实际又很远。
有一段时间,图书馆被拆除重建。重建的过程很长,那段时间,我们只能在小城博物馆里见到图书馆的影子,以照片的形式。小城博物馆变得更加芜杂,里面安放着我们想到或想不到的旧物。一些书被堆放在博物馆。写着“图书馆”字样的牌匾被人收起来,也放入博物馆。那时我打着一把破烂的雨伞,遮雨效果不是很好,我不是有意拿那样一把雨伞,这无心之举让我与那个环境之间,有了一种奇妙又感伤的契合。有时,一座图书馆被拆,总会让人有一些复杂情绪,会莫名伤感。当我们意识到图书馆必然会被重建时,那种沉重的感伤又弱化了一些。
图书馆的搬迁,发生在记忆的不久以前。图书馆成为废墟,发生在记忆的很久以前。时间在这里呈现出某些诡异的特质,会让一些记忆变得很清晰,又会让一些记忆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人去关注图书馆的重建,人们纷纷被图书馆以外的世界所吸引。后来那里重新建起了别的建筑,但建筑的用途是住人,不是用来装图书的,不是用来装思想的,里面最多只能是住着为数不多的思想者。后来图书馆被重建,只是一些思想早已发霉,早已沉入地底。
在图书馆管理员的沉默下,我至少是一个正常的阅读者。一些东西被重建,或是新建。在图书馆原来所在的位置上,重新建起了一个博物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方志馆。方志馆与博物馆是不同的,它们在一些方面又很相似。方志馆旁建了一个阅览室,里面有一些孩子在翻阅图书。我带着年幼的女儿进入其中,她随意翻了翻就拉着我走出了阅览室,她要在阅览室外面喧闹宽敞的广场里玩耍。
2
博物馆这个空间是隔绝外界的、不受时间影响的、精致的,也是脱离语境的。它是一处杂交了动物园、避难所和安全区的特质的场所。
——【美】乔舒亚·斯珀林《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木雕。女性。雕刻的各种。女性雕刻者的存在,其实早已经很正常,只是我忍不住还是要强调她们的存在。这样的强调里,并没有任何偏见。我在进入那个空间时,所有的雕刻者都还没有出现。面对那些雕刻作品,我无法分辨出哪些是男雕刻者的作品,哪些是女雕刻者的作品。雕刻技艺的高低,与性别没有任何联系。在那个木雕博物馆里,遇到了正在练习弹唱三弦的男孩和女孩。一开始,我还以为走错路了。当看到其中一件木雕作品雕刻的就是类似的场景时,我开始意识到男孩和女孩就应该出现在那里。里面摆放着很多在这之前我们不曾见到过的木雕作品,与我们对于木雕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那完全是对自己固有思维的冲击,也是一次很重要的打破。是否真打破了?我不能肯定,但在里面确实感受到了强烈的冲撞感。在这之前,对于木雕作品,我往往会先入为主,以为木雕作品总是单一的,毕竟走在一个木雕的建筑群里,里面有很多东西大同小异。在这个木雕博物馆里,并不如此。
3
这之后,我在《旅行者》之外有机会在一个博物馆里看到了《时间老人》。从一个棚铺里闪现出一位老人,他挥起镰刀又让它落下,动作缓慢,钟表的齿轮旧得生了锈,在镰刀的起落中有涌动,有静止,有反复,时钟不再指示我们通常对时间的概念。而此刻的我,紧贴着玻璃窗,如痴如醉,我无法给出另一种假设。
——【法】伊夫·博纳富瓦《隐匿的国度》
昔日的灰尘在那个空间里已经具有黏性,沾染在那些墙体与旧物上,然后凝固,像画家画一幅画时的用色,色彩落下,劣质的颜料慢慢干结。那依然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私人的民间的博物馆,私人博物馆往往无法真正被擦拭一新。有时,如果在房檐或者角落里看到一些蜘蛛网,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我们进入那个博物馆时,门是敞开的,没有人守着那个空间。一定有守着那些东西的人,一开始可能是博物馆的主人亲自守,慢慢他感到疲惫和厌倦,即便自己很喜欢博物馆中那些花了很大气力搜集来的东西;然后是其他人,其他人也慢慢感觉到疲惫。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物件,随意堆放在一起,那是会让心受到挤压的无序。那样的无序与拥挤,也拒绝着一些人的参观。没有人,没有介绍的文字,光线不是很明亮,需要你俯下身子,仔细凝视。你终于看清了是甲马,不是甲马纸,是雕版,你一眼就看到了众多的雕版,你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些图案。你也发现还有一些陌生的图案,那是你在苍山那些村落中行走时未曾遇到的图案。一些甲马纸被焚烧,还有一些甲马纸被贴于门上,它们都是通灵的纸张。那些雕版,出现在那个空间里,也意味着它们已经被弃用,它们的意义都在那个空间被消解。
4
博物馆里有霍尔拜因、霍德勒、埃尔·格列柯和马克斯·恩斯特。长长的廊厅里一片寂静。身处其中,你会明白伟大意味着什么。
——【美】詹姆斯·索特《暮色》
我们看到了旷野的色彩,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都在那个空间里,它们的存在并不矛盾,或是清澈,或是混沌,或是烟雾弥漫,或是落日余晖。一些人影出现在这些色调中,失去了原来的色彩。那些梯田里都是水。梯田成了装那些河流的容器。水流似乎就是从地底下涌出来,成为一面又一面支离破碎的镜子,裂纹是那些黑色的田埂。人影暂时不在里面。人影开始出现,水位下降了一些,人们开始插秧,在田里感受着凉风习习。那时的色彩是绿色。绿色中夹杂着人影的各种色调,粉色出现。女兒说她最喜欢粉红色,她问我有没有粉红色的稻田,我一开始肯定地说没有。当某天看到那些五彩的稻田、七彩的油菜田时,我才意识到真有粉红色的稻田,只是在那个空间里没有而已。稻田开始黄了,风一吹,稻浪翻滚,蚂蚱在田里扑腾,人影远远看着这样的场景,那时的色彩只是单一的金黄。我与其中一个人影重叠在一起。我们都看到了童话的色彩。我问女儿,童话应该是什么色彩?她说应该是粉红色的。我们每个人心中关于童话的色彩都是不一样的。冬天同样没有缺席,冬天并不是在那些田里落下一场雪,只剩下空,田里没有水的影子,只剩干涸的迹象,甚至出现一些裂痕。如果在现实中的冬天出现在那里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担忧。我们看到了四季有序的延续,我们看到了时间在静止中的有序变化。在那样的变化里,焦虑会消失,我们还会涌起一些对未来的希望。那时,我们会谈论美与希望。大家开始窃窃私语,都是关于美与希望的。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被长时间谈论美与希望所迷惑,或者是所麻痹。我们也确实感觉到那个空间里所呈现出来的美。那是摄影,那是瞬时的捕捉,对于光与影的要求很高。一些人开始激烈争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摄影?很明显,一些摄影作品有着太过明显和失真的后期制作,许多色彩都是被制作的,似乎他们在那样争论这样的想法时,总觉得现实中的自然将无法拥有那样的色彩。当我跟他们说这样的想法时,他们立刻反驳我,我误解了他们,他们所要强调的是色彩的自然与自然的色彩。
5
每天早晨,一只胳臂底下夹着个画夹,另一只胳臂底下夹着个绰号叫“小马”的条凳,散散漫漫地走进博物馆;黄昏时分,而这个时候经常早早光临博物馆内部,他们又带着各自的重负回去。
——【美】约翰·厄普代克《鸽羽》
各种工匠的影子出现在那里。工匠的作品。那时,最重要的应该是工匠的作品。工匠重要吗?工匠同样很重要。工匠让自己隐于无名。即便在那个博物馆里,有着工匠的名字,但有名与无名都差不多。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工匠的身份和信息都很模糊的作品。
唢呐出现,各种常见的唢呐在橱窗里被展示着,没有唢呐手的存在,它们只是唢呐。唢呐上面似乎覆盖着一些金黄的色泽。工匠隐身,唢呐手也隐身。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制作唢呐的乡村艺人了,那些唢呐往往已经过几代人的传承,沾染着很多人的指纹。唢呐手的话,还能见得到。我刚刚参加了一场婚礼,唢呐手出现了,那是一个唢呐手。在童年记忆中,唢呐手会有两个。一个和两个,是不同的。我还参加了一次葬礼,没有唢呐手,也就没有人吹奏那些过山调过水调了。当唢呐手缺席,当工匠缺席,那些唢呐成了一个唢呐,它们在我眼里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它们只是摆放在那里的物,让人们认识唢呐的种类,还让人在唢呐上找到一种情感的寄托。静默的唢呐放在那里,我有意数着它们的数量,“16”。那时的数字可能会有一些隐喻意义,或者人们在时光与那个世界中找到的唢呐就有那么多。一些唢呐之间的差别不大,有时区别只是铜锈的多与少而已。
当唢呐手开始吹奏唢呐时,我们往往会被唢呐悲凉的一面吸引,我们只是听出了无尽的感伤。命运感的东西,唢呐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即便是一场婚礼上的唢呐里,都有着无尽的分离与悲凉,其中有那么几个调子把人从悲伤的境地拖出来,为了不让人在感伤中沉陷得更深。葬礼上的唢呐声,似乎只剩下忧伤。一些唢呐手说,并不只是有忧伤,还有要让人超脱的东西。只是面对着唢呐声,面对着两腮鼓胀的唢呐手时,我们似乎只是在里面听到了死亡的伤感的沉重与声嘶力竭。我参加了一些婚礼,也参加了一些葬礼,我无法说出他们所使用的唢呐是什么样子,我只是被唢呐声吸引,并被唢呐声感染,我也开始变得莫名忧伤了。唢呐声,还有人的抽泣声交杂后,我也会情不自禁地落泪。
面对那些已经失去最大功用的被闲置的唢呐时,内心百感交集。我说不清楚,与我们一起出现在博物馆里的人中,是否有一些就是曾经的唢呐手。能肯定的是,大部分都只是与我一样的人,我们只是听过一些唢呐调,只是见过一些唢呐手,却对与唢呐有关的很多东西孤陋寡闻。唢呐旁边有一些文字介绍,给人的印象却并不深刻。如果是一个唢呐手把自己的唢呐拿出来,吹奏一会儿,又停顿一会儿,耐心地讲解的话,印象和感觉又将是完全不同的。我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有一次,我为了向一个年轻的唢呐手了解一些东西,与他饮得酩酊大醉,当唢呐手深情地讲述与唢呐有关的东西,甚至讲述自己作为一个唢呐手的半生时,我早已倒在火塘边呼呼大睡。
当想起一些唢呐手时,那些唢呐开始变得不一样。它们开始不再静默,沉睡的音符纷纷在那个世界苏醒,一些唢呐的调子开始在那个空间如飞鸟如河流,那个空间就是它们的整个世界。世界的声音,开始变得丰富起来,我分辨出了那些曲子之间的细微差别。那些唢呐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6
爱的姿态,这座甜蜜的博物馆,这条以烟雾为像的画廊。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南方高速》
幻想博物馆。不是命名为“幻想博物馆”,也不是幻想出来的博物馆。那是现实中有的博物馆,当我们看到里面展示的东西,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充满了想象意味的博物馆。一进入其中,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在提醒我们,那是想象之物。博物馆的主题便是“幻想”,那是我在里面时所认为应该是的主题。有太多的物,在这之前不曾被我们认真想象过,当想象力变得无比贫瘠时,那些物的出现会让我们觉得很诧异。用那么多的东西,来暗示我们想象力的重要。有好些就是时间长河中的幻想之物。时间长河中的壁画,被讲述的传说以壁画的形式在那里展现,还有一些画家画的像,一切看起来都不再是现实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异常鲜明。那些幻想之物,会让人对自己贫瘠的想象力感到沮丧,也会让人思考想象力为何孱弱不堪。我没想到自己竟然进入了这样的博物馆。是在梦境中,抑或是現实中?需要符合幻想的氛围与情境,幽暗的,模糊的。我们看到的是与现实完全不同的轻盈。空间里的那些物,符合我们的一切幻想。我应该是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博物馆。我在现实中到处找寻着这样的博物馆,并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建造着,我还在脑海里想象着,这样的博物馆里应该放一些什么样的物,才能真正表达那个主题。其实我不用困扰于此。当真正出现在博物馆时,有很多东西就是幻想的产物。我跟女儿说起想象力的重要,那是她在白纸上涂抹时,我竟然会无端忧虑,担心她的想象力会一点一点地从生活中被动地消失。我需要带女儿进入这个幻想博物馆之中。我们至少在里面看到了想象力的飞升。远方的声音。雕刻的主题是梦境,一些长有翅翼之人枕于石柱上安然入睡,这块残损的壁画,也应该被放入以“幻想”作为主题的博物馆中,画本身就充满幻想意味,他们的梦境也将无限接近幻想这一国度。
7
在这次演出的第二阶段,也许可以说这家剧院收起某几种特色,把自身变成了一座艺术博物馆——里面只有一幅画的博物馆。
——【美】斯蒂文·米尔豪瑟《危险的大笑》
里面都是一些动物的尸骸骨架。有些动物的身影,只剩下这些没有血肉的骨骼。我们在那个空间里,需要把那些空的部分慢慢填充起来,填充一些血肉,然后加一些毛发,再加一双可以冲破幽暗灯光的眼睛。我们看着那些身形巨大的动物或是正在进化中稍显怪异的身影,时间顷刻间倒退,我们的想象力瞬间恢复。我们可以借助那个有羽翼的动物飞升起来,停在那些只有树可以长到上面的悬崖上。悬崖的缝隙里长了一些树,在风中摇晃着,那是生命的一种在摇晃中的存在,那还像是冥想的轻盈,可以在空中飞着,也可以轻松地落在地上。我习惯了冥想。我们谈到了要让紧绷感偶尔放松的必要。但很多时候,要变得放松,不让思维僵化和狭隘太难了。我们谈到了生命的冥想,谈到了建造精神城堡的重要性,我们也有些颓丧地意识到,又有多少人能建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城堡,我们连塑造一些精神的骨骼都很难。我们还在那里提到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标签,还提到了少数民族作家应该给文学贡献什么,而不是依然给人们一些刻板的印象。在面对着那些空空的骨架时,我们的内心深处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一些东西随着时间悄悄地从中流失了,或者是被吞噬了,一直低着的头颅抬了起来,我们似乎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似乎看到那些骨架纷纷碎裂。那是自己的另外一只耳朵听到的,那是没有被放在这个空间里的尸骸可能的一种结局。这个空间的骨架,似乎坚硬无比,它们的摆放,在时间的作用下,竟没有给人一种易碎感。另外一只眼睛,看到了一些易碎的骨头,看到了那些骨头里的裂纹。在某个梦境中,那些骨头纷纷碎裂,那个空间因为那些骨头的消失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个空空如也的世界,多少人能忍受?那样梦境的出现,与内心的一些担忧有关。
那只老虎的标本,如果消失了,也便意味着高黎贡山中最后一只老虎的彻底消失。我听说了关于高黎贡山中最后一只老虎的说法,被毒死,放在乡间的街市上被人观赏,然后经过处理后出现在了博物馆。毒液并没有影响它的样子,毒液只影响了那个空壳之内的血肉。最真实的情形便是它成了那个博物馆中的标本,与其他标本只剩下骨骼不同,那个标本还有着清晰的毛发,那真是一只老虎。当走出那个博物馆,我只记得那个老虎的标本。似乎那只是放了一个老虎标本的博物馆。如果真的有只有一只老虎标本的博物馆,我们在置身其中时不知道又该是什么心情。标本在那时候的意义,可能就只是说明“一”,可能就只是强调。那时,它又成了在乡间摆放着,我们付五块钱就可以看一下。一只稀有的老虎只值五块钱,一只稀有的老虎标本并不需要钱,当我有了进入那个博物馆的想法并把它付诸行动后,我又猛然意识到那是一次简单的遇见,博物馆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能唤醒自己内心一些微妙的情感,对于失去的唏嘘,对于一些东西失去时会带来的痛苦。我们都知道,那是那座山中最后的老虎。
8
这时我回想起了在博物馆度过的那些严冬的下午,我们四人,我们的对话,我们对于符号煞费苦心的推测,我们的解释,我们的热情。
——【意大利】安东尼奥·塔布齐《安魂曲》
在博物馆中工作的其中一个人(一个人能否代表一个群体?显然不能)。她从旷野中暂时回到了博物馆。我们就在博物馆中进行了一次对话。那是我期待已久的对话。我想从她那里获取在博物馆工作的感受。她面对的都是文物,都是有文物价值的东西,没有文物价值的东西被筛选一遍后,没能真正进入那个空间。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器物,又想起那个修复文物的老人。似乎老人无处不在,老人修复了很多东西。我跟她谈起老人的话,她一定知道他。我们没有谈起那个老人。一个本应该出现在我们对话中的人,一个本应该会让我们的对话抵达另外一个维度的人,竟缺席于我们的对话中。
我问她,为何会选择在博物馆中工作?问题提出的那一瞬间,我便后悔了,这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她说自己学的是考古专业,在博物馆中工作,还算是与专业对口。她在一些时间里,会走出博物馆,把自己放入旷野中。她必然会与那个老人相遇。她将会问那个老人一些问题。她进行挖掘工作时的样子,我很好奇。一开始时,她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个问题似乎要好一些。她说自己在当时并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她也意识到自从热爱考古学那一天起,这是她最好的工作。
为何会喜欢上考古学?是对地理山川河流的热爱,对于世界的好奇,以及幻想主义,考古学里包含着对于世界想象的力。有了在山野间在古道上的田野调查后,你才能真正意识到考古学的迷人。我想跟她说,每次出现在博物馆中,看着那些文物时,我同样也会感觉到考古学的迷人。当她不断诉说考古学的迷人时,我对她的专业与工作表现出了歆羡之意。如果我也拥有这样有关考古学的体验的话,是否会对我的文学经验有一些帮助。我想跟她谈谈考古学和文学之间的联系,但最终我们没有谈论文学,我克制着自己,不再像往常一样一直想谈文学。如果我们真谈论起文学,她一定会说旷野对文学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进入博物馆的同时重返自己的内心,对文学应该同样有意义。现在要谈论的对象是博物馆,是眼前这个看似柔弱、与考古学很难扯上联系的女子。
如果不是在博物馆遇见她,如果不是知道她有很多时间是在做田野调查和考古挖掘工作的话,我们关于她的想象又将是另外一种。我目光中闪过一丝不信任,竟被她捕捉到了。她问我是不是不相信她能胜任那些艰苦的工作。在博物馆里和走出博物馆,是不同的。在博物馆里,一切安静下来,在安静中,她把目光都放在了那些文物上。我知道这仅仅只是她工作的一小部分。在博物馆内,时刻面对那些文物,她成了一个观察者,博物馆成了她进行思维训练和审美训练的场。走出博物馆,涌向自然与废墟。对考古学知识的不甚了解,我只能想象那是一个又一个涌向诗意的过程。
我出现在那些考古现场,人们不断地挖掘着,土层坚硬,人们一寸一寸地往下挖掘,一无所获的沮丧感随时会出现,当然,也会出现一些让人兴奋和激动的时刻。她跟我说起第一次发现一些古老的器物时,她需要让自己的考古学知识和那些器物之间完成互证。她去勘察一条河流,那是古文献中的河流。在真正找到那条河流时,她最强烈的感受便是发现了自我,那是由一条河流带来的对于内部的唤醒,河流缓缓流淌着,落日倾泻在河面上,被河流缓缓拖着往前。我们也出现在了那条河流边,河流的流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望着苍山的方向,苍山上斑驳的雪迹依然很清晰。我想跟她说,我看到了她所看到的,我感受到了她不曾感受到的。与她一样,她也感受到了我不曾感受到的。我们被河流唤醒和濡湿的內部是不同的。
她给了我一些照片。那是博物馆中,被她认真重新标注过的文物,出土的时间与地点、文物的年代与价值等都要被她一一标注和说明,那是一个必须无比精确,也因此无比枯燥的过程,那是作为旁观者所轻易就能感受到的枯燥。她跟我说,作为旁观者的我,也将很难感受到从事那个工作有所获时的激动,那是体现自己价值时才会有的激动。我对她的激动深信不疑。那是一个无比清澈纯净的女子所说的,那是最真实的东西,那是最稀缺的真实。博物馆之外,一些真实已经打碎一地,再也无法被拾掇。
我还要问她什么问题。让我再想想。我竟想不到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在进入博物馆之前,我是想了好些问题,其中有好些问题在我进入博物馆时,便已经有了答案。只有她是未知的,她的存在会让我固有的一些认识发生变化。她的履历很简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这个博物馆里工作。一些文物,就是关于美的表达,工匠不在,在时间作用下,越发释放出斑斓的美。虽然那些工匠不在,但那些美的熏陶会通过物本身来完成。
我们还说起了博物馆同样适合孩子去。孩童的好奇与想象力天然就弥补了博物馆所缺失的一些东西,同时博物馆也会给孩童一些东西,比如对美的感受与狂喜。我在博物馆门口等着五岁的女儿,一群孩子从博物馆里走出来时,他们都很兴奋,那是与在这之前从未见到过的物相遇后的表情。女儿还说里面的一些东西,自己曾经在梦里见到过。博物馆的一些东西,它们只能属于孩童梦境的一部分。当我在进入其中一个博物馆时,我已经不再年轻,我至少已经是一个青年。童年的许多梦境都已经变得淡薄,在与博物馆中的许多东西相遇时,我竟然没有任何似曾相识之感。她说自己会经常再次成为女孩。我也想跟她说,自己在一些时间里,同样想再次成为男孩。我们需要再次成为男孩和女孩,为了能在博物馆里再次感受时间与艺术带给我们的狂喜和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