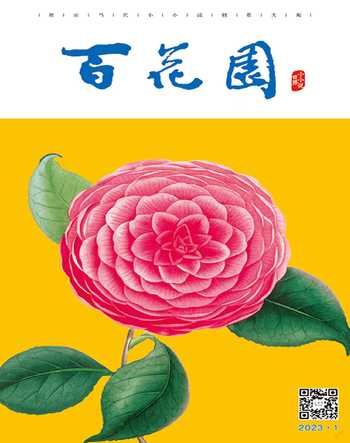杀 驴
李士民

那年的秋霜,要比往年来得早,我爹的眉头,却皱成了一团苦霜。我爹已经下定决心,准备杀了我家的驴子。
对于那头驴子,我爹又爱又恨。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中秋节的时候,大成叔要借俺家的驴子。大成叔是个脸皮薄的人,在俺家门前转悠了好几圈,才敲开了俺家的门。大成叔张了几张嘴,才说出了借驴子那句话。
大成叔不仅是俺家的邻居,还是对門。平日里,我爹待大成叔不薄,大成叔待俺家也厚道。前一段,大成婶上房顶晾晒玉米,摔伤了腿。摔伤腿的大成婶,中秋节想回娘家,于是,大成叔就来我家借驴。
大成叔的话金贵,我爹的话爽利。我爹说:“自家的驴,啥借不借的,牵走就是了。”然后,我爹走进驴屋,专门给驴加草添料。
喂饱了驴,我爹还套好驴车,交给大成叔。大成叔嘴笨,感激的话想了一大筐,脸憋得通红,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只是一个劲儿朝着我爹点头。
大成叔赶着驴车,穿过秋日里透亮的乡间,心里也分外亮堂。
到了沱河桥,驴子站在桥头,不走了。开始,大成叔还以为桥上人多,驴子不敢过呢。等桥上没人了,驴子还是愣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大成叔左赶右催,前呼后喊,驴子像路边的一截木头桩子,没有表情。就算大成叔扬起鞭子抽打驴子,驴子依然像茅坑里的一块石头,又臭又硬。
没办法,大成叔只好赶着驴车回村了,坐在车上的大成婶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我爹的脸上挂不住了,打了驴子三顿,饿了驴子三天。我爹打驴子的时候,恶狠狠地说:“打死你个龟孙!”我爹饿驴子的时候,凶巴巴地说:“饿死你个驴日的!”
让我爹更生气的还在后面。
收了秋,就要犁地了。
那天,鸡还没叫,我爹就起来了,喂饱了驴子,备好了犁子。
沱河堤岸下,有我家的一块田,方方正正的二亩地,是我爹的一块宝,夏天麦子饱满,秋天玉米圆润。每年,我爹都要精耕细作。
家有家邻,地有地邻。我爹赶着驴来到沱河岸边的时候,春生伯已经在地里吆喝牲口了。村里人都知道,春生伯和我家的地挨着。每年,我爹都和春生伯较劲,看谁家的地犁得好,犁得快。比来比去,每年都是春生伯认输。
开始犁地了,我爹把鞭子甩得脆响,把犁子扶得笔直,翻起了一道道泥土,飘散着新鲜的气息。这时候的我爹,就像诗兴大发的诗人,写下了行行优美的句子。
犁地三圈的时候,驴子突然停在地中间,任我爹怎么赶都不干了。摸摸浑身是汗的驴子,看着近处犁地的春生伯,我爹那个急呀,像驴子一样浑身大汗。那时,我爹挥舞着鞭子,使劲地往驴身上抽。抽一下,我爹就心疼一下,可是,我爹也没办法呀。
谁也没想到,那头驴子昂昂几声,扑通一声,卧倒在田沟里,彻底罢工了。我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所以,我爹起了杀驴之心。
听说我爹要杀驴,我娘躲在驴屋里,眼睛都哭肿了。我娘说:“不是驴子不愿意干了,是驴子上年岁了。”
回忆起来,这头驴来我家已经八年了,农忙的时候,驴子拉庄稼,犁地,打场;农闲的时候,套了驴子拉石头;过节的时候,赶了驴车走亲戚。驴子给我家出了多少力,干了多少活儿,我爹算不清了,我娘也记不住了。
平时,我爹是个抠门儿的人,自己不舍得花钱,也不舍得往家里买好吃的,只是,我爹不亏待驴子,最好的大豆留给驴子吃,最好的一间房让驴子住。平时,我爹是个粗心的人,常常穿反了衣服,忘记了生日,只是,我爹照顾驴细心得很,驴吃的草要淘得干净,驴喝的水要烧得温暖,驴吃的料要炒得喷香。
我弟弟两岁那年,我娘为了哄他,往他嘴里塞了一个花生米,哭闹的弟弟就卡住了,憋得满脸青紫。我爹赶紧套了驴车,拉着弟弟到了镇卫生院,医生说:“要是晚来一步,孩子就没命了。”我爹说:“多亏了驴子跑得快。”
这次,驴子却丢尽了我爹的脸,伤透了我爹的心。
杀驴,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爹关严大门,捆牢驴子。
我娘蹲在堂屋门口,一个劲儿地擦鼻子。
我弟弟蒙着被子,把自己包成了一只蚕,像是睡熟了,也许是害怕。
等到下半夜,我爹开始行动。他把驴子的眼睛用毛巾蒙上,红着眼睛说:“你可别怪我,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当我爹拿着一把长长的尖刀,准备杀驴的时候,我弟弟突然从被窝里钻出来,光溜溜地跑到我爹面前说:“爹,你杀了俺吧。”
我爹愣住了。
这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来到了弟弟跟前,抱头痛哭。
我爹决定免驴子一死。
我爹还对我弟弟说:“以后咱们接着好好照顾它,像照顾你爷爷一样。”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