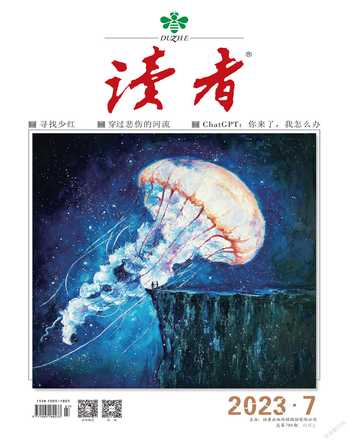寻找少红
张惠雯

一
科学家都说地球气候在变暖,但我觉得冬天越来越冷,今年冬天尤其冷。
那天晚上,爷爷和奶奶说起二爷。我记得二爷上一次到家里来,是我刚考上高中的那个暑假,一晃快三年了。我们也快三年没提起他了。爷爷说,二爷中风了,他们下午刚去医院看过他,二爷的情况不好,话也说不清,嘴歪了。他们去的时候带了一箱牛奶、一箱鸡蛋和一袋水果,但他们担心这些东西最后还是会被二爷的侄儿带走,二爷自己一口也吃不上。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说想去看看二爷。爷爷奶奶齐声反对,说我应该待在家里学习,高三了,不能再浪费时间,况且他们俩已经去看过,这就代表了全家。奶奶说,病房也是姑姑托医院的熟人安排的,他们都去探望过,在二爷出院前他们会再去一趟,这样,我们家的礼数也算尽到了。听起来二爷就要瘫痪了,我很惊讶他们这个时候在乎的还只是“礼数”。我没再说什么,但我还是想去看看二爷。
二爷是爷爷的堂弟,比爷爷小了十几岁。这些年他不怎么来了,但很奇怪,我心里一直把二爷当成这家里的一员,也许是小时候的印象深刻。我记得以前我们家老房子被拆了,爷爷把二爷叫来帮忙,每天早上四五点钟,我们都还在睡觉的时候,二爷就起床干活,一车车地拉砖,把码好的砖从老宅子拉到我们的新房子后面,再把砖卸下来,整整齐齐地码好。
只要我们家有活儿,我爷爷就会叫二爷过来帮忙。二爷喜欢到我们家,来了他闲不住,到处找活儿干。我喜欢看二爷干活儿,因为我也想长大了有那份男人的力气!没活儿可干的时候,他就变得局促,好像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心神不宁地在院子里、屋里进进出出。周末,姑姑们的孩子也都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玩儿,二爷这时候才又自在、快活起来。他在旁边看我们玩儿,也会乐得笑出声。有时看着看着,他突然起身走了,很快又回来,手里提着从食品店买来的冰棍儿、山楂片、虾条,分给我们吃。我们往他脸上、手上贴纸条,在他手臂上画小人儿,他都笑着任由我们捣蛋。
二爷自己没有孩子,奶奶说过,二爷命不好,一辈子没娶上老婆。二爷一生都是靠卖力气生活。他四处打零工,去砖窑给人烧砖,去面粉厂帮人磨面、扛面袋子,去养猪场给人家喂猪……二爷干的是苦力,雇主却只给很少的工钱,有些雇主甚至连工钱也不给,只是包吃包住,走时送两条劣质烟。他一生没有什么乐趣,只是爱抽烟。
那些年,二爷春节从外面打工回来,都在我家过年。我们家的条件是二爷家没法比的,但他每次都给我们这些孩子发数目不小的压岁钱。二爷穷,但大方。他只要出门,就不会空着手回家,不是买两只鸡回来,就是拎两条鱼回来,或是捎点儿我们小孩儿爱吃的鸡蛋糕、奶糖、果脯。有一年春节,他走到开封车站,身上揣着的一年的工钱全被人偷走了,幸好还剩下一张买好的汽车票。回家后,他和我奶奶说起这件事,像小孩儿一样呜呜哭起来。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二爷失声痛哭。过完吉兆,他回了乡下老家一趟。除夕那天又回来了。他大概是借了钱回来的,回来时带着两只宰好的鸡,还有一大块羊肋排。除夕夜,他按照惯例给我发压岁钱。他喜欢我们家里的每一个大人、孩子,但最喜欢的还是我爸和我。
我小时候觉得二爷的力气是用不完的,我把二爷当成现实中的大力水手。我从没想过,二爷的力气也会衰竭。二爷最后那份儿工是奶奶的一个远亲介绍的,远亲传话给奶奶,说二爷干活不够卖力,还贪睡,不干活儿的时候坐在那儿都会打瞌睡。这是我没法想象的。几年后,我再见到二爷的时候,已经是初中毕业的暑假。那时二爷已经不外出打工了,住在农村老家。和我小时候记忆里的样子比,他老多了。他头发花白,粗壮的身体消瘦下来,还有点儿伛着。他那次来没有像以往那样在我们家里住一阵,说是第二天有事儿要赶回家去,爷爷奶奶也没有挽留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去二爷住的放杂物的小偏房和他说话。二爷就像上了年纪、容易动感情的老妇人一样,话多了、碎了,有时激动得眼泛泪光。他说到养猪场的活儿,说别人不让他干了,不是他干不动,是人家看他年龄大了,怕他万一病了给他们惹麻烦。他们也看不惯他和村里的一个女人来往。我问他那个女人是不是他的女朋友。二爷看起来害羞了,挠了半天头。他要我答应不把这事告诉爷爷奶奶。他说他在商水丁村那个养猪场干活时认识了一个女的,她家也住在丁村。他说她的心就像我奶奶的心一样善。猪场的伙食不好,她经常给他送吃送喝贴补他,他干完活儿没事就去找她说话……“我这一辈子,除了你爷爷奶奶,没有其他人待我这么好过。”二爷说。说到这些,他那脏兮兮的、看不清肤色的脸上泛起一层红光。“那她好看吗?”我逗二爷。二爷嘟哝着:“啥好看不好看,反正是个女人……离了婚的。”我问二爷她叫什么名字。二爷支支吾吾半天,告诉我她叫少红。
二
知道二爷住院后的第二天,我还是去看他了。我对奶奶说我去澡堂洗澡,然后去了医院。我找到姑姑的朋友问了二爷的病房。
我找到307病房,推门进去,发现他躺在左边角落里的那张病床上,闭着眼睛,眼角粘着大粒的眼屎。他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皮肤灰黑,树皮般又皱又粗。
标着红色号码的白色棉被把二爷的身体压在下面,只有一只手臂露在外头,脏兮兮的秋衣袖子卷上去,胳膊上插着两个输液针管。他看起来像七十多岁,但我猜他还不到六十岁。
被子底下,二爷的身体好像缩小了很多,我看着他枯瘦的手臂,突然觉得他是被什么东西榨干了。我坐了将近十分钟,他侄子还没回来。我觉得床动了一下,看看二爷,他睁开了眼睛,正看着我。我从没见过那么浑浊的一双眼睛。
“二爷,我是小光。”我说。
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像摔坏了的、布满裂纹的玻璃球。他认出我了,脸上有了表情,像个面老的凄苦孩子。他想说话,发出“呃呃咦咦”的声音,嘴往一边歪斜着。我努力听了一会儿,只约略听到我的名字。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二爷,我听不清。不过你不用急,医生说再输几天液体,就能恢复得和原先一样了。”
他那张歪斜的嘴抖动几下,总算不再试图说话。但过一会儿,他的身体开始使劲,嘴里又发出一串含混的声音,看起来有点儿急。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们的那女的说:“他是要上厕所吧。”在她的指导下,我帮二爷上了趟厕所——要一手搀着他,一手举着输液架。他左边的身子看起来不灵便,但还不算瘫痪。我第一次看到人老了、病了是这么无助,即使是曾经像大力士一样的二爷也无法幸免。
回到病房后,我把枕头靠着床头立起来,让二爷倚坐在那儿。我总得说话,就顺口编了些谎话,说我从姑姑的朋友那里听说,他的病情一点儿也不严重,我还说我爸爸很快要回来,会把他接到我们家里一起过年……这时候,我看见眼泪从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流下来,流过他脸上的沟沟壑壑。
我在医院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二爷的侄子一直没回来。二爷只有这么一个侄子,从爷爷奶奶说的话里,我觉得这个侄子不怎么孝顺。因为我要在午饭前赶回家,所以我跟二爷说我得走了,二爷“哦哦”地应着,但他那只还能动的右手仍然紧紧抓着我的手。
没有时间去洗澡,我去路边理发店让人家给我洗洗头。这样奶奶就不会怀疑我没有去洗澡了。
午饭时,我问爷爷奶奶:“二爷那个侄子孝顺吗?要是二爷瘫痪了,他会照顾二爷吗?”
奶奶说:“他应该照顾。你二爷挣的钱、名下的地都给他了。”
我说:“但是农村里有的人连自己父母都不照顾。”
爷爷叹口气说:“那就不是咱们管得了的事儿了。”
我说:“这个病如果家属照顾得好,不是就能恢复得很好吗?”
奶奶说:“是这么说。但乡下的条件不比城里,年轻人都忙着打工挣钱,能给他看病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谈话被引到我想要的方向了,趁机对奶奶说:“那为什么不让二爷住在咱们家呢?咱们家有的是空房子啊。”
爷爷奶奶的眼睛都瞪大了。
“住咱们家?谁照顾他?”过了一会儿,爷爷问。
“他有亲侄子,东西都给他侄子了,轮不到咱们家管。”奶奶说。
“可是二爷如果住咱们家,肯定能恢复的,他又没有瘫痪。到了乡下,没有人管,只会……”我嗫嚅着说。
“你一个小孩儿,操那么多心干什么!住这儿你照顾他啊?再说,万一人死在咱家里怎么办?”爷爷训斥我。
我回答不上爷爷的问题。其实,我愿意照顾二爷,我愿意给他养老,但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
两三天后,爷爷奶奶又去了医院一趟。他们说,二爷当天下午就要出院。
“二爷好点儿了吗?”我问。
“好一点儿了,能说一两句话。恢复得还算不错。”爷爷说。“再住几天就好了,医院的意思是再住几天,治疗彻底一点儿。但他侄子急着回家。”奶奶说。
“也不光是时间的问题,你没看出来他侄子的意思吗?害怕住得久花钱。”爷爷对奶奶说。
那个夜里,我睡不着。我隐约猜到等待着二爷的是什么命运。我想帮二爷,但我能干什么呢?谁又会听我的呢?我厌恶自己的年少,年少的无能。
三
我知道二爷最后打工的那个养猪场在商水县张庄乡一个叫丁村的地方。到了商水县城后,我在车站打听去张庄乡的车。有人带我上了一辆小巴。我蜷缩在没有暖气、车窗四处漏风的肮脏小车里,沿途是千篇一律而又无休无止的中原农村冬日的凋敝景象……
二爷出院后,下过一场雪,雪后天气冷得出奇,屋檐下结了冰凌。听说,二爷没有住在侄子家里,因为侄子媳妇爱干净,就让侄子在地里给二爷搭了个塑料窝棚。奶奶说那哪是人住的地方,就是狗窝,臭得熏人……我猜这大概是因为二爷已经下不了床、大小便失禁了。爷爷奶奶都说脑血栓最经不住冻,一冻血流慢,血管就又堵了。爷爷过去也得过这个病,前些年,因为他的病,爸爸会把他接到深圳过冬。现在,他完全好了。
“那二爷现在病得更重了?”我问他们。
“唉,还没有出院时候好,又说不成话了。这种病没人照顾是不行的。”爷爷说。
我等了一会儿,但他们没说接下来要怎么办。
过一会儿,奶奶说:“这都是命,没办法。上辈子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命这么苦。”奶奶信佛,信命,信六道轮回。她早晚上香,每隔一段时间要去市场买鱼放生。
所以,我现在坐在这辆开往陌生的、我毫不向往的一个地方的小巴上。我知道我不能说服爷爷奶奶,但我又不能什么都不做。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寻找少红——二爷说的那个体恤他、对他好的女人。
破烂、肮脏的小巴行驶在公路上,发出吱吱呀呀、散架了似的噪声。路两边排成行的落光了叶子、枝丫在寒风里瑟缩的杨树,就像一个个饱受饥寒的垂暮老人。杨树后面是冬天贫瘠、肃杀的田野,赤裸裸的,令人生畏。而二爷就是睡在这样的地方——在野地上一个用塑料布临时搭成的窝棚里。北风会一无遮挡地扫进他住的窝棚,这个曾经力大无穷的人瘫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没有一个人给他一碗热汤,没有一个人能扶他一把。如果二爷还能想,他会想什么呢?我想象不出那会是什么滋味,想必比刀子剜心还疼痛,比窝棚外被冻僵的田野还冷,冷得无边无际。
为了这次远行,我把这个月剩下的伙食费和平常攒的零花钱都带在了身上。
我辗转进了丁村。土路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我在路上大踏步地走,为了让自己暖和,也为了压住心里起伏得太强烈的情绪。我怕我找不到少红,我怕二爷等不及我找到少红,我还怕找到少红,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找到少红以后能让她做什么。但她好像就是唯一的希望。我一个人走在这坚硬的村路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她。寒风呼啸,我说不清楚是什么情绪让我想哭。
我打听到了过去那个养猪场,但他们说猪场闹过一次猪瘟,早就关了。我问起那个叫少红的女人,没有人知道。最后,有人带我找到原先猪场主人的家,招呼我的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冷漠男人。他一边倚着门剔牙,一边和我说话。他说:“你说的是那个老光棍啊?我当然有印象。”当我窘得满头大汗、问他少红的事情时,他竟然大笑起来,说要是村里有哪个女人和二爷说句话、给他个好脸色,他看见人家就走不动路了……
四
那天,我赶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和我意料中的一样,班主任给爷爷打了电话,家里的一场风暴正等着我。
很快,放寒假了,过几天就是除夕。爷爷接到二爷的死讯,说侄媳妇一天早上去窝棚里给他送饭,发现他已经“过去”了。爷爷奶奶接着商量去参加二爷葬礼的事,他们是很重视礼节的。他们商定出一份厚礼,两个姑姑也去。他们坐上大姑姑那辆黑色的高级轿车走了,对二爷的侄子来说,他们在葬礼上的出现会是莫大的面子。
听说二爷死了,我倒没有太难过了,还松了一口气。就像奶奶说的,二爷这一死,不再受罪,算是解脱了。我之前揪着的心平静了。
下午三四点钟,参加葬礼的人都回来了。他们聊着葬礼上的情况,说那个侄子请了两个鼓乐班子,侄子侄媳妇都披麻戴孝,行了孝子礼,在乡下算是厚葬了。我想,这大概算是他侄子的庆祝吧。
远处哪里有人放鞭炮,传来寥寥的几声。虽然天阴、刮着狂风,但过年的气氛仍然弥散在空气中。我眼前摊着书和模拟试卷本,但我什么也做不下去,只能身心空空地听着楼下哗哗的洗牌声和说话声。他人的悲伤也是这么不可靠,转瞬即逝。如果二爷的灵魂跟着他们回来了呢?如果他正在那大屋子里站着看这些亲人,或是正在他过去住的杂物间里游荡呢?他还想过在这个地方和善待他的亲人安度晚年。
当然,那只是他孤苦一生中寥寥几个卑弱却不可能实现的梦之一。还有另一个梦,那就是少红。他大概在心里编织了很多次这个荒唐的美梦,以至于他给梦里的女主人起了个名字,以至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忍不住在那天晚上告诉了我他的“秘密”。他只是没想到,我真的会去寻找少红,而我也早已原谅了他的谎言。愿他安息。
(大浪淘沙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飞鸟和池鱼》一书,本刊节选,宋德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