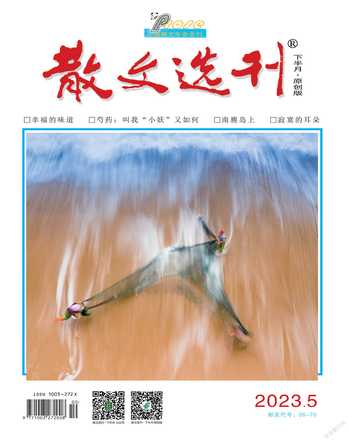跟着外婆拣粮食
杨枥

簸箕里的麦粒打着滚儿,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左右它们的,是外婆弯曲成耙子一样的手。
外婆是在拣粮食里面的石头子儿、土坷垃和草棍儿。过去,乡下磨面没有一遍净的机器,磨粮食得先淘洗。淘洗前,要拣出里面的异物,否则磨出的面粉牙碜不说,还有可能刺破、硌坏电磨的罗布或磨瓦。
力所能及的事情里,我最喜欢帮外婆拣粮食。只是往往还没认真三分钟,我就把簸箕当成两军对垒的战场,把麦粒儿当成千军万马。此刻,我连大海碗都托不起来的小手,成了主宰千百兵甲命运的统帅。我想让谁往东,谁就得往东;想让谁和谁一拨,谁就得和谁一拨。哪怕它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此刻也不得不装作亲密无间的模样。我胡闹,外婆也不恼,只是嘱咐我不要把麦子撒到地上。
别看我玩得不亦乐乎,一旦发现异物,哪怕只是半个绿豆大的土坷垃,我也会当成大西瓜般举到外婆的眼皮子底下。外婆便笑着说:“俺娃真能干,跟咱家的阿黄似的。”我心里顿时喜滋滋的。
拣的次数多了,我也长了见识。随手扒拉几下,就能分辨出这些粮食来自哪块庄稼地。
黑红、干瘦、料礓子儿多的,肯定来自杨岭。杨岭属于秦岭的一小段,它像被烈火煅烧过,土红得不像土,像颜料,挖一瓢兑上水,都能刷红墙。
料礓石混杂其间,像是一块块永远也不会生芽的姜块。杨岭的土地充满火性,自然也长不出寻常的粮食。不仅料礓多,杨岭的麦子也异常干瘪,颜色和庄稼人的脸色一样,黑里透着红。
干沟的粮食里,草籽多、草棍儿多、土坷垃多,因为干沟下面有一条小溪。土地沾了水性,不單庄稼长得好,草木也好。干沟打出的粮食和磨出的面,不像杨岭的那么黑。两个地块的庄稼,收分开收,藏分开藏,磨分开磨,蒸馍也分开蒸。
亲戚上门、逢年过节、外公干重活时,才吃干沟的粮食,其余时间吃的多是杨岭的。别看我干不了什么活,我吃的也是干沟的粮食。好歹我是客呢。
拣杨岭的粮食时,外婆格外当心。一簸箕粮食,外婆要反复拣好几遍。我拣出的料礓子儿,被外婆接过去搁在苇席一角,外公回来,外婆会说:“瞧,娃子能干吧。”
而她拣出的,顺手就扔到了远处,惹得埋伏在旁边、一直虎视眈眈的那群母鸡,轰隆一下跑过去……
很神奇,每当我以为绝对拣干净时,外婆总能挑拣出我认为的不可能——多像我现在从事的文字编辑工作啊。只不过,我那时拣的是粮食,现在拣的是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