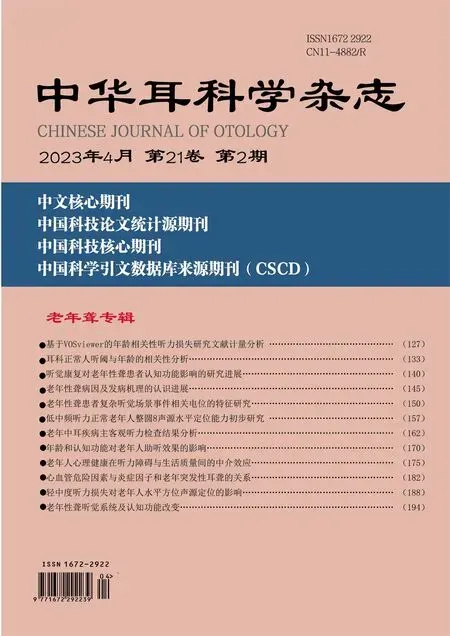婴幼儿人工耳蜗与助听器双模干预的调试与客观评估
晏小惠 周梦莹 赵燕 史文迪 王永华
1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 310000)
2 杭州仁爱耳聋康复研究院(杭州 310000)
3 惠耳国际听力学研究中心(杭州 310000)
单侧人工耳蜗植入患者远高于双侧人工耳蜗植入,国内外专家均认为单侧耳蜗植入患者在非植入耳具有残余听力的情况下,应及早佩戴助听器实现双耳聆听[1,2]。避免了中枢可塑性受双耳间长期不协调的信息输入而出现变化,从而造成了听处理偏侧化,激化无听力刺激的一侧语言辨别能力进一步下降[3,4]。
双耳双模式实现了双耳聆听,是一侧耳为人工耳蜗植入通过电刺激提供信息,另一侧选配助听器通过声刺激提供信息的聆听模式。人的听力系统结构精密,无法彻底地被现有商品所取缔,从人工耳蜗的植入电极长度、通道数量多寡、言语编码策略等都可以简单提取发声资讯,却无法得到准确的音调资讯,尤其母语为普通话患者对于音调的感知明显欠缺,因此为补偿助听器增益不足,人工耳蜗无法获取音调信息的缺陷,双耳双模式逐渐被广泛用于临床。史文迪等对非植入耳及时实施听力干预者与未经干预者进行比较,前者是非植入耳对声母、韵母、单语调、双声调、句子识别率等都有了明显提高。与陶仁霞等研究一致,单侧人工耳蜗植入的患者较双耳双模式的患者声调识别率降低了13.04%[5,6]。同时,双耳双模式缩短了普通话音节识别时间、加快了处理信息的速度[7]。双耳双模式匹配调试会因为听力师凭借经验调试、患者的主观反馈调试或客观的电生理检查数据等原因而呈现不同的结果,在Zhang 等[8]研究中得出,安静环境下比较单音节识别率情况,双模聆听患者较单侧人工耳蜗者好15-30%。相反,Tao等的研究得出,最终导致双耳双模式对于有些患者出现更差的言语表现[9],这是由于双侧辅听设备刺激产生的响度不平衡及二者电刺激与声刺激在设备上体现出来的信号处理有延迟、不同步,使得电刺激和声刺激信号在大脑皮层听觉中枢出现了融合干扰。为了优化双耳双模式患者的聆听需求,补充婴幼儿无法主观表达指导调机的不足,我们需要寻找合适的补充方式来调试人工耳蜗与助听器。因为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双模匹配调试技术对调机人员的技术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尤其是针对婴幼儿而言,另外也需对调试后的双耳双模式效果进行评估,所以客观检查方式即使不能“一锤定音”提供调试依据,但是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辅助参考,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来实现较佳的聆听目标。
从调试上来说,双耳双模式调试由频率响应策略和响度平衡策略组成,频率响应中包括了:1)全频段放大策略2)频率互补策略3)移频策略[10]。系统的听力学检测和评估可以使得双模干预效果量化、精准化。

图1 双耳双模干预的听力学检测示意图Fig.1 chematic diagram of an audiological test with binaural bimode
婴幼儿助听器-人工耳蜗声电联合双模式的精准调试工作方法与测评方法为:1)估算确认人工耳蜗最低电激发量(T/M 值):电诱发听性脑干反应阈检测;2)估算确认人工耳蜗最高电激发量(C 值):电激发镫骨肌反应阈检测;3)对助听器一侧耳通过频率特异性听性脑干反应(F-ABR)检测裸耳听阈值,声反射阈值预估不舒服阈(UCL),根据真耳分析选定的适合公式完成助听器各强度放大与频响曲线的调试;4)双耳助听听阈均衡调整,双耳响度均衡调整后,可结合进行言语识别率测试,通过不同强度下的言语识别率评分进行比较,进一步对人工耳蜗和助听设备进行微调,如无法进行言语测试的患者,可行双耳声场下的皮层听觉诱发电位测量(如图一所示)[33]。
人工耳蜗的调试需要正确的判别阈值(T-level)和最高舒适强度(C-level),然而T 值和M/C 值的测量多采取患者主观行为测听方式,不但受患者年龄、残余听力、情绪、注意力及测试工作人员经历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且每次要花费较长的调试工作时期,患者主观行为测听很难获得满意T 值和C 值,需行电诱发听性脑干反应(electrically evoked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s,EABR)、行电诱导镫骨肌反射阈值(electrically evoked stapedius reflex threshold,ESRT)、神经反应遥测(neural response telemetry,NRT)等客观听觉检测。同样对于此类较难配合主观行为测听方法的患者,TB-ABR、SRT、真耳测试、助听后声场ABR在助听器调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1 人工耳蜗的调试与客观评估
人工耳蜗技术的普及性与安全性使植入年龄逐渐呈下降趋势[13],植入人工耳蜗的小龄化让调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听到且舒服”,是在调整人工耳蜗调机时的重要目标,T 值和M/C 值是两条标准线制作出电听觉动态范围。T、M/C 值和动态范围决定了术后患者言语识别的好坏[14]。准确的T值和M/C 值都必须通过患者的主观行为测试确定,婴幼儿需要通过视觉强化定向条件反应测试及游戏测听能够得到T 值。如果植入者的言语和听觉经验足够的话,可以配合调试者获得最大舒适响度,但这对年幼儿及语前聋儿是很难的。以图形指认声音大小来确定最大舒适度只能用于6 岁以上儿童。行为观察法耗时且易引起植入者对装置的反感,因此迫切需要客观的方法来对最大舒适度的确定提供参考。如ESRT和EABR。ESRT阈值与M/C阈值的关联性高,应该把ESRT 的阈值当作调机M/C 的参照值,而EABR 与T 值的关联性高,也应该把EABR的阈值当作调机T值的参照值。
1.1 EABR
患者存活的螺旋神经节细胞数量较多,听觉神经纤维功能健全,并且听神经中枢并无明显改变,对人工耳蜗效果起到决定性作用。EABR 能评价残余螺旋神经节功能,并评价听神经细胞与脑干传输通道的完整度和功能状况;EABR 为耳蜗植入和ABI 听觉脑干植入过程进行术中监测,并辅助植入后的启动与调试工作,预测人工耳蜗的效果,以及对病人植入后语言功能的预测等进行评价[15]。我们这里主要关注EABR 在人工耳蜗调试中的作用。EABR 可模拟人工耳蜗,同时激活相似部位、并提供近似的刺激电流,可体现听神经细胞-耳蜗核-上橄榄核结合体-外侧丘系-内下丘这一较完整听觉信息传输通道,也可用作为评价人工耳蜗植入效果的一种客观评估工具[16]。电诱发听性脑干反应法作为目前较完善的检测手段之一,是一个可以客观测量听觉功能的较佳方式,可不受主观因素影响,可以精确地达到阈值,一般认为,EABR 的阈值与T 值的相关性比阈值与C 值的相关性好。对不能进行主观检测、主观检验参考意义不大或初次调试困难的患者,EABR 阈值的测定可提供较大帮助[17]。EABR 的ⅲ~ⅴ波间期都在正常范围,提示上橄榄核及下丘段的听神经通道生长发育健康有益[18]。
1.2 ESRT
M/C 值为一心理物理量,受患者主观反应所影响。声诱发的镫骨肌反射也称声反射,是人类一种对强声的保护性反射。镫骨肌收缩运动可以保护内耳结构免受强声刺激后引起损伤,肌肉收缩动图被记录[19],表示为不舒适阈值,且镫骨肌反射阈(即能够引起镫骨肌反射的最小声音强度)与不舒适阈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指出电诱发的镫骨肌反射(ESR)的学者Jerger等[20],同年指出ESRT与M/C值期间存在相关性且,ESRT 一般比最佳舒服阈低[21],而Hodg 等[22,23]比较了ESRT 成为最佳舒服阈值后的言语识别率和使用行为测试得到的最佳舒服阈值后的言语识别率之间存在一致性。说明使用ESR 是一个可参考用于指导调机确定M/C值的客观方式。使用ESR 完成术后调试不会对听神经系统产生太大干扰,而且不会对病人听阈产生强烈负面影响。但ESR在部分病人无法引出[24],有如下三个因素:一是最大激发强度远小于直接植入者的最高不舒适阈范围;二是由于病人身体不能协调,从而导抗探头放置受阻、因头部或面部活动,而导致了咽鼓管的开放等;三是由于诸如耳蜗骨化等因素,导致的耳蜗中残存的螺旋神经节神经元的数量相对较少。研究发现,考虑到开机后多个电极的总和效应影响,C值调图数据需低于ESR阈值10~15 CL[25,26]。
1.3 ESRT/EABR与NRT之间的差异
早期NRT 检测作为一种简便快捷(测试环境要求的近场记录)的方式用来预估T 值和C 值[27,28]。但研究人员指出,由于人工耳蜗术后病人的听神经传递通道呈动态变化,因此EABR 在评价人工耳蜗植入术后的病人短期听力通路可塑性方面,比NRT更加灵敏[29]。NRT 检测对于部分内耳存在畸形患儿,不能引出NRT 波形,无法确定其听觉功能,这主要是因为该类患者不残存的神经纤维分布状况以及局部电极状况,NRT 记录增益延迟等问题[30]。此外,EABR与行为测听的主观T值呈显著相关性,因而可利用EABR 阈值预测T 值,并将T 值设定在EABR 阈值左右。由于听神经反射的“全或无”现象,且镫骨肌反射和听神经数目关系并不是一定关联,更有利于对内耳畸形的患儿进行监测。在理论上阈值和C值相近[23],ESRT阈值和人类行为测听的主观C值呈显著相关性,因此,可以使用ESRT阈值预估C 值。NRT 经常成为部分听力师简便调试人工耳蜗的主要工具,虽然它十分方便,但是NRT 检测方法具有以下缺陷:1)无法反映存在于更高级听觉传递通道的功能状况;2)仅可记录听神经复合动作电位;3)NRT与EABR存在刺激强度差;4)只有在人工耳蜗植入后可进行检测。
2 助听器调试与客观评估
正确检查听力、佩戴合适的助听器、较佳的调试和定时随访,是听力损失患儿听觉康复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对于无言语能力的婴幼儿来说,临床上常见Click-ABR检测听力,但它被认为频率特异性差,仅能反映2-4kHz频率处的听觉功能,无法反映中低频。对于如陡降型听力损失的听阈评估存在局限。分频听性脑干反应(TB-ABR)可提供较为可靠的500Hz1000Hz2000Hz4000Hz的客观听力水平。
但儿童外耳道尚未发育完全,与成人外耳道存在很大差别,即使是同一儿童,由于外耳道成长变化也会导致其声学特性发生改变,容易出现听力损失儿童助听增益不足或过度放大。儿童真耳测试[31,32]是指在儿童的外耳道中进行声学测量的过程,结合听力损失儿童的外耳道形状特点、容积多少及助听器的声学特性。真耳测试使儿童助听器的验配和调试更为直观方便、精确、科学,并且避免了许多在验配中容易出现的猜测情况,提高了验配的满意度,对于聋儿的听力与言语康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针对儿童助听器的调试,真耳检测以实际的增益值为基准,从而能够合理地确定儿童助听器对最小声(55dB SPL)可以听到,对中声(65 dB SPL)感到舒适,对大声(>75 dB SPL)不难受,以及对最大声输出(90dB SPL)安全限度的控制,从而最终实现了科学补偿聋儿听力损失的目的。测量的过程中,要求聋儿较长时间保持安静并配合测量,无法用上述方式对聋儿进行真耳测试的,可以采用取真耳耦合腔差值(real-ear coupler difference,RECD)的方法。通常在助听器验配时,尤其是年纪较小或不能配合的儿童,通过运用RECD 测试,有助于得到较精确的接近于真耳的助听器输出频响曲线。每次儿童复查时,除了常规的听力学检查之外,调试助听器之前还需要重新进行RECD 的测试。同时,下列情形的检查也必须再次进行对RECD 的检测:1)验配新助听器,并重新制造耳模;2)助听装置及耳模的声学特性出现了改变;3)因为中耳及内耳的病变引起听觉波动;4)以前验配助听器时,没有做过真耳分析。
3 助听器与人工耳蜗双耳双模式的响度匹配调试与客观评估
响度平衡是指双耳辅听设备发出的声音响度一致,若两侧不平衡会导致言语识别率降低。助听器自动化算法在单耳验配中会叠加双耳累加效应,增益放大同时对侧人工耳蜗相融合会使得响度过大。患者在声音响度一致的条件下可以得到双耳强度差,以便进行声源定位[10]。当这种响度平衡被打破时,如将已达到响度平衡的各电极的舒适阈随机地在其动态范围±20%以内改变时,大多数患者的言语辨识能力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难主观表述不同电极阵列间音调和响度之间细微差异[13]。
双模干预效果的判别不能只根据响度反映情况,仍需要依靠患儿言语改善情况及语言的康复评估[26]。针对中低龄儿无法使用的言语测试评估,研究人员表明听觉皮层诱发电位(cortical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CAEP)的P1波的振幅和潜伏期可以用作人工耳蜗植入后的婴幼儿中枢听力系统发育程度的重要参照依据,可用于婴幼儿康复效果的一种客观评估方法。它能被语音信息激发,是由人脑产生对声音信息进行感受、理解、记忆过程中形成的电位,与言语感知有较好的相关性。如CAEP 测试结果体现为P1波潜伏期增长,则听觉语言能力低下,而P1波潜伏期缩短,则听觉语言能力显著增强。双耳双模式调试的关键在于响度平衡,双耳融合、双耳累加效应在响度上增加6-10dB,反应阈提高了3 dB,患者同一声强下调试后较调试前对刺激声更敏感,反应时间缩短,潜伏期提前,振幅增高[33,34]。
4 结论
双耳双模式匹配和调试一直是听力学专业人士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如何对听力损失儿童尽早进行科学正确双耳聆听,使他们能更好地回归主流社会是每个听力师、语训康复教师和家人的共同责任。听力学检查需要交叉验证进一步提供证明依据,客观的听力学检查能够较好为双耳双模式干预患者的调试和评估提供参考依据,但该检查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仍需要多指标交互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