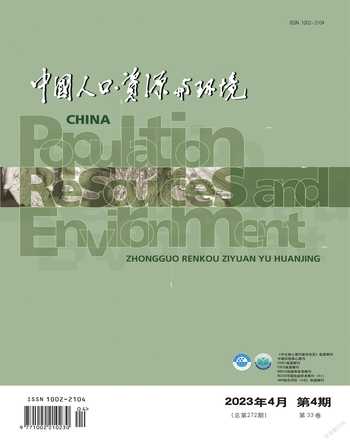“河长制”政策能否激励绿色创新?
王川杰 李诗涵 曾帅



关键词 环境规制政策;河长制;绿色创新;多期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 TV213. 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3)04-0161-11 DOI:10. 12062/cpre. 20220924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希望中国加快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走高质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中,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水污染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为应对这一挑战,河长制政策已成为中国水污染防治的有效举措,以及大多数河流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依托和落实手段。河长制的施行也为识别官员规制类的水污染环境治理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机会。区别于之前的环保政策,河长制政策首次全面落实“责任到人”的地方党政领导负责制度,通过差异化的绩效考核评价,将环境治理与官员的晋升机制紧密关联,旨在提升地方官员治理水污染的能动性。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对河长制的制度思考[1]。诸多学者研究并验证了河长制政策对河流水质的显著改善作用[2]。后续研究也发现,河长制通过降低企业的水污染排放行为,改善了河流水质[3]。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减少污染排放,一种是调整产出,另一种是采用新设备、新技术等[4]。在面临河长制政策的环境治理压力时,企业为达到当地河长监督的环境标准,可能在降低产出或加快绿色技术研发之间进行抉择。鉴于此,文章检验企业是否选择绿色技术创新以应对环境治理压力,对河长制政策的效应评估有着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1. 1 水污染治理的相关研究
1995年,“波特假说”被提出,该理论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促使企业进行更多创新活动,而这些创新将提高企业生产力,从而抵消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并提升企业在市场的盈利能力[5]。此后,诸多学者尝试验证这一理论,即环境规制政策能实现环境保护和创新进步的双赢效果[6-9]。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从科技进步和绿色发展两方面,提出对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逐渐有文献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5, 10-13]。企业出于最大化利润的考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动机相对较弱,因此企业往往缺乏绿色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为构建支持环境保护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中国政府出台并施行了一系列针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引导和服务型政策。这些政策按照规制主体可分为企业规制政策和官员规制政策,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环境规制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等,而作用于地方政府官员的环境规制政策主要体现为加大对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压力,将环境治理成果与晋升挂钩。
水污染治理政策是环保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分别下降8%。有关研究多从政策效果视角切入,考察各类水污染治理政策对地区水质、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居民健康等方面的影响[14-18]。然而,在水污染治理政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方面,尚未有研究讨论水污染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1. 2 地方“河长制”政策与绿色创新
早在2003年,浙江省长兴县率先实行河长制。2007年,无锡市作为河长制试点的首个地级市,出台了《无锡市河(湖、库、荡、氿)断面水质控制目标及考核方法(试行)》的文件,将水质监测结果列入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政绩考核内容中。随后浙江、江苏等省份陆续推动省内建立河长制。2016年底,中央下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到2018年底中国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的河长制体系,河长制也从试点城市正式向全国推广,并于2017年6月正式写入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与其他水污染治理政策不同,河长制作为对党政一把手的问责机制,执行时间、执行强度和治理效果等方面在不同地方存在明显差异。全国各省份的地级市按照自身发展水平和水污染状况,选择不同时间点相继出台地方河长制文件,在辖区内正式启动河长制的推广和实行。
现有文献关于河长制政策对河流水质达标率的提升作用已经达成共识,如She 等[19]发现河长制能够较大幅度改善水质,且在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城市,水质改善水平存在差异。王班班等[3]证实了河长制将在“向上扩散”地区和“自发首创”地区实现企业减排效果。沈坤荣等[2]基于国控监测点水污染数据,发现河长制能够实现初步水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但并未降低水中深度污染物。河长制将河流水质状况纳入地方官员政绩的考量,这一特征使得地方官员从自身政绩角度出发,积极采取措施以降低水污染,这种政绩与环境治理挂钩的激励措施往往富有成效[20-21]。在巡视监督中,地方官员问责辖区内各类主要污染排放来源的企业,并为各类企业设置排放目标,以完成环境治理的考核要求。
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已经对河长制的环境治理效应进行充分讨论,而缺乏对企业面临河长制政策时反馈的关注。鉴于此,文章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作出有益补充:一方面,文章旨在确定企业层面水污染治理政策的效应来源,企业实际可通过调整产量和提高绿色技术水平实现地方官员制订的排放目标。文章认为在绿色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环境治理久久为功,持续减产以满足环境考核要求的策略,在短期损害企业经济效应,在长期使企業经营难以为继。因此,主动进行绿色创新将是企业应对河长制政策环境的理性决策。另一方面,在机制检验和效果分析中,文章顺承已有文献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机制分析,区分企业应对水污染治理政策的内外部动机来源,并从官员激励和治理广度两个维度,深化已有文献关于水污染治理政策效果的认识。
2 识别策略、变量和数据
2. 1 计量模型设定
评估河长制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最为直观的方法是比较河长制实施前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差异,但是在政策实施前后,可能存在其他干扰因素影响河长制实施效果,从而使政策评估出现偏误[22]。与此同时,各地区逐步推行河长制政策的现实特点,也为文章选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提供可能,以更好地识别政策效果。因此,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来识别河长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政策影响,能有效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一方法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环境规制政策的效应评估中[23]。借鉴沈坤荣等[2]、王班班等[3]的研究思路,文章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2. 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时间区间选取为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至2019年,以此为样本实证检验地方河长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是否有激励作用。根据沈坤荣等[2]以及文章的统计,超过70%的地级市推行河长制的时间在2013年以后,因此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政策效应的完整评估,文章选用上市公司作为调查企业。文章主要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取各年度上市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和负面新闻报道数量,并从公开信息渠道手工收集整理地级市河长制数据,其他的财务数据和地级市的人均GDP数据从万得(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获得。在完成原始数据整理后,文章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①删除样本期内上市的企业;②剔除样本期内曾被ST的企业;③删除资本结构特殊的金融企业;④删除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经过处理,文章最终得到1 031家企业共11 341个样本。
被解释变量是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考虑到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能够有效测度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且不同的绿色专利授权所需时间存在差异,因此文章选用各上市公司每年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对绿色创新能力進行指标构建。具体地,参照王班班等[24]、齐绍洲等[10]、徐佳等[13]的指标构建方法,文章分别对上市企业每年度的绿色专利申请总数、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加1后取对数处理,得到三个被解释变量Pat?Green、PatGreen_inv 和PatGreen_uty。
核心解释变量为上市企业总部所在地级市是否推行河长制的情况。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有293个地级市。但是,按照前文的样本筛选方法,并非所有地级市都存在沪深A股上市公司,因此文章首先梳理总结样本企业总部所在地级市样本,共有232个。在此基础上,手动整理这些地级市样本实际推行河长制的时间以及相应的政策文件,从知网政策文件库、百度新闻以及地级市政府官网等三个渠道进行信息搜集,并对结果进行汇总交叉验证,以构建核心解释变量River?Chief。参考张琦等[25]、徐佳等[13]、李青原等[11]的研究,选取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独立董事比例(Dep)和企业属性(SOE)等12个企业控制变量,以及企业总部所在地级市人均GDP(Lnpgdp)作为城市控制变量,控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因素,缓解遗漏变量偏误,具体变量信息见表1。
3 实证结果
3. 1 描述性统计
表2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沪深A股上市企业绿色创新水平(PatGreen、PatGreen_inv 和Pat?Green_uty)中位数均为0,超过50%的上市企业没有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说明整体绿色创新动机和能力较弱,而从绿色专利的类型来看,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的均值大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均值。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3. 2 基准回归结果
在基准回归中,将上市企业的各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模型(1)为基准,结果见表3,分别列示了以不同绿色创新衡量标准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分析都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表3结果显示,河长制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显著性水平不受控制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河长制政策使得绿色专利申请总量的对数提升了约7. 3%,在区分绿色专利类型的情况下,政策对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略高于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因此,从结果来看,河长制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政策效应是显著的,通过加大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压力“倒逼”企业进行绿色专利研发。
3. 3 假设检验
尽管前文已经初步证明河长制政策的施行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但是DID的合理性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前提下,为了验证识别策略的可靠性,文章接下来对重要的识别假设进行检验分析。
3. 3. 1 平行趋势检验:事件分析法
双重差分法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假设是,在政策冲击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绿色专利研发水平具有相同的趋势,即如果没有实施河长制政策,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绿色专利变化趋势不应随时间变化有系统性差异。借鉴Jacobson等[26]、沈坤荣等[2]的做法,将模型(1)中的核心解释变量RiverChiefjt 替换为河长制推行前和推行后若干年的虚拟变量,具体模型设定为:
3. 3.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河长制政策的效果是否源于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或遗漏变量,参考Chetty 等[27]和La Ferrara 等[28],通过随机确定河长制在各城市的推行时间设计了间接的安慰剂检验,基于随机选择的样本,重复进行500次基准回归,最终得到因变量分别为PatGreen、PatGreen_inv、Pat?Green_uty 的500个参数估计结果。结果发现,基准回归的系数完全独立于参数估计的系数分布之外。因此,文章可以排除河长制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源自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或者遗漏变量的可能。
3. 3.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文中还针对基准模型(1)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相应的结果在表4和表5中报告。
首先,为克服样本选择偏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选择对照组,随后根据基本估计模型进行PSMDID检验,结果见表4的列(1)至列(3)。尽管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大小有细微变化,但是河长制政策仍然对所有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正向影响,即结果并未改变文章的主要结论,文章基准结果稳健。
此外,参考Ren[29]、郭峰等[30]的做法,为了控制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例如行业层面逐年变化的景气度对企业绿色专利研发产出的影响,文章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乘项。从表4的列(4)到列(6)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且系数值与基准回归的值差异较小,表明估计结果并未受到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最后,为了保证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衡量的可靠性,借鉴李青原等[11]的思路,替代性地采用企业当期绿色专利授权情况衡量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即将因变量替换为当期绿色专利授权总数、绿色发明型专利授权数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分别加1后的对数值。表5的列(1)至列(3)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都为正。因变量为绿色专利授权总数和绿色发明型专利授权数时,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为代理变量的参数估计不显著。
考虑到专利授权存在滞后性的问题,一项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往往需要1至2年的时间[10] ,因此文章进一步考虑以滞后一期的绿色专利授权情况来衡量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表5的列(4)至列(6)报告了该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河长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仍然为正,同时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绿色专利授权总数和绿色发明型专利授权数为因变量时,显著性水平为1%。总的来说,在替换因变量的情况下,上述结果仍与文章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3. 4 作用机制分析
为了考察河长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参考李青原等[11]的研究,分别考察企业内部激励和外部壓力两种可能渠道。分别用前三名高管薪酬和媒体报刊中负面新闻的数量来构建内部激励变量(Salary)和外部压力变量(News)。如果变量值大于中位数,相应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反之则为0。理论上,在面临河长制政策外部环境治理压力时,前三名高管薪酬越高,高管将有更强的内部激励动机进行绿色技术专利研发;媒体报刊中对于企业报道的负面新闻数量越多,企业面临的监管强度将更严,河长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明显。
表6报告了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源的检验结果,列(1)、列(3)和列(5)显示核心解释变量RiverChiefjt×Salaryit 的参数估计值都为正,且以绿色专利申请总数和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数构造绿色创新水平因变量时,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下显著;列(2)、列(4)和列(6)的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RiverChiefjt× Newsit的参数估计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表明,企业在面临河长制政策的环境治理压力时,外部压力水平和内部激励水平越高,会加大环境治理压力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且外部压力的效果强于内部激励的效果。
4 进一步讨论与异质性分析
前文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河长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且分析了内部激励和外部压力两种传导机制。那么,河长制政策的影响范围如何,是否受到地方党政领导治理动力的影响,以及政策效应是否受企业特征影响,仍需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4. 1 政策影响广度分析
在基准回归中,文章仅考虑利用河长制政策的推行构造虚拟变量,进行政策效应评估,以判断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压力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前文并未考虑河长制政策与已有河流环境治理政策在执行力度和影响广度方面的区别。文章创新性地测度了企业离最近河流的距离Dist_River,作为河长制政策执行力度和影响广度的代理变量。根据水利部制定的《河道等级划分办法》,中国河道分为一级至五级共五个等级,其中五级支流流域面积小于100 km2,这对于研究地级市推行河长制政策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实际选取四级支流作为基准计算上市企业到最近河道的距离。为测算上市企业距离河流、地级市边界的最近距离,文章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1∶400万主要河流矢量分布图和全国地级市行政区划矢量图中提取河流和地级市边界信息,进一步利用ArcGIS软件进行近邻分析计算得到最近距离。
由于在全面推行河长制政策之前,中国政府已经推行过许多水污染防治措施和法律法规。例如,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2008年出台的《淮河、海河、辽河、巢湖、滇池、黄河中上游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06—2010年)》,这些政策都是通过施加全国范围的水污染防治压力来改善水体质量。因此,在企业已经受到水污染防治措施影响的背景下,文章进一步检验“责任到人”的河长制政策是否扩大了环境治理压力影响广度,更大程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表7报告了回归结果,重点关注RiverChiefit× Dist_ Riveri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所有列的估计结果都是正值,并且以绿色专利申请总数和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数计算的绿色创新水平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责任到人”河长制的水污染治理压力之下,距离河流越远的企业受影响更大,绿色创新水平增长更明显。因此,相较于河长制政策推行前的水污染治理措施,河长制影响程度更为广泛,官员直接面临主要领导责任制的考核红线,对于水污染的治理能动性更强,对于离河流较远的污染企业也能“虽远必治”,覆盖了此前政策的治理盲区。
4. 2 官员治理动力分析
为了检验河长制政策之下官员的治理动力差异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文章主要将考虑以下两个维度的检验:一方面,检验河长制政策是否受到水污染治理“以邻为壑”的政策松懈因素影响,另一方面,检验河长制政策是否受到以地方党政领导年龄衡量的晋升激励因素影响。
首先,地方党政领导在担任“河长”进行河流水污染治理时,可能会存在“以邻为壑”的侥幸心理,即在离行政区域边界越近的地方,会相对放松治理力度,因此会降低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借鉴Huang等[31]的做法,以距离边界20 km 为阈值设置虚拟变量Dist_City,若企业在距离边界20 km以内,该虚拟变量取值为1,反之则为0。表8 的列(1)、列(3)和列(5)报告了检验结果,尽管沈坤荣等[2]并未发现基于河流水质情况的河长制水污染治理效应因是否靠近行政边界而存在显著差异,但是表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均为负,且以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数衡量绿色创新水平时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越靠近行政边界,河长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正向效果越弱,即河长制政策下行政官员担任河长在边界处存在政策松懈。在实践中,地方河长面临水污染环境治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使得水污染环境规制政策引起地区间的策略竞争,这种成本收益的权衡在行政边界处体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河长制政策的官员治理动力还源于官员的晋升激励预期。参考Wang[32]和He等[33]的做法,将57岁作为地级市党政领导晋升激励的分水岭,分别设置市长和市委书记所对应的虛拟变量Age_Mayor 和Age_Secretary。若时任地级市党政领导年龄超过57岁,其获得提拔的概率降低、晋升激励缺失,相应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结果见表8中的列(2)、列(4)和列(6)。结果表明,在同时引入地级市党政领导晋升激励的情况下,仅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衡量绿色创新时,地级市市长年龄对应的参数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其余情况结果都不显著。这与He等[33]的发现部分一致,即市长在晋升激励缺失的情况下,会削弱河长制的治理效应,因此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效应越弱。但是整体而言,晋升激励缺失诱发的治理动机衰减较弱。
4. 3 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分析指出,河长制政策通过施加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各级河长在推行水污染治理举措时,可能对不同规模或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有不同的关注度和执行力,同时也可能会对水污染行业的企业进行特别关注,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异质性效果分析。
首先,分析企业规模异质性的影响,河长制政策对不同企业规模绿色创新水平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见表9中的列(1)、列(3)和列(5)。可以发现,该政策对大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更显著,且核心解释变量RiverChiefjt ×Sizeijt参数估计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河长制政策对大企业的规制更强,大企业受到的政策关注度更高,因此也导致其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更明显。
其次,分析企业产权异质性的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情况在中国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由政府任命,其经营目标也主要与政府目的或社会责任相关,而民营企业经营目标重点在最大化股东价值[34]。在面临河长制政策的环境治理压力时,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将受影响更大,更有动力加快绿色技术研发,因此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更多。企业产权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9中列(2)、列(4)和列(6),与前文假设相同,核心解释变量RiverChiefjt× SOEijt的参数估计结果均为正,并且所有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河长制政策显著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证明了国有企业对河长制政策的环境治理响应相较于民营企业更为积极。
最后,分析企业行业异质性的影响,生态环境部于2020年发布了《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其中将水污染物分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石油类、挥发酚、氰化物、重金属等八种种类,并对每种污染物排放量位居前3位的行业进行统计。为检验河长制政策是否针对水污染重点行业进行着重监管,进而更大程度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文章整理了八种水污染物排放量前三的行业共计10种,若企业属于这10种水污染重点行业,则设置虚拟变量PoWateri= 1,否则PoWateri= 0。
表10列(1)至列(3)报告了河长制政策对是否是水污染重点行业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RiverChiefjt× PoWateri的参数估计结果都为负值,且在以绿色专利申请总数和绿色发明型专利申请数量为被解释变量时,参数估计结果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下显著,这反映了水污染重点行业并未因河长制的重点监管压力而进行更多的绿色技术研发。为进一步说明水污染重点行业如何应对河长制政策的重点监管,在表10中的列(4)报告了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Revenue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河长制政策在1%的水平下显著降低了水污染重点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因此,水污染重点行业可能是通过减产应对河长制的环境治理压力,而非专注于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5 结论与建议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的重要课题,在此基础上“完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强化河长制、湖长制”成为健全现代水体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文章率先研究了河长制这一典型的水污染治理政策对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为河长制对水体治理的影响提供了绿色创新的视角,是发展绿色经济的有益借鉴。同时,差异化地分析治理政策在不同官员治理动力和企业激励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机理,对顶层设计加强对政策薄弱环节的管控,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目标有重要价值。
5. 1 结论
文章以2009年至2019年的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河长制政策的推行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河长制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水平,并且主要可通过企业内部激励和外部压力两种渠道产生作用,再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引入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和改变变量定义等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进一步研究发现,河长制对离河流更远的企业效果更明显,这说明河长制因“责任到人”的主要领导责任制,覆盖了此前水污染防治政策的治理盲区。同时,文章发现河长制转化为官员的环境治理压力时,在行政边界处有“以邻为壑”的松懈效应,对于年龄越大而缺乏晋升激励的河长,其执行河长制政策的动力更弱,在一定程度上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小。在异质性分析中,对于规模越大的企业、国有企业,河长制政策都会更大程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是水污染行业的企业更多选择通过减产来规避监管,并未聚焦于绿色技术研发。需要指出的是,文章也有一定的不足,主要在于研究样本为上市企业,可能存在代表性不强的问题。待未来大规模的企业微观数据可得时,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5. 2 建议
文章为水污染治理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探索了河长制政策治理河流污染的具体途径,诠释了地方党政领导负责制的水污染治理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显著促进作用。基于文章的研究,这里提出以下三条政策建议。
5. 2. 1 落实“责任到人”的主要领导责任制
中央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应严格遵照习近平“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的要求,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与环境治理目标有机结合,充分调动担任河长的地方官员环境治理主动性,通过有效、有力的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同时,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应注意官员治理动力的薄弱环节,进行引导性的机制设计,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投机行为,保证环境规制政策的充分执行。
5. 2. 2 常态化媒体监督渠道
要把常态化媒体监督等渠道作为水污染治理政策的辅助手段,增强企业绿色创新、节能环保的内生动力。政府机构应该加大对绿色创新的舆论引导,对积极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在环保方面取得成绩的企业应该加大媒体关注水平和报道力度,而对污染排放不达标的企业坚决曝光,并依法予以惩罚,通过建立舆论奖惩的有效渠道加强水污染治理政策对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
5. 2. 3 水污染治理政策的推行应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力争实现政策全覆盖
政策应更加聚焦于绿色创新水平不足、创新动力缺乏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于这类型企业,政策制定者应主张“以帮促管”,通过合理的科技扶持计划和技术支持带动绿色创新水平,最终实现环境治理目标。此外,应该避免对政策的僵硬执行,不可对污染企业“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应帮扶企业积极进行绿色转型,同时也要关注企业对政策的应对策略,推进企业通过绿色创新而非消极减产应对环境治理压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责任编辑: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