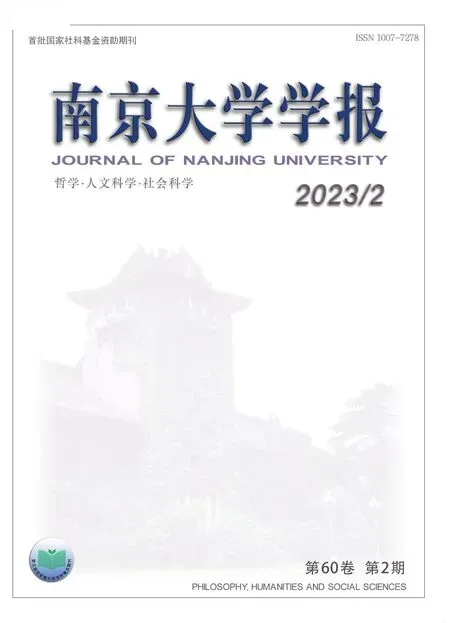西方来源与本土化创造:中国翼兽飞翼源流考
俞方洁
翼兽造型艺术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经典的文化传播案例,早在公元前四千纪,这种想象的生物已经出现在两河流域。到公元前三千纪,西亚已普遍可见翼兽形象。伴随战争、贸易以及人员、文化的交流,翼兽形象大量出现在西方的希腊、罗马和东方的波斯、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等文明中。虽然学界对中国翼兽的起源尚有争议,但我们至少可以确信翼兽对中国有着深入的影响。在翼兽母题中,飞翼是翼兽形象的重要标志。西亚的古代文明认为,走兽生出翅膀,可以获得鸟类飞行的能力,能够翱翔天地,成为神灵,获得神性。这种思想影响了希腊、波斯等文明,虽然西亚翼兽的内在含义在这些古代文明中逐渐淡化,但表达巨大、强壮的翅膀仍是翼兽母题的必然之义。
然而可以发现,翼兽母题在东传的过程中,翅膀逐渐被装饰化、符号化,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的翼兽双翼逐渐缩小,巨大、强壮的翅膀不再是翼兽的标志性特点。春秋至汉晋时期,翼兽在中国开始大量出现,中国的翼兽更是融入了本地特色,尤其是双翼的装饰化、符号化意味更加明显。而且自始至终,翼兽在中国神兽图像中并未占据主流,可见,飞翼并非中国神兽的标配。
在古代中国思维中,飞行升天不一定需要翅膀,翅膀与神性也没有必然关系。外来翼兽母题的传入,并未取代中国本地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是逐步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探索翼兽造型的源头,关键在飞翼,通过梳理欧亚大陆翼兽飞翼的造型演变,可以发现中国翼兽是在春秋中晚期以后受到西方造型艺术的显著影响。本文将溯源而上,探寻翼兽飞翼造型的起源和传播,最终探讨这种造型艺术传播到中国后改造熔铸和重塑新质的问题。
一、源头:本土还是西来
目前,学界认为中国境内最早的疑似翼兽的动物造型共五件,时代为殷末周初。这些动物造型与西亚的翼兽有较大差距,具有中国独特的风格。由于学界对这几件动物造型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仅从几个角度谈谈它们的造型特征。
先来看宝鸡石鼓山M4出土的两件“牺尊”,其中M4:212体型较大(下页图1:1),M4:214体型较小,二者形制十分接近。这种“神兽”混合了麂(1)雄性麂的角顶端向内卷,角下部至少有一半被毛皮包裹,角基在脸部形成纵向的突起,与该器物表现的动物形象比较接近。因此我认为其头部、躯干更接近鹿科动物麂。、凤、猫科动物和龙等多种动物造型。其中,这两件器物与张家坡M163出土的铜尊一样,在腹部靠下的位置有一对鱼鳍状突起。罗泰和郭静云将这对鱼鳍状突起视为翅膀,因此认为中国早在殷末周初就已出现翼兽。但从生长位置、造型等方面来看,尚不能确定它们就是翅膀。这两对突起安置于神兽的下腹部,而不论是西亚的翼兽还是战国两汉翼兽,或生于肩,或生于背,均未见腹部生翼者。腹部生翼并不符合鸟类和走兽的生理结构,翼兽虽是想象的产物,但作为鸟翼与走兽形象的合体,翼兽双翼的生长要大致模仿两者的生理结构,腹部生翼显然与现实世界的动物格格不入。此外,从造型来看,这对类似鲨鱼鳍状的突起很难断定为鸟翼。除视作鸟翼外,结合器物身上的鳞片状纹饰和蛇纹进行推测,这对突起还可能模仿自鱼鳍,或者蟒退化的后肢(2)不少蟒在泄殖腔孔两侧尚保留爪状后肢残余,例如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东方沙蟒就有后肢残余。蟒的后肢残余略呈爪状,从侧面看与器物中的突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也很难排除这对突起模仿蟒退化后肢的可能性(感谢陈之旸先生提供相关资料)。。

1.宝鸡石鼓山牺尊M4:212;2.苏萨封泥;3.乌尔印章;4.米坦尼印章;5.亚述王印章;6.尼姆鲁德宁胡尔萨格神庙浮雕;7.希腊双耳细颈瓶浮雕;8.科林斯陶瓶画;9.奥林匹亚陶瓶画;10.萨摩斯岛陶瓶画;11.库班斯基泰银镜;12.南俄斯基泰黄金饰片;13.南俄斯基泰黄金饰片;14.南俄斯基泰杆头饰;15.阿姆河宝藏黄金臂环;16.巴泽雷克一号墓马鞍毛毡;17.巴泽雷克一号墓马鞍毛毡;18.西西伯利亚黄金牌饰;19.萨尔马提亚黄金圆盘;20.巴克特里亚金头饰。图1 中国早期翼兽飞翼与西亚、希腊和欧亚草原翼兽飞翼对比
M4:212融合了麂和凤的形象,其主体为麂,但身体上装饰有以凤鸟为主体的纹饰,其中“鹿与凤同首。凤鸟身躯盘曲于牺尊前肩胛处,带状纹从角下延续到颈前。牺尊腹侧中部饰有三根宽大的长条状凤鸟羽翅,凤爪置于牺尊前肢,在凤鸟羽翅及爪足区域饰有数排羽鳞纹。牺尊后肢两侧的凤鸟,躯体肥硕,圆睛,勾喙,角状羽冠,羽翅下折至牺尊臀部”(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期。。这两件器物前身与后肢的凤鸟形象非常相近,将凤鸟形象融入到麂的前半身,尤其是麂凤共首,巧妙地借用麂的头部纹饰和眼睛,作为凤鸟的喙和眼。器物腹部的三根宽大羽翼在展示凤鸟形象的同时,又赋予了走兽飞翔的能力,似乎可以从这方面推测中国翼兽最初的形象。在这种意义上,虽然不能断定这两件器物腹部的突起就是翅膀,但中国最初的翼兽显然与西亚翼兽存在较大差异。郭静云概括翼兽的基本定义为“原本没有翅膀的动物,在基本保留其主要特征的同时,另加上一双翅膀”(4)郭静云、王鸿洋:《探讨中国翼兽问题之要点》,《中国美术研究》2019年第3期。。这种翼兽形象源于公元前四千纪后的两河流域,广泛影响了希腊和里海以东的广大区域,继而影响了中国。但在殷周时期的关中,中国人心目中的翼兽并非在走兽身上另加上一对翅膀,而是把鸟与兽融为一体,用纹饰的形式赋予走兽飞翔的能力。这类翼兽与春秋至两汉时期的形象全然不同。
另外,关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神坛底座,罗泰认为是一种翼龙(5)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6页。,而郭静云认为是一种“独角独翼马”形象。若将尾部上扬的部件视作翅膀,那这种翼兽显然与西亚和商周有较大区别,另成一个系统。因此,不论是商周还是三星堆的翼兽,两者的形制与西亚、春秋之后中国的翼兽形象截然不同,正如郭静云所说:“这些‘翼兽’造型相当独特,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大传统。”(6)郭静云:《从历史“世界化”的过程思考中国翼兽的萌生》,《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
我们现在对翼兽的定义诚如前引郭静云所言,均为走兽加上一对双翼。根据中外学界研究,这类形象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四千纪后半叶的两河流域,逐渐固定为翼狮和翼牛的形象,它们都是有明确意涵的具体之神。两河流域的翼兽形象影响了叙利亚北部和希腊的翼兽形象。从西亚出土的封泥(图1:2)、印章(图1:3、4、5)、神庙浮雕(图1:6)等可以发现,“翼兽的翅膀都强大,符合身体比例,是可以飞翔于天空的大翅膀”(7)郭静云、王鸿洋:《从西亚到东亚:翼兽形象之原义及本土化》,《民族艺术》2019年第3期。。当然在继承性和共性之外,希腊翼兽出现了自己的特点,例如从科林斯(8)John Boardman,Early Greek Vase Painting,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8, p.91.(图1:8)、奥林匹亚(9)Adrienne Mayor, Michael Heaney, “Griffins and Arimaspeans,”Folklore,104(1-2), 1993.(图1:9)、萨摩斯岛(10)John Boardman,Early Greek Vase Painting,p.163.(图1:10)、基克拉底群岛等地的黑绘陶上可以发现,希腊翼兽的双翼出现了新的样式,将初级飞羽由自然伸展的姿态改变为螺旋状内卷。除却飞翼造型外,古希腊狮鹫的脖子变得细长而区别于东方粗短的样式,四脚为狮爪而非东方常见的鹰爪,以及不见于西亚的单旋涡卷须,从头顶处延伸至颈部。(11)Oscar White Muscarella,“The Oriental Origin of Siren Cauldron Attachments,”Hesperia,31(4), 1962.另外,希腊翼兽虽然渊源自西亚,却失去了两河流域翼兽的内涵,它们不再是被崇拜的具体之神,而是成为信仰内涵不明的“狮鹫”怪物(12)郭静云、王鸿洋:《探讨中国翼兽问题之要点》,《中国美术研究》2019年第3期。。从外形到内涵,这种希腊样式的翼兽直接影响了斯基泰文化,而流动的草原民族恰好成为翼兽形象向东传播的中介。
二、东渐推动者:欧亚草原部落
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前半叶,欧亚草原上活动着若干伊朗语系的游牧族群。这些族群主要活动于黑海以北的草原和亚速海,以及更遥远的东欧森林草原和中北亚地带。他们以共同的物质文化——马具、武器和草原动物艺术风格著称,统称为斯基泰文化。(13)斯基泰文化是在一个大的领域内由各种部落组成的游牧文化。这些游牧部落形成了一个同质的群落,分散在一个广阔的地带,从叶尼塞盆地到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坡,跨越了50多度的经度。他们的统一取决于共同的生活,而不是共同的血统,因为种族的统一不可能存在于这么广阔的一片土地上。在古代,在许多地方,有说伊朗语的游牧民族,甚至有高加索血统的游牧民族,他们之间没有自然屏障。欧亚大草原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形成了共同的物质文化特征,如车马具、武器以及动物艺术风格。Boris Piotrovsky,“Early Cultures of the Lands of the Scythians,”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32(5), 1973-1974.虽然斯基泰族群的文化面貌相当多元,各区域文化特征有所不同,但狮鹫作为以动物艺术风格著称的斯基泰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母题,流行于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以及南西伯利亚、中亚、阿尔泰等地区。它们在共同的文化基质上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
在欧亚草原族群文化中,狮鹫流行于公元前6世纪南俄大草原的斯基泰文化。斯基泰文化虽然与亚述、巴比伦以及波斯有着不同程度的文化联系,但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以来与希腊联系更为紧密,它们保持着长达几个世纪的稳定关系。尤其是南俄大草原的斯基泰文化,受到希腊文化的浸润最深,最能体现希腊艺术特质。正如希腊艺术史家舒富德所言,斯基泰样式是古拙期的希腊艺术影响其四周诸民族后产生的一个结果。(14)V. A. Il’Inskaia,“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roblem of the Scythian Animal Style,”Soviet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21(1-2), 1982.希腊文化对南俄草原的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罗斯托夫采夫研究表明,希腊文化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渗透到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中,至公元前5世纪影响逐渐增强,公元前4世纪影响达至顶峰。(15)Michael Rostovtz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2, pp.64-69.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流行的艺术母题——狮鹫可以看出,希腊文化从一开始就对斯基泰文化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公元前7至前6世纪,斯基泰文化的狮鹫飞翼复制了希腊初级飞羽内卷的飞翼。例如库班地区的凯尔姆斯(Kelermes)墓中有一面镀银圆镜(16)Kenneth Lymer,“Griffins, Myths and Religion:A Review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Ancient Greece and the Early Nomads of Central Asia,”Art of the Orient,7, 2018.(图1:11),表现了初级飞羽微微内卷的希腊式翼兽鹰翼。公元前5世纪,狮鹫飞翼仍然照搬希腊样式,但大覆羽被省略,仅表现飞羽,例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公元前5世纪黑海北岸迈科普(Maikop)墓葬出土的黄金饰片(图1:12)。相较于希腊人,斯基泰人更偏向简洁化表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公元前5世纪迈科普的另一件黄金饰片上,狮鹫飞翼的飞羽被一条直线生硬地分割开(图1:13)。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公元前4世纪的斯基泰青铜杆头饰上,狮鹫飞翼简化为两条粗细一致的弯弓状,初级飞羽内卷,希腊式螺旋状的纵向排列变为重叠的横向排列,极具装饰主义倾向(图1:14)。
欧亚草原像一个巨大的海盆,斯基泰文化从南俄大草原一直延伸到阿尔泰山脉的斜坡。公元前5至前3世纪前半叶,在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盆地至阿尔泰一带的斯基泰文化影响区域,狮鹫及相关的动物搏斗母题颇为盛行。可见在与东方各国的艺术交流中,中亚游牧民族的斯基泰文化融入了近东的古代艺术。除了动物搏斗母题的艺术图像外,他们在技术方面借用了巴比伦、亚述和波斯传统技术——金属胎珐琅工艺(将彩釉烧附在金属表面)(17)尼姆鲁德(Nimrud)的新亚述人物品中,象牙也采用了几乎相同的工艺。同样的镶嵌技术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的土库曼斯坦、伊朗等地。Michael Rostovtz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p.57.,从而发展出了独特的斯基泰—南西伯利亚风格。公元前5世纪“阿姆河宝藏”(Oxus treasure)中的一件黄金臂环上的狮鹫(18)Guitty Azarpay,“Some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Artibus Asiae,22(4), 1959.被简化为一层覆羽和一层飞羽的双层结构(19)Ormonde Maddock Dalton,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With Other Objects From Ancient Persia And India,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905, p.28.(图1:15)。覆羽被分成不同的鳞状区域,其上施彩色珐琅的技术体现了近东艺术的直接影响。初级飞羽内卷的飞翼明显是希腊艺术影响下的斯基泰早期风格。
南西伯利亚狮鹫飞翼从一开始就有两大发展趋势,一种是自然主义倾向,其中西亚艺术是它的源泉,而希腊艺术为它提供了周期性补充;另一种是游牧民族的装饰艺术倾向。(20)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9年,第12页。从内涵上看,承袭自希腊的斯基泰狮鹫失去了两河流域的原义,其越来越模糊的含义使翼兽造像失去统一标准,驱使人们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文化对这种造型进行改造。由于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使牧民和猎手对材质和装饰工艺的追求远远大于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自然主义的艺术倾向逐步让位于以纯装饰性为目的的艺术倾向。公元前4至前3世纪前半叶,南西伯利亚斯基泰艺术向程式化的装饰艺术转变。在阿尔泰巴泽雷克一号墓马鞍毛毡上的狮鹫身上,初级飞羽内卷的飞翼有着类似花边的飞羽(图1:16)。同墓另一件马鞍毛毡的带角狮鹫飞翼融入了希腊植物——半棕榈叶(21)Guitty Azarpay, “Some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Artibus Asiae,22(4), 1959.的形象(图1:17)。这种用植物对动物形象进行纯粹的装饰性处理,既是斯基泰人对希腊艺术的借用,也是他们自身的创造。然而一旦动物形象服从于装饰的目的,就失去了所有的现实感。狮鹫的飞翼尽管保持着初级飞羽内卷的希腊样式,但纵向并列的初级飞羽以及植物化的处理失去了希腊样式螺旋式排列的特色。总之,斯基泰艺术自始至终都建立在对动物形体的装饰性改造上,而非对自然的观察上,这形成了翼兽飞翼以装饰性为主的斯基泰样式。
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南俄罗斯草原被有着与斯基泰人相同血统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侵入,斯基泰人被赶回了克里米亚老家。(22)萨尔马提亚人和斯基泰人一样,属于亚细亚民族的伊朗人。萨尔马提亚人最早的作家是塞乌多·西拉克,他和尼多斯的尤多克索斯在公元前338年听说过顿河的萨尔马提亚人。在波力比阿斯的时候,提到了公元前179年萨尔马提亚人为克里米亚斯基泰人的敌人。此后萨尔马提亚人的称谓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普遍使用,是在公元前2世纪,所有在南俄罗斯大草原上取代斯基泰人的不同部落的通用名称。斯基泰人是马上弓箭手,身穿宽袍,头戴萨迦帽。而萨马提亚人使用长矛,身披鳞甲或环甲,有时是铁甲,使用钢盔和马镫,铁甲重装骑兵。萨尔马提亚人在中亚某个地方发展起来,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虽然他们的艺术形式也以动物风格为主,但他们对程式化和几何图形装饰的偏好更甚于斯基泰人。(23)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6页。相较于斯基泰艺术较多使用金属胎珐琅工艺,萨尔马提亚艺术更偏重宝石镶嵌技术。宝石被嵌入铸造留下的凹槽中,制成美观的镶嵌器物。多彩的宝石镶嵌器物往往使人们愈加关注物体的色彩和光泽,从而降低形态学和解剖学的要求。因而物体造型一旦脱离原始内涵,就会逐步向装饰艺术发展。例如狮鹫搏斗场景中,狮鹫形象往往采取程式化的枝状方式,它的飞翼也被几何化。在一件公元前3世纪西西伯利亚的黄金牌饰上,一只正撕咬狼的狮鹫的飞翼简化为初级飞羽内卷的水滴形,覆羽嵌以绿松石(24)Kim, Moon-Ja, “A Study on the Scythian Buckle,”Journal of Fashion Business,10 (6), 2006.(图1:18)。这种几何化的水滴形飞翼除了内卷的初级飞羽保留了希腊样式外,与鹰类飞翼相去甚远,现实感已荡然无存。这很可能与宝石嵌金属工艺直接相关。萨尔马提亚人的黄金圆盘(公元前3至前1世纪)中周边表现的四只猫科动物,四肢和躯干几乎填满了水滴状的珐琅(25)Ann Farkas,“Sarmatian Roundels and Sarmatian Art,”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8, 1973.(图1:19)。多色宝石镶嵌工艺的盛行使萨尔马提亚艺术的狮鹫飞翼失去了自然主义的写实特征,变为以纯装饰为目的的符号化产物。
总之,斯基泰、萨尔马提亚艺术的狮鹫飞翼基本保留了初级飞羽内卷的希腊样式,并在希腊样式基础上进行了或多或少的程式化处理。这主要是因为金属镶嵌珐琅、宝石工艺盛行,使得造型的法则并不来源于自然,而是服从于装饰的需要。由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在斯基泰艺术中式微,至萨尔马提亚艺术中则不复存在。如果说斯基泰艺术还保留着西方自然主义的基因,那么萨尔马提亚艺术本质上是装饰性的。尤其是在萨尔马提亚艺术中,翼兽飞翼经程式化的处理后变成了水滴状,明显流露出东方装饰主义的痕迹,从而构成萨尔马提亚独特的动物风格。萨尔马提亚动物风格对邻近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主要向东传播,影响中亚、中国。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大月氏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即今阿富汗北部发现的黄金冢出土了一件金头饰,一人双手握住两侧的带角翼龙,翼龙飞翼作水滴状,覆羽和飞羽镶嵌绿松石,与萨尔马提亚翼兽飞翼如出一辙(图1:20)。不少学者将萨尔马提亚人与大月氏视为同一民族(26)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第5页。,也有学者认为大月氏是与斯基泰—萨尔马提亚人有密切关系的吐火罗人。(27)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8页。我们从大月氏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黄金冢”出土的万件金器中,可以看出萨尔马提亚与大月氏之间的亲缘关系。总之,从希腊到斯基泰再到萨尔马提亚,翼兽从造型到内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果说希腊还残存着两河流域翼兽的一丝神性,那么从斯基泰到萨尔马提亚,翼兽最终失去神性的原意,转变为“内涵不明的怪物”。从造型上也可以清晰发现这种转变,相较草原族群,希腊的翼兽更为“写实”,自然主义的特点明显,而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的装饰主义风格更为突出。内涵模糊的翼兽也失去了造像的统一标准,巨大强壮的飞翼不再是标配,装饰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取代了自然主义的风格。因此,在从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中,翼兽从内涵到外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内涵的模糊使翼兽造型相对其源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融入了本地的文化特色和符号。这种传播和变化最终也影响了中国,翼兽在中国完成了最终的在地化。
三、仿制与创造:中国
公元前7世纪末,原本活动于欧亚草原西端的南俄斯基泰人不断向东扩展,他们的足迹远达南西伯利亚。欧亚草原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在这一时期连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在整个欧亚大草原,每个地理区域内部都形成了彼此关系密切、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合体。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我国春秋中期,北方草原地区先后进入游牧时期。正是由于欧亚草原畅通无阻的地理优势,以及部落内部之间天然的经济文化联系,斯基泰文化向东影响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斯基泰风格三要素——武器、马具和动物装饰出现在河北北部以及太行山以西的北方地区,包括山西和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甘肃、宁夏和新疆。(28)Emma C. Bunker,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The Eugene V. Thaw and Other Notable New York Collections,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9-24.在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下,春秋中期我国长城沿线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动物装饰艺术的题材和表现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翼兽正是在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文化东传的背景下出现的。春秋早期素命镈钮上出现了双翼龙噬兽的形象(2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9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9页。(图2:1)。

1.素命镈;2.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莲鹤方壶;3.鄬子倗簋;4.新疆新源县71团鱼塘墓地翼虎铜圈;5.山西侯马陶模;6.中山王墓方壶;7.中山王墓错金银神兽;8.大都会博物馆藏铜翼虎;9.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金冠饰;10.汉长安武库遗址玉牌饰;11.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玉辟邪;12.陕西宝鸡北郊汉墓玉辟邪;13.滇文化石寨山7号墓银带扣;14.河南南阳宗资墓石翼兽;15.河南方城东汉画像石;16.成都东汉六一一墓陶座;17.四川郫县东汉画像石墓。图2 先秦汉晋时期中国翼兽飞翼
两龙两兽均生出翼,其中两龙飞翼出自肩部,形态简化,呈镰刀状,翼尖上卷。李零发现,春秋中期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器腹四隅的下方还各饰爬兽……背树双翼,翼尖朝后。其造型比较简率,缺乏细部描写”(30)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2页。(图2:2)。孙机发现,“淅川出土的春秋晚期之鄬子倗簋的龙形耳上的翼置于腹部”(31)吕章申主编:《国博课堂(2011-20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图2:3),飞翼呈“S”形,初级飞羽内卷,翼尖朝前(32)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0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9页。。稍有不同的是,这里用两条并列的弧线刻划出上卷飞羽,与巴泽雷克和图克廷(Tuektin)出土的斯基泰翼兽飞翼相似。另外,郧县乔家院M4:10铜盏盖顶有四条透雕镂空夔龙绕成的圆捉手(33)黄凤春、黄旭初:《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翅膀生于背部,形态呈“S”形,翼尖朝上,形态与鄬子倗簋接近。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最早的翼兽不全然同于西方,是程式化的斯基泰样式飞翼与中原造型元素龙的结合体。翼龙的飞翼生长于背部,甚至腹部,不同于西方翼兽羽翼从肩部生出的特征。而且飞翼明显变小,覆羽和结构特征多被省略。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龙腾云驾雾、遨翔天地并不依靠飞翼的扇动。而西亚和希腊的翼兽全凭羽翼飞翔,故有着巨大强壮的飞翼。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下不同的设计意匠、审美趣味和神话背景,中国工匠在借用外来图像时,对斯基泰翼兽的飞翼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
公元前4至前3世纪,匈奴凭借灵活的骑兵和高超的骑射技术,成为足以同中原诸侯国抗衡的强大力量。他们与燕、赵、秦等国之间不仅战争频发,而且商贸联系更加密切。匈奴人以牛马羊等畜产或他处得来的珍奇异物,交换中原的粮食、纺织品和各种工艺品。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一件鹿形格里芬,这种长着钩喙状嘴,头顶若干鹰头的大角格里芬(34)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第12期。与巴泽雷克2号墓男性墓主的纹身图像(35)John F. Haskins,“China and the Altai,”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2, 1988.如出一辙。另外,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的中国铜镜、丝绸等物也为双方的商贸往来提供了实物证据。我们知道匈奴的疆域从漠南河套和阴山一直延伸到鄂尔浑河(Orkhon)流域的德贝加尔(Transbaikal),西与阿尔泰地区为邻。斯基泰文化进入长城以北地区很可能主要通过匈奴民族。除了早期的贸易联系外,以匈奴为首的北方胡人部落联盟时常侵扰中国北方边疆。公元前4世纪,“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36)《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5页。。中国北方边地也不得不仿效胡人的骑兵,故有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在汉人与北方胡人持续不断的战争中,匈奴充当了斯基泰和中国北方汉人之间的中间人,并提供了中国和南西伯利亚、阿尔泰之间的间接联系。
战国时期,长城以北地带受到南西伯利亚—阿尔泰的斯基泰艺术的直接影响,翼兽飞翼具有浓厚的南西伯利亚—阿尔泰风格。在我国北方发现的匈奴墓葬中,翼兽飞翼复制了斯基泰艺术。新疆新源县71团鱼塘墓地出土的翼虎铜圈,飞翼由一层覆羽和一层飞羽组成,初级飞羽内卷,翼尖朝前,为典型的斯基泰样式(图2:4)。新疆乌鲁木齐阿拉沟战国时期匈奴墓出土两枚圆形金牌,翼虎的翅膀表现为内卷的初级飞羽(3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371、163页。。这也暗示出斯基泰艺术很可能通过匈奴从南西伯利亚绕道天山南北传入我国境内。实际上,除了长城以北地带的匈奴墓外,我们很少发现汉人完全照搬斯基泰翼兽飞翼样式的迹象。中国的工匠往往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加以改造和重塑。除随意处理飞翼的生长位置外,飞翼本身也被倒置。山西侯马的陶模和陶范上的翼龙,鹰翼不仅倒置,而且覆羽呈横向并列,不同于西方的纵向排列(3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图2:5)。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春秋时期翼兽飞翼的新创造。中国工匠不仅对外来艺术母题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还创造出全然不同于西方的样式。战国时期翼兽本土样式飞翼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呈“Y”形,从背部生出,飞羽分叉为两片,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方壶上攀爬的翼龙飞翼(3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9卷,第157页。(图2:6)、四川什邡城关墓葬铜矛的翼虎飞翼(4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什邡市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此形制并非来源于鸟类的飞翼,更像是艺术上的夸张。另一类型则是翼尖朝后,最内侧飞羽朝前的飞翼,羽毛为多层垂鳞状,紧贴于身后,且有外卷的初级飞羽,如中山王墓错金银神兽(41)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9卷,第74页。(图2:7)和大都会博物馆所藏铜翼虎(图2:8)。此类飞翼倒是不见于西方,而与春秋晚期太原金胜村赵卿墓鸟尊(4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太原晋国赵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5页。双翼相似。也就是说,这种翼尖朝前、紧贴于体的翅膀并非鹰翼,很可能是中国人对鸟类翅膀的艺术想象,有中国自身的传统。
东周时期欧亚草原斯基泰游牧民族与我国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联系密切,故长城以北少数民族墓中的翼兽出现了斯基泰南西伯利亚—阿尔泰风格的飞翼。长城以南地区由于在中原文化直接控制和影响之下,完全照搬斯基泰翼兽飞翼的现象极为罕见,本土化的想象多过改造。翼兽出现了翼尖朝后、最内侧飞羽朝前的飞翼,成为东周时期独具特色的中国样式。
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欧亚草原西端的斯基泰人被萨尔马提亚人排挤到克里米亚,萨尔马提亚人征服了大部分生活在欧亚草原西端的斯基泰部落,东部的一支大月氏人势力达到敦煌与祁连山之间一带。公元前3世纪末至前2世纪,匈奴统一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草原帝国。大月氏人在匈奴的打击下被迫西迁至现在的阿富汗一带。(43)《汉书·西域传上》:“老上单于杀月支,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廷。”《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1页。一方面,匈奴人向文明程度更高的萨尔马提亚文化学习,他们的重型骑兵装备和训练模式就源自萨尔马提亚的阿兰人。战国时期的中国人,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从中亚邻居匈奴人那里借鉴了头戴铁兜鍪、身披鱼鳞甲等的重型铠甲装备。萨尔马提亚文化通过匈奴人渗透到中原。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和亲、贡赐或劫掠,匈奴与中原的联系愈加紧密。相较于前期的斯基泰文化,萨尔马提亚文化通过匈奴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影响。战国晚期流行于长城以北地区的动物纹腰带和马具的饰板,到西汉中期流传至中原及南方地区。事实上,翼兽飞翼的形态变化与北方草原动物纹在西汉中期深入中原密切相关。西汉初期翼兽飞翼延续了东周时期样式,自武帝以后,翼兽飞翼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一方面与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畅通,东西方文化交流愈加频繁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外文化频繁接触中,中国艺术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内涵方面在外来艺术基础上改造的结果。
如果说东周至汉初的翼兽飞翼更多的是富有想象的色彩,那么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翼兽飞翼则是在外来因素基础上的改造。这一时期翼兽飞翼的生长部位由过去的以背部为主转至肩部,东周时期充满幻想性的“Y”形飞翼消失不见,还出现了一种类似于萨尔马提亚艺术水滴形状的飞翼。例如,哈萨克斯坦东南部阿拉木图地区发现的一件西汉晚期的金冠饰,翼龙作为羽人的坐骑,飞翼被几何化为水滴状,初级飞羽微微内卷 (图2:9)。与此同时,中国工匠对外来艺术母题也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中国翼兽飞翼偏小,翼尖未超出背部,如汉长安武库遗址出土的西汉晚期带翼独角山羊(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年第4期。(图2:10)。除了细节方面的改造外,西汉中期至东汉,翼兽翅膀融入了云纹装饰,不仅形象上与东周时期翼兽翅膀有所区别,更是将传统艺术元素融入其中,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样式。翼兽飞翼添加了云纹的装饰,造型方面主要表现为两大类。
一类是勾云型双翼,羽翼由一层覆羽和一层飞羽构成,羽纹重叠呈条带勾云纹状。实际上,此类型飞翼是在斯基泰南西伯利亚样式基础上,在每片羽毛末端增加了勾云纹。例如陕西省咸阳市新庄村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的玉辟邪(图2:11),肩生双翼,翼由三条并列的飞羽和覆羽构成,初级飞羽内卷,与斯基泰南西伯利亚翼兽飞翼相近。不同的是,玉辟邪飞翼紧贴于身,每片羽毛末端饰以勾云纹,这显然吸收了汉代云纹的本土元素,是在外来因素基础上进行的改造。东汉时期,此类型翼兽飞翼不仅羽翼根部简化为一个涡状云纹,末端的飞羽也变成了长长的云带状,向外卷,穿越身体长达后腿,如陕西宝鸡北郊汉墓所出玉辟邪双翼(45)刘云辉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1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171页。(图2:12)。中国人热衷于表现较长的初级飞羽,从战国时期(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公元前4至前3世纪铜翼虎)初见端倪。东汉翼兽飞翼的云带状初级飞羽可能是对东周翼兽初级飞羽外卷翅膀的继承和发展。
另一类飞翼为尖翼型,飞羽聚合成尖状,翅膀呈一个弧边三角形。这种类型的飞翼与萨尔马提亚艺术翼兽飞翼相似,但有时初级飞羽内卷的希腊特征不太明显,体现了水滴形飞翼的中国化,如滇文化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西汉中期翼虎纹银带扣(46)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图2:13)。这类翼型也常见于汉代羽人形象中。东汉时期,翼兽羽翼根部出现了涡卷云纹,如河南南阳宗资墓前石翼兽(图2:14)、河南孟津老城乡油坊村出土石兽(47)林通雁主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第3卷,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3、24页。、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的石天禄承盘(48)韩维龙、李全立、史磊:《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4期。等。云纹的融入使翼兽飞翼增添了中国艺术独有的灵动之气,体现汉代艺术以线造型的流动感。这与中国艺术重线轻色、重意轻形的传统观念密不可分。中国线条以波曲表现柔美,以平直表达劲力,河南方城东汉画像石(49)常任侠主编:《中国美术全集19 绘画编 画像石画像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37页。(图2:15)上的翼兽翅膀,平直有力的线条就使翅膀富有劲力。
郭静云指出“先秦时期翼龙造型并不多见,华北地区多于华南,而中山王墓多于其他华北地区”(50)郭静云、王鸿洋:《从西亚到东亚:翼兽形象之原义及本土化》,《民族艺术》2019年第3期。,与北方草原族群交流频繁的华北地区,尤其是中山国最早出现斯基泰羽翼式样的翼兽,但这些翼龙除了多了飞翼,其他特征与无翼龙并没有多少区别。到了汉代,翼兽形象大量出现,但“有翼仙兽和无翼仙兽的形象意义基本一致,带翅膀并不是仙兽必有的特征”(51)郭静云、王鸿洋:《汉代有翼仙兽:从多样形像到新创典范》,《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2期。。从西亚、希腊到斯基泰、萨尔马提亚,最终东传至中国,在经历漫长的文化传播后,这种“内在信仰模糊”的形象已完全失去了西亚翼兽的最初内涵和信仰意义。中国的工匠并不知晓这些翼兽的神性,也就不存在造像禁忌,他们把斯基泰翼兽与中国传统的神兽形象相结合,塑造了中国风格的翼兽,这就是对翼兽形式模仿后的再创造。
飞翼最能体现翼兽模仿—创造过程中的演进。两汉基本完成了对外来图像的中国化改造,使翼兽羽翼表现出中国艺术的美学特点。以线条表达对象的生命力,是中国人重主观表达而非客观实体的体现,因此传神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欲传神,就不能再全部纯写实地描画,而须抓住几个特点。正是因为画工们“用抽象的笔墨把捉物象骨气,写出物的内部生命”(52)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01页。,汉代翼兽飞翼多有灵动之感。成都六一一所东汉墓出土陶座上的翼兽,流动的线条表现出飞翼迎风展开之势(53)四川省博物馆藏。(图2:16)。透过四川郫县东汉画像石墓(54)常任侠主编:《中国美术全集19 绘画编 画像石画像砖》,第76页。(图2:17)、陕西绥德东汉画像石的翼龙、翼虎形象,我们均能感受到这些翼兽羽翼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如果说希腊艺术是自然主义风格与主观表达的有机结合,那么中国艺术则体现了东方艺术重视主观表达的传统。此外,云纹是中国艺术最重要的艺术母题,尤其是在秦汉时期。秦汉神仙思想盛行,神仙往往肩生双翼,腾云驾雾。东汉王充在《论衡·无形》中记载仙人生翼、乘云羽化的画面:“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55)刘盼遂集解:《论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32页。东汉画像石墓中屡见肩生羽翼的西王母或东王公,以及伴随于他们左右的羽人。由于汉人对羽化升仙的想象,带有羽翼的神兽也拥有超自然力量,升降自如,遨游于缥缈的云气之间。如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以及尉犁县营盘遗址出土的“登高明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锦等画面中,有翼神兽穿梭于流动起伏的云气之中,成为祥瑞的化身。可见汉代艺术对翼兽飞翼的中国化改造离不开当时风气和神仙思想的传播。六朝时期翼兽飞翼基本延续了汉代翼兽飞翼造型,其云纹化倾向更为显著,飘扬的云带成为新的造型样式。
结 语
中国虽然在商周时期出现了类似翼兽的造型,但这些造型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翼兽不同,也与春秋之后的中国翼兽造型差别较大,我们不能仅仅把它们视作中国翼兽的源头,还需要到域外寻找中国翼兽的来源。学界公认翼兽造型起源于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翼兽具有明确的内涵,是美索不达米亚先民崇拜的具体神明。翼兽的飞翼具有实际的功用,神兽飞翔必须借助飞翼。因此,包括两河流域在内的西亚翼兽生有强大的飞翼,飞翼生长部位更接近鸟类的身体结构,即一般生于肩部。两河流域翼兽母题传播到希腊后,翼兽逐渐成为内涵模糊的怪兽“格里芬”,希腊翼兽的翅膀出现了自己的特点:翼尖朝前,初级飞羽内卷,但希腊翼兽依然保留着较为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翅膀生于肩部并且大而强壮,羽毛细节丰富。希腊形式翼兽直接影响了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尤其是其翅膀的造型在斯基泰艺术中十分普遍。一方面由于神明内涵的消失,再加上漫长岁月的流逝,翼兽母题在欧亚大陆上被接触、模仿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已不清楚翼兽最初的精神内核,而是把该母题融入本地文化中,这在萨尔马提亚和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装饰主义风格替代了自然主义,翅膀不再是飞翔的必备工具,短小简洁的翅膀大量出现。中国翼兽在吸收斯基泰艺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不论是用传统的龙、虎代替狮鹫,还是翅膀形态、生长位置的变化,都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翅膀形制方面,中国翼兽形态多样,除了斯基泰式飞翼外,“Y”形翼、云纹的大量使用都是中国对飞翼的新理解和再创造。当然我们要看到,翼兽在先秦时期并不多见,中国神兽不凭借翅膀就可以升天,不论是有翼还是无翼的神兽均可以起到辟邪、导引的作用。由此可见,飞翼并非中国神兽的标准配置。再加上形态多样的飞翼和造型,可见在先秦、秦汉时期,翼兽尚未形成外在典范的形式(56)郭静云、王鸿洋:《汉代有翼仙兽:从多样形像到新创典范》,《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2期。,没有固定的内涵,并非中国人信仰的传统神灵。这也为我们确认翼兽属于外来母题的观点提供了逻辑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