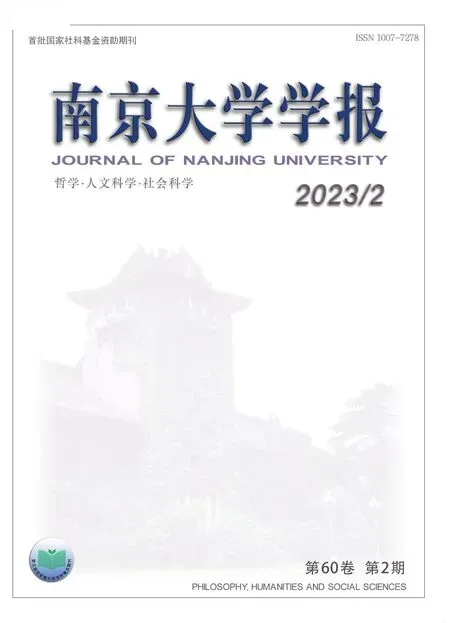青铜器纹样研究的两种视野与“关系美学”的建构
黄厚明
一、问题与方法: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的回顾及反思
商周青铜器纹样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论域,也是20世纪美学与艺术史研究的风向标。20世纪上半期,伴随着艺术史在西方的学科化与全球化运动,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先后经历了汉学与艺术史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脱胎于美学的艺术史与美学之间也处在复杂的纠缠之中。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美学和艺术史皆将艺术的形式问题与人的审美活动联系在一起,虽然它们皆以康德艺术哲学为认识论前提,但由于不同的目的论和方法论,两者逐渐从混融走向分离。这种面相与格局不免将一些美学问题带入艺术史研究领域,从而共同形塑了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范式。
20世纪初,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持续流失国外,商周青铜器纹样遂成为西方汉学关注与研究的重点。20世纪20年代之前,其研究还大致处在基础性的资料整理与图录出版阶段。进入30年代,相关研究日趋专业化,艺术史作为一股新势力介入到汉学阵营中。由于风格分析与汉学研究在方法上的显著差异,双方一度处于水火不容的对峙局面。(1)John A.Pope,“Sinology or Art History: Notes on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t,”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0(3/4), 1947.20世纪下半期,随着汉学和艺术史从冲突走向融合,西方学界对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步入新阶段。此时期高水准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如《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礼器》(2)Robert W. Bagley,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Ancinent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1,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3)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 第二卷 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赛克勒收藏的西周青铜礼器》(4)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Ancinent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2,Washington D.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赛克勒收藏的东周青铜礼器》(5)Jenny So,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Ancinent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 Vol.3,New York: Harry Abrams Inc., 1995.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果皆是围绕西方博物馆藏品而展开的,这凸显出西方学界在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领域固有的限制与不足。
与西方兴趣点和研究主旨不同,国内学界对商周青铜器纹样的研究一直保持着对考古出土材料的关注与探究。不过,受早期科学发掘材料以及对传世青铜器断代、编年的现实任务的限制,早期的研究者如郭沫若、容庚、陈梦家等人皆对传世青铜器纹样予以特别的关注。其中,郭沫若还创造性地提出“彝器形象学”概念,以期为青铜器纹样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序说——彝器形象学试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东京:文求堂书店,1934年,第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田野考古的广泛开展与考古学知识的持续增长,国内学界对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进入新阶段,不仅在形式分析及分期问题上建立起基本的认知框架,对青铜器纹样的含义也进行了种种富有建设性的探索。然而,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也不免存在各种意见上的分歧与争议。究其大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抽象与具象孰早孰晚的问题,它源于纹样形式规律的讨论。二是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它关涉到纹样功能与内涵的探究。它们作为青铜器纹样研究的基本问题,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并延宕至今。
抽象与具象的早晚问题,最先由高本汉提出。他对归为殷式的1 285件传世青铜器纹样进行类型学分析,将其划分为A、B、C三组风格类型,其中,A组为写实性纹样,B组为抽象性纹样。高本汉总结出A组纹样早于B组纹样且两者相互排斥,从不共存于一器,因而推定原生性的写实纹样出现的时间早于次生性的抽象纹样。(7)Bernhard Karlgren,“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Antiquities,(9), 1937.与高本汉“写实先于抽象”的观点不同,艺术史家巴克霍夫、戴维森、罗樾等人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巴克霍夫是西方形式分析学派奠基人沃尔夫林的弟子,他套用其师沃尔夫林的风格史范畴,将商周青铜器划分为古风式、古典式、巴洛克式和新古典式等不同风格发展阶段,指出商周青铜器在不同时期总有一种型式占据主导地位。戴维森同样质疑高本汉纹样分类的合理性,指出其B组纹样实质包含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类型:一种如形成于早商的分解饕餮纹(B1),年代早于A组的连体饕餮纹(A2);一种如形成于西周初期的长尾鸟纹(B3),则由A组纹样发展演变而来,并在西周中后期成为青铜器流行的母题。(8)J. Leroy Davidson,“Notes on Karlgren’s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The Art Bulletin,22(3), 1940.相较于巴克霍夫与戴维森,罗樾对高本汉的质疑最激烈也最成功。他参照李济关于殷墟小屯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将殷墟青铜器纹样划分为五个连续的发展阶段。(9)Max Loehr,“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7), 1953.其分期结论与高本汉迥然不同:高本汉所谓原生性A组纹样,在罗樾那里仅属于最后两个阶段,而所谓次生型B组纹样则散见于罗樾所分的五个阶段中。尽管罗樾的分期同样遭到高本汉的批驳,但罗樾关于前两种型式应该居先的立论,随后不久被郑州、辉县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所证实,这为罗樾在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领域赢得了声名与地位。
受美学家苏珊·朗格“形式第一性”观点的影响,罗樾后来干脆直接否定写实性纹样的存在。他援引朗格的符号美学理论,指出商周青铜器纹样只是纯粹的形式图案,并不存在对现实世界的再现或模仿:“中国古代没有再现性艺术,只有赋予了艺术家情感的、可以称得上艺术的纯粹性装饰。”(10)Max Loehr,“The Fate of the Ornament in Chinese Art,”Archives of Asian Art,21, 1967/1968.鉴于罗樾在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其认为纹样作为纯粹装饰的观点一度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过,其形式论观点拥趸寥寥。对绝大多数学者而言,商周青铜器纹饰是富含意义的,只是具体到何种含义,学界对此仍然莫衷一是。(11)黄厚明:《探索与证伪:关于饕餮纹含义的几种学说》,《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年第1期。从方法论角度看,既往对青铜器纹样内涵的种种解读虽多具探索性与启发性,但都无法合理解释青铜器纹样的形式结构、风格变迁与信仰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故而从艺术史维度对纹样进行形式结构与风格分析,成为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艺术史视野中的商周青铜器纹样研究
既往对青铜器纹样的形式分析与风格分期,多着眼于单一母题的类型学考察,对母题与母题的结构关系及其历时性变迁缺乏必要的探究。然而,根据夏皮罗三个层次的风格理论(12)Meyer Schapiro,“Style,”Selected Papers in Thero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itist and Society,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94, p.54.,对单一母题的类型学分析只是风格研究的初级阶段,要想探究风格的表现品质,必须考察母题与母题之间的视觉结构关系。这是风格分析的关键所在。(13)方闻:《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学术定位及学科发展问题——答黄厚明、申云艳、邱忠鸣、彭慧萍同学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或许是风格分析传统的缺失,国内学界对商周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多从考古类型学入手,将青铜器纹样按照饕餮纹、龙纹、鸟纹等不同母题进行分类与分期,由此带来了一个学术上的盲区,即饕餮纹、龙纹与鸟纹在形式结构上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彼此之间有何视觉同构性?原因何在?有关这方面的思考,高本汉曾从形式相似性的角度,提出饕餮纹和龙纹同源的观点,并为此发明了一个专用名词——“龙形化饕餮纹”(14)Bernhard Karlgren,“Notes on the Grammar of Early Bronze Décor,”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23), 1951.。艾兰也注意到饕餮纹与龙纹在形态上的相似性,认为饕餮纹的面部可视作完全分开的两条龙纹。(15)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5、181页。与此看法相近,李零亦认为饕餮纹是商周龙纹的面部特写。(16)李零:《说龙,兼及饕餮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至于龙纹与鸟纹,其区分标准同样是含混不清的,如夔龙纹就有“龙身鸟首神”“龙鸟纹”“鸟喙龙”等不同称谓。(17)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 第二卷 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第128-132页;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第183页。鉴于商周青铜器纹样在视觉结构上的高度同构性,实有必要重新调整纹样的分类方法与研究视角,代之以一种结构化的眼光来分析纹样的形式结构及其风格变迁。
商代青铜文化一般分为早中晚三期。早商文化期大致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代表。此时期青铜器一改夏代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素面的做法,开始出现以抽象拟形为主调的装饰纹样。其主体纹样通常被视为饕餮纹,就形式结构而言,可分为一首双身连体型与一首多身连体型两种风格类型。一首双身连体型,两侧身部为左右对称的抽象龙纹或鸟纹(暂统称为龙鸟纹),两两相对并构成共同的面首(下页图1:1-2)。一首多身连体型,则是在一首双身连体型的基础上,在身部两侧另行配置抽象化的龙鸟纹(图1:3)。以上两种风格形态,其躯身、面首通常是相互勾连在一起的,彼此之间含混不清而缺乏明确的边界。此外,在饕餮纹左右两侧或上方,还出现少量龙鸟纹(图1:4-5),这是其后青铜器龙纹和鸟纹独立于饕餮纹图像系统的先声。

1.鼎,盘龙城;2.簋,盘龙城;3.尊,盘龙城;4.鼎,郑州张寨南街;5.尊,盘龙城;6.罍,安阳小屯M388。图1 商代早中期青铜器饕餮纹图像系统
中商文化期,大约从二里岗文化上层晚期到殷墟文化第一期,以河南安阳洹北商城遗址、小屯一期遗址、郑州小双桥遗址以及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为代表。该时期青铜器饕餮纹的形式结构变化不大,但出现以鸟羽形纹和雷纹作为形式元素以装饰饕餮纹的新风格,且线条亦由早期的粗犷而趋于细密和繁复(图1:6)。
晚商文化期即殷墟文化第二期到第四期,以安阳殷墟遗址为代表。这是青铜器纹样风格嬗变期,饕餮纹的形式结构与风格形态发生较大改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一首双身连体型仍在延续,但躯身与面首逐渐形成相对明确的界限,整体轮廓峻锐简洁,与雷纹地形成鲜明的视觉区隔,并且躯身呈现出逐渐简化与缩小的趋势(图2:1-2)。第二,一首多身分体型取代一首多身连体型成为流行样式,原先构成连体的龙纹或鸟纹从主体纹样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首双身连体型饕餮纹与两侧龙鸟纹的新组合(图2:3)。此现象表明龙纹和鸟纹不仅是构成饕餮纹的基本母题,也是青铜器饕餮纹图像志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提醒我们在分析饕餮纹形式结构时,不能简单地将两侧的龙纹或鸟纹撇出饕餮纹图像系统。第三,伴随着饕餮纹的分解、简化与重构,以独立浮雕形式出现的有首无身型饕餮纹开始流行,甚至出现可辨认的人面形五官面首(图2:4-5)。与此一致,附属的龙纹和鸟纹亦多有相对独立的表现(图2:6-7)。

1.司母戊鼎,妇好墓M5;2.妇好大方尊,妇好墓M5;3.卣,小屯M238;4.偶方彝,妇好墓M5;5.大禾方鼎,湖南宁乡;6.鼎,殷墟;7.偶方彝,妇好墓M5。图2 晚商青铜器饕餮纹图像系统
入周以后,青铜器纹样风格形态再次发生一系列嬗变,其中尤以饕餮纹和鸟纹变化最大。西周早期,有首无身型饕餮纹与龙纹或鸟纹的种种组合成为流行样式(下页图3:1-3)。其整体变化趋势是,居于中间的面首浮雕从大变小,逐渐收缩、简化,至西周中期趋于消失;与此相反,居于两侧的龙纹和鸟纹则逐渐增高变大,并最终取代日渐式微的面首浮雕而成为西周时期流行的装饰母题之一(图3:4)。从风格形态看,西周早期的鸟纹多趋于写实化和凤鸟化,与殷式鸟纹区别明显,通常以昂首引颈、身作长尾、头戴花冠为基本造型风格。受其影响,西周早期的饕餮纹与龙纹也呈现出明显的凤纹特征(图3:5-6)。值得一提的是,在既往对商周青铜器鸟纹的分期研究中,殷末周初通常被视为一个连续的风格发展阶段。(18)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第123-126页;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然而,仔细考查此时期鸟纹的材料来源,除了部分类型属于殷墟期或殷墟期余绪之外,绝大部分可以归为凤形鸟纹系列,并且这些凤鸟纹大多出自岐周及附近地区,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与族群文化色彩。

1.觚形尊,东京大学人研所资料;2.作宝用簋,西安贺家村;3.曲沃曲村M6243簋;4.父庚觯,上博;5.厚趠方鼎,上博;6.宝鸡茹家庄M2:2。图3 西周早期青铜器饕餮纹及其附属纹样
西周中期,虽然传统意义上的饕餮纹图式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纹样依然保留着原先的位格结构。彭裕商考察了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的演变脉络,指出流行于西周中晚期的窃曲纹是饕餮纹和所谓象鼻龙纹的变形,进而将窃曲纹分为饕餮窃曲纹与龙纹窃曲纹。(19)彭裕商:《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从其举列的窃曲纹型式结构看,大致沿用了侧身龙纹两两对称的构图格局,只是由于中间面纹以及两侧龙纹的简化而异于早先的饕餮纹图式(下页图4:1-2)。然而,取代饕餮纹位格的纹样并非只有窃曲纹,还有一种被容庚、王世民等人称为波纹或波曲纹的纹样(图4:3)。(20)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191 页。近年来,李零根据山西大河口西周中期墓霸伯山簋的综合研究,指认这类纹样应统一正名为山纹。(21)李零:《山纹考——说环带纹、波纹、波曲纹、波浪纹应正名为山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1期。有关“山纹”的说法,最早见于林巳奈夫著述,参见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 第二卷 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第360-363页。这为重新审视饕餮纹的形式流变与意义变迁提供了新的契机。由于青铜器饕餮纹的简化、变形与重构,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各种组合的龙纹与鸟纹成为青铜器常见的装饰主题(图4:4-5)。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龙纹和鸟纹数量和类型逐渐减少,且多饰于青铜乐礼器之上(图4:6)。至战国中晚期,商周青铜器纹样趋于全面式微,取而代之以宴乐、狩猎、采桑、水路攻战等更具生活气息的新主题。
在饕餮纹图像系统中,除了龙纹与鸟纹为基本构图元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纹样——日纹。日纹是商周青铜器纹样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母题,从早商二里冈期一直到春秋时期,日纹经常出现在青铜器的主要装饰部位,并与龙纹、鸟纹形成相对固定的配位关系(下页图5:1-2)。此外,龙纹和鸟纹常常以日纹的造型方式加以表现(图5:3-4),其相互替代和转化的形式结构暗示出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

1.簋,钟殷父簋,西周晚期;2.鼎,岐山北郭乡,西周中期;3.逑鼎,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晚期;4.逑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晚期;5.丰卣,扶风庄白村,西周中期;6.钟镈,战国早期,美国赛克勒博物馆。图4 西周中期及其后青铜器主体纹样

1.三联甗,妇好墓M5;2.方彝,西周中期,眉县李村;3.仲南父壶乙,西周中期,岐山董家村;4.壶,西周中期,扶风庄白村。图5 商周青铜器日纹与龙纹、鸟纹的关系
商周青铜器纹样演变轨迹表明,商代早中期的鸟纹多偏于抽象化,通常很难将它们与抽象的龙纹区分开来。或许是因为这一缘故,陈公柔、朱凤瀚等人皆认定青铜器鸟纹出现的时间是在商代晚期即殷墟中后期。(22)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9页。对此,周亚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青铜器鸟纹出现的时间应在商代中期。在其看来,商代中期的鸟纹不像商代晚期鸟纹那样有完整的身体造型,通常只是表现鸟的头部,以目纹、勾喙和头部轮廓线为基本构图元素。(23)周亚:《商代中期青铜器上的鸟纹》,《文物》1997年第2期。以此而观,构成早商青铜器饕餮纹的龙鸟纹同样属于这种鸟纹的原初形态,只是鸟的特征更多的是通过羽状纹样体现出来。与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鸟纹从抽象到具象的演变轨迹不同,西周青铜器饕餮纹则呈现出向几何抽象方向的转变。商周青铜器纹样先后两种完全相反的演化方向,表明抽象与具象的演进关系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美学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命题。
对此类问题的回答,同样关涉到形式与内容相互关系的讨论。艺术史家方闻曾对罗樾的纯形式论提出批评,认为其形式分析理论割裂了装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联系,因而陷入美学而不是艺术史范畴。方闻援引南朝颜延之关于三种“图载”的理论,指出青铜器纹样既表“图理”又示“图形”,因而不可能是纯粹的设计或作为纯粹形式的意义。(24)方闻、黄厚明、谈晟广:《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研究方法与途径》,《西北美术》2015年第1期。在方闻的一次学术访谈中,他再次指出:“非再现或‘抽象’艺术如果有美学效力的话,也不可能是任意和偶然的,而应源自服膺某些有价值的限制或源头。”(25)方闻、谢伯柯、何金俐:《问题与方法:中国艺术史研究答问(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年第3期。艾兰同样认为青铜器纹样“既不是纯粹的装饰,也不是完全的再现,跟神话一样,它影射现实,但不描绘现实”(26)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第161页。。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对罗樾的批评皆涉及“再现”“装饰”两大美学概念。在西方经典艺术文献中,“再现”通常是与艺术史“进步模式”联系在一起的。贡布里希关于视觉再现的错觉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学与艺术史界共同信奉的原则。然而,正如美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指出的那样,“再现”绝不是呈现某种客体形象并加以匹配这种简单的模式,而是取决于审美主体的意图模式:“将某物当作某物所再现的,或者我们如何再现某物,都是文化决定的问题。”(27)理查德·沃尔海姆:《艺术及其对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其将“再现”看成是审美主体制造视错觉的一种结果,倒不如将它看成是探索事物本质并建立相应文化反应的认知过程。
从视知觉角度看,人类早期知觉形象的建构,基本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制造视错觉效果,而是着重对含有再现属性的知觉形状及其大小、方位、空间、色彩等视觉元素进行智性建构(28)黄厚明:《知觉的回归与中国早期美术史的重构》,《美术研究》2018年第6期。,其所形成的诸如平衡律、正面律、比例律、重复律、节约律等造型法则,不仅存在于作为图形的绘画与作为图理的卦象之中,也体现在作为图识的字学之中。从绘画和卦象的角度看,原始装饰作为“图载”的综合形式,本身就离不开各种原始属性的再现技巧。过去对“装饰”的理解,通常被视为一种追求审美愉悦的视觉艺术。然而,这种看法实是一种泛文化观点,并不适宜用来解释商周青铜器的装饰传统。装饰艺术当然不排除审美愉悦的功能,但强调视觉的愉悦性并不意味着信仰与思想的缺席。在中国人心目中,图理、图识与图形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既是形式系统又是意义系统。这种形意同构关系,亦可从字学的层面再作阐释。东周就有“六书”之说,这是依据殷周字学的造型方式所作的分类名词。东汉班固对“六书”进行定义,将其分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与假借”六种类型。(2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2页。稍后的许慎则对“六书”的名称、次序及内涵作出新的解释。(30)其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作为六书名称及先后次序。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5-756页。从美学的立场看,“六书”不仅涉及抽象与具象、表形与表意等审美范畴,亦涉及通感与移形、比类与合意、指代与并置等各种艺术思维。
象形字是一种画图文字,属于一种象物以形、以形见意的造字形式。商代甲骨文与金文中的象形字,多以对象物的侧面轮廓形象作为字形结构,如虎、鸟、鹿等字,其中少数字形如龟字则兼具侧视与正视形象。这种情形与商周青铜器主体纹样的表现具有同构性,如龙纹和鸟纹多见侧视形象,且通常由左右对称的侧身龙纹构成正视的饕餮纹形象。这是古人“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在商周青铜器纹样中的反映。象事字不是象形而是象“事”或象“意”,它属于一种抽象的意符文字。象形字和象事字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视觉机制:象形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以具象为旨;象事字“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则以抽象为要。当然,两者仍存在共通之处。比如,不少象事字是在象形字基础上加入指示性意符组合而成的,这使得两者具有了视觉同构性。这种视觉逻辑思维再次提醒我们,在探究青铜器纹样的形式意义时,不能简单地将所谓的装饰与再现对立起来,否则就会陷入西方再现理论预设的认知误区。
不同于象形字与象事字,象意字则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表意的象形符号或指事符号进行“比类合义”,使表象、表事与表意同时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构建出象形字与象事字无法单独表达的意义符号。象声字则是在此基础上加入表音的符号组合,进而衍生出“同意相受”的转注字与“同音借代”的假借字。将音、形、意关联在一起,这是通感与移形、比类与合意在视觉艺术中的观念呈现。这对于理解饕餮纹的形式结构以及饕餮纹与龙纹、鸟纹的同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说,不少学者对殷墟中期以来饕餮纹出现的各种角纹多作具象化的理解,进而将饕餮纹解读为各种具体的动物形象。(31)Herrlee Glessner Creel,The Birth of China: A Surver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37, p.117; Florance Waterbury,Early Chinese Symbols and Literature: Vestiges and Speculations,New York: E. Weyhe, 1942.在杨晓能看来,这种汲取各种动物成分并加以变形的饕餮纹图像,旨在“发明一种或一套高度聚合性的图像,以概括和象征众多祖先和神灵(包括自然神),并获得所有使用青铜礼器的个人和实体的认可”(32)杨晓能:《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72页。。然而,“六书”的造型思维告诉我们,这是通感与移形、比类与合意在饕餮纹图像系统中的运用。艾兰注意到那些由饕餮纹而联想到的诸如牛、羊、鹿、虎等动物,事实上都是商人祭祀活动中用于祭祀的牺牲。(33)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第171页。从宗教思维发生学立场看,这种通感方式系由原始的交感巫术传统发展而来,旨在通过指示与比类、借代与并置的方式实现交互感应,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特定的宗教目的。
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解读商周青铜器纹样的意义,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诚如前述,商代及西周早期,青铜器最常见的纹样只有饕餮纹、龙纹与鸟纹三种,它们不仅占据青铜器的主要装饰部位,彼此之间亦形成一种等级化的形式结构关系。基于此,笔者尝试对商代青铜器纹样含义进行解读,将饕餮纹看成是商族祖神的象征。作此解释主要出于如下三点考量:第一,饕餮纹是人格神,这不仅体现在饕餮纹人面形的构图结构中,也存在于周人对商人污名化的话语模式里。(34)《左传·文公十八年》将“饕餮”归入“四凶”族之列,《吕氏春秋》《山海经》也有类似的记述。第二,鸟纹作为商族鸟祖的象征,不仅见于《诗经·商颂》与《史记·殷本纪》等早期文献记述中,在殷墟卜辞中也存在以鸟形直接指代商族祖神的视觉证据。(35)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第三,龙纹在商代青铜器纹样的位格结构中居于饕餮纹与鸟纹之间(36)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 第二卷 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第108页。,其神性高于鸟祖自然神而低于人格化的饕餮祖神。
然而,承认饕餮纹是商族祖神的象征,需要正视并回应如下问题:既然周革殷命的政权迭代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代祖先祭祀的合法性和可能性,那么,象征商族祖神的饕餮纹为何仍然延续于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之上?西周中期青铜器饕餮纹消失,与之同构的龙纹与鸟纹为何依然流行?西周凤鸟纹的兴起是否意味着新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些问题复杂难解,这里仅从研究思路与方法层面略作讨论。
对于青铜器饕餮纹在周初的流行,张光直曾从技术层面作出解释,认为周革殷命后继续任用殷代工匠铸造青铜礼器,从而使周初青铜器纹样不可避免地带有殷代流风。(37)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340页。这种解释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忽视了商族与周族在意识形态上的关联与分界。从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看,商人与周人祭祖活动在内涵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仅商族祭祀异姓部族的祖先,周人在祭祀本族祖先的同时也同样祭祀商王祖先。(38)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在这种背景下,青铜礼器上的饕餮纹作为商王朝信仰体系中天下共祖的象征,延续于周初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对于饕餮纹在西周中期趋于式微而变得难以辨认的原因,杨晓能认为这是通过抽象化的艺术形式淡化青铜器纹饰在使用者心目中的原有含义,以使人们忘却动物崇拜的习俗和商王朝对此信仰的权威性。(39)杨晓能:《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第372-373页。与此看法类似,罗泰亦认为西周中期青铜器纹样的“纯装饰”转型肯定淡化了最初的宗教含义。(40)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1页。然而,根据李零的最新研究,西周中期取代饕餮纹的所谓几何化纹样大多是以山纹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从周代青铜器铭文和先秦文献看,周代的山岳崇拜较之于殷代确实有了显著的提升(41)王晖:《论周代天神性质与山岳崇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这为山纹的流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意识形态背景。

余论:“关系美学”刍议
将商周青铜器纹样的含义置于其形式结构与风格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和阐释,这是艺术史研究对形式美学解构形式与内容同构关系的反拨与修正。然而,商周青铜器纹样的历史表明,其纹样的制作与使用对于审美主体而言显然只是一种或然性而非绝然性的选择。事实上,不论是商代还是周代,都存在不少素面的青铜礼器;即便是饰纹青铜器,构成其主体纹样的饕餮纹、龙纹、鸟纹与日纹也不都是同时出现的。鉴于这种或然性、含混性和多元性,学界以往对商周青铜器纹样意义的各种解读都只是一种理论假说。其准确与否,不仅要在商周青铜器主体纹样的脉络中获得合乎逻辑的理解,同时也要借助于青铜器次要纹样而获得完整的认知。与此同时,青铜器作为纹样存在的“家”,探讨纹样的含义亦须结合青铜器本身的功能、权力存在方式以及地方性传统作出连贯一致的解释。于我而言,从形式与内涵同构关系解读商周青铜器纹样,既是提供一种可供讨论的方案以便后来者充实并修正它,同时也希望从中国自身的材料出发建构本土性的知识体系与审美理论,以拓展、修正甚至颠覆来自西方文化实践的美学理论体系。
从上文的相关讨论可知,商周青铜器纹样既不是单纯的装饰,也不是现代再现意义上的写实形象。将装饰与再现截然二分的美学认知框架,不仅割裂了中国古代绘画、文字与八卦图像作为“图载”的同构关系,也与中国古代“六书”的造型思维背道而驰。作为西方美学理论的部分替代方案,笔者将中国古典美学视为一种“关系美学”。其“关系”的维度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类比象的象思维,它是天地之人通过仰观俯察、远取近求的关系建构以感通天地万物之变易。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分的形象理论,象思维把握的对象并非实体存在物,而是“唯变所适”的动态关联的“生生”之易。班固的“四象说”以及商周青铜器纹样繁复多变的比拟形态,正是这种独特艺术思维的多维表征。春秋战国以来,伴随着礼坏乐崩的社会变迁,青铜艺术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结构逐渐解体与重塑,青铜器审美主体也从之前的群体性、外向性更多地转向个体化与内省化。在此进程中,以类比象也朝比兴美学的方向转变。(45)张节末:《比兴美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9页。
第二,以数示象的作用机制,它为易象提供生成动力与演化方向。象数非以形式美为旨归,而是“以数示造化之本”。比如说,先秦两汉铜镜纹样乃至更早的黄河流域史前彩陶所流行各种等分的图案(46)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编:《必忠必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铜镜》,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程征:《“彩陶图画”与方圆意识》,《文艺研究》1994年第6期。,其均匀齐整的构图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罗樾所说的作为纯粹形式的设计。然而,诸如7等分、11等分、13等分这样的质数,其等分构图并不能以尺规进行直观的分割。其中涉及的无限分割原理以及“万世不竭”的理念,亦是先秦诸子讨论的一个哲学议题。(47)《庄子·天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21页。这种穷极造化的努力,用数学家刘徽为西汉《九章算术》作注的说法,就是“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
第三,以时位关系为等级秩序的空间美学与时间美学,这是中国关系美学的表征系统。先秦时代的宇宙论是基于时空关系的宇宙生成论(48)尸佼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佼撰、汪继培辑:《尸子》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页。《淮南子·齐俗训》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刘安编:《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2页。,这种动态关联的有机模式强调时空的变化与过程,与西方强调因果关系的目的论模式有着显著的区别。(49)郝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对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考》,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商周青铜器纹样尽管变化多端,纹样所处的位格结构却保持稳定。既往的研究对形式母题与形式母题的结构关系及其隐含的等级秩序关注不多。然而,这种位格空间具有浓厚的信仰意义与政治空间秩序,如西周“宅兹中国”说、东周以来的“夷夏”之辨、先秦秦汉“五岳四渎”的空间格局演变以及时空一体的阴阳五行学说,正是华夏空间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重要表征。
第四,以天地人三才作为关系美学建构的基本要素,天地之人通过“法天则地”而与天地万物化合为有机的整体。先秦时代,伴随着神力与王权的此消彼长,关系美学也呈现出从早期生命美学到诸子时代人生美学再到秦汉时代生活美学的逻辑进程。作为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战国以来在社会、文化与思想领域皆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诸如动物崇拜的生肖化、日用铜镜的审美化、历史人物故事的视觉化、国家祭祀与民间祭祀的等级化以及审美主体的底层化与个体化,它们作为全新的意识形态结构彻底改变了先秦时代的审美形态。与此同步,战国中后期青铜器纹样透露出来的浓重生活气息,与战国早期之前青铜器纹样抽象多变的面貌形成鲜明的反差,其所带来的改变共同开启了通往秦汉时代面向现实的生活美学的大门,华夏审美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