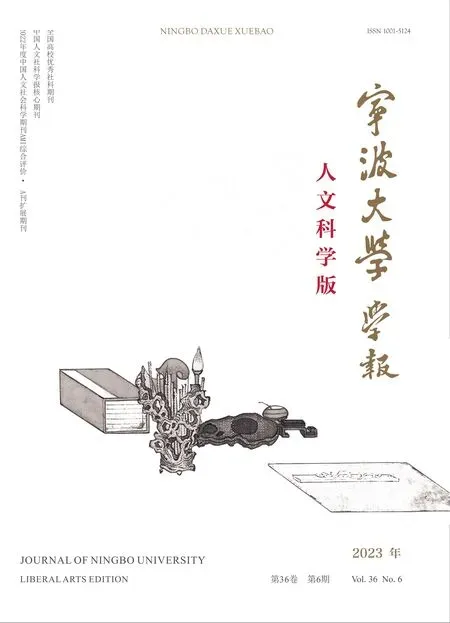鲁王使臣陈谦被杀一事考论
王浩淼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陈谦是鲁监国政权的一名总兵,曾率领部曲参与宁波抗清运动,大多数南明史籍均记载其在隆武二年(1646)曾奉鲁王命出使福建。《明季遗闻》记载陈谦在使闽过程中的身份为“鲁王使”,《小腆纪年》称“鲁使臣”,《所知录》为“奉(鲁)监国使”,《南明野史》作“奉鲁藩使”。另外《思文大纪》称呼裘兆锦、林必达为“鲁藩使臣”,《东南纪事》称呼柯夏卿等为“鲁王使臣”,均意为“奉鲁王之使”。本文承之,称陈谦为“鲁王使臣”(下文简称“鲁使”),非谓“鲁地之使”,相应地,福建使臣均以“唐使”相称。由于同时期鲁王监国于绍兴,从地域来源看鲁王使臣亦可作浙东使臣,又有《鲒埼亭集选辑》称陈谦为“越使”,以与“闽使”相对。
陈谦在使闽期间被唐王诛杀之事,使唐、鲁二藩政权间的关系进入紧张阶段,并成为唐王政权灭亡的前奏。学界并未重视陈谦使闽一事,仅徐晓望简略地考析了陈谦使闽的时间[1],并对唐、鲁二藩各自灭亡的原因稍有深究。针对唐王政权,蔡杰从黄道周的角度分析了忠臣在隆武政权的困境[2],徐晓望则认为士大夫与郑氏决裂的主要原因是士大夫内心不想与海商分享政权[1],此外他又分析了闽军失败的原因,包括闽军实力较差,及隆武帝制定的战略计划粗略等[3]。关于鲁监国政权失败的原因,顾诚认为与鲁王尚没有摆脱藩王沉迷酒色、处置不公等特点有关[4],韦祖辉在此基础上认为存在战略和军事部署失算、悍将跋扈等因素[5]。鲁使陈谦使闽及被杀之事关系着闽浙两地的政治权和话语权争夺,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考析陈谦使闽的真实性,继而探论南明史籍中的文本话语权。
一、陈谦被杀原因的两种说法与不足
隆武二年五月,浙东派遣使臣陈谦造闽,不料反为唐王所杀,究其缘由,各本叙说不一,其中以“不称臣”说和“挟功”说流传最广。
(一)“不称臣”说
该说认为唐王首先因为陈谦不称臣,抑或是鲁王给予唐王的信函开头不称陛下,而将陈谦打入地牢,继而在钱邦芑的建议下处死陈谦。
早在福建派遣刘中藻劝谕鲁王称臣时,浙东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以郑遵谦、黄宗羲为主,多倾意于闽浙相助,甚至希望鲁王能听从唐王的号召,黄宗羲尤为激烈,他反对鲁王拒却唐王诏谕的做法,在给熊汝霖的书信中指出:“夫神器流离,草创未有成绪。公何不引闽师为助,而分唐、分鲁自开瑕隙,议者以公为暗。”[6]137华廷献则从相对中立的角度痛斥闽浙相怨,借侯若孩之语感叹:“此时宜枕戈待旦,勠力一心。乃处累卵之危,而修笔舌之怨;忘敷天之愤,而操同室之戈,吾其济乎!”[7]321这些士人所撰写的文献多重视唐王,但又不可否定鲁王,于是在叙说鲁使陈谦被杀事时采取简写方式,省略其被杀原因,将罪责直指钱邦芑。如《闽事纪略》云:“御史钱邦芑劾其(指陈)外媾有状,逮下诏狱。郑芝龙力救,不听;寻杀之。”[8]42《海东逸史》称:“都督陈谦奉使至闽中,为御史钱邦芑所劾,被杀。”[9]4另外部分与鲁王关系较密的中下级官员在文集中则完全隐去陈谦的任何事迹,如黄宗羲所撰之《行朝录》等。
另一派以张国俊、陈函辉、熊汝霖、张名振等为代表,主张鲁王不接受来自福建的诏谕,力求独立以保证浙东人心不散。部分士人将闽浙对立矛头直指唐王,对“隆武独与鲁王为仇”极表愤慨。代表作如邹漪的《明季遗闻》,其云:
都督陈谦奉鲁使,与行人林垐至关。及关,趔趄未敢入,郑芝龙以书招之,乃入陛见。启函,称皇叔父而不称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议,皆下狱。芝龙疏救,不许……有镇将钱邦芑者,召对中旨,擢为监察御史,实出芝龙门下,而与隆武亲,最蒙信任。密启隆武:“陈谦为鲁心腹,与郑至交,不急除恐有内患。”或以告芝龙,芝龙谓刑所必经其门,临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内传片纸,别移谦斩之。[10]105
仕清较早的吴伟业以浙东为正统,其所撰之《鹿樵纪闻》虽集诸传闻,然其目的在于蔽鲁王之耻,同时强调“唐王败盟”的影响。与浙东遗臣不同的是,吴伟业将埋怨唐王的郑芝龙换成方国安,并称方国安杀害唐使陆清源是对唐王杀浙使的报复,甚至提到“鲁王恐闽中来讨,定议抽兵;使张国维西出,别遣余煌视师奖赏,故人心益涣”[11]57。《浙东纪略》称王之仁杀唐使陆清源起因是犒师不均,浙东分军是因为当时清军有南侵动作,为配合湖州义军,五月的西征正式施行,与陈谦无任何关系[12]21-23。《台湾外记》也认为陆清源被杀才是造成江上之师单弱的原因[13]87。可见《鹿樵纪闻》的记载是江浙传言中对闽浙败亡因素的主观看法。此后浙东人士往往采自此说,如顾炎武在《明季三朝野史》肯定了唐王过于注重“陛下”称呼以及钱邦芑破坏闽浙和好的机遇[14]33-34。
(二)“邀功”说
支持“邀功”说者以隆武政权遗臣为主,该说缘起隆武太常寺卿彭期生之子彭孙贻所撰的《靖海志》[15]10-11,受其影响,桐城人钱澄之也将该事件记录于《所知录》[16]16-17,在传抄过程中造成数处偏差,致使“不称臣”说最终演变为另一种说法。第一,《靖海志》是根据“不称臣”说详载鲁使陈谦在衢州逗留原因和钱邦芑弹劾陈谦的具体内容,而《所知录》直接舍弃了陈谦初次觐见唐王时因不称臣而下狱的过程。第二,《靖海志》记载陈谦久驻衢州是为了利用鲁王已封郑芝龙为靖虏侯这一事件来向唐王邀封,《所知录》更是夸大了陈谦的行为,他省略了彭著中的“郑芝龙”,认为陈谦在衢州首鼠两端的具体表现是自称已被鲁王封为靖虏侯,借此再向唐王邀封,此说完全违背彭著之意。第三,陈谦被杀的影响,《靖海志》直言郑氏兄弟与清朝洪承畴早有往来,借陈谦被杀一事径直北走,而钱澄之则将陈谦被杀一事作为郑氏与清军相通的开始,又将相通已久的说法作为某一假说而附于段末,称此说不过是郑芝龙“特以愚朝廷也”。査继佐在《罪惟录》又对此说加以总结和定性[17]420。可见《所知录》完全将陈谦之死归咎于陈谦自身,认为陈谦作为鲁王使臣不应首鼠两端,行挟制之术,其死不诬。
综上,两说侧重点不同,所阐述的目的也有差异。“不称臣”说的重点在于将造成闽浙矛盾的缘由直指唐王和钱邦芑,其中较为倾意于唐王的浙东士人则将闽浙不和归因于钱邦芑的唆使。有些士人将唐王政权灭亡也归咎于钱邦芑,如林时对在记载唐王令钱邦芑西行清路时,将钱“颐指郡邑,恐吓金钱”的行为定为唐王西行失败的主要原因[18]145。而“邀功”说指出陈谦在出使事件以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诸如闽浙不援助、福建失陷等其他相关事件中需要承担主要责任,钱邦芑需负次要责任。然而需注意的是,“邀功”说本就是“不称臣”说派生出的一个版本,因此陈谦被杀的实际过程应是两个版本的重叠,彭孙贻的记载相对客观。
然而针对唐王、钱邦芑密谋杀害鲁使陈谦的说法,清中叶的学者徐鼒率先质疑:
不曰杀都督陈谦,而曰杀鲁使臣何?绝晋、郑之交,结谭尚之怨,论者咎王之失大计也。顾鼒以为未尽然者。登极之书,浙中不拜;犒师之使,江上不归;衅隙已成,调停无术。且是时北兵日逼,闽、浙固莫能相救,其势亦何暇相仇哉!若芝龙,故国之心已如脱屣,即不杀谦,岂遂革面?彼归狱钱邦芑者,岂笃论乎?[19]598
陈谦使闽恰处清军南下之际,不管是唐王还是鲁王,都意识到民族危机将在不久爆发,双方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积极扩大破裂关系。当时唐王致力于拉拢浙东人士,如朱大典与方国安不相协,唐王劝谕“协心和气,共济时艰”[20]82,左都督杨鼎卿不尊鲁王号令,唐王云:“若鼎卿者,可谓忠尽能明大义者矣!朕与鲁王原无嫌疑,前付柯、曹二使答王书,或未之见乎!”[21]789因此唐王因重视称呼和陈谦的行为而轻易破坏闽浙关系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鲁使陈谦被杀一事还存在一系列文献未能解答的问题:第一,钱邦芑由郑氏所荐,而唐王在当时又极为倚重郑氏,纵使钱邦芑有心帮助唐王提高君主威势,但当涉及郑芝龙时,唐王也很难牺牲自己与郑氏的关系而诛杀一位与自己关系不大的鲁王使臣。第二,朱大典在弘光政权灭亡之际留守金华,曾劝鲁王监国,事后鲁王晋升他为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但朱大典“止遣其孙一朝,未尝发一兵至江上,而所遣戍卒亦未尝过严州一步,其意固有在也”[22]244。同时朱大典又劝进于唐王,唐王也授予他文渊阁大学士之衔,封婺安伯,“大典两受,并表谢”[17]404。面对朱大典“两受之”的行为,一些浙东人士将之视为闽浙相合的介使[23]9,也有人怀疑其有二心,而唐王仍将入闽通道寄希望于朱大典,当听闻清军攻克常山,诏谕朱大典、顾应勋入闽勤王[24]17。由此可见,朱大典持两端尚且被唐王所倚仗,陈谦仅仅因为挟封而被诛杀,似不能解。第三,陈谦使闽前后亦有鲁使入闽,如鲁王在拒却刘中藻诏谕后随即委派职方郎中柯夏卿、科臣曹惟才使闽,唐王“不用疏奏,止叙家人叔侄礼”[12]13,又赠予柯夏卿等闽官。唐王大学士黄鸣骏以陆清源之截而问罪于鲁王,自衢州向新安进军,鲁王又遣王绍美、沈綵南下示好,书函中鲁王自始至终没有自称臣,仅称唐王为皇叔父[22]58,为何唯独陈谦出使时事态就发生恶化。从陈谦不称臣或者书函中未称臣来看,不管是陈谦之错还是鲁王之错,唐王都没有私自惩处陈谦的必要。何况唐使多次入浙,鲁王疏奏中也没有屈尊之意,唐使陆清源甚至被鲁监国大臣所害,唐王尚未直接迁怒于浙人,此次却因为称呼之故诛杀鲁使陈谦,似不妥。第四,陈谦之死未打消鲁监国遣使入闽的顾虑。隆武二年五月,“唐、鲁颁诏之衅,使臣或被戕,(鲁)议遣一能者往”[19]616,兵部主事倪懋熹请行,至闽向唐王奏称:“方今闽强越弱,然无越则闽无所蔽。且均为太祖子孙,乃区区争虚号耶?”奏告中并未替鲁王屈尊,然唐王的态度是“喜”,后宁波人谭贞良、王翔等亦往闽求援[25]357。可见唐王因鲁王不称臣而诛杀鲁使陈谦之说似有嫁祸或建构之嫌。
因此,彭孙贻的记载虽可视为陈谦被杀的具体过程,但其被杀的真正原因绝非仅用称呼、挟功和诸不法状来说清,而应从闽浙纷争的角度去探寻。
二、伴使考与外媾说
鲁使陈谦使闽的其中一个不明之处在于他的伴使,尽管南明时期勋将势力逐渐凌驾于文臣之上,但是君主授任使命的人员仍以文臣为主。如唐使刘中藻、陆清源、王之栻,鲁使柯夏卿、夏惟才、王绍美、沈綵、倪懋熹等皆为文官。究其缘由,弘光政权的江北四镇桀骜不驯,南明君主在军事上虽依赖于武将,但仍忌惮之,潞王降清就很可能与惧怕马士英及其部曲来杭有关,而鲁监国有方国安、马士英,唐王政权有郑芝龙、郑鸿逵诸辈,皆不听各自君主的管制。另外,在重文的明朝,君主最信任的莫过于自己选拔的文臣,世宗凭借兴王世子身份登基皇位,利用大礼仪之争排挤出旧臣,重用倾意于自己的中下级文官。唐王即位,虽提拔故内阁大臣、耆儒为大学士,“一时耆硕,尽列卿贰”,然而“翰林、吏部专循资格”,尤其是“翰林一席,资格独重”,以至于当时有“重翰林、轻宰相”的评论[16]3-4。唐王在派遣陆清源出使浙东时,以陆为正使,“听其自择一人为副”[20]62。由此可知,正使为文官已是约定俗成之事,而副使可由正使自择。因而按照明制和唐王重文的特点,鲁王所遣使者不当止一武将。
多数文献仅记载陈谦一人使闽,而另外一些文献已经注意到使臣应当为文官,但称与陈谦一起使闽者为林垐。林垐(1606-1647),字子野,福建福清人,崇祯癸未年进士。林垐在明季任海宁令,以计擒获家奴李刀三,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26]。杭州沦陷不久归籍,海宁百姓号哭相送十余里[27]。隆武初(1645-1646)任户部员外郎,寻随督师黄道周宣谕浙西义军,不久征还,担任御史、吏部文选司主事等职务[28],主铨政,不久被罢免[29],后不满郑芝龙独断政事,“垐不得自行其志,于是,散遣其众入山”[6]12。唐王殉难,与兵部左侍郎林汝翥等同时起乡兵抗清,不成被杀,弟子陈确将其殉国行为记为“节义同天壤”,以示林垐因“节义”而死,同时因自己未死而“惭愧旧升堂”[30]。有的浙东文献因其在唐王死后响应闽中义师,又曾得到鲁王的追封,将之视为鲁王遗臣,但对于其入浙的行径又模棱两可,为了彰显唐王的昏聩和林垐对鲁王的忠心,以至于在传抄中将林垐的形象转变为使闽被捕的鲁王忠臣。综上,林垐不曾在鲁监国任职,也不可能为鲁王使臣,《圣安本纪》[31]213、《明季遗闻》[10]105、《明季南略》[7]320、《皇明四朝成仁录》[32]等称陈谦与行人林垐来到福建,“趔趄不敢入”,后在郑芝龙的邀请下方觐见唐王,继而下狱,此说法不符合事实。
另有个别文献认为,陈谦的伴使是一名林姓文臣,如《粤游见闻》记鲁监国派遣林必达和一武弁出使福建,而且事后林必达被释放[19]598。《东南纪事》载林必达、裘兆锦和陈谦使闽[24]28。日本修撰之《台湾割据志》直言是林必达受鲁王之遣约见郑芝龙[33]24。据民国《鄞县志·舆地志》记载,在县西上陈山有行人林必达墓,墓表由谢为雯所撰[34]。光绪《慈溪县志》记载裘兆锦虽为武官,然善诗作,原为榆次县丞,崇祯十一年因讨登州孔有德有功,由兖州通判转任宁绍参将,完成了“文官易武”的转变[35]638。因此,官授行人的林必达当为此次出使的正使,都督裘兆锦为副使,而总兵陈谦同为副使似也可说通。
尽管这些文献重点突出了使臣当以文官为主这一特点,但与未载有伴使的文献相比,则忽视了陈谦本人对私利的追求,如《明季三朝野史》《明季南略》均注明伴使为林垐,着重点明此次出使与平时无二,因而省略了陈谦在衢逗留、在闽挟功等背景[14]32。如果将林姓文官和陈谦作为此次出使福建的主角,最终唯独作为副使的武官陈谦被处死,这足以说明此次出使福建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政治性回聘,而陈谦之死恰与出使福建的另一个目的有极大关联。
福建沦陷后,福建失地曾短暂归于鲁监国,鲁监国文人在反思闽浙抗清失败缘由时,虽客观认识到闽浙两地不和是失败的主因,但多数仍认为唐王乱杀使臣是间接因素,而未反思陈谦因何而死。如果忽略文献中的主观记载,单看各文献均有的成分,只剩下钱邦芑对唐王的谈话以及陈谦与郑成功的亲密关系等线索,换言之,钱邦芑关于陈谦密结郑芝龙的奏言是基于自身对客观事物的建议,应较真实。除大部分由浙东士人在蔽鲁王耻的思维引导下撰写的文献外,仍有少量史料尽力摒弃主观情感,用简笔叙说陈谦被诛的原因,这些文献主要是倾意于闽浙合作的浙东士人所作。其中华廷献的论说最切中要旨:“御史钱邦芑劾其外媾有状,逮下诏狱。”[8]42华廷献是鲁监国大臣,他在撰写著作时虽多取材于传言传闻或他著,但言陈谦“外媾有状”是经过一定的理性思考。
当福建使者刘中藻出使浙东并颁布唐王诏谕时,唐王的诱结江上诸将方针已正式展开。据《罪惟录》记载,鲁王之所以断然拒绝唐王要其臣服,并使“江上之师受其约束”[36]4的诏谕,除了熊汝霖等人的坚持外,还在于“唐平卤(虏)侯郑芝龙私表愿效鲁力”[17]404,自此始,双方公开拉拢对方的武臣。刘中藻的诏谕虽然遭到部分鲁王大臣的拒绝,然江上诸臣多通过刘中藻“私上职名于唐矣”,监察御史杨文瓒“自请使闽约为唇齿,唐王留之,并召其兄文琦”[25]355。大学士朱大典、督师钱肃乐、勋将方国安等人认为“权宜称皇太侄以报命,未为不可;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非闽人所能夺也”[37]49,认为闽强浙弱,浙东处于不利之地,当暂时修好以解决收复金陵这一主要任务,方国安甚至私自接受唐王的银印、爵位封赐。刘中藻在浙遭受中书舍人谢龙震等羞辱后离去,不久在朱大典的举荐下,经金华回闽[23]9,“召对称旨,加太仆少卿”。刘中藻的出使虽未完成既定目标,但保证了福建与浙东诸臣的联系,可称得上不辱使命[37]73。隆武元年秋,金堡自浙入闽,坚持提议唐王出仙霞关守御徽州、浙西和上江,以此保证清军不会从淳安、徽州方向袭击方国安部,这说明此时方国安通过金堡等与福建相通[38]2。次年四月,唐王宣称“靖夷侯方国安,江上战功独多,归向又敦切”,此处表明唐王仍在不断劝谕方国安归闽。但不久,出使浙东宣谕鲁王归顺的金堡回到福建,讲述了自己被陈函辉、方国安、王之仁追杀的经过,认为“国安即欲杀臣,则请命于陛下耳;乃假手鲁藩,此何者也”[38]15,可见方国安在此时又高举鲁王的旗帜,为了迎合鲁王,大肆驱逐唐使。《东南纪事》也记载到鲁王曾派法司抓捕金堡,陈函辉“密启”鲁王诛杀金堡,金堡不得不亡奔衢州[24]28。此前鲁王派遣使者柯夏卿入闽,唐王出于“广播王言”和稳固浙东抗清一线的目的[20]62,也派遣陆清源前往浙东犒师,其目的在于阴结诸将,不料马士英等未得到犒赏,唆使方国安杀害陆清源,方国安正式与福建断绝往来,但郑遵谦、刘孔昭在金堡等人的努力下均有趋闽的想法[9]34。唐王多次派遣使者劝说钱肃乐来闽[39]7,至清军取得钱塘江战役胜利的片刻,鲁监国兵部左侍郎钱肃乐、右都御史沈宸荃、义兴伯郑遵谦最终“皆弃浙入闽,隆武皇帝召对,晋秩有差”[6]2。
结合当时闽浙两地使者的任务,在陆清源被截留浙东后,陈谦出使福建有着另一层使命,即阴结郑氏集团。记载隆武朝史事的《思文大纪》,最早提及林必达出使福建的目的,就是诱结郑氏,但未提及有陈谦之人,其云:
(隆武二年四月)囚鲁藩使臣左军都督裘兆锦、行人林必达。鲁藩以公爵封芝龙兄弟,兆锦、必达奉藩命而来。上以其招摇煽惑,欺侮肆行。兼以芝龙兄弟愧愤不出,故令囚之,以候常朝日面质。后兆锦以金赎刑,必达准复原官。[20]91
日著《台湾割据志》与《思文大纪》对应:“鲁王遣行人林必达来,必达窃通信芝龙,欲私招徕;芝龙闻之隆武,隆武怒囚必达。”[33]24此著为郑氏避耻,摆正了郑氏的态度,同时省却了陈谦的出场,然至少说明林必达等此次使闽的目的并非常规的回聘,而在于“窃通信”。
瞿共美所著《粤游见闻》将林必达使闽和陈谦使闽记为先后两件事:
(隆武二年三月)鲁王遣行人林必达来。必达同一武弁通书郑成功,意欲私自招徕之而不及表闻。芝龙以上闻,逮下诏狱。会百官廷鞫,上大怒,切责必达。已而释之,改必达福建督学御史。[8]38
(七月)杀总兵陈谦。御史钱邦芑劾其外媾有状,逮下诏狱。郑芝龙力救,不听,寻杀之。[8]42
此说中,除陈谦独使不合规制外,七月出使、已释又杀、郑芝龙态度变化等细节也存在疑问。
受业于黄宗羲的邵廷采,归并了《思文大纪》中的林必达使闽事件和其他浙东文献中的陈谦使闽事件,在《东南纪事》的“唐王”卷中将陈谦因未称臣而死的细节详加叙述,但在“鲁王”卷中又将陈谦之死放置于整个闽浙纷争中,如此完美解释了陈谦被杀的原因。《东南纪事》是为数不多公开将陈谦之死与闽浙拉拢勋臣相联系的浙东文献,说明作者受黄宗羲影响,也倾意于闽浙交好,但又不否定唐王的反面形象,这在该著以“唐王”卷为卷首即有所体现。其云:
鲁王使陈谦奉书,称皇叔父,不称陛下。王怒,下谦狱。郑芝龙与谦有旧,钱邦芑出芝龙门,而亲见于王,密奏谦为鲁心腹,与郑至交,不急除,恐变生。王斩谦。浙闽聘好遂绝。[24]11
大清顺治三年丙戌春正月朔,鲁王御殿受朝。遣兵部尚书柯夏卿如福州聘,唐王深自抑损,手书报王,言:朕无子,王为太侄,和衷协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取东浙职官均列朝籍,转饷十万犒师。王意终不慊,发敕封郑芝龙兄弟为公。于是,唐王大怒,囚使者裘兆锦、林必达,斩陈谦,浙闽竟成水火。[24]28
所举的第一部分是浙东士人针对陈谦被害的普遍想法,即陈谦出使福建仅仅是奉鲁王之命,唐王仅因陈谦与郑芝龙有旧交而诛杀他,咎在唐王。但在第二部分,邵廷采改变叙述方式,将陈谦之死置于当时的闽浙纷争中,解释了陈谦出使福建的真正原因以及伴使的文武性质等相关疑问。鲁王接到刘中藻的劝谕后,又派遣柯夏卿等至闽以回复自己抗诏的原因,唐王对此深表不满,但对于鲁使仍采取劝诱的策略,加封柯夏卿等闽职,并派遣陆清源犒劳浙东诸将,以此作为对鲁王拒诏的报复。一些文献认为陈谦出使福建在陆清源来浙之前,这虽然是错误的,但说明了陈谦与林必达使闽的时间是相近的[11]57。徐芳烈是鲁王大臣,他记载了陆清源来浙发生在隆武二年三月初一日,这与《思文大纪》大体相符。《思文大纪》将唐使陆清源的两次使浙事件分置于二月和三月,而将鲁使林必达使闽置于四月。据史籍记载,陆清源出使浙江是回复鲁王的叔侄礼,因浙东诸将分饷不和相杀[12]13-14,欲借此时机“取浙东所用职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故而犒师[20]121,因此鲁王不可能在派遣柯夏卿后不久即令陈谦入闽,陈谦使闽是在陆清源入浙之后。唐王又派遣黄鸣骏进兵新安,鲁王不得不使王绍美等前往衢州谢罪、犒师、讲和。对陆清源犒师及闽“诸科部诸臣出监浙师”而不以闻于自己的行为,鲁王自始至终深表怀疑和不满,在方国安等人的唆使下,效仿唐王假以回聘的形式,派遣裘兆锦、林必达、总兵陈谦为使,暗中诱结郑芝龙。有些文献也稍提及鲁王册封郑芝龙,使陈谦招徕之,但所赐爵位不一,《海上见闻录》作“南安伯”[40],郑芝龙本有南安伯之爵,为弘光帝所封,唐王又封郑芝龙为平彝侯,位在伯之上,鲁王赐予伯爵显然起不到招徕效果,此说不确。《靖海志》等作“靖虏侯”[15]10,亦与平彝侯地位相等,不确。唯有《东南纪事》的“封公”说较为可信,然爵名缺略,为陈谦使闽之伪埋下伏笔[24]28。诸本又称钱邦芑是郑芝龙门生,能够获悉郑氏言行,深得唐王信任。据载,熊开元弹劾钱邦芑无资格授御史,然唐王不听,熊愤然辞官离去[19]576。钱邦芑对唐王深怀感激,因此当听闻陈谦与郑芝龙密谈时,不再顾忌郑氏对自己的恩情,于是奏请唐王诛杀陈谦以阻断郑氏北投的想法。从钱邦芑的角度看陈谦被处死的过程似乎很合理,然《所知录》作者钱澄之对钱邦芑的行为和遭遇较为关注,他的态度经历了从对不满口舌得官的厌恶到破格授御史的认可的转变,却从未提及钱邦芑为郑芝龙门生[16]13。
综上,粗看已有文献,关于陈谦使闽存在建构过程,较早的史料只提到林必达使闽,随后的浙东史籍开始编入陈谦,除了个别士人质疑陈谦单独使闽外,其余史籍以陈谦出使事件作为影响唐鲁关系的史事来看待。那些质疑陈谦使闽的文人又无直接证据,或采取折中说,将陈谦使闽融入林必达使闽事件中,或以附说形式提出自己的困惑。从伴使角度切入,陈谦出使必然跟随一位文官,而这位文官绝非大多数文献所言之“林垐”,诸多细节又说明陈谦与外媾有关,这与林必达使闽相似,因此若存在陈谦使闽事件,当与林必达同行。
三、陈谦之子追击说与陈谦使闽有无考
清史档案无鲁使陈谦记录,而官修明史又多借鉴浙东史籍,因此仅能从浙东文献探寻蛛丝马迹,拼凑出陈谦使闽的真实情况。陈谦之死的记载与浙东士人的主观意识有密切联系,浙东士人在记载隆武政权灭亡时存在对陈谦之死的余恨,认为引导清军追杀唐王至汀州者正是被唐王误杀的陈谦之子。
关于清军对自延平府奔往汀州府的唐王的追击,清朝档案文献多认为是博洛所派遣的图赖所为,如《清史稿·图赖传》记载一等公图赖率部经仙霞关入闽,分兵予阿济格尼堪、杜尔德、和讬等追击唐藩御驾[41]9320,在汀州击败明军并俘虏唐王及诸王[41]9435。《清实录》《清史稿》《东华录》及清修《明季编年》均称“大兵奄至”,剿杀唐王,且清军攻陷汀州当夜,明总兵姜正希率兵二万来夺汀州,若攻下汀州城仅是南明文献口称的陈谦之子所率数骑,不可能做到“大兵击败之(指姜部),斩万余级”的效果[42]。
明代浙东遗臣主持的文献多认为陈谦之子引导清军自浙东进入仙霞关,继而率先带领骑兵围击汀州府城,并俘虏(或杀害)唐王,此说往往与前文陈谦因称呼之故被处死相呼应。如《靖海志》记载称唐王在汀州停留一日,陈谦之子率部突入府城,在行宫杀害唐王[15]13。然而当时博洛作为清军主帅定然亲率主力攻打省城,而陈谦之子作为前锋追击逃亡中的唐王,清廷也会赐予其官爵作为降者的奖赏,档案、史籍也不可能隐去他的名讳。最明了的案例即上虞人周祖尚随清将佟岱入闽有功而被授予海澄教谕[43]。
钱澄之通过钱邦芑的口述,证明陈谦之子不可能为父报仇。清军进入仙霞关后,福建郡县皆盛传陈谦之子为清军向导,有人建议钱邦芑避祸,钱回复:“谦子蒸(烝)其父妾,岂能报父仇乎?”事后果然再无陈谦之子的消息。钱澄之也发现,陈谦之子“陈六卿”(陈六御的讹写)为郑成功裨将,后被清军所害[16]20。李长根依据陈谦之子烝父妾一事认为“陈六御”不是能报仇之人,追杀之事不真[21]864。从人物品行来看,陈谦之子引导说当属讹传。
另有部分文献综合清、南明、郑氏史料,一面对陈谦之子抱有怀疑态度,一面又无法避开盛传的汉人追击说,于是采用李成栋追击说。如本质疑陈谦之死的徐鼒认为贝勒博洛派遣总兵李成栋率部追击唐王于汀州,而自统主力趋福州[19]619。《台湾外记》称博洛在延平府通过土人得知唐王已西走汀州,于是令李成栋率部追击[13]89。《罪惟录》完全不载陈谦相关之事,追杀唐王者乃“北师李成栋”[17]422。
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陈谦与郑氏、唐王之间的关系,陈谦之子不可能追逐唐王。陈谦被唐王无故杀害,其子痛恨唐王固然正常,在浙东投降清军后引领清军追击唐王也无可厚非,陈谦又与郑芝龙友善,因此陈谦之子有两个时间段的降清机会。然《爝火录》直言若从忠义角度来思考,陈谦作为抗清阵营一员,其子“陈六御”为父复仇是不成立的[21]864。在郑成功的副将中也有一位名唤“陈六御”者,为监督[44]、北镇、总制[45],《行朝录》作“陈雪之”[6]84,《鲁之春秋》将“雪之”作为陈谦之子“陈御六”的字号[37]200,可见“陈御六”是“陈六御”的讹写,陈六御是真名。顺治六年郑成功派遣陈六御、阮骏攻克舟山,次年清军复取舟山,陈、阮二人战殁[6]86。如果陈六御是追杀唐王的清朝向导,却未跟随清将平定闽郡,抑或是跟随郑芝龙北上入京,而是跟从郑成功出海抗清,前后行为大相径庭不免使人起疑。而且对派系分明的郑成功竟收纳一位曾追杀自己恩人的清朝降将也是值得怀疑。因之,陈谦之子追杀唐王的说法缺乏充分依据,当是在口耳相传过程中的建构之作。
结合陈谦之子追击说是建构之作,可反推陈谦使闽的真实性。与陈谦一起出使福建的文官为林必达,然而根据《思文大纪》的记载,裘兆锦此次出使的武官,通过赎刑还浙,陈谦却被处死。不管是主记隆武朝事的《思文大纪》,还是鲁王亲密的大臣如黄宗羲、张岱、林时对等所撰之南明史料,都没有记载陈谦使闽一事,更不曾提及陈谦之子为父复仇之事,要知道其中不乏擅长为鲁王讳耻的文人,如张岱兼有埋怨鲁王的复杂心理①。而《思文大纪》并未受野史、清修史料中的“唐王朱聿钊”“唐王朱聿镇”影响,明晰隆武帝朱聿键和唐王朱聿间的关系,这在早期南明史籍中较显可贵,故其可信度极高,作者也很可能是当事人,或言是福建官员陈燕翼。清朝定平闽浙后,一些浙东籍士人或鲁监国遗臣如华廷献、吴伟业、邹漪、彭孙贻等网罗逸事野传,或讽说闽浙不睦,或为鲁王避耻,俱将陈谦之事载入文集,此后在野遗臣、清朝士人又将之作为编年的一部分,遂成定事。另一方面,最初承认林必达使闽的文献一般将其与裘兆锦搭配,当陈谦使闽说出现后,或只提及陈谦,或将三人合谈,然若将林、裘、陈合谈则会出现正使为一名文官,副使为两名都督的现象。鲁王既然派遣与郑氏有交情的陈谦,则无需再派裘兆锦,唐王也无需多此一举,杀害陈谦。另外,浙江东部地区的韵母发音往往会有前缀音[i]或[y],且口音杂乱,鼻化音脱落,因此裘兆锦的“裘”“锦”发音分别为[jiu]和[ji],中间的“兆”[zie]又容易与“裘”连读,整体发音与“陈”[dzien]——“谦”[qi]极为相近[46]。在三人中,陈谦是文献传抄过程中后添的对象,当是后人在裘兆锦的基础上掺杂入陈谦形象的产物。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基于人们对裘氏的同情和对唐王的不满,在获取传言中误将“裘兆锦”听成“陈谦”,士大夫们有意或无意将“陈谦”作为事件的记载对象。针对前者,裘兆锦通过赎刑的方式还浙,将对福建怀有怨恨,继而影响鲁监国士大夫群体。裘兆锦,字绍东,宁波府慈溪人,自闽还浙后被鲁王封为平波伯,其子裘永明为诸生,任左军都督,战死于钱塘之役,孙裘琏是康熙时期著名的浙东学者、戏剧家,曾参与修撰《定海县志》《南海志》等。裘兆锦侄子裘姚崇在为其伯父作年谱时即称:“大父以合并策上鲁监国,拜平波将军,使闽,唐王怒监国不奉朔,杖使八十,归,监国以不辱命,晋封平波伯。”[35]638-639此传与记载陈谦使闽中的“启函称皇叔父,而不称陛下”[31]213之意近乎相同,如此相似的使闽过程表明二者当为同一人。
陈谦只是林必达、裘兆锦使闽的文本“替代品”,如此能解释许多不明之处:
第一,除了亲征一事,唐王终包庇郑氏,而林必达之囚的另一层因素是“郑芝龙兄弟愧愤不出,故令囚之”[20]91,如此唐王囚禁裘兆锦、林必达也就无需考虑郑氏兄弟的心情。
第二,林必达被囚后,鲁王更不可能再派遣陈谦诱结郑芝龙,不仅在于唐王会有所防范,还在于将林必达供出后[47],郑氏兄弟会更加羞愧而抗拒鲁王的封爵,査继佐仍称郑芝龙为平卤侯,显见郑芝龙未受取公爵[17]407。因此林与陈必然是同时出使,但如此又存在裘兆锦和陈谦之间关于职位相同而结局不同等矛盾。
第三,陈谦与郑芝龙友善,又与方国安关系紧密,且是鲁王亲信之人,随意处死鲁使不仅使有入闽趋向或已在闽之浙人灰心,同时闽人也会就此抛弃他。且唐王熟读文史,断知不斩来使之理,何况当时他正积极招徕浙人。故囚禁之说更为可信。
第四,陈谦在鲁监国建权初即被封为镇威伯[18]134,同时期的公伯皆领兵在外,除了方国安、王之仁,永丰伯张鹏翼为衢州总兵[37]200,威远伯方元科为前锋总兵[12]1,开远伯吴凯为南洋协镇[12]8,靖南伯方任龙、定南伯②俞玉曾为方国安标下总兵[12]9,总兵镇夷伯王鸣谦为王之仁子,又有平南伯陈可立,永京伯张世凤。以上伯爵多为方、王部将。黄道周在《请酌用人材疏》中提及自己在劝谕浙北的益阳王时借助了鲁藩总兵陈谦与方国安的亲近关系[48],以此可推知陈谦受封公爵亦与方国安有极大关系。若陈谦被处死,方国安必然心灰,试图南侵,然实无此迹,甚至诸多史籍称方与马士英等在钱塘江之役战败后曾谋划入关[14]34。
第五,时间方面。徐晓望先生发现各史籍所载陈谦之死的发生时间各不相同:《东南纪事》《靖海志》载于隆武二年一月,《小腆纪年》《南疆逸史》在五月,《明季南略》在六月。徐先生意识到这些史籍都为后人所记,不可信,唯有《闽游记月》《粤游纪闻》《隆武纪略》可信度最高,其中瞿共美所著《粤游纪闻》有明确时间,因此认为事件应在七月朔至望之间[3]。事实上,熊开元、华廷献与瞿共美在隆武二年五月以后皆不在朝,熊归籍,华出宰归化县,瞿在赣,均不属于当事人,且《粤游见闻》存在抄录他人文集、奏疏的成分,如听取吴其靁奏疏,认为清军赚取汀州城是借用何吾驺部逃兵的衣物,这与清军赚取广州城的方式如出一辙,存有传抄或听取流言之嫌[8]44。六月,鲁王在钱塘之役兵败走台州,七月次海门卫,趋舟山[37]7-8,此时唐王“切责鲁王调度乖方,使速归藩服,不许海外弄兵”[49],民间甚至有唐王君臣“酌酒相庆”的传言[8]41。在此之际,江上战事起,鲁王不可能要求在外带兵之都督、伯爵脱离战场遣为使者,陈谦也不会替早已成败局的鲁王承担外媾之罪,唐王在此时更不用担忧郑芝龙会投奔鲁监国政权。若发生在七月以前,此时唐王尚十分信任郑芝龙,以其部将防守入闽各要道,丝毫未受诱结影响。学界对于郑芝龙离福时间的认识不尽相同,事实上明确有郑芝龙主动离福南下的记载是在鲁王兵溃之后,这与诸书所言郑因陈谦之事北上相悖。因此陈谦使闽在时间上无法说通。
综上,陈谦之子追击说多为谣言,与之相策应的陈谦被杀事件亦很有可能为虚构之说。笔者从当时环境、伴使和书写时间等角度出发,认为陈谦使闽事件是林必达使闽事件的复制品,出现的缘由在于浙东士人在掌握东南抗清的文本话语权后为鲁监国政权避耻。
四、浙东士人的文本话语权
由于唐王政权的影响力过大,其正统地位随着他的灭亡很快被永历政权取代,其部分辖土为鲁王所守。从文化方面,注重以史论理的浙东学术逐渐从学理上兼并福建学术,故而浙东士人在史载方面占据南明史的主导地位。
裘氏三代中,裘兆锦、裘永明为鲁王忠臣,裘琏又为著名的浙东学者。一方面,清朝忌讳南明史事,浙东士人不得不避开政局对裘氏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又急于对鲁王政权失败的责任加以推卸,于是或无意或有心地利用与郑芝龙有恩情的陈谦,使这次使闽事件更具合理化,以此回应唐王派遣使者诱结江上诸将的行为,从而衬托出唐王的贪婪和昏庸。同时利用陈谦与郑芝龙的关系,将郑芝龙外媾清朝的原因归结于钱邦芑和唐王,以此为清军顺利南下张本,少数文献将陈谦之死呼应陆清源被截杀一事来省去对鲁王的不利因素。
根据对陈谦使闽和陈谦之子追杀唐王的叙事,可推知南明史籍之所以没有点明陈谦出使福建的真正目的,在于规避“外媾”之举。浙东文人多为鲁王辩护,往往只记载唐王使者来到浙东后的不端行径。如张岱在记载陆清源被杀一事时,将所有罪状归结于马士英和张体元,称陆清源使浙以及此后福建所委派监察浙东水师的诸科部“不以闻监国,而监国亦故不知也”[22]58。査继佐也有相同论断:“夏四月,遣御史陆清原赍三万两,往犒浙师,私散江上,猝为方营所劫,清原见杀。乃复遣科部诸臣出监浙师,不以闻鲁监国,因尽取鲁温台之粟,以官填郡邑,鲁不能争。”[17]421这一记载证实唐王开始拉拢鲁王势力,但称陆清源使浙而鲁王不知,则完全是为鲁王辩解。《思文大纪》记载陆清源犒江上之师的目的是“广播王言之师”,唐王交予其致鲁王书信、及前勉答鲁王书稿三百册、亲征后诏御营敕谕三十册,纵使陆未及时通报鲁王,但陆的举动不可能瞒过好胜的鲁王[20]62。《南明野史》称陆清源分饷不平是激起军士哗变的主要因素[50]121。吴伟业更是认为方国安截杀唐使陆清源的缘故在于唐王擅杀陈谦[11]57,江日升也认为陈谦之死与方国安杀陆清源两事是激起张国维说出“自相戕毒,祸不远矣”一语的主因[13]85,此说认为陆清源之死在陈谦被杀之后。结合全祖望的“唐鲁争颁诏之礼,越使陈谦入闽而死,闽使陆清源入浙亦死”一语[39]21,表明清初学者已注意到陈谦与陆清源出使的目的具有一致性。
唐王在汀州遇害,两广乡绅忙于推选下一任皇位继承者,对唐王的下落和隆武政权失败的原因则漠不关心,鲁王流离至闽东北,号召在闽之故浙臣起兵响应,继而收复闽地三府一州二十七县,并全力攻打福州府。为了避开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对鲁王而言不光彩的因素,浙东文人往往避重就轻。这些具有推卸意味的评述对于反思抗清失败没有多少推动作用,与两广忙于择嗣的性质并无不同。
这种推卸思维其实与明朝传统的政治风气有极大关系,是明代儒生在发扬正统思想和注重生存策略综合之下的产物。科举入仕后,读书人的首要目的是谋取官职,受儒家经典的束缚,儒生熟识儒家伦理纲常,但多数人对于治国理兵之道则视同异路,所期待的仍是敛财保权。不管是北京陷没、南京陷没还是福州陷没,各区域的士大夫们或只关心自己的权势,或心知忠义而无力补救,当有人询问如何不为故主报仇,仅仅只能同史可法所言:“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50]30-31唐王政权尽管区域影响极广,然起自于传统体制,朝局所用儒生多为庸人,学术遭到时局压制,各区域与中央貌合神离,故虽坐居战线外围,但灭亡最早,因此缺乏必要的文本话语权。此时的浙江经济繁荣,学术活动异常活跃,鲁王依靠当地的乡绅武装而崛起,并夺得清初的文本话语权,其正统地位和人物品质被该区域士人设定在唐王之上。后者在儒家伦理之外偏重本位主义。儒生经历了多种朝廷乱局的锤炼,失去了原有坚毅的谏官品质,特别是在张居正执政之后习惯于内部结党斗争和在重大决策面前默不作声,并铸造出攀附、结党、结社、贿赂等多种保权手段,虽相应提高了君主集权,但加剧了朝局的政治腐化和君臣猜忌。在内阁与科道官斗争的催化下,区域性竞争也更为激烈,万历、天启年间形成的齐、楚、浙三大区域性党派最具代表性,明末学社也往往参与朝中党争。南明时期,乡绅们只关心所属政权,用自己擅长的笔墨为其发声,他们的眼界多局限于一地,当清朝剃发令开始实施,唐、鲁二藩成为他们保全区域文化和家族财富的工具。在此之时,这些区域观念极强的乡绅一面排挤或瓦解异地政权,一面在本区域划战区自保,一面又不欲与勋将共事,使唐、鲁二藩政权内外均冲突不断。尤其是鲁监国内部,一部为主张降清的耆硕、文人,另一部为新兴士大夫,双方的理念既对立又共存。当鲁王离开浙东,遗臣往往为自己的苟活寻求依据。张岱和黄宗羲就认为明季官员无须殉国,张认为归隐者“苟能以义卫志,以智卫身,托方外之弃迹,上可以见故主,下不辱先人,未为不可”[22]153,黄认为“遗民者,天地之元气”[36]213,与之相呼应的是对鲁王政权失败的推卸和避耻。
浙东士人对东南抗清的记载,虽存在许多不实之处,但使义士家属和学术种子在清初得以保存。因陈谦之子死于舟山之役而裘氏之孙名显于文坛,以裘兆锦记作陈谦的记载方式很可能在于保全裘氏。戴名世言及建文、南明事迹,认为义士匿迹在于全宗党,“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颇多有,使吊古之士莫能详焉,岂不可惜也夫”[51]!钱澄之也曾提到,其在康熙年间再游福建,适值建宁府修志,钱提出节义备选人员过少,修志人回复:“当事人不欲以丙戌秋死难者入志。”钱于是意识到:“吾人耳目既隘,地方居官者复以此事为忌,人传者益少,则吾人之所得知者盖亦寡矣。”[52]由此看出,清廷为防止民间崇拜南明死难者,于是加强社会文化约束力,地方当局或士绅或是为了契合清朝统治者,或是为了保护义士家属,主动避开南明抗清的话题,以至于史实因传承媒介的阻滞而逐渐化为零星。
五、结语
陈谦出使福建的目的与其他鲁使不同,它是鲁王效仿唐使拉拢对方勋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该事件成功引导闽浙纷争和全国局势进入新阶段。在南明史籍中,陈谦本人的存在并未受到重视,然而陈谦作为鲁使被唐王诛杀却关系到文本中针对闽浙失和和隆武败亡的归因。浙东大部分史籍多非该事件亲历者所著,但这些著者中的绝大多数都认同唐王应对陈谦之死负主责。若仔细甄别这部分史料,不仅可以发现相关的时间线索模糊,而且诸多的事件细节与人物关系和政治环境不合。本文先从伴使入手,认为使者有正有副,正使一般为文官,副使可为武官,南明史籍一般只提到鲁使陈谦而不涉及文官,这与事实不符。在少数文献中提到林必达、裘兆锦使闽事件,《思文大纪》更是提及林必达使闽存在鲁王以公爵诱结郑芝龙的目的,这与其他史料关于陈谦使闽的原因相似,然二者不可能先后进行,因此如果存在陈谦使闽事件,则只能与林必达同时进行。然而使臣中陈谦与裘兆锦同为武官不得不让人怀疑陈谦是此次使闽事件多余的人物,与鲁王有密切相关的浙东士人所撰著作以及《思文大纪》等均未提及此人,陈谦使闽之事又存在建构嫌疑。假使陈谦使闽一事存在,又会出现时间、社会环境及人物关系等方面的矛盾,故林必达使闽事件中的“陈谦”很可能就是指代裘兆锦。陈谦使闽事件是浙东遗臣,或误听传言,或刻意置换的产物,以此烘托出陈谦之死与唐使陆清源被截杀在浙东的性质是一样的,从而稀释对浙东的不利因素,突出唐王及钱邦芑在东南抗清失败过程中的主要责任。
注释:
①张岱之父张耀芳曾为鲁府官员,然鲁王即位后并未重用张岱,因此张岱在文集中稍有贬低鲁王之意。
②该著称俞玉的爵号为定安伯,结合《浙东纪略》,可知当为“定南伯”。参见:(清)李聿求《鲁之春秋》卷21《张鹏翼传》,《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