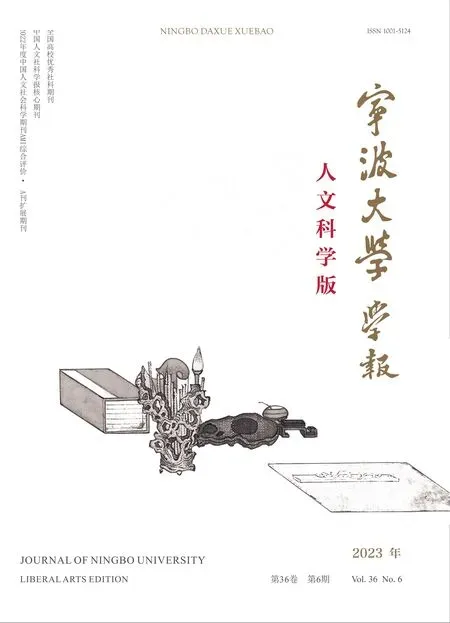国家翻译实践的对外译介主体行为研究:特征与模式
谭福民,杨 澜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翻译研究在经历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后,一方面促进了翻译本体的学科化与学科融合发展,为进一步腾飞奠定基础,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如理论与实践脱节、创新不足、社会应用性匮乏、对国家宏观实践观照不足等。从国家层面考察翻译理论与实践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取向,蓝红军曾断言当前正在经历翻译学的国家转向[1]。“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专门的译学术语最早见于任东升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研究”,此后,这一术语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任东升[2-3]、高玉霞[4]、蓝红军[5]、周忠良[6]等对国家翻译实践做了深入研究,深化了学界对翻译国家属性的认识。
秉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初心使命,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我国一直致力于开发并推动具有重要意义的优秀出版项目,将高品质图书推向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便是代表之一,该项目推出了中英、中葡、中法、中西、中德、中俄、中日、中韩、中阿、中泰十个语种对照版本的图书,向国外介绍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习惯,传播中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章依托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框架,重点探讨以“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图书项目为代表的国家翻译实践主体的行为特征与模式,加深学界对翻译研究应用价值的认识,同时探索对外译介中华文化的理念与路径。
一、国家翻译实践
为探索翻译研究未来在国家层面的建设,首先需廓清国家翻译实践与其行为主体的基本内涵,从话语影响的角度出发使国家翻译实践的多重优势得以显现。
(一)国家翻译实践与行为主体
在借助国家翻译实践视域审视译介主体前,需明确“国家翻译实践”这个中国原创译学话语的内涵嬗变。该话语经历了从构建到发展的过程,早期被界定为“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2],随后,其内涵得以拓展,“凡是以国家名义具体实施翻译行为或受国家机构委托的其他翻译机构、组织或个人的翻译行为,均可视为国家翻译实践”[7]。蓝红军也对该话语进行了解读,认为“获得主权国家赋权的机构或个人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实施的翻译实践”[8]。一方面,翻译的国家性毋庸置疑,翻译活动承载国家意志与社会意识,具备服务国家发展的能力,能助力国家整体战略发展。另一方面,从强调主权国家,到凸显获国家赋权的机构或个人,提高了概念的理论涵括性与解释力。
对于国家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任东升将其划分为高位主体、中位主体与低位主体[3]。具体而言,高位主体即国家,是翻译工程的发起者、赞助者、受益者以及实施主体;中位主体即获得国家授权与委托的机构或组织;低位主体是第一线的项目实施队伍或者个人,如翻译人员、编辑、出版商、外宣者等。
总之,“国家翻译实践”作为本土原创译学话语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内涵得以明确且适用性逐渐扩大。另外,该视域下译介主体划分的社会学特征较为明显,翻译学界已开始关注镶嵌于社会实践网络中的翻译实践各层级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与牵制的关系,并将其置于社会实践网络系统中观察与讨论。
(二)国家翻译实践的话语影响
国家翻译实践的方向可分为向内与向外,文章主要聚焦后者,即国家翻译的输出实践或跨国语际实践。当前我国对外翻译实践面临巨大挑战,如信息流通的逆差、形象构建的反差及软硬实力的落差等,在此背景下,国家转向的翻译实践致力于服务国家主权利益,提升国际话语影响力。首先,在政治话语传递方面,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译介主体更谨慎且恰当地表达国家政策、立场与意图,并考虑目标受众所在国家与地区的文化背景、地域差异、历史景观等特殊因素,适时调整传播主题、工具及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关系到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与氛围。其次,国家翻译实践具备特殊的文化传播与影响力,凸显更符合国家与民族文化气质的元素,并自上而下多方位向外传递中国文学、影视、音乐、绘画等文化产品,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互通,大幅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可见度。再者,由于国家翻译实践各系统组成部分均代表国家水准,输出的文化产品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高品质的国家翻译实践产物将有助于树立友好、创新、多元且可持续发展的民族形象。
除此之外,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的基本属性,即自利性、自发性与自主性[2],国家领导下的翻译实践享有制度系统化、流程信息化、资源集约化以及目标战略化等多重优势,能够更强劲地宣传我国的制度优越性与理念先进性,这便是我们的话语影响力。
二、对外译介主体的行为特征与模式
(一)对外译介主体
为验证“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项目的国家翻译实践属性,需明确该项目的成果特征及与国家部门间的关系,同时探究其作为中位主体的独特之处。
外研社图书项目“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受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产出项目成果《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系列图书。它具备原创性、思想性与学术性,拥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符合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资助条件与标准。任东升认为国家翻译实践的中位主体有三点主要特征:首先,应是受政府委托或指导的机构或组织;其次,其工作目标不在于财务盈利;最后,直接面向低位主体,指导其工作[7]。“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图书项目受国务院下属部门国家出版基金会遴选与支持,图书主题符合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与集体需求,不以盈利为目的,公益性质突出。该图书项目的参与者包括负责中文编著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莫旭强、邓炯、余珊三位专家学者,以及负责多语种编译的该校25位专家,他们均属于项目实践的低位主体,其中集体翻译与合作翻译行为受到制度化译者行为社会化机制的约束,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8]的象限上不断调整,各项行为决策需受到项目组织即中位主体的指导与制约。这些具体特征均符合任东升对于国家翻译实践中位主体的条件限制。总之,该项目的图书译介行为应视为中位主体的国家翻译实践。
(二)对外译介特征
对外译介活动强调精准把握翻译与传播的语境内涵。为了对中国在国际场域的话语输出有更微观与具象的了解,本研究主要聚焦该项目的成果之一《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中英对照)》一书[9],对其进行分析与解读,发现它在行为倾向上表现出明显的弱政治化,在文本选择上力求符合我国价值观,在翻译实践中采取本地化翻译策略。
1.坚持弱政治化的行动准则
国家翻译实践“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导向”,“服务于国家政治体制稳固和国家战略实施等政治价值目标的实现”[2],可见其内涵侧重对政治价值的阐释。然而,对该项目成果进行多方面分析发现它体现出明显的弱政治化特征,这是否会模糊自身的国家翻译实践属性,此问题值得思考。
在叙事主题与切入角度方面,面对海外媒体与民众对中国当代文化认知匮乏甚至偏颇的现状,该书以老百姓日常生活为基底进行叙事,内容平实,语言浅白,数据翔实,以开阔视角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图书首章设计了地球村居民身份证(identity card of China in the global village),介绍我国的基本信息,以人类整体视角俯瞰这个坐落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国家,这种版面与内容设计强调共性,可以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提升话语亲切度,从而缓冲分歧、实现对话。
在话语互动方面,不同类型的话语互动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巧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输出了不少接地气与个性化的语言样态,体现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同时也是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良性互动的直接体现。当前国际各方正激烈争夺话语权,翻译从业者更需摸清目标群体的视野期待与认知惯性,侧重对受众的亲和力和感召性,促成新时代各类话语的跨界联动。例如:该书每章均设有“你知道吗(did you know)”和“了解多一些(to know more)”版块,以补充章节内容,拓宽读者视野。首章对于“一国两制”(one country,two systems)的介绍,使读者了解到“The concept of ‘one country,two systems’…formulated by Deng Xiaoping…was first proposed for the purpose of solving the Taiwan question”,体现出党和国家为实现民族大一统所付出的真诚努力,人民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新高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指向,软文化的输出与潜在力量会缓解“中国模式”的“被接受焦虑”,以生活故事为载体进行价值观输出能增强党和国家在国际场域的亲和力,与大国政治外交形成联动态势。弱化政治意图并非放弃国家使命,反而会助推目标达成,这也是国家翻译实践目标达成的有效战术。
2.选择符合中国价值观的文本题材
国家翻译实践输出的是国家话语,反映的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精髓”[3],翻译题材需服务国家意识形态,符合民族主流价值观。
在图书内容与栏目选择上,以服务国家利益为宗旨,同时参照目的国受众的现实需求,凭借内容感染力激起受众对中国的好感。从古代文化切入,结合当代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在中国概况、服饰、饮食、家庭、交通、居住、收入、通信、就业、教育、历法与节日、文化与休闲、人际交往、卫生与健康、民间习俗、民间禁忌、信仰与价值观、中医、传统象征物、气功与功夫、绘画与书法、戏曲与乐器、诗词与小说、名城与古迹、工艺品等方面,表现出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冀与期盼。例如:在“民间习俗”一章,中国父母为婴儿举行取名礼(naming the baby),这些名字中通常会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如:“康”“健”“强”等是希望孩子身体健康(health and strength);“光”“伟”“正”是希望孩子长成一个光明磊落的人(honesty and good character)。在“信仰与价值观”章节中写道,中国人常说“大河无水小河干”(The rivulets will run dry if there is no water in the big river),蕴含中国人民深沉的共同体意识与家国情怀。另外,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Habits vary 10 miles apart,and customs vary 100 miles apart),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各异,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禁忌,秉持包容态度,就不存在文化冲突,全国各族人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共同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总之,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更需具备国家意识,以本土文化概念为载体,传播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符号,加强中国在国际传播链条中议题设置的主动性与策略性,提高自我故事讲述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3.采取中国特色的本地化翻译策略
在具体的国家翻译实践活动中如何展示中国的“符号特色”“价值特色”“主题特色”“资源特色”以及“问题特色”[10],我们可以从主体运作与翻译策略两方面出发进行探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若想收获理想的传播效果与正面的受众反馈,在翻译中需要实现“‘编’‘译’一体化,严选翻译队伍,流程质量管理”[11]。聚焦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团体运作方面,项目成果由专业语言与翻译队伍历时近5年编译而成,团队优质人才资源集中,信息完备,交流畅通。由外研社牵头对该项目实行“译”“校”“审”“定”的规范化流程管理,符合国家翻译实践层面的制度化翻译生产特征,在资源与价值方面带有强烈的中国印记。
翻译中国文化时应兼顾传统观照与发展性理念,“既反对任何脱离原文的自由主义,也反对死扣原文字面的机械主义”[12],本地化策略的实施也必不可少。在翻译策略的执行方面,为适应异语环境下受众的讯息需求与审美倾向,除语言转换外,还需采用多模态文本叙事的方式,多层面与受众对话,避免“文化折扣”的发生。“同一文本,是否配有图像会带来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13],在文本中合理植入图像,故事内容会更加多彩。国家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显示,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印象最好,饮食文化元素可作为当前文化传播的象征符号。该书中插入多张中国传统美食图片,如豆浆、油条(soybean milk and youtiao)、北京烤鸭(Beijing roast duck)、龙井虾仁(longjing shelled shrimps)、剁椒鱼头(sauteed fish head with diced spicy pepper)等,以及中国烹饪方式的图画,如:蒸(cooking by steaming)和炒(frying)等,形象展示不同省份与民族大不相同的饮食风味,蕴含了中国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的饮食思想,也体现了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符号特色与主题特色。
总之,通过系统的项目团体运作以及采取贴合受众的本地化翻译策略,一方面可以对外传达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与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可以表达友谊,激发外国读者对中国以及中国式生活探索的渴望,减少误解与文化冲突的可能性,服务整体国家战略的实施。
(三)对外译介模式
译介分为翻译与传播两个链条,若将二者强行割裂,恐难达到理想的译介效果。国家层面的对外译介行为存在于跨语际的国际交往中,一国的制度文化与价值观主动对外译出,向域外普及与诠释。
1.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以我为主”
韦努蒂曾说翻译所体现的语言角力实质上是其背后的文化及民族身份的角力[14]。他在《译者的隐身》中批判了以往通顺的倾向目的语文化的翻译,即归化(domestication),主张在翻译中表达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文化有其自身逻辑,在结构上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者由表及里,其中精神文化在文化逻辑中处于核心地位。精神文化层面上“以我为主”,要求在对外译介中凸显中国特色,摆脱在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桎梏。值得强调的是,“以我为主”与“以我为准”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别,前者强调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与主体意识,后者则倾向于民族中心主义,“以我为主”可适当缓解“中国威胁论”以及“东方中心主义”的消极舆论。
我国的对外译介活动重在宣传中国的治国方针与理念,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与元素,对当代中国形象的展示相对欠缺,因此现阶段更需重新思考当代国际语境中的动态背景与战略需求,规划符合国家话语体系的翻译策略与传播模式。一方面,选取的内容既需延续传统文化基底,又需杂糅多元的现当代文化元素,借助多样化叙事策略与风格,将中国文化有所变通地传递给受众,提升党和国家的国际认知度。例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就恰到好处地阐释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化身为倒计时器,从“雨水(rain water)”开始,至“立春(beginning of spring)”结束,同时也体现了古代文化在现当代时代语境中的适应性杂糅。另一方面,由于许多文化概念本身具有鲜明历史性与阐释的语境性[15],且内涵丰富,浓缩了深刻的民族价值观念和哲学思想,在文化特色词的处理上,可采用音译、意译、音义兼译,必要时可用扩注。例如:“铁饭碗”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就业形式,如果直接音译为“tie fanwan”或直译为“iron rice bowl”,令外国读者不明所以,翻译时采取音义兼译的方式更能令读者明白文字背后隐含的“a secure job”及“paid a fixed salary and…at no risk of being dismissed from employment”的隐喻内涵,言简意丰。
总体而言,在国家翻译实践项目中,在精神文化层面应保持中国性与民族性,主张适度异化的译介策略。
2.在语言文字层面上“兼顾他人”
现阶段国家翻译实践在语言层面应尽量照顾其他语系读者的阅读心理与接受习惯,适当采取变通的手段,如:“增、减、编、述、缩、并、改、仿”[16]。有些出自中国文化典籍的术语在其他语言系统中无对应表达,译介时在不影响整体内容表达的前提下可尝试进行删减。另外,还需根据上下文语境的连贯一致校准译本,适应目标语社会文化的具体语境。在句式结构上,贴合目标语的语言结构特征,必要时需要重新调整句式结构,这有利于解决读者在理解我国文化与文字时的认知障碍。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某些特色因子,可借音译加注的方式,既保留中国特色文化因子,同时带领外国读者进入中国社会情境进行文化适应,使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在不同时空场域中得以沟通,产生共鸣。该书每个章节最后都附有词汇表(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总结了该章核心词汇的汉语、拼音、词性以及英语释义,帮助读者跨越文字理解障碍,对一些蕴含深刻含义的文化核心词有更透彻的理解,如“四世同堂”的英语释义“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展示了中国的家庭结构与规模,以及中国人对于“家和”的向往和重视。另外,在汉语文化圈较流行的概念对于非汉语母语者相对陌生,例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了使读者明白“四大文明古国”这个概念,该书采用脚注的形式进行了补充解释,“The four great ancient nations…refer to the areas in which the earliest human civilizations were born—ancient Egypt,ancient Babylon (Some believe it is Mesopotamia,i.e.roughly Iraq today),ancient India and China”,读者借此可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与发展进程。
总之,译者需考虑目标语读者的需求,语言文字层面的变通有助于加深对译介活动的认识,推进译介模式的改良,回应中国文化外译事业的现实需求。
三、结语
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后疫情时代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各领域的宏观变迁正对世界格局、传播秩序、话语权力等产生深刻的结构性影响,中国翻译学者需主动回应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发展需求,探索翻译学科的应用价值。从国家层面观照翻译理论与实践,将推动翻译本体紧密贴合社会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以“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项目为代表的国家翻译实践主体的译介特征与模式进行探讨,可助力我国制定更行之有效的译介路径,挑选与国家外宣战略适配度更高的项目,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效能,自塑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