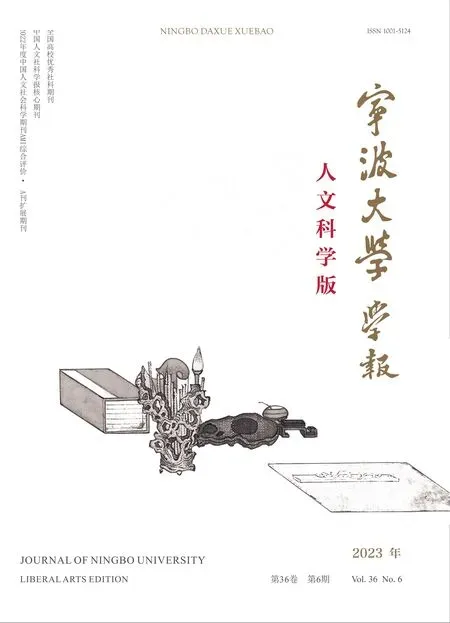不立宗旨与建构道统
——全祖望《陆桴亭先生传》的价值及其反响
韩书安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与陆陇其并称“二陆”,是清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然而,倘若细察清初思想界的实际状况,我们不禁会发现僻居乡里、终身未仕的陆世仪,在当时的学术影响力,远不及黄宗羲、孙奇逢、李二曲等陆王学派的海内“三大儒”①。即便是与同样服膺程朱理学的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等人②相比,也略显不逮。陆世仪进入清代理学的核心叙事话语,乃至成为清代为数不多的从祀孔庙的儒者③,深究其因,这一切与全祖望所作《陆桴亭先生传》的表彰之功有莫大关联。鉴于当前学界对此问题尚未有所论述,笔者拟以陆世仪形象从边缘到中心的历史变迁为考察线索,诠释全祖望《陆桴亭先生传》一文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及其在后世所带来的反响。
一、不立宗旨:全祖望对陆世仪学术风格的表彰
全祖望作为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不畏清廷严峻的政治形势,留心于搜罗明季文献,表彰忠义之士,体现了浓厚的民族文化情结。举凡清初第一流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李二曲、傅山等,他都撰有专门的碑传文字记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论学宗旨。相较而言,全氏所作的《陆桴亭先生传》一文,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则显得比较独特。因为全氏既不是久仰陆世仪的名声,也不是受桴亭后人所托,而是在阅读陆世仪的遗书后,感慨其学识深邃却令名不彰而主动撰写的:
予惟国初儒者,曰孙夏峰、曰黄梨洲、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及读其书,而叹其学之邃也,乃仿温公所作《文中子传》之例,采其粹言,为传一篇,以为他日国史底本。[1]517
全祖望将陆世仪比作隋末大儒王通④,认为其学养不在孙奇逢、黄宗羲和李二曲之下,这无疑极大提高了陆世仪的学术地位。而全祖望之所以极力表彰陆世仪,则有着深刻的学术缘由:
理学、心学之分为二也,其诸邓潜谷之不根乎?夫理与心,岂可歧而言乎?是亦何妄如之。当明之初,宗朱者盖十八,宗陆者盖十二,弓冶相传,各守其说,而门户不甚张也。敬轩出,而有薛学;康斋出,传之敬斋,而有胡学;是许平仲以后之一盛也。白沙出,而有陈学;阳明出,而有王学;是陈静明、赵宝峰以后之一盛也。未几,王学不胫而走,不特薛、胡二家为其所折,而陈学亦被掩,波靡至于海门,王学之靡已甚。敬庵出于甘泉之后,从而非之,而陈学始为薛、胡二家声援。东林顾、高二公出,复理格物之绪言,以救王学之偏,则薛、胡二家之又一盛也。蕺山出于敬庵之后,力主慎独,以救王学之偏,则陈氏之又一盛也。是时,晋、楚之从,几交相见。要之,溯其渊源而折衷之,则白沙未始不出于康斋,而阳明亦未尝竟见斥于泾阳也,是乃朱子去短集长之旨也。耳食之徒,动诋陈、王为异学,若与畴昔之诋薛、胡为俗学者相报复,亦不知诸儒之醇驳何在,故言之皆无分寸。[1]512-513
全祖望在《陆桴亭先生传》的开篇,即以明代儒学史的流衍变迁为例,指出朱陆后学为争门户,割裂理学、心学为二,互相攻讦对方是异学、俗学,是不明朱子“去短集长”的为学宗旨[1]513。全氏认为,必须首先了解诸儒之学的醇驳所在,然后评价其得失才会合乎分寸。陆世仪在这方面,显然深契全祖望的期许:“桴亭陆先生,不喜陈、王之学者也,顾能洞见其得失之故,而平心以论之,苟非其深造自得,安能若是。”[1]513虽然陆世仪为学不喜欢陈、王之说,但他却能平心论学,不持门户之见,自然成为评判诸家纷争的最佳人选。所以,全祖望在称赞陆世仪学问精湛的同时,特别强调“其最足以废诸家纷争之说,而百世俟之而不易者,在论明儒”[1]516。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征引了陆世仪评价陈献章、王阳明、罗钦顺、湛若水以及阳明后学的文字。这竟然占《陆桴亭先生传》全文篇幅的一半以上,在同题材的碑传文中极为罕见,足见全祖望对陆世仪论学公允之由衷钦佩。陆世仪对明儒的基本看法如下:
首先,陆世仪在评价陈献章时,指出他有儒门曾点气象,反对世人以禅宗视之。并且,他认为“白沙‘静中养出端倪’之说,《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惧慎独,而惟咏歌舞蹈以养之,则近于手持足行无非道妙之意矣。不言睹闻见显,而惟端倪之是求,则近于莫度金针之意矣”[1]514,进一步指出“白沙所谓自然者,诚也。稍有一毫之不诚,则粉饰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达为自然,非也”[1]514。陆世仪将陈献章的学问宗旨溯源到先秦儒学以还原其思想面貌,较之不假思索而简单拒斥为禅学者,无疑更能让人信服。
其次,陆世仪在评价王阳明时,一方面肯定“阳明之学,原自穷理读书中来”,强调其不废“道问学”的为学面向;另一方面也揭示格竹子七日而病“是则禅家‘参竹篦’之法,元非朱子格物之说”[1]514,指出王阳明对朱子学说的误解。总体说来,他认为王阳明的本意是“主于简易直捷,以救支离之失”,“致良知”也是入圣之门,但“切莫打破敬字,乃是坏良知也”,“阳明在圣门,狂者之流,门人眛其苦心,以负之耳”[1]514。陆世仪对王阳明的评价较为中肯,并不像其他程朱理学家那样将之视为“清谈误国”的罪魁祸首,在清初思想界尤为难得。
再次,陆世仪在评价罗钦顺时,认可其“四十余年,体认深切,故其造诣精粹”[1]515,但也指出罗氏在理气论上“不识理先于气之旨,而反以朱子为犹隔一膜,则是其未达也”[1]515的不足之处。关于罗钦顺和王阳明的学术争论,他指出:“阳明工夫不及整庵十分之五,整庵才气不及阳明十分之五。于整庵,吾恨其聪明少;于阳明,吾恨其聪明多。”[1]515由此,也可见陆世仪致力于调和各家的“去短集长”之苦心。
复次,陆世仪在评价湛若水时,认为湛氏“随处体认天理”就是“随事精察”,王阳明批评他“求之于外”是不对的。同时,陆氏认为明代在书院聚徒讲学、开创门户的传统肇始于湛若水。他指出“门户之盛,则实始于甘泉”,之前的儒者都是“质过于文,行过于言”,“甘泉始有书院生徒之盛,游谈奔走,废弃诗书,遂开阳明一派。东林继统,欲救其弊,而终不能不循书院生徒之习,以致贾祸。此有明一代学术升降之关”[1]515。陆世仪考察明代书院讲学的流传演变,对其滋生门户之盛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最后,陆世仪在评价阳明后学时,明确指出“姚江弟子,吾必以绪山为巨擘”[1]515,认为钱德洪救正王学末流的功业甚大。“绪山当日,虽以天泉之会,压于龙溪,然不负阳明者,绪山也。终背阳明之教者,龙溪也。”[1]515钱德洪的“四有说”相较于王畿的“四无说”,更加注重功夫践履的笃实一面,自然也就避免了“玄虚而荡”的流弊。
陆世仪对明代诸儒的斠评,本着实事求是的客观立场,能正中各家之利弊得失,洵为不可多得之识论。然而,全祖望之所以看重陆世仪,除了他注重践履,不尚空谈,符合浙东学派的一贯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陆世仪所强调的“不立宗旨”的讲学态度,甚合全祖望“去短集长”的论学宗旨:
又尝谓学者曰:“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譬之大医国手,无科不精,无方不备,无药不用。岂有执一海上方,而沾沾语人曰‘舍此,更无科、无方、无药’也?近之谈宗旨者,皆海上方也。”[1]516
全祖望在介绍完陆世仪评论明儒得失的具体看法后,特别标举其“不立宗旨”的文字以作总结,显然是有深刻寓意的。在全氏看来,陆世仪能够平心议论前人,泯去门户之见,根源于他本人讲学“不立宗旨”,不执一“海上方”为定见。职是之故,无论明儒讲学是宗朱抑或宗陆,薛、胡、陈、王哪一家,他都能不以己意之好恶评判,还其是非曲直。由此,不难发现,“不立宗旨”正是“去短集长”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就从更深层次上解释了全祖望为何要写《陆桴亭先生传》一文了:他不只要像司马迁或希罗多德那样保存人类历史记忆,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遗忘;更重要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学术主张找到坚实的立论基础,彻底解决朱陆异同的百余年公案。他的这一“以公心辨”的学术诉求,在当时门户林立的氛围中难觅知音。
二、去短集长:全祖望对《明史·儒林传》和《明儒学案》门户倾向的批评
如何评价有明一代学术,其实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在现存的两部评价明儒的重要著作中,我们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明儒学案》称赞:“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2]14《明史·儒林传》则批评:“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3]7222可见,基于学术视角、价值立场、思想观念以及时代风尚等方面的差异,后人对明代学术的评价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全祖望之所以大力表彰陆世仪,详引其论明儒的文字,乃在于他对以上两种出于尊朱或崇王的学术心态,有意抬高或贬低明代儒学而不能予以客观评价的现象之不满。
全祖望如此旁征博引陆世仪论明儒的文字,最直接的动机便是检讨《明史·儒林传》的不足之处。全氏在《陆桴亭先生传》中称赞陆世仪的学问“上自周、汉诸儒,以迄于今,仰而象纬、律历,下而礼乐、政事异同,旁及异端,其所疏证剖析,盖数百万言,无不粹且醇”[1]516。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陆世仪论明儒的文字“《明史·儒林传》中,未尝采也,予故撮其大略于此篇”[1]516。
虽然清初徐元文兄弟主修《明史》时,在设立《道学传》的问题上,曾引起各方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决定只列《儒林传》[4]。但乾隆时最终定稿的《明史》,其《儒林传》中仍有“尊朱辟王”的思想倾向。如《明史·儒林传》序言中说:“《宋史》判《道学》《儒林》为二,以明伊、洛渊源,上承洙、泗,儒宗统绪,莫正于是。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是以载籍虽繁,莫可废也。”[3]7221既然官修的《明史》不肯承认《宋史·道学传》所引起的学术纷争的弊病,那么它在评骘有明一代儒学史时,必然带着极深的门户之见: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3]7222
在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清代,《明史·儒林传》对明代儒学史的叙述具有鲜明的价值倾向。它把践履笃实的曹端、胡居仁看作“守先儒之正传”,而把思想创新的陈献章、王阳明说成“别立宗旨”,这并不能令宗主心学的儒者信服。黄宗羲之前便说过,“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2]79,“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2]178。这自然是认为陈献章、王阳明的造诣高于曹端、胡居仁。并且,站在客观的学术史立场来看,黄宗羲的说法无疑比《明史·儒林传》更加符合实情。因此,作为一部流传后世的官修正史——《明史·儒林传》中所存在的严重学术偏差,便是全祖望所不能接受的。
全祖望不满于《明史·儒林传》中专崇程朱的态度,并不代表他对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深以为然。全祖望极力表彰陆世仪论明儒的学术价值,其实也暗含他对黄宗羲《明儒学案》偏袒王学的微讽。尽管全祖望在学问上私淑黄宗羲,对他评价颇高:“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1]220但全氏也曾明确指出,黄宗羲身上有两个缺点:“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无我之学。其一,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亦其病也。”[1]1695-1696由于黄宗羲“门户之见深入”,所以他并不能像陆世仪那样完全做到“不立宗旨”,以“无我之学”的态度来评价诸家利弊得失⑤。由是,尽管全祖望在《黄梨洲先生神道碑》中将黄宗羲《明儒学案》称之为“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1]221,但并未引述《明儒学案》中论明儒的任何文字。
如所周知,黄宗羲所作的《明儒学案》,相较于周汝登《圣学宗传》“扰金银铜铁为一器”的狭陋和孙奇逢《理学宗传》“不复甄别”的粗疏,更加全面系统,堪称后出转精。黄氏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者。”[2]15他对自得之学的肯定和推崇,为全祖望所继承和发扬。但是黄宗羲对讲学须有宗旨的强调,却是全祖望所要极力避免的: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2]14
黄宗羲认为,“宗旨”既是思想家简明扼要地总结自己核心观点的“得力处”,也是读者提要钩玄地领会他人学说要旨的“入门处”。就像杜牧《注孙子序》中的那个比喻,倘若知晓立言之宗旨,讲者与听众的关系就像是“丸”和“盘”,处在一种既定的游戏规则之中。进而,黄宗羲强调,通过对讲学宗旨的把握,就能祛除诸家论学纷争的迷雾,明晰“一本万殊”的为道真谛:“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万殊也。”[2]15但是,黄宗羲“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实则仍不过是其心本体的哲学外化:
盈天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夫苟工夫着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2]7
黄宗羲直言不讳“盈天地间皆心”,批评后儒将理悬之于外去探求。既然如此,他对明代儒学史的整体观察,自然和《明史·儒林传》相反,是尊陆王而贬程朱的:“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而以崇仁为启明,蕺山为后劲。”[2]12他所讲的“一本”其实就是性命之源的“心体”,“万殊”就是诸儒讲学的“宗旨”。黄宗羲已预设“心体”而非“性体”是道体的本然呈现状态,那么其客观性原则就要大打折扣了⑥。《明儒学案》仍然是一部道统意识强烈的理学之书。
全祖望对此早有察觉,在续修《宋元学案》时,他进一步突破道统论的观念,扩大宋元思想史的取材范围[5]。在《与郑南溪论明儒学案事目》中,他对《明儒学案》提出了十一条商榷意见,指出黄宗羲考证的疏漏或议论的粗疏。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两条,兹摘录如下:
杨文懿公⑦讲学,不专主朱,亦不专主陆,深造躬行,以求自得。其所著《五经四书私钞》,皆不苟同前儒,其大略见愚所作《镜川书院记》中。鄞之儒者,前则南山,后则甬川,文懿之行,与之鼎足,而著书更富,宜为立一学案。[1]1692
阎征君百诗曰:“嘉靖初年,五星聚室,司天占曰‘主兵谋’,而先生归为阳明之祥。天启时,四星聚张,先生以为五星,而归之蕺山之祥。似当将此等语删去,弗予后人口实,则爱先生者也。”愚按百诗之言是也。其后先生之子百家作《行略》,又谓“五星聚箕,而先生之《学案》成”,愚亦尝语黄氏,当删去之。[1]1693
在第一条中,全祖望提到杨守陈应该列一学案,不仅是出于对乡贤学术的表彰,更重要是表达自己的学术理念:唯有做到“不专主朱,亦不专主陆,深造躬行,以求自得”,才能免去“后学门户纷争之习”[1]1283-1284。在第二条中,全祖望转引阎若璩之语,指出黄宗羲把“五星连珠”的天文异象比喻圣贤出世,尤其是在违背历史事实的情况下,就更显得荒诞不经,这也是全氏所要极力摒除的。诚如梁启超所言,全祖望和黄宗羲有两点不同:“第一,梨洲虽不大作玄谈,然究竟未能免;谢山著述,却真无一字理障了。第二,梨洲门户之见颇深,谢山却一点也没有。”[6]116这两点归结起来看,就是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并没有玄谈性理的特殊思想倾向,所以自然能做到胸中没有门户成见。因为他深刻体会到“门户之见,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词说”[1]1050,即便自己宗主某一师说,也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人心之各有所见,所以为朱学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1]1055,全祖望对待黄宗羲其实就是这种态度。
总体说来,不论是对官修《明史·儒林传》中“尊朱辟王”的门户之见,还是对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褒王贬朱”的论学心态,全祖望都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这些都是他作为史家所极力反对的。因此,全氏即便是面对作为浙东先贤的黄宗羲,也不敢苟同其“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能弥合各家宗旨,他始终认为“去短集长”才是调停学术纷争的可行之道。从全祖望和黄宗羲论学原则的根本差异,也可以看出浙东学派在内在学术精神上从“明道”到“求是”的演变轨迹,即清初的黄宗羲犹未脱晚明讲学习气的影响,致力于以哲学家的形上关切把握学术史的存在价值;而身处乾嘉的全祖望则在朴学氛围的熏染下,只希望以史学家的形下考索还原学术史的事实真相。明了这一点,我们便更能体会全祖望撰写《陆桴亭先生传》所蕴含的弦外之音了。
三、建构道统:唐鉴与钱穆对全祖望立传初衷的背离
全祖望对陆世仪的表彰之功,在后来的学术史叙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清史稿·儒林传》称陆世仪:“其于明儒薛、胡、陈、王,皆平心论之。又尝谓学者曰:‘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故全祖望谓国初儒者,孙奇逢、黄宗羲、李颙最有名,而世仪少知者。”[7]1318徐世昌所编《清儒学案》评价陆世仪:“于明儒得失,穷源究委,平心剖析,以息门户之争,卓为清初大儒。”[8]142这些显然都是受全祖望《陆桴亭先生传》一文的影响,从而标举陆世仪不立宗旨、平心论学的价值。不过,陆世仪的形象在不断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重塑与再造的现象,由此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则是全祖望所始料未及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晚清的唐鉴和近代的钱穆。
关于唐鉴的治学态度,时人评价其“生平力崇正学,辟阳明,不为调停两可之说”[9]7,可见他门户之见已深入骨髓。唐鉴以程朱为正统,视陆王为异端,因此他对黄宗羲和全祖望等人所修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表示强烈不满⑧,其所著《国朝学案小识》把清儒分为《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心宗学案》五类,具有极其鲜明的道统论色彩。其中最核心的是《传道学案》,仅列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把他们看作清代理学的正统,认为“其传道四人,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而言与行卓然表见于天下,上可以此追宗乎孔曾思孟,下可以此接近乎许薛胡罗,盖广大精微,传古圣贤之遗绪于不坠者”[9]733。然而,与陆陇其、张履祥、张伯行这三位有着强烈“尊朱辟王”观念的理学家不同,陆世仪讲学尤为反对门户之见,强调不立宗旨。那么,唐鉴是怎么把他塑造成“恪守程朱家法”的传道之人?
首先,唐鉴认为学术分歧是程朱理学格致、诚正之道不明造成的。“夫学之所以异,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岂有他哉!皆有不识格致、诚正而已。”[9]263原本朱子已经“得程子之嫡传,以《大学》之纲领、条目,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门传授心法,以居敬穷理为尊德性、道问学功夫,集诸子之大成,救万世之沉溺”[9]261,但是后人不肯循其次第,贪便喜捷,于是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才会“天下闻风者趋之若鹜,骎骎乎欲祧程朱矣”[9]261。因此,他认为真儒应该“扫新奇而归荡平,去歧趋而入堂奥,还吾程、朱真途辙,即还吾颜、曾、思、孟真授受,更还吾夫子真面目”[9]262。其充满独断色彩的道统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其次,唐鉴认为真正解决程朱陆王之争的是陆陇其。“蒙是编自平湖陆先生始重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后知阳明之学断不能传会于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笃,而后知程朱之学断不能离格致、诚正而别为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辅翼于学术败坏之时,而后知天之未丧斯文。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陆先生也。与先生同时诸儒,以及后之继起者,多不及先生之纯,而能遵程朱之道,亦先生之心也。”[9]262-263他把陆陇其看作今之朱子,认为他在同代诸儒中最为醇粹无疵。所以,唐鉴对陆世仪的评价也是全然以陆陇其为标准,把陆世仪塑造成了一个专宗程朱的卫道士形象。他描述陆世仪“隐居不仕,笃志圣贤,谨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程,以居敬穷理、省察克制为功夫”[9]290,这无疑是典型的程朱理学的践履之士形象。尽管唐鉴也不否认陆世仪在学术上“能窥天人之微,发周子《太极图说》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性理所未尽”[9]290-291。但是,唐鉴必须正面直视陆陇其在《思辨录序》中指摘陆世仪“未尝力斥深拒”姚江之学的微疵问题。如果不能把陆世仪塑造成醇儒的形象,那么他所建构的道统传承谱系必然会动摇。所以,唐鉴细大不捐地征引《思辨录》中辨析“无善无恶”说、本体与工夫、尽性与复性、天泉证道、九谛九解等相关内容,来说明陆世仪本人确实意识到了阳明学的流弊并且曾予以严斥,只不过是陆陇其没注意到这些文字罢了。在巧妙地化解了陆陇其对陆世仪卫道不严的质疑之后,唐鉴最后松口气地说道:“此数条者,辨之明而诋之切,先生忧世之心,其亦同于清献乎?”[9]296经过上述煞费苦心的辨析论证之后,唐鉴终于成功建构了“二陆二张”的道统传承谱系,但却严重背离了全祖望所揭橥的陆世仪“不立宗旨”的本意。
继唐鉴之后,对陆世仪评价最高的当推钱穆。不过,钱穆对陆世仪的认识和评价,是一个逐步深入和提高的过程。最初,或是受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影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颜元为清初四大家,列有专章重点论述,并附上与之相关的重要交游学者。他仅在《引论》中提到“清初学者,如太仓陆桴亭、容城孙夏峰,虽各有偏倚,而斟酌调停,去短集长,仍是东林以来之旧辙”[10]15。可见,这一时期,钱穆对陆世仪只停留在笼统的印象之中,并未认真阅读其著作。后来,抗战期间,钱穆作《清儒学案》一书,列有《桴亭学案》,次于夏峰、梨洲、杨园之后,评述陆世仪的学问:“清初学者,多主调和朱、王,折衷宋明。其著者,北方有夏峰,南方有桴亭。桴亭之论明儒,尤为后人所称。至其究心六艺,实辟学术之新向。颜习斋闻声想慕,引为同调;而其弟子李恕谷南游,得读桴亭书,欲以心性存养补师门事物经济之不逮,此可见桴亭学术之恢张与平称焉。”[11]365他对陆世仪的评价相较于之前,显然有进一步充实和展开。晚年,钱穆在完成《朱子新学案》后,又有《研朱余沈》的写作计划,其中撰有《陆桴亭学述》一文。他在开篇即指出朱子后学最令他钦佩的有四人,分别是元代黄震、明代罗钦顺和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陆世仪。并且,综合比较四家言性理和治道方面的学问,认为《思辨录》较之《黄氏日抄》《困知记》和《日知录》,有“益见清新特出之妙。陈辞措意,脱落恒蹊,称心而道,摆尽缠缚,别开生面,洵不可多得之书也”[11]19。他揭示出桴亭之学是“以宋明儒之精微回阐孔孟之平实”,“实可谓宋明道统殿军”,特别表彰他于理学与经济两面之兼尽,“自朱子后,能本末精粗,内外体用,一以贯之,实惟桴亭有此蕲向,亦有此造诣”[11]40。此时,钱穆认为,陆世仪是朱子以后一人,能全面发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他对陆世仪的评价,可谓无以复加!
然则,尽管钱穆高度评价陆世仪是“宋明道统殿军”,但他又不能否认陆氏“不立宗旨”的讲学原则。那么,钱穆是怎么调停的呢?他以陆世仪所批评的“为学五弊”⑨为例,认为“桴亭之学,于此五者,皆所涉猎,然皆能祛其弊而见其大,可谓卓然而不失为道学之正统矣”[11]22。钱穆这里所讲的“祛弊见大”的方法和全祖望所强调的“去短集长”原则,表面看起来十分相似,但实则有本质的不同。全祖望是站在客观中立的史学家立场上评判各说,钱穆则是站在“道通为一”的理学家立场上吸纳百家。他明确强调“道学当统摄一切学问,非可外于一切学问而自立一道学之门户。在前惟朱子有此见解,在后惟桴亭具此识趣也”[11]22。既然如此,那么“不立宗旨”就是朱子学的原本精义,并非简单的调停之说:“盖不立宗旨,亦不立门户,诚所谓卓尔不群。而桴亭在当时,能剖析及此者,殆已无人,亦可谓朱子之学,实亦至是而绝响也。”[11]26因此,他对陆世仪论学的看法就和全祖望完全不同了:“桴亭论学观点,致广大而尽精微,会性理与经济而一之,实与向来一辈道学家不同,洵不失为朱子学之正统嫡系也。”[11]23钱穆将全祖望所推崇的陆世仪“不立宗旨”的学术风格,转手一变为“建构道统”的朱子学之“正统嫡系”,这显然比唐鉴固步自封的论学立场高出一筹。
要而言之,无论唐鉴还是钱穆,不管其学术立场是保守狭隘抑或开放多元,只要他们服膺程朱理学,必欲定为一尊,那么就难以克服道统论的思想倾向。因此,他们对陆世仪“不立宗旨”的学术风格,无论赞扬也好,贬低也罢,都来源于他们所理解的儒家义理之学的形上追求,其最终指向也都服务于“建构道统”的价值关切。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所批判的黄宗羲学术史著作中渗透的门户观念,也正是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下重蹈的历史覆辙。
四、结语
陆世仪在清初思想界本是一个声名不显的地方儒者,其学术影响力在当时远不及孙奇逢、黄宗羲、李二曲等人。乾嘉时期,经过全祖望的大力表彰,他才逐渐为世人所熟知。以后各种重要的清代学术史著作,也都会对陆世仪有所提及论述,大体上仍是因袭全祖望的评价。全氏之所以极力推崇陆世仪“不立宗旨”的学术风格,根源于他对《明史·儒林传》和《明儒学案》尊朱或崇王的门户倾向的不满。全祖望所追求的“去短集长”的客观中立原则与黄宗羲所坚守的“一本万殊”的形上价值立场的根本差异,也揭示了浙东学派这一独特的历史哲学流派在内在学术精神上从“明道”到“求是”的演变轨迹。晚清以降,唐鉴、钱穆等人从他们各自所理解的程朱理学的道统论出发,批评或赞扬陆世仪“不立宗旨”的学术风格,都是基于他们“建构道统”的谱系传承的考虑,这自然也违背了全祖望撰写《陆桴亭先生传》一文的初衷。由此,不难发现,由于人们观察视角和价值诉求的差异,面对同一客观存在对象,经常会得出不同的认知结果。而作为该对象的直接经历者、间接还原者以及神话制造者,他们的叙事话语中的事物形象汇总起来又会形成所谓的“历史三调”。正如美国汉学家柯文所言:“重塑历史、直接经历和神话化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12]6这无疑值得后来的研究者进行深入思考。
注释:
①据全祖望所言,将孙奇逢、黄宗羲和李二曲合称,最早出自清初理学名臣魏象枢。“左都御史魏公象枢曰:‘吾生平愿见而不得者三人:夏峰、梨洲、二曲也。’”参见: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②由张履祥发端、吕留良开拓、陆陇其发展到顶峰的清初“尊朱辟王”思潮声势浩大,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张天杰、肖永明《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
③清代共有九位本朝儒者从祀孔庙,按时间顺序排列依次是陆陇其、汤斌、孙奇逢、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其中,陆世仪是在光绪元年(1875)从祀孔庙的。
④笔者认为,全祖望将陆世仪比作王通,主要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二人学识渊博,但都比较隐逸,不被时人所知;二是王通主张“三教可一”,陆世仪反对程朱陆王的门户之争,都体现了开阔的学术胸襟。
⑤梁启超也认为,陆世仪评价各家的文字“极公平极中肯”,“所以桴亭可以说是一位最好的学术批评家——倘使他做一部《明儒学案》,价值只怕还在梨洲之上。因为梨洲主观的意见,到底免不掉,桴亭真算得毫无成心的一面镜子了”。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4页。
⑥钱穆对《明儒学案》的评价就有一番转变:“余少年读黄梨洲《明儒学案》,爱其网罗详备,条理明晰,认为有明一代之学术史,无过此矣。中年以后,颇亦涉猎各家原集,乃时憾黄氏取舍之未当,并于每一家之学术渊源,及其独特精神所在,指点未臻确切。乃复时参以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参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
⑦即杨守陈(1425-1489),字维新,号镜川,一作晋庵,浙江鄞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弘治二年,杨守陈去世后,谥号文懿,追赠礼部尚书。《明史》有传。
⑧唐鉴把黄宗羲列入《经学学案》中(相反,则把顾炎武列入《翼道学案》),批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数百年来,醇者驳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并于此三编中。学者喜其采之广而言之辨,以为天下之虚无怪诞无非是学,而不知千古学术之统纪由是而乱,后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也。”参见:唐鉴《唐鉴集》,岳麓书社,2010年,第653页。
⑨分别是“谈经书则流于传注”“尚经济则趋于权谲”“看史学则入于泛滥”“务古学则好为奇博”“攻文辞则溺于辞藻”。参见:钱穆《陆桴亭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