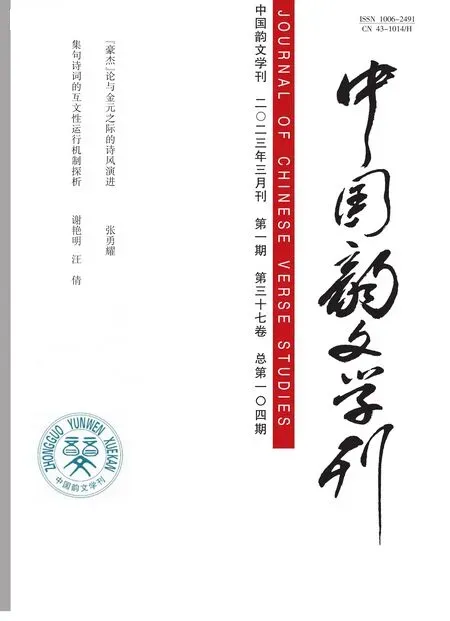规矩立而后天下有良工:论按谱填词与清词创作之兴盛
王延鹏
(合肥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清词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特色鲜明,成为继宋词之后的又一高峰。清词中兴原因众多,而守律一端尤其值得关注。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的文廷式在《云起轩词钞自序》中说:“有清以来,此道复振。国初诸家,颇能宏雅。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1](P325)嗣后,近代词论家张尔田提出著名的“清词四盛”说,称:“倚声者人知守律,是为词学之一盛。”[2](P140)前贤名家虽关注到清词守律之特色,但目前尚未有专文从按谱填词的角度来解释清词创作兴盛这一问题,故本文就此略加申述。
一 词谱本质为学词规范
词谱是词学中一类特殊的文献,一般指明清以来出现的格律谱。(1)参见宛敏灏《谈词谱——词学讲话之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谢桃坊《怎样解读词谱》,《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年第6期;谢桃坊《词谱检论》,《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目前所知之最早词谱是明代弘治七年(1494)周瑛、蒋华编的《词学筌蹄》。《词学筌蹄》之后,明代最重要的词谱当属张纟延《诗余图谱》和程明善《啸余谱》。有清一代,词谱踵事增华、后出转精,尤其是《词律》与《钦定词谱》两书的问世,带动了清代词谱编修的热潮,最终确立了词谱在词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词谱文献的性质,前贤多有论及。《四库全书总目》强调:“今之《词谱》皆取唐、宋旧词,以调名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句法字数,取句法字数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平仄。其句法字数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又一体,其平仄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可平可仄。自《啸余谱》以下,皆以此法推究,得其崖略,定为科律而已。”[3](P1827)《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词谱的作用在于“定为科律”,实则强调了词谱的格律规范作用。近人徐敬修指出:“张南湖有《诗余图谱》,程明善有《啸余谱》,万树有《词律》,皆专讲词体而兼及作法之书也。”[4](P123)徐敬修强调词谱除了讲授词体格律规范外,更兼具指导填词之功用。作为一类专门文献,词谱是元明以来词乐失传后为规范并指导词的创作而产生的,其主要功能在于强调词体规范、指示填词门径。换言之,词谱文献的核心在于“如何写”,而非“写什么”。
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在《诗学的定义》中指出:“还有一种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它表现在规范诗学中。对现有的程序不作客观描述,而是评价、判断它们,并指出某些唯一合理的程序来,这就是规范诗学的任务。规范诗学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5](P80-81)张伯伟先生据此将唐代的诗格称为唐代的规范诗学(2)参见张伯伟《论唐代的规范诗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同理我们也可以将明清词谱称为明清时期的“规范词学”。作为“规范词学”的词谱,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便于初学。作为指导“如何写”的教学书,词谱通过为学词者提供明晰的格律规范而达到方便初学的作用。程洪《记红集序》云:“听翁吴先生因有《选声》一集,考订精密,为词家之珍久矣。独其间诸体颇有缺遗,予兹复为校正,广搜博采,按调选词,以成一书,题曰《记红集》,盖取昔人红豆记歌之意云尔。夫舠虽如叶,而欲济者必问之;户扃甚闭,则操匙者频顾之。余之此谱亦犹是也。已济已启,彼如叶者舍之矣。如其未启未济,而思启思济,则操匙驾舠之为功,又曷可少哉。”[6](P289-290)正如程洪在序中所指出,《记红集》在《选声集》基础上“广搜博采”“复为校正”,其目的就是要凸显渡人过河的作用,以便初学者找到学词的门径。
韩侯振在《诗余谱纂序》中对词谱便于初学的特点有更为清晰的表述。《诗余谱纂序》云:“今观其采辑唐宋以来名人杰响,汇成一书,别其圈法,次其句读,开无限法门,俾读者了若指掌,由是登之剞劂,公之吟坛。喜者可以当歌,怒者可以当剑,思者可以当月,愁者可以当花,郁者可以当酒,梦者可以当钟。不特作者之情形,宛乎楮上,并述者之精神,亦宛乎楮上,则曾可嘉惠后学,岂浅鲜哉?且是诗余也。”[7](P439)在韩侯振看来,郭巩编修的《诗余谱纂》清晰明了,方便易学,一卷在手可以开启学词之法门,并由此步入词坛,嘉惠后学的功效十分明显。
当然,对词谱既便初学的功能和定位认识最到位、阐述最精到的还是首推万树《词律》。万树有感于此前词谱使用○●等符号容易带来的迷惑混淆,为方便初学者清晰明了地阅览《词律》,所以选择用小字旁注韵叶。他在《词律·发凡》中指出:“盖往者多取简便,不知欲以此晓示于人,何妨多列几字。《图谱》云方届文旁者,总求简约,以省刻资耳。此虽讥诮,亦或有然。然论其模糊圈之与竖,亦犹鲁卫。本谱则以小字明注于旁,在右者为韵、为叶、为换、为叠、为句、为豆,在左者为可平、为可仄、为作平、为某声。句不破碎,声可照填,开卷朗然,不致庞杂。”[9](P16)在这里看似只是对谱式标注的方式加以调整和优化,但实则却说明万树对方便初学者阅览和使用的高度重视。
由此可知,无论是被奉为圭臬的《词律》,还是影响相对有限的《诗余谱纂》《有真意斋词谱》,都是以便于初学为宗旨,这说明程洪、钱裕、万树等人在制谱时已经充分考虑到词谱的传播与使用了。
(二)保存矩律。作为教人“如何写”的教科书,词谱除了要便于初学,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并保矩律”。元明以来词乐消失,旧的填词规范不复存在,新的规范尚未建立,词体从原体词到变体词转化的过程中(3)“原体词”和“变体词”的概念参见鲍恒师《清代词体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9-10页。,亟需一种新的填词规范来指导创作,在这个历史条件下,词谱应运而生。吴兴祚《词律序》指出:
于是世之自命为才人宿学,遂不问古作者制词之所以然,而窃谓裁割字句、交互平仄之间,无事拘泥,可任情率意更改增减。讵知古调尽失,词之名存而音亡矣。嘻!设词可不拘成格,惟凭臆是逞,则何不以诗、以骚、以赋,不必句栉字比者为之,而必词之为耶?夫既刻意为词,复故失其音节之所在,不惑之甚耶。阳羡万子有忧之,谓古词本来,自今泯灭。乃究其弊所从始,缘诸家刊本不详考其真,而讹以承讹,或窜以己见,遂使流失莫底,非亟为救正不可。然欲救其弊,更无他求,惟有句栉字比于昔人原词,以为章程已耳。[9](P4-5)
《词律》正是对元明以来填词“凭臆是逞”多有不满,为了保留“古词本来”,而“句栉字比于昔人原词,以为章程已耳”,这里“句栉字比于昔人原词”正是为了保存词体规范。其实不仅是《词律》,其余词谱也多因保存词体规范而出现。林大椿《词式》称:“词之本性,原具矩律,后之作者,纵在歌法失传、字谱零落之今日,岂可遽使违背本性、顿失原则。谱法虽亡,旧词尚在,尽可择其格律严整者,仿用多数决之标准,以定依违,所以距宋元数百年之后,尚得凭之以制谱,虽与原有之谱合否未可知,而大体要亦勿违。”[10](P1099)可见,同《词律》一样,林大椿编修《词式》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确立法度、保存规范。
词乐失传后,明清以降的制谱者不得不考虑如何保存词体矩律的问题,最终他们选择以比勘归纳的方法为学词者提供清晰规范的格律样本。龙榆生指出:“自词之音谱失传,后世填词者无所准则,于是有人焉,广采众制之同一曲者,排比推勘,以求其共同之规式,而注平仄之词谱出。”[11](P219-220)虽然通过归纳法来确立词体规范未必吻合唐宋词之原貌,但词谱“正诸家之缺遗,俾词有准绳,学存矩矱,厥功甚伟”[11](P220)。换言之,由于词谱以保存矩律为目的,所以学词者无论选择何种词谱为参考,只要勤加研习,都可以掌握填词规范,从而避免随意与散漫。
综上所述,由于词谱详注平仄韵叶,又以名家词作为示范,既便初学,又保矩律,对学词者来说不啻为新的填词教科书,因此我们有理由将词谱看作明清时期的学词规范。词谱虽产生于明代中晚期,但受刊刻、传播等因素的限制,其对填词产生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明代词谱对明人填词的影响往往不易厘清。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尚未出现《词律》《钦定词谱》这样严谨规范的词谱,按谱填词还没有真正成为时代风尚。
二 按谱填词成为清人填词风尚
有清一代,按谱填词成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具体来说,是指清人填词大多遵从词谱规范,故填词有法可依,有范可循。可以说,词谱的出现,特别是《词律》和《钦定词谱》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清词的创作方式,开启了填词的新时代。
较早对此加以关注的是清初的邹祗谟,其《远志斋词衷》云:“今人作诗余,多据张南湖《诗余图谱》,及程明善《啸余谱》二书。南湖谱平仄差核,而用黑白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别之,不无鱼豕之讹。且载调太略,如‘粉蝶儿’与‘惜奴娇’,本系两体,但字数稍同,及起句相似,遂误为一体,恐亦未安。至《啸余谱》则舛误益甚,如‘念奴娇’之与‘无俗念’‘百字谣’‘大江乘’,‘贺新郎’之与‘金缕曲’,‘金人捧露盘’之与‘上西平’,本一体也,而分载数体。‘燕春台’之即‘燕台春’,‘大江乘’之即‘大江东’,‘秋霁’之即‘春霁’,‘棘影’之即‘疏影’,本无异名也,乃误仍讹字。或列数体,或逸本名,甚至错乱句读,增减字数,而强缀标目,妄分韵脚。又如、‘千年调’、‘六州歌头’、‘阳关引’、‘帝台春’之类,句数率皆淆乱。成谱如是,学者奉为金科玉律,何以迄无驳正者耶。”[12](P643)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虽对明代张纟延《诗余图谱》和程明善《啸余谱》多有批评,但却清晰地表明清初之人按谱填词的客观事实。
之后,随着《词律》和《钦定词谱》的刊行,词谱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按谱填词之人也日益增多。康乾之际田同之《西圃词话》称:“故浙西名家,务求考订精严,不敢出《词律》范围之外,诚以《词律》为确且善耳。至于《钦定词谱》,虽较《词律》所载稍宽,而详于源流,分别正变,且字句多寡,声调异同,以至平仄,无不一一注明,较对之间,一望了然。所谓填词必当遵古,从其多者,从其正者,尤当从其所共用者,舍词谱则无所措手矣。”[13](P1474)田同之注意到浙西词派与词谱之间密切的联系,甚至已到了“舍词谱则无所措手矣”的程度。这一时期,除《词律》和《钦定词谱》受到重视外,《诗余图谱》和《啸余谱》仍有一定影响,不少人填词时仍奉之为章程。据田同之《西圃词话》记载:“近日词家,谓词以琢句练调为工,并不深求于平仄句读之间,惟斤斤守《啸余》一编,《图谱》数卷,便自以为铁板金科,于是词风日盛,词学日衰矣。”[13](P1470)可见,当时词坛虽遵循按谱填词之模式,但所按之谱却有所差异。
到了同光时期,按谱填词更成为词坛的通行模式。裘廷桢《海棠秋馆词话》云:“当今作者,大半对调填字,不过依样葫芦。”[14](P1331)
及至清末民国时,按谱填词依然是词坛恪守的准则。闻野鹤《忄皿簃词话》曰:“《填词图谱》,红友诮为板腐,余谓拘泥固是,然初学亦有不能不遵者。”[15](P2312)在闻野鹤看来,即便是存在缺憾的《填词图谱》对初学者也同样有所裨益。近代词学家顾随在《致卢伯屏》的书信中记载自己按谱填词的经历,他说:“直至九时以后,出户小解,见满庭月色,心始畅然。返室即检谱填词,词成,心益释然,如放下重担者。”[16](P3310)可见,即使是到了清末民国时,填词之人也大多恪守按谱填词之规范。
作为清代词坛风尚的按谱填词,不仅影响有清一代之始终,其影响范围也如涟漪般持续扩大。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载项鸿祚乙稿自序云:“近日江南诸子,竞尚填词,辨韵辨律,翕然同声,几使姜张俯首。”[17](P3519)所谓“江南诸子”实际指以戈载为首的吴中后七子。吴中后七子十分重视律谱的作用,强调写词必须遵从律谱的规范。在他们的影响下,围绕在其周围的朱和羲等人均以按谱填词为学词法门。朱和羲在《万竹楼词自序》中说:“于是始知有词学之道,依谱填腔,奉为圭臬。”[19](P1155)杜文澜《憩园词话》也曾记载吴中按谱之风的影响,曰:“初,戈顺卿论词吴中,众皆翕服。独长洲孙月坡茂才麟趾与龃龉。长洲宋铭之茂才云:‘窃谓守戈氏之界,可以峻词体。游孙氏之宇,可以畅词趣。二者皆是,不可执一,愿与同侪通两家之驿可乎。’同人韪之。余则谓词仍当以韵律为主,未可越戈氏之范围,不敢附和月坡也。”[18](P2857)占籍浙江秀水的杜文澜对戈、孙二人论争之品评,说明杜文澜对戈载观点的肯定和推崇,这反映出按谱填词的观念已超越吴中一域,被越来越多词人所接受。
此后,按谱填词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对我国台湾地区和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也多有影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曾记载旅台词人肖严按谱填词之事,云:“肖严自台湾移书曰:‘客里无聊,取读《词律》,略有兴会,依谱填之,未知顽铁有可铸否。’”[20](P3363)日人田能村孝宪在其所撰《填词图谱》之《填词总论》中说:“今也国家升平,二百余年矣。经济文章以至稗官小说,无不尽备。独于词谱一书,寥寥无几,尚未闻有绮丽精绝之作,犹红袖青衫尚缺翠黛点缀也。考其原因有三:一、词句之作有短长多少之别,非比诗也;二、作词用韵须工平仄,稍有差讹即为笑柄;三、文人学子,真能悉心研究者极少,因此竟付缺如,能不为之叹息乎?是书之编,专集唐宋以来名人杰作,汇订成册,俾世之有意于词章学者或可借镜焉,想文豪学子,当亦许我赞同也。”[21]田能村孝宪有感于日本没有自撰词谱之缺憾而发愤著书,终于撰成《填词图谱》,从而为日本词人学词提供借鉴,这说明按谱填词的模式也深深印刻在日本学人心中。
以上,我们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对清代按谱填词风尚进行梳理,可以看出按谱填词已成为清代词坛共识而被广泛接受和遵从。
三 词谱在清词中兴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教人填词的词谱,在被清人广泛接受和遵从后,自然会从多方面影响清人的词学创作,故清词创作的兴盛与词谱的推动和指导息息相关。具体来说,按谱填词对清词中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革新了填词的范式。词本倚声,一曲有一曲之谱,一均有一均之拍,唐宋时期的词都是合乐而作,宋元以后乐谱散佚,原有的填词规范随之消失。《四库全书总目·钦定词谱》云:“词萌于唐,而大盛于宋。然唐、宋两代皆无词谱。盖当日之词,犹今日里巷之歌,人人解其音律,能自制腔,无须于谱。其或新声独造,为世所传,如《霓裳羽衣》之类,亦不过一曲一调之谱,无裒合众体,勒为一编者。元以来南北曲行,歌词之法遂绝。姜夔《白石词》中间有旁记节拍,如西域梵书状者,亦无人能通其说。”[3](P1827)元明以降,由于歌词之法散佚,词人无法按照乐谱来填词,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行词学创作成为困扰词学界的首要问题。而格律谱最大限度保留了词体的音乐性,又将其以文字格律的方式展现出来,为清人填词提供了新的规范。“按谱填词,沨沨乎可赴节簇而谐管弦矣”[22](P1),所以词谱一经出现就受到词学界的欢迎,并正式取代音乐谱成为新的填词范式。正如余意指出:“主要以标示平仄、韵脚、句读等为主的格律词谱的出现,使人们得以作律诗的方式作词,对词的发展而言是一次大的进步,它摆脱了自宋末以来词与音乐的长期纠缠不清的状态,承认词在写作方式上与律诗无异。”[23](P35)在这个意义上,格律谱以一种更确定、更清晰的规范填补了元明以来词乐散佚的缺失,这正是词学发展中寻求确定性的必然,也为清词创作的兴盛提供了新的范式。正如俞樾《词律拾遗序》指出:“至万氏出而规矩先民,张皇幽眇,为词家功臣。今徐君拾遗补阙,绳愆纠缪,又为万氏功臣,从此两书并行,用示词林正轨,俾后之论词者,知我朝词学之盛,直接两宋。”[9](P462)在俞樾看来,正是万树《词律》、徐本立《词律拾遗》等格律谱的出现,才使填词重新走上正轨,并为清词创作的繁荣提供了保证。
降低了填词的难度。词谱通过谱式来分析平仄韵叶,又选择名家例词以为示范,指导门径细致而翔实,为填词之人提供了能学、可学的规范,极大地降低了学词、填词的难度。顾宪融称:“初读一生调之词,必取谱旁置,认明此调之声韵及句法,然后发声吟咏,而字音必须个个准确,不令稍有牵强。苟能如是,则即使无人面授,读二三遍后,亦自能上口,且自觉其疾徐轻重之间,固有一定之标准。入耳会心,词句之美乃与音调之美融而为一。”[24](P276)词谱不仅有助于初学者体会词之声韵、句法,而且对如何填词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顾宪融强调:“长调记忆较难,而初学者尤患无所依据,则词谱亦自有用也。”[24](P285)对初学者来说,即使是较难入手的长调,有了词谱的详细指导和清晰示范,也变得较易掌握了。更为重要的是,格律谱出现后,学词之人只需要考虑词的文字格律,而不用再考虑纷繁的音律问题,进而从五音六律中解放出来,大大降低了填词的难度。谢无量称:“然诗余谓之填词,则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至于句之长短,虽可损益,然亦不当率意为之。譬诸医家加减古方,不过因其大局而稍更之。”[25](P28)谢无量将按谱填词比作加减古方,形象地说明词谱在学词过程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余意进一步指出:“没有了音乐的顾虑,作词只有文字形式的考虑,徒诗化的词面临新的挑战机遇,作词变得比前代要求具备的先决条件少,几乎是懂得作律诗,基本就可以作词。依据词谱作词,作词变得相对简单便捷,于是乎迎来了词创作的极大繁荣。”[23](P35)
扩大了填词的队伍。由于按谱填词降低了填词的难度,使得填词的门槛大幅度降低,由此带来清人填词队伍的扩大。粤东人颜师孔自述其学词经历颇具代表性:“至诗余一种,粤中为之者鲜。童时见王龙潭师为此,亦不解所以。《粤东词钞》自五季时黄损始,至此仅五十余人,已搜索无遗矣。盖粤中讴歌,每操土音声韵,不能播之管弦,故不为也。三江皖浙人避乱,客粤者多,时与往还,动为所讥,谓粤人尽不解填词。因取《填词图谱》观之曰:‘是不难也,不过取轻倩字面作掩挹语,按谱谐声,逐字嵌入矣。’遂奋然为之,时年已六十一二,积之三载得若干阕,谬灾梨枣,谓其不工可也。诚不工也,即谓其终不解亦无不可。请以质诸三江皖浙人,以为解否?”[26](P4-5)因粤东方言不能入乐,故从五代至清,粤东词人寥寥,为江浙皖等地词人所讥。颜师孔以自身学词经历表明,即便是没有根基的初学者也可以通过研习词谱来掌握填词的技法,这充分证明了词谱对扩大填词队伍所起的重要作用。类似的记载在词话中也时有体现,孙兆溎《片玉山房词话》云:“茂林侄本不工词,偶填一小令,为同社徐春雨所见,笑曰:‘我诗不如君,君词则不如我也。’茂林遂究心图谱,数月后,竟得其中三昧,春雨为之折服。”[27](P1673)这样的故事当然有虚构的可能,但无论是否属实都透露出按谱填词对于初学者掌握填词技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按谱填词便于初窥填词之门径,有助于激发填词的热情。正因为有了词谱的指导,清词数量才会呈现井喷式增长。胡云翼《中国词史略》称:“清代的词人之多,真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王昶的《清词综》编到嘉庆初年止,王绍成的《清词综二编》编到道光时止,黄燮清的《清词综续编》编到同治末年止,丁绍仪的《清词综补编》编到清亡为止。单此四书,共录词家三千余人,合宋、金、元、明四朝,尚无此盛。”[28](P768)饶宗颐在《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中也指出:“词衰于明,至清而复盛。作者之众,为旷古未有。”[29](P298)可以说,清代词人队伍的扩大正与按谱填词的帮助和指导有着莫大的关系。
提高了填词的水平。词体规范是词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基本特征,历来词家都对此格外重视与关注。叶恭绰强调:“能够按谱填词,一丝不错,且意境字句,均臻上乘,方可说到自己创作。”[30](P340)特立馆主《词林卮言》称:“然一词之间,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虽句之长短,略可通融,顾亦不能率意为之。则初学者且斤斤于轨范之不暇,尚何望得清空之灵机耶。”[31](P837)换言之,倘若词人连起码的格律规范都无法做到,又如何有精力去追求要眇宜修的境界?詹安泰明确指出“声韵、音律,剖析极严,首当细讲。此而不明,则虽穷极繁富,于斯道犹门外也”[32](P3)。可见,掌握词之韵律是填词入门之先决条件,而按谱填词能保证平仄韵律基本符合规范,这对于提升有清一代填词的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相比较格律谱产生前明人填词之随意,按谱填词后的清代词坛在格律规范上有了明显的进步。清代樊景升曾在《湖海草堂词序》中详细记载词谱对其提高填词水平之助益:“予自十五岁读《草堂诗余》,始学为小令。第一首乃平韵《忆秦娥》,有‘梧叶敲窗愁’之句。家大人见之,谓较胜于诗。自是每年必得数十首。后读《词律》,乃知法律之严,遂将少作一火焚之,至今二十年,所可存者不及百首,乃深知此中甘苦也。”[33](P1495-1496)从樊鹤龄之学词经历可以看出,在没有词谱指导时,其填词较为随意,而研读《词律》后,不仅意识到之前填词的缺漏,更掌握了填词的技法,最终实现了填词水平的提高。叶恭绰指出:“词本合乐,到南宋后歌词的乐谱即渐渐失传了,自元迄明,大家都不讲究了,在清顺治和康熙两朝的词,不合律的也很多,直到万树、戈载编著《词律》《词韵》,归纳各大家作品,定出一个标准来,于是填词的人,始兢兢于守律。所以清词大家很少有不合律的,不但讲求平仄,即四声阴阳亦不容混,这也是清词独优之点。”[30](P337-338)叶恭绰的评价充分肯定了词谱在提高清人填词技术水平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客观公允的。
四 结论
作为一种指导填词的教科书,词谱在清词中兴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正如吴兴祚在《词律序》指出:“夫规矩立而后天下有良工,衔勒齐而后天下无泛驾。吾知嗣是海内词家必更无自轶于尺寸之外,而词源大正矣。”[9](P5)吴兴祚的这一论断虽然着眼于《词律》,但实则可视为对词谱在清词中兴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说,词谱让填词有法可依、有据可循,革新了填词的方式,降低了填词的难度,扩大了填词的队伍,提高了填词的水平,为清词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