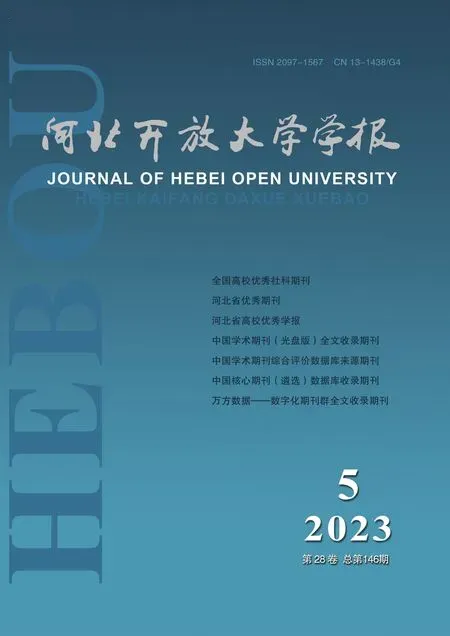刑事司法中行政证据转化问题研究
申纪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32)
一、证据转化难题何在
1.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从20 世纪开始,就由自然犯时代进入法定犯时代。”要求执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处便毫无错漏地准确定性实不可能,又因司法资源和效率的要求,以及部分证据的毁损灭失或改变,较好地进行两法证据转化是法定犯时代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之一。另一方面,自然犯领域的证据转化亦有必要。如在鉴定意见作为依据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先行政立案后,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的情况。此时,在行政调查程序中收集的相关证据若不可作为刑事案件证据,则可能导致关键事实的难以证明。
2.证据转化的困境
立法机关显然也关注到了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并做出了一定回应。2012 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54 条第2 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可能性[1],回应了在法律修改前“由于证据收集主体与形式不同,行政证据不能转化为刑事证据”和“行政执法机关收集证据亦有明确法律依据,尽管与刑事依据不同,但对事实仍有证明力”的争议。但遗憾的是,在“何种类型的证据可以转化”这一关键的问题上面,各方均未给出明确且无争议的答案。如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1 解释)中未对“行政机关”的外延作出规定,使用“等”字造成语义模糊,可转化范围仍然存在疑问。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则较之刑诉法和刑诉法解释增加了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三种证据,最终产生实践和理论上的无所适从。
3.证据转化问题的集中
第一是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外延为何,第二是未明确列举的证据种类能否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第三是相关证据应采何种审查标准。这些问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难以寻求到答案,但却实际影响着证据转化的实践。立法论的研究方式已被时间证明并不能解决当下问题,故应该选择从法律解释论的角度做出尝试。
二、可转化的证据收集主体
证据法理论中关于取证主体对证据能力的决定作用主要有着否定说、绝对肯定说和相对肯定说三种观点。即便采取对取证主体要求最为严格的“否定说”,行政机关亦可成为刑事诉讼取证主体。此处的“行政机关”应做广义理解,即不局限于工商、税务机关,也应当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监管部门等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组织,但不包括根据行政授权而参与到行政活动中的组织。21 解释在第75 条第2 款中肯定了这一观点,即狭义的行政机关和经行政授权的行政主体所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作为证据使用,而依行政委托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则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这是因为:第一,行政授权中,被授权组织在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行政职能时是行政主体,具有与行政机关基本相同的法律地位[2];而受委托组织并非行政主体,其地位与行政机关也有较大区别。所以,在被授权组织就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调查取证时,满足刑诉法证据转化规定中对证据收集主体的要求。第二,行政授权的本质属于一种立法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被授权组织一般就本领域内事务有着较强的专业知识、能力储备,若不允许相应的证据进入刑事诉讼,则可能导致部分专业性较强的犯罪行为如证券相关犯罪难以得到处理。而行政委托的本质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受委托的主体根据行政委托这样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再进行调查取证这样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呈现出“具体之具体”的结构,如此收集的证据难言严谨、客观、准确。第三,行政授权组织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相应的调查,并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利于相应的刑事证据监督工作。但行政委托的情况下,以委托机关的名义从事各项活动,由委托机关承担相应后果,一方面是责任承担相关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个人被行政委托的情况下,难以想象其收集的证据起到证明作用。
综上所述,在两法衔接证据转化中,可转化的范围限于行政机关和根据行政授权进行相关活动的组织所收集的证据,根据行政委托而参与行政活动的组织或个人所收集的证据不能转化为刑事证据。
三、可转化的证据种类
在两法衔接证据转化问题既往研究中,属何证据种类的行政证据可转化为刑事证据形成了三种主张:狭义说,即只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广义说,除明确列举的证据种类外,还可以包括笔录、鉴定意见等非言辞证据;最广义说,包括言辞证据在内的其他证据。
应当认为,最广义说的观点是恰当的。理由在于:第一,刑诉法等均采取正面列举的方式肯定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可进行转化,但由于最广义说与其他观点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第二,最广义说的观点是所有证据“均有可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而并非任何行政证据都“必须”或“一定”作为刑事证据使用,最广义说的观点仅仅是赋予相关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可能性[3],在具体情况中仍然需要进行相应的审查;第三,如果不采纳最广义说的观点,将可能导致在一些情况下的不当轻纵,如作为定案关键的现场笔录类证据、证人证言只有采最广义说的观点才有可能进入刑事诉讼,在经相应审查或印证后成为定案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最广义说的观点并非一律对行政证据全篇接受的观点。正如狭义说和广义说反对最广义说观点时所强调的,行政机关鉴定意见、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的收集程序与刑事诉讼中不同,其证据的合法性存在一定缺憾。但问题有二:一方面,证据转化相关规定的设置目的就在于,允许行政证据这一类合法性存在一定瑕疵的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中,并经审查作为定案根据,如果依照刑事标准相关证据的收集程序毫无瑕疵,则根本没有必要在刑事诉讼规范性文件中设置证据转化的条款。另一方面,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收集物证、书证等狭义说和广义说共同认可的证据时,亦存在程序上的区别,如果按照狭义说与广义说“不得有任何瑕疵”的判断标准,那么几乎任何行政证据都不可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实际上,狭义说与广义说均采取的观点是“可重复收集说”的观点,即当且仅当相应证据不能够经刑事程序再次收集时,才使用行政证据。只不过诸如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天然地具有不可重复收集的属性,而言辞证据并不全部具有不可重复收集的属性,在这一点上无论何种学说均达成了共识,但只有采取最广义说,才能保持逻辑的一致性。
四、转化证据的审查标准
关于转化证据的审查标准,主要形成了刑事标准说与行政标准说两种观点。应当认为,对于待转化行政证据的审查判断,应当采行政证据标准。理由在于:第一,正如上文所述,证据转化条款的设置目的即在于使得从传统刑事证据标准观之合法性存在瑕疵的证据有机会进入刑事诉讼中,如果采取刑事标准说,则不必适用转化条款的规定,存在使得该条款架空之虞。第二,从逻辑上讲,只有采纳行政标准,才使得行政机关的行政取证相关程序规定不被架空,这是因为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时,不可能对案件性质做出毫无错漏的判断,如果采用刑事标准说,则将迫使行政机关对所有案件均采用刑事标准调查取证。问题在于,一方面行政执法的效率要求难以得到保证,行政的效率原则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由于绝大多数行政机关并无刑事侦查权,也就不可能实现刑事标准的证据收集,最终使得证据转化无法实现。第三,证据转化条款是在证据刑事合法性上的一定程度放松,但不代表经由证据转化条款而来的证据的合法性不需得到确认,证据转化条款仅仅是使得“刑事标准”的要求降低为“行政标准”,呈现出法律所拟制的“行政标准+证据转化条款”等于“刑事标准”的情况。证据转化条款的法律拟制本质需要得到充分认识,即将本不满足刑事合法性要求的证据拟制成为满足刑事合法性的证据。
五、结语
法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司法实践,脱离了司法实践的法学研究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法学研究服务司法实践有立法论与司法论也即解释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为建构更完善的法律制度当然需要对现行法做出批判与反思,这是立法论的价值所在。但当立法者无意修改法律或者实务问题迫在眉睫时,法律修改建议并无助益,此种情况下的解释论是解决实践问题的唯一路径。在解释论中,应当认识到证据转化条款的法律拟制本质,即将本不符合刑事证据标准的行政证据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建立在这一本质的基础上,很多实践问题均可以得到妥善解答。此外,解释论的基本原理还要求在问题的认识上逻辑严密且标准统一,尽量寻求各种“例外”“少数”情况的“最大公约数”,使得“原则上……但……除外”的情况尽量减少,如此才能够实现法律适用的协调,以此最终实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法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