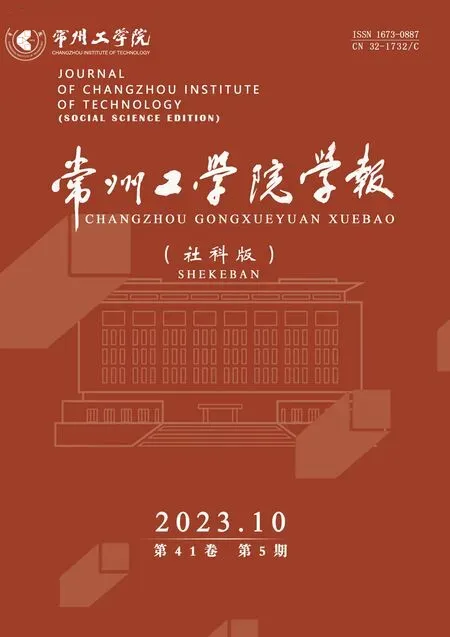浪子形象·都市漫游·现代性反思
——评李永平的小说《海东青》《朱鸰漫游仙境》等
林婕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李永平(1947—2017)是在台马华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研究当代马华文学还是研究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李永平都是一位绕不开的重要作家,朱崇科称其为“马华现代主义长篇第一人”。目前两岸以及海外学界对李永平小说创作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其关注焦点大致可以归纳为族群关系、离散与原乡书写、“乌托邦”书写、精神世界、漫游主题、语言实验、女性书写等。值得注意的是,李永平的一生经历了多次迁徙:他祖籍广东揭阳,1947年出生于英属婆罗洲沙劳越邦古晋市,1967年高中毕业后负笈来台,1976年前往美国留学,最终定居台湾。他30多年来漂泊流浪,地理位置的变迁也伴随着身份的转变。李永平屡屡在访谈、书序中自称“浪人”“浪子”“游子”,小说中人物也带上了自我的投射,常以漫游者的姿态出现。《海东青》《朱鸰漫游仙境》《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以下简称《雨雪霏霏》)3部小说皆是以主人公的漫游贯穿故事的主线,无家或不想回家成为浪子的共性,他们无所事事地游荡,观赏着一出出世情好戏。靳五、朱鸰、永,或让身体漫步于浮华色情的台北,或随记忆牵引到鬼魅忧郁的婆罗洲古晋。这些浪子形象是作家自我精神的形塑,交织了李永平对国族、原乡、身份认同、现代性、殖民与后殖民的忧虑思索,在个人的记忆之外呈现了社会性的创伤。
一、浪子的身世创伤与彷徨出走
《辞海》中对“浪子”的解释是“不务正业的放荡子弟”[1],从定义来看,“浪子”被判定为一个贬义词。浪子在社会中给人们的印象也多为负面形象,他们被归为精神堕落、挥霍物质的一类人。浪子形象时常出现于李永平的小说中,不同于《吉陵春秋》中的泼皮无赖,《海东青》《朱鸰漫游仙境》与《雨雪霏霏》中的浪子是颇为体面的,是从南洋来的大学教授与未步入社会的台北市小学女生。《海东青》与《朱鸰漫游仙境》是李永平“弃绝南洋”之作,有关南洋的记忆几乎从小说中隐去,闭口不谈。前者书写靳五与朱鸰的台北漫游,后者只以朱鸰作为漫游的主体,通过二人的都市探险,展现出充斥着欲望、罪恶、伤痕、虚幻的台北都市。而到了《雨雪霏霏》中,中年永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替换了靳五,他与朱鸰重游台北,但在漫游过程中却不由自主地召唤出对生命源头婆罗洲的童年记忆。在3部小说中,台北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成为李永平反复描写的对象。城与人持续牵扯勾连,塑造了浪子们的精神面貌。婆罗洲则作为一种记忆的补充,同不断回溯的永的过去,与台北形成历史的对话。靳五/永是从南洋走出的浪子,朱鸰是从台北家中走出的浪子,二人无家或有家不回,看似毫无瓜葛的浪子们,深陷现代都市的漩涡,有着“同病相怜”的身世创伤,具体表现为父位的缺席与原乡的失落。
(一)父位的缺席
“无父”或“父的失职”是李永平小说的常态。早期小说《围城的母亲》和《黑鸦与太阳》即是“寡母—独子”的模式,丈夫/父亲处于缺席的状态。“父的失职”则更集中地体现在《吉陵春秋》中,小说中的父亲大多无所作为,沉浸在自我的原始欲望之中,甚至严重影响到了后辈的成长。黄锦树因此提出:“‘父亡’的必然结果是道德失序、法规荡然无存。《吉陵春秋》中充斥着色欲的罪恶,原因在于那是一个生父已经亡故的空间。李永平的道德寓言:父法荡然的社会便是这样一副末日的景象。”[2]《海东青》弃绝了李永平的南洋记忆,一同抛弃的还有浪子靳五的父亲,他对婆罗洲唯一的牵挂是母亲。《雨雪霏霏》中,永虽然屡屡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但父亲给予自己童年的却都是不好的回忆。父亲生性放浪、脾气暴躁,事业一蹶不振,无力改变家境,还总是让母亲陷于无止境的生育之苦。一胎又一胎的生产使母亲的身体日渐消瘦,常年病怏怏。母亲的生产苦难来源于父亲,“哀母”意识与“憎父”心态形成一对矛盾。对父母性事的恐慌也加剧了永与父亲的对抗关系。少时生病,母亲让永与自己同睡,父亲不顾永的在场强行与母亲发生性事,当永醒了之后拍了他一巴掌并斥责他转过去。这一情节出现在了李永平多部小说之中。父亲粗暴的处理方式无疑给少年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朱鸰的父亲则是一个失势又失职的父亲,身体肥大、老态龙钟,终日蜗居于家中观看早已落伍的“中华少棒队”比赛的录影带。妻子借口“留学”日本,实则是去做暗娼;大女儿朱鹂从师范大学退学,甘作“日本双雄”的情妇甚至怀了孕;二女儿朱燕无心学业,沉醉于物质享受,一放假就去“第七天国”酒店当“公主”,服侍日本买春团。面对妻女的堕落,朱父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安理得地居住在靠她们的皮肉生意买下的豪华公寓。
李永平执着于“无父”或“父的失职”的书写固然有作家自身现实的因素,但“父亲缺席”的现象背后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心理。“父”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矩也,家长率教者”。“父亲”是规矩、威严、权力的象征。李永平一方面憎恨父权的围困,另一方面又对父亲无能失势的状况感到深深地焦虑。在缺父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或如朱鹂、朱燕人格偏离健全的轨道,或如靳五、永永远处于心灵失根的漂泊处境,甚或如“小朱鸰们”陷入失贞的焦虑。李永平通过“父亲缺席”的书写呈现出社会之“不可无父”。“无父”至“不可无父”,是李永平对父亲的深刻寓言。
(二)原乡的失落
“原乡的失落”是靳五、朱鸰、永的第二重身世创伤。《海东青》里的靳五是一个典型的异乡人,他是“海西”客家人,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婆罗洲,留学美国,又客居鲲京。这位南洋浪子一心向往中国文化,但此时早已异化的鲲京显然无法承载起他对原乡乌托邦的想象。鲲京即台北的化身。小说中的鲲京是一个人心浮躁、歌舞升平、光怪陆离的欲望都市,这与李永平在台北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那些年,我目睹了转型期的台湾在政治、社会和人心上的混乱,将它记录在《海东青》和《朱鸰漫游仙境》中。”[3]小说不断地描写台北的堕落:猖獗的娼妓业、接踵而来的日本老兵买春团、被迫早熟的无辜少女……种种都市乱象暗示了靳五把台北作为中国原乡假托地的虚妄,南洋早已告别,而理想的中国又无处可寻,个人的飘零交杂着政治、文化、历史的衰颓,加深了浪子作为异乡人的失落感。
而作为外省第二代的朱鸰同样面临着原乡的认同难题。小说中写到了海东人与海西人对“光屁股”与“开裆裤”的争论。海东人认为40年前海西人是光着屁股逃来宝岛,而海西人则称自己是捧着黄金来的,反驳海东人穷得连大人都穿开裆裤。这种看似粗鄙的划分标准背后,影射的是由于两岸分离所引发的政治话语、历史叙述、身份认同争论。朱鸰的父亲是从大陆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国军老兵,40岁后渐觉“反攻大陆”无望,便花3根金条买了年轻的台南乡下姑娘做老婆。所以朱鸰具有外省籍与台籍的双重属性,“身子的一半跟着我爸光屁股,身子的另一半跟着我妈穿开裆裤”[4]301。“感觉上,就好像有两股血液在我血管里,乱窜乱流,好像两个大人在我身体内打架,每天把我整得晕头转向坐立不安,在家里实在待不住,烦躁得要死,只想逃到外面大街上乱跑乱逛,有时候好痛苦哦。”[4]301
“当复数的‘多乡’仅被承认其一,排除即是一种压抑,或一种离弃。”[5]从《吉陵春秋》到《朱鸰漫游仙境》,李永平一再压抑作品中的南洋性,到了《雨雪霏霏》才终于接纳了自己身份的混杂性。《雨雪霏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身处台北,只能通过对童年往事的追忆归返婆罗洲。只是即使主人公回到了生命最初的源头,也因为种族、殖民与后殖民等问题而一再陷入身份认同的难题。“我”的父亲是广东人,年轻时来到沙劳越,本想赚点钱回唐山盖房子,却因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滞留南洋。“我”在内心深处一直将中国作为自己生命的源头,但父辈的原乡早已失去。作为英属殖民地的子民,“我”一再受到排挤、压抑。在经历了艾莉雅修女辱华观影活动之后,面对朱鸰的质疑,永内心的委屈轰然爆发:“朱鸰,你到底要我们这群小孩子怎么做?怒气冲冲站起来,指住银幕上的却尔登·希斯顿,破口大骂?还是要我们圣保禄师生相拥在一起,为支那母亲蒙受的耻辱,同声一哭?妈的!我们是殖民地百姓,我们是英女皇的子民。”[6]“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英国人,一再陷入身份认同的难题。
不少文艺作品中都出现了人物“出走”这一情节,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娜拉,从巴金《家》的高觉慧到曹禺《北京人》的瑞贞,这些经典作品蕴含着作家对人物“出走”的不同理解。与娜拉“砰”的一声试图冲出黑暗的闸门不同,李永平笔下的出走没有强烈的戏剧化效果,不如说是浪子彷徨的一种表现。他们虽然出走,但始终与最初的“原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走是为了理清生命中种种不可解的困惑与缺失,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原点”。“无父”“无乡”故而寻父、寻乡,这正是其心心念念的“原点”所在。然而出走只是浪子们的第一步,更深刻的生命体验还有待在漫游中展开。
二、漫游者的观看姿态与意义生成
“都市漫游者”是本雅明在阐释波德莱尔其人其诗时提出的一种主题意象与观察视角。这类人无所事事,四处闲逛,他们身处大都市中,但对周边的资本主义环境百般不适,因而把游荡当作一种战斗,在漫游中表达不满。在本雅明提出的概念与原初语境的基础之上,众多学者对“都市漫游者”进行了重读与拓展,该词的内涵与外延逐渐向漫游性转化。它不再独属于巴黎,而是以多种表现形式出现于不同时空的文学作品中。从中国文学中的《西游记》《围城》,到西方文学中的《堂吉诃德》《尤利西斯》,这些作品都掺入了漫游的笔法。漫游体小说给予了人物更充分的自由性、开放性和流动性。主人公在游荡的过程中穿梭于各种不同的场所,与社会上不同年龄、职业、阶级的人物打交道,他们掌握着城市街巷大小新闻的第一手资料,是瞬息万变、千姿百态的都市景观的见证者。李永平笔下的“浪子”与本雅明“漫游者”意象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他们看似没有目的地行走,“闲逛”成为其基本的生活方式。漫游于同一个都市,3位浪子在“观看”台北时呈现不同的姿态:靳五在漫游的过程中不断形塑了他的国族想象,朱鸰在漫游中更多地显露出反讽的立场,而永则将漫游作为一种记忆重启的工具。
(一)文化原乡的追认
在《海东青》中,靳五漫不经心地闲逛,看上去逍遥自在,好似与眼前所见保持一定的距离,像旁观者,像局外人。在一次次漫游中,靳五加深了对台北空间的阅读,逐渐构筑了他的国族想象、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从阴魂不散的日本买春团到过早凋零的台北雏妓,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血泪记忆到后殖民的肮脏交易,台北的今昔形成了一组意味深长的对照,使他的脚步愈加沉重,不由自主地回溯厚重的政治历史。小说中靳五不厌其烦地考证台北的街道名称。日据时期,日本人将台湾街名改为日本名字:金田町、猪苗代町、男鹿町、日和佐町、丸龟町……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接管台湾,又将台湾的街名改为具有古中国色彩的商丘街、丹阳街、城濮街、建业街、纪南街、荆门街、归州街、华阴路……不变的物理空间,在历史的轮转中卸去昔日的指代意义,街名的变迁象征着权力交叠的符码与历史的创伤。此外,《海东青》中书写了形形色色的海西浪子:苏北邳县名门望族的朱鸰父亲、操着苍凉西北腔的面摊子老兵、湖北自忠的马清六……他们表面上在台湾“落地生根”,但终其一生都在遥望着彼岸的故乡。而外乡人靳五与他们一样,同为所谓的外省第一代,虽生自南洋,从未到过海西,但作为客家人,一心思慕着大陆故乡。李永平常常用“母亲”隐喻靳五对原乡中国的想象。在小说中,靳五十分反感安乐新这个皮条客,但安乐新的一曲“寻母谣”却牵动着靳五的心。声声哀怨寻的是安乐新对素未谋面的母亲的思念,寻的是朱父等外省老兵对故乡的期盼,还有靳五等海外华人对精神文化原乡的追认。归根到底,他们寻觅的是认同感、归属感。如果“母亲”无处可寻,那么安乐新、老兵、靳五便只能像蜉蝣般,永远漂泊、游荡下去。
(二)儿童视角的反讽
在《朱鸰漫游仙境》中,朱鸰的“观看”一方面代表着儿童对成人的模仿与揶揄,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一种民间的立场,形成了对官方、权威的嘲讽与解构。暑假一来临,朱鸰等小学生纷纷上街漫游,观摩台北大街小巷的一幕幕“好戏”:军警联合大扫黄、工地内衣秀、立法院大混战等等。这些“看戏”的小学生,正如鲁迅笔下的看客一般,冷眼旁观,并不时发出笑声。身处堕落、腐败、浮躁的大环境中,孩子们潜移默化中早已接受、服从了成人的思想、价值理念以及生存处事原则。他们无意间模仿了大人的言语和行为,比如朱鸰“鹦鹉学舌”,向同学们讲起“又是出埃及记又是避秦、又是桃花源记又是海中有仙山”[4]321的神话,可这套大人的神话在柯丽双等人听来索然无味。对于“光屁股”与“开裆裤”、“走狗”与“垃圾”的争论,孩子们也发出了不解、反抗的声音,“那是他们大人的一笔烂账,算也算不清,不关我们小孩子的事!”[4]301立法院大混战中的两位立法委员,白天斗得你死我活,晚上却相约上酒店喝酒取乐。成人的世界令朱鸰们百思不得其解,孩童稚嫩的视角背后是作者对成人、官方的冷峻鞭挞。在沸沸扬扬的“雏菊专案”中,当局发动军警、媒体,试图在3个月内将色情业赶出宝岛台湾。如此大的阵仗,看似势在必得,然而特殊行业从业者早已做好了十足的应对措施,在扫黄来临的那一天紧闭大门、人去楼空。事后,媒体却热烈声称暑假的第一场宝岛扫黄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穿梭于街巷、见证城市藏污纳垢的漫游者,朱鸰们以儿童、民间的眼光,无情揭穿了官方的遮羞布,直指当局的无能、虚伪。
(三)南洋记忆的召唤
在《雨雪霏霏》中,台北景观在中年永与朱鸰的漫游过程中自由流转,不断变化,又通过朱鸰一步步的追问与审视,永的童年记忆创伤相继揭开,台北成为唤起古晋城童年往事的装置:台北的宝斗里酷似少时误入的古晋城暗巷妓院;台北华西街夜市的杀蛇斩鳖节目使永回想起集体覆灭的沙劳越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人为灭绝的新店溪庵仔鱼和浊水溪边的芦花则勾起了永对婆罗洲3名台籍慰安妇的愧疚与忏悔。台北的景观屡屡将主人公拉往异时异地,个人的记忆裹挟着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婆罗洲和台湾某种意义上成为同病相怜的命运共同体。诚如詹明信所言,“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7]。台湾和婆罗洲同样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侵害,日本对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又向南洋发动战争,《望乡》一节中的月鸾三姐妹即是日本殖民者从台湾强征送往南洋战场的慰安妇,这3名台籍慰安妇的悲惨遭遇使得叙述者的台湾、婆罗洲的双乡经验得以共通。此外,英属殖民地被殖民者与华人的双重身份,使叙述者从小就感受到了更为深刻的种族政治。来自爱尔兰的艾莉雅修女,千方百计地贬低汉字,将汉字称作“撒旦的符号”,并在华校举行观影活动时播放辱华的好莱坞电影《北京五十五天》,以此离间华人的认同感。种种行为背后,是西方帝国主义向东方的文化、精神殖民。一向敬爱的老师、朝夕相处的同学纷纷加入游击队,却在一夜之间被绞杀殆尽,这背后的震惊、酸楚折射出永对历史伤痛的刻骨铭心。然而,漫游于台北这一繁华都市,叙述者发现,台湾都市化与现代化的背后仍是阴魂不散的殖民主义。后殖民时期,日本人、美国人改头换面,收起了往日的大炮,他们带着东方想象、猎奇心理以及对自身政治、制度、种族、文化的优越感,再次踏上了昔日的殖民地,在华西街街头、宝斗里妓院寻欢作乐,殖民罪恶依旧笼罩着台湾。
漫游作为小说人物的行动方式,超越了其单纯的活动本身,而成为一种观察社会、反思历史的途径,在看似无目的的“闲逛”中处处表露出作者对历史创伤、都市罪恶、殖民与后殖民的审视。浪子从“家”中出走,借漫游宣示着特立独行的生活姿态,在走马观花地接收着社会讯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回溯各自的身世创伤、人生经历。
三、台北的都市体验与现代性反思
李永平在《海东青》的序言《出埃及记第四十年》中谈及该书的创作缘起:“《海东青》这一部不入大人先生们法眼的小说书,长篇叙说,唠唠叨叨,写的也只是(上天有眼!)‘道德’已被狠狠唾弃的自由狰狞金钱世界中的‘人心’——时下男女作家都不屑一提的两个字。”[8]日据时代结束后,台湾并没有摆脱日本文化殖民的影响,加上美援文艺体制下美国对台湾的文化、经济殖民,台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地景的改变。《海东青》的开篇,靳五学成归国,8年未见,海东早已变样,他迷失在夜雾中,误闯烟花巷,找不到回家的路。比物理空间面貌的变化,更深刻的是人心的骤变、精神的断裂。通过消费、身体的双重异化书写,小说中的台北呈现出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交杂的面貌。
(一)消费的异化
在《朱鸰漫游仙境》中,十几岁的少女争先恐后地去酒店当“公主”,她们手持新款“大哥大”,喷香奈儿香水,穿少女专卖店里的品牌服装,拥有十几张信用卡、贵宾卡、会员卡。“公主”出游,身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引起一群高中女生的艳羡。“水晶玻璃大窗”“高级橱窗”“玻璃旋转门”,这些透明的窗口“既是当下‘流行文化’的博物馆,也是引领社会消费趋势的公众示范处,又是表征日常生活变化的‘晴雨表’”[9],招引着蠢蠢欲动的台北少女堕入尘俗。法国社会学者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人们消费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在后工业社会,人们消费的是商品的象征交换价值,如象征着地位、声誉、品位、时尚等符号性的标志。“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用来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队,或作为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的参照来摆脱本团队。”[10]41物的符号价值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消费品被划分为各个等级,物的等级对应的是人的地位的等级,包含着人与人的分类。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造成了一种“平等”的假象,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同一件商品而获得貌似“平等”的社会地位。因为有了物品傍身,少女卖淫似乎成为了一件公认的好差事,尊贵的大学教授买不起“公主套房”,而月薪30多万的妓女则可以轻松拿下,整个社会信奉“笑贫不笑娼”的扭曲价值观。
(二)身体的异化
李永平笔下的台北都市还面临着身体异化的危机。性与肉体成为商品,女性按照年龄、外貌、家庭、学历等被分为三六九等,明码标价。烟花场地被名副其实地包装成各种休闲娱乐场所,服务本岛与原殖民宗主国的男性,甚至有一群台湾妇女远赴日本、美国从事色情业。《海东青》弥漫着靳五对少女失贞的焦虑,他保护着朱鸰、亚星等纯洁的女孩,害怕朱鸰过早长大。而安乐新、姚素秋、哈路桑等皮条客则像饿狼般等待着一个个“未开苞”的少女上钩,女性的身体在这个欲望都市已毫无安全感可言。《朱鸰漫游仙境》中的柯丽双为了卖出手中的花,只好忍受老男人的猥亵,以至于8岁的小女孩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欲望横流的台北现代都市,金钱至上,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父不父,母不母,一个家庭中的女儿往往无法健康安全地求学、成长,她们背负着父亲、兄长的生活账单,走上深夜、凌晨的繁华夜市。此外,身体的异化还体现在男性对女性肉体的规训以及女性对于男性喜好的迎合。《海东青》《朱鸰漫游仙境》上演了荒诞色情的“牛肉秀”“工地内衣秀”,将少女的肌肤、体毛、体香、丰乳、肥臀当作卖点公然意淫。艾弗琳·苏勒罗认为:“人们向女人出售女性的东西……女人自以为是在进行自我护理、喷香水、着装,一句话即自我‘创造’,其实这个时候她在自我消费。”[10]79台芬公司初夏内衣的设计宗旨是让男性产生“我见犹怜,吾愿把玩”之感,真正的消费者由女性转为男性,商品由内衣转为了女性的性和肉体。男女疯狂追求“娃娃脸,妇人臀”的审美标准的背后,是台北都市愈加扭曲的女性观。男性巨大的征服欲、控制欲,折射出了女性不可避免的被物化的命运。
台湾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大都会的繁荣与生活方式的变化,酒店、商城、公园、博物馆、霓虹灯、玻璃橱窗等现代性景观将台北包装成一个纸醉金迷的魔幻之都。琳琅满目的商品、歌舞升平的不夜城冲击着都市的神经,物欲、性欲无限膨胀,使现代人精神振奋。现代都市人的性格、精神状态、生存逻辑也悄然改变。李永平书写的台北空间全然无法“诗意栖居”,充斥着玩世不恭、丧失理想、追求现世享受、金钱至上、崇洋媚外的风气。靳五等人混迹人群,都市速度或许使其稍感不适,但实际上他们也兴致盎然地参与着这一都市狂欢,正如朱鸰虽视花井芳雄为“一个鬼”,但却迟迟未摘下其赠予她的日本名牌手表。李永平笔下的台北俨然异化为一个负面空间,呈现出消费、身体乃至整个社会价值观扭曲的复杂面貌。
四、结语
《海东青》《朱鸰漫游仙境》《雨雪霏霏》透过靳五、朱鸰、永这些背负身世创伤的浪子之眼,揭露了台湾现代化进程下的都市乱象与主体异化,深入国族历史、后殖民文化与资本主义层面去开掘左右社会发展与个人命运的隐力,足见李永平笔力之精湛、用意之深远。
事实上,除本文所讨论的3部小说之外,李永平后期创作的“婆罗洲冒险故事系列”《大河尽头》《朱鸰书》等也屡屡提及台湾。然而,台湾却不仅仅是他的书写对象,也是他寻找“文化母国”的起点。他曾自言:婆罗洲是他的“生母”,台湾地区是他的“养母”,而他的“嫡母”则是“文化原乡”中国大陆。我们不难发现在李永平的台北叙事中,常常出现如古中国地名、中华历史传说、方块汉字、月娘、虎骨酒等颇具中国色彩的文化意象。朱鸰这一重要人物也是以书写、吟诵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一《诗经》中的著名诗句登场的。此外,《海东青》中出现了很多叠字、叠韵、文言词语和古生僻字等,营造了一种秾丽仿古、飘逸缠绵的“语言乌托邦”,“借‘再造语言’来再造中国文化的幻象”[11]。这些皆是李永平追寻/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痕迹。李永平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既有抵抗台湾恶性西化现象及本土化浪潮的意味,同时也固守了自己的中华文化身份,映照出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