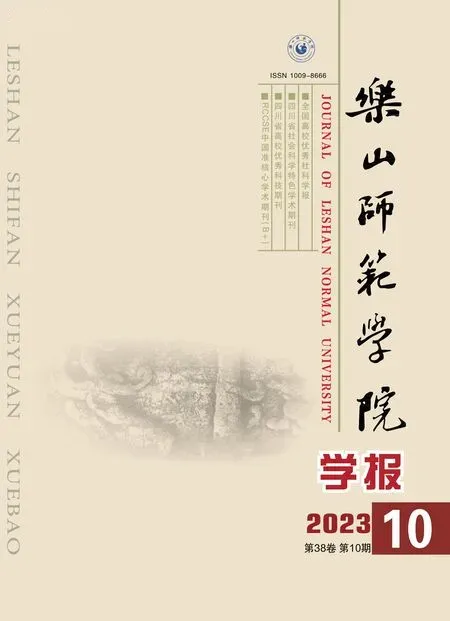中国古代戏曲题材中的杨贵妃之死
秦永芝
(广西大学 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04)
唐玄宗天宝年间(755),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叛唐,由于权臣的无能及玄宗的错判,唐兵节节败退。潼关失守后,玄宗携杨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近侍从延秋门出逃。陈玄礼所率禁军行至马嵬坡,止步不前,怒杀权臣杨国忠,并逼迫玄宗缢杀杨贵妃,至此,“炙手可热势绝伦”[1]的杨家退出唐朝政治舞台。此一举国震惊的“马嵬兵变”,历来为诸多文学家所再现。自元以后,戏曲逐渐兴起,这一历史事件,尤其是其中的李杨爱情纠葛也被戏曲家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为不同目的,再现于戏曲舞台,现存作品有:元白朴《梧桐雨》(全称《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明吴世美《惊鸿记》、明屠隆《彩毫记》、清尤侗《清平调》(又名《李白登科记》)、清张韬《清平调》、清孙郁《天宝曲史》及清洪昇的《长生殿》。其中,《彩毫记》与二部《清平调》,皆以诗人李白为主角,展示天宝年间历史的一部分,其余几部作品,皆于安史之乱的背景下着力渲染了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情史,尤马嵬坡兵变中“贵妃自缢”这一关目,各具特色。
据《旧唐书》,马嵬坡兵变、杨贵妃自缢的记载如下:
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大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上皇自蜀还,令中使祭奠,诏令改葬,礼部侍郎李揆曰:“龙武将士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葬礼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2]
《新唐书》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与《旧唐书》相似,《资治通鉴》中对贵妃之死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屡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联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申,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3]
上述可知,史官在描写杨贵妃之死时的态度是冷静客观,几近冷漠的,综合他们在史书中对杨贵妃生平的描述,不难发现史官笔下的杨贵妃是骄纵善妒、恃宠而骄的形象,杨家则借其权势霍乱朝纲,最终导致唐朝廷日益衰败。可见,史官对杨贵妃其人,是贬大于褒的,因此对马嵬坡兵变这一事件,史官们更多站在忠臣立场上对杨家进行批判,大有借此垂戒来世之意。同时,根据上述史书对杨贵妃之死的还原,可得出几点贵妃自缢的关键信息:一是杨贵妃自缢前,明皇并未与其道别,而是令高力士传诏;二是安史之乱平后,明皇秘密遣人将杨贵妃改葬,确有其事;三是杨贵妃初葬处确有尸骸,存一香囊不毁。官方的记载简短、客观,贵妃自缢的细节略去不提,给人留以无限遐想。杨贵妃自缢前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杨贵妃的心理是怎样的?唐明皇当时的态度又如何?贵妃死后明皇又作何区处?各位戏曲家都基于不同目的,在戏曲中作了不同呈现,从中可一窥“杨贵妃之死”所含文化意蕴的变化轨迹。
一、杨贵妃之“怨”:白朴《梧桐雨》
白朴(1226—?)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原名恒,后改名朴,字仁甫,后改字太素,号兰谷。白朴生际金元之世,仓皇失母,入元不仕。[4]生平所著杂剧、散曲颇丰。《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末本戏,由正末扮演唐明皇并演唱曲文。据考,白朴移居真定后,杂剧创作活跃,《梧桐雨》当也作于其居真定期间,是时白朴已历经朝代更迭,在此剧中不免流露一代兴亡之感慨。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在唐代文学中多有叙述,其中以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影响最大,白朴《梧桐雨》即取名自诗句“秋雨梧桐叶落时”[5]一句。此剧,虽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为主线,实际上更多着墨于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杨贵妃的出场并不多,且多伴于明皇旁声色歌舞。在【楔子】中,安禄山被派遣至渔阳做节度使,心下言“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远离,怎生放的下心?”[6]490白朴一开始就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丑事揭露,并在第二折中,借宰相李林甫之口道出“陛下,只因女宠盛,谗夫昌,惹起这刀兵来了”[6]498。可见,白朴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唐朝由盛转衰的缘由,与唐明皇盛宠杨贵妃有所联系,因此在第三折编排马嵬坡事变、杨贵妃自缢时,白朴并未维护杨贵妃的形象。陈玄礼率众军斩杨国忠之后,逼迫唐明皇处死杨贵妃,李杨二人的几段对话如下:
(旦云)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尚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身怎生割舍。
(正末云)妃子,不济事了,大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
……
(旦云)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
(正末云)寡人怎生是好!
……
(旦回望科,云)陛下好下的也!
(正末云)卿休怨寡人。[6]504
第一段对话,面对大军逼迫,杨贵妃立即向唐明皇求救,可见杨贵妃对唐明皇尚抱有幻想,望以情动其心,换取性命。第二段对话,陈玄礼再度相逼,杨贵妃更是直接而急迫地向明皇呼救,求生欲望愈发强烈。第三段对话,杨贵妃求救无望,高力士引其至佛堂,她终于绝望,回头望向曾经的枕边人,发出了怨恨之声。可见,白朴笔下的杨贵妃有以色误国之嫌,在生死面前亦有自私的一面,被迫自缢前心有不甘,对此时无能的明皇更是充满了怨恨。值得注意的是,在《梧桐雨》中,杨贵妃死后,陈玄礼还“率众马践科”,出现了“马践杨贵妃”的关目,可见众军对杨贵妃的愤怒非常。宋金之际《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中第五出提到的剧目便有《马践杨贵妃》[7],可见在宋金时的民间已有众军以马践杨贵妃遗体的传说流传,白朴受此影响,在杂剧中进行了艺术加工。《梧桐雨》全剧于唐明皇长生殿中思忆杨贵妃中落幕。
白朴《梧桐雨》一剧,“因歌舞而坏江山”的主旨是较鲜明的,这不仅是受前代史官笔墨的影响,亦与白朴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天兴二年(1233),元兵攻破汴京,白朴时年八岁,与元好问北渡,拘管于聊城,白朴生母也于动乱中丧命。白朴成年后迁居真定,拒绝仕元,亦可见其内心的战争创伤。他将白朴自身战乱经历代入到剧作《梧桐雨》中,便能理解他对杨家的痛恨,批评杨贵妃的以色误国,添油加醋将贵妃之死搬演上戏曲舞台,自然情有可原。细读《梧桐雨》中所述贵妃之死,杨贵妃对唐明皇有怨、有恨,随着事态的愈发紧急,白朴对杨贵妃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与明皇的几句宾白中,有些许惋惜与同情。尤其第四折,白朴用一整折的内容,让读者与观众随着唐明皇的视角思忆杨贵妃,让人与明皇产生共鸣,所以说白朴对杨贵妃的处理又是有些许矛盾的。元破京时,白朴才是幼童,白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入仕,但其生平基本都靠着依附朝中做官的亲友生活,且据《录鬼簿》记载,白朴曾受赠嘉议大夫太常卿[8],所以他也并非一概以金遗民自居。或许正是白朴这种对元朝廷的暧昧不明,造成了《梧桐雨》中杨贵妃之死这一关目的矛盾建构。
要之,白朴《梧桐雨》中的杨贵妃享尽明皇恩宠,却与安禄山有染,有以色误国之嫌。马嵬坡兵变,杨贵妃临死前向唐明皇挣扎求救,赴死时她是不甘的,对唐明皇众人更充满怨恨。杨贵妃死后,唐明皇对她的思忆又极令人动容,可见白朴《梧桐雨》创作中的矛盾,而这与白朴的个人经历分不开,他幼经战乱,仓皇失母,心中有战争创伤,虽不仕元,却依附仕元亲友,对元朝廷的态度暧昧不明,这种暧昧反映到创作中,形成了对杨贵妃之死的矛盾表达。
二、杨贵妃之“怒”: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
王伯成是晚于白朴的戏曲作家,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均不详,但据明贾仲明挽词,王伯成与马致远为忘年交,与张仁卿为莫逆友。[9]50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仅于《雍熙乐府》《太和正音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北词广正谱》等著作中存得残曲,郑振铎、冯沅君、赵景深等学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曾各自整理过辑本,近代学者朱禧在此基础上辑成《天宝遗事诸宫调》一书,便于查阅。据朱禧所辑,有关杨贵妃马嵬坡身亡的套数共存十八套,从这十八套曲辞中,可看出王伯成书写杨贵妃之死的重要转变。
诸宫调是流行在宋、金、元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由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牌体韵文和若干段散文夹杂组成,用来叙述一个长篇故事,是当时说唱诸宫调的艺人的文学脚本。诸宫调的说唱特点,使得曲文必须要充分表达人物的情绪和心理,《天宝遗事诸宫调》描述马嵬坡杨贵妃身死时,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唱词便颇耐人寻味。
马嵬坡军士哗变,面对禁军压迫,唐明皇哀告陈玄礼,乞饶贵妃,无力扭转局面时,他只能舍弃杨贵妃,为不牵连自身銮驾,急急催促:
【柳叶儿】可怜见唐朝天下,教寡人独力难加。将条素白练急早安排下,把娘娘咽喉掐。他是娇滴滴海棠花,卿呵,怎下的千军万马踏!
【兴龙引】重权独霸,久养威转加,致教主弱臣强,内外忒差。其间事节,莫不也干连着銮驾?赐一条素练,撅三尺黄沙!
【么篇】斟量口气,见得将他难救拔。教娘娘速赴辕门,早受刑罚。非干易舍,便告的半霎儿严假,枉与他广增些怨望,剩添些惊怕。[10]77
唐明皇一面假惺惺地怜惜杨贵妃,觉她是“娇滴滴海棠花”,“怎下的千军万马踏”,一面又担心其间事节“干连着銮驾”,于是“将条素白练急早安排下,把娘娘咽喉掐”,催促杨贵妃“速赴辕门,早受刑罚”,可见在危难面前,唐明皇为保全自身,舍弃了杨贵妃。杨贵妃对此自然不甘,但她不像白朴笔下的杨贵妃般挣扎求救,满心埋怨,而是将愤懑全力输出:
【么篇】“陛下!着哀告敢为敢做的陈玄礼,更不弱如当世当权郭子仪。又不曾背叛朝廷,篡图天下;又不曾违犯国法,误失军期。平白地处死,无罪遭诛,性命好容易! ”[11]64
【金菊香】“早忘了长生殿夜参差,悄悄无人私语时,枕边誓约中甚使?钿盒金钗,放着证明师![11]66
【么篇】“早则耳干眼净众娇姿,早则意断恩绝两姓子。有句话再三嘱咐你,若得见君王,却道俺传示![11]66
【尾声】“把我生勒死,不知为何事?若施行了之后,却休教死骨头上揣与我个罪名儿。”[11]66
通过以上四支曲,杨贵妃把对唐明皇的怨恨一股脑全倾诉出来,且她认为自己“又不曾背叛朝廷,篡图天下,又不曾违犯国法,误失军期”,并未到要遭众军屠戮的地步。她责问唐明皇是否早已忘了长生殿中二人私语、枕头边誓约、金钗为证,更不甘自己死后,被背上亡国祸水的罪名!【金菊香】【么篇】【尾声】三支连曲层次递进地宣发杨贵妃临死前的愤怒,易引起听众的共情,作者王伯成也借杨贵妃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该历史事件的理解,即杨贵妃只是被政治裹挟的一位女子,难担祸国殃民的罪名,所以王伯成有意为她鸣不平。也正因此,在描写“马践杨贵妃”这一关目时,王伯成并不像白朴,仅以一科介示之,而是用了四套曲,详尽描绘了杨贵妃死后被千军万马践踏的情形,她“马蹄踏荡无寻处”的下场,令人不忍卒读。
相较于白朴的《梧桐雨》,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中,对唐明皇统治下的唐朝廷批判色彩更明显,这不仅体现在唐明皇对杨贵妃的舍弃上,还体现在其他亲历者的口述中。高力士是全程目击了李杨爱情及安史之乱的人物,在杨贵妃死后,他曾哭祭道:
【干荷叶】明明是不曾题,暗暗地早任谁知,做多少英雄势,见放着乱宫贼,不敢与他做头敌。既然教奸妇一身亏,你却须合问那奸夫罪![11]74
【六么令】早则都你东我西,惩平地葬送三不归:却教父南子北无前事,间隔在两下里;到黄泉,见寿王迎礼,第一句说甚的?是子是皇妃?情理却也受煞你将军气![11]75
【干荷叶】一曲,王伯成借高力士之口,道出了君臣的虚伪及无能,不敢与叛军做头敌,而是强加罪于杨贵妃。【六么令】点出了杨贵妃死后的尴尬处境,至黄泉,其身份究竟“是子是皇妃”?讽刺唐明皇强夺自己儿媳的行为,此乃君王的失德。
虽王伯成生平事迹不可考,却也不难从《天宝遗事诸宫调》的【引辞】部分推测其创作意图。《天宝遗事诸宫调》流传下来的引辞有三套,主要保存在《雍熙乐府》这一戏曲选本中,引辞云“将天宝年间遗事引,与杨贵妃再责遍词因。剔胡伦公案全新,与诸宫调家风创立个教门。”[10]89(《天宝遗事引》)“胡伦”,即“囫囵”,整个儿之意,王伯成要重新评价李杨这桩历史公案,据上述文本分析不难看出,王伯成有批判唐明皇、为杨贵妃鸣不平之意,与之前大多数作品(包括白朴《梧桐雨》)的主要思想都不同。关于安史之乱爆发的缘由,王伯成也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恩多决怨深,慈悲反受殃,想唐朝触祸机,败国事皆因偃月堂。张九龄村野为农,李林甫朝廷拜相。”[10]80(《遗事引》)偃月堂,是李林甫堂名,《新唐书·李林甫传》载:“林甫有堂如偃月,号偃月堂。每欲排构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伤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12]后因以喻称权臣嫉害忠良的地方,可见王伯成认为安史之乱罪魁祸首乃李林甫等一众权臣,而非杨贵妃之过也。
要之,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一作,描写马嵬坡杨贵妃身死与前作有很大区别,他以杨贵妃的视角,愤怒地责问、抨击危难时舍弃她的唐明皇,坚决不肯背负亡国罪名,并详尽地“唱”出杨贵妃缢死后万马践踏的凄凉场景,令闻者伤心。同样是艺术虚构,相较于白朴创作的矛盾,王伯成更清晰的表达了对唐明皇及当时权臣的批判,为杨贵妃发出不平之音,《天宝遗事诸宫调》也成为文学艺术虚构中杨贵妃形象由贬到褒的转折之作。
三、杨贵妃之“真”:屠隆《彩毫记》与吴世美《惊鸿记》
明代有两部传奇作品涉及到李杨题材,即吴世美《惊鸿记》及屠隆《彩毫记》。继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之后,这两部作品对杨贵妃的维护之意更明显,并大力宣扬了李杨之间的爱情。
吴世美,字叔华,乌程人,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初前后(1573)在世。其《惊鸿记》中,杨贵妃形象的塑造比《彩毫记》要更立体一些,主要演唐明皇与梅妃、杨贵妃事。该作的主要角色是梅妃,作者不免将杨贵妃塑造成一个恃宠而骄、善妒的宠妃形象,但吴世美对她并未过多谴责,而是颇具欣赏的眼光,更遑论将亡国罪名安在一妇人身上。《惊鸿记》在叙述马嵬兵变、杨贵妃身死关目时,又有不同的艺术虚构,涉及出目有:二十七出《马嵬杀妃》、三十五出《马嵬移塟》、三十七出《香襄起悼》、三十八出《仙客蜀来》、三十九出《幽明大会》。
《马嵬杀妃》一出中,杨贵妃得知军士哗变、众军逼明皇赐死自己时,她的反应是:“(贴向生作悲跪云)陛下顾远计宗社,何必恋一妃?妾诚负国,死无所恨。”[13]132杨贵妃从国家宗社的角度出发,深明大义地诚劝明皇顾及国家、不要贪恋儿女私情,杨贵妃的形象相比前作,有了质的跃升。吴世美之后用大段曲文和宾白来渲染帝妃死别之情状,可见二人之情真,极令人动容,最终贵妃在嘱托高力士“你为我坚心圣皇”[13]135后从容赴死。吴世美还有意略写了贵妃缢死的过程,且未虚构将士以马践尸的情节。《马嵬移塟》一出,演安史之乱后,高力士与李念奴奉旨于马嵬坡移葬杨贵妃,高力士在遗骸处寻得锦香囊,归还与明皇作一念想,该出内容与正史符合。《香襄起悼》一出,演明皇见香囊而思悼杨贵妃。《仙客蜀来》一出,演杨贵妃死后归列仙位为太真王妃,托临邛道士传书与明皇,内有钿合金钗为证。《幽明大会》一出,演杨贵妃(太真王妃)借道士口与众人会,道士开解明皇等人道:从今后那悲欢索无益,莫痴心,向七夕迷离。[13]187颇有些佛道思想的意味。
上述可见,吴世美《惊鸿记》与《梧桐雨》《天宝遗事诸宫调》相较,最大的不同是同时拔高了杨贵妃与唐明皇的形象,在马嵬坡贵妃身死一关目中,表现了二人之情深,将杨贵妃塑造成考虑家国宗社、深明大义、从容赴死的形象。太真王妃托道士传信这一情节,也是前作未曾出现的,加之临邛道士对李白、唐明皇等众人的传道,可体会到吴世美在此作中融入的佛道思想。
屠隆(1543—1605),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别号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客,晚年又号鸿苞居士,其《彩毫记》主要演李白事,约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后,此作描写杨贵妃的情节占比并不多,主要有贵妃荐李白、贵妃捧砚、贵妃请死等关目。杨贵妃总体形象是一个爱才的宠妃,至安禄山叛乱,杨贵妃听说安禄山叛乱是“以诛杨氏为名”时,说道:“反贼既以诛杨氏为名,罪在贱妾,敢效一死,以谢万姓。请赐自尽,勿误国家大事。”[14]3281可见此时的杨贵妃是深明大义的,相比前作,唐明皇对此事的应对也变得更正面:他安慰杨贵妃“彼不过借你为兵端,卿亦何罪?誓同生死”[14]3281。需单独说明的是第三十四出《蓬莱传信》,该出描写了唐明皇遣清虚道士上天入地寻求杨贵妃游魂,道士终在蓬莱仙宫与杨贵妃得见,替明皇、贵妃二人传相思之情。《蓬莱传信》一出,杨贵妃为主唱,思忆唐明皇时,唱词颇缠绵悱恻,为二人的爱情添一份真意。当她得知明皇如今的处境,还自责道“李君多难,皆贱妾为之也,追悔何及”[14]3314,将明皇遭受的苦难归咎于自身,再现杨贵妃之“真”,此出对道士寻访杨贵妃、替李杨传信的描述颇为具体,当受《惊鸿记》的影响。
上述吴世美《惊鸿记》与屠隆《彩毫记》有颇多相同之处,二者都有意维护唐明皇与杨贵妃之形象,赞扬二人之间的真情,最后杨贵妃升仙、蓬莱传信等关目,都融入了佛道思想,这些共同点与二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与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二人都生活于明万历时期,此时社会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们对戏曲这种通俗文学的需求也愈发旺盛。明中叶王李之学兴起以后,文学创作倡导真情实学,汤显祖、袁宏道等人将其思想发扬光大,以至“士大夫靡然信之”,“士风大都由其染化”[15],由此汤显祖开启戏曲“至情论”的创作之路,戏曲家纷纷效仿,很明显,吴世美与屠隆都受到尚情社会思潮的影响,并作出了响应。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虽吴世美生平不可考,但他与屠隆一样,笔下的杨贵妃都从家国宗社出发,自愿赴死,且有意维护了唐明皇的形象,屠隆受恩于皇朝,剧作中难免掺入儒家正统思想,由此看来,吴世美应当也接受过儒学教育。两部作品中,杨贵妃升仙、蓬莱传信等内容也颇为一致,屠隆晚年曾遨游吴越间,寻山访道,且从他自号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客、鸿苞居士可看出其修禅问道之心,因此在作品《彩毫记》中融入佛道思想,既迎合了民众尚情、尚奇的娱乐需求,又表达了自己的本心。
要之,明代吴世美《惊鸿记》与屠隆《彩毫记》在描写杨贵妃之死时有颇多相似之处,二部作品都较生动地描绘出李杨二人临别时的不舍,表现二人之情“真”,杨贵妃赴死的态度不同于《梧桐雨》的求助、《天宝遗事诸宫调》的责问,而是为唐明皇考虑,自愿请死,其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拔高。吴世美、屠隆二人在明中叶以来解放人性的呼声下,自发描写了李杨之间的真情,下意识忽略安史之乱中李杨的过错,又出于个人学习、生活经历融入正统意识和神仙教化思想。
四、杨贵妃之“忠”:洪昇《长生殿》
清时与李杨题材有关的戏曲作品有四:尤侗《清平调》(又名《李白登科记》)、张韬《清平调》、孙郁《天宝曲史》及洪昇的《长生殿》。
尤侗、张韬的二部《清平调》皆演李白事,未正面描写安史之乱、马嵬坡事变,杨贵妃以正面形象出现,二剧中的杨贵妃皆慧眼识珠,欣赏李白之才学,未涉安禄山事,与明时《惊鸿记》《彩毫记》相比,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杨贵妃形象。孙郁《天宝曲史》一剧,从剧名即可看出孙郁“以剧写史”的目的,所以他多从历史史实描写杨贵妃事迹,并未过多美化。
写李杨题材最为细致生动、影响最大的当属洪昇的《长生殿》。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树、南屏樵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洪昇《长生殿》共五十出,将安史之乱、唐朝盛衰背景下的李杨爱情娓娓道来,剧中将贵妃之死描述得更为详尽,从上卷第二十四出至下卷第五十出,用整整大半的篇幅,编排了杨贵妃马嵬坡身死、李杨生死诀别、别后明皇追忆、改葬、寻访、重圆等内容,通过第二十五出《埋玉》、第三十出《情悔》、第四十三出《改葬》、第五十出《团圆》等出目内容的分析,可见洪昇描写杨贵妃之死与前作的异同。
《埋玉》一出,杨贵妃赴死时的态度又有一定的变化,当陈元礼(即前作中的陈玄礼)率众军要逼杀杨贵妃时,面对悲伤无措的唐明皇,杨贵妃不仅不惧怕,还三劝唐明皇舍弃己身:
(旦哭介)陛下呵【耍孩儿】事出非常堪惊诧,已痛兄遭戮,奈臣妾又受波查。是前生,事已定,薄命应责罚,望吾皇急切抛奴罢,只一句伤心话。[16]181
(旦跪介)臣妾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16]182
(旦)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焚,徒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16]182
杨贵妃第一段曲白,将此劫定为命数所归,劝明皇早日抛弃自己,明皇不肯,杨贵妃跪下再劝明皇,舍却自己,稳定军心以保证明皇安稳至蜀地,明皇再三挽留,杨贵妃以保家国宗社为由,三劝明皇赐死自己,可见杨贵妃之忠,既忠于情义,亦忠于家国。面对这样的杨贵妃,洪昇亦贴心地删除了元代文学戏曲作品中常见的马践杨贵妃的关目,众军仅入内查验杨贵妃尸首后退场。
相比前述李杨题材戏曲作品,《长生殿》最独特之处是安排了《情悔》一出,该出述杨贵妃游魂在马嵬坡飘荡,思忆往昔,忏悔道:(悲介)只想我在生所为,那一庄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姐妹,扶势弄权,罪恶滔天,皆总由我,如何忏悔得尽?[17]33杨贵妃悔自己生前恃宠而骄,家亲借此搬弄权势,以致家国遭难。上述屠隆《彩毫记》杨贵妃亦有忏悔之举,但她只是感慨自己牵连唐明皇,至洪昇《长生殿》,杨贵妃的格局更大。洪昇安排《情悔》一出的意图,在其自序中便可寻得蛛丝马迹,其自序言:“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且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未有不悔者也,玉环倾国,卒至殒身死而方知情悔何极,苟非怨艾之深,尚何证仙之与?”[16]8可见洪昇写玉环情悔,有“垂戒来世”的目的,凸显了其正统思想及忧患意识。
洪昇写《尸解》《改葬》《重圆》等出,又具新意。前述戏曲作品中,杨玉环埋尸处,确有遗骸在,洪昇《尸解》则演杨贵妃在织女引导下练形度地、尸解上升,因此坟中已无遗骸痕迹。《改葬》一出演唐明皇为杨贵妃改葬事,正史记载唐明皇因顾及军士,密令人改葬杨贵妃,前述《惊鸿记》亦叙明皇令高力士、李念奴改葬杨贵妃,而在《长生殿》中,唐明皇亲返马嵬驿,为杨贵妃迁葬,可见二人情谊之坚。前述几部涉及杨贵妃之死的作品,《梧桐雨》《天宝遗事诸宫调》皆止于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忆之中;《惊鸿记》《彩毫记》至道士寻访杨贵妃仙魂、李杨以信传情结束;《长生殿》则用近五分之一的篇幅(《雨梦》《觅蒐》《补恨》《寄情》《得信》《重圆》),重新虚构上述关目,并安排了李杨重逢、玉帝赐旨二人永结夫妻的大团圆结局,给这段姻缘画上了完美句号,这是作者对笔下那位忠于情义的女子最好的慰藉。
洪昇《长生殿》很明显也承继了晚明“尚情”创作思潮,同时亦具正统思想与忧患意识。据章培恒所编《洪昇年谱》可知,洪昇与妻子相互扶持、恩爱甚笃,想必这也是他塑造杨贵妃忠情、忠义的原因之一。洪昇外祖黄机尝仕清为大学士,父亦仕清,家饶藏书,他本人天资聪颖,髫龄即跻身作者之林,平生放荡不羁,好诮讽权贵,以此取憎于时。[18]可见洪昇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且傲视权贵,忧心国家。正是洪昇个人经历与成长环境的结合,才诞生了既具“尚情”风格又兼正统思想的《长生殿》。
五、结语
历史中的杨贵妃常被批评为亡国祸水,正史对她的评价贬大于褒。她集六千宠爱于一身,骄奢淫逸,杨家借此权倾朝野,得宠并非过错,然杨家专权误国、败坏朝纲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致于安史乱起,红颜薄命,身死马嵬。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美人,自然是通俗文艺作品中广受作家与民众喜爱的人物,从历史到虚构,从文本到表演,许多关于杨贵妃的说唱、戏曲、小说,塑造出了不同的贵妃形象、对贵妃之死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艺术虚构。元白朴《梧桐雨》指出杨贵妃以色误国、唐明皇因歌舞而坏江山,却又将明皇思忆的曲白写得极为凄婉动人,体现出白朴描写贵妃之死的矛盾心态,这与其对元朝的暧昧态度有关。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有为杨贵妃翻案之意,贵妃临死前的愤怒,既是作者为她鸣不平,也是对造成王朝衰败的权臣的痛恨,这部作品可视为戏曲作品中杨贵妃形象由贬到褒的转折之作。吴世美《惊鸿记》、屠隆《彩毫记》二部作品,亦承前人王伯成的脚步,美化贵妃形象,但他们是从杨贵妃对唐明皇的真情出发,而非政治上的直接评判,吴世美、屠隆都受到明中叶以后“尚情”思想的影响,着重写男女之情,李杨之间的真情通过马嵬坡贵妃之死达到高潮,同时也因作者个人经历与喜好,加入了儒家正统意识与佛道思想。至清洪昇《长生殿》,李杨爱情题材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洪昇叙述马嵬坡贵妃之死时,贵妃是一个为明皇、为家国宗社再三劝明皇舍弃自己的妃子,她忠于情、忠于义、忠于家国,李杨爱情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更显珍贵,令人动容。唐明皇亲自为杨贵妃改葬这一细节,更证二人之忠情,最难能可贵的是杨贵妃魂游马嵬时的情悔,体现出作者洪昇的忧患意识。为褒扬李杨爱情、也为了寄托心中所愿,洪昇特意安排了大团圆结局,这是从前作品从中未曾有过的创新之举。显而易见地,洪昇作品中一方面既继承了晚明“至情论”的戏曲创作风格,一方面也体现了洪昇的正统思想与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