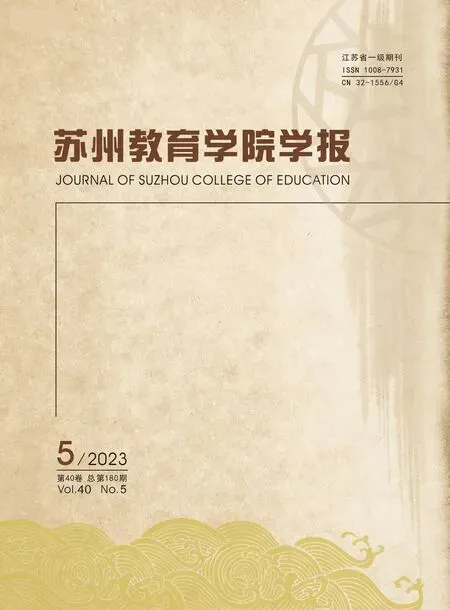戏仿的侦探小说与解殖民诉求
——论周瘦鹃《临城劫车案中之福尔摩斯》
张锐雪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1923年5月,津浦线上的一辆特别快车在即将行至临城站时,被盘踞在此的千余名土匪持枪肆意劫掠,车上百余名中外旅客被绑架,上演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由此引发了严峻的外交危机与殖民问题。同年,周瘦鹃在杂志《滑稽》①《滑稽》由包天笑编辑,1923年10月创刊,16 开本,仅出过2 期,由大东书局在上海出版发行。在当时有两份名为《滑稽》的刊物,另一份《滑稽》为月刊,1920年1月创刊,由漫画家张聿光、钱病鹤、丁悚等联合发起创办,上海生生美术公司出版发行。上发表了以此案为原型的短篇小说——《临城劫车案中之福尔摩斯》[1](以下简称《临城》)。小说戏仿了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创作的神探福尔摩斯,描写了他在中国的旅行与奇案故事。这既是一次戏仿、重构西方侦探小说的文学实践,也是周瘦鹃对殖民问题的现实回应。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长期处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语境之中。以周瘦鹃为代表的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遭遇了怎样的冲击?除商业性与娱乐性外,其对西方小说的戏仿是否蕴含了更深层的价值观念?面对这些问题,《临城》正可以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然而,在有关周瘦鹃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解殖民冲动的众多研究中,该文本并未受到重视,在王智毅编的《周瘦鹃研究资料》、范伯群和周全编的《周瘦鹃年谱》及范伯群主编的《周瘦鹃文集》中均不见其身影。因此,本文拟以《临城》为窗口,探讨民初知识分子在半殖民环境中,交织在解殖民叙事中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向度。
一、半殖民视角下戏仿的侦探小说
周瘦鹃所处的半殖民语境是其创作的重要历史背景。就晚清民国的国家形态而言,中国处于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和被奴役殖民国家的中间状态。诚如李永东提出的“半殖民性”的特征:“近代中国受到多重帝国多层次的殖民宰制,殖民区域与主权地区、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并置共存,二者构成了碰撞、协商、互动、交融的动态关系,殖民与解殖民同时进行,从而造成殖民宰制的有限、零散、流动和区域不均等。”[2]9清末民初亡国灭族的危机导致社会秩序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变动,中华民族文化以及人民长期的价值认同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适逢1923年5月发生的“临城劫车案”,悍匪劫持两百多名中外人质长达数月,盘踞在山东抱犊崮与政府及列强谈判。由于其中涉及在华诸国西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因而引发了进一步的殖民危机。内忧外患之际,北洋军阀政府选择弃国人安危于不顾,承诺“以保全外人生命为第一目的”[3]。政府讨好列强、罔顾国民性命的行径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感。幸而此时的中国并未完全沦为殖民地,中国的知识分子尚有甄别与回旋的余地。
面对列强的趁机倾轧,周瘦鹃企图用小说创作诉说半殖民地知识分子解殖民的冲动。解殖民,是对“Decolonization”一词的翻译,意为“拆解、消解、消融、抹去殖民化的不良影响,解构殖民宰制话语和西方中心主义,重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2]7。清末民初,各方殖民势力的强势介入对中国造成了多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变动过程体现在人民的文化态度及信仰的变化中,在此背景下,新的价值观迅速萌发、生长。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存危机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便处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语境之中,其中充斥着西方对中国的侵蚀、欺辱、不平等的国耻以及创伤意识。由此,近现代的中国人民不得不在东、西方碰撞的复杂环境中褪去“华夏中心主义”的骄矜,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
由此,晚清民国的有志之士企图以科学文明等话语启蒙大众、革除旧习,“小说”这一文体便被梁启超等知识分子赋予了改良群治、救亡图存的作用。有学者称,“近代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学首先是从小说开始的,而在西方小说中,接受最早、理解最快的是侦探小说”[4]。从消费与读者接受的视角看,中国作家本土再造的滑稽侦探小说,显示出异域侦探小说对本国读者的强大吸引力。而正是这些大量被引进的侦探小说与翻译文本,帮助本国读者掌握、熟悉了有关探案的主题内容及异域形象,使得《临城》一类的本土文人戏仿作品有所凭依。
另外,周瘦鹃翻译域外小说的经历为其戏仿异域文学形象提供了前提条件。周瘦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其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受到鲁迅嘉奖,盛赞其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5]。同时,周瘦鹃也是“福尔摩斯系列”及“亚森罗苹系列”①周瘦鹃与天虚我生、半侬等人合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中译合集。同时,周瘦鹃也是大力翻译“亚森罗苹”系列小说的翻译家之一。1914年《时报》刊出周瘦鹃翻译的《胠箧之王》;1915年《礼拜六》第3 期刊出周瘦鹃翻译的《亚森罗苹之劲敌》和《亚森罗苹之失败》;1925年周瘦鹃又联合大东书局推出《亚森罗苹案全集》。等侦探小说进入中国的有力推手。侦探小说布局悬念叠生,情节曲折离奇,极受读者欢迎。从周瘦鹃集编、译、著三者的文化身份来看,其中也不乏商业考量。但除商业牟利因素外,侦探小说作为特殊的文类,实可见证西方启蒙时代的人文传统、政法制度、都市文明以及科技发展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加之侦探小说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在主题内涵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在文化心理上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然而,这两种小说类型实则展现出中西文化的极大差异——如法治与人治、科学实证与主观臆断、人权与皇权等价值冲突,正呼应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公理、正义、民权的呼吁,与救国和革新的急迫性不谋而合,因此被视为启蒙的全新模板。这也是周瘦鹃选取侦探小说这一文类作为宣扬其文化价值的载体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临城》以娱乐杂志《滑稽》作为发表刊物,且作者署名为“周瘦鹃戏述”,由此观之,小说的通俗娱乐性乃是题中应有之意,其意趣似乎与救亡图存等话语相去甚远。文中也不乏戏谑的描写,如写绑匪登场:
瞧他的手中正握著一枝挺大的手枪,注著自己的脑门,接著又听得嘴里叽哩咕噜的骂著,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话,只觉得一股葱臭直冲鼻观,达到五脏殿,几乎把刚才吃下去的面包、牛油、牛尾汤、铁排昌鱼一起呕了出来。[1]
周瘦鹃用语极尽夸张之能,将绑匪的滑稽形象勾勒出来,消解了严肃紧张的绑架氛围,令人捧腹。此类戏作乃“洋为中用”,尽管《临城》的情节荒诞不经,叙述幽默诙谐,但诚如周瘦鹃早在1921年所言:“须知道孔圣人所说的‘游艺’,就是三育中发挥智育的意思。诗人所说的‘善戏谑兮’,就是古来所说‘庄言难入,谐言易听’的意思。可见(游戏)这两个字,真是最正经的。”[6]可见,《临城》并非只为“游戏”而生。在“戏述”的形式背后,作品中的“戏谑”与“说教”仍需细细打磨,作家期望能在新型媒介中形塑出启蒙大众的新型文本。在半殖民背景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除了商业谋划和经济目的等因素,《临城》中还潜藏着作者传递文化价值观念的功能。这类小说是作者利用晚清时期侦探小说之“热”,通过戏仿异域小说、新编与杂糅中西文化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塑造国民文化观念。
二、代言的侦探与另类的“凝视”
《临城》中的福尔摩斯叙述有何独特性?一个西方文学形象是怎样经周瘦鹃之手传递文化讯息的?福尔摩斯形象的本土化又有何文化意义?这其实是思考其他问题的出发点。《临城》讲述了大侦探福尔摩斯与华生来中国游历却遭遇了临城劫车案的故事。这场异国旅行是故事的背景及叙述的中心,小说交代了福尔摩斯选取中国作为旅行目的地的原因:“中国是东方古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物,一定是大有可观的。”[1]短短一句话便点出了中国对于西方人的吸引力。福尔摩斯和华生乘坐了“大中国号”轮船,福尔摩斯毫不犹豫地指出对参观对象的期待,“两颗心别别地跳著,似乎早已飞到中国去了”[1]。这艘轮船本是要开往上海,华生在途中读了一本英国人写的北京游记,“见了那前清的皇宫和颐和园、天坛一类照片”,便又“搭火车到南京,渡了江,搭津浦车北上”。[1]小说呈现了中国交通运输之便利与器物之发达,文中随处可见这位西方人对中国的夸赞,“华生见车中装饰很讲究,又快乐非常,觉得英法两国的火车也不过如此”[1]。《临城》中很少花费笔墨正面塑造福尔摩斯的形象,更像是把他当作一个文化符号,指代的是周瘦鹃心目中任何一个可以被替代的异域游客。
中国最早译入的侦探小说,大约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1896年,上海《时务报》首先刊登了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福尔摩斯以睿智过人的私家侦探形象出现在晚清人民的视野中。①1896年,《时务报》刊登了由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歇洛克·呵尔唔斯即福尔摩斯。参见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 期,第81—85 页。睿智与正义是福尔摩斯的主要特征,以机敏的头脑侦破悬案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固定模式。这近乎为福尔摩斯贴上了智力超群、无所不能的标签,使得此后文本的论述中心皆未偏离以上特征。吴趼人评价道:“侦探手段之敏捷也,思想之神奇也,科学之精进也,吾国之昏官、聩官、糊涂官所梦想不到者也。”[7]吴趼人将中国的昏庸官僚与福尔摩斯进行对比,突出了西方的进步与福尔摩斯的神思敏捷、机警过人。而在临城劫车案发生过程中,福尔摩斯失掉了原著中的智慧,完全被绑匪牵着鼻子走。《临城》中福尔摩斯自述:“全世界赫赫有名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和他的助手华生可怜竟做了抱犊崮中中国强盗的俘虏了,一连一礼拜困在强盗们包围之中,再也逃不了。”[1]福尔摩斯既没能逃离绑架的危险,更无法侦破凶手,反而以被戏弄告终。显然,《临城》并未将福尔摩斯置于叙述的中心,连“神探”思考与破案的步骤也不愿多作展示。作者仅仅将福尔摩斯作为代言异域文化的符号,将其性格特征进行了简化,明显跳出了睿智、机敏等独特的个人形象特征。
那么,对福尔摩斯形象的戏仿和简化体现了作者怎样的叙述意图?“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8]因此,《临城》中塑造的异国形象的背后也隐藏着半殖民地文人对于异域与本土的文化想象。以异域的视角“凝视”本土,不仅可以杂糅与转化他者形象,还能通过“他者”的视角重塑“自我”。周瘦鹃在想象“他者”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于“自我”的定位。
作为来到中国的西方游客,福尔摩斯的言行代表了作者眼中的西方,周瘦鹃迫切地需要在与“他者”的对比中找到自身定位。作为游客的福尔摩斯在对比中定义“他者”,呈现中、西方的文化差距;而阅读文本的读者,则借助福尔摩斯这一形象,对比自己眼中的他者——即福尔摩斯代表的西方人,从而把握自己的文化身份。由此观之,福尔摩斯是作者的代言人,也是作者所塑造的西方文化的代言人。周瘦鹃的读者大多是市民阶层,他们不了解世界的风貌,需要依靠阅读报刊才能窥见世界的一角。借由福尔摩斯之眼,周瘦鹃带给本国读者全新的世界观与自我认知。这种被形塑的价值观传达出中国并不劣于西方的认知,从而降低读者“亡国灭种”的身份焦虑,这便构成了周瘦鹃解殖民叙事的一环。
不过,周瘦鹃笔下福尔摩斯的“凝视”作为一种观看方式,缺少了福柯理论中“凝视”暗含的主体的强势与客体的无力和被动的特征[9],而呈现出一种“另类的凝视”——在“凝视”过程中,周瘦鹃借福尔摩斯之眼选取他们眼中异域文化意义稠密的参照物与西方景物进行对比,证实中国的交通之便利、器物之先进,将游客凝视的主体强势性完全抵消,其目的是帮助本国读者逐渐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符号,确认中国的优越性。
此外,从福尔摩斯被卷入临城劫车案起,他就从悠闲的异域游客转变成被中国强盗绑架的外国俘虏。柯南·道尔塑造的“神探”在周瘦鹃笔下成了无法逃脱中国强盗控制的普通人,隐约构成了“庸人”与“能人”的分裂。如果说福尔摩斯约等于周瘦鹃眼中西方的代言人,那么,在临城劫车案中福尔摩斯的落败,则是周瘦鹃有意突出中国的胜利,他对福尔摩斯的矮化也间接代表着对西方文明的矮化。周瘦鹃对西方文明的矮化,则有益于安抚中国读者因身处半殖民地所产生的自卑情绪,进而达到强化民族身份、增强民族自信的叙述效果。这符合处于半殖民地的清末民初民众对于国家发展前景和国家身份的期望与预设。
在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中,由于土匪绑架了洋人,各国列强反应激烈,更欲以此为借口趁机扩大势力范围,便于实施进一步的殖民计划。公使团提出以12日午夜为最后解决期限,否则将依时提出加倍赔偿。[10]列强更意图代管中国铁路干线、进行联合海军示威、派遣国际军队赴山东驻扎……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半殖民地的民族创伤持续刺痛着中国人民,国土被侵占和瓜分的屈辱以及对政府无能、社会混乱的不满形成了一种新的张力,在此张力笼罩下的中国人迫切需要探索和确定自己在外部世界的位置。曾经天朝上国的最后一丝骄矜还残留在半殖民地文人周瘦鹃的笔下,小说通过戏仿的侦探、虚拟的“凝视”重申文化身份,并以小说的现实意义帮助读者在与他者文化的接触中重拾文化自信。
周瘦鹃借福尔摩斯之口渲染中国的器物之先进、交通之便利、建设之宏伟,以福尔摩斯的落败矮化西方,使读者在对比和审视中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实现对异国文化的预想。正是在另类的“凝视”体验中,小说通过福尔摩斯的“代言”实现了中国读者对于西方文化的想象。周瘦鹃对西方文学形象的戏仿,完成了他对中西文化语境的交互与重构,使小说人物的文化身份游移于本土与异域、自我与他者之间。
三、“归化”的盗贼与正义的召唤
《临城》中,相较于被矮化的福尔摩斯形象,作为“剧贼”的亚森罗苹才是周瘦鹃要突出的人物形象。莫里斯·勒布朗笔下的亚森罗苹是法语侦探文学中一个不朽的形象,在《空心岩柱》《一颗炮弹片》等小说中,亚森罗苹总是劫富济贫,连连挫败叛国者与资本家的阴谋。勒布朗将这位几乎无所不能又专事劫富济贫的盗贼,描绘成神通广大的英雄人物。
亚森罗苹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是《小说时报》于1912年第15 期发表的杨心一译的《福尔摩斯之劲敌》一文。[11]亚森罗苹一出场,便是置于福尔摩斯的对立面。“劲敌”一词不仅表明亚森罗苹智慧计谋与福尔摩斯不相上下,也表明其身份立场与福尔摩斯的相异。在《临城》里,亚森罗苹被作者称为“剧贼”。他来到中国,伙同抱犊崮土匪策划了劫车绑架案,将福尔摩斯及一众中外游客关押数月,并通过易容术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而福尔摩斯却被塑造为江郎才尽的普通人,被天才盗贼玩弄于股掌之中。然而,强盗主导的绑架案本就是非正义案件,而“贼”所包含的否定性意义,也使亚森罗苹的身份并不符合与法律及正义相关的道德叙述。那么,为何周瘦鹃在小说中反复盛赞亚森罗苹的“神通广大”?
《临城》开篇便交代福尔摩斯开启中国之旅的原因是“和剧贼亚森罗苹斗智失败以后心中懊恼非常,觉得没有面目见江东父老”[1],便前往中国散心。亚森罗苹还未出场,作者就以“神探的落败”拔高了读者对亚森罗苹的心理期待。福尔摩斯常因自己的失败而懊恼,他夸赞亚森罗苹“神通广大,狡计百出,自己当了好多年侦探简直是所向无敌,谁知竟失败在他的手中”[1]。随着福尔摩斯被卷入临城劫车案,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的对比就越发鲜明。福尔摩斯感觉有一个蒙面人与众不同,隐隐觉得“这人似乎有一种制服自己的魔力,能使自己束手就缚,不敢抵抗”[1]。其实,小说中多次暗示黑衣人就是亚森罗苹,如“瞧他既不开口,又没一些儿粗手毛脚的野蛮行为,任是法兰西鼎鼎大名的剧贼亚森罗苹可也比不上”[1]。小说中有一些叙述有违逻辑,但作者却不愿多作解释,因为只要树立起亚森罗苹的智谋高人一等的形象特征,他便达成了目的,进而直接借福尔摩斯之口评价道:“这黑衣人大概是一个有学问有本领的盗魁。”[1]此时,周瘦鹃已将亚森罗苹“剧贼”的形象提升到了“盗魁”的高度。侦探小说中应有的推理情节与斗智场面,都被简化为对亚森罗苹形象的盛赞。小说中大量的不合理叙述恰恰表明了周瘦鹃意图通过亚森罗苹形象宣扬其文化观念的急迫性。
原著中的亚森罗苹虽也是秉承着“盗亦有道”行事原则的法国绅士,但在周瘦鹃的笔下,他的行为模式却颇具中国古典侠客行侠仗义的风范。亚森罗苹虽捉弄福尔摩斯并使他卷入绑架案中,但又对他进行暗中保护甚至给予优待,还妥善保管他的财物,“生怕你们的东西或有遗失,因此都由我一人掌管”[1];亚森罗苹有一套自己的行事准则,虽行绑架之事,却释放了妇女和小孩,只留下富商大贾;亚森罗苹虽是盗贼,待人处事却注重礼仪,从其常常“鞠躬”行礼的动作便可看出;亚森罗苹与福尔摩斯之间的交往除了斗智之外还增添了友人的关怀,“我虽暗中保护著你,特别优待……你病了我心中更觉不安”[1]。由“剧贼”至“盗魁”,由“绅士”到“侠客”,周瘦鹃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杂糅转化,一步步塑造出中西结合式的“侠盗”亚森罗苹。
周瘦鹃也曾袒露过自己对侠客的偏爱:“我思侠客,侠客不可得,去而读《游侠列传》,得荆轲、聂政诸大侠;我又于西方说部中得大侠红蘩蕗,得大侠锦帔客;我又于西方电影剧中得侠盗罗宾汉,得侠盗查禄,千百年后,犹觉虎虎有生气。”[12]在周瘦鹃眼中,西式盗贼正是与荆轲、聂政等古代刺客类似的英雄人物。而作为义贼的亚森罗苹,从伦理身份到价值选择,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侠客也存在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说,亚森罗苹是被周瘦鹃“归化”的侠客。侠客崇拜作为渗透入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价值观念,为亚森罗苹的本土再造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和土壤。然而,盗贼取代政府和侦探,在已经构成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被大众盛赞,实则构成了充满伦理悖论的价值观念。鉴于此,周瘦鹃对盗贼的高扬意欲何为?
《临城》写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时地方军阀仗势欺人,作恶乡里,抱犊崮百姓痛苦不堪,甚至“宁被土匪劫掠,莫被官兵搜查”[13]。在劫车案发生之时,时任中华民国直系军阀首领的曹锟对此无暇顾及,而是“腐心于最高问题”[14],欲任新总统。在引发外交危机后,军阀政府更是扬言以“对外为第一目的”[3],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出于对政府的失望以及对军阀的厌恶,在周瘦鹃心中,蔑视权威的盗贼乃是另类的英雄人物。强盗尚且知晓忠义,而理应保护民众的军阀却横行乡里,对百姓骚扰不断;强盗尚且敢于公开与殖民者对抗,而政府却做出卖国求荣、讨好列强的行径。在民族危机的沉重拷问下,周瘦鹃不惜歌颂盗贼,其高扬的实则是他心中的正义。亚森罗苹正如中国英雄传奇小说中的绿林好汉,其不轨于正义的行为,在列强倾轧、军阀混战的半殖民社会里,响应了民众反抗强权、匡扶正义的心理。
周瘦鹃曾公开表示:“我虽是个书贾,也是国民一分子,自问也还有一点儿热心!当这个风雨如晦的时局,南北争战个不了,外债亦借个不了。什么叫做护法?什么叫做统一,什么叫做自治?名目固然是光明正大的,内中却黑暗的了不得!”[6]面对“风雨如晦”的半殖民社会,他深知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乾坤,而只能花费大量笔墨揭露病态社会的罪恶根源。他借戏仿的亚森罗苹游走于临城一案的边缘地带,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病,对殖民者、资本家欺压百姓的行径,对统治阶级及其利益集团种种卖国求荣的嘴脸都给予尖刻的讽刺。
“为了摆脱强势文化的操控和被强加的他者身份,弱势文化译者努力寻求文化的‘自我表征’,实质上就是‘解殖民化’,也称‘反殖民化’。”[15]王东风论述的解殖民翻译策略同样可以应用到周瘦鹃的写作之中——利用半殖民社会文化杂交的特性,在完成对中西文化价值重写与置换的同时,给予殖民者以及软弱的政府以嘲弄与讽刺。在半殖民社会,旧道德逐步瓦解而新道德又尚未全面建立,周瘦鹃期望召唤敢于与强权对抗的英雄人物,所以戏仿塑造了中西结合式的剧贼亚森罗苹,在他身上,劫匪的大胆张扬与侠客的忠肝义胆共存,儒家的君子之道与西式的实证思维并行。新、旧价值观的交锋与融合在周瘦鹃所描绘的小说世界里都可寻得踪迹,而周瘦鹃最终的目标则是表达对重建新秩序的渴望与对公理正义的呼唤。
四、周瘦鹃的解殖民迷思
戏仿的侦探小说可以看作是周瘦鹃利用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讽刺政府、抒写解殖民诉求的一次文学实践。对于周瘦鹃而言,不管是借福尔摩斯矮化西方,还是对西式盗贼的归化与正义化,都是其精心谋划的解殖民策略。他将惊险刺激的探案情节与滑稽搞笑的人物形象相结合,在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的同时,也传递了民族本位立场和本土价值意识,由此召唤公理正义、提振民族自尊心。
实际上,周瘦鹃一直被评价为“哀情巨子”。跳出其哀情小说哀男女爱情之悲的情感范畴,他也一直在哀政府之无为,哀民族之受辱。面对中国的国耻、积弱与政府的腐败,周瘦鹃的作品表现出了半殖民地文人“道义的使命感,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16]。一方面,《临城》在消闲、游戏的表层叙述下,隐含了周瘦鹃作为半殖民地文人的最真诚的创作欲望,其中融汇了赤诚的爱国热情、深沉的民族忧虑与朴素的现世精神等丰富的情感向度;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免看到周瘦鹃隐藏在小说中的保守倾向、伦理错位及身份焦虑等解殖民迷思。
尽管周瘦鹃选取福尔摩斯作为代言人,用另类的“异国凝视”诉说其抵抗殖民的叙事,但也在实质上默认了观看位置与观看框架,隐匿了看与被看的失衡模式与权力位阶。引用英人游历中国并发表赞叹的言论正好体现了周瘦鹃的迷茫与焦虑,以虚拟的异国凝视表达赤诚的国族认同固然可以觅得心灵的抚慰和文化的论述资本,却也在潜意识中拔高了西方的话语权,强调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投射出半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创伤与精神震颤。正如史书美所说的:“这种世界主义极力将自己放在与西方和日本都市文化进行对话的全球语境之中,因此它就必须系统地掩盖住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半殖民统治的现实……这种对话的本质只能是虚幻和想象的……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中国根本没被西方关注和倾听,而所谓中国人的活力只是一种姿态而已。”[17]423周瘦鹃以对西方强国的想象来克服殖民主义的后果,便是在半殖民社会的残酷现实中再一次碰壁。
半殖民统治的裂缝与残存的主权也在帮助中国知识分子获得发挥文化主动性的可能。因此,在文本叙述中,周瘦鹃用以西证古、洋为中用的方式,显示出半殖民地文人特殊而隐蔽的抵抗。小说呈现了周瘦鹃对真理的召唤,而他之所以在中国本土的强盗掠劫案中戏仿西人,也隐含了中西文化力量强弱的对比。“(亚洲知识分子)对西方威胁自身文化和政治完整的感受越强烈,他们需要坚持理想化的东方文化观念的心理也就越强烈,因为在后一种心理中,东方文化可以作为砝码平衡掉西方势力和影响。”[17]423正如史书美所说,周瘦鹃以西方文化为工具召唤中国古典礼义规范及公理正义,不仅表达了半殖民地文人的自尊与自矜,而且隐含了焦灼的解殖民诉求,西方的文化霸权恰好成为周瘦鹃想象中西方文化的注脚,并通过建构虚拟的异国形象达到凝聚国体、召唤国魂的目的。此外,周瘦鹃对亚森罗苹的褒扬实则是借西人形象传递对中国盗贼的肯定。周瘦鹃将此次绑架案视作对抗政府、向殖民者施压的反强权行为,但绑架的本质却与法律、道德相抵牾。其为强盗侠义行为的辩护不能掩盖临城劫车案的犯罪事实,绑匪实施绑架的非正义行为更不应被美化。在半殖民社会伦理转型的阵痛中,周瘦鹃面对与列强和政府的博弈以及尚未健全的道德秩序,陷入了难以调和的伦理困境。
综上,《临城》作为戏仿的侦探小说,包含了周瘦鹃的复杂心态与叙事困境。他试图通过侦探小说的科学理性启蒙民智,又企图利用通俗娱乐的方式获取更多的读者与经济收益;他被西方文明所吸引,把它视作治病的良方,又惧怕失掉文化自信,所以不厌其烦地重申儒家秩序;他祈祷英雄人物的出现,但他又将真正的正义与道德视为冲破黑暗的绊脚石。在这样复杂矛盾的叙事话语中,包含着他者与自我、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正义与不义等多重价值观念的缠绕与拉扯,周瘦鹃在抵抗殖民的迷思中磕磕绊绊地诉说着爱国深情。
然而,在周瘦鹃那里,尽管文学带有保守性、矛盾性与娱乐性等特征,其创作本身却是对晚清民国特定的半殖民历史的间接回应。他杂糅中西文化,通过戏仿异域形象,试图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半殖民性”来临下的惶恐与焦虑;又因报刊媒体的消费性与娱乐性,以反精英式的嬉笑怒骂启蒙大众,形成了启蒙、苦难与游戏的多重联结。《临城》这类戏仿的侦探小说实则负载着种种历史景况——跨文化交流中文学生产机制的变革、社会伦理秩序与正义观念的嬗变、中西文化的杂糅与转化、受殖者对于西方的模棱态度、个体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关联……以上微妙的历史细节都能在《临城》中觅得踪迹,可见其意义不仅是对历史的投射,更可勾勒出半殖民地文人在种种嬗变中的多重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