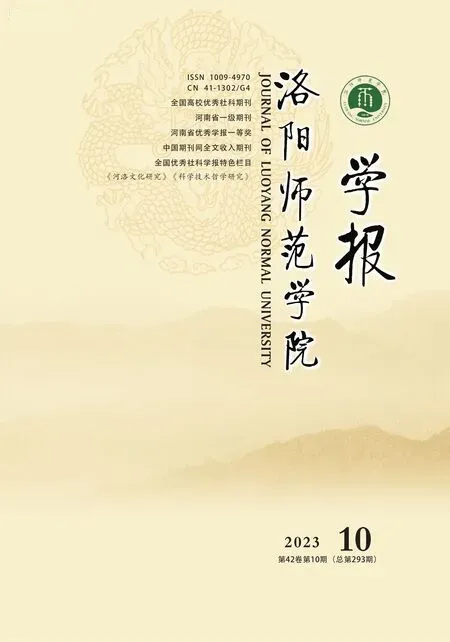近代思想史上董仲舒的接受史考察
——以董仲舒地位的升降为中心
吴 涛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洛阳 471934)
从董仲舒去世到清末今文经学兴起之前, 其历史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清末今文经学兴起后, 董仲舒地位急剧上升。 民国以后, 随着现代学术的转型, 董仲舒的地位开始回落。 对近代以来董仲舒的地位进行梳理, 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近代的董仲舒研究史, 而且也是认识近代以来学术变迁的一个窗口。
一、 清中期以前董仲舒的地位
自西汉以来, 董仲舒虽然一直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但在朱熹看来董仲舒仅一两句话值得肯定。 他说: “汉儒惟董仲舒纯粹, 其学甚正, 非诸人比。 只是困苦无精彩, 极好处也只有‘正义、 明道’两句。”[1]甚至在陆九渊看来, 董仲舒的灾异说已经流为“术数”, 他说: “汉儒专门之学流为术数, 推类求验, 旁引曲取, 徇流忘源, 古道榛塞。 后人觉其附会之失, 反滋怠忽之过。 董仲舒、 刘向犹不能免, 吁, 可叹哉!”[2]正因为如此, 董仲舒长期徘徊于孔庙门外, 直到明代才得以进入孔庙。
清初顾炎武等人倡导实学, 经学复兴。 清朝首先复兴的是古文经学, 作为今文经学家的董仲舒并非学界关注的重点。 《四库全书总目》对《春秋繁露》的态度或许可以被看成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代表: “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 而无关经义者多实, 《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 向来列之经解中, 非其实也。 今亦置之于附录。”[3]清代的宋学家对董仲舒也没有过高的评价, 他们对董仲舒的评价往往在其品行而非其学术。 毕竟随着时代的变迁, 董仲舒的哲理体系已经不能令后人信服。
在清代学术重视文本研究的背景下出现了对《春秋繁露》系统的注释和校勘整理。 但无论是董天工的《春秋繁露笺注》, 还是凌曙的《春秋繁露注》, 都不能说是真正认识到《春秋繁露》的价值所在。
二、 今文经学派兴起以后董仲舒的地位
(一)常州今文经学派兴起背景下的董仲舒研究
乾隆中后期, 常州今文经学派逐渐兴起, 董仲舒是他们构建自己学术体系的重要资源, 董仲舒的地位开始逐渐抬升。 庄存与在构建其思想体系过程时主要依托董仲舒《春秋繁露》。 比如《奉天辞第一》, 庄存与开篇就讲: “初一曰建五始。 元正天端, 自贵者始。”[4]显然与董仲舒在《玉英篇》中所讲有继承关系: “是故《春秋》之道, 以元之深正天之端, 以天之端正王之政, 以王之政正诸侯之位, 五者俱正而化大行。”[5]70庄存与之徒孔广森对董仲舒也十分景仰, “胡毋生、 董生既皆此经先师, 虽义出传表, 卓然可信, 董生绪言犹存《繁露》”[6]。 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是常州学派门户的光大者, 他对董仲舒推崇备至: “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者, 董生治《春秋》倡之也。”[7]
清朝末年社会的剧烈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董仲舒地位的升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倡导“自改革”的龚自珍就已经高度关注董仲舒, 他曾仿效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撰有《春秋决事比》。 相对于龚自珍, 今文经学立场更明确的魏源, 其学术追求是: “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 由六艺求圣人统纪, 旁搜远绍, 温故知新, 任重道远, 死而后已。”[8]
在晚清社会剧烈转型中, 部分学人从今文经学中寻求思想资源以应对挑战的背景下, 董仲舒《春秋繁露》也受到更多关注。 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 于《春秋》学最赞赏的就是董仲舒, 他说: “孟子之后, 董子之学最醇。 然则《春秋》之学, 孟子之后, 亦当以董子之学为最醇矣。”[9]
(二)晚清极端今文经学流行时期董仲舒的地位
康有为将今文经学作为其变法的理论依据, 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也是其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康有为还专门写有《春秋董氏学》一书, 以发董氏《春秋》大义。 康有为一再称董仲舒为“醇儒”, 而这也是董仲舒言论可靠性的保证, 进而董仲舒“醇儒”的身份, 又成为康有为理论的背书, “自汉前莫不以孔子为素王, 《春秋》为改制之书。 其他尚不足信, 董子号称‘醇儒’, 岂为诞谩?而发《春秋》为新王、 当新王者, 不胜枚举。 若非口说传授, 董生安能大发之?出自董子, 亦可信矣”[10]535。 康有为极力论证孔子倡导改制立法以作为其变法主张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因详述受命改制之义而受康有为的推崇, 他说: “孔子作《春秋》改制之说, 虽杂见他书, 而最精详可信据者莫如此篇。”[10]542康有为认为: “幸董生此篇犹传, 足以证明孔子改制大义。”[10]543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称其撰述宗旨为: “因董子以通《公羊》, 因《公羊》以通《春秋》, 因《春秋》以通六经, 而窥孔子之道本。 ”而康有为之所以选择董仲舒作为认识孔子大道的入手, 就是因为董仲舒所言“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 而非董子之为之也”[10]109。 朱维铮评价道: “《春秋董氏学》其实是在重新诠释传统经学的基本概念, 给这些概念注入康有为自己的‘微言大义’。”[10]109
为进一步阐释《春秋》学, 康有为还撰有《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一书。(1)於解康在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一书所作的《评介》中称: “作者《自序》称, ‘此书旧草于广州羊城之万木草堂及桂林之风洞’1899年随《清议报》馆一并被焚, 后于1900年12月至1901年8月补成, 然书中述及1904年游历法国及1911年袁世凯迫清帝退位事, 可知全书后续屡有增补。 ”载康有为: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卷首第2页。他在自序中说: “董子, 群儒首也。 汉世去孔子不远, 用《春秋》之义以拨乱改制, 惟董子开之。”[11]20就这样在晚清乱局中, 董仲舒终于获得了“群儒首”的地位, 达到了董仲舒研究史的顶峰。
(三)民国初年今文经学余波中的董仲舒研究
苏舆学术立场明显带有晚清湘学的今文色彩。 不过, 与康有为把今文经学作工具不同, 苏舆则纯粹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 苏舆不满于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歪曲利用。 他说: “余少好读董生书, 初得凌氏注本, 惜其称引繁博, 义蕴未究。 已而闻有为董氏学者, 绎其义例, 颇复诧异。”[5]1其所指显然是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在阐释董仲舒之说的同时, 坚守《公羊》经学立场, 对晚清极端今文经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时加辩驳。 实则, 苏舆之于康有为, 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苏舆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立场, 在很多地方也不惜曲解董仲舒原意。 比如《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最能体现董仲舒的民本思想, 而苏舆则直接断定此篇为伪作。 其实是苏舆保守的政治立场, 使他根本不愿意相信董仲舒赞同革命。 苏舆是观念先行, 然后再试图证明它。 而其证明, 并不能经得起推敲。 但苏舆对董仲舒的推崇, 并不在康有为之下。 在这一点上, 苏舆和康有为是相同的。
三、 近代以来否定董仲舒的先河
董仲舒地位的上升也逃不脱物极必反的规律。 就在康有为把董仲舒尊为“群儒首”的同时, 已经有了重量级的批评者。 章太炎不仅政治立场和康有为对立, 而且学术立场也与康有为完全相反。 康有为把今文经学作为其理论依据, 章太炎力主古文经学。 康有为等人极力推崇董仲舒, 章太炎自然要对董仲舒大加挞伐。 章太炎说: “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 垂则博士, 神人大巫也。 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 苟得利禄, 而不识远略。”[12]228
章太炎对董仲舒《春秋决狱》深恶痛绝, 早年就在《訄书·儒法》篇中说: “仲舒之《决事比》, 援经附谶, 有事则有例。 比于酂侯《九章》, 其文已冗, 而其例已枝。 已用之, 斯焚之可也!著之简牍, 拭之木觚, 以教张汤, 使一事而进退于二律。 后之廷尉, 利其生死异比, 得以因缘为市, 然后弃表埻之明, 而从縿游之荡。 悲夫, 儒之盭, 法之弊也。”[13]后来章太炎将《訄书》修订为《检论》时, 将《儒法》篇题改为《原法》, 对董仲舒的痛斥有增无减。 章太炎还作了一条注释: “汉世儒者, 往往喜舍法律明文, 而援经诛心以为断。 ……盖自仲舒以来, 儒者皆为蚩尤矣。”[12]221
章太炎的学术成就罕有其匹, 但是无论是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说, 还是从对《春秋繁露》研究来说, 其影响都十分有限。 诚如梁启超所言: “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 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14]但是, 章太炎对董仲舒决绝的否定态度是前所罕见的, 开了否定董仲舒的先河。
四、 现代学术体系确立后被视为学者的董仲舒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宣告了传统学术的终结。 现代学术确立后的重大转变, 不仅体现在学术规范、 学术表达的不同上, 尤其体现在学术立场的不同上。 传统学术, 不论属于哪个学派, 都是儒学的信仰者。 但现代学者, 除却少数遗老遗少, 不论其文化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 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生。 体现在《春秋繁露》研究上, 现代学者基本上都把《春秋繁露》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 而非为了通过《春秋繁露》以阐释圣人之心。
同时, 当代《春秋繁露》研究者所用的研究方法有重大进步, 其理论与工具都迥然有别于传统学者。 正因有了新视角、 新理论、 新方法, 《春秋繁露》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了全新面目。
董仲舒的地位也随着现代学术的转型而有所变化。 从整体上看, 董仲舒的地位相对于晚清极端今文经学, 有着明显的回落。 学者多从史学的角度来认识董仲舒。 在学者心目中,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而非清儒心目中的圣贤。 不过, 由于学术路径和学术旨趣不同, 研究者心目中董仲舒的地位也略有差异。 大体而言, 现代学术转型后, 董仲舒在学者们心目中的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 哲学家(思想家)和经学家。
(一)作为思想家的董仲舒
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后, 中国古代的贤哲往往被冠以哲学家的名号。 有些学者称他们为思想家, 其实他们所理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并没有区别。 而董仲舒就被认为是西汉哲学家的代表。 在这里选取胡适和冯友兰的研究, 以见其梗概。
作为现代哲学史开创者的胡适1930年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称董仲舒是一个积极有为的哲学家, 是西汉有为主义的代表。 胡适高度赞扬这种积极有为的态度, 他说: “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 不但建立了汉帝国的一代规模, 还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思想与制度, 他们的牺牲是值得我们同情的。 ”对于董仲舒的历史地位, 胡适也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说: “董仲舒的许多主张, 有一些后来竟成为汉朝的制度。”[15]相对而言, 胡适对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更多的意义体现在新路径的开辟上, 如同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所说: “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16]
相对于胡适, 冯友兰对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则要深入很多。 在晚清今文经学兴起过程中, 董仲舒《春秋繁露》虽说受到高度重视, 但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当中国哲学史学科兴起后, 对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关注重点就从《春秋》学转向了阴阳五行思想。
冯友兰并没有孤立地看待董仲舒, 而是以董仲舒为其时代的代表, 他说: “此时代之精神, 此时人之思想, 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17]9冯友兰认为西汉是“阴阳家空气弥漫之时代”[17]8。 冯友兰对董仲舒的研究也从阴阳五行思想入手, 比如他在谈及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天”时说: “董仲舒所谓之天, 有时系指物质之天, 即与地相对之天; 有时系指有智力有意志之自然。 ”“有智力有意志之自然”系冯友兰自创的名词。 对此他解释道: “有智力有意志之自然一名辞, 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处; 然董仲舒所说之天, 实有智力有意志, 而却非一有人格之上帝, 故此谓之自然也。”[17]11
冯友兰高度评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他说: “人在宇宙间之地位, 照此说法, 可谓最高矣。”[17]18董仲舒的人性论, 冯友兰对比了董仲舒与孟子、 荀子, 以及孔子言论的不同后, 认为: “董仲舒之论人性, 盖就孔、 孟、 荀之说而融合之。”[17]21董仲舒的纲常伦理, 冯友兰尤其指出其循环论证模式, “盖儒家本以当时君臣、 男女、 父子关系, 类推以说阴阳之关系; 及阴阳之关系如彼所说, 而当时君臣、 男女、 父子关系, 乃更见其合理性矣”[17]23。 冯友兰指出董仲舒“三统论”荒谬的同时, 也指出其价值之所在, “此说吾人虽明知其为不真, 要之在哲学史上不失为一有系统的历史哲学也”[17]33。
冯友兰并未忽视董仲舒的《春秋》学, 他说: “盖董仲舒之书于《春秋》, 犹《易传》之于《周易》也。”[17]11不仅如此, “及董仲舒讲《春秋》……而孔子之地位, 亦由师而进为王矣”[17]33。 至于《春秋》学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冯友兰说: “《春秋》乃董仲舒所谓‘天理’之写出者, 所谓‘体天之微’者也。”[17]35
(二)作为经学家的董仲舒
近代学术转型之后, 对于中国传统经学之“学”的研究, 正如周予同所倡导的, 新研究更注重“史”的研究。 周予同说: “在现阶段, 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 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18]在民国《春秋》学史研究中, 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始终受到高度关注。 这里略举陈柱、 杨树达、 段熙仲的研究以见其端倪。
1928年陈柱在其《公羊家哲学》自序中主张搁置过去传统经生的根本问题, 直接把书名命名为《公羊家哲学》。 他说: “自董仲舒、 何休以下, 皆说公羊之学, 而亦各不能尽其同, 与其定孰为公羊之真, 无宁统名为公羊家之学。”[19]10可见, 陈柱已经跳出了传统经学研究的篱藩, 其研究应被纳入到史学的范围。 在《公羊家哲学》中, 《春秋繁露》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他说: “今按此书(《春秋繁露》)论《春秋》之旨, 发明公羊家言, 甚多精语。”[19]138陈柱《公羊家哲学》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 革命话语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陈柱非常重视《公羊》学说的革命思想, 把革命放在首位来讲, 他说: “公羊学说之富于革命思想, 则显而易见。”[19]11民国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频仍, 民众呼唤和平。 陈柱《公羊家哲学》在引用《春秋繁露》之后说: “董子此言, 于《春秋》弭兵恶战之旨, 可谓深切矣。 此可以代表公羊家之思想矣。”[19]39
不过陈柱《公羊家哲学》更多的是采纳董仲舒《春秋繁露》以证《公羊》之说, 而不是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这显然有别于前人由《春秋繁露》以达《公羊》的路径。
全国性抗战爆发以后, 著名学者杨树达以学术报国, 于1941年完成《春秋大义述》一书。 他在自序中说: “二十八年(1939)秋, 乃以是经(《春秋》)设教, 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 切复仇之志, 明义利之辩, 知治己之方。”[20]7杨树达对董仲舒极为推崇, 《春秋繁露》成为《春秋大义述》的主要依据。 他说: “汉代大儒, 首推董子。 《春秋繁露》一书, 今虽残缺不全, 而义据精深, 得未曾有。 本书于董书说明经义者录之特详。”[20]9因而, 《春秋大义述》虽本《公羊》以立义, 实则以《公羊》从董生。 比如《春秋大义述》特别强调复仇, 首先引用的是《春秋繁露·竹林》, 而非《公羊传》之文。
《春秋大义述》为救时之作, 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经学史研究。 其方法也是立论在先, 根据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提出若干《春秋》大义, 然后再从《春秋繁露》《公羊传》《榖梁传》等文献中寻找佐证。 比如复仇的确是董仲舒等《公羊》学家所非常强调的《春秋》大义, 但杨树达不是从《春秋繁露》或者《公羊传》中归纳出复仇的大义, 而是先立复仇之义再求证于《春秋繁露》等文献。
段熙仲的《春秋公羊学讲疏》大体完稿于1948年, 后来又有过一些修订。 此书一直没有机会出版, 到2002年才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末《公羊》学虽成为显学, 但大多是在借用《公羊》的画皮而已。 段熙仲自序中说, 撰述此书意在“复其本真”。 而董仲舒《春秋繁露》则是重要依据, 他说: “义莫明于董君。 ”《春秋公羊学讲疏》精华在第五编, 全书论及《春秋繁露》最多的也在此编。 第五编第二章《述董》中, 段熙仲说: “温城董君目不窥园, 亦云精力, 世传《繁露》, 虽非全书, 而二端、 十指, 则凡《春秋》义旨之荦荦大者, 已多揭橥。”[21]417《春秋繁露》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公羊传》。 比如讲“三正”之义, 段熙仲的核心观点则是秉承《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在论述改制之义时, 段熙仲详细阐释了董仲舒的改制学说: “新王改制之说, 董君较何君言之大详, 其导源皆出于孔子。”[21]457第八章《善善恶恶》中《春秋》大义之是非标准, 多同于董仲舒。 如论经权, 则曰: “董君之言经权, 足与《传》相发明。”[21]562论信义, 则曰: “董君曰: ‘《春秋》之义, 贵信而贱诈。 诈人而胜之, 虽有功, 君子弗为也。 ’”[21]575论恶战重民, 则曰: “谨按: 《春秋》以仁为天心, 董子说子反之事, 发明重民之义, 信乎义几可谕矣。”[21]583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充分揭示了《春秋繁露》在《公羊》学史上的地位。 比如《春秋》王鲁是《公羊》家的根本大义之一, 段熙仲在引用《三代改制质文》之后说: “此则王鲁之说远起于何君以前之明证。”[21]473再如“异内外”之义“自近者始”, 段熙仲说: “董君《繁露·仁义法》篇, 发明《春秋》此义尤详。”[21]506段熙仲对清代《公羊》学术的评价, 也着重考察其对《春秋繁露》所提大义的阐释, 如段熙仲评价孔广森, “按孔氏说三世异辞, 发明董君屈伸之志甚畅”[21]498。
同时, 如同汤大民所言: “段熙仲教授……虽强调‘家法’, 但其旨归为‘复其本真’, 而不是信以为真, 所以他并不囿于门派之见。”[22]段熙仲虽说重视董仲舒, 但他并不是董仲舒的维护者。 比如三纲观念是董仲舒的核心政治观念之一, 段熙仲并不因其观念不符合当代的主流价值观而选择性地忽视, 或者强作新解。
晚清以来, 《公羊》学以经世为特色, 段熙仲此书撰于国难方殷之际, 亦不能不有所寄托。 如《救中国, 攘夷狄》诸篇, 皆有其深意在焉。
可见, 进入民国, 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确立, 儒学、 经学已经失去了信仰的地位。 民国学者多把董仲舒作为研究对象, 其研究相对于前人表现出明显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他们都无意通过对董仲舒的研究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或者说他们对董仲舒的研究与其本人的思想观念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虽说他们对董仲舒评价很高, 但相对于晚清极端今文经学家们的无限拔高, 都有所下降。 无论被视为经学家还是哲学家, 学者是董仲舒最主要的身份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