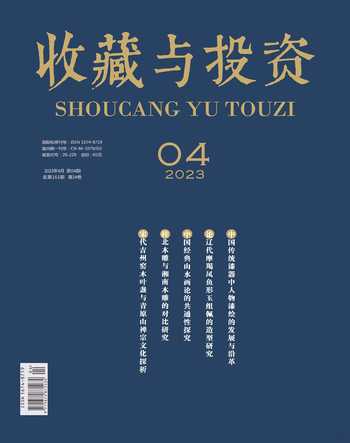“竹林七贤”图像演变过程中其象征意义的模式化倾向
李 慧(西安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一、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为例探讨该图像通过文本所建立的符号体系
1959年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1)砖刻壁画是诸多“竹林七贤”砖画中相对规模最大,也是保存最完善和精细的一件作品。该图像(图2)中,画面以线条为主,人物表现力求生动。其中共有八个人物形象,注明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每一个名字所对应的人物都形态各异,人物的个体形象接近文学作品或其他文本对人物的描述,如嵇康盘膝抚琴、神态怡然的形象符合《晋书·嵇康传》①中记载的“(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对阮籍的口作长啸之态符合《晋书·阮籍传》中所描述的“嗜酒能啸”。山涛的执杯欲饮符合《晋书·舆服志》中的“饮酒至八斗方醉”。王戎手执如意符合庾信《乐府·对酒歌》中的“山简竹篱倒,王戎如意舞”。向秀的闭目沉思之态符合《晋书·向秀传》中的“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时也”。刘伶的品酒之态符合《晋书·刘伶传》中的“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盍提壶”。阮咸手抱琵琶符合《晋书·阮咸传》中的“咸通韵律,善弹琵琶”。荣启期手抱琵琶的动态在《高士传·卷上·荣启期》中的描述为“鹿裘带索,鼓琴而歌”。此外,在人物间隙间,还绘有十株植物,分别是五株银杏树、两株垂柳、一株槐树、一株松树和一株阔叶竹,以平铺的构图方式与人物并列。

图1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一组高78 厘米,长242.5 厘米,二组高78 厘米,长241.5 厘米

图2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
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②的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③(《宪问》)之数。但根据记载,吕安、阮浑、袁准、郭遐周、郭遐叔兄弟、阮侃等也常与山涛等人相聚一起,但最终历史的真实性妥协于文本的艺术性,产生了这个被广为流传的数字。陈寅恪还认为“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西晋末年,人们喜好引用佛教经典来比赋,由此可见,“七贤”的相聚与印度“竹林精舍”的讲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可能被加以比拟的,其经由艺术加工,颇有标榜之义。此外,“七贤”相聚之所以以竹林为背景铺垫,抑或是因为“竹”所象征的坚韧、孤傲以及给人以自然、远离尘俗的意蕴,它是在一个在文化积累中形成的文化符号,比拟贤者的高雅、清远和不畏世俗。
二、“竹林七贤”图像在文本信息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独立性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的主题架构是建立在相关文本和现实的逻辑关系之上的,但却在此基础上取其所需,呈现出非纪实和理想化的特点。因为从客观现实来看,“七贤”未必是“七贤”,所谓的“贤者”或许也只是借以旷达和归隐的外表来掩盖在出仕与入仕中感到矛盾和焦虑的一个悲观群体。不论是文本还是图像,“竹林七贤”的创作者们都有选择性地刻意呈现出这一群体的高尚清洁和这一故事的唯美性质,以带有“偏见”的视角实现作者个人的表达意图,并以此引发普遍的情感共鸣。此外,荣启期的出现在学者们看来主要是基于平衡构图的考虑,这意味着该创作出于构图的因素,对不同的空间与时间进行了叠合,使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独立性和自由性,从这一点来看,它是超现实主义的。这种穿梭时空的表现方式,使画面进一步脱离文本,呈现出虚幻性,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南朝墓室玄学、升仙等主题,增强其象征意味,同时也体现出构图、形式等因素超越了现实和文本,对图像美感的追求超越了对主题客观的追求。与此同时,观者也会注意到“竹林”的缺失,在这一图像中,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竹林”,而是十株树木的简化形象,其中只有一株阔叶竹与竹相关。
但在表达文本的象征目的层面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却表现出直截了当的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主题进行直接的取舍——摘除了贤者们人生经历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以及消极的一面,从“特定的角度”对他们的哲学理想和人生态度表现出赞誉;(2)跨越时空的主观表现——荣启期的出现。荣启期作为春秋时期的高士,与南朝贤士共同出现在同一画面。创作者有意将他与其他“七贤”的共通性归到一起,甚至不考虑时空合理与否,以非现实主义的途径直接传达创作意图。
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可以得知,作为最早的“竹林七贤”主题创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在表达象征意味的同时保留了与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其符号化、模式化程度相较于之后历代的“竹林七贤”图像都是较轻的。
三、相较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图像,后世的“竹林七贤”图像演变
晚唐画家孙位所绘的《高逸图》(图3),经考证亦是对“竹林七贤”主题的描绘,虽然是残卷,但通过对画面仅存的“四贤”人物相貌、动作姿态及器具等方面的观察,可以确定其所绘人物分别符合人们对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四位人物的固有印象。该作品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颇有共通之处。从构图上看,同样采用了并列式的构图方式安排人物和植物在画面的位置;从人物特征看,四位贤者的动作姿势、服装头饰以及用以表现个性喜好的器具不仅对应“竹林七贤”文本的描述,同样也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图像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从环境氛围来看,用于分割或连接画面的山石植物,包括芭蕉、银杏、松槐等同样是并列式构图,且并未给观者一个明确的“竹林”氛围。只是在该卷画面中央的湖石背后,出现了几株类似于“墨竹”的植物。从艺术表现来看,该画用笔细劲流畅,十分注重对人物眼神的刻画,颇有东晋顾恺之“传神写照”的艺术特色。树木的画法各不相同,大体技法为细线勾勒轮廓,然后皴擦出树枝结构,再用色罩染。从画面的意蕴来看,《高逸图》充分表现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魏晋士族名流风度,人物形象给人崇高肃穆、自由豁达的感受。相对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图像,《高逸图》的主要差异在于技法、色彩、表现方式等方面,许多方面都保留了与前者的共性。由于画卷的不完整性,观者未能见到完整的“七贤”,但在象征意味和对人物特征的表现方面,该画卷已具备了固有印象的模式感,模式化倾向相对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图像已有所增强。

图3 唐 孙位《高逸图卷》纵45.2 cm 横168.7 cm 绢本 上海博物馆藏
明代李士达的《竹林七贤图》采用了细笔小青绿法,赋色艳丽,与上文前二者“竹林七贤”相比,除了技法和画面表现方面,不同之处主要有四点:(1)“八贤”回归到“七贤”(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比较)。这在数量上符合已约定俗成的文本信息;(2)“竹林”的回归。画面中对“竹林”的大篇幅描绘,是相较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以及《高逸图》的主要变化而作出的设计,目的是使图像对应故事的基本框架;(3)颇有“相聚”意味的画面氛围。较之《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和《高逸图》的并列式构图,这幅画的构图更具有空间错落感,使得七贤“相聚”的氛围感更加明确;(4)人物的个性化削弱。在这幅作品的远景构图中,“七贤”与环境、与其他人物(侍童)共处一个空间,虽然观者在该图像中得以窥见人物的“袒胸赤足”“抚琴饮酒”等具有代表性的动作特点,但这种个性特点的优先权显然已让位于郁郁葱葱的竹林和气势磅礴的自然山水,其高远素雅、豁达洒脱的气息遍布整个画面,进一步从深层强化了主题的象征意图。这四点不同促使“竹林七贤”的文化符号得到更加明确的体现,且在当时或后期大量的“竹林七贤”图像中皆有所体现,例如清代禹之鼎、沈宗骞、任伯年、冷枚等人的“竹林七贤”主题作品。虽然受时代特征或画家个人因素等影响,“七贤”的个性化特征发生了变化,人物形态与服装以及绘画的表现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基本的两个符号——“竹林”和“七贤”,以及这一故事主题的高远意蕴始终保留并不断强化。后期张大千的《竹林七贤》与傅抱石的《竹林七贤》(图4)更是将该主题的画面结构直接简化为仅剩“竹林”与“七贤”这两种元素,并以写意的方式表现挥洒悠扬的画面气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删减和最强意图的突出,传达出“竹林七贤”潇洒自如的品质和该故事的唯美主义性质,使其符号化和模式化呈现出直截了当、平铺直叙的意味。

图4 傅抱石《竹林七贤图》故宫博物院藏
四、结语
在“竹林七贤”图像的演变过程中,客观世界、文本信息以及已有的图像都在潜移默化地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的模式,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出于象征意图而进行删减与突出,使固有的文化符号不断增强。历代“竹林七贤”图像所发生的变化主要在于特定时代的文化特征、服装、绘画风格或表现形式,不变的却是这种在时间沉淀中日渐被极端简化、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文化符号,将图像向文本的社会意义不断靠拢,最终使主题的象征意味不断强化而逐步走向模式化、符号化。
注释
①晋书:中国《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该书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
②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年。
③《论语》中关于“七贤”有这样一段: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由此引出“贤者七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