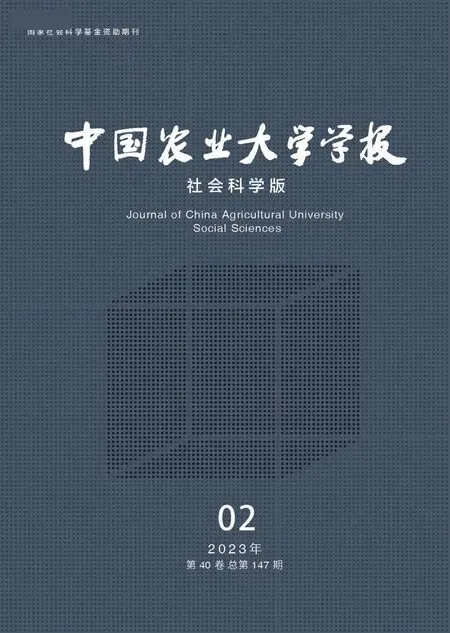“角色混乱”: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运行困境
——以广东省G市为例
张紧跟 胡特妮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司法为民和基层法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既是畅通中国公共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又是健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突破口。在推进中国特色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应运而生。在一些省份试点探索的基础上,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机制很快实现了“创新扩散”。截至2020年,全国64万多个村(居)配备了法律顾问,从局部地区的“星星之火”快速实现了基本上全覆盖的“燎原之势”。
纵观近10余年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运行,一方面,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全面实施,“较好地弥补了基层公共法律服务难以全面覆盖的不足,有利于增强村(居)民法治意识,在减少和及时化解纠纷以及维护基层和谐稳定、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曹吉锋,2017)。在此基础上,作为国家治理社会的触底工程和国家柔性控制社会风险的政治建设工程,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加强了基层治理能力(戴康,汤峰,2020)。另一方面,实践中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运行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收益并不显著,在一些村(居)甚至被虚置(杜承秀,张聪锐,2019);部分存在着村(居)法律顾问效率低、质量不高和效果欠佳的实践困境(周喜梅,黄恒林,2019);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在一些民族地方不接地气,导致其很难成为一项被信仰的法律制度(杜承秀,2021);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存在“群众知晓率低、与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驻点律师缺乏动力等”明显短板(孙伟峰,古钰钦,2021)。
那么,“作为一种探索创新性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政府推行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牛广轩,姜国兵,2015),村(居)法律顾问为何难以实现制度建构的目标?
从既有研究来看,制度设计是讨论的焦点。研究者认为过度行政化导致村(居)法律顾问制度难以持续(杜承秀,2021),供给非均衡对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有负面影响(张紧跟,胡特妮,2019),“语言混乱”(朱晓阳,2007)和“结构混乱”(董磊明等,2008)制约了现代性法律在基层社会的成功实践。
毋庸置疑,完善的制度设计是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有效运作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既有研究对作为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这一关键行动者缺乏应有的关注,而行动者往往会重塑制度。因此,除了立足于完善现有制度设计外,还有必要从行动者视角来思考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本文尝试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立足于律师行动这一微观视角来回答为何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未能实现预期目标这一问题。回溯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发展过程,广东“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制度创新始终扮演着“先行先试”的“探路者”角色,具备了案例研究所需要的典型性。为此,2018—2021年,我们在粤东G市跟随FY律师事务所的驻点律师,全程观察其在238个镇(街)开展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案例研究中的一手资料来自参与式观察和访谈,二手资料来自相关法律制度文件、媒体报道、网络舆论以及学术研究文献。
二、文献综述与新的研究视角
(一)既有的制度设计研究视角
既有研究注意到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全覆盖对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提升基层法治化管理水平意义重大,但诸多制度因素导致其难以有效运转。
首先,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制规范。例如,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立法滞后等使其缺乏法制保障,社区工作机制衔接不够导致服务场所设置与现行管理规定冲突(马军港等,2008),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配套制度建构不及时(杜承秀,张聪锐,2019),以及人才保障不足、资源配备不均、经费保障不够等因素制约着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有效运作(王鲁宁等,2016)。
其次,过度行政化。邵珠同(2019)认为村(居)法律顾问制度难以持续的原因在于过度行政化,其中行政性与公益性杂糅导致运作混乱、系统性和灵活性不足导致推行机制僵化、权利与义务配置失衡导致社会主体缺位。杜承秀(2021)认为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设置的过分一体化及运行的过度行政化使其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无法充分激发其社会功效和法律功效。
最后,与非正式制度不兼容。研究者普遍认为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是国家主导下的“法制下乡”,而作为正式制度的国家法在进入基层社会时如果不能与基层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1998:58)就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司法制度下乡导致“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反而破坏了礼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苏力(1996:23-37)观察到“乡土中国”中“熟人社会”的内在机制与现代性法律制度难以兼容。强世功(1997:488-520)笔下的“炕上开庭”则呈现出法律在进入乡村后更多的是权力运作的策略和技术。进入21世纪,朱晓阳(2007)将现代司法制度与乡土社会的种种不适归结为“法律的语言混乱”,呈现出乡村社会的内生正义观和价值与现代性法律所彰显的外来正义观和价值之间的紧张性;董磊明等(2008)认为,流动性、异质性和理性化的加剧以及社会关联、村庄认同、公共权威的衰退等引发的“结构混乱”,呈现出“迎法下乡”中传统的地方性规范解体,而国家权力也渗透不够的新型治理困境。
(二)行动者研究的新视角
既有制度研究在折射出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中现代国家建设“步履艰难”的同时,为国家不断完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参考。但是,制度设计不仅要考虑制度设计的规范化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兼容,而且应该关注制度设计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因此,完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就是通过驻点律师等多元行动者与既有制度的互动,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与供给的过程。显然,作为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是该制度运行的关键行动者,其对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有效运作的影响在既有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众所周知,在新制度主义话语中,制度为行动者提供了有关其他行为者现在或将来行为的确定性程度(Peters,1999:24),无疑是制约行动者的基本规范。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用以框定和约束行动者的制度是通过相关行动者的活动引起行动者的策略性响应而发挥作用的;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为行动者提供“认知”“规范”,影响着行动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不仅影响着行动者如何去界定自己的利益,而且确立了特定行动者特定位置上的责任和与其他行动者的相互关系(Hall &Taylor,1996)。显然,尽管新制度主义话语在制度如何作用于行动者上众说纷纭,但都强调行动者并非完全丧失自主性,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会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并重新塑造制度。诚如吉登斯(1998:79-82)所言,制度是为行动者提供稳定预期、结构化社会互动的一种存在,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行动并受制于制度,但行动者又再生产了制度。具体而言,这一实践过程可能体现为两个面向:一方面,行动者运用各种权变性策略,迎合正式制度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行动者采取变通、非正式运作的方式,运用“生活中的资源”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日常反抗”以与正式制度进行博弈协商(肖瑛,2014)。因此,有必要从作为法律顾问的律师在村(居)中的具体行动入手,深描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践过程,以揭示其运行困境的实践逻辑。
而根据行动者所处的社会角色去解释其行为并揭示其中的规律,自然离不开社会角色理论。社会角色理论聚焦个体行为与社会互动,认为个体生活一定是依托群体而存在,如戏剧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扮演着不同角色。当一个人履行某一权利与义务时,他就在扮演一个按照社会功能产生互助关系的大系统之中的角色。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行动者,因应复杂社会分工功能之需求,往往要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当这些角色在特定的条件下互不相容时,“角色混乱”就在所难免。换言之,当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承担多项角色时,角色之间与单一角色内部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抵触,从而妨碍个体正常地进行角色扮演(奚从清,2010:56-72)。具体而言,个体在同时承担多重角色的过程中,由于外界角色期望之间以及外界期望与自身价值体系之间的不一致、多种角色任务之间相互矛盾,往往导致特定个体因难以满足角色期望和适应角色行为而陷入内在冲突状态(丁水木,张绪山,1992:26)。在律师调解过程中,“代理人”与“调解员”的双重角色导致了地位、理念、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的内在冲突,从而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律师调解制度的绩效(赵毅宇,廖永安,2019)。在实践中,作为法律顾问的律师在村(居)社区扮演着法治宣传员、纠纷调解员、法律咨询员、案件代理人等多重角色,这些角色承载了国家、村(居)社区等不同场域中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角色期待”,必然导致“角色混乱”。期望主体的多样性导致的期望内容多元化,进而引发了村(居)法律顾问身份的角色冲突(期望之间的冲突)、角色妥协(满足所有期望的不可能性)和角色失范(缺乏明确的期望、未能回应期望)等“角色混乱”现象。最终,多重身份引致的“角色混乱”势必制约村(居)法律顾问的有效行动。因此,社会角色理论为解释作为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所面临的“角色混乱”提供了理论逻辑和研究视角。
三、案例描述:G市村(居)法律顾问的“角色混乱”
在司法部印发的文件中(1)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居) 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2018-06-25)[2022-01-09].http://www.moj.gov.cn/policyManager/policy_index.html?showMenu=false&showFileType=2&pkid=2ac14879334e4ac0acbe32a950ac8f39。,村(居)法律顾问的职责主要有三项:(1)为村(居)管理人员提供法律专业意见。包括为村(居)重大经济、民生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引导村(居)依法管理;协助起草、审核、修订村(居)自治组织章程、村规民约以及其他管理规定;协助村(居)解决换届选举中的法律问题。(2)为村(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包括为村(居)民解答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特别是在征地拆迁、土地权属、婚姻家庭、上学就医、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以及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村(居)民提供法律援助。(3)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协助处理信访案件。包括协助村(居)完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为调解员提供法律专业知识培训;协助村(居)组织处理信访案件,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反映诉求。据此,我们可以把作为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需要扮演的角色具体化为以下八个方面(见表1)。

表1 村(居)法律顾问的多重角色
通常情况下,行动者会受到其所扮演角色的影响,其失范、越轨行为与其表达角色和处理角色冲突的能力密切相关。当行动者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并且这些角色与身份的要求出现对立时,就会面临满足不同角色期待之间的“角色混乱”。而当“角色混乱”发生时,“行动者就可能会做出取舍、妥协,或是产生自我保护、自利行为”(王海军,简小鹰,2015)。由于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在一个村(居)内扮演的角色众多,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角色混乱”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基层法治化治理的目标偏移。具体而言,G市村(居)法律顾问的“角色混乱”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角色冲突
在G市,基层治理中大量存在着“官民”纠纷。然而,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作为地方政府向律师事务所购买、为村(居)社区提供的一种公共法律服务,形塑了一种准“雇佣关系”。尤其是由于市、县(市、区)承担了40%的费用,使得村(居)法律顾问在面对基层“官民”纠纷时地位尴尬。不仅如此,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纠纷,驻点律师一般也会“回避”。FY律师事务所的L律师认为:
“理论上我们是村民和村委这个共同体的法律顾问,所以一旦冲突发生在内部,必须回避,不能代理任何一方。举个例子,我负责的某村片区里,村委状告村民占地不还,村民表示此地是上一届领导班子租赁给他合法使用的,故村民和本届村委发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只好请负责其他片区的律师来代理这个案件。但是如果是本村与村外发生纠纷,我们就可以代理。如因中国移动占地搭建发射架与村委发生纠纷,我们就可以代理村委告移动。” (调研日记,20180615)
显然,作为村(居)法律顾问,律师一旦代理了村(居)组织,就很难同时为个别民众代言;同样,当镇(街)与村(居)集体、村(居)集体与村(居)民发生纠纷时,这些律师由于受雇于政府的特殊背景就会处于“两难”状态。于是,村(居)法律顾问既是调解中的“组织者”,也是为村(居)民提供服务的“服务员”,还是镇街事务的“咨询员”。多重角色面对的是不同对象。当不同对象的期望产生冲突时,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便陷入“角色冲突”的困境。而面对这种“角色冲突”,村(居)法律顾问普遍选择“回避”。
2.角色妥协
与因“角色冲突”引致村(居)法律顾问“回避”不同的是,在有些履职事件中,驻点律师会由于弥合不同期望难度之高而出现“角色妥协”。FY律师事务所的W律师认为:
“先问身份再谈事,如遇冲突见面说;释法、循法、不支招,重大隐患及时报。少说、多听、多赞同,论情、论理、少论法;律师自知非圣贤,但求自保疏怨气。具体在实践中,村(居)法律顾问面对电话来访咨询的咨询人及相对人身份,如果有利益冲突,则谢绝咨询。如果无利益冲突,才会进一步了解具体事项,居中答复法律相关规定及依法解决途径,不会提供应对策略。村(居)法律顾问面对现场来访咨询的咨询人也是如此。在了解咨询人及相对方身份后做好书面登记,如果有利益冲突,则告知冲突情况,谢绝咨询;如果咨询者坚持只咨询法律规定,则告知所涉及法律的大概情况;如果无利益冲突,则了解具体情况,居中答复法律相关规定及依法解决途径,不会轻易提供应对策略。” (调研日记,20180115)
FY律师事务所H律师也认为:
“基层矛盾错综复杂,各方利益盘根错节,历史问题迷雾难辨,很多事情地方政府解决不了,当地村(居)解决不了,律师就更解决不了。对于来访者,律师能充当一个倾听者、一个润滑剂、一个出气筒足矣!” (调研日记,20180723)
村(居)法律顾问作为村(居)共同体的服务者,面对基层治理的复杂性,由于弥合不同主体期望难度之高,便陷入了“角色妥协”困局,只能成为“倾听者”“润滑剂”“出气筒”,以致无法有效行动。
3.角色失范
在G市,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的“角色失范”主要表现为形式主义、行为草率、怕苦畏难、思想被动。形式主义是指驻点律师不是为村(居)民办实事进村,而是为完成服务次数、服务时间进村,使律师进村(居)沦为形式。最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村(居)法律顾问仅是走街串巷似的到村(居)服务处“喝茶”,茶过三巡即走人(调研日记,20190718)。行为草率是指村(居)民遇到一些因历史原因、时间长造成的土地、山林等纠纷时,一些驻点律师疏于掌握案件缘由而草率地提出意见,结果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导致矛盾激化。怕苦畏难是指一些驻村(居)律师因路途遥远、山路难行、驻村(居)服务时间长、影响律师正常工作等而打退堂鼓。思想被动则是指工作不主动联系、不主动解决,使一些本来可以及时化解的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在访谈中,FY律师事务所Z律师认为:
“每个村(居)都有大量乡规民约,无论成文与否、内容如何,都起着支撑村(居)运转的作用。比如,股份福利分红、户籍迁移、民主选举、资产管理处置、宅基地分配、外嫁女、外来媳妇、规划建设等等。切忌在未因此发生矛盾纠纷的情况下主动提出修改意见,也就是说不要没事找事。村(居)历史遗留问题和重大矛盾纠纷,大多积怨颇深,而且利益冲突较大,若非机缘巧合,断然不是律师所能解决的。但是,村(居)律师绝对有必要知悉相关信息,不然稍有不慎,轻则引火烧身,重则酿成大祸。村(居)民生活、经济发展以及民主选举等过程中,存在大量难以解释、难以避免、难以依法的客观需求和实践,如‘无证不动产处置’‘规划外房屋建设’‘寻求律师曲法协助’等,这些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本人无力提出系统性解决方式。但(凡)认为有必要提出警示:务必审慎,无论口头或是书面,都要首先阐明法律规定和后果,有限度介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自保为上,最好是借故‘闪’!”(调研日记,20180115)
于是,作为G市村(居)法律顾问的驻点律师们往往面临“角色失范”。首先,由于地理区隔,被聘任为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往往对G市独特的风土人情、邻里关系、宗族影响等社情民意缺乏深入了解,面对村(居)民纠纷难以介入。其次,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缺乏扎实的民意基础。虽然村(居)法律顾问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有公开,但是许多村(居)民要么不知悉,要么根本就不信任这些律师,主动联系村(居)法律顾问的不多。对此,许多秉持“不挑事”的驻点律师反而“乐在其中”。最后,村(居)与法律顾问间的关系存在热情接纳、礼貌接待、冷漠对待和激烈反对的差异。在热情接纳型和礼貌接待型的情况下,村(居)法律顾问尚有活动空间,而在冷漠对待型和激烈反对型中,村(居)法律顾问举步维艰,仅限于完成“文牍”工作。于是,G市的村(居)法律顾问不同程度地存在“角色失范”。一方面,仅仅为完成服务次数、服务时间而进村(居),对那些因历史原因、时间长造成的土地、山林等纠纷“退避三舍”;另一方面,个别驻点律师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主动挑起基层法律纠纷,小事化大、鼓动村(居)民通过诉讼维权,以此提高“成功调解案件的数目”。
显然,“角色冲突”与“角色妥协”使得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难以在基层纠纷调解中“主持正义”,而“角色失范”则使他们偏离了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预期目标。
四、村(居)法律顾问因何陷入“角色混乱”
(一)村(居)法律顾问制度逻辑的内在紧张性
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提供专业化法律服务,有效化解村(居)矛盾纠纷,确保基层安定和谐,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2014 年 1 月,司法部印发的《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将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17 年8 月,司法部印发的《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中首次明确了村(居)法律顾问的职责是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服务村(居)依法治理、为村(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开展宪法法律学习宣传工作。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指出,落实乡村法律顾问制度对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法治乡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检视上述政策规范,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主要有如下三项预期。第一,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通过村(居)法律顾问在基层的普法宣传、法律指导、法律援助、纠纷化解等,有效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引领作用。第二,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村(居)法律顾问坚持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排群众之忧、解群众之难为落脚点,针对当前基层矛盾纠纷多发的状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努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第三,提供公共法律服务。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全覆盖,是把公共法律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毋庸置疑,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有助于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但也始终弥漫着基层治理的“法治”与“治理”的内在逻辑紧张性。陈柏峰和董磊明(2010)认为基层司法存在“法治论”与“治理论”的二元逻辑结构,必须在法治化和治理化之间保持平衡。张青(2015)认为二者间实际体现出的是价值与事实的紧张与对立。具体而言,一方面,在价值层面上,法治秉持的公平正义与治理追求的切实有效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张力;另一方面,在事实层面上,法治强调的普遍化、规范化与治理所彰显的“地方性知识”和“本土资源”等也会“针锋相对”。
正是在基层治理法治化和基层法治治理化的交叠性目标制度环境下,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必须扮演组织者、服务员、宣传员等多重角色。而在多重制度目标存在内在紧张性时,村(居)法律顾问陷入“角色混乱”在所难免。
(二)“送法下乡”与“迎法下乡”之间有张力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视野中,“‘送法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其有效权力的边缘地带以司法方式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权力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苏力,2000:33)。在这个意义上,“送法下乡”凸显国家如何为“社会”订立规则并取得社会服从的过程(黄冬娅,2010)。基于法治逻辑,国家通过制定村(居)法律顾问制度“送法下乡”,是力图将法治作为一种秩序来整合基层社会。于是,在相关政策规范中,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承载了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规则之治”这一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诉求。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地方政府购买律师事务所的专业法律服务,将法治宣传融入纠纷化解、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过程中,普及日常生产和生活涉及的法律知识,增强民众和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改变传统基层治理模式,走出一条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中国道路。
而地方和基层社会基于自身社会秩序维持的需求,有“迎法下乡”的需求(董磊明等,2008),更多地将“法治”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特别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治理工具。因此,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强调将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视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要通过村(居)法律顾问客观、理性地化解矛盾纠纷。例如,G市司法局阶段性工作总结认为:由于积极引导村(居)法律顾问参与村务管理、乡村振兴、信访纠纷等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了法律顾问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的“调解作用”,所以切实保障了“矛盾化解在基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人员不上行”的氛围。于是,在G市基层运作中就出现了“层层加码”:要求驻点律师作为维稳干部“包案”,定时定量解决一些历史遗留疑难问题,被要求深入征地拆迁户家中去做思想工作,等等(调研日记,20190115)。
而在国家不断加大力度的“送法下乡”中,“法言法语”也在相当程度上走进了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持续的“送法下乡”使国家法律能够在乡村社会填补某些空白;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很多矛盾纠纷只能求助于政府和法律(杨华,2021:243)。于是,持续的“送法下乡”之花似乎已结出了“迎法下乡”之果。农民从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的规训对象和国家法律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其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度明显提高。但是,“迎法下乡”的实践并非意味着“送法下乡”目标的实现。法律在化解乡村民间纠纷时往往使其在司法场域中持续“发酵”,甚至异化为“斗气”“依法纷争”或“争斗”。显然,在乡土社会结构混乱和权威多元的场域,“迎法下乡”中的农民更多的是根据自身的经验、资源和逻辑对纠纷解决途径进行理性选择(郭星华,邢朝国,2010),折射的不单是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更多的是当下中国法律下乡后关系运作下的“利用法律”之内在逻辑(何绍辉,黄海,2011)。于是,“迎法下乡”使得法律离村民越来越近,但越来越多的村民在“依法纷争”(陆益龙,2019)。
显然,在“送法下乡”与“迎法下乡”之间存在张力,甚至分殊为“规则之治”与“裁决之治”。而在民众“迎法下乡”中,基层社会和谐的破坏、人际关系的恶化以及法律威信的下降也正在凸显。简言之,由于这种张力的存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可能不仅难以给村(居)社区人际关系改善、公平正义维护与基层秩序维持带来利好,反倒成了多元主体间利益竞逐的“跑马场”。
(三)驻点律师的有限理性使其在多重角色之间漂移
首先,律师服务的市场化与公益性之间存在紧张性。当前,全国各地在聘请村(居)法律顾问的经费安排上不尽相同,即使是在补贴较高的广东省,每月1万元补贴也远远低于活跃于市场的律师的平均酬劳。广东FY律师事务所W律师表示,“按照市司法局和市律协安排,我担任G市边远山区等八个村的法律顾问,其中从G市出发开小汽车到达最近距离的B村约4个小时,最远距离的C村需要5个半小时,每个月至少要花3.8天在村居中,任八个村的法律顾问,工作补贴只有8万元,减除油费、路费、食宿费和纳税等,剩下不足4万元,对于年营业额超过100万的律师来说,做这样的法律顾问工作是得不偿失的事。”(调研日记,20190225)律师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付出与收入不对等,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酬劳远低于市场化酬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律师怠于完成职责,“委托助手代劳”“委托其他律师一并完成任务”“只挂名不走访”等现象层出不穷。甚至有驻点律师为牟利而将村(居)内服务对象“引流”为自己的私人业务对象,违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初衷。
其次,驻点律师因“理性”而退却。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中,驻点律师既是宣传员和代理人,又是咨询员和调解员,多元角色承载着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诉求。而在参与基层纠纷化解中,驻点律师的“多元角色”使其游走于基层政府与民众、民众与村(居)组织、民众与民众之间,既是基层政府和村(居)组织的法律助手,也是民众诉讼代理人,更是基层政府与民众、村(居)组织与民众冲突的调解人。多重角色、基层政府的维稳诉求以及基层社会客观存在的“地方性知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使驻点律师的行动往往“举步维艰”。显然,在此情境下,驻点律师主动避免卷入基层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是一种理性选择。
最后,作为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角色能力有限。一方面,对于多数长期在城市执业的律师而言,村(居)法律服务涉及的土地流转、村规民约、宅基地与相邻权纠纷等是相对陌生的领域。因此,作为村(居)法律顾问,不仅要具备一般性法律专业知识,还要掌握一些纯粹的“地方性知识”。诚如广东FY律师事务所H律师所言,“在服务对象方面,专业社会律师遇到不熟悉或不是其专攻领域的案件可以转交其他律师或拒接,担任法律顾问时服务对象的类型更多样,碰到的案件更复杂且不可挑选。”(调研日记,20190525)不仅如此,G市既是广东典型的方言区,也是宗族、村规民约等“地方性知识”影响甚大的区域。这对于那些以普通话为主要沟通语言、游离于G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之外的驻点律师而言,履职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驻点律师困于诉讼思维与调解思维的平衡之中。在追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诉讼思维和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调解思维之间,驻点律师必须在“利益对抗”与“利益趋同”、“法律视角”与“多维视角”中寻找平衡(孔凡义,2020)。对于诸多精于诉讼而短于调解的驻点律师而言,出于执业惯性甚或节省时间精力,难免会消极对待调解服务,甚至倾向于将其导入诉讼程序。
显然,在既有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制度设计与村(居)法律顾问这一关键行动者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当既有制度规范和关键行动者被放置于一个其意义能被理解的世界时,合法化的制度程序就被生产出来了;另一方面,当行动者赋予的制度现实自身意义不明确时,合法化的制度秩序就会受到威胁(Berger &Luckmann,1967:121)。这说明,村(居)律师并不是既有制度规范的被动遵从者,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只有建立在行动者之间的共识之上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在“送法下乡”和“迎法下乡”的交互过程中,实践中的基层秩序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在不断完善理性化制度设计以不断夯实理性制度秩序基础的同时,制度规范也处在行动者的建构之中。因此,作为被制造和建构之客体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在赋予村(居)法律顾问特定角色并规范其行为的同时,也需要村(居)法律顾问的认同来使其存在合法化。简言之,脱离了村(居)驻点律师行动的理性化,秉持理性设计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是难以有效运转的。
五、结论和讨论
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抓手,是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决策与步骤之一,但在实践中却呈现出较大落差,与制度目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从作为行动者的村(居)法律顾问行动角度切入,笔者发现村(居)法律顾问难以行动的原因在于陷入了“角色混乱”的困境,体现在“角色冲突”“角色妥协”与“角色失范”三个层面。而其之所以陷入“角色混乱”困境,从根本上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村(居)法律顾问制度逻辑的内在紧张性使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必须扮演多重角色并面临多重角色之间的张力。其次,国家“送法下乡”与基层“迎法下乡”的张力使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可能成为多元主体诉求竞逐的对象。最后,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之有限理性使其在多重角色之间漂移。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律师,在市场化与公益性法律服务的冲突以及多元角色的内在冲突中,趋利避害是无可指责的理性选择。而复杂的“地方性知识”“权力的文化网络”“平衡诉讼与调解”等也使驻点律师在扮演多元角色中“举步维艰”。显然,建立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不仅在于完善制度设计的规范化并聚焦顶层设计在基层的具体落实,而且需要从行动者视角来重新审视相关制度建设。
那么,上述发现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应该深化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研究。众所周知,制度研究离不开行动者,脱离行动者会导致制度研究的空洞化和虚假化。不管制度相对于行动者而言有多庞大,总是一个人类制造、建构的客体。制度固然塑造了行动者的行动规则,但制度存在的正当性离不开行动者认同,行动者对制度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诚如吉登斯(1998:89)所言,“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显然,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存在互嵌(张军,王邦虎,2010)。因此,相对于既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制度设计而言,从作为村(居)法律顾问的驻点律师行动入手,深描其在村(居)场域中因承载多重角色而遭遇的“难以承受之重”,不仅有助于丰富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践性知识,而且有助于深化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研究的多重视角。
另一方面,开启了完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新思路。基于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在资源配置、服务规范和作用发挥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司法部明确了要加强人员配置、明确工作职责、规范服务行为、创新服务方式。与之相应,既有学术研究也提出了诸多完善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保障的思路。毋庸置疑,不断完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构建规范高效的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体系。但是,立足于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这一行动者视角,来观察其与制度之间的互嵌,发现制度设计不仅要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且要考虑制度实施所涉及对象的主观感受与认知,尤其要正视关键行动者在制度运行中客观上发挥着“重塑制度”的影响。只有既符合形式规范要求又能为行动者主观认同,能将制度理性与行动者理性兼容的制度才真正有生命力。因此,完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不仅要调适国家的治理法治化目标和地方与基层的法治化治理目标、精准回应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而且应该正视作为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这一关键行动者的行动。具体而言,完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不仅要从“送法下乡”“精细化”“精准化”入手,还应该立足于简化村(居)法律顾问的“角色”和增加村(居)民的法治获得感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