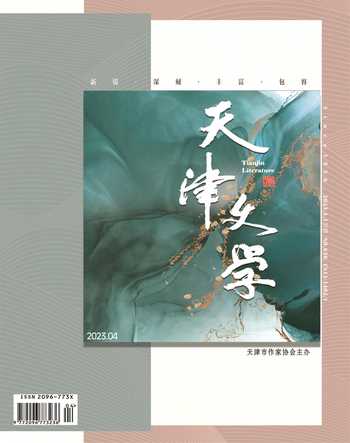草木笔记
荆棘王冠
放在大飘窗台的虎刺梅的花龄已经20年了。枝条溢出了盆子的边缘,像伸出长长臂爪的章鱼。喇叭状细碎小花从细密尖刺的茎顶萌放。“虎刺梅”是国人的叫法儿,或叫“铁海棠”,其根部长得缓慢,枝干随时间长得粗壮。
丁丁小朵的虎刺梅,稀稀疏疏,挤得阳光酡红。蚕豆大小的花朵,趋向窗子,长长的枝干,被玻璃顶弯,花蕊触镜,似要冲破阻挡,跟外面的阳光抱在一起。我看花枝顶得难受,便将盆子转了个方向,原先朝向窗子的长枝朝向了室内,刚好触到了室内第二道落地窗帘。那天,我忘记了调整过来的长枝是碰不得的。清晨拉开窗帘时,用力过猛,掠到了紧贴在窗布上的虎刺梅的长枝。
瞬间,右手小指扎入了几根细小的刺儿,麻辣辣地疼。赶紧找出缝衣小针,将毛刺一根一根剔除。小毛刺,尖锐、短小,容不得碰。我领到教训,“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当然,我被扎也是记性的退化——花盆旋了一个方向,花朵朝向了屋内,但也让更多的小刺子面向了我。原来没有贴近窗帘的,我不转动花盆,或者转动后,修剪一下支棱触碰到窗帘上的长臂茎枝,就不会被扎了。
这盆虎刺梅花是对门杜老师家的。她去海外,把钥匙给我,让我给花浇水。她家的几盆花,每周要浇一次,长势良好。后来她把一些花送了人,这盆虎刺梅没人要,她舍不得扔掉,就“寄养”在我家了。我不擅养花,此前书房养了文竹、君子兰、绿萝、龟背竹和滴水观音,不是水浇多了,就是忘了浇水,最后都没成活。可是现在,唯一活的,竟是这盆愈来愈盛的虎刺梅。按现在的长势看,已枝茎繁密,四处洋溢了,把一个近3平方米的大飘窗占了一半。有时候也拍张照片给杜老师发去看看。她说这花儿占了你的空间了,若不喜欢,就扔掉吧。我哪舍得呢,也喜欢这种细密的、常开不败的小花。即便花儿落了,也是整个儿与茎秆儿一起落。有时候打开窗子,干枯的花,被风吹拂着,落到了纹理曼妙的棕色的波洛格地板,异常好看。我将干花积攒,置放在一只白瓷碗里,时间久了,色泽仍然鲜润。有时候也懒得清理地板,就让这些色泽完好的干花儿留在地板上。
虎刺梅属于野生植物,登不了庭榭雅室。不像牡丹、玫瑰、芍药或郁金香,甚至不如蔷薇或鼠尾草,更遑论与可以塑形成景的杜鹃、水仙或兰花相媲美了。它或者算不上花,但是四季却常开不败,旧花去,新花来,一茬又一茬。不需要施花肥的土壤,只要有阳光和清风,就会开得汪洋恣肆。那些密密麻麻的小丁小朵,虽细小,但热烈。像珊瑚,细尖毛刺儿托起的,是小叶花骨。我想,牡丹与玫瑰,硕大好看,却应季而开,且花期短暂,几天便落。如遇风雨,更是不耐。
我的书桌邻窗,与虎刺梅近在咫尺。花儿如袖珍蝴蝶,阳光洒来,月光洒来,镀上了一层美妙色调。有时晚上我不拉窗帘,让幽白的月光,尽情地洒进来,品咂一种曼妙的情境。我看见,它们凌空飞跃,在不大的空间里,划出了一小截一小截的香气。我躺床上欣赏剪影。女儿也常用喷壶为花儿喷水,从花蔓尖部开始,浇到根部,像施洗一个古董瓷器那般的小心谨慎。水不用太多,一玻璃杯,半瓶矿泉水,足够让它维持一周。花儿需要清水、阳光和月光的泽溉。我懒散,从未施过花肥,更没有在虎刺梅的周围放置其它花儿,让他无所阻碍,枝茎随意伸展。
虎刺梅像一个天性淘气而又懂事的孩子,喧闹但不夸耀。我想起在云南某地看见农户的屋檐下有颈口朝外放的陶罐,乡亲说是驱邪纳福。我相信冥冥之中的神祇。虎刺梅的确太有生命活力了,不需精心照顾,任它在一隅,无拘无束地活着。
有一天,杜老师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一幅几乎贴地生长的虎刺梅。她在游逛当地植物园时,发现了一小片儿虎刺梅。虎刺梅在欧洲不叫“虎刺梅”,叫“荆棘王冠”(crown of thorns)或者叫“麒麟花”“花麒麟”。我惊诧这“荆棘王冠”名字如此之美,初闻觉得不太般配,叫“荆棘”倒是名副其实,后面加了一个“王冠”有些牵强了吧?又想,这个花名,前面是植物的属性,后缀一个形容词或者喻词,倒也没错。它长着长着,枝条就会打弯变圆,形同冠冕,舍它又会是谁?本来此草本植物是碰不得、动不得、摸不得的,天生威严,凌厉峭拔,可近之但不可欺之。
“荆棘王冠”这个名字有隐喻性。它向阳而开,给阳光加冕,为月光画影。
“只有一朵仍然活着,就是沾着戴荆棘冠冕的人所流出的血的那朵。”
“凡·高的自杀已成为艺术殉道之路上伟大的终章,这是他的荆棘之冠。”
我发现有许多关于“荆棘王冠”的诗,择录几个隐喻性强的句子嵌入此文。当然,我是诗人,也为它写了几句——
我看见了一位诗人
他戴着荆棘王冠
吹着芦笛
怀抱《天问》和《离骚》
以及一块沉重的石头
走在郢都坎坷陡峭的悬壁与奔腾汹涌的江河之间……
折耳根
鱼腥草,也叫折耳根,是西南山野草根,能当菜吃。
第一次吃“折耳根”,是2001年去云南怒江州六库镇。那年我与两位驴友行走怒江大峡谷,当晚住在六库镇。怒江军分区的战友招待我们,满桌子全是山里的、森林里的和江河里的特产:水煮怒江细鳞鱼、香葱拌杉树花、牛肝菌炒腊肉、鸡菌炒山猪肉、清煮芭蕉花蘸水、油炸竹虫、油炸薄荷、白参菇炒牛柳、带皮黑山羊火锅、凉拌折耳根等等,每种菜都是北方难以品尝到的美味。当中,有一种类似小甘蔗、小白藕或者青草的白根儿的菜,以糟辣子、米醋、豆豉和酱油当佐料,看上去诱人,一入口,差点儿吐了——浓重的鱼腥味儿,将舌尖儿搅得腥膻酥麻。
啥菜呢,被砧板的生鱼片染味儿了?
战友哈哈大笑,向我示范,夹一小根,“嘎嘣嘎嘣”嚼得脆响。这可是地道的鱼腥草,也叫折耳根,中草药,解毒清火,健胃利湿,增力增气。不吃这个不算来滇西。战友告诉我,吃折耳根,第一次吃,肯定有鱼腥味儿。吃得多了,你就离不开了。我夹了一根细嚼,果然嚼出了清甜。后来我们沿怒江大峡谷行走一路,片马、福贡、洛本卓、贡山、丙中洛等地,每天的餐桌都有这个菜:折耳根炒腊肉、折耳根拌猪皮冻、折耳根拌腐竹、折耳根拌豆豉、折耳根拌粉丝等等,但都少不了以碎辣子调味儿。后来知道折耳根跟小米红辣子或者糟辣子是绝配,辣椒碎碎,能调动其鲜脆的原味儿。有时候店家也将折耳根切成细碎的沫儿做汤料,把面条和米线,与芫荽、韭菜或者薄荷一起,放入汤汁里,那种鲜味儿,简直美极了。
折耳根属于老百姓的民间菜,上不了大酒店的筵宴。当然,若想吃地道的折耳根,就只能到贵州和云南。
一个飘洒小雨的日子。我和一位同学到黔东南千户苗寨,夜宿苗族老李客栈。老李爱人给我们做了三个菜:清炒豌豆尖、水煮腊肉和酸木瓜煮土鸡(酸木瓜是我从大理带来的)。我们吃酸木瓜煮土鸡,喝着米酒,却觉得缺了什么。
又来了一位上海女孩和一位老外,我们便邀请他们一同吃。外面的雨还在下,无法出门买菜,这时候老李家已无菜可做了。忽见厨房里放了一大堆还带着湿泥土的折耳根。我对老李说:把这个凉拌了。老李说,刚才想做这个菜,可又担心你们大城市人吃不惯啊。我说,不但能吃,还离不开呢!老李爱人赶忙将折耳根择净用水冲洗,白亮白亮的,放于砧板,切成小段,佐以香醋、小葱和糟辣子,淋上麻油,端了上来。我和同学大口大口嚼得香。上海女孩看我们吃得起劲儿,也夹了一根放入口中,一嚼,“哇”的一声跳起来奔出屋外,狠劲儿往外吐。老外也试探夹了一小根,皱了皱眉头不知何物。我对他们说,不吃这个,能算来贵州?从祖上开始,贵州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的,不吃药,嚼嚼草木,喝一杯山泉水,上下轻松,身心舒爽。这山中哪,不只是折耳根,更有许多山野食材。对于养尊处优的城市小资来说,对这山野草木,肯定不感兴趣。上海女孩还未从刚才品尝的不适中解脱出来,大声说,不可吃,不可吃!我说,山野食材,天地所赐,哪有不可吃的道理?与同伴几口便将一盘折耳根一扫而光,又叫老李拌了一盘。吓得那上海女孩和老外直瞪着我们这两个“什么都敢吃”的家伙,掩鼻,皱眉。
折耳根是一种生长湿地或溪边的草本植物。《本草纲目》《本经逢原》《滇南本草》以及《中国药典》都有对折耳根的药理记述。亦是西南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卑微草根,胜过鱼肉。在苗寨转悠时,看见苗家人从溪边采来了一大车折耳根在河边洗摘,带着小小竹节儿的、小甘蔗似的乳白根茎的植物用河水一漂一洗,发出小藕般的光泽,根根肥嫩。我对同学说我要带些回北京。同学说这种东西,就是现拔现吃新鲜,搁两三天,恐无味也!
云南和贵州的许多小餐馆还用它来佐食吊味儿,就连早餐桌上还摆着一小碟任大家随便吃呢。在云南和贵州,折耳根廉价、多产,一块钱一大堆,人人爱吃。若哪位云南人或贵州人不吃这个,定会被当地人嗤笑“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我每次到滇和黔都要吃折耳根,糟辣子清拌也好,腊肉火腿同炒也好,都是下酒的好菜。有时候,还可以往米线里加一点儿,既能调味儿,又能去油除腻。
折耳根当然是刚刚挖出来的最好。那次我到黔东南黎平县肇兴镇新平寨子,那天的午餐有凉拌折耳根,是一位老师从下雨的山地里现挖出来的,小小的根还带着泥土。洗干净了切成了段,再拌上辣子。同伴只吃了一根就吐掉。我旁若无人地大嚼,让当地人诧异,他们问我,也能吃这个?我告诉他,我吃折耳根已有十多年历史了,每回来云贵边地都点这个菜。有次我在贵州的一位朋友家吃饭,满桌子的菜,独缺折耳根。我跟主人要这个菜,主人说,这菜哪能上桌?但还是给我上了盘野葱拌折耳根。贵州朋友听了我这些年吃折耳根的经历,站起来,为我倒满了一杯酒说,来我们西南边地的兄弟,能吃折耳根,能数得上折耳根好处的,绝对是亲兄弟!来,干了这杯!
不敢相信的是,这些年,京城超市也出现了折耳根。塑料小盒二两重,标价五六块。但总是感觉运输过来的食材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度了。但我还是忍不住买了一盒。家人无法容忍我吃这种草根,责怪我不该将这种东西端上餐桌。我就把这盒折耳根用清水浸泡,然后洗干净,沥干水分,切段装盘,洒入一点儿盐,淋上一点儿味汁,拿到书房,边看书边嚼。有时开一罐生啤,与喝茶吃水果,有同样的感觉。
银 杏
银杏是北方落叶乔木。国家图书馆西门老馆院子右侧、距紫竹院公园隔水之地,有两株大银杏树,据说这里是700多年前的元朝,于忽必烈皇后建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的镇国寺遗址。今寺不存,唯这两棵古银杏树被保存了下来。两株枝虬根劲的大银杏树,如同两位修炼高深的佛陀,披着时间的征袍,一路趺跏,一路祷祝,为汗牛充栋的国家图书馆,增添了悠远而雅致的韵味儿。
当年的白石桥至中关村路段,于20世纪90年代将其南北一趟的白杨树掘根锯伐,换栽了银杏树。银杏树发芽出叶早,初春时节,当阳光愈来愈足时,银杏叶子便随阳光萌发于枝。柔嫩,鹅黄,一小撮、一小撮,从大小枝桠萌生出来,就连粗壮的主干皱褶缝间,也会吐出一朵两朵芊柔细嫩的小扇叶子。
无盛夏浓重深绿,有融金般鹅嫩绒黄。此时银杏树最美。我有时候从魏公村走到国图,一路数着树,每株相隔5米,在我看来,在喧闹的街道已是很密集了。春天,树叶摇动无数小扇;夏秋,阳光照耀,鱼游波浪,鸟跃云霓。树在阳光照映下变幻着不同色泽。每次去紫竹院都是心情大好,或因这一趟赏心悦目的银杏树吧。
银杏是银杏科银杏属的统称,是中生代侏罗纪的“活化石”,分布北半球,白垩纪的晚期开始衰退。第四纪冰川降临后,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绝大部分地区灭绝。野生状态的银杏残存于浙江西部山区,北方也广为栽植。
从春草初萌,到夏树盈绿,再到秋霜染草斑斓似金,白石桥路,银杏树是最大的看点。清风中的树枝摇曳着无数个小扇子,随秋入深,色泽加重,直至有一天成了金黄或橙黄,叶子开始凋落,变得稀疏,银杏果儿便显露出来。在银杏树下行走,银杏儿在天空飘着摇着。突然从树上“啪啪”掉下两枚银杏果儿,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两枚果儿先后落在脚下。绵软的囊皮里,露出了圆粒白果儿,小心剥开,然后用纸巾擦掉果核上黏糊糊、臭烘烘的软皮,用路边草地的洒水管冲洗,这两枚玲珑可爱的白果核儿,像刚刚出水的小白贝壳卧在掌心。
“一切法性皆虚妄见,如梦如焰。”
掌心的纹络似时光之水涌动,漫过了岁月的堤坝。乳黄色的果子,那般的小巧、玲珑,外皮儿清薄,让人不忍捏揉,触碰或碎裂。壳儿光滑,核有硬感。里面包裹着的,是一座完美的圣殿。有血肉、骨骼和灵魂。小小的籽粒儿,以敬神的姿态拥有它所有的功能。银杏果儿以圆实蚕豆儿的姿态,卧在了我的掌心,像一对双胞胎婴儿。那里面的生命,也仿佛急着挣脱出壳。我听见薄薄的壳里有雷电的鼓鸣、净露的琴韵、清霜的笛声。圣殿与果壳,内心与灵魂,想象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那满结树上的,到底有多少座小小的圣殿?
深秋十月,坐在紫竹院银杏林子里,所见到的则是另一种生命体验。那天风很大,吹得银杏叶蝴蝶般飞舞,银杏树下,小果儿“噼啪噼啪”,雨点儿落,声音短促。或是植物种子生命的本能——柔弱绵软,坚韧强劲。软与硬,柔与坚,只在于它的体外,大部分的能量和品质却储于体内。它必须有一个软软的皮肤包裹果实。这是造化的设计,不会损坏里面的果核。我拾起几个,没有一个将里面的果壳儿摔裂的,是外面的果皮皱成了绵绵软软的保护层。如同从天外飞回的卫星,落了地,然后弹跳了几下。将皮皱弄破,里面构造设施,却是完好无损。自然神灵的设计。
银杏果儿大多都是成熟即落,它们绝不滞留枝桠。有一年,我在中南海墙外厚厚黄黄银杏叶子里捡起许多银杏果儿。回家捏破表皮,用水洗出一大盆儿白白的果实。摊开,晾干,非常好看。多年前央视农业频道约我为盛产银杏的泰兴写过歌词,从资料摭拾几种:金坠子、七星果、大龙眼、大梅核、玉佛指、海洋皇、大马铃、大圆铃……。我不知道白石桥路的银杏树是何品种?据说,银杏树都是一雌一雄对生的。若是一棵死去,另一棵也不会活长久。怪不得我所见的白石桥北边魏公村银杏树都是雄雌隔生,有果儿和没有果儿的那种排列。
银杏树慷慨大方,每到成熟时节就会毫无保留地把籽实奉献。夏天时,果儿依枝桠而生,树下的人难以看清,颜色与叶子一样。深秋不同,待叶子落光,果儿却还在枝头挂着,虽然摇摇欲落,但果实一定要等到大部分的叶子落了后才会跌落。
银杏果仁可食,入药有润肺止咳、强壮身体之功效。酒店饭馆也有“银杏西芹百合”这道黄绿白素菜,须用新鲜的银杏果仁儿来搭配西芹和百合,清甜爽口,软柔香糯,深得吃惯了大鱼大肉的食客们的喜爱,它还有一个好听的菜名:炒素什锦。也有烤食的银杏仁儿的,比如德川家、和坐、黑松白鹿等日式料理,小碟白果,寥寥几枚,剥去烤煳的外壳,搓掉裹在果肉上的棕泽薄皮儿,露出了金黄灿灿的柔嫩果肉,有点栗子或红薯的味道。虽然银杏也叫长寿果儿,但每餐不宜多食。
科学家从银杏叶中提取银杏汁和银杏精,可治疗人的脑部或身体的血液循环障碍,疏理血管,通畅血脉。我多年前有过一段头疼,曾服过一段银杏叶胶囊,感觉周身上下,血脉畅通、舒泰,精神旺盛。据说还有银杏养生酒,我没喝过。
野 草
有小撮儿的蕨草生于山石。细看,岩石裂缝有一点儿泥土,萌出毛茸茸的细小蕨草。蕨草也叫“起死回生草”。山谷燠热,岩石灼烫,草虽枯黄,却未死亡,只需点滴雨水或者清露,即刻鲜活起来。若将之拔除,曝晒多日,只要有根,就会复活。山石或坑穴的缝隙,清风吹入带有蕨草种子的泥土,即刻萌绿。我从一个石缝间连根带土抠出一丛小蕨,赤峰朋友给了我一个小塑料袋,将之小心包裹,放入背包,准备带回京城,置阳台养殖。后来几天住酒店,又时不时取出,用矿泉水滋其根、润其叶,怕它枯死。其实不必担心这一小撮的起死回生草,就是放十天半月,只要有一点点水润一润,就不会死亡。
阿尔福雷德·丁尼生说:“当你从头到尾弄懂了一朵小花,你就读懂了上帝和人。”维克多·雨果说:“所有的植物都是一盏灯,而香味,就是它的光。”野花仙草,都是智者。它们选择山野生存,离开人间烟火气。与自然共生的草木,本身就带着山野的仙灵气儿。若想读遍百花、阅遍百草,就得到蒙古的山和草原去走走。
山路开始较宽,再往上走,植被增多了,逐渐变窄,最后竟变成了一根羊肠小道,隐进了密实的灌木丛里了。尽管双脚能够插入,但心有余悸。我穿短裤,脚踝被细小草茎和荆条灌木枝蔓刮掠发痒,山路崎岖,草木茂盛,可有蛇蝎?
山坡的山花还是赏心悦目的。它们高举小灯,将山坡照亮。小绣线菊、多裂翅果菊、委陵草、虎榛、青蒿、紫菀、羊胡子草、碱草、苔草、野石竹、紫苜蓿、蓝盆、酸塔、莎草、防风、曼陀罗、香附子、石竹、紫苜蓿、唐松草等等,春天的山谷,万木萌芽,野花盛开,阳光下闪烁着清透光泽。小时候的我到山里采挖野菜和山草药类,蒲公英、马齿苋、荠菜、苣荬菜、大头蒜、旋覆花、车前子、紫地丁、大小蓟等等都认识。现在,仍有大多的野草叫不出名字。后来友人送我一部《识花图鉴》,了解了一些北方山地的花草。
有的野草可当野菜上餐桌。小时候,要赶在清明时节前后,到山上挖野菜。清明前,阳气上升,雨水清纯,生出野菜,有清火祛疾之效。小孩食之,可保一年不生病、不发毒疮。野菜虽苦,生出的小花,却甜嫩无比。家乡人有吃清明前野菜的习惯。将野菜茎叶、花蕾,连同根须洗净,做成美味菜汤或包野菜肉馅儿饺子、包子或馄饨。清明前第一顿饺子,味道鲜美。此时节蔬菜还未出畦,野菜却已漫山遍野了,特别是荠菜猪肉馅儿饺子,我上学时是美味午餐,至今想起,仍清香满口。
野草野菜,开着漂亮小花。这些遍布向阳山坡的小花,清风吹拂,发出金黄、浅红、粉白、浅紫、靛蓝的光泽,煞是好看。梭罗说:“既然我们身边的植物发出如此的芳香,那么谁又会对自然的年轻和健美表示怀疑呢?”
我小时候家的院子栅栏边常见野生的牵牛花,我常把牵牛花与打碗花、田旋花混淆。这三种,其实都属于茎蔓科匍匐植物,都有喇叭形状的花瓣,因此又统称“喇叭花”。与野菜开的野花不同,牵牛花、打碗花和田旋花,只能观赏,不能食之。初萌时,是纺锤状的花,然后慢慢打开瓣儿。小时候喜欢将“纺缍”揪下,花与柄与蕊脱离,拿在手里的是“纺缍”花瓣,然后用嘴吹其底部细小的断裂口,看花儿被气儿吹得“噗”的一声,打开了连接一起的环形的喇叭瓣儿。
三种花,十分相像,但也容易辨别——
田旋花,叶子呈尖形,花边圆满,花瓣浅粉,花蕊浅紫。
牵牛花,叶子互生,花边相连处呈圆状,花瓣纯紫,花蕊纯白。
打碗花,与田旋花相似,花蕊一是乳白,一是紫黑。
牵牛的花期最长,从5月至11月,都有花开。特别是肃杀之秋,当百花凋谢,牵牛依然在有阳光的荒地旋转着,盛开着。
自然界植物从不会迟到。野草每到开春,就比赛似的开花。先是萌生嫩叶,然后从嫩叶中抽出长长茎条儿,结出小小花蕾,当第一粒露珠落上花蕾,花便开了,香气便释放了出来。山坡、河岸与还未播种的田野,都可见到摇动的小身子。一时间,阳光把所有的色彩和醇香全给挖出来了。小野花儿多是生在湿度和温度相宜的向阳土地,长势葱郁,煞是好看。每年准时萌芽开花结籽儿,就像定准了时钟似的。这些野花杂草,都是一流的旅行家、植物界的浪子。它们的足迹遍布山河。它们被水牵着、被风携着,游走千里,最后被一座汀渚或洲岛挽留,驻下来,扎下了根,然后开花、结实。
也有如香附子和蔓草,只恋溪流、滩涂,到这两种地方,再也不肯离开。当我看见一株生在浅溪里摇来摆去的芊草,就觉得它们很坚强。通常,一些鸟儿诸如捉鱼高手的小翠鸟,喜欢在有水的岸堤筑巢垒窝,随时猎取水里的小鱼、小蝌蚪或小蛙类。更多时候,花草籽儿随清风飞翔,像蒲公英的种子包裹小绒球里,漂泊数百里,越过群山大江。山岗、河岸、田野、路边、岩缝,都可看到它们举着嫩黄的小花儿。我在滇西北高黎贡山和怒江峡谷常看到好多野兰花生在粗实的古杉树或柏树的枝杈处且衍生旺盛,它们根须杂多叶子硕大,随风飘曳,如须髯飘飘的世外仙人。
人类给到处生长的野草一个不雅的名字——杂草。
事实上任何植物生来肯定都是有用的,杂草也是有用途的。爱默生说:“所谓的杂草,不过是那些其优点尚未被我们发现的植物。我们认识自然实在太少太少,许多不为所知的本态,是我们不知的。在这方面,动物却要比我们人类更有直觉和先验,它们对许多杂草的潜在功用早已十分熟悉。”花开季节,蜜蜂从巢里飞出来,进入花丛。蜜蜂是大自然最出色的花卉鉴赏家和品酒师。阳光下这些淘气的孩子,总是趴在花蕊深穴,吃着花粉,喝着蜜汁,浑身沾满花粉,最后总要把自己喝得东倒西歪,醉醺醺的。
但我仍有许多不认识的草木。在野外即便它们以开花的姿态向我打招呼,我也认不出来,只能凑近,闻闻香气,就像我回到故乡或在哪里见到了故乡人一样,打了招呼,却忘了人家的名字。于是就想,如果我是一株野草就好了,我能与它们相处,结识许多花草植物。它们生于山中,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类的医师。
比如羊胡子花,根清凉解毒、凉血止痢;水杨梅,有除湿止痛镇痉之效;萝草果,可治劳伤,根可治跌打、蛇咬;防风,可治五劳七伤、肚子痛和盗汗;覆盆子或叫牛叠肚,果实酸甜,样子好似草莓,却要比草莓好吃多了,我小时常采食它,补肝肾、祛风湿;马齿苋,最常见的野草,也叫五行草、长命草,开米粒儿大的小黄花,遍布田野滩涂、山坡河汊、路边旮旯,常食之,清热解毒、治菌痢。
每年春天,母亲都要采来许多蒲公英,晾干,冬天煮水喝或腌渍当菜。
黄牛和山羊是绝好的中草药鉴定师,它们吃草时,会躲过夹杂其中的有毒花草,只要以它们灵敏的嗅觉闻闻就解决了。牛在春天喜食山葱,能防病防瘟。还有一些是蜜蜂不闻、牛羊不吃的花草,到了秋天和冬天,其种子却成了鸟儿喜欢的食物。
野花和杂草是坚强、卑微的植物。即使人类再疯狂侵占土地,也不能完全让它们消失。它们有着天生的生命本能,人为的铲除,是不能将它们消除殆尽的。
有时候我常常对城市小区里草坪栽种的清一色绿草充满了怜悯,它们在规定的地方生长,按时修剪,清理,完全丧失掉了自由自在的天地。其实,城市的草也是从野草进化而来的,只是它们是“挑出来”的一种,经过人工培植,成为供人享用的“标配”绿地。事实上,一枚史前三叶草化石证明,大地上的野草早于人类而生,从远古,一路不歇地绵延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时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来又一片。举着香味的草木照亮了民间。
核桃叶子
院子里的老核桃树发芽了,老枝老皮疤瘤处,也绽出了点点嫩叶芽儿,再萌开鹅黄软嫩的叶子,然后,再展开。进入仲夏,就变成宽大厚重的叶片了。核桃叶子的香气,总是在最柔嫩的时候香味儿最浓,也最容易被嗅到。或许,柔嫩的叶子,还不能锁住香气,就像花儿刚刚开放时,香气最浓郁一样,时间久了,香芬却减弱了许多。这是春天的大地带来的生命气息。
人人爱吃核桃,但少有人会对核桃叶子感兴趣。
核桃叶子,羽状。生于上端者较大。成形时候,有小孩儿手掌那么大。生于下端叶柄处的较小,兼生小叶,长约寸许的小叶柄。
核桃叶子,轻飘飘的。初春嫩叶,呈现的是浅绿,薄软。到了夏天,叶子变得厚重,老绿,甚至墨绿。有的叶子,长得会像巴掌那样大。
我喜欢春天的核桃叶子,它们拥挤着,风吹着,在阳光下翻涌着。掩映其间的核桃花蕊与萼密生,雌花三两朵聚生,花柱像细碎的金子。一些鸟鸣,在树叶间穿梭,小巧的脚趾把风踩弯。鸟儿们,或飞在绽开叶子的核桃树里,或用树叶的香气,将全身梳洗。但我并没有看到蜜蜂来采集花蕊酿蜜。
走在核桃树下,立即进入了一种沁凉,如果是下了雨,叶片上闪烁着湿湿的水光,像缀满可追忆的故事。花蕊隐入了时间深处,不急切,不懈怠,只开不起眼儿的细碎小花,并安然藏于宽大的叶子下面。如果细心观察,只有下雨的时候,才会于树下,发现一些如同黄金细碎的、轻屑般的小花瓣儿。
有一次,我无意撩开挡在眼前的核桃叶子,谁知碰到鼻子上——就那么轻轻地一碰,竟然有一股薄荷的清香味道,像某个年轻漂亮的美人从我面前经过,那洒了香水的衣衫,清香直冲过来。
醒脑的味道!我站住,到垂下枝叶的树枝面前,摘下了一枚叶子,被折断的叶柄处,有香气溢出。手指轻捻叶子,一小点儿嫩绿,沾在了手指上,味息浓烈,像风油精,又不完全像,像薄荷油,要比薄荷味儿淡些。但的确像南方火锅吃的那种薄荷,我很爱吃薄荷,它与蔬菜不同,可除腥膻,或解油腻,或可以当作调味料。
我有些惊异,是不是自己太过于敏感?我几乎每天,都要从核桃树下路过,竟没有发现核桃叶子还有这般好闻的薄荷味道,而身边的树木花草,我也浅薄得连它们的名儿都不知道。
农科院的小植物园,有许多树种,比如:元宝槭、三角枫、杜仲、七叶桫椤、紫槐、大树桑椹、梧桐、花皮松、西府海棠等等。当然我不认识的树,或许更多。核桃树是北京的常见树种,却少有人觉察到它的叶子有一种薄荷的味道,叶子只有被摘下来,或者触碰到了它,才会发出这种气味。如同认识了多年的心仪的人,却不知道她还有着更令人感动的自然之美质。
枝叶的香味是草木的精神,更是草木的灵魂。
走在核桃树下,听小鸟以一溜儿轻小脚趾,在嫩绿间踩踏出了一条条小路。核桃树盈绿了,大好时节,充满期待。而只要一伸手,就可触摸到明亮的阳光之下那些悬垂的叶子,然后轻轻地一捻,满手心薄荷香味儿。或者,摘下一枚,在手里拿着,生怕折坏了叶脉。柔嫩的叶子倒是不怕折,相对老些的叶子,却能听见折裂声。回到家里,将叶子夹在书中当书签。时间久了,偶尔翻到了这册书时,那两页与叶子就会散发出提神醒脑的香气,会让我蓦然想起某年某个时节,我曾从一株核桃树下走过的情境。
如此每回,都有意无意,与一株核桃树建立了细微的联系。那么,当我看到了叶子干枯,则会想到生命铅华,几多洗尽,几多蹉跎,几多殒逝。唏嘘、慨叹。
有一次几位友人晚上来我的书房喝茶。送客时,我们经过核桃树下,我让其中一位女士捻捻那核桃树叶儿。她惊讶道:真真不知道耶,想不到,核桃树叶子,还有薄荷味道。那味道,醒脑提神,像风油精、清凉油。
藏在时间指缝里的幽香,总是不经意地闪现在生命里。
酿酒用的葡萄里有很高的单宁。据说,核桃鲜叶榨取汁里富含的单宁,是葡萄酒含量的几倍之多。现代技术从核桃叶子里提取了单宁,可用于做传统的蚊香,或可用来制作工业原料。研究发现,核桃叶子中的干物质所含蛋白高达70%以上。核桃叶子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可治疗伤口、皮肤病以及肠胃疾病等等。平常我们只在意它甜脆香酥的果仁儿,有谁在意似乎无一用处的核桃叶子呢?
但当核桃果儿成熟时,日趋枯萎的叶子,其香气便渐渐地淡了。
那些浓郁的香气跑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去处,或者敛进了果壳里,还是被时间的风雨洗净淘尽?从而让那些香气淡远了、稀散了,只能等到来年春天再从树下走过,让我再闻到呢?
闻香识佳人?
可是我没那么浪漫。我只有闻香识树、识花、识草了。
站在核桃树下,我与那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叶子是惺惺相惜的。像是与一位久别的老友见面交谈。核桃树那粗粝的腰身,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熙熙攘攘的叶子,却如同年轻人的肌肤,始终焕发着活力。
乌那罕,满族,中国作协会员,在《人民文学》《十月》《诗刊》《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等。
责任编辑:杨荣